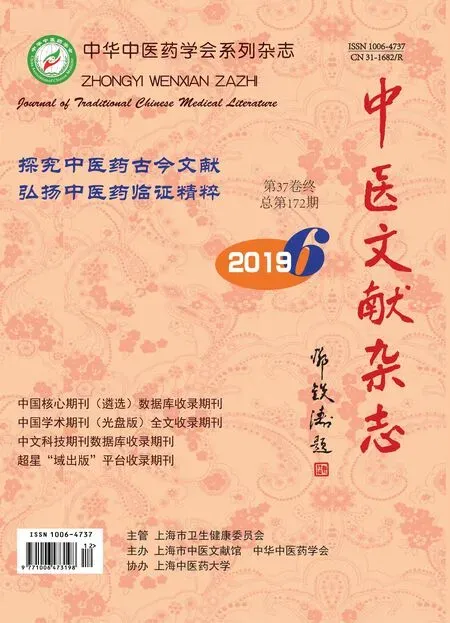中医文献学家*
——谢仲墨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北京,100700)
葛 政 王咪咪 解博文△
谢仲墨(1912—1971年),中医文献学家,著有《国药之历史观与改进论》、《中国历代医学伪书考》、《中医病名之研究》、《温病论衡》等。这些著作直到今天,在学术上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仲墨先生是中国中医科学院1955年建院时应召入京的第一批中医专家,为缅怀前辈,也为我们所不断继承、发扬的中医事业,特写此文以表纪念。
因谢仲墨的主要研究方向在于中医文献,故不被很多人所知晓。今天的中医工作者大多已不知道谢仲墨在中医文献领域所做的研究工作及成就。我们从新中国成立前众多的中医期刊中收集到了近百篇先生的学术论文、笔记、书稿,得以认真审视谢先生的生平、志向、为人,及尚能留于世的学术成就。谢先生勤于笔耕,除留下了学术著作、医学论文,还有大量的读书笔记,字里行间中记述了自己求学的艰难,生活的奔波,对中医事业的热爱与追求,及做事一丝不拘的风格……以这些为依据,略向大家描述一位中医文献大师的从医经历、生平志向、治学方法和学术成果。
简要生平
我院的医史人物传里有简单的谢仲墨相关材料介绍。
谢仲墨,字诵穆(其撰文著述时多用其字),生于1912年,卒于1971年,浙江萧山人。小时候和当时许多人一样,读私塾,念古文或时文。后来随父亲迁居安徽怀宁、广德等地,在学习古文的同时,开始自学中医。谢先生为人勤谨努力,年纪轻轻就打下了非常扎实的文字功底,写得一手好文章,这也是他后来发展的重要根基。
1930年,为衣食计,他投考了章次公、陆渊雷创办的上海国医学院。他对中医的热爱和刻苦用功,很快获得老师们的赏识。毕业后章次公先生推荐他到世界红十字会上海分会医院任职。谢仲墨书富五车、又写得一手好文章,在学医、行医的同时,开始用他的笔随时总结自己的临床经验。从谢先生进入中医界伊始,他的医学文章就频频见诸学术刊物。最初的文章多为临证与医疗经验的介绍。不过他对疾病史的关注和研究已经从此时起步,那时的谢仲墨才不过十八九岁,是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学子而已。
1932年,谢仲墨的老师陆渊雷举办中医“遥从部”(即函授部),创刊杂志《中医新生命》。陆氏诸事繁忙,打理不过来,于是在1933年,聘请谢仲墨来帮助编辑《中医新生命》杂志,并协助举办中医函授。谢先生一下子变得异常繁忙。
谢仲墨年轻有为、才气横溢,但为人却非常谦卑,一心只想做一个好医生。所以他的文章虽然在很多学术观点上师从陆渊雷,但行文风格却迥然不同于陆氏,他的文章敦厚谦逊,多以谈学术为主。
1933—1937年,是谢先生一生最为勤苦,也是最为辉煌的几年。他一生正式发表的论文多在这几年。从这些文著中,已经可以看出他治学与专攻的取向。在临床诊治研究方面,他下功夫最多的是温病。其治学方法最擅长的是文献考据,在考据中医病名、本草文献、伪书考证等方面多有建树。谢先生深厚的文史学功底,使之在中国医史文献研究、中医书籍刊订等方面游刃有余。约于1935年,谢先生编印了《金匮补充讲义》,今仅存石印本残卷。1936年,谢先生将其在《中医新生命》上发表的温病考证连载文章,结集修订为《温病论衡》一书,由上海知行医学社出版铅印本,这是谢先生存世不多的正式出版物之一。
1937年,日寇侵华,战火已经蔓延到了上海。谢仲墨结束了在上海操办《中医新生命》及函授的工作,返回老家浙江,在杭州浙江中医专门学校担任教授,在这段时间内,他还协助裘吉生先生编辑《珍本医书集成》的医书提要。直到抗战胜利以后的1947年,谢先生的零星文章才在《华西医药杂志》、《医史杂志》上发表,其内容仍是旧日所做的医学伪书考,并没有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1955年,卫生部所属中医研究院成立,谢先生在这一年的7月,由浙江调至中医研究院,成为首批应召入京的中医专家,在院学术秘书处编审室,从事中医文献整理研究工作。后来辗转与医史研究室合并而为医史文献研究室,此即1982年成立的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的前身。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先生当年对中医文献的几个研究项目,以油印本的形式进行内部交流。谢先生的《历代医书丛考》2卷,是其毕生力作。该书考证了古代医学伪书近百种,其中谢先生对诸多医学伪书的价值表达了他自己的见解。该书浸透了谢先生考证文献的心血,内有许多考证文献的方法很值得后人参考。
学术成就
总结谢仲墨的主要学术成就,可以有以下诸项。
1.阐明中医文献研究之方法,改革中医从研究中医病名始
早在民国间三十年代初始,谢仲墨就不只提出“中医往何处去”,而且身体力行为中医的继承与发展开始了对中医病名之研究。谢先生认为:“西法诊断中之名词意义,往往与国医旧说不合。生理之大脑,乃国医旧说之心与心包;生理之运动神经,乃国医旧说之所谓肝;此其最显者,其他名实乖异极多,近人颇有论譔,仍多附会错误,若不一一疏证明白,则科学终不得连用于国医学也。至国医常用之学术语,如阳盛阳虚,阴亏阴盛,痞硬动悸,心肾不交,热入血室,以及瘀血湿邪、痰饮肝气之等,自科学头脑者视之,莫不突兀难晓。然国医学之特长,往往在此等处,若不用科学原理详释之,则国医终不得世界学者之信仰也,此皆须编纂专书者也。”[1]要摆脱当时中医在社会上生存的困境,首先要让西医认识和理解中医,中医要进一步发展,在社会争得自己的一席之地,也要接受新思想和新事物,首先要做的就是统一中医病名,这一工作至今都还有人在做,可想而知这是很多中医人多年来的一种共识。为赢得更多人的理解和参与,谢先生向大家介绍:“愚所科学之方法,指切实之方法,凡切实之方法,皆得归纳于科学之范围以内。治医学之方法,与治病之方法,其范围不同,质言之,治医学之方法,即研究‘治病名论、治病方法’之方法。犹逻辑为科学中之科学,研究科学之方法,有一定之原则,即所谓逻辑。研究医学,亦有种种切实方法,与逻辑相默契之方法,作为工具,犹开矿之有器械,此即愚所举之科学方法,此即愚所举之治学方法,综言之,则曰科学的研究医学之方法。愚所举之方法,略分两种:一曰考据之方法。一曰统计之方法。考据之方法,略带演绎性;统计之方法,纯为归纳性。”[1]对中医文献研究的这一考据的方法,时至今日仍在使用。对于让西医同道看懂中医,理解中医,对于中医病名研究这一课题至今也仍在探研,努力沟通。
当时谢先生对众多繁杂的中医病名形成做了归纳,认为可以归纳为七类:(1)以解剖部位命名的,如胃脘痛;(2)以病因命名的,如中暑;(3)以病理命名的,如痰饮;(4)以证候命名的,如咳嗽;(5)以时令命名的,如春温;(6)以地域命名的,如广疮(即杨梅疮,首先从广东传入);(7)以迷信命名的,如鬼击。
中医一种病名中可包括西医若干种病,亦有若干中医病名包括在一种西医病种中。中医以一个证候为一病名,如头痛,而西医的多种病中都可以有头痛症状(如脑炎、感冒等都会有头痛的症状)。而中医的咳嗽,在西医又可分为感冒咳嗽、百日咳、肺结核咳嗽等。西医之丹毒即中医之大头瘟、赤游丹火等。中医以发在头部为大头瘟,在胫者为流火,在身者为赤游丹。随着时代变迁,中医病名所表达的含义也有所变化。如古之“疝”的病名,为“腹痛、小腹痛”之称,而今天多只指“小肠急痛”。另如“痰饮”,又称“淡饮”,古时指“水流肠间”,为消化器病。而后呼吸器一部分症状亦归于痰饮之内。今人所谓痰,亦是《金匮》所指“浊唾”。再以“疹”为例:浙江曰“瘄子”,以其忌用醋,恐酸敛不发也;江西曰“麻子”,以其粒如麻子也;吴人曰痧子,以其碎如泥也;四川曰麸子,以其如麦之麸壳在皮肤也;湖南曰瘙子,以其如蚤咬之迹也。总名疹子,其形证治法皆同也。又有两地虽说之病名相同,而所指之疾病却不同者,譬如吴鞠通在甲地著书,称“发颐”为“温毒”,乙地则仍以温毒为温病之重症,是甲乙两地病名虽同,而所指之病则异,这有地理的原因,也有随着时代变化,认识也随之改变的意思。谢先生在中医病名的研究中尤注意了对传染病病名的研究统一。如对丹毒,首先定义为一种连锁状球菌,并称据近代细菌学家研究,丹毒连锁状球菌实无异于化脓性连锁状球菌,所差异者,彼则常于皮肤淋巴道内繁殖,而此则多在组织实质内发见耳。中医所谓丹毒,其名至隋唐以后而始著,所函之病,亦非纯为丹毒也。并引诸书以证实:《素问·至真要大论》云:“少阳司天,则丹疹外发,及为丹熛”,熛飞火也;《史记》云:“熛至风起”;刘河间谓之大头;李东垣谓之大头天行;喻嘉言、沈金鳌谓之大头瘟;陈时功《外科正宗》谓之时毒,名虽不同,实皆头部之丹毒也。在西医,则强调是某细菌所感染。从此一病名之考证,谢仲墨以从古至今的文史书、中医书来印证一个病名的起始、发展、流传和病证表现,从西医的病理和中医的病理来说明疾病的本质,一丝不拘地诠释,切实地为发展和光大中医作着最大的努力。这些八十年前的考证方法,八十年前的总结和结论,对今天我们研究中医病名仍然有着重要的引领和启迪作用。他依这样的思路,对100余种疾病病名做了考证。非常可惜的是,先生这部重要的《中医病名研究》未能正式出版。
2.中医文献研究及伪书考
1935年,谢先生首次以《中医伪书考》为名,开启了他考证中医伪书的研究。他在该文之前,先条理了中国伪书考证的历史,其中提到:“明初宋濂著《诸子辨》,晚明胡麟著《四书辨伪》,辨伪之学始专。清·姚立方际恒,著有《尚书通论》,辨伪古文;有《礼经通论》,辨《周礼》与《礼记》之一部分;有《诗经通论》,辨毛序。其专为辨伪作者,有《古今伪书考》,列书九十一部,虽体例凌杂,篇帙简单,要亦绝有价值之作也。”[2]谢仲墨是中医文献的有心人,正因其通晓文史杂书,在上了国医学院之后,更勤奋读书。良好的读书习惯使得谢先生更重视对中医古书的比较研究,而他也坚信一本好的医书会对读者有更大的帮助,故而从年轻时起,就开始进入对中医古书的辨伪考证领域。这里面既有谢仲墨重要的学术成果,充分显示了其深厚的文献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也是先生对中医文献考证方面的一项重要贡献。谢先生认为:“无论做哪门学问,总须以别伪求真为基本工作。因为所凭籍的资料,若属虚伪,则研究出来的结果,当然也随而虚伪,研究的工作,便算白费。所以辨伪书为整理旧学里头很重要的一件事。”[3]这一重要性即使今日也并非中医人都能认识到。谢先生不只是认识到这一点,而且以为继承并发展中医,首先就要从这些最基础的方面入手。辨别伪书,需要多方面的知识,不只要有广泛的阅读量,而且要具备历史、文字等多方面的修养,且对伪书也不是一棒子打死,而是分析其做伪动机,内容之真假,许多卓见对今天的读者是很有意义的。谢仲墨说:“余喜读中国医书,寝馈有年。医书之外,亦喜考据,于辨伪之业,略涉藩篱,恒思以辨伪之方法,衡鉴旧有医书。以为中国医学,有相当之价值,如采矿之山,煮盐之海,蕴藏至富,取汲无穷,但历世既久,伪造之医书滋多,往往真伪两书之理解,……故辨明古代医书之真伪,足以甄汰陋劣之伪书,廓清学者之头脑,发古人之虚妄,解后学之大惑,诚为切要之图,固不仅考正医学进化之历程,求医学史上记载之真实而已。频年涉猎,发见伪医书不少,考索所得,条次成册,凡三卷,辨医书百四十余种,厘为本草、方剂、诊法、伤寒、杂病、女科、医经、医史、医论等二十二类,颜曰‘中国历代医学伪书考’。“《难经》虽然是伪作,然而一书之价值,并不因真伪而决定,真的不一定好,伪的不一定坏,书的本身如果有价值,那么就是伪也没有关系,书的本身如果没有价值,就是真也不足以增高其地位,所以《难经》的价值,是要以他自己的内容来估定的。”[3]
从谢仲墨文章的字里行间不但能看到作者一丝不拘的做学问的态度,而且将满腔改革中医的愿望化作踏踏实实的行动,以独特的眼光评价真伪医书的价值,努力为中医古籍的辨伪工作开辟一条新路。谢先生说:“本书所列医书,有书不伪,后人误疑其伪者,如孙思邈之《千金翼方》是也。有书虽出于伪托,而其言不可废者,如依附褚澄之《褚氏遗书》是也。有书既出于伪托,而其说亦不足取者,如依附叶天士之《医效秘传》是也。良窳不齐,当分别观之矣。”[4]对古书的考证不只有内容的辨伪,也包括对年代的考证。如对中医经典《神农本草经》、《内经》成书年代的考证,通过书中内容引证成书年代,都是需要大量文献功底的。可以想见,谢先生非家学出身,又年纪轻轻,竟然阅读了如此多的中医书,再看旁搜博引的大量文史、文字、文学古书,以此来研究考证中医古书,不能不令人敬重。
谢仲墨先生文献考订最显功力的文著,即为“中医伪书考证”。而中医伪书确为不少,“如叶天士之书,多为伪托。读者不察,遽信为叶氏手泽,以为叶氏之主张当如是,则流毒难尽矣。因仿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之例,辑为本篇。然医书之价值,往往与真伪无关。若以为伪者必一无足观,遽废弃不读,则非作者之初意也。”[2]
在谢先生列举的伪书中,有《神农本草经》、《内经》等经典名著,也有清代的《叶天士遗书》等。对叶天士的著作,谢先生在引述诸家评论之后指出:“盖叶天士书除《指南》、《存真》、《温热论》、《幼科要略》外,其余皆后人伪造也。”[5]
1935年谢仲墨就已经提到:“鄙人所搜集之伪医书达三百种,拟多集参考材料,再行执笔。”[6]可见当时的《中医伪书考》不过是小试锋芒而已。据谢氏《中国历代医学伪书考》1937年11月写就的自序,可知其时谢氏已经完成了《中国历代医学伪书考》一书。该书分为三卷,辨医书140余种,分为本草、方剂、诊法、伤寒、杂病、女科、医经、医史、医论等22类。但因时局动荡,此书的自序和例言一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才发表于《医史杂志》。其全文在建国后有油印本,内部交流,从未正式出版。
3.温病研究
谢仲墨对温病的研究始于1930年,其时他发表了论文《瘟疫研究》(连载)。他之所以用“瘟疫”为文名,也经过一番考证,他认为:“所谓瘟疫,是有传染性的疾病。直捷的说,就是传染病。”之所以不用“温”字,是因为用温字容易引起误解。1930年,谢先生才只有18岁,但他的研究思路,却绝对是一条正道。谢先生学医虽非家学,进入上海国医学院之后,又以文献考证为自己所长,但其在临床上也颇为认真,随时都会把临床上的体会著于文字,和同行讨论。除在期刊上多发一些文献类的相关文章外,也有关于“腹诊”、“痞病”、“传染病”的临床文章,足以显示谢先生在中医临床上也是个有心人。尤其是对于温病,谢先生将自己的临床体会与大量温病、瘟疫文献相结合,写下了近十万字的《温病论衡》一书。
在这之前谢先生还曾发表过《瘟疫研究》一文,谢先生设立了“释名”一项,举凡与传染病相关的名称都在其考证之列。当时谢先生已经把“瘟疫史”作为其《瘟疫研究》的篇目,并从历代正史中搜集了部分瘟疫流行史料。谢先生《瘟疫研究》一文中的内容,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虽然还不十分成熟,但他设计的研究框架,却已经像模像样。到1935年,经过数年的锻炼,谢先生完成了《温病论衡》,该书的考据结果已令人对他的学识刮目相看。
在《温病论衡》中,谢先生将清代著名温病大家的重要观点逐一评述,其中有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章虚谷、王孟英、陈祖恭、柳宝诒、戴天章、陆九芝等。谢先生分别研究他们的温热观,采用的研究法则是他极力倡导的考据法。谢先生引吴鞠通的温病观,列温病之大纲凡九。曰:风温、温热、温疫、温毒、暑温、湿温、秋燥、冬温、温疟、暑温。
引章虚谷的温病观:章氏曰,夫经论伏邪为病,四时皆有,惟温病则有内伏而发外者,有外感虚风贼邪,随时气而成温病者,其由内而伏发外者,又有虚实两证,如经所云,“冬伤于寒,春必温病,是冬寒伏于少阴,郁而化热,乘春阳上升而外发者为实证”[7]。
王孟英的温病观:“士雄所著,有《温热经纬》四卷,经纬者,以《内经》、仲景之文为经,以叶、薛诸家之说为纬也,……故仲圣著论,亦以伤寒统之。而条分中风、伤寒、温病、湿、暍五者之证治。与《内经》、《难经》渊源一辙,法虽未尽,名也备焉。”[7]
在研究温病学说之变迁之后,谢先生得出的结论是:“其最可注意者为王安道、叶天士、陆九芝三人。温病学说之剧变,王安道启其端。温病名实之淆乱,叶天士为祸首(虽不止天士一人,而天士之过最大)。处叶、吴学说积威之下,作大举之驳击,则陆九芝殿其后。”[7]等等。
谢先生对温病的整理,侧重在温病病名的名实考订。他不仅考订了湿温、风温、温毒、温疟、冬温等病名的异同,也进而考订了伏气、外感两种温病病因的发展源流。谢先生在温病的论述中同样是用的考证的方法,捋清病名,讨论实质,归纳现实温病病名名实之歧异。
湿温——章太炎先生曰:夏秋之交,有病寒热往来如疟,胸中满闷者,久久不治。或致小肠蓄血,始作时,时师辄谓之湿温。
风温——取仲景、叔和之风温,与天士、平伯之风温,较而论之,则此数者之证治,大相悬异。仲景之言风温曰: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若发汗已,身灼热者,名曰风温。风温为病,脉阴阳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语言难出……陈平伯云:风温为病,春月与冬季居多,或不恶风,必身热咳嗽烦渴,此风温证之提纲也。
温毒——伤寒例曰:阳脉洪数,阴脉实大,更遇温热,变为温毒。温毒为病最重也。吴鞠通曰:温毒咽痛喉肿,耳前耳后肿,颊肿面正赤,或喉不痛,但外肿甚则耳聋,俗名大头瘟、蝦蟆瘟者。
温疟——《金匮要略》曰:温疟者,其脉如平身无寒但热,骨节疼烦时呕,白虎加桂枝汤主之。渊雷夫子云:疟论,以先热后寒者,为温疟,但热不寒者,为瘅疟。《金匮》则瘅疟似无别。
冬温——《小品》之冬温,若以后世言伏气者观之,可假称之为伏气冬温。吴坤安之冬温,殆所谓新感冬温矣。又案:如第一条之湿温,病名相同而证状不同,是谓名同而实异。如第五条之《小品》冬温,与《活人书》之温毒,病名虽异,而证状则大致相同,是谓名异而实同,亦不可以辨。[8]
谢仲墨坚持:“如上所陈,则伤寒与温病,温病与时行,时行与伤寒,循环校验,皆无明确之界限也。主张伤寒与温病有区别者之学说,清以前论伤寒、温病之区别者,综合之约有四点,为病因说、病理说、证状说、治疗说。”[8]
最后的意见是:“三者之所包罗,既不止一病,则所包之病,得无有相同者,或伤寒与温病同,温病与时行同,时行与伤寒同,苟有所同,则三者查异之藩蓠,即有崩决之倾向,而以温病与伤寒对抗者,将自显其悠谬。以时行与伤寒为绝相同者,亦将自呈其败缺也。丁福保氏以肠窒扶斯为伤寒,其师渊雷以湿温为肠窒扶斯,章师次公以肠窒扶斯为湿温,其所编之医案讲义中有曰:湿温症……,按之西医藉,亦甚吻合,已故西医钱崇润之言曰:伤寒病人之心脏,易为伤寒杆菌所侵害,故易于心脏衰弱。”[8]
谢先生认为,“湿温”症状表明,该病就是西医的“肠窒扶斯”(肠伤寒),有人将此病归于温病,有人却归于伤寒。于是导致“伤寒、湿温、肠窒扶斯者,一病而三名也”。类似这样的考订,在《温病论衡》中比比皆是。若非专门研究温病、伤寒者,未必能有耐心去细读此文。现代的温病研究者们读过谢仲墨此文者恐怕不多,因此该文集的出版,可以为当今研究伤寒、温病之类的疾病提供参考。
4.国药之历史与药物文献研究
《国药之历史观与改进论》是先生于1934—1937年发表在《神州国医学报》的一篇连载的文题。这篇文章连载了34期,发表时间持续三四年,洋洋近10万字,是谢先生发表论文中篇幅最长的,若结集出版,实际上就是一本小书。近年对本草颇有建树和研究的郑金生教授在看过此文后曾下结论,此文可以说是我国近代史最早的系统本草历史探讨。
谢仲墨为什么要撰写国药历史?用谢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时势之所急须”。在民国初期,某些西医一边指责“国医之学理荒诞”,但一边又承认“国药之功效确实”。这种废医存药的论调为谢先生所不齿。谢先生认为:“吾中国之药学,有广漠无涯之历史。吾中国之药学,经千万亿人之实验。发挥之,光大之,吾侪之责。”正是出于发扬光大的责任,谢先生写下了这篇中国药学史的长文。在此文之初,谢先生就指出:“史学之志切求真,亦正与其它科学之精神无异。”也就是说,他把为中国药学撰史作为科学整理的一个方面。其目的在于:“拟以史学之方法,作一鸟瞰式之观察,以研究药学发达变迁之沿革。于古来药学界之文献,就所知者,网罗排比,参稽互察,冀能予以新意义,予以新价值,以求其会通因仍之道,以求其盛衰张弛之故。”[9]
关于“药物之起源”,自古以“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的观点最为盛行,也最为权威。针对此说,谢先生详尽地罗列了古代关于神农尝药的各种历史记载,以及清末以来诸家对此说的考订,指出神农尝百草的神话传说,原本是说明先民寻求食物的过程,并非为发明医药而尝草。神农是一个神话人物,单凭一人尝百草而发明医药是不可信。何况药物也不限于只有可尝味的植物。神农时代文字还没有造出来,自然不会有《本草经》之类的书。
谢先生认为,“一种事物的发现,决不是从天空里掉下来的”。既然中国的药物学不是神农尝出来的,那它总会有个源头。谢先生把药物的起源,还是归结为找寻食料的过程,并把这过程分为迷惘、怀疑、认识、应用、研究。从无意识地寻求食物,到意外发现药性,引起怀疑注意,并有意识地进行试验和应用,最后加以研究,并用文字记录下来。因此药物学是“牺牲了不少先民的生命,经过了千百次的试验,结合了无数无名药物学家的心血成功的”。其起源时代可以推溯到有史以前,早于神农时代。
谢先生探讨药学史的视野非常广阔。他在80多年前就能注意到宗教与药学的关系,尤其是早期中国医药与巫觋之间的某些渊源纠葛,充分认识到中医药的发展是受到巫觋、宗教各方面的影响。“自是以来,巫废而医孤行,故就其初而言,则巫与医,皆圣人为之者也。极其末流,则巫堕而医贵,始合而终离也。……回族至今人人犹尊奉可兰宝典,以医为业者,亦皆教民。印度之佛教,自玄奘游学而后,外道盛行,佛教反见衰微,故回教与医学,今犹杂糅不分。佛教则以自身之衰落,而无形与医学脱离矣。”[10]文中除引用了《说文》、《太平御览》、《玉海》、《山海经》外,还旁引了日本僧侣及印度耆婆、基督教、回教等对中医的影响。
这些认识难能可贵。谢先生的史学视野受当时西洋、日本学者的影响比较大,因此他治史并不拘于中国传统的旧史学套路。
此外,谢先生也注意将中国药学发展与西洋古代药学发展相比较。例如其中谈到“药物学上之表征说、形象说”时,谢先生就引用了《英文医学辞典》。
在史料方面,谢先生与其他民国时期前辈学者一样,善于从文史资料中发掘药物史料,对先秦时代药物史料发掘更是细致入微。今人研究古代药物史,多得益于前辈学者发掘之功。例如关于“本草”二字的来历,早在民国间已经比较清楚,至今没有发现更新的史料。《神农本草经》被视为中国本草的源头,对此书的研究向来为本草学者所重视。谢仲墨也不例外,他广采博集有关的研究成果,加上自己的研究心得,对神农之名字沿革及托名神农之书、《神农食禁》是否即《神农本草》、《博物志》所引之《神农经》等《神农本草经》佚文、《神农本草经》之辑本以及该书成书年代、内容与体例等,均有比较详细的论述。
谢先生在该文穿插了许多新颖的主题,对后世学者有很多启示。例如该文设计了“道家与药学”、“佛教与药学”、“外来药物之输入”、“医与药之分途”、“理学与药学之关系”等主题,都非常有意思,这可能与当时的社会氛围与发展有关,很值得后人继续拓展研究。
该文在后世本草文献的研究方面虽显得粗浅,具体表现在对多数本草著作的介绍不过是罗列序言和梗概,并没有触及其特色及学术源流,但总体已经勾画出了整个中国药学史的主要脉络,其中尤其是对药学发展早期的历史探讨更为深入。从学术研究角度来看,谢先生所撰国药历史,综述多于研究,但他在此文中涉及的药物学史诸多主题,至今没有一部药物学史著作能对这些主题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从这一角度来看,谢先生在中国药学史领域的研究功不可没。
除以上诸项研究成果外,谢先生还曾相继发表过数篇中医文献的考证文章。由于其平时读书非常认真,常有旁人所未查之收获。如谢先生的《医家座右铭》一文,介绍了古今许多医学名家的言论心得,发人深省。该文分为学医、医范、修养、临症四类,摘取前人的一些警句名言,其中有些言谈看似琐屑,实则为医家最为实在的心得体会。如。
裴执中云:“医者常须爱养自家精力。精力不足则倦,倦生厌,厌生躁,厌躁相乘,则审脉辨证处方,皆苟率而无精意矣。思欲救死全生,庸可期乎?今之医者,鲜不以奔竞为专务,徒劳苦而不自知,大戒也!”又云:“医之误人有六:有学无识一也,有识无胆二也,知常不知变三也,意有他属四也,心烦冗沓时五也,偶值精神疲倦六也。”(《言医选评》)
陆以恬云:“作事宜从容详慎,为医尤甚。不特审病为然,即立方亦不可欲速,以致贻误。杭州某医治热病,用犀角七分,误书七钱;某医治暑症用六一散,又用滑石,大为病家所诟病——此皆由疏忽致咎也”。(《冷庐医话》)[11]
谢先生的《读书随笔》在期刊中也曾连载多期,其内容为在读书之余的笔记。谢先生读书面非常广泛,举凡经史子集,凡与医学相关的内容,都曾涉猎。因此这些笔记囊括的内容十分广泛,有书籍、人物、故事、新闻、方剂、药物、治疗经验、医学趣闻等,很受读者欢迎。即便是今日来读这些笔记,依然令人兴趣盎然。由此也可知谢先生读书之广,用功之勤,足可为后学之楷模。
(谢先生早年的研究项目虽个别有过出版或油印以内部参考,终因量少、年代远久,已不为广大中医同道所知晓。借此次收集谢先生的新中国成立前期刊所发文章之际,我们会将谢先生早期研究项目的期刊连载(包括“读书随笔”)辑录陆续发表,多则十余万字,少则数万字,以备广大读者参阅,纪念这位早逝的中医文献学家。)
(本文参考了《谢仲墨医学论文集》中郑金生教授所撰“生平”一文,特此感谢!)
——兼与《论流行性感冒与伤寒、温病的关系》一文作者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