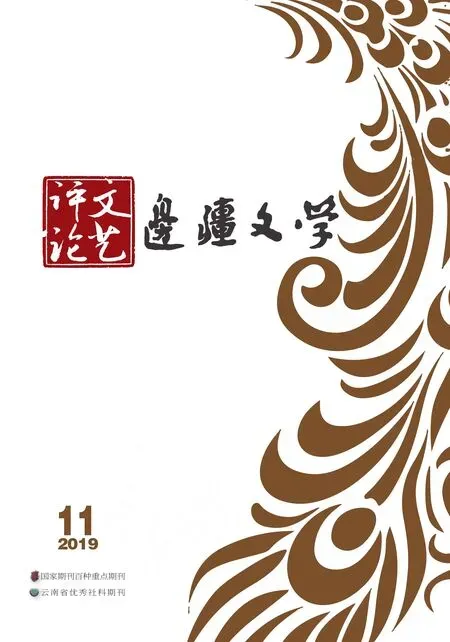用挑剔的眼光读小说
周荣新
近期,因为创作长篇小说的缘故,读了李佩甫《羊的门》,张炜《爱约堡秘史》《九月寓言》(重读),梁斌《红旗谱》,王蒙《活动变人形》等几部长篇,牢记前辈先贤的教导,带着“挑剔的眼光读小说”,在学习众家之长,学习他们结构小说、塑造人物、编织情节、凝练语言的同时,也多少看出了大大小小的毛病或说缺陷,尤其是关仁山的新作《大地长歌》和维克多·雨果的经典名著《巴黎圣母院》,分别存在着“叙事的纰漏”“多余的炫耀”问题。
叙事的纰漏
关仁山先生的《大地长歌》(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12月第一版),以1978年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为起点,表现了河北一个叫“响马河村”的农民及县、乡干部,在党的领导下承包土地、释放生产力,彻底解决了温饱问题后,发展乡镇企业、现代企业等走上致富道路的40年宏伟蓝图,塑造了支书周东旺、高贺,村主任谷香,乡党委书记马童力、县委书记云秀,村民金元宝、谷大贵、周秋山、红霞及依附伯父高贺、好吃懒做又专干坏事的“高粱杆”高彼得等人物群像。作家是想通过一个乡镇、一个农业县40年天翻地覆的变化,讴歌我们伟大的党,我们伟大的时代和勤俭创业、积极进取的伟大人民,主题是鲜明的,表现手法也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读这样近50万字的长篇大作,是一种鼓舞与激励,是一种教诲与鞭策,更是一种面对历史的史诗长歌,为此,读者是认可的,也是深受感染的。可能,由于写作赶时间要在“改革开放40年”的2018年出版吧,更或许是对这段40年的历史缺乏深入研究、深入生活不够等缘故吧,反映在行文中,读者发现第十九章出现了叙事纰漏,问题还很严重!
从时间线索上说,第十八章第54节第一段有一句话是明显的时间节点提示,即“可是,夏天的‘非典’,让编制厂的运转一下子停顿了下来。全民抗击‘非典’,众志成城。”也就是说,本节的故事,事件发生在2002年。一个小节的叙述后,时间一下子跳到了第十九章第55节的第一句话:“十一月八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这一天,响马河村一片欢腾。”也就是说,故事表现的时间,一下子跳跃了11年,跨到了2013年——这样叙述,按照本小说一直“顺叙”的思路本无不可,可问题是,到了第二十三章第67节的时间提示,“谁也没有时间跑得快,一眨眼,一年一度秋风劲,一出溜,十年八载成为过眼云烟。滦河波涛拍打堤坝间,不知不觉已经是二〇〇六年的秋天了”;而到了再之后的第二十五章第73节开头的时间提示,“时光在响马河水的流淌中,悄悄流逝着。转眼到了2011年。”这就是说,整部小说的叙事,都是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的,第十九章明显出现时间叙事纰漏,不仅表现在前后矛盾,更主要的是,内在逻辑发生了错误。具体表现在:
1.“代理村主任”错误。
第十九章55节有“彼得‘啪’地拍了下桌子,惹不起被吓了一跳,说道:‘有话说话,拍啥桌子啊?生怕谁忘了你是代理村主任是吧?’”众所周知,中国村民自治法规定,过去的村委会主任每三年选举一次,可以连选连任,结合前面十八章54节的故事,“非典”发生在2002年,之前,村支书高贺的亲侄子高粱杆已经是“代理村主任”了,怎么11年后的2013年,他还在“代理”呢?三年一选,至少也选举过三届了吧?“代理”二字早该去掉了吧?但作者没有拿掉“代理”二字,说明作者既对村民选举缺乏必要认识,也缺少对文本叙事的认知,到了59节第一句“村干部换届选举工作即将开始了”,和第60节第一句话“元宝听说了东旺当支书,谷香当主任的事。”也从这“选举”和第二十三章67节标志2006年到来,“响马河村的人们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新老交替,老支书高贺卸任、进城颐养天年,周东旺“他今年五十三岁了,做村支书,团结带领乡亲们种水稻、编制手工艺品、参股旅游度假村,富了集体,也富了村民,村民年收入在全县数一数二”等故事情节发展来看,十九章之后不是“倒叙”,脉络都是沿着时间先后发生、发展的。可见,一个“代理村主任”的细节及其时间节点的混乱,造成了多大谬误,几乎把整部小说都破坏了,至少产生了对作者的信任危机,对整部小说的信任危机!
2.关于老支书高贺年龄疑问
。高贺的侄子高彼得(因娶了一个俄罗斯媳妇而改名,原名“高粱杆”),一直无恶不作,皆因有权倾乡村的二叔(实际是二伯父)高贺罩着、庇护着,高彼得“代理村主任”时的十九章,2013年了,高贺还在任支书,应该多大年纪了?早就超过七十岁了吧,怎么还任职?一路读来,隐隐判断出高贺早过了“古来稀”之年,该退休了。读到后面反映2011年的第二十五章,作者说高贺已经85岁——这又说明什么?说明,第十九章行文的2013年,跟“代理村主任”一样,是个大错误,也证明,该章以后不是“倒叙”,十九章的叙事逻辑严重错误了。3.关于对手机惊奇的落后变现。
第56节第二段有句话:“(高)彼得得意地晃了脑袋,掏出新买的手机给二叔打电话说,你们先吃吧,别等我。红霞惊奇地看着那个手机,说:‘这个玩意儿没有电线,也可以传话?真是神了!’”——老天,再是落后的农村,2013年党的十八大都胜利召开了,竟然没有见过手机?当年笔者回乡当村主任,村里最不济的人家,至少也是一部老年手机在手了。说明什么,说明“时间”和社会生活严重脱节,所表现的改革开放的时间节点是错误的。作者想表现的,实际应该是“非典”的2002年至2006年间的社会人生。如何才能消除以上错误?笔者认为,只要去掉十九章55节的第一、第二两段明晰表明“2013年十八大召开”、“庆祝”的有关内容即可,还原成2002-2006的社会人生。第三段的“春节过后企事业单位上班的第二天,马童力调到县委当副书记了,原县委书记云秀调进清泉市当副市长去了,乡党委副书记叶光明任党委书记……”不是既表示时间在“非典”后延续,也表示人物任职变化了,故事向前推进了吗?
多余的炫耀
小说很忌讳风景、景物单章独篇的孤立描述,像维克多·雨果大师《巴黎圣母院》的第三卷这般长达27页的写作。
一是它阻断了故事情节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凝滞,破坏了小说的节奏;二是吃力不讨好,读者并不买你的账,你成了“炫耀式”的写作,最终破坏了阅读的兴致。
最巧妙的做法应该是,在情节发展中,适度地、精致地插入景物、风景的描写,而且最好是以人物的眼光(视点)或是心灵观望,风景、景物吻合或反衬人物情感思想,既是对特定环境的展现、塑造,也是对社会人生的渲染,成为小说有机的组成部分。同时,又恰当地减缓了故事的快速推进,造成必不可少的“隔”,也增添了、扩展了小说表现的时代风貌、社会人生,更增添了小说的趣味、层次,扩大了文化的涵盖面。
古今中外,尤其是现代的小说,像雨果这样独辟一卷,静态地、孤立地描写圣母院及巴黎全城(鸟瞰)的长篇小说,是绝无仅有的。虽然文笔优美、饱含抒情的文字准确生动,对巴黎当时的状况把握极为全面形象,读来增长地理学、历史学、建筑学等专业知识,但说实话,没有几个人能耐着性子读完吧?要是我等默默无闻者也这般写,编辑能不全给删了?相反,现代很多小说不写风景、景物,显然又走向了另一个不好的极端,小说除了故事情节,就什么也没有了。最好学曹雪芹,通过人物的经历、活动、命运,带出风景、景物来,风景、景物又深化、展示、推进了人物性格、命运和结局。即古人说的“一切景语皆情语”是也。
例如《巴黎圣母院》第九卷之一的《昏热》一节关于副主教、神甫堂·克洛德在看到单相思、波西米亚流浪歌舞女艺人拉·爱思梅拉达“走上绞刑架”,以为真的死了,回到圣母院后的传神描写:
“他慢慢地爬上钟楼的楼梯,心中充满了一种不可告人的恐怖,害怕巴尔维广场上稀少的行人看见神秘的灯光在这样夜深时刻从钟楼高处一个个枪眼里射出去。
“忽然他感到有一阵清风吹到他的脸上,发现自己已经爬到了最高的楼廊口。空气寒冷,天空里云彩斑斓,大片的白云层层重叠,云角破碎,像冬天河里的冰块解冻时一般。一弯新月嵌在云层当中,就像一只船在天上被空中的冰块环绕着。
“他从一排连接两座钟塔廊柱的铁栏当中向远处俯瞰,透过一片烟雾,看见了成堆静悄悄的巴黎的屋顶,尖尖的,数不清的,又挤又小,好像夏夜里平静的海面上的波澜。
“月亮投下微弱的光,使天空和地上都是一片灰色。
“这时教堂的大钟响起了嘶哑微弱的声音,是半夜了。神甫想起了中午,也是同样的十二下钟声。‘啊’,他低声地自言自语:‘她现在一定已经僵冷了!’
“忽然一阵风把他的灯吹灭了,差不多就在那同一刹那,他看见钟塔对面的角落里出现了一个人影,一身白衣服,一个人体,一个女人。他战栗起来。那女人身边有一只牡羊,跟着最后几声钟声咩咩地叫着。
“他鼓起勇气看去,那的确是她。
“她苍白忧郁,头发和上午一样披在肩头上,可是脖子上再没有绳子,手也不是绑着的了。她自由了,因为她已经死去。
“她穿着一身白衣服,头上盖着一幅白头巾,仰头望着天空,慢慢地朝他走来,那神奇的山羊跟着她。他觉得自己变成了石头,太重了,逃不开了,只能做到她向前走一步,他就往后退一步,他就这样一直退到楼梯的黑暗的拱顶下面。想到她或许也会走到楼梯上来,他浑身都凉了,假若她真的来了,他一定会吓死。
“她真的来到了楼梯口,停留了一会儿,向黑暗里看了看,但是好像并没有看见神甫便走过去了。他觉得她仿佛比生前更高,他看见月光透过她的白衣服,他听见了她的呼吸。
“等她走过去了,他就起步下楼,脚步慢得跟他看见过的幽灵一样,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幽灵。他害怕极了,头发根根直竖起来,那盏灭掉了的灯依旧在他手中。走下曲曲折折的楼梯时,他清楚地听见一个声音在一边笑一边重复地念道:
‘一个鬼魂在我面前走过,我听见一声轻微的呼吸,我的头发直竖起来。’”(陈敬容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8月版《巴黎圣母院》331-332页)
有了第三卷的风景、风物描写后,又来了第五卷第二节大卷的宗教、历史等极易过时、画蛇添足的议论。
这种游离于小说,对展示人物性格、思想情感和命运毫无意义的议论文字,越少越好啊!十八、十九世纪那时的读者,可能有钱有闲,能心平气和、饶有兴致坐下来读书、研讨,那时的作家“应对市场”,可能太喜欢卖弄自己的知识和才华,在小说中不当的时间、不当的段落,心痒手痒都要急着展示。小说是什么?不管怎么说,你得写故事情节,在故事的发展、高潮中展示人物的性格、思想,最终展示这种性格、思想导致的个人命运,好的坏的结局、喜剧或悲剧、正剧的人生。空泛的议论不属于小说,就某个问题、方法、技巧的专论,只适用于“论文”。小说不是议论出来的,而是人物、故事展现出来的。
而撇开以上两处过分的风景、景物描写和空泛议论,整个《巴黎圣母院》故事非常连贯、情节诱人、人物命运悲催,善恶是那样分明、美丑是那样对立错位、命运是那样不可把控,塑造的爱思梅拉达集善良与美于一身,最后被表面严肃、崇高而内心淫荡肮脏凶残的神甫给嫉妒、毁灭,一出悲剧一百多年来令读者嘘唏不已,回味无穷,不愧是大师手笔的经典。要是没有这两处炫耀的败笔多少败坏了阅读兴趣,笔者认为,《巴黎圣母院》声名绝对要高于《红与黑》《简·爱》等一大截,跻身最伟大的经典作品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