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小说连环画改编的诗性建构
赵树勤 路诗滢
沈从文小说被誉为“乡土抒情诗化小说的集大成之作”[1]杨义:《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197页。,其诗性的散文化叙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随着图像时代的来临,许多现当代文学名家的经典之作都陆续被改编成丰富多彩的连环画,深受读者的喜爱与欢迎,并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探究。遗憾的是,有关沈从文诗化小说连环画改编的探讨却几近阙如。实际上,迄今为止已有十余位画家参与了沈从文小说的连环画改编,他们将其10篇小说改编成了13个不同版本的连环画,其中不少版本曾荣登数届全国大型画展,并屡次斩获国家级荣誉奖项,这一图像改编现象,无疑是一个饶有兴味而又极具学术价值的研究课题。
一、矛盾:沈氏原则与改编倾向的博弈与出路
沈从文小说融叙事、抒情、状景于一炉,因其行文间展现出田园牧歌式的乡土风情画卷而成为艺术改编的“香饽饽”,其中涉及影视、戏剧、连环画等诸多领域,改编的方法莫衷一是,改编的结果也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沈从文的作品属于典型的诗化小说,其语言文字是散文化、跳跃式的,而情感表达又是意象化、隐喻式的,因此,故事情节具有碎片化和片段式的特质,与传统图像叙事所要求的情节连贯发展不尽符合。在改编过程中,如果完全尊重原作,会因过于诗化而难以引起读者的共鸣;若是舍弃小说中宝贵的诗意氛围,又面临着改编失败的危险。因此,要将如此充满“诗性气质”的沈从文小说进行成功的图像改编绝非易事。
一直以来,大多数沈氏小说的图像改编尝试都存在着一个缺憾——二次创作对原著诗意氛围的淡化和消解。这个缺憾首先暴露在影视改编上,同时也引起了作家本人的关注与介入。1953年,导演严俊将《边城》改编为电影《翠翠》,沈从文阅片后大失所望,他认为影片在画面和视听语言上丧失了小说的诗韵,并对此评价道:“(改编者)主要是看不懂作品,把人物景色全安排错了……应当作一个沅水流域画卷来处理,才会成功”[1]沈从文:《沈从文全集》(2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36页。。有了前车之鉴,1983年凌子风导演在二度改编《边城》时,就特别邀请了沈从文亲自参与剧本审阅,并请其写下大量修改意见,以确保影片能够尽量忠于原作。然而,尽管导演做了很多努力,仍有学者指出:“小说轻故事情节,重主观、重情绪、重印象的诗化风格,被电影转换成了重起承转合、重故事流畅的传统好莱坞风格”[2]李美容:《从诗化小说到诗电影——论电影〈边城〉之改编》,《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第100页。,可见改编后的作品依然具有“诗性气质缺失”这一通病。针对这一点,沈从文在与友人往来的信件中反复强调,希望将小说“当成个抒情诗画卷般处理”[3]沈从文:《沈从文全集》(2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88页。,不仅仅指《边城》,还包括许多其他作品,如《贵生》《萧萧》《丈夫》等[4]参见沈从文:《沈从文全集》(2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03页。。后来,小说《丈夫》在1986年被导演黄蜀芹改编成电影《村妓》,《萧萧》在1988年被导演谢飞改编成电影《湘女萧萧》,但遗憾的是,两位导演均摒弃了沈从文在小说中极力营造出的诗情画意,使改编走向商业化、政治化的道路,几近丢失了原著的神韵。
回溯沈从文对作品影视改编的介入,不难发现,他对自己小说被图像改编的心态十分复杂。一方面,他深怀隐忧,无法接受背离写作本意的二次创作,认为不被改编也许是幸事[5]参见沈从文:《沈从文全集》(2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80页。;另一方面,他又对改编的倾向进行了细致的思考,他借用好友汪曾祺的话语表明:“不必侧重在故事的现实性,应分当作抒情诗的安排”[6]沈从文:《沈从文全集》(2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49页。,坚持要绝对尊重原作“抒情诗画卷般处理”,这是他对于改编的底线所在。
无独有偶,在沈从文小说的连环画改编中,也存在着与影视改编相似的问题,且集中表现为:传统连环画“重故事性”与沈氏原则坚持“抒情诗化”相矛盾。一般来说,当小说被改编成连环画时,其文学脚本的编撰往往不同于小说原著,它有着一套合乎自身艺术规范的编写原则,强调“故事性强”“要有连续性”“尽量把情节展开”“心理描写要受到一定的限制”[7]白宇:《谈连环画脚本》,《美术》1958年第7期,第31页。等。因此,沈从文的诗化小说在被编排成连环画的文学脚本时,将面临着“去诗化”的选择。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沈从文小说在被改编成连环画后,其叙事中的诗性气质必定会走向消解,因为连环画的图像作为故事画,本身即是叙事的图像,能够表现小说叙事的内容与风格,正如莱辛在《拉奥孔》中言:“诗(文字)和画在摹仿真实时所使用的媒介符号不同,前者是时间性的艺术,后者是空间性的艺术”,但两者可以相互转化[1][德]莱辛:《拉奥孔》,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90-92页。,钱锺书则把这种转化称作“出位之思”,他指出“艺术家总想超过这种限制,不受材料的束缚,强使材料去表现它性质所不容许表现的境界……诗跟画各有跳出本位的企图”[2][日]浅见洋二:《距离与想象 中国诗学的唐宋转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13页。,这是在说:作为空间性叙事媒介的图像,可以“跳出本位”去表示时间性叙事媒介的语言。因此,当沈从文小说被改编成连环画时,图像的内容可不必局限于文字脚本,还可拓展到存在于原作中的故事,这表现为图像对小说文本的摹仿,从叙事学的角度上看,小说是对现实或想象中生活的一种叙事,那么其图像便是对文本的再叙事,即叙事中的叙事。
此外,连环画家尤劲东认为,可以通过连环画的图像叙事来构筑一种新的“连环”。他指出:“绘画是‘虚幻的空间’……而连环画正是这种‘虚幻空间流’,它的特征是‘流’,即一种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不意味着只是合乎某一文学情节(故事)或某一事件的产生、发展、终结的过程,而更重要的是艺术家的思维、情感的流衍过程”[3]尤劲东:《连环画要摆脱文学的束缚》,《美术》1985年第9期,第51页。,李晨作为热衷于沈从文小说连环画改编的画家之一,他与尤劲东的观点不谋而合:“何为‘连环’?一定是单纯的故事情节的‘连环’吗?画家尤劲东曾提出‘连环’为‘表现’过程,也是思维、情绪、造型的变化过程……”[4]李晨:《连环画将迎来柳暗花明》,《中国美术馆》2010年第4期,第72页。在把沈从文小说改编成连环画时,李晨就试图以一种新的形式来构筑诗化小说的“连环”,他将这种“连续性”灌注于图像叙事之中,通过图画里意象、空间和思维的连缀,来表现时间的线性流动与人物的情绪变化,这恰恰为解决连环画改编“重故事性”与沈氏原则要求“抒情诗画卷般处理”的矛盾提供了一种可行的出路。
综合来看,在13个沈从文小说的连环画改编版本中,有5个版本较为巧妙地做到了“诗性”与“连环性”的融合,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其小说“原汁原味”的诗意氛围,呈现出抒情诗画的良性互动,它们分别是画家李晨版《边城》《萧萧》和《雨后》,画家廖正华版《边城》以及画家董英杰版《丈夫》,因此以下论述主要就这五个有典范性的连环画改编版本进行探讨。

图1 李晨连环画版《萧萧》 图幅21
二、叙事:“空间之并置”展现情节故事线
约瑟夫·弗兰克在《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中写道:“现代小说家把他们的对象当做一个整体来表现,其对象的统一性不是存在于时间关系中,而是存在于空间关系里”[1][美]约瑟夫·弗兰克:《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秦林芳编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Ⅱ页。,沈从文的小说颇具“空间叙事”的特征,在叙事上呈现出弱化时间,强化空间的特点。譬如:《边城》不是传统的时间性叙事结构,而是借由不同空间的转换来推动情节的演变,通过爷爷和翠翠常出现的小屋、渡船、河街、吊脚楼等不同空间的切换来实现情节的发展。
连环画的图像叙事也是典型的“空间叙事”,画家依照文本绘制出多幅连续的图画,再依据情节线索重新排列形成一个个叙事片段,由于绘画是隶属于空间的艺术,组合图画也就是将多个空间进行时间排序,通过多张图像里物体的空间转换就能实现故事情节的变化发展。通常,小说在改编成连环画时,绘者都会采用一幅图像对应一个空间的形式,让多幅图像的多个空间排列组合,形成整个叙事架构中的某一个情节事件,然而这并非是处理图像空间表现的唯一指向,富有创造力的画家会根据沈从文小说独有的艺术特点进行自觉探索,通过重组空间的排列组合方式——或为分解、或为并置,来突显原著文本的叙事特质,丰富连环画的叙事手段。
在李晨版《萧萧》的连环画改编中,画家摒弃了传统连环画里单幅图像对应单个空间的绘图方式,创造性地采用了“三联一体”的构图格式,以“一面多幅”的并置空间进行叙事,将想要同时表现的情节限制在同一画幅里,通过空间的交替、切换、对比,强化出更为生动丰满的故事情节。小说叙述中萧萧在怀孕后欲离家出走却被识破,童养媳与他人珠胎暗结是件不得了的大事,婆家便请了众乡亲说理评判。李晨在图幅21里(见图1)巧妙地绘制了三个分割的不同空间,又将它们并置到一起:最左侧是特写——婆家人竖目叉腰,怒气冲冲;最右侧是近景——萧家人手足无措,背上的婴儿嘟嘴皱脸,仿佛在为萧萧的处境难过;中间是拉远的中景——乡亲们闻讯赶来,聚集在外指指点点。这一组画面的空间组合是一个由两侧向中间拉远的过程,事件的受害方婆家与萧家是近景,而与此事利益无太大关系的众乡亲是中景,这种空间并列切换的方式,便形如约瑟夫·弗兰克为解释“空间并置”的概念时所说:“并非只简单一个词的组合或一则轶闻的片段,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情节的各层次的组合”[1][美]约瑟夫·弗兰克:《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秦林芳编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3页。。画家通过并列放置故事情节里不同人物的神情和反应,使这些元素相互统一,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叙事片段,这种新颖的组合形式既能让读者体会到各方当事人迥异的心情,又能使空间叙事变得更为紧凑、连贯。
同样的处理方法不止这一处,李晨在图幅16里也围绕小说情节,主动分割了单幅图像中的空间,把孕后的萧萧找二狗对质时两人截然不同的神态动作并置到一起,两侧为中景,分别是:二狗仓皇无措、萧萧掩面痛哭,中间则是近景特写:萧萧殷切地望向二狗,二狗却低头回避。读者可以通过人物神色的差异来揣摩他们的思维性格与行为逻辑,并在脑海里推测出情节的最终走向,这也就形成了读者与画本之间良性的思维互动。
不得不说,画家将多个空间并置于同一画幅,通过空间的切换来展现情节线性流动的做法,是一种极其精巧的处理方式,不仅打破了传统连环画一幅图像对应一个空间的叙事传统,丰富了单幅图像的故事情节,节约了连环画图幅的数量,还圆满契合了沈从文诗化小说“强空间性”“弱时间性”的叙事特点,使得线性叙事在空间表现中层层递进、重点突出,进一步显示出连环画改编者在艺术创作中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三、抒情:“诗之意象”连缀情绪思维流
诗人郑敏说过:意象之于诗歌,犹如情节之于戏剧和小说[2]参见郑敏:《中国诗歌的古典与现代》,《文学评论》1995年第6期,第81页。,可见“意象”是诗歌的基础组成单位,也是诗性气质最为显著的体现。在现代文学作品中,沈从文小说因其意象化的表达而颇具“诗意”,有学者曾评论他的小说真正实现了“观念和象征意蕴、情节和意象的水乳交融”[3]龙慧萍:《沈从文诗化小说的叙事学研读》,《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第47页。。的确,沈从文的诗化小说往往能兼顾意象与情节,他擅长创造小说故事分支的“副文本”,以雅淡的意象取代曲折离奇的情节,成为主人公情感世界外化的重要标志,真正做到了“以优美而哀伤的情致动人”[4]龚刚:《论〈边城〉的“诗语”风格与结构模式——基于形式主义与结构主义视角》,《中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1期,第121页。。譬如,在《边城》中,作者多次用“虎耳草”的意象来寄托翠翠对傩送没有宣之于口的情思,汪曾祺在追忆沈从文时曾聊到他与“虎耳草”的羁绊:“沈先生家有一盆虎耳草,种在一个椭圆形的小小钧窑盆里。很多人不认识这种草。这就是《边城》里翠翠在梦里采摘的那种草,沈从文喜欢的草”[1]汪曾祺:《汪曾祺全集 四 散文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61页。,由此可见,沈从文有将生活中物象转化为小说中意象的习惯,他将对湘西言之不尽的复杂情感寄托于《边城》里“白塔”“渡船”“虎耳草”等诸多意象之中,这些意象在不同时段、不同场景中的反复呈现恰恰透露出作家在艺术创作中的诗性思维。

图2 廖正华连环画版《边城》 图幅102
廖正华对《边城》的连环画改编就很好抓住了“虎耳草”的意象,他在图幅74、图幅101、图幅102中分别绘制了翠翠在梦中攀崖采虎耳草、翠翠借口到后山偷摘虎耳草、翠翠编织虎耳草头饰戴在头上这三幅图像(见图2),画面中“虎耳草”是中心物象,它的反复出现使得翠翠本应平常的动作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构成了小说的分支情节,画家正是通过描摹翠翠三次对待“虎耳草”时做出的不同情态,来递进暗示她对傩送悸动的爱恋。
除此之外,董英杰版连环画《丈夫》也试图用意象来侧面表现主人公的情绪流变。小说《丈夫》讲述的是一个乡下丈夫到县城看望以做妓女谋生的妻子,在当时湘西乡下的贫困家庭中,婚后女人去到船上做“皮肉生意”,得来的钱能够给夫家补贴家用,是所谓“名分不失,利益存在”的行为,被视为正常的营生手段。然而,对于男主人公来说,将妻子的身体给予船上人来人往的他者去享用,就相当于让度了自己作为丈夫的部分权利。由于这是乡里多年来约定俗成的潜规则,男主人公此前并没有深入思考过“丈夫”与“妻子”的身份观念与权利意识,沈从文在小说中多次写道:蜗居后舱的丈夫不得不直面妻子在前舱一次又一次用身体接客的残酷现实,他试图通过这种对“权利丧失”的直面暴露来引出丈夫与妻子心态上的变化,进而引发他们对自我身份意识的觉醒。
在董英杰版连环画《丈夫》中,就通过“胡琴”这一意象重点表现了夫妻两人情绪变化的过程。丈夫在得知妻子今晚要接客时,曾愤怒地表示要立刻离开,但妻子随后将集市上买来的“胡琴”送给丈夫,让他觉得妻子心里还有自己,便没有立即回去。在图幅30中,妻子为丈夫调好了琴弦,丈夫拉琴后愉快地笑了,然而这种和谐没能持续太久。醉酒的兵士上船大吵大闹,叫嚷着要让拉琴人出来唱曲;在画幅34中,丈夫挟着胡琴躲到后舱,而妻子却被迫出去赔笑脸,“胡琴”作为妻子赠予的礼物,虽然象征着关心与爱,但是这种“身体自主权利丧失”的爱对于丈夫来说不过是一种幻象,当他人可以光明正大地享用妻子的身体时,自己却只能带着“胡琴”躲躲藏藏,这种充满讽刺意味的反差与情绪上的失落,从图幅34丈夫仓皇狼狈的背影中可见一斑。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丈夫刚想同哄完醉鬼的妻子说一些家常私话,却又被大娘提醒接下来妻子要去接待干爹水保,丈夫的情绪彻底爆发了。在图幅50中,他把妻子做“生意”得来的钱票撒到地上,像孩童般嚎啕大哭。紧接着图幅51里,妻子也感知到这种身份错位的荒诞,她抬头望向船梁上的“胡琴”沉默不语(见图3)。在小说原著里,作者可以通过大量的对话和动作描写来书写丈夫与妻子情绪上的变化,然而改编成连环画后,文学脚本的重编限制了这些描写的篇幅,诗性语言的表达也在不同层面上被削弱,此时画家很聪明地在图像绘制上融入了诗性思维,以物象为载体把夫妻二人的心理情绪外化,让朴素的物象变成抒情的心象,在需要传递情绪的情节中,用图像凸显出灌注主人公情感的意象。“胡琴”意象的反复出现连缀了妻子与丈夫的心理变化,从两人弹奏“胡琴”获得愉悦体验到妻子独自望着“胡琴”沉默失语,巧妙暗示了两人对自我身份意识的觉醒,画家通过图画中典型意象的连缀,成功展现出丈夫对船妓旧俗从接受到质疑,又从反思到反抗的心理变化过程,可以称得上是一次较为圆满的改编尝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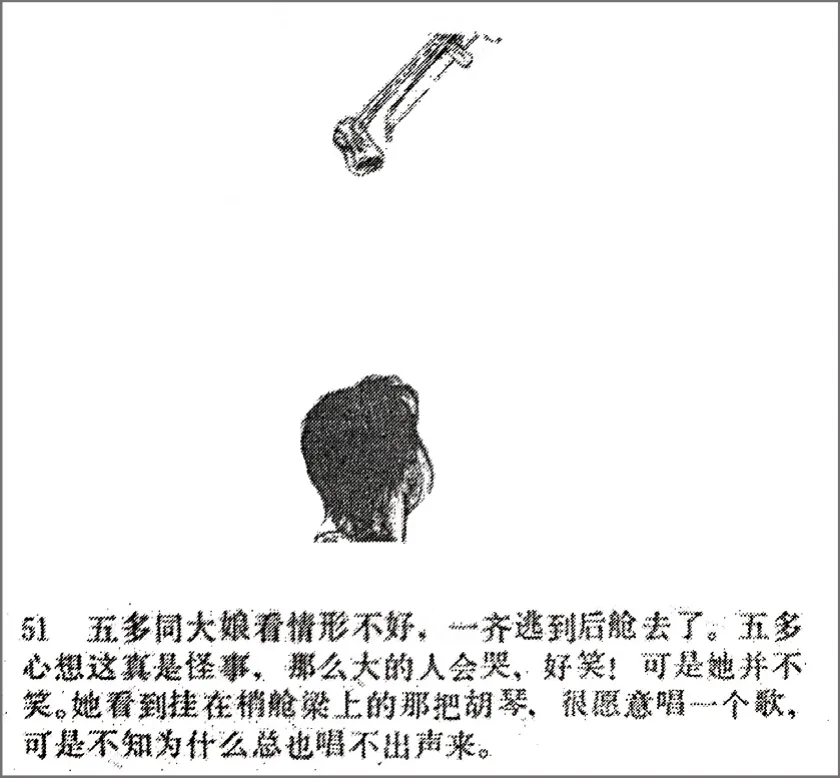
图3 董英杰版连环画《丈夫》 图幅51
由上可得,这些连环画改编后的作品重点描摹了小说中反复出现的经典意象,将人物的情绪变化寄托于物象中,使简单的物象演化为复杂的心象,不但没有丢失沈从文诗化小说里“重意象化”诗性表达的神韵,还在某种层面上实现了故事情节、人物情感的“连环性”发展,让作品兼具连环画连续流畅的阅读体验以及沈氏风格独有的审美意蕴。
四、状景:“语之留白”生成阅读联想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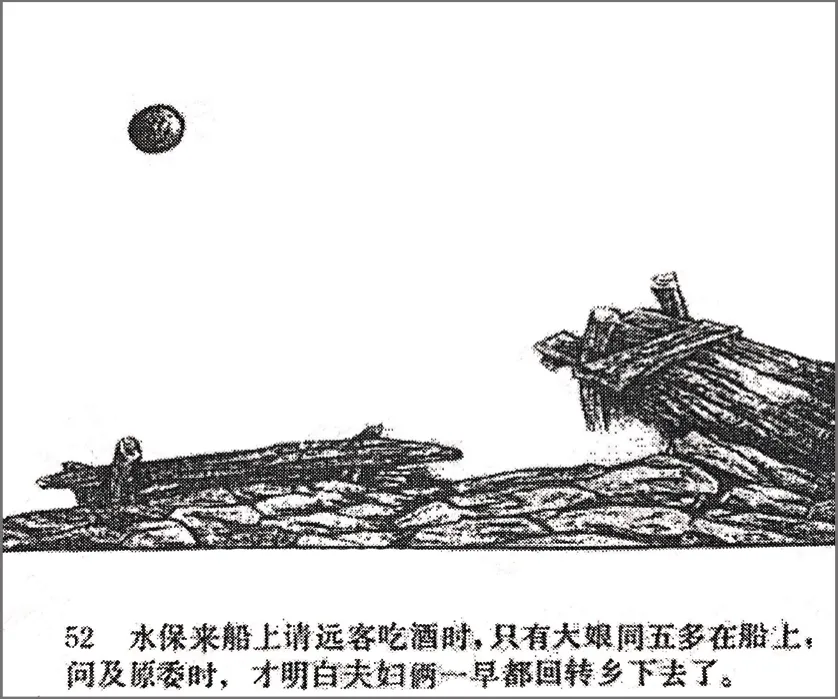
图4 董英杰版连环画《丈夫》 图幅52
众所周知,小说三要素是人物、情节和环境。传统小说往往以情节的曲折离奇取胜,而沈从文却大反其道,其笔下人物、情节所占故事的比重并不大,他似乎有意识地在这些其他作家用心耕耘的板块留下大量的艺术空白,去填充他想要书写的面貌——湘西风情,这与中国传统绘画中“留白”的技法有异曲同工之妙。笪重光在《画筌》中言:“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1][清]笪重光:《画筌》,《艺林名著从刊》,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1983年,第9页。,就是在说国画的留白处往往是全局的关键,不仅衬托了画面的主体,扩大其自由活动的空间,同时也成为主体形象的延伸,拓展了画面的意境。
沈从文在创作短篇小说时,就倾向于将绘画“留白”的技巧融入写作中,“尤其重要处,便是那些空白处不着笔墨处,因比例上具有无言之美,产生无言之教”[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6卷 文论》,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505页。。譬如,小说《边城》最后写道,“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没有明确点明翠翠与傩送的结局;《雨后》的结尾“雨已不落了。她还是躺着,看天上的云,不去采蕨……”同样没有揭示阿姐与四狗在鱼水之欢后的故事,他似乎有意将后续的发展在小说中省略,使之留下空白,以此来激发读者的联想与再创造。沈从文对情节的语言表达是模糊化、空白化的,看似平淡却饱含深刻的思想意蕴,这种虚实结合、有无相生的留白艺术,既能彰显出小说的诗情画意,又能使读者产生意犹未尽的阅读体验。
画家们在对沈从文的小说进行连环画改编时,自然也注意到了小说“重环境描写”和“重叙事留白”的艺术特点。他们将两者结合,在为文学脚本绘制对应的图像时,便有意识地将人物剔除在外,把笔墨挥洒在其周边场景环境的白描上,使得整个图景犹如湘西山水画卷,只现物景不见人像,言已尽而意无穷,形成艺术上的留白。李晨版连环画《雨后》中画幅15所对应的情节是:四狗的手在阿姐身上“撒野”,画家没有直接绘制出人像与动作,反而只描摹了这件事发生的场景:小船停靠在石头铺就的河岸边,不远处有一个草搭的棚子,他们便是在这草棚下唱歌嬉戏、共赴巫山。董英杰版连环画《丈夫》中画幅52(见图4)对应着小说的结局:水保到船上吃酒时被告知夫妇俩一早就回到乡下去了,画家没有根据脚本描摹出任何一个人物,整个画面除去上方的太阳以及下方无船只停靠的河岸,其余皆为空白。画面看似简单,却暗含无限深意:妻子随丈夫走了,以后还做船妓吗?她不做了,其他丈夫的妻子呢?若都回乡了,这片河岸的船妓是不是都不再有了……读者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反复品味画面的空白之景,可以在联想和再创造中构建出一个完整的故事图景,为叙事留白的小说文本生成新的意义与内涵。
除此之外,画家也试图通过再现小说里的自然风光来构建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并借自然环境中的物象暗示情节的推演,以还原其叙事上留白的特点。小说《边城》的高潮部分由一场酝酿许久的雷雨拉开序幕:在雨夜的电闪雷鸣中,爷爷走向了生命的终点。然而,沈从文没有把叙述的重点放在爷爷身上,对他的描写仅寥寥数笔——“原来这个老年人在雷雨将息时已死去了”,他将更多笔墨放在雷雨夜的环境描写上:电光从屋脊掠过,紧接着大雨倾盆,河溪洪流滚滚,渡船脱离缆绳,白塔业已坍塌……学者刘进才将这种景物描写称为“非情节因素的空间化”[1]刘进才:《京派小说诗学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8页。,指的是那些不参与小说情节发展的叙述或描写。他认为这是京派作家在文本内部对空间形式的艺术追求,京派小说更看重环境,而沈从文小说里对自然环境的描写和民情民俗的展示恰恰就是他最想要突显的部分。李晨版连环画《边城》对这段情节的处理很好地还原了小说的诗化风格,也兼具留白的艺术美,他似乎与沈从文先生秉持着同样的审美意趣,没有直接绘制出爷爷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情态,反而是描摹了两个具有暗示意味的自然物象:硕大的闪电划破黑云直击大地(见图5),湍湍流水席卷砖石向河岸涌去……闪电破空、河水奔流、白塔坍倒、渡船离去,它们将爷爷和翠翠的分别推向了生命的另一个阶段,这些自然物象在沉默中爆发出强大的审美潜能与艺术张力,绘画艺术上的留白也带给读者可以反复咀嚼、无限品味的空间。

图5 李晨连环画版《边城》 图幅84
总而言之,部分绘者在连环画改编中与作家志趣相投,同样追求“留白”的含蓄美。虽然他们所采取的艺术媒介不尽相同,但最终仍是殊途同归,不论是在图像里留下大片可填充的空白来映衬小说叙事的“言已尽而意无穷”,还是通过描摹自然风光以渲染环境氛围,传达主体情绪,都是画家对沈从文笔下诗情画意的抒写与再创造,使得作品在文画互动中实现了“诗性”的解放,给读者带来全新的阅读审美体验。
综上可见,改编者们努力挣脱以往诗化小说图像改编难以与原作风格有机契合的拘囿,有意识地将沈从文作品的“诗性气质”融注于连环画创作,建构了一个富有“连环性”的诗意世界。
五、启悟:在开放与创造中探求新生
在传统连环画日渐式微的今天,重新检视与思考沈从文诗化小说连环画改编的成功案例,为当今读图时代的连环画及相关图像改编提供了积极的启示,即在开放与创造中探求新生。
回顾沈从文小说连环画改编的历程,我们看到,改编者们一直以开放的姿态,积极借鉴其他艺术门类的叙事技法,促使传统连环画向现代转型的方向努力。当代影视动漫的叙事手段丰富多样、造型动作新颖夸张,能满足时下大众的审美情趣。沈从文诗化小说连环画改编的创作者从中得到启悟,在绘制图像时利用视点转移、时空交错等影视叙事技法来叙说故事,从“三联一体”的空间并置到“聚焦特写”的镜头表现,画家将沈从文小说的情节段落重新分解组合,以富有内在逻辑的空间切换来诠释小说中的湘西世界,使得连环画本呈现出电影蒙太奇叙事般的质感,不但没有破坏连环画一气呵成的阅读体验,还恰到好处地营造出了沈从文小说独特的诗意氛围,弥补了过去影视改编时“诗性气质”缺失的遗憾。从这点上看,沈从文诗化小说的连环画改编无疑是一个值得学习的改编典范,这意味着新兴连环画的创作观念与技巧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哺影视。这种绘画、影视及动漫技艺的互补交融,为图像叙事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艺术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