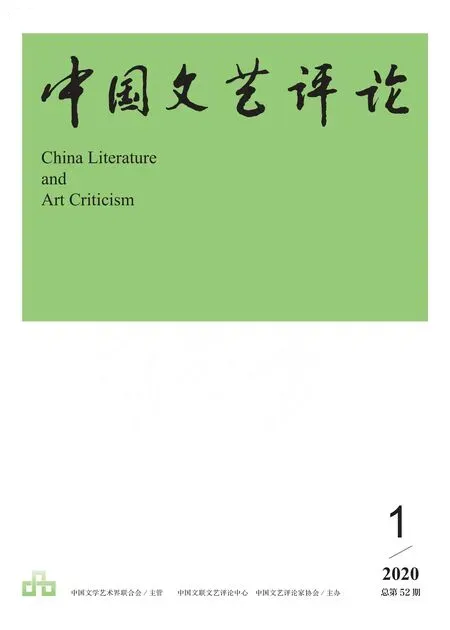2019戏曲:前行在回归本体之路上
傅 谨
在刚刚过去的2019年,戏曲在回归本体的路上曲折前行。戏曲的演出与新剧目创作、经典传承与当代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多年来一直衍生出各种各样的争议。这些颇具时代特色的问题,既因戏曲在中华民族艺术发展进程中的特殊地位而备受关注,也因当代戏曲演出市场不振,而经常逸出学术与艺术的轨道。通过对2019年戏曲领域现状的审视,就可以找到许多与之相关且令人深思的现象。
戏曲题材丰富多样
2019年在上海举办的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和在福州举办的第十六届中国戏剧节,无疑是这个年度戏曲界最重要的活动,如果从这两大戏剧艺术盛事中戏曲剧目的题材选择趋势看,这一年里出现的变化是令人瞩目的。
2019年5月20日至6月2日,由文化和旅游部、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在上海举行。中国艺术节中的“文华奖”评选和“群星奖”评选是国内最重要的艺术赛事之一,尤其是2019年采用了新的剧目遴选规则。除东道主外,每个省市区均可自行决定选送一台剧目参加演出,从而为各选送主体提供了创造性地运用不同剧目遴选策略的机会。尽管选送优秀剧目参演在表面上仍是核心原则,但在实际遴选过程中,往往受到更多非艺术因素的左右,各种各样的考虑与安排五花八门,大家绞尽脑汁、排兵布阵,以求获得佳绩。
戏曲在历届艺术节参演剧目的数量上均有明显优势,但本届艺术节上的戏曲剧目数量却有所下降,仅有一半略多。如果从题材选择的角度看,更令人玩味。在所有参演戏曲剧目里只有三部古装戏,其余14部都是一般所说的“现代戏”,而且最终获“文华大奖”的四部均为现代戏,这在历届戏曲类展演中非常少见。而在所有现代戏里,反映改革开放以来的现实题材作品多达九部,占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所有参演戏曲剧目中的一半,这样的比例更为历届艺术节所仅见。
如果我们对全国各地的表演艺术类展演活动作更全面的审视就会发现,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虽只有三部古装戏,但古装戏毕竟还未绝迹。而此前有超过两个省在本年度举办的艺术节上,所演出的全部都是现代戏,甚至都是“当下题材”,即以近十年来的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剧目。正因为题材选择较为集中,一时间出现大量雷同的戏曲新剧目,甚至在同一次展演中,就出现数部反映国家近年来通过向农村选派第一书记等方式推动“精准扶贫”的成就的剧目,而且连剧名都大同小异。恰恰因为这些创作的背后,明显包含了对戏剧功能急功近利的理解,当戏剧家仅仅为即时任务而创作时,很容易忽视艺术规律。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戏剧作家往往无暇真正沉潜到丰富的现实生活和戏剧人物内心世界中,发现并表现有个性和有力度的戏剧内容,所以艺术质量就很难让人满意。这让我想起1963年初华东话剧汇演前,柯庆施号召文艺家要“写十三年”的往事[1]“写十三年”的口号是1963年元旦华东区兼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在上海文艺界联欢会上讲话中提出的,此后很快升级为“大写十三年”,意即提倡文艺创作者选择1949年至1962年这13年的题材。当时政治风云诡谲,在这个口号背后有很多非艺术的动机,通常认为那就是后来“文革”时期遍布全国的文化大萧条的前奏,而针对柯庆施明显带有现实政治动机的“写十三年”提出的反对意见,恰好成为“文革”中陆定一、周扬、田汉等人挨批判时的罪状。详见拙著《20世纪中国戏剧史》下册相关章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柯庆施这一在当年就引起时任中宣部、文化部领导异议的提法,看似只不过是政府官员对戏剧创作中题材选择取向的要求,实际上在它的背后潜藏着简单用政治横加干涉艺术创作的逻辑。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需不断重温历史,深化对当代艺术史曲折历程的认识,避免重走弯路。
当然,从整体上看,我们要充分信任戏剧界自身矫正偏差的能力,正是由于历史的曲折会不断加深我们对戏剧功能客观且正确的认识,在2019年的戏曲发展进程中,才可以欣慰地看到这样的结果。在2019年10月26日至11月12日举办的第十六届中国戏剧节上,参演剧目与中国艺术节相比就有了明显的变化,不仅风行一时的各类“第一书记”的身影不再那么频繁出现在舞台上,古装剧目的比例也显著增加了。虽然当代题材作品仍然不少,但却更好地体现了题材的多样化。在本届戏剧节上,所有参加演出的30台剧目里有九部新编古装戏,这占到了总数的近三分之一,而且表现出了较高的艺术水准,比起其他剧目更受观众的喜爱。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戏曲的兴衰始终与其题材选择密切关联,而戏曲题材的多样化与丰富性,正是戏曲繁荣发展的积极信号。这一届戏剧节上受到好评的剧目中,既有北京市选送的河北梆子《人民英雄纪念碑》、江苏省选送的淮剧《送你过江》、山东省选送的吕剧《大河开凌》等充分体现当代价值观的优秀现代戏;亦有福建省选送的莆仙戏《踏伞行》、闽剧《红裙记》、歌仔戏《侨批》和上海市选送的淮剧《武训先生》等相当出色的古装戏,而这些古装戏也无不体现着正确健康的价值导向。包括石家庄市丝弦剧团演出的《大唐魏徵》、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演出的《不越雷池》和河南省豫剧院一团演出的《张伯行》,都能将历史情怀和现实观照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以此激起当代观众的强烈共鸣。尽管每个省区市多数都只有一台入选剧目,全国各地仍有多达七个省市选择了报送古装戏,说明超越题材的局限、从艺术质量角度出发遴选剧目的观念,获得越来越广泛的认可。
当然,戏曲题材的多样化与丰富性,并不是2019年度中国戏剧节特有的现象,也逐渐体现在2019年下半年以来各地的演出剧目中。尽管仍有一些来自艺术之外的意见,但从整体上看,戏曲界本身对现代戏、尤其是对当下题材戏曲创作一边倒的现象的质疑具有普遍共识,并且逐渐形成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动戏曲创作演出逐渐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我们希望这种趋势能够持续下去。
演员重新回到舞台中心
2019年5月,张火丁再次以她新创排的京剧程派剧目《霸王别姬》,担纲“相约北京”大型联欢活动的闭幕演出,11月又携该剧赴上海国际艺术节演出,均引起强烈反响。在上海演出之后,当地专家学者给予高度评价。张火丁的演出在今天这个时代具有多重意义,不仅是由于她别出心裁地用程派演出了当年梅兰芳最著名的保留剧目,程派的唱腔与表演风格与梅派是如此不同,张火丁让这出古老的经典展现出全新的面貌,更由于这是传统经典剧目高水平呈现的极好例证。如京剧表演艺术大师叶少兰先生所说:“京剧有很多经典剧目,但在继承和弘扬经典时,必须具备高超的艺术、技术标准以及专业水平……如何让更多的京剧经典剧目在当代舞台上再现,张火丁的努力提供了一种答案。”[1]叶少兰:《经典剧目需要高水平传承——从张火丁演出〈霸王别姬〉谈起》,《人民日报》2019年11月28日第20版。
张火丁的《霸王别姬》演出之所以值得深入讨论,是因为她将这出梅派经典搬上舞台的过程,始终围绕其艺术风格与表演特点展开。为了这出不足一小时的小本戏的重新演绎,张火丁和对她的演唱风格极为熟稔的作曲家万瑞兴一起,为剧中的女主人公虞姬设计了全新的唱腔。为增加剧中虞姬为霸王项羽舞剑表演的观赏性,张火丁在武生演员张火千的帮助下,重新设计了这段闻名遐迩的剑舞,尤其是她在虞姬所舞的剑上加了长穗,这样一来,几乎所有剑舞的动作都要重新排,经过一年左右的练习,这段剑舞才臻于完善。[1]有位非常优秀的戏曲演员曾对我说,她无数遍欣赏张火丁的这段演出,初看时只觉得不错而已,但看得越多越是感到“怕”,因为越看越明白要演到如此天衣无缝有多困难,需要下多大的功夫。也有戏迷将张火丁这段戏外流的视频用慢动作播放,试图找到其中的破绽,却发现在慢动作播放下张火丁的动作依然如行云流水。在这个很多人都习惯于“倍速追剧”的时代,这类可以用慢速欣赏的表演艺术就愈显珍贵。因此,在张火丁这里,这出老戏不只是在唱腔和表演上呈现出全新的面貌,并且用高难度的剑舞,陡然提升了这出戏的技术标准。
然而她的这一创作过程对京剧乃至整个戏曲界而言,可以说既熟悉又陌生。说它熟悉,是由于这样的创作路径,是历史上京剧乃至于戏曲发展演变的常态,千百年来各剧种的戏曲演员就是通过自己对剧目的理解和自由发挥,造就了精彩纷呈的戏曲文化。说它陌生,是由于一方面,在进入20世纪后,愈益商业化的演出市场催生出海量的新剧目,表演者在新剧目创作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远远比不上对传统剧目的个性化演绎那么重要。另一方面,20世纪50年代以来,戏曲的创作模式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不仅由职业化的编剧负责剧本创作成为新常态,更关键的是职业化的导演成为舞台形态设计最核心的承担主体,而表演者反而在剧目创作过程中成为越来越次要的角色。
程派《霸王别姬》的出现,让张火丁这位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戏曲演员的创造能力得到充分体现,更说明优秀的表演者完全有可能站在创作的中心位置。如果我们把这一现象级事件看成“演员中心制”的再现,一点也不为过。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戏曲领域“演员中心制”的批评不绝于耳,它的另一面就是文化主管部门强力推行的“导演中心制”,或者叫“编导制”。对“演员中心制”的批评内涵异常复杂,其中包括对晚清民国城市剧场中“明星制”商业模式的批判,包括对以京剧为代表的地方戏剧本中大量存在的文辞粗疏现象的不满,更包括了在模仿学习前苏联戏剧“先进”经验时所引进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等人的理论,他们倡导为了努力实现戏剧的整体性,必须由导演完全掌控舞台。就像那个年代许多艺术和学术上的争论一样,对“演员中心制”的批评也是一边倒的。主张推行“编导制”理论的倡导者既有主导权,又在理论上借前苏联理论的“权威”之助,很快形成一种话语霸权,但是却忽视了戏曲史上演员在表演中作为创作主体的特点,因此戏曲发展逐渐离开传统。改革开放以后,“导演中心制”不再有直接的权力支撑,前苏联理论的影响力也日渐式微,但戏曲界仍大致行进在历史的惯性中,直到那些完全不理解戏曲的导演在戏曲创作中挥舞着指挥棒的现象引起越来越强烈的不满,让戏曲重新回到“演员中心”的呼声才零零星星地响起。
但是戏曲创作要重新回到“演员中心”的模式并不容易,半个多世纪以来,戏曲新剧目创作的“导演中心制”不会在一夜之间改变。差不多有两代戏曲演员都已习惯于在导演的指挥与安排下从事新剧目的创作了,如何把握新剧目创作时的主动性与主体性,对多数戏曲演员来说都是个全新的课题。如果说张火丁的《霸王别姬》只是偶然地因她对这个剧目多年的痴迷而不自觉地萌生了用程派重新演绎该剧的念头,因此才有我们看到的这出有强烈张火丁个人风格的新经典的话(如她全新创排《江姐》和《梁祝》时,仍可看到对导演的高度依赖),那么莆仙戏《踏伞行》就是新的,是更自觉地让演员成为新剧目创作过程中的主导者的思想结晶。
福建省莆仙戏剧院创作演出的莆仙戏《踏伞行》,由周长赋编剧,徐春兰导演。该剧巧妙地将莆仙戏传统剧目《双珠记》中未婚夫妇陈时中和王慧兰乱世中逃难遇亲这条副线单独抽出,又截取与化用了传统剧目《蒋世隆》里的“走雨”“抢伞”等精彩场面,经过重新构思和精心糅合,综合这些材料将它们改编发展为一部新的大型剧目。徐春兰最初是毕业于江西省文艺学校的赣剧演员,既有戏曲表演的功底,又经过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的训练,是一位极具场面掌控能力的优秀导演。但是福建省莆仙戏剧院并没有完全依赖于她的编排工作,就像福建泉州当年创作梨园戏《董生与李氏》一样,在请外来导演完成了剧目舞台呈现的基本骨架后,更重要的是由演员本身来完成具体的一招一式的表演设计与安排。在这里,莆仙戏表演艺术家、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王少媛,以及姚清水等莆仙戏名家所起的作用,一点不比导演少。《踏伞行》之所以令人惊艳,除了剧本的情节设置精妙,场面调度流畅外,更重要的是,在扮演男女主人公的黄艳艳、俞植等主要演员的表演中,莆仙戏传统科介在剧中得到充分运用,如风摆杨柳般的动态和娴淑内敛的静态相得益彰,尤其是精美绝伦的蹀步和车肩,更让全剧融化在浓郁的古典风韵中,美不胜收。
无论是张火丁的《霸王别姬》,还是莆仙戏《踏伞行》,都是因为经过一个以演员为主体的磨戏过程,才呈现出如此的精彩。事实上,戏曲史上优秀的经典几乎都要经历一个由演员“磨戏”的过程,只是这种“磨”有两大途径:一是在编排阶段的“磨”,一是在演出中的“磨”。余叔岩曾经花几年时间精心琢磨和模仿谭派唱腔,最后卓然成为大家,他的“十八张半”唱片至今仍是京剧老生行中最好的经典。程砚秋演《锁麟囊》、梅兰芳演《天女散花》都经过类似长时期的磨戏,最后才搬上舞台。但是,戏曲史上更为多见的现象,是表演者在同一剧目、同一场次的多少次反复演出中,不断探索、寻找最具魅力的表达方式。而我们现在所见的各地方剧种的精彩表演,多半都是在漫长时间的流淌中,无数演员一点一滴的积累,他们以群体的方式完成了这个磨戏的过程,因此才能让剧本文学水平相对不高的地方剧种仍留下无数经典作品。张火丁的《霸王别姬》和莆仙戏《踏伞行》的磨戏当然属于前一种,而且由于戏曲演出市场不振,后一种磨戏的模式,即在长期演出过程中,通过磨戏让演出日益完善的可能性,已经变得越来越小。所以演员在编排阶段的磨戏,或者更直接地说,在新剧目创作过程中能否更关注表演这一戏曲的核心,尤其是在具体的表演环节是否能回归“演员中心”的剧目创作模式,就成为今天能否出现新的戏曲舞台经典的关键。
倡导戏曲创作向“演员中心”的传统回归,并不是要简单地否认在戏曲新剧目创作中导演所起的作用,而是指表演者不能放弃自己的主体地位。多年来,在戏曲新剧目创作过程中,人们更多关注的是编剧和导演在故事情节、人物形象、思想感情等方面的得失,却忽视了戏曲史上另一个普遍现象,即表演者如何用心于舞台上的一招一式,这是吸引观众最直接的要素。张火丁的《霸王别姬》和莆仙戏《踏伞行》为“演员中心”的创作提供了直观的范本,必将刺激戏曲界更多优秀表演艺术家向着这条创作道路前行。
国家艺术基金助力戏曲发展
从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发《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以来,国家陆续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戏曲进校园、戏曲进乡村等等,对戏曲的传承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其中对戏曲发展最直接的支持与投入,就是国家艺术基金。
国家艺术基金于2013年正式启动,在包括戏曲、话剧、舞剧、歌剧和交响乐、曲艺、杂技等多种类的舞台艺术作品中,对戏曲的支持力度是最大的,历年资助项目中戏曲都占到将近总数的一半。从2016年开始每年度的滚动资助项目里,戏曲剧目也经常占到一半。据统计:在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助的59部大型戏曲剧目中,有相当部分在2019年搬上了舞台,另有五部戏曲作品列入2018年度滚动资助项目;2019年度资助了53台大型戏曲剧目的创作,其中有七台为2019年度滚动资助项目。这些资助项目成为了2019年戏曲新剧目的主体,从中涌现出多部优秀作品。从结果看,2019年获第十六届“文华大奖”的秦腔《王贵与李香香》、豫剧《重渡沟》、苏剧《国鼎魂》、河北梆子《李保国》,和2019年获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的滑稽戏《陈奂生的吃饭问题》、秦腔《王贵与李香香》、豫剧《重渡沟》、闽剧《生命》等,全部都是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充分体现了国家艺术基金在戏曲精品剧目创作中的突出作用。
诚然,我们不能把获奖与否看成是衡量剧目水平的唯一标准,毕竟各类奖项的评选需要考虑的不仅有艺术水准,还包括更多其他的因素。但即使完全从艺术的角度看,2019年最值得关注的戏曲新作品里,除了前述的莆仙戏《踏伞行》之外,还有河北梆子《人民英雄纪念碑》和长沙花鼓戏《蔡坤山耕田》等,它们都是国家艺术基金资助创作的优秀作品。
河北梆子《人民英雄纪念碑》从20世纪50年代北京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往事中选择了一个巧妙的切口,将思想与文化的魅力融为一体,叙述河北某县大石村石雕匠人世家参与纪念碑建造的曲折故事。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极具爆发力的王英会、王洪玲两位优秀表演艺术家,在剧中将梆子唱腔酣畅淋漓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为该剧营造了强烈的情感冲击力。编剧通过虚构的大石村,和村里石、张两个手艺最好的石匠世家,让他们两家世代累积形成的难解的心结,成为主人公石老爹是否参加纪念碑建设的情感阻力,为擅长浮雕的石老爹最终加入纪念碑建造者行列营造了充满戏剧性的冲突,建构了令观众难忘的感人情节,塑造了生动的人物形象。
《蔡坤山耕田》作为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助剧目,荣登2019年度国家艺术基金滚动资助剧目的榜首。这个既令人意外又在情理之中的结果,包括了太多令人咀嚼的内涵。该剧由于具有非常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浓烈的民间趣味,为观众喜闻乐见。其主创人员包括湖南国家一级编剧吴傲君、国家一级导演韩剑英和优秀青年演员朱贵兵、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叶红等。剧情内容是微服出访途中饥肠辘辘的正德皇帝偶遇为农夫蔡坤山送饭的媳妇,因为吃了碗红薯饭感觉香甜无比,于是生出一系列笑料百出的事件。剧中朱贵兵丑扮的蔡坤山和叶红扮演的蔡妻,均典型地体现了花鼓戏里小戏的风采,全剧充满乡村气息的风趣与诙谐,县老爷和师爷的表演也同样非常出彩。在这个喜剧作品非常稀缺的时代,这部看似并不涉及多么深刻的思想、也没有宏大主题的作品,却因为传统与民间文化资源成功的当代转换,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在2019年度国家艺术基金滚动资助剧目名单里,还有吕剧《大河开凌》和淮剧《送你过江》等。《大河开凌》讲述的是中国最早版本的《共产党宣言》在鲁北农村经历几度战争的烽烟,终于完好地保存至今的传奇经历。该剧主人公迷糊是身份低微的长工,因无意中救下他东家的女儿——共产党员刘新雨,由此接触到《共产党宣言》,并且在后来的日子里,通过他和《共产党宣言》从偶然相遇到搏命呵护的过程,逐渐领会和理解了《共产党宣言》的精神内涵,完成了人物由普通人向革命者的转化。无论是剧中的主人公迷糊,还是女主角刘新雨,都有质朴的初心,并且透过对中国社会和普通人生日渐深邃的理解,折射出《共产党宣言》所表达的社会理想指引中国革命的现实意义。江苏盐城市淮剧团创作演出的淮剧《送你过江》,写的是解放战争渡江战役中支前民工的故事。用剧作家陈明的话说,在渡江战役这个背景下,他把一个江边女性的人生经历、命运浮沉、情感抉择,有机地植入到坚定的革命信仰与常人俗情世理的冲突之中,所以才有了该剧的情感力量。剧中仿佛处于次要位置的江老大形象,尤其具有生动传神的感染力。他心甘情愿地要为渡江贡献力量,但又如同所有平凡的百姓一样,还要顾全家人的生计和血脉传递,该剧就在这两者的冲突中完成了这位老船工的形象塑造。
在2019年度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的戏曲剧目中,闽剧《生命》和晋剧《起凤街》都名列前茅,同样都有其突出的情感表达。在闽剧《生命》里,2019年刚刚获得“文华表演奖”的周虹在剧中扮演一位因身心创伤而对爱与性心怀拒斥的青年女性,命运偏偏让她带领和保护一支孕妇队,在和这批婆婆妈妈的孕妇相处的过程中,她逐渐被人间的母爱所融化,感受到了孕育着新生命的母亲的伟大。几乎所有表现女性革命者的文艺作品,都将笔墨用于描写她们如何从个人家庭生活的私人情感领域走向为人类解放事业而献身,从柔弱的普通女性成为坚定的革命英雄,而闽剧《生命》却选择了一个截然相反的向度,周虹扮演的陈大蔓从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经历,同样令人动容。晋剧女老生谢涛在《起凤街》里扮演一家炝锅面店的女老板,从一个侧面呈现了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社会的巨变,而这位女主人公的善良、坚毅和胸怀,更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总之,国家艺术基金的设立以及对戏曲的重点支持,在全国各地各戏曲剧种的创作中所产生的推动作用,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当然,正由于每年接受资助项目的数量较大,相对而言,有关艺术质量的争议难免随之而来。如果只聚焦那些最优秀的戏曲新作,人们会比较倾向于高度肯定国家艺术基金推动戏曲创作的积极作用。但如果只聚焦那些质量堪忧的作品,就容易抱怨其近乎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此外,在戏曲演出市场严重失衡的背景下,已经开始出现一些令人不安的迹象,比如某些俗称“吃基金饭”的剧团,他们很快发现申请国家艺术基金远比培养观众、开拓市场要轻松容易得多。对基金的依赖程度日益增高,极易导致一种畸形的剧团运营模式的出现,这对戏曲发展而言绝不是好现象。当然,如何提升基金资助项目的水平,不完全是基金的职能,关键在于戏曲界本身。
“传记剧”成为戏曲新流行
从古希腊的悲剧,到中国的元杂剧,戏剧无不被看成是一种通过叙事表达思想情感内涵的艺术体裁。明清传奇每每用“某某记”作为剧名,尤其突出地体现了它以叙事为主的文体特征。然而在刚刚结束的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上,有专家戏称,本届艺术节的演出犹如近年电视流行的“真人秀”,意指艺术节参演剧目里,有太多以“真人真事”为题材的作品,其中更以“真人”题材为其显著特点。确实,本届艺术节17部戏曲剧目中,居然有多达九部剧目是以真人真事为内容的。其中最集中的是当代英模,包括河北梆子《李保国》、黄梅戏《邓稼先》、沪剧《敦煌女儿》、黔剧《天渠》、秦腔《民乐情》等,都是此类剧目;苏剧《国鼎魂》和豫剧《重渡沟》虽然并非表现当代英模,但同样是以真人真事为题材的作品。此外,还有像《钦差林则徐》等以历史名人和《杨靖宇》等以抗日英雄为题材的作品。
将各地的历史文化名人或英雄模范搬上舞台,借戏剧形式弘扬他们的事迹,这样的创作模式在戏曲界早就具有普遍性,只是在最近数年里显得尤其集中和突出而已。如果我们忽略“真人秀”这种明显的调侃称谓,更认真严肃地看待此类作品,或可将它们视为某种意义上的“传记剧”。这不仅是由于它们均以真实人物为戏剧表现内容,更因为相当多的类似剧目,都采取从戏剧主人公的一生中撷取数个阶段来表现其功绩的结构。这种类型的剧目,其动机往往是要通过戏剧的方式为某个人物撰写传记,其内容也基本是传记的布局。
具体而言,在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的参演剧目中,豫剧《重渡沟》写的是河南基层乡干部马海明的事迹,黔剧《天渠》以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荣誉称号的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黄大发为原型创作,黄梅戏《邓稼先》展现了“两弹元勋”邓稼先承担原子弹、氢弹研制的事迹,沪剧《敦煌女儿》再现了樊锦诗以坚韧柔情润泽戈壁大漠的传奇人生,河北梆子《李保国》更是以英模人物李保国帮助农村种植果树为内容,获“文华大奖”的苏剧《国鼎魂》则描写了苏州收藏世家掌门人潘达于的人生经历。其实不仅中国艺术节,第十六届中国戏剧节同样如此。在所有30部演出剧目里,几乎完全以人名为剧名的戏曲剧目,就有豫剧《张伯行》、越剧《林巧稚》、京剧《游百川》、川剧《江姐》、弋阳腔《方志敏》、丝弦《大唐魏征》和淮剧《武训先生》七部,已经超过四分之一。还有不以人名为剧名,却更类似于传记剧的黄梅戏《不越雷池》等。而以历史文化名人或英模人物为题材的戏曲新剧目远远不止于此,如果我们纵览每年的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和文化部门有关剧本扶持项目的选题,同样会看到其中名人题材剧目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如此多的人物传记题材戏剧作品出现在一次艺术节和戏剧节上,决非偶然现象。我们要“浓墨重彩记录英雄、塑造英雄,让英雄在文艺作品中得到传扬”[1]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2016年11月30日)》,《中国文艺评论》2016年第12期,第8页。,但在创作中也要尊重艺术规律、注重演出效果。值得讨论的是,这些剧目不只是在表现某人的英雄模范事迹,多半是以传记的方式在舞台上描述与表现他们的一生。各地不约而同地创作大量的“传记剧”,当然不完全是戏曲艺术家们的自然选择,更不是出于戏曲演出市场的需求。从创作者的角度看,如同我数年前在《剧本》杂志发表的一篇题为《写人与写事》[2]傅谨:《写人与写事》,《剧本》2009年第1期。的文章里所说,对戏剧“塑造人物”之功能的错误理解(与之相伴的就是对戏剧化叙事所擅长的情节结构的鄙视),无疑是导致当代戏剧家错误地用戏剧形式为人物立传的原因。当然无可否认的是,更具支配性的因素,是当下的戏曲创作在很大程度上为各地方宣传当地名人或英雄模范的动机所左右。从这个意义上说,真人真事题材盛行的现象,“传记剧”盛行的现象背后,主要是各地借戏曲新剧目创作营造地方形象的诉求在推动,这些当然都不是艺术的或市场的理由。
在“传记剧”盛行的背后,明显有戏剧艺术功能“工具论”的影子,它给戏曲新剧目创作带来新的困惑。由于当下戏曲自身的生存发展能力有限,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争取财政经费的支持,就更难逃脱“工具论”的摆布。这或可看成当代戏曲的宿命,而假如戏曲院团改制继续延滞不前、演出市场仍未得到有效修复,戏曲就很难回到艺术和市场的轨道上来。因此,“传记剧”的盛行只不过是表象,就像地域题材的风行一样,在它背后有无数值得深思的动因。促成变化的主导权并不完全在戏曲界手上,实为牵涉面非常之广的系统工程。
总之,2019年的戏曲发展,仍体现了逐渐回归本体的可贵迹象,而最终实现这一目标,还需要经历一个多通道并进的复杂过程。除了在表演上坚持戏曲化的原则,坚守其美学上的风格与特色,还需要通过多样化的题材选择,正视戏曲内容丰富性原则的意义。在传统剧目赓续和新剧目创作过程中,表演者的主体作用应该得到更直接的彰显。最后,在题材选择上,还应更多地尊重艺术与市场的逻辑。所有这些都是戏曲“本体”的题中应有之义,而要回归这一“本体”,前行的路并不平坦。历史与现实给予我们太多经验与教训,只要经常汲取经验,记取教训,戏曲就能越过所有坎坷,迎向光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