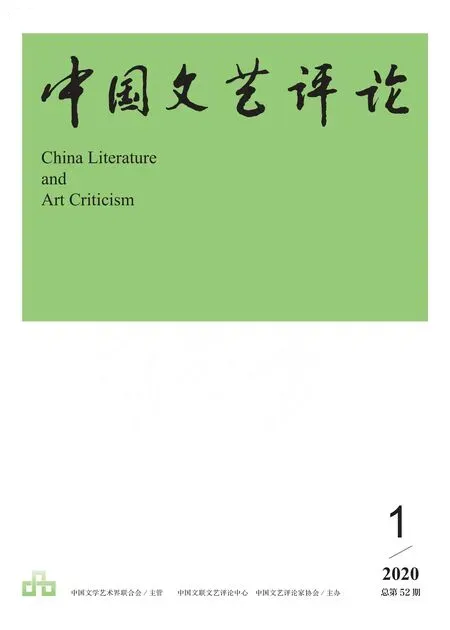构建面向“美好”的生活美学范式
——以新世纪以来中国城市电影为例
林 玮
晚近以来,生活美学成为哲学转向的主潮之一。事实上,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哲学在“语言论转向”之后,其主流面貌就始终暧昧不明,众多学术取向(身体转向、视觉转向、空间转向、文化间性转向、人类学转向、符号学转向、物质转向等)纷纷登场;但与其不同的是,“生活论”转向带有整合此前诸取向的雄心,力图以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作为囊括身体、视觉、空间等视角的哲学基础,形成理解、阐释世界的一种体系化哲学思想。从对象上看,它把日常生活所涉及的基本领域都纳入了审美范畴,极大地扩展了美学原本作为艺术哲学的学科外延;从主体经验来看,生活美学试图打破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将纯粹的审美经验泛化为日常的生活经验,从而使生活呈现出另一颜面。
《布莱克威尔美学指南》指出,生活美学(Aesthetics of the Everyday/Everyday Aesthetics)乃是将“纯艺术经验与其他生活经验联系在一起的指认”,“那些与艺术或自然并无本质关联的对象与活动同样具有审美品质(aesthetic properties),并且/或者可以引起显著的审美体验。由此,美学分析被恰当地扩展至几乎所有生活领域”。[1]IRVIN, SHERRI. "aesthetics of the everyday." A Companion to Aesthetics: Second Edition. Davies, Stephen, Kathleen Marie Higgins, Robert Hopkins, Robert Stecker and David E. Cooper (eds).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9. Blackwell Reference Online. 12 July 2013.然而,也正是在其试图包举人类“几乎所有生活领域”的理论野心上,“生活美学”很容易“过于笼统而又缺乏具体范式内涵,因而实际上是无意义命题”。但毕竟生活美学“从重新关注生活来看具有一种合理性”[2]王一川:《物化年代的兴辞美学:生活论与中国现代美学II》,《文艺争鸣》2011年第1期。另可参见王一川:《中国诗学现代II刍议:再谈中国现代性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王一川:《中国现代I文学与现代II文学的断连带》,《文艺研究》2008年第4期;王一川:《革命年代的心化美学:简论中国现代美学I及其传统渊源》,《江海学刊》2011年第2期。。这种合理性能否上升为学理性,进而回应中国当代文艺创作与理论建构?特别是在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型的时代语境中,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内在地成为“生活美学”重构的动力和契机。而如何理解“生活”的美的质感,是需要理论创见与阐释的。本文尝试以新世纪以来的城市生活电影为例,对已有的生活美学理论加以梳理,并提出构建面向“美好生活”的存在论生活美学的可能性。
一、“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消费美学
如果生活美学仅是指称以生活为审美对象的门类美学,那在中外美学史上都不罕见,将人的感性体验作为研究对象,必然涉及日常生活。因此,一般美学教材大多专列“社会美”或“生活美”的章节,与“自然美”“艺术美”“科技美”等并列。[3]如陈望道:《美学概论》,广州:民智书店,1927年,第122-125页;胡连元主编:《美学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08-116页;叶朗:《美学原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02-231页;彭富春:《美学原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95-100页。但这不过是将生活视为审美的对象之一,难以构成一种自洽的学理性范式。[4]较为典型的例子是成远镜、朱晶编著的《生活美学》(湖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它包括人体、服装、饮食、建筑、旅游等内容,是一本实用性很强的“生活指导手册”;相关批评参见刘悦笛:《“生活美学”:是什么与不是什么?》,《艺术评论》2011年第4期。毋宁说,把“生活”当作人类社会实践众多领域之一的美学观,仍是本质论美学,即认为在生活、自然、艺术、科技等平行范畴之后,存在着一个统一的本体“美”。经过现象学与后现代思潮洗礼的“生活美学”转向,与此当有根本不同;更为显而易见的是,进入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生活”本身经历了消费主义的冲击,其美学价值也得到了新的理解。
从历史逻辑来看,生活美学在晚近中国的“重新发现”,与新世纪以来中国兴起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讨论关系极大;而西方学界对生活美学的讨论也出现在“文化研究”之后。[5]一般认为国内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争始于2001年周宪和陶东风的相关文章,国外讨论则由1985年费瑟斯通所提出,而文化研究则始于20世纪50年代;也就是说,作为文化现象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在中国的兴起基本开始于中国现代II时段。参见赵勇:《关于文化研究的历史考察及其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艾秀梅:《“日常生活审美化”争论述评》,《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王德胜、李雷:《日常生活审美化在中国》,《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第1期。因此,不少人把“日常生活审美化”当作“生活美学”的当然范式。它主要讨论现代商业生活中所出现的审美现象,从广告到装潢,从服装设计到城市规划,“现实中越来越多的方面被审美所覆盖,现实已经成为一种审美的构造”[1]Wolfgang Welsch, Undoing Aesthetics, translated by Andrew Inkpin,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1997, p 1.。这种审美构造主要以符号为对象,机械复制且日益增多的符号在市场操纵下,伸手摘下了艺术的光晕,抹平了人的真实感受与被创造出来的虚假感受之间的差异。因此,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主要以批判为美学旨趣,力图揭示现代社会中看似审美泛化、审美自由之后所隐匿的权力关系。
这在新世纪以来的电影美学中,主要表现为对“新都市电影”的指认与批判。“新都市电影”中城市往往被看作是物质富裕的象征,引导人们单向地朝着物的交换价值聚拢。如《小时代2:青木时代》(2013)中,顾里大学毕业时用三大卡车把其所有“物”从大学宿舍拉进她在上海市中心租住的别墅中。在装行李的卡车上,三个女生不但“被物包围”,还从容地打开香槟,倒入高脚杯中对饮。这辆卡车顿时构成了一个与世隔绝(周围是搬运工人的劳作场景)的“小世界”,她们无法构成普遍意义上的日常生活。更有意味的是,她们的“小世界”中的生活是按照占有物的逻辑来排列情感交往(友谊)的。顾里之所以成为她们的中心(女王),是因其富有;而反复出现的林萧、唐宛如用虚拟王冠给顾里加冕的细节,则明示了林、唐的从属位置——不仅在“经济”上(顾里总为她们花钱),也在微观“政治”上(顾里总安排她们的生活)。如果说这仍是一种生活现象而非价值判断,那么,《小时代》系列中“顾里总是对的”的剧情安排就无疑显现了“新都市电影”导演的价值取向。
而“新都市电影”对日常生活的表征,也往往以“物”为标签,以消费划分群体。陈正道导演的《101次求婚》(2013)的序幕画面就并置琴弦和锯子、Iphone和拨号座机、兰姿挎包和工具包、全英文菜谱与小饭馆菜单、龙虾意大利面与雪菜面、刀叉与筷子、红酒与开水、信用卡与零钱、香水首饰专卖店与便利店等一系列对立的“物”,来表现出叶熏和黄达之间近乎不可逾越的阶层差距;李蔚然导演的《我想和你好好的》一开始就是一场兰博基尼与普通轿车的狂飙角逐,同样标示了富二代和蒋亮亮之间的阶层界限。正如布迪厄所言,将“纯粹美学”原则“运用于日常生活中最日常的事项(如烹饪、服饰或装潢)……是一种最具区隔性、最使其与众不同的能力”。[2]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trans. Richard Nice, London: Routledge,1984, p.6.这些充满日常生活意味的物——尤其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美食、香水、酒、车等物品,极大地彰显了群体/阶层差距。
这种生活美学,无疑可以用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大众文化研究来加以批判。在这里,“日常生活审美化”与大众文化研究便共享一套批判取向,剑锋所指本都在文化或审美现象之后的意识形态与市场权力,亦即是工具理性对人的全面异化;或者干脆说,“日常生活审美化”讨论本就是作为大众文化研究的分支而出现。在这里,传统“审美无功利”的精神超越美学几乎没有立锥之地,其研究指向从酒吧到手游,从可穿戴设备到智能家居,符号替换了“日常生活”的全部内核,日常生活被等同于视觉上的“物的包围”[1]Katya Mandoki称其为“美学的恋物癖”(The fetishes of aesthetics),并分为“美的恋物癖”(the fetishes of beauty)、“艺术品的恋物癖”(the fetishes of artwork)和“审美对象的恋物癖”(The fetish of the aesthetic object),参见Katya Mandoki:Everyday Aesthetics, Burlington: Ashgate, 2007, pp.7-12.。
而被物包围的生活固然“美”,但未必“好”——前者是感性层面的,后者是伦理层面的。它忽视了“生活”本身的丰富性,特别是人的情感表达及其交往在生活中本该占据的主导位置,而以纯粹的感知觉(尤其是视觉)作为美的内容。这种生活美学的研究范式也不以审美体验(美感)为核心——这是传统美学关注的重点[2]参见吕征:《美学浅说》,北京:商务印书馆,1926年,第6-25页。日裔美籍学者斋藤百合子在对日常生活美学的讨论中也指出,以艺术为中心还是以审美经验为中心是现代美学的两大基本方向;而生活美学则应将此二者统一起来。参见Yuriko Satio, Everyday Aesthe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2.,而是重视审美体验的可操纵性及其操纵策略,甚至可能自反为其批判对象的吹鼓手。这是“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生活美学范式的本质欠缺,它只能改善物质生活,而无法构成“美好生活”的基础。
二、“为艺术而生活”的艺术化生活美学
作为商业化生活美学范式对立面而出现的是唯美主义,其在中国早期的代表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周作人、张竞生等人提倡的“为艺术而生活”或“生活之艺术”。在电影美学上,这种生活美学的主张是刘呐鸥的“软性电影”,即“电影是给眼睛吃的冰激凌,是给心灵坐的沙发椅”[3]石恢:《三十年代“软性电影论”检视》,《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晚近以来,这种艺术化美学的目的日益倾向于指导生活如何变得精致且美(Beauty),以此来对抗“市侩现代性”[4][美]卡琳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52页。。如插花、茶道、香道等带有强烈生活化表征的美学形态,都是其代表。它与“日常生活审美化”范式的不同在于其精神高度超越的心化特征,它极其“治愈”而空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竞生才会说:“凡一切人类的生活:如各种工作、说话、做事、交媾、打架等等皆是一种艺术。”[5]张竞生:《美的人生观》,《张竞生文集》(上卷),广州:广州出版社,1998年,第28页。
艺术化生活美学所影响的电影,擅长把城市生活拍得极其唯美,给“物”中注入满满的情感。如张一白《关于爱·上海》(2005)这个仅有33分钟的“微电影”,出现了三次小蕴在天台上收取修平晾晒的白衬衣的场景。第三次的情感注入最为显豁:在咖啡店,小蕴告诉修平,她妈妈邀请他赴席,为他返回日本送行,修平因有事而婉拒了;这时天降暴雨,小蕴忽然飞奔出咖啡店,冒雨骑单车回家,直奔天台收起修平晒的白衬衣;小蕴在雨中抱着湿透的衬衣哭泣,画外音是雪子寄给修平的分手信——这显然可以视为小蕴与修平情感沟通的“结尾”,而这一结尾却是由前两次“天台收衣”的场景作为铺垫的。尽管观众在线性叙事的观影过程中未必能体会到这一点,但前两次“白衬衣”看似日常、随意的出现却已经蕴含了小蕴的情感(心)与白衬衣(物)之间的关联。以第二次的场景为例:
这个20秒的影像段落共有七个镜头,可分为四组:(1)风把衬衣吹落,蒙在了小蕴的脸上(两个镜头);(2)她透过衬衣看到急急忙忙跑上来的修平(两个镜头);(3)修平一面道歉,一面取下小蕴脸上的衬衣(一个镜头);(4)小蕴用手遮着阳光,修平仍在道歉(两个镜头)。第(2)(4)组镜头均为小蕴隔着衬衣看到修平的近景,第(3)组镜头则是小蕴脸上蒙着衬衣的鼻唇特写,也是她与象征了修平身体的衬衣之间唯一的一次感官接触。第(2)(4)组镜头与此前修平在拆开雪子寄来的包裹和分手信时,小蕴坐在他身旁,举着一杯水,透过玻璃杯凝视修平的痛苦表情极为相近——“隔杯窥人”与“隔衣窥人”所得到的视觉效果并不清晰,但正是这种模模糊糊且隔着中介物(杯子、衬衣)的意象暗示了高中生小蕴对日本进修生修平的暧昧情感。在这里,生活被电影框定在美的单维中。
由此,无论是周作人“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1]周作人:《北京的茶食》,《雨天的书》,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第41页。,还是张竞生“自衣食住至一切的物品器具”“一切家常日用的物品”[2]张竞生:《美的人生观》,《张竞生文集》(上卷),广州:广州出版社,1998年,第28、31页。,都可以被表现得极为艺术,带有精神超越之感。只是,这种感受一方面很可能被商业化操纵,如各种挂着“生活美学”之名的培训、灵修、旅游,而另一方面这种完全将刺痛感、震惊感、敬畏感,甚至恐惧、恶心、悲悯完全排除出“美”的范畴之外的生活美学,显然是不够真实的。它并没有真的把一切形态的日常生活视为审美对象,即便标举“一切关于人生的事情皆是一种艺术化”的张竞生也认为“丑恶的物质生活”与“疲弱的精神生活”并非美的存在,他所主张的服装也只是低领、高跟鞋的“洋女装”[3]同上,第28、40页。。这不但充分显现出艺术化生活美学的保守性,也使其缺乏更为广阔、深刻的哲学基础与生活视野。
三、第三种生活美学范式的可能性框架
上述两种“生活美学”范式(如果存在范式的话)存在着互相关联的局限性,即其观点的核心是美学应该始终围绕漂亮、愉悦且具体的“物”而展开:第一种范式因为过分接近物,而“表现出工具理性对人更为彻底的操控”;第二种范式又过分远离平常的物质性之物(商品),“因而也更加远离物质生活的喧哗与骚动”[1]周小仪:《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18页。。而这看似相反的对立面暗通款曲,才使王尔德、邓南遮、梅特林克等人成了“文化产业的先驱”[2][德]阿多诺:《美学理论》,王柯平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08-409页。(译文略有改动)。晚近以来,这两种生活美学范式的合流,更被抬到显学地位——社会上以茶道、花道、香道等为代表的餐饮、休闲、旅游美学,至少在表现形式上多半是这两种范式的结合。其成立固然有其复杂的时代性和历史缘由,但美学作为“所有支配性思想或工具主义思想的死敌”这样一种思路[3][英]特里·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王杰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0页。,实在难以在上述两种生活美学范式中从容地展开。这使美学本身失去自由。
其实,从西方美学史来看,先锋派的艺术实践也意味着唯美主义不可能是一种真实意义上的生活美学。与真实的生活美学相反,在先锋派看来,唯美主义应该是一种完全与生活脱节的“艺术体制”,它和审美经验的纯粹化一并构成“资产阶级社会中艺术发展原理的两个要点”;而“先锋派的抗议,其目的就在于将艺术重新结合进生活实践之中”[4][德]比格尔:《先锋派理论》,高建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88页。。日常生活是复杂的容器,包含两种不同的体验:“既是百无聊赖,又是神神秘秘”,先锋派正是将这两种体验同时加以呈现,才形成了一种陌生化与震惊的美学效果[5][英]本·海默尔:《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导论》,王志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40-42页。。这就出现了一条有趣的美学自反性路径:唯美主义(在自律、非功利等层面上与现代主义相通)反对“市侩主义”,先锋派又反对唯美主义。吊诡的是,先锋派借以反抗艺术自律的资源,很大程度上就是“市侩性”:一种陌生化了的市侩现代性,它是一种“同自然的永恒崇高和传奇式中世纪过去的辉煌相反的”粗俗、乏味,“对物质价值摆脱不了的关心”[6][美]卡琳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50页。。
“日常生活审美化”与“为艺术而生活”都无法概括先锋派的艺术实践,这就为第三种生活美学范式提供了可能。先锋派虽极力模糊生活与艺术的界限,可其实践却仍是一种“艺术(品)”,而非生活。当杜尚宣称任何物体一经标记便可成为艺术品时[7][英]史密斯:《西方当代艺术》,柴小刚等译,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2年,第23页。,这“一经标记”就意味着“物”脱离了生活而得到某种艺术体制的认可,从而获得了外在于日常生活的美学价值——在这一意义上,先锋派的艺术品所具有的生活色彩,甚至还不如“日常生活审美化”范式中的具有高度文化附加值的商品。因此,第三种生活美学也无法囿于先锋派艺术中,而必须扩大视野,将生活本真作为审美对象,使日常生活呈现出美感。
于此,可以加以引述的是马克思对生活的理解。在他那里,“生活”本身叠加着“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双重状态,“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搏斗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式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1][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28-929页。。在“必然王国”中,真实甚至残酷的生活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虽然对审美来说,真实生活的“必然王国”之上还存在着“自由王国”,但真实是“自由王国”的基础,是其审美来源。因此,马克思对“真实”有着虔诚的信仰,无论他对伦勃朗的批判,还是对巴尔扎克的赞同,都暗含着对“真实”的高度认同。这种审美取向被恩格斯直接地表述为“现实主义”,它要求“具体生活和富有生活气息”[2][德]恩格斯:《现代文学生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3页。。因此,可以说,马克思的生活之“美”即在于“真”——而前文所谈及的两种生活美学范式危险之处恰在于易流向“假”[3]如马尔库塞所言,“现行的大多数需要,诸如休息、娱乐、按广告宣传来处世和消费、爱和恨别人之所爱和所恨,都属于虚假的需要这一范畴之列”。参见[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6页。,或变成商业助推的“伪情感”,或附庸风雅的“装腔作势”——这与中国美学中“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王国维《人间词话》)的传统,是内在相契的。他们一者倾向“真”的批判性,一者倾向“真”的超越性,却不约而同地把“真”视为“美”的第一要义。
以真为美,是主体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能激发起深厚的情感,即所谓“兴”。但对具有社会关怀的生活美学来说,“兴”只是基础,在“美”之后还有“好”。前者是主体自我情感的兴发,后者则是个体情感的沟通与关联。中国古代“乐主和同”的美学思想,将此视为常识。而马克思也认为在生活“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无论“自由王国”的彼岸有多远,“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28页。。由此可以拓出面向“美好”的第三种生活美学范式,即当代中国的“生活美学”。
仍以中国城市电影加以说明。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生活美学”首先崛起的是对“真”的认识。第六代导演的作品就多以城市生活为表现对象,他们不试图讲述完整的故事,而将生活流直接映于银幕之上。这种近乎未加修饰的生活可以被认为是悬置了此前电影中常见的以民族国家为重心的现代性体验,转而基于日常生活立场,传达生活的原生态体验[5]陈旭光:《电影文化之维》,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173页。。而从第三种生活美学的角度看,第六代导演的美学意义恰在于,将生活的复杂面相予以本然的揭示,即显现其“真”。如表现“物”的复杂性,其宏观层面是“世界”,微观层面则是“金钱”。贾樟柯的《世界》(2004)在整体上就构成了对“物”之宏观的反讽。在世界公园和公园人际关系的全球流动(俄罗斯来的外籍演员、赵小桃前男友去蒙古、成太生的情人去法国等)下,个体的渺小又在“物”的微观层面(金钱)上得到表现——三赖为个人私欲盗窃同事财物、大老板以金钱诱惑赵小桃、“二姑娘”为赚钱加班而意外身亡。电影中,城市的“打工者”在“世界”中随波逐流的生活,是如此的真实,甚或残酷,也成了观众反思自我的契机。这种强烈突出“真”的“新都市”电影,曾赢得过国际影坛与中国观众的广泛赞誉,在依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天注定》(2013)中达到顶峰。
而强调在“真”的兴发感动之后,还有“好”的城市生活电影也开始受到关注。如顾晓刚的《春江水暖》(2019),就在真实(美)的基础上注入了情感关联的强烈效果(好)。故事以同母异父的四兄弟围绕赡养母亲而展开,横向上四兄弟之间的相互关联与纵向上祖孙三代人之间的相互关联,以及由此生发出顾喜与江一的恋爱等情感关系,甚至老四与陌生人的情感关联,都可以通过其诵读信件表现出来。所有这些纵横交错地构成了整部电影的叙事主流。在电影中,无论人际关系如何冲突,最终都能归于生活的平静与和谐,就如同电影开篇顾家老大与妻子的争执,两人吵着吵着就笑了。电影聚焦作为中国传统生活美学象征的“富春江”两岸,显然有把“和为贵”的意识贯穿其间的考量。
这种从生活本身出发,通过情感激发,最终产生情感关联的生活美学,在新世纪头十年之后,逐渐沉淀为“美好生活”的理念与核心。以第六代导演为例,王小帅在拍摄《十七岁 的 单 车》(2001)、《二 弟》(2002)、《青 红》(2005)、《左右》(2007)等电影时,都以残酷的撕裂情感关联为其激活主体情感意识的“由头”,甚至最可能产生情感关联的父子、夫妻都难以和谐;而到了《地久天长》(2019),连最不可能达成和解的弑子之仇都可以通过情感关联而获得圆满。这不得不说,一种面向“美好”的生活美学范式正在生成:它以“真”为“美”,以“善”为“好”,最终通向理想的社会生活形态。
如果说新世纪之后以第六代导演为代表的中国城市电影彰显了一种求真的生活美学,其着眼于“美好生活”的不可实现性,凸显的是人在工业化景观中的荒诞与异化,姑且可以成为“生活存在论转向”的话,那么以2013年(《天注定》与《小时代》的上映)为分界,中国电影电影就开始出现了“生活美好化转向”。这种转向高度维系于主体的自觉,它要求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生活的本真之美,并投身于对它的调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