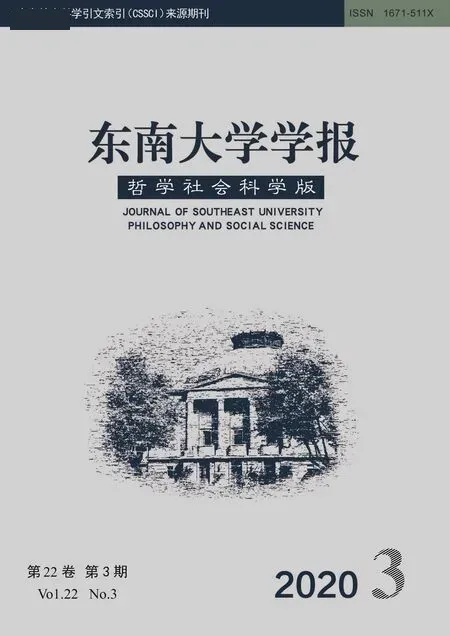“乌合之众”及其改造:西方现代戏剧中的“大众”问题
高子文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戏剧理论家布罗凯特(Oscar G.Brockett)认为,西方现代戏剧的诞生与社会学的创立有着紧密的联系,他写道:“在(戏剧的)所有这些改变观念的影响中重要的是孔德……他认为社会学是科学的最高形式,所有知识最终都应该被用于促进社会进步。”(1)Oscar G. Brockett, The Theatre: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4,p.332.19世纪中后期,“大众”(mass)作为新出现的研究客体,一方面成为社会学所关注的对象,另一方面也成为西方现代戏剧的描绘对象。易卜生在《人民公敌》中最早表现出对“大众”的质疑。在这个戏的结尾,小镇居民通过不记名投票,(除一个醉汉外)一致认定揭发浴场污染真相的斯多克芒医生为“人民公敌”。易卜生借男主角的口写道:“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正是最孤立的人。”(2)易卜生:《人民公敌》,《易卜生文集》,潘家洵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400页。在西方现代戏剧中,易卜生这种对“大众”的批评并不是偶然的,在他之后,众多剧作家表达了与此类似的主题。而易卜生所处的时代同时正是“群众心理学”创立的时代。“群众心理学”把“大众”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大众”的特性,质疑“大众”的正当性。由于“大众”概念与民主观念紧密相连,涉及西方现代文明的根基,因此,从戏剧学视域进入,考察西方现代剧作家如何呈现“大众”,如何判定“大众”的价值,能够为我们更深地理解西方现代文明的构成提供一个切入口。
一、作为“乌合之众”的大众
从文化史看,在19世纪前,戏剧作为众多艺术门类中的一种,并不是以表现“大众”为目的的。戏剧主要处理的是个体的激情,以及这种激情所包含的社会的、伦理的、哲学的内涵。“大众”这一对象较少地出现在戏剧之中。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戏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3)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9页。。而“大众”很难作为某个具体行动的主体,它只能作为主体发生行动的背景。比如,古希腊戏剧中的歌队。歌队一般由十二到十五人组成,他们可以是忒拜城的长老、特洛伊的妇女,或一队酒神的信徒。作为背景的“大众”因此往往是善的,或至少是公正的。他们对戏剧主人公的行动加以评判和感叹。歌队与角色之间的对话,体现了有缺陷的英雄与大众之间的沟通,而歌队从来不曾作为一种恶的存在被古希腊剧作家所表现。从文艺复兴开始直至19世纪,西方戏剧对大众的描绘几乎一致地站在肯定与颂扬的立场。(莎士比亚的《科里奥兰纳斯》是一个特例。)大众总是代表着正义的一方。对贵族精英的嘲讽,对民众力量的肯定是西方戏剧艺术发展的主要线索。
法国社会学家勒庞(Gustav LeBon)这样描绘他的时代(19世纪后期):“民众的各个阶层进入政治生活,现实地说,就是他们日益成为一个统治阶层……群众现在成立了各种联合会,使一个又一个政权在它面前俯首称臣。他们还成立了工会,不顾一切经济规律,试图支配劳动和工资。”(4)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7页。在一个世纪前的启蒙主义者眼里,这样的状况几乎是他们的理想,社会终于落入了大众的手里,而不是少数几个贵族或者僧侣的囊中。然而勒庞对此却并不这么想:“它(大众)全然不知怀疑和不确定性为何物。”“在群众中间,傻瓜、低能儿和心怀妒忌的人,摆脱了自己卑微无能的感觉,会感觉到一种残忍、短暂但又巨大的力量。”“个人一旦成为群体的一员,他的智力立刻会大大下降。”(5)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7-69页。在他看来,个人一旦聚集起来形成集群,就会立刻失去自己的个性,丧失独立思考和理性判断能力,在剧烈情感的冲击下,大众冲动、多变、急躁、易受暗示、偏执和专横(6)刘国强、汤志豪:《去蔽勒宠:身体规制与多维的集群“非理性”》,《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1期,第134页。。因此,民众对国家的控制、对社会的掌握的事实并不必然地导向一种正义的,或者善的政治,相反,因为大众的这种 “乌合之众”的特质,恰恰可能带来巨大灾难。西方现代戏剧与“群众心理学”在这一问题上似乎达成了一致。
可以说,“大众”作为戏剧表现对象这一事件本身,与戏剧形式在19世纪中后期的现代转向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经过以狄德罗为代表的启蒙作家的努力,戏剧中的人物在18世纪后半叶即从贵族渐渐转向了普通市民。彼得·斯从狄(Peter Szondi)观察到易卜生戏剧的形式与其内容发生了矛盾,易卜生的戏剧中“过去本身成为主题”(7)彼得·斯从狄:《现代戏剧理论》,王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1页。。循着斯从狄的思路,人们发现,不仅“时间”成了新戏剧的内容,“大众”同样作为一种戏剧的新的表现对象出现了。可以说,正是现实主义戏剧将创作视野转向了社会与政治生活,“大众”才在戏剧中成为了表现对象与表现主题。
西方戏剧进入现代之后,剧作中这种对“大众”的怀疑越来越频繁地出现了。从社会学看,其中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当民主政治发展并不充分,它仍与古老的封建贵族政治进行角力的时候,它的缺陷显然不会那么轻易地被认知和表现;而当社会流通与信息传播的加速进一步强化了民主观念,使得“大众”最终成为政治力量的重要构成时,它所有特征才会真正显露出来。易卜生的《人民公敌》第一次明确地将主人公的悲剧归罪为愚昧的大众。易卜生更是推而广之,他指出大众的愚昧并非这一小镇的特例。斯多克芒医生对他太太说,即便搬到别的地方去,情况也一样,因为“全国的人都是党派的奴隶。我并不是说,在自由的西方情形也许会好一点,在西方,结实的多数派、开明的舆论和种种别的鬼把戏也许闹得跟这儿一样猖狂。”(8)易卜生:《人民公敌》,《易卜生文集》,潘家洵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382页。易卜生的这个作品里,斯多克芒医生是以全善的形象被群众无情毁灭的。它甚至让人产生这样一种观后感:斯多克芒正因其与大众的对抗而获得了一种英雄式的崇高。这在易卜生之前的所有西方戏剧中几乎不曾出现过。在过去的戏剧里,崇高往往属于那些为大众的福祉而战斗并牺牲了的人。
在易卜生之后,西方现代戏剧中的“大众”经常被描绘成“乌合之众”。最显著的例子有瑞士作家迪伦马特(Friderich Durrenmatt)的《老妇还乡》,英国作家萨拉·凯恩(Sarah Kane)的《费德拉的爱》。《老妇还乡》描绘的是一个贵妇回到她出身的居伦城,报复曾经抛弃她的恋人伊尔的故事。居伦的居民原本朴素、单纯,但在得知小镇有可能获得贵妇的捐赠时,一个个都变得自私、残酷。直至最后,小镇居民集体表决接受贵妇的捐助判处伊尔死刑。该剧与《人民公敌》的不同之处在于,迪伦马特把小镇居民这种由善转恶的状态作为剧本表现的重心,细致地刻画了大众在面对诱惑与道德之间的犹疑与最终对道德的放弃。在《出版后记》中,迪伦马特写道:“与男主人公相关的人都是和我们一样的人……他们那样做只不过是出于轻率,出于一种感觉,以为一切都会妥善解决的……那诱惑实在是太大了,整个居伦人都在这诱惑面前渐渐屈服了,连那位教师也不例外,但我不能不说,这种屈服是可以理解的。”(9)迪伦马特:《老妇还乡》,叶廷芳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267页。尽管迪伦马特在此似乎为“大众”做了辩护,但剧本所集中呈现的却是大众的“谋杀”行为。可以说,正因为这些居民原本如此普通,在他们集体沦为杀人犯的时候,才给人以如此强烈的震撼。
《菲德拉的爱》是对古希腊戏剧的一次改写,是为菲德拉与希波吕托斯之间的爱情做的翻案文章。该剧塑造了一个看透道德与宗教之伪善的哲人希波吕托斯。但是萨拉·凯恩的这种正面塑造却是以主人公对大众的轻蔑与拒绝来表现的。戏开始时,希波吕托斯颓废,堕落,了无生趣。直到菲德拉因为得不到他的爱而自杀,并留下遗书控告他强奸,才唤起他的生机。他认为菲德拉的爱是真诚的。为了挑战“大众”的观念,希波吕托斯坚定地承认与菲德拉之间的乱伦关系,肯定菲德拉的爱的正当性。在戏的结尾处,他被暴民们围攻打死,并被割掉生殖器,开膛剖肚。当他躺在地上看到头上盘旋的秃鹫来啄食自己的内脏时,终于获得了存在的愉悦,感叹道:“如果能再多一些这样的时刻该多好。”(10)Sarah Kane, Sarah Kane Complete Plays, London: Bloomsbury, 2015, p.103.希波吕托斯对虚伪道德的反叛为自己赢得了一种类似于普罗米修斯的崇高感,唯一的区别只在于,惩罚普罗米修斯的力量来自专制的宙斯,而这里,这种力量来自“大众”。
表现主义作家托勒(Ernst Toller)在他略显粗糙的作品《群众与人》中,对“大众”的形象及其原因做过很有意义的思考。剧中的 “女人”原本是革命群众的一员,呼吁大家罢工,对抗资产阶级。但她拒绝杀死作为资产阶级代表的丈夫,因此陷入两难中。剧本同时塑造了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 “无名氏”作为群众的代言人。而“女人”最终道破了群众的真相,她说:“群众不是神圣的。是暴力创造了群众。财富的不公正创造了群众。群众是贫困所产生的冲动,是信仰的谦卑……是残忍的复仇……是盲目的奴隶……是虔诚的意愿……群众是踩踏了的田亩,群众是掩埋了的人民。”(11)托勒:《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一册),杨业治、孙凤城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第578-579页。
二、“大众”改造方式:统治与启蒙
事实上,西方现代戏剧同时提供了另一种“大众”形象,尽管这类作品并没有像前者那样在西方戏剧史中获得经典的地位。比如霍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的《织工》和奥德茨(Clifford Odets)的《等待老左》。这两个作品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将“大众”限定于某一特定阶层的群众。因此,他们非但不是“乌合之众”,还是某种新的未来的创造者。
这类特殊的“大众”都生活于底层,他们是妓女、纺织工人、出租司机等等。尽管这类作品也试图提供这些人的个体差异,但在基本的道德判断上,他们则无疑是全善的。他们因其社会处境的不幸而获得了道德上的补偿。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的论述为这类人的道德优越性提供了理论支撑:“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一切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衰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12)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76页。列宁则表达得更直接些:“无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才是力量的源泉。无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才能保证为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13)列宁:《六月十八日》,《列宁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35页。他们显然具有强大力量,而在剧中这种力量也以群体暴力的方式呈现出来。这类“大众”所处环境的罪恶被剧作者预先设定了,因此他们的暴力就带有无可争议的正义性。正如《织工》中暴动领袖西克尔所说的:“咱们用好心拿不到的任何东西,就得用暴力去夺取。”(14)霍普特曼:《霍普特曼戏剧两种》,韩世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92页。这是一种抽象的正义。这些剧作大多数是为了宣扬一种既定的革命价值观,作家对于革命需要的认同和对底层的同情,阻碍了他们看到群体的不良特性。有趣的是,勒庞也曾写道:“群体可以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但是也能做出崇高的献身、牺牲和不计名利的举动,即孤立的个人根本做不到的极崇高的行为。”(15)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2页。这些作家也许正是体认到了革命事业的崇高,因此给予底层群众以浪漫的想象。
在这类作品里,大众中通常可能涌现出某个特殊的人物,成为大众的领袖,如《织工》中的西克尔、《等待老左》中的老左。他既是大众的代表,又具备控制大众的能力。他能把正确的世界观教给普罗大众,进而领导人们创造新世界。在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普列汉诺夫(Georgi Plekhanov)看来,易卜生的斯多克芒医生完全可以成为这样的人物。他认为斯多克芒的失败应该归咎于他自己的思想杂乱,他没有能够团结多数人:“进步的真正敌人,并不是他为了令无政府主义者高兴而大声疾呼加以反对的那个‘多数’,而仅仅是这个多数的发展不够,这是由于在经济上有势力的少数迫使他们处于依赖地位所造成的。”(16)易卜生:《易卜生文集》(第八卷),潘家洵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340页。照他的看法,如果斯多克芒医生能够团结那些从四面八方跑来这个城市治病的病人们,他就能够掌握多数,因而便可以取得这次斗争的胜利。普列汉诺夫因此非常蔑视易卜生在这个问题上的犹豫。在他看来,大众之所以被易卜生表现得如此糟糕,并不是大众本身出了问题,而是易卜生成长的社会环境使他目光狭隘,憎恶大众。普列汉诺夫拥有马克思主义者的自信,这种自信主要源于他相信已经掌握了真理,相信用这一真理统治“大众”的正当性,统治他们,进而改变整个世界。易卜生则选择了相反的道路,也许正是为了避免使主人公成为一个普列汉诺夫式的群众领袖,他把斯多克芒塑造成一位不与世俗合作的孤独者形象。
“群众心理学”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站在马克思主义作家这一边,研究者们提出,领袖对于群众的统治的正当性是应当被怀疑的。莫斯科维奇在《群氓的时代》中写道:“长期以来,这门学科冷峻地考察了我们这个时代,研究了人对人的无情统治,并且指出了领袖在大众社会中行使这种权力的手腕。我拒绝它的历史观,也怀疑它的真理性,但是我承认并接受这种现象。”(17)莫斯科维奇:《群氓的时代》,许列民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4页。在《乌合之众》里,勒庞总结了领袖动员群众的三个手段:断言、重复和传染(18)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0页。。他的这个总结显得比较温和。但仅仅是对温和的手段的描述,我们也能认识到在这一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形成中,正义并不总是扮演主要角色。莫斯科维奇注意到:“领袖总是充满着偏执的狂热,每一位伟大的领袖都是一位狂热者。”(19)莫斯科维奇:《群氓的时代》,许列民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2页。可以说,正是通过狂热者的某种暗示行为,群众获得了团结一致的行动力。在《菲德拉的爱》中,萨拉·凯恩完整地描述了这个操控过程。在最后一场戏开始时,群众只是偶然地聚在法院旁,有的只是带着孩子来野餐,他们并无暴动的计划。忒修斯在这时扮演了鼓动者的形象。
忒修斯:可能会按他喜欢的宣判。对不起殿下,每天读一读我的圣经吧,别再做这种事了,本案撤销。他们难道还会把一个王子关起来?无论他做什么!
男人2:的确如此。
男人1:没有正义。
忒修斯:皇家的成员。王权反对王权?他们又不是蠢蛋!
男人1:都是些猪狗不如的东西。
男人2:她还算不错。
男人1:她死了。
忒修斯:你怎么可能统治几个世纪?要是连这点脑子都不动一下!
男人2:的确如此。
忒修斯:给人看审判,把他押在庭上,牺牲一点小王子的声誉,把他逐出家族。
男人2:正是如此,正是如此。
忒修斯:然后说,他们已经把腐败的因素去除了。但是专制却仍然存在。
男人1:我们应该做什么?
男人2:为所有人的公平!
女人1:他必须死。(20)Sarah Kane, Sarah Kane Complete Plays, London: Bloomsbury, 2015, p.99.
在这段戏的开头我们可以看到,忒修斯的发言用了问句,但在问句之后又加上一句不容质疑的事实陈述(21)英文原文中的句式正是如此,笔者根据原文翻译。。听众完全可能因为相信他的陈述的正确性而同时接受他的断言。这是一种心理暗示的技巧,他重复用了三次。然后他用激将法,假设出一种最轻的惩罚,激起群众的愤怒。事实上,他的五次发言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他在希波吕托斯乱伦这一个体行为和群众被王权压抑这种群体需求之间建立起联系,成功地鼓动了听众。莫斯科维奇善良地认为:“领袖不是通过暴力组织来施展自己的威力——这经常是次要的手段,而是通过组织信仰来施展自己的威力的——这才是主要的手段。”(22)莫斯科维奇:《群氓的时代》,许列民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59页。但通常的情况却恰恰是暴力是促成信仰的最重要手段。在这出戏里,忒修斯对群众的动员,最后使用的手段正是暴力,他带头杀害了自己的女儿,群众因此从辱骂上升为行动,并最终陷入到一场残暴的狂欢之中。当然,把“大众”的这种盲目与暴力归罪于独裁者是不合适的。即便从历史看,事实也可能正相反,独裁者往往是大众暴力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勒庞写道:“领袖最初往往不过是被领导者中的一员。他本人也是被一些观念所迷惑,然后才变成了它的使徒。”(23)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5页。
显然,我们有必要将易卜生的“少数派”和统治大众的领袖作一个明确的区分。看上去,“少数派”一样有着领导或至少是影响群众的意图,与领袖很类似。但实际上,他在本质上缺少成为领袖的基本条件。这一条件并非如普列汉诺夫所认为的“没有能够团结大多数”,而是他对真相与真理的极端追求与成为领袖所必需的功利性妥协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易卜生笔下的“少数派”事实上类似于科塞(Lewis Coser)所总结的“理念人”(Men of Ideas)。科塞写道:“理智(intellect)有别于艺术和科学所需要的智力(intelligence),其前提是一种摆脱眼前经验的能力,一种走出当前实际事务的欲望,一种献身于超越专业或本职工作的整个价值的精神。”(24)刘易斯·科塞:《理念人》,郭方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页。领袖在面对群众时,“理智”很显然会成为他统治的障碍。“少数派”永远只能是少数的,它在“多数”之外,而不在“多数”之上。以斯多克芒为代表的“少数派”,不是通过统治,而是通过启蒙,不是作用于大众,而是作用于个体,来最终实现每个人都成为“自由高尚的人”(25)易卜生:《人民公敌》,《易卜生文集》,潘家洵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399页。的目的。
普列汉诺夫和易卜生代表了对待大众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前者强调统治与引导,后者则呼吁个体先从大众中独立出来,进而对其进行启蒙。批判大众为“乌合之众”的西方现代戏剧作品,基本都采取了易卜生的态度。在《老妇还乡》里,迪伦马特所设置的主人公伊尔与大众的关系更加耐人寻味。临近结尾处,伊尔预感到小镇居民准备判他死刑,市长劝他自杀,这样就可以不必开市民大会。伊尔对自己的生命已不报希望,但却拒绝自杀。他说:“你们可以杀死我,我不抱怨,不抗议,不自卫,但想要我免掉你们的宣判,这我做不到。”(26)迪伦马特:《老妇还乡》,叶廷芳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246页。伊尔所坚持的是“大众”可以对其进行谋杀,但必须要有现场。他试图迫使“大众”在其集体犯罪的现场感知其应承担的责任。他的这一行为,带有比斯多克芒更深的反抗意味。《菲德拉的爱》的结尾与《老妇还乡》有很大的相似性,希波吕托斯平静地接受了大众的暴动,以自己的死结束了专制君主时代。
三、剧场变革与“大众”转型
尽管我们看到,左派剧作家的“大众”是一种想象的善的集合,比起易卜生、迪伦马特笔下的“大众”显得更不真实,但是“大众”是否一定意味着是“乌合之众”呢?勒庞所总结的“大众”的这些特性会不会只是历史的、暂时的,可改变的?
戏剧是一种大众的艺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它所面对的观众都是一个群体。很多时候,往往是一个同质性较高的群体。戏剧从诞生之初,其功能就包含了形塑、改变或至少是影响观众的意图。直至19世纪末,这一功能仍然没有改变。然而,整个文化界对“大众”特性的这样一种自觉,深刻地反映到了戏剧领域,迫使戏剧拥有了作为“大众艺术”的自觉,并因此将观众与演出的关系置于剧场革新的重要位置予以考虑。当“大众”的正当性受到质疑的时候,戏剧的观众同样变得不再可信了。现代剧场艺术因此不再满足于仅仅在所表达的文学内容上呈现并批评“大众”,剧场的形式,尤其是观演关系必须同时作出反应。在这之中,阿尔托(Antonin Artaud)和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是最重要的代表。他们都不再相信亚里士多德式的引起观众情感共鸣的戏剧。在他们看来,这种情感的共鸣非但无法促使观众发生变化,反而使观众获得更多的安全感,并因此越发固步自封了。很显然,与传统的艺术家相比,甚至与易卜生的“启蒙”相比,在迫使“大众”发生改变这一问题上,阿尔托和布莱希特表现得更为急迫,也呈现出更大的野心。他们为戏剧艺术提出了新的任务。
在《戏剧与瘟疫》这一文章中,阿尔托借助“瘟疫”来说明他所理解的戏剧的功能。他注意到戏剧观众与瘟疫传播期的“大众”在暴力与非理性上的相似性:“民众中的渣滓似乎由于贪婪的狂热而免疫,他们走进开着门的房子,抢夺财宝,而他们知道这财宝毫无用处。这就是戏剧。戏剧就是立即的无偿性,它尊重无用的、对现实毫无益处的行动。”(27)阿尔托:《残酷戏剧——戏剧及其重影》,桂裕芳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3年,第18页。在他看来,至少在戏剧领域内,这种暴力与非理性的行动是必须的,因为 “戏剧之所以象瘟疫,不仅仅是因为它作用于人数众多的集体,而且使人心惶惑不安。在戏剧和瘟疫中,都有某些既获胜的又具有报复性的东西。瘟疫在所到之处点燃了大火,我们明显地感到这场大火正是一次大规模的清算”,“戏剧的作用是群体排出脓疮。”(28)阿尔托:《残酷戏剧——戏剧及其重影》,桂裕芳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3年,第21、26页。他呼唤一种新的戏剧,并把它命名为“残酷戏剧”。由于时代的原因,阿尔托对瘟疫的认知并不是科学的,但这并不影响今天的我们对这一类比的理解。在他看来,瘟疫过后,活下来的人获得了某种免疫,而进入剧场看戏的观众,在接触了真正的戏剧之后,他们的精神也应该获得某种洗涤。正如阿尔托自己所明确指出的,他的戏剧理想是一种“暴露”。它既是对个体心理内在阴暗的暴露,也是对群体特质的暴露。由此,阿尔托采取了极端的手段,摒弃了语言(文学)在其中的核心作用,将身体与剧场元素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试图复活戏剧中的仪式性内容。
阿尔托的这种彻底颠覆观众的戏剧理想是值得肯定的,然而其实现的途径——既强调“身体”,又强调仪式——却带有矛盾性。德里达注意到“身体”在阿尔托理论中的重要意义,他写道:“惟一永不让人注释的东西就是身体之生命,是剧场保持其完整性以对抗恶与死亡的那种活生生的血肉”(29)雅克·德里达:《书写与差异》,张宁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332页。。在他看来,这是因为身体在语言之前,它还未被任何语言所书写。的确,将人与人作根本区分的也许不是我们的精神,而是我们的身体。“残酷戏剧”观众的戏剧参与是一种比传统戏剧更为明确的清醒的个体参与,因为“身体”将天然地摆脱任何假造的意识形态(文学)控制。然而,阿尔托却同时强调仪式。仪式却是一种集体行为,是放弃身体独特性的行为,因为它把身体降格为一具肉体。即使这类仪式是德里达意义上的一种“非重复的”“原初的”的行动,这种行动也将很快走向某种固定的虚假。或更可能的是,它本身即是被一种先验的观念所控制的群体行为。身体的独特性与仪式的集体性之间的矛盾正是残酷戏剧的悖论。简单地说,残酷戏剧的危险在于,观众被作品所唤起的恐惧与激情以一种怎样的方式宣泄掉是不明确的。它可以是反思的、深刻的、静默的,也可以是危险的、肤浅的、暴力的。它可以实现对个体理智的唤起,也可以实现对集体盲动的鼓动。对此,我们可以在美国“生活剧团”(The Living Theatre)的《天堂此时》(Paradise Now)中找到印证。该剧被认为是阿尔托残酷戏剧的继承。一方面,它深刻地刺激了观众的僵化思维,比如在戏的开场,裸体的演员置身于观众之中,低声询问“我们为什么要穿衣服”;另一方面,它又操纵群体,鼓动一场政治运动,正如戏剧史家尚克(Theodore Shank)所描述的,在该剧的结尾,所谓的“永恒的革命”一章,剧团将观众引向街头,演出随之演变为集体游行(30)Theodore, Shank.American Alternative Theatre,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82. pp.21-23.。
同样出于对改变观众的迫切愿望,布莱希特却选择了另一途径。在布莱希特眼里,他的时代的戏剧观众是这样的:“观众似乎处在一种强烈的紧张状态中,所有的肌肉都绷得紧紧的,虽极度疲惫,亦毫不松弛。他们互相之间几乎毫无交往,象一群睡眠的人相聚在一起,而且是一些心神不安地做梦的人……他们在瞪着,却并没有看见;他们在听着,却并没有听见。”(31)布莱希特:《布莱希特论戏剧》,丁扬忠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第15页。在他看来,正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共鸣戏剧,塑造了这样一批观众,而那类戏剧正是“建立在催眠术式的暗示的基础上的”(32)布莱希特:《布莱希特论戏剧》,丁扬忠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第22页。。与阿尔托强调身体与仪式不同的是,他借助“间离效果” 对故事与表演进行陌生化来实现对剧场的革新。他的目的是将“可以受到社会影响的事件除掉令人信赖的印记”(33)布莱希特:《布莱希特论戏剧》,丁扬忠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第22页。,唤起观众的自由思考能力,对舞台上发生的一切进行反思和批判。
这样一种新型的戏剧,布莱希特曾将它命名为“教育剧”。在中文的语境里,“教育”这一词语很容易引起误解,因为它必然包含“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两种不同的身份。如果说“被教育者”是作为观众的“大众”的话,那么“教育者”显然是戏剧创作者无疑了。戏剧学者雷曼(Hans-Thies Lehmann)为布莱希特作了辩护,他说,“教育剧”在布莱希特的表述中应当是“学习剧”。所谓“教育”,是针对戏剧实践者自己,而不是针对观众(34)雷曼:《布莱希特教育剧中的宗教性主题》,《戏剧与影视评论》2017年第5期,第1-2页。。这样一来,那种凌驾于“大众”之上的权威形象就被去掉了。学习是一个探寻结论的过程,而教育往往是就一个结论的宣传。如果我们综合考虑布莱希特的作品的话,也许我们的确应该相信弗里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的判断,他写道:“布莱希特从来没有确切的供说教用的教条,甚至没有一个可称其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相反……他的‘意见’和教训——他乐于提供的寓言和谚语——是属于方法方面的——而不是积累的事实、思想、信念、重要原则等等。”(35)詹姆逊:《布莱希特与方法》,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2页。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和“教育剧”理论中所表露出来的对待观众的态度,使布莱希特远离了普列汉诺夫式的马克思主义行动者的角色,而退回到仅仅是一个带有马克思印记的思想者的位置上来。
阿尔托和布莱希特的戏剧思想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下半叶至今的戏剧发展,使得我们在当今戏剧作品中能够轻易地辨识出其中的元素,比如法布雷(Jan Fabre)的《奥林匹斯山》之于阿尔托,“大嘴突击队”(Gob Squad)的《西方社会》之于布莱希特。然而问题是,经历了大约一个世纪的努力,戏剧的任务完成了吗?戏剧的观众改变了吗?“大众”的特质改变了吗?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现代戏剧在戏剧文学与剧场艺术两个方面都表现出了对待“大众”的谨慎态度。从20世纪的人类历史,我们也的确看到了诸多来自“大众”的令人恐惧的力量所造成的灾难。然而,在这样一种看似全面的考察之中,我们是否可能遗漏什么?“少数派”真的如易卜生所说的,总是对的吗?或者说,“多数派”因此而变得总是错的?我们只能选择这样一种精英立场吗?对于“大众”,我们是否过于简单地相信了勒庞所得出的结论?事实上,对于勒庞的理论,弗洛伊德就曾提出过质疑。他说:“倘若一个个体在集体中放弃了他的特点,而让其他成员通过暗示作用来影响自己,这就会使人想到,他这样做是因为感到有必要和他人保持和谐,而不是与他人相对立——也许说到底他是‘为了爱他们’。”(36)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98页。他为大众的盲从找到了某种正当性。
而在对现代剧场的分析中,我们事实上忽略了戏剧艺术创作者们在批评“大众”时背后所隐藏着的为“大众”的未来而奋争的渴望。无论是易卜生、迪伦马特、阿尔托、布莱希特,都带着改变“大众”的理想而投身剧场艺术。这种理想,契诃夫在《三姐妹》中借威尔士宁之口表达得更为清晰,他说:“周围广大老百姓的愚昧,你们克服不了,那也是很自然的事……你们也会迷失在这十万居民的人群当中,生活也会把你埋没了。但是你们依然不会完全消失,你们不会不发生影响。也许继你们之后,又会出现六个像你们这样的人,再以后,又出现十二个,如此以往,总有一天,像你们这样的人终于形成了大多数。两三百年以后,世界上的生活,一定会是无限美丽、十分惊人的。人类确实需要那样的生活,那么,既然那种生活现在还没有出现,我们就应当具有先见之明,就应当期望它,梦想它,为它去作准备。”(37)契诃夫:《契诃夫戏剧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262页。然而,威尔士宁说完这段台词后,一百多年过去了,情况似乎并没有多少改变。“大众”的未来是否真能如契诃夫所料,仍然是未知数。
——王忠祥教授访谈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