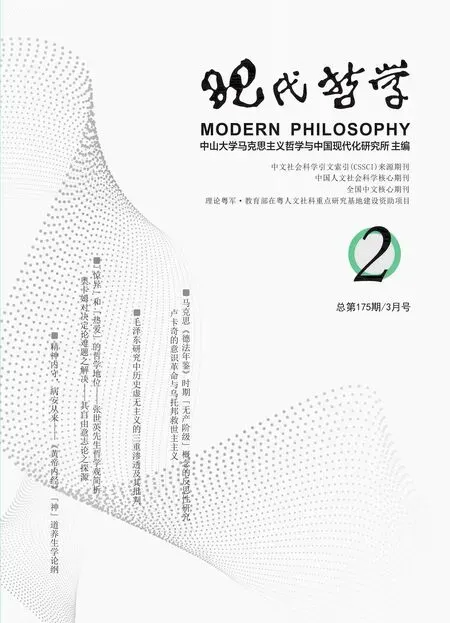“文明社会”与“商业社会”
——苏格兰启蒙思想中的双重现代社会想象
苏光恩
一、问题的提出:“文明社会”与“商业社会”是一回事吗?
在现代世界图景的塑造上,18世纪的苏格兰启蒙运动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是苏格兰思想家们赋予经济或商业在现代社会中的核心位置,并对它的运行机制作了深刻的探讨和揭示。今天人们通常认为,苏格兰人是用“商业社会”(commercial society)一词来命名他们置身其中的这一新的时代或社会类型,而这一社会的基本意涵在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这部代表了苏格兰人的思想雄心的巅峰之作中得到简明扼要的界定:在一个劳动分工完全确立的社会里,“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一切人都成为商人,而社会本身,严格地说,也成为商业社会”(1)[英]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0页。。虽然这句话只是强调人们在生活资料上的相互依赖,但后世的许多研究者相信,所谓商业社会便是人人皆为商人的社会,在这一社会里,交换关系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成为整个社会关系的本质,或者更准确地说,商业社会中的关系是根据商人间的关系来构建的(2)Isvan Hont, Politics in Commercial Socie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3; [英]贝里:《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社会理论》,马庆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53页;[美]约瑟夫·克罗普西:《国体与经体:对亚当·斯密原理的进一步思考》,邓文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2页。。研究者们实际上不是在《国富论》而是在《道德情操论》中找到了他们所认为的关于商业社会中人际关系特征的经典表述,尽管“商业社会”一词从未在《道德情操论》出现过。在该书中,斯密设想了一种社会,其成员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爱和感情,但仅仅“出于对其效用的认识”,社会就可以“像存在于不同的商人中间那样存在于不同的人中间”,“即便在这一社会当中,没有人负有任何义务,或必需对任何人表示感激,它仍然可以根据一种一致的估价,通过着眼于实利的互惠行为而得到维系”(3)[英]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06页,译文有改动。。这一没有爱和感情、仅靠效用来维系的社会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商业社会。
然而在斯密的所有著作中,“商业社会”仅在《国富论》里出现2次,而且只有在前面所引的这句话中,斯密对“商业社会”的使用是不加任何限定的;在另一处,他使用的是“一个文明和商业的社会”(a civilized and commercial society),“文明”与“商业”被共同用来修饰他所置身的现代社会(4)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2, pp.37, 784.。事实上,在《国富论》中,“文明社会”(civilized society)出现的频率远高于“商业社会”(5)“文明社会”在《国富论》共出现13次。(See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pp.26, 97, 265, 376, 679, 695, 712, 782, 783, 785, 788, 794.)。这不免带来一个问题:仅仅以“商业”来界定现代社会是否充分?“文明”是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修饰语?“文明”与“商业”的并置,同样出现在其他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中。例如,弗格森(Adam Ferguson)在《文明社会史论》(AnEssayontheHistoryofCivilSociety)中便使用过“优雅与商业的民族”(polished and commercial nations)这一提法;在米拉(John Millar)那里则多次出现“富庶与优雅的民族”(opulent and polished nation);而在18世纪英国,polished与civilized几乎是同义词(6)Adam Ferguson,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London: T. Cadell, 1782, p.315; John Millar, The Origin of Distinction of Ranks,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2006, p.272; John Millar, An Historical View of the English Government,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2006, pp.131, 238, 751.。我们知道,追溯文明社会的历史,即人类从粗鄙野蛮的状态发展为优雅文明的状态,构成包括休谟、斯密、弗格森、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凯姆斯(Henry Home, Lord Kames)和米拉在内的诸多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共同旨趣。在这一文明演进的历史叙事中,经济的内容,如财产权的出现、商业的兴起和繁盛,仅仅构成其中一个面相,文明同样涉及科学和艺术的进步、常规政府的建立,以及人们在风尚上变得更为人道(humanity)和文雅(politeness),等等。因此,对18世纪后半叶的苏格兰人而言,他们置身其中的不只是一个商业社会,也是一个文明社会。如果说前者所强调的是商业在社会生活中的支配地位,那么后者所关切的则是开明(enlightened)战胜蒙昧、文明驯服野蛮、优雅柔化粗鄙,这两个不同称谓背后隐含着对同一个社会的不同想象。那么,这两种现代社会想象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它们存有区别,还是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许多研究者都强调“商业社会”与“文明社会”的同一性。例如,克罗波西(Joseph Cropsey)认为,在斯密那里,“文明”与“商业”是不可分割的,文明指的是“自由和世俗的社会,这一社会只有在商业取代了人们生活中的精神和世俗主宰的地方才会出现”(7)Joseph Cropsey, Polity and Economy: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Principles of Adam Smith, The Hague: Springer, 1957, p.94.;贝里(Christopher J. Berry)的近著《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商业社会观念》同样没有在“商业社会”与“文明社会”之间做出明确区分,在那里,“文明”本身是商业社会的特征之一(8)[英]贝里:《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商业社会观念》,张正萍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5页。;波考克(J.G.A. Pocock)虽然更多地从公民人文主义的角度切入苏格兰人的“文雅”论说,但其结论与贝里等人基本一致,即文雅取代公民美德,成为商业社会中的意识形态(9)[美]波考克:《德行、商业和历史》,冯克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169—170页。。不管这些研究者的立场和诠释路径有何区别,他们都相信“文明社会”不过是“商业社会”的另一副面孔,或者说前者是后者的产物,他们即便注意到“文明社会”概念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存在,也只是以商业的逻辑来演绎文明社会的特质。果真如前面所言,商业社会只是商人间关系的一种扩展,那么这些解释并没有真正消弭这两种现代人肖像之间的差异:一个冷漠的、仅仅出于自利而与他人发生联系的人,为何同时也是文雅的、富于人道的?
与强调“文明社会”与“商业社会”的同一性相反,本文试图表明,这两者构成了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对现代社会的双重想象。一方面,笔者承认这两个概念在苏格兰人那里所具有的亲缘性,但正是这一亲缘性证明了“商业社会”不是一个没有爱和感情、仅靠效用来维系的社会;另一方面,对于本文来说更重要的是,“文明社会”并不单纯是商业繁荣的产物,“文明社会”与“商业社会”虽然在苏格兰人的具体使用当中有时候是重合的,但它们之间仍然存在着差异、张力甚至冲突。廓清这两个概念在苏格兰启蒙思想中的关系,不仅可以深化我们对苏格兰启蒙思想的认识,也对我们为现代社会所勾勒的那些经典图景提供了一些反思视角。当然,用“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来涵盖诸多重要的思想人物,势必淡化他们之间的分歧和对立,尤其是他们对置身其中的这个“文明和商业的社会”的态度并不全然相同。但他们在立场上的这种分歧并不损害他们在诸多事实判断上的一致性,譬如“文明和商业的社会”的伦理特征、商业和文明的关系以及劳动分工的弊病等,正是这些一致性构成本文讨论的基础,也使我们理解苏格兰人的这种双重现代社会想象成为可能。
二、“文明和商业的社会”的伦理特征
首先需要讨论的是,商业社会本质上是不是商人间关系的扩大?斯密在设想一个无需爱与感情、仅凭效用便能维系的社会时,其背景是比较正义与仁慈的区别,他借此说明正义是比仁慈更为根基性、更不可或缺的美德。那么,斯密是否认为,这一社会便是商业社会?这是不少研究者所持有的看法,在他们看来,斯密对仁慈与正义的区分实际上暗示了从仁慈到正义的古今伦理转型:古代社会是熟人社会,人们彼此间以仁慈和友谊为纽带;现代社会则是陌生人社会,陌生人之间互不关心,他们所遵从的只是互不伤害的正义原则(10)[美]克罗普西:《国体与经体》,第58—60页;高力克:《正义伦理学的兴起与古今伦理转型——以休谟、斯密的正义论为视角》,《学术月刊》2019年第7期,第47—53页。。贝里虽然不否认仁慈在商业社会中的存在,认为商业社会中的成员可以既正义又仁慈,但在他看来,仁慈只存在于更为亲近的熟人之间,而陌生人之间的抽象关系才是商业社会的核心特征(11)[英]贝里:《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商业社会观念》,第134—135页。。
将仁慈和正义视为伦理的古今之别,称前者适用于熟人社会,后者适用于陌生人社会,实际上是将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关于“共同体”与“社会”的经典区分套在了斯密身上(12)滕尼斯便是这样来理解斯密的“商业社会”概念的。在他看来,“市民社会”是一种“人人皆商”的状态。“civil society”而不是“civilized society”被等同于“commercial society”,这清楚地反映了黑格尔的影响。(参见[德]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第148页。)。这种现代人想象,从根本上说与斯密乃至整个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道德心理学并不相一致,因为依照他们的道德情感主义,人身上存在着自然的亲社会的情感,人对社会的需要不仅仅是利益上的,更是情感上的。一个没有爱与感情的社会是背离人性的,即便这样的社会有可能获得维系,它也是“不很令人愉快的”(13)[英]斯密:《道德情操论》,第106页。。苏格兰启蒙哲人们确实关切伦理的古今之别,但在他们那里,这一伦理的古今转型并非从古代的仁慈转向现代的正义,而是从自制(self-command)或坚毅(fortitude)转向人道(humanity)(14)同上,第259页;Adam Ferguson,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p.333; John Millar, The Origin of Distinction of Ranks, p.114; Henry Home, Sketches of the History of Man,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2007, p.198; William Robertson, A View of the Progress of Society in Europe, London: T. Cadell, 1840, p.67; David Hume, Essays: Moral, Political, Literary,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7, p.414.。依照斯密的界定,人道指的是旁观者对当事人的强烈同情(15)[英]斯密:《道德情操论》,第237页。。这一“文明社会”的伦理特征显然与许多研究者所认为的“商业社会”各成员间的彼此冷漠截然相反。事实上,在苏格兰人笔下,冷漠更接近于野蛮人或未开化社会中人的关系特征,一个文明人会为素不相识的人的不幸伤心落泪,而一个野蛮人却可能在观看自己同胞受刑时无动于衷(16)同上,第261页。。文明人是对他人的情感更为敏感、更具同情心的人。诚然,在一个“文明和商业的社会”,人们与陌生人打交道的机会越来越多,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彼此之间变得越来越冷漠,相反,与陌生人交往所带来的是对陌生人态度的根本变化:在未开化社会,由于不同的部族之间互不往来,人们对陌生人缺乏了解和信任,从而总是抱着本能的怀疑和敌意,对他们而言,“陌生人”与“敌人”实际上是同义词;而商业社会中更多元、更广泛的交流增进了陌生人之间的相互了解,倾向于消除彼此间的偏见和敌意,从而使他们在对待彼此时更为友善(17)Adam Ferguson,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p.33; Adam Smith,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2, p.432; Henry Home, Sketches of the History of Man, p.196; William Robertson, A View of the Progress of Society in Europe, pp.73, 77.。因此,即便“文明和商业的社会”可以称为陌生人社会,也是对陌生人更为友好的社会,人虽然无法摆脱其情感的地方性,但他不再仅仅依据地域和血缘的远近亲疏而划分敌友。
商业除了增进不同群体之间的了解之外,它所带来的富庶也有助于人道美德的培养。如斯密所解释的,野蛮人时刻处在危险之中,这一环境“不仅使他习惯于各种困苦,而且教育他不屈服于困苦所引起的各种激情”,“他不可能期望他的同胞因这种弱点而表示同情或纵容”,因此,他学会克制自己的激情,不愿意在他人面前暴露自己;相反,“在文明和有教养的各个时代到处可见的那种歌舞升平和幸福安宁,使人很少有机会磨炼出对危险的轻视和忍受劳累、饥饿和痛苦的耐心”,他有更多的机会满足自己的激情,这也使得他更有可能去同情他人(18)[英]斯密:《道德情操论》,第259—260页。,因此,文明人更习惯于听从天性倾向,他们敢于在同伴面前表露自己的情绪,而非加以遏制。正是在这一点上,斯密认为,文明人的交往类似于朋友之间,是坦率的,相反,野蛮人的交往倒类似于陌生人之间,是有保留的(19)同上,第262页。。
在情感上,野蛮人更自制,而文明人更为放纵,苏格兰人所呈现的这一伦理的古今之变似乎与我们关于文明化的惯常看法背道而驰,即文明是对野蛮的激情的驯服。关于这一问题,可以这样看:首先,苏格兰人普遍否认存在一个先于社会的自然状态,而野蛮人也不是如曼德维尔和卢梭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非道德的动物,他们同样奉行与其自身处境相适应的伦理,因此,文明的进程并非一个简单的由激情不受约束到对激情的控制越来越严的过程。其次,苏格兰人并不认为人道与自我克制是矛盾的。斯密便指出,“具有最完美的德性的人”是这样一种人,他既能“最完美地控制自己原初的和自私的感情”,又能“最细腻地感觉到他人原初的和同情性的感情”,“具有最强烈的人道精神的人,自然也是最有可能获得最高度的自我控制的人”(20)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p.152.。对斯密而言,无论是对他人的同情还是自我克制,都出自同一种原则,即对他人情感的敏感(sensibility)。使文明人真正区别于野蛮人的与其说是人道,不如说是敏感。虽然对他人的同情是人的自然禀赋,但只有通过广泛的社会交往,才有可能培养出这种细腻、敏感的同情。而野蛮人由于他们不幸的处境,也由于其有限的社交范围,他们对他人的感受更为迟钝,因而他们的道德体系更为粗糙,他们的激情总是在极端的自我克制与极端的猛烈狂暴之间摇摆(21)[英]斯密:《道德情操论》,第264页。。更准确地说,不是文明人更放纵或更能自我克制,而是他们更温和、更不极端。
仅仅证明商业社会并非商人间关系的扩大,尚不足以驳倒“文明社会”与“商业社会”具有同一性这一普遍看法,而我们关于商业促进人道的讨论似乎反倒确证了这一点。我们无需否认“商业社会”与“文明社会”在苏格兰人那里的亲缘性,虽然并不是他们最早看到商业与文明之间的联系,但他们确实赋予商业在文明社会形成中的核心重要性。在苏格兰人那里,“文明社会”的诸多特征,如常规政府(regular government)的确立,富庶、优渥的生活,繁荣的科学与艺术,高雅的文学和品味,以及风尚上的人道和文雅等等,往往与商业的发展密不可分(22)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p.412; John Millar, An Historical View of the English Government, pp. 729-730, 773, 787, 809; William Robertson, A View of the Progress of Society in Europe, pp.33, 72, 77; David Hume, Essays: Moral, Political, Literary, p.119.。尤其是他们所持有的四阶段理论将从野蛮到文明的过程纳入从渔猎社会、游牧社会、农业社会再到商业社会这一生存模式的变迁中,作为最后阶段的商业社会显然成为最文明的社会(23)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pp.782-783; Adam Ferguson,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pp.135-136; John Millar, The Origin of Distinction of Ranks, p.170; Henry Home, Sketches of the History of Man, pp.176-177.。
不过,“文明社会”与“商业社会”的亲缘性并不意味着它们是一回事。首先,并非只有商业发达的社会才有可能是文明社会。一个经典的反例便是古罗马,对苏格兰人而言,古罗马代表了上一个文明的顶峰,而现代欧洲文明是在罗马帝国覆亡后的废墟上缓慢重生的(24)[英]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351页;Adam Ferguson,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p.184; John Millar, An Historical View of the English Government, p.13; Henry Home, Sketches of the History of Man, p.105; William Robertson, A View of the Progress of Society in Europe, p.2.。而罗马人的崛起、他们由野蛮变为文明所主要依靠的不是商业,而是征服,他们通过征服而变得富庶,但他们对商业抱持着强烈的蔑视(25)Adam Ferguson,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pp.227-228; John Millar, An Historical View of the English Government, p.775; Adam Smith,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p.229.。就此而言,富庶对于文明社会的形成来说更不可或缺,而商业只是获得富庶的手段之一。其次,商业最发达的国家也并不必然是最文明的国家。在苏格兰人眼里,荷兰这个全民皆商的国家便以风尚粗鄙、高雅艺术不发达而出名。如斯密所指出的,商业所带来的富裕只是“艺术的进步和生活方式的文雅”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26)[英]斯密:《修辞学和文学讲演录》,石小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86页。。文明风尚的形成常常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苏格兰人那里,政体便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荷兰人的粗鄙源于他们的共和政体,公民彼此间的平等使得他们缺少取悦地位更高者的动力,而且他们也缺乏闲暇和社交;相反,法国这样的君主制国家则被普遍视为当时最文明的国家之一,尽管在这个国家中,商业仍然被认为是不体面的(27)John Millar, An Historical View of the English Government, p.753; Henry Home, Sketches of the History of Man, pp.297, 365; 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p.207; David Hume, Essays: Moral, Political, Literary, pp.90-93, 124-127.。
事实上,在苏格兰人那里,作为现代风尚之特征的人道也并非纯然由商业繁荣所致。相较于古代文明国家,现代文明国家的一个卓越之处在于,他们即便在战争中也恪守人道,不滥杀平民,并优待战俘。这种战争中的人道有两个重要来源:其一,古今政体的差异。在弗格森看来,现代欧洲国家长期采用君主制,在此政体下,国家与君主合一,两国国民之间并无彻骨的仇恨,也没有理由要消灭对方,因此战争更为人道;而古代文明国家普遍采用共和政体,在此政体下,国家与国民合一,两国间的战争即是两国国民间的战争,战争必然是残酷的(28)Adam Ferguson,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p.324.。斯密同样指出,诛戮暴君或杀死敌国将军在今天遭到普遍的蔑视,正是因为君主国在今天具有更大的影响,它为其他政体树立了榜样(29)Adam Smith,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pp.427-428, 549-550.。其二,骑士精神的影响。骑士在战场上的慷慨、豪侠(gallantry)、恪守正义,以及对孤儿寡母和无辜者的保护,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现代的人道精神。事实上,在苏格兰人那里,人道、荣誉原则和对女性的殷勤这些现代风尚均与骑士精神有着密切的渊源(30)Adam Ferguson,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pp.334-340; John Millar, The Origin of Distinction of Ranks, pp.133-138; Henry Home, Sketches of the History of Man, pp.297-298, 413; William Robertson, A View of the Progress of Society in Europe, pp.65-67; Ernest Mossner, “David Hume’s ‘An Historical Essay on Chivalry and Modern Honour’”, Modern Philology, 1947(1), pp.59-60; David Hume, The History of England, vol.1.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3, pp.486-487.。
三、商业与文明的张力
作为“野蛮”的对立面,“文明”意味着对粗鄙、贫穷和无知的克服。“文明”的概念为苏格兰启蒙哲人们提供了一个有关“完美社会”与“完美人性”的标准。虽然在他们那里,文明人与野蛮人拥有同样的天性,甚至文明化的动力本身便出自人的天性,即人所具有的改善自身境况的倾向和能力(31)[英]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112页;Adam Ferguson,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p.10; John Millar, The Origin of Distinction of Ranks, p.84.,但文明人与野蛮人在这些天性的运用和锻炼上存在着根本区别。文明的进程既是人之天性逐步展开的过程,也是人之激情得到润饰和柔化的过程。尽管我们不能说文明人必定比野蛮人更有美德,但至少文明驯服了人性中的残忍,人的共情能力、智识能力和审美能力在文明的进程中都获得提高和完善,而文明使此世成为一个宜人的居所。苏格兰人对商业社会的赞美正在于它所带来的文明成就,但商业与文明之间并不总是一致的,而文明的理想成为苏格兰人审视商业社会弊病的根本性视角。
今天的研究者几乎都看到苏格兰启蒙哲人们对商业社会的矛盾态度:他们一方面赞美商业带来的进步,另一方面则忧虑于商业社会所面临的衰败的危险:商业的繁荣滋生了奢侈,从而带来对欲望的放纵;商业社会中广泛的劳动分工和和平倾向造成勇武精神的丧失,以及劳动者普遍的精神矮化。关于这一矛盾,研究者往往强调了古典资源尤其是共和主义的影响,由此商业社会的两面性实际上体现为商业与美德之间的张力。我们无需否认共和主义语言在苏格兰启蒙思想中的位置,但单纯的共和主义视角不足以解释这一批判与文明话语之间的关系,而我们将看到,即便在最明确地使用共和主义语言的弗格森和凯姆斯那里,共和主义的立场也完全从属于一个更大的文明史叙事。凯姆斯将文明的进程视为社会感情出现并逐渐增强的过程:在猎人时代,个体间几无联系,自私、冷酷;在朝向游牧、农业和商业生活的过程中,人的社会性得到很大发展,严酷的风尚得到柔化,人变得更富仁慈之心;但奢侈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光明的前景,它使人沉溺于自身的享乐,导致社会感情衰落,自私重新占据上风,人又回到原点(32)Henry Home, Sketches of the History of Man, pp.176-178.。在凯姆斯那里,公民美德或爱国主义并非野蛮人的风尚,相反,它正是社会感情的最高体现,也是文明人的特征(33)Ibid., p.417.。商业社会的一个危险倾向在于,它使人专注于个人的私利和享受而抛弃了这一崇高的社会感情,因此,商业社会中的美德危机实质上是商业社会对文明方向的某种偏离。与之类似,弗格森虽然批判现代风尚中的矫揉造作和虚荣,但并不否认文明的内在价值,在他那里,希腊人和罗马人虽然比现代人更重视美德,但不人道的奴隶制的存在使这些古代政体难称完美(34)Adam Ferguson,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pp.65-66, 310.。凯姆斯和弗格森都不试图像卢梭那样,将文明的进程展现为一幅人类的堕落史,他们始终是现代人,他们接受既有的许多文明成就,对古典美德的推崇仅仅在于认为它与现代文明是兼容的,并且是抵御商业社会的衰败倾向的唯一良药。
另一些苏格兰人则怀疑古典美德与现代社会的相容性。其中,休谟对“文明和商业的社会”的前景最为乐观,他否认商业的发展、技艺的进步会必然带来腐败和勇武精神的丧失,其理由之一是荣誉感在“知识和进步的时代”(ages of knowledge and refinement)最为充足,这种荣誉感比之野蛮人单纯基于愤怒的勇敢更强烈、更持久、也更容易控制,而且荣誉感的存在约束和控制了商业社会中人们对金钱的热爱(35)David Hume, Essays: Moral, Political, Literary, pp.268-280.。米拉则认为,欧洲其他民族并没有像意大利人那样因为商业的发展而变得怯懦和奸诈,其原因是“由骑士精神所引入的风尚更为牢固”(36)John Millar, The Origin of Distinction of Ranks, p.141.。换句话说,现代文明风尚本身就有可能遏制商业社会中的一些不良倾向,而无需诉诸古典的美德。但即便在这些辩护中也可以看到,文明与商业之间是可能存在张力的。
苏格兰人关于劳动分工的讨论最清楚地呈现了这一张力。在斯密那里,正是劳动分工使社会成员相互依赖,从而形成一个人人皆为商人的社会。劳动分工极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实现了社会的普遍富裕和繁荣;同时,它以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取代封建制下单向的人身依附,使个人获得解放。因此,劳动分工构成整个商业社会的基石。但是,包括斯密在内的诸多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又不无忧虑地看到,劳动分工使劳动者长时间地专注于某一个简单的操作,造成他其余的能力得不到锻炼。但无论将这一讨论视为马克思之前的劳动异化理论,还是一种共和主义批判(37)[英]温奇:《亚当·斯密的政治学》,禇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78页。,均不足以清楚地呈现苏格兰人看待这一问题的根本立场,对他们而言,文明才是尺度。
不妨更具体地引述苏格兰人关于这一弊病的论断。在斯密看来,“一个人如把他一生全消磨于少数单纯的操作……他自然要失掉努力的习惯,而变成最愚钝最无知的人……他对自身特定职业所掌握的技巧和熟练,可以说是由牺牲他的智能、他的交际能力、他的尚武品德而获得的”(38)[英]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第339页。。弗格森则指出,“在心灵最得不到运用,在车间被视为一台机器,而人是其组成部分的地方,制造业最为繁荣”;由于缺乏知识和人文教育,下层阶级养成极端卑鄙的性格,在弗格森看来,他们与野蛮人无异(39)Adam Ferguson,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pp.305, 311.。与斯密的表述类似,在凯姆斯看来,“持续进行一个操作,会将心智局限于一个目标,排除所有的想法和发明,在这样的训练之下,操作者会变得迟钝、愚笨”(40)Henry Home, Sketches of the History of Man, p.106.。同样,米拉认为,劳动和专业分工使工人们几乎不可能获得广泛的信息或智慧,习惯性的思想空洞使他们变得跟机器一样,“对他们职业对象的持续关注,和这些对象的狭隘性,具有使他们变得无知和愚蠢的倾向”(41)John Millar, An Historical View of the English Government, pp.731-733.。可见,他们共同强调了劳动分工对劳动者智力上的影响,即把他们变得愚钝无知。尚武精神的丧失当然也是其中的一个弊病,但斯密也提到“交际能力”的缺失,他所关切的是人的整体能力的缺失。
我们可以通过斯密的两组参照对象更好地理解这一点。第一组参照对象是未开化社会中的成员,在一个制造业和商业并不发达,不存在广泛的劳动分工的社会里,每个人都不得不从事大量各不相同的事务和职业,这一境况使他们各方面的能力都得到锻炼,知识也相应地得到扩展(42)[英]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第339—340页;John Millar, An Historical View of the English Government, p.734.。如果说文明的进程是一个人性不断完善的过程,那么商业社会中的劳动者恰恰与这一进程背道而驰,他们反倒堕入一种野蛮无知的状态,或者说,劳动分工却导致他们远远不如未开化社会的成员文明。第二组参照对象是商业社会中的有闲阶级,他们不以劳动为生因而拥有闲暇,有充裕的机会享受商业的繁荣带来的多样化的生活,这一优渥的处境使他们的理解力、社交能力和敏锐的品味都得到充分的锻炼(43)同上,第340页;Adam Ferguson,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p.306.。因此,与其说劳动分工造成社会成员的普遍无知,倒不如说它造成文明社会内部的两极分化:一部分人变得更为精致、文雅,更有理解力和判断力,另一部分人却变得无知、迟钝和麻木;一部分人变得越来越文明,另一部分人却堕落到连野蛮人都不如。事实上,正是这一部分有闲阶级的存在,使劳动者的野蛮化这一事实没有取消文明进步的真实性。有闲阶级的这些智识能力远非未开化社会中人所能企及,在斯密看来,这是因为未开化社会中的职业数量毕竟有限,而在文明社会中,社会总体的职业种类数不胜数,这给“那些自己未从事何等特定职业,有闲暇有意志去研讨他人职业的人,可以说提供了无限的研究对象”,而这必然会迫使他们“不断运用心思,比较着、组合着,从而使他的智能,变得异常敏锐,异常广泛”(44)同上,第340页。。因此,斯密对未开化社会中人拥有更广泛能力的褒扬与其说是一种原始主义的乡愁,倒不如说是出于对劳动者不幸处境的一种忧虑。基于类似的理由,米拉指出,当我们谈论商业与文明的一致性,期望“财富的获取会带来知识的拥有”时,这种一致性只有在国家层面才是有效的,而在个人层面远非如此,尤其在底层中间,情况甚至截然相反(45)John Millar, An Historical View of the English Government, p.736.。
广大劳动群体的野蛮化使苏格兰人对商业促进文明的赞许承受着考验,虽然他们普遍相信商业的发展使穷人的境遇得到很大改善,但物质上的进步无法抵消他们在精神上的退化。一个真正堪称文明的社会有义务对后者的不幸处境做出道德补偿,公共教育便是可能的补偿手段之一。尽管这种教育不足以弥合劳动者与有闲阶级在个人能力上的巨大鸿沟,但它可以使下层人民免受“狂热和迷信的迷惑”,使他们“更知礼节,更守秩序”(46)[英]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第341—342、345页。。换句话说,公共教育试图培养的是更合乎普通人身份的“文明礼貌”(civility),而不是有闲阶级的“文雅”(politeness)。
我们也只有在“文明”的视野下才能理解,斯密为何一方面认为文明国家的保存只能倚靠常备军,另一方面又认为维持大多数人民的尚武精神是必要的。他将尚武精神的丧失称为“精神的残疾”,如同劳动分工所导致的下层人民的普遍的无知和愚钝一样,这种人性的退化与文明的方向全然背离。在他看来,防止这种怯懦在人民中间蔓延传播,“政府应加以最切实的注意”,“纵使除防止社会的这种大害外,没有何等其他公共利益”(47)同上,第269、344页。。正因为在一个“文明和商业的社会”中,商业与文明之间可能存在着冲突,政府作为矫治者的角色才变得更为必要。
四、何为“文明和商业的社会”?
基于前面的考察,我们可以尝试着回答,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所理解和设想的“文明和商业的社会”究竟是什么模样。首先可以探讨的一个问题是,谁是这一社会的担纲者?诚然,商人在苏格兰人那里得到非常多的褒扬,他们被认为是最秉公办事、诚信和守时的人,弗格森甚至认为,即便在普遍腐化的时期,商人也是最有美德的人(除了勇武的德性之外)(48)Adam Ferguson,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p.239; John Millar, An Historical View of the English Government, p.775; Adam Smith,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p.538.。但商人的这些品行并不足以使他们成为这个文明和商业的社会的代表,事实上即便在这一社会中,人们对于商人的传统蔑视并没有完全消失。对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乃至整个18世纪文明话语的参与者而言,一个真正称得上文明或文雅的人应当是有着良好教养的人,他们有广博的学识、精致的审美品味、与人交往中富有机趣和风度,而这些人是人们通常所谓的“绅士”(gentlemen)。换句话说,18世纪文雅理想的担纲者是我们在讨论劳动分工时提到的有闲阶层。仅就商业对文明的影响而言,他们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在一个更为复杂多元的商业社会中,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培养他们的智识能力、审美品味以及文雅和人道的情感。虽然商业的繁荣导致社会阶层的流动变得越来越频繁,但苏格兰人置身其中的仍然是一个贵族还未走下舞台的等级社会,上流社会依然是文化的主导者,他们是那些渴望得到地位的新贵的效仿对象,或如斯密所说的,人人都渴望成为绅士(49)Adam Smith,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p.492; [英]克拉克:《1660-1832年的英国社会》,姜德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36页。。就此而言,苏格兰人所理解的文明社会与商业社会之前的时代有着更多的延续性,而非断裂。如前所述,苏格兰人认为骑士精神和君主制都对文明风尚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影响。18世纪的文雅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宫廷礼节向下扩散的产物,尽管这种扩散本身得益于商业的发展。
不过,苏格兰人也不是旧的等级秩序的捍卫者。斯密便时常流露出对大人物或上流社会生活方式的蔑视,认为他们的行为往往背离美德,或者说属于一种放纵的道德体系,与普通人通常奉行的严苛的道德体系截然相反,后者需要的是勤勉、吃苦耐劳和坚持不懈等等(50)[英]斯密:《道德情操论》,第66页;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p.794.。如果说文明在于人之天性的充分展开,那么上流社会另一半美德的缺失也使他们难称完美。在这意义上,休谟对中等生活进行热情的讴歌,称之为最幸福的生活,一方面是因为“过中等生活的人有充足的闲暇”,另一方面“它也为实践美德提供了最充裕的机会,为展现每一种我们可能具备的良好品格创造了条件”:过中等生活的人既有机会展现地位低下者的忍耐、顺从、勤奋和诚实这些美德,也有机会像身居高位者那样施展自己慷慨、人道、和蔼、仁慈的美德;而且过中等生活要比身居高位“更容易获得智慧与才干”,“有更好的机会洞悉人世间的人情世故”(51)[英]休谟:《论道德与文学》,马万利、张正萍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6—128页。。换句话说,中间等级才是“一个文明和商业的社会”中最完满的等级。但休谟对中间等级的赞扬并不意味着他将商人奉为楷模。尽管与法国相比,18世纪英国的“绅士”概念具有更大的包容性,但这种包容性主要体现在它是通过文化而不是经济来界定的,即它强调的是拥有闲暇、良好的品味、幽默的谈吐和广博的学识等,商人即便有望赢得绅士之名,也不是因为他们的商业行为(52)[英]克拉克:《1660-1832年的英国社会》,第205页。。
苏格兰人赞美商业,是因为商业对文明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他们也确实相信,相比起其他三个社会阶段,商业社会是最为文明的阶段。但文明并非单纯的商业繁荣的产物,它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商业的繁荣对文明的进步来说不是完全正面的。因此,即便不是所有苏格兰启蒙哲人们都相信,商业的繁荣在促进文明进步的同时也播下衰败的种子,他们也仍然都会同意,商业与文明之间存在某种张力,它们并不总是携手并进。
诚然,在哪种生活方式更值得追求上,弗格森这样的斯巴达式美德的推崇者与休谟这样的现代文雅的赞美者之间存在着尖锐分歧,但他们都并不否定作为一种理想的文明本身,弗格森对商业社会中的腐败的批判也是通过文明的语言来呈现的,而且休谟对现代文雅的赞美也没有使其毫无保留地去赞美商业。商业的繁荣的确造成人们在生活资料上的相互依赖,但苏格兰人并不认为“文明和商业的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只是商人间关系的一种扩展。或者说,他们所忧虑的正是商业精神渗入所有其他社会关系中,金钱成为整个社会唯一追求的目标。如米拉所看到的,尽管商业有助于扩大人们的交往范围,使他们在对待陌生人时更为人道和正义,但商业也有可能侵蚀和损害更为亲密的私人关系,使亲情和友谊都变成一种利益上的算计(53)John Millar, An Historical View of the English Government, pp.773-783.。弗格森则认为,人对自身利益的过分关注将使人变成为一种疏离的、孤独的存在,而且对利润的渴望“抑制了对完美的热爱”(54)Adam Ferguson,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pp.31, 364.。因此,这种人性的狭隘与其说是文明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必然特征,倒不如说是对文明本身的扭曲甚至背离。如前所言,休谟之所以不认为对金钱的狂热会成为这个“文明和商业的社会”中的支配性原则,是因为在一个文明时代,由于对他人看法的极度敏感,这种对金钱的欲望会受到荣誉感和道德感的约束。休谟并没有将这个社会想象成完全由商业精神所主宰的社会。
在本文看来,“文明社会”和“商业社会”构成苏格兰人对于现代社会的双重想象,在他们那里,这两种想象之间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可能是彼此冲突的。在这一点,苏格兰人远不是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们接受了商业在今天对于一个文明社会的必不可少性,但在他们那里,文明才是尺度。正是借助“文明”概念,苏格兰人得以在接受或拥抱商业社会的同时,获得一种对商业社会进行自我审视和自我批判的视野。在他们那里,虽然现代文明风尚有其等级制的渊源,但文明和商业是可以共存、共生的,商业促进了文明的进步,而文明则有可能约束商业社会的腐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