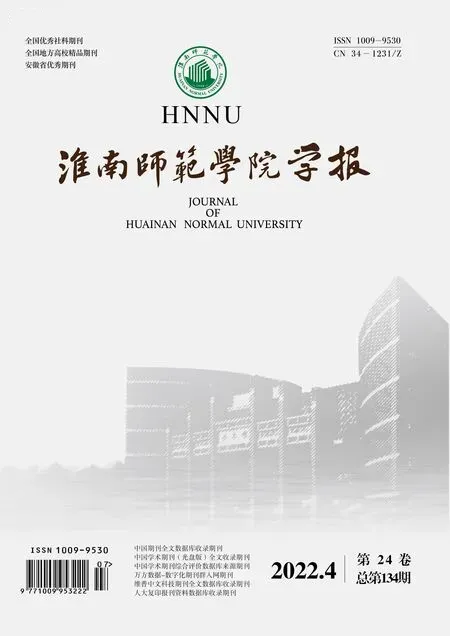论《周南》《召南》为周初淮汉诸姬所作
贝承熙
(清华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084)
《诗经》以“二南”为首,但所谓“周南”“召南”究竟何义,历来争论不休。《诗大序》载:“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 南,言化自北而南也。 《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 ”[1](P569)此处将“周南”“召南”视作体现周公、召公之德的诗篇,“南”被解释为动词,字面上指的是周公、召公之德教广播南土。这一说法可谓奠定基始,郑玄《诗谱》结合周、召分陕的故事,以为“二南”为自陕而始,及于南国之诗,曰:“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国也。 ”[1](P558)后朱熹《诗集传》亦延续了这种思路,只是相比郑玄将“二南”范围缩小到周、召所治南国之诗,曰:“南,南方诸侯之国也。 ”[2](P1)
自清代以来,学者逐渐提出脱离“南”字方位含义的解释。 马瑞辰基于郑玄《诗谱》“周、召者,《禹贡》雍州岐山之阳地名”[1](P557)之说,将“二南”解释为周公、召公采邑中所得之曲,以为:“‘南’盖商世诸侯之国名。”[3](P11)而近人陈致基于甲骨文研究,认为“南”原指一种乐器,“周南”“召南”可能指的是流行于周公、召公采邑的乐曲[4]。 可见,两位学者将“二南”仅仅视作周公、召公在岐山地区采邑中的乐歌。
“二南”为《诗经》最为重要的篇章之一,其名义由来竟至今难有定论。 鉴于此,本文将从历史地理的考察入手,正本清源,探究“周南”“召南”之意义,考察二者完篇之背景与得名之由来。
一、论“二南”作于周公、召公南征后所封诸姬
(一)“二南”所涉地理名物的南北冲突
对于“二南”名义由来的分歧,核心问题在于“二南” 指的是周公、 召公的采邑还是南方诸侯之国。这俨然是历史地理层面的问题,以往马瑞辰、陈致等人纠结于“南”字字义,苦心从训诂之中寻找外证,而对《诗经》内本身明确称呼的地理名物有所忽视,即是未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路径。笔者以为,考察“二南”名义,仍需从《周南》《召南》诗篇中的地理名物入手。
“二南”诸诗明确指明了诗作者所见河流之名。在《周南》中,《关雎》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1](P570)“河”即黄河,周时为王畿所在,则《周南》作者似当长居于中原之地。 《汉广》 曰:“汉有游女, 不可求思。 ”[1](P592)可知《周南》作者又能亲见汉水。 又《汝坟》曰:“遵彼汝坟,伐其条枚。 未见君子,惄如调饥。 ”《毛传》曰:“汝,水名也。 坟,大防也。 ”[1](P593)则“汝坟”即指汝水之畔,是诗作者亲涉其境。如此,则“周南”境内似乎涉及黄河、汉水、汝水三条河流。《召南》所录河流不多,然其《江有汜》一诗即涉周之江水,亦及今之长江,而其中“江有沱”一语又兼及江之支流沱水。
仅从河流上来看,“二南” 所涉区域难以确定。黄河虽至今几经改道,但在西周时期,宗周、陕等周朝核心区域仍主要分布在黄河中游,“河”往往是周朝核心区域的标志。 而汝水为淮水支流,据《水经》所载,“汝水出河南梁县勉乡西天息山……南入于淮”[5](P497-508),则自北至南皆距黄河颇远。 至于汉水或者说沔水,则“沔水出武都沮县东狼谷中”[5](P642),而最终“沔水与江合流,又东过彭蠡泽。”[5](P682),更在汝水之南。 除此之外,南方的江水距离黄河更加遥远。 由此而言,“二南”的范围似乎北至黄河所在的中原地区,而南涉南方诸侯之国。 这一过于广袤的范围,正是阻挠前儒确定“二南”地域的一大因素。
另外,《召南》中经常出现“南山”这一名物,《草虫》曰:“陟彼南山,言采其蕨。 ”[1](P601)《殷其雷》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阳。”[1](P609)《草虫》传提及:“南山,周南山也。 ”[1](P601)按“周南山”即周王畿内终南山,《小雅》有“南山有台”[1](P897)“节彼南山”[1](P943)“幽幽南山”[1](P934)等句;至于东周之时,秦收周朝故地,南山又入秦国境内,《秦风》遂亦有《终南》之诗。 以此山目之,“二南”又似当出畿内。
但在草木等名目上,“二南”仍有较多的南方特征。《葛覃》《樛木》诸诗多言葛藟,《毛传》即曰:“南土之葛藟茂盛。 ”[1](P585)至少在毛公看来,葛藟当为于南方更为多见的植物。 又《汉广》提及“南有乔木”[1](P592),考《禹贡》可知,南方扬州“厥木惟乔”[1](P312),高大树木正是周代南方的特点。 此外,《召南》多言水滨之事,多有“于沼于沚”“于涧之中”[1](P597)“南涧之滨”“于彼行潦”[1](P602)之语,虽然水泽并非南方独有之物,然而北方国风鲜有多言水泽者,反而《禹贡》载荆、扬等南方州“厥土惟涂泥”[1](P312),则当时南方多低湿之地,更有可能是《采蘩》《采蘋》的写作地点。
综上所论,从地理范围上言,“二南”所提及的名物既有周室地区的特征, 又多涉及南方之物,似乎简单地执“南方诸国说”或“周召采邑说”都不合适。 事实上,问题的解决需要在基本预设上进行转换, 诗作者所写名物未必能代表其切实身处之境,“二南” 的写作地点与作者素来生活的地方可能原本并不一致。
(二)北人南迁视角
“二南”的诗作者往往确实身处南方,如《汝坟》言“遵彼汝坟,伐其条枚”[1](P593),非身在汝水者不可言之。《汉广》言“之子于归,言秣其马”[1](P592),非身在汉水者不可亲秣。 且于乔木、樛木、葛藟等南方名物,诗作者皆细为描摹,可见均为诗人常能亲见之物。
然而,“二南”诗作者却多似北人身份,诗中视角皆非南人所自有。 《汉广》曰:“南有乔木,不可休息。 ”[1](P592)《樛木》曰:“南有樛木,葛藟累之。 ”[1](P585)南人称自身生长之地曰“南有”,即于情理不合;唯有以北人身份视南方之物,方才会有“南有”之言,以示此等名物皆为北方所无。 如《小雅》亦有《南有嘉鱼》一诗,即为周王畿内贵族述说南方江、汉名物之语,则“南有”之辞非南人本身所有,《召南》诸诗亦当为北方来客评判南方名物之论。
就此而言,“二南”的诗作者大多是以北人身份身处南方。 而又可以确定的是,“二南”诗作者几乎都是贵族身份,如《关雎》所提及的“琴瑟”“钟鼓”,于当时皆为重器,非士大夫不能有之。 而《葛覃》提及“言告师氏”,《毛传》曰:“师,女师也。古者女师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1](P580)女师为当时贵族教导家中女子时所设的女官,则《葛覃》作者亦当为贵族女子。又《樛木》言“乐只君子”[1](P585),《汝坟》言“未见君子”[1](P593),《草虫》言“未见 君 子”[1](P602),《殷其雷》言“振振君子”[1](P609)。 “君子”之称于西周时为上层贵族所特有, 则此诸诗皆当为贵族家眷所作。
(三)周公南征故事
北方贵族大规模向南方迁移,并非建国承平已久后所能见到的寻常事件,典籍中能相合者亦不为多。 唯《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提到“汉阳诸姬,楚实尽之”[1](P3961)之说,恰能证明周初之时,汉阳地区分封了大量周室同姓诸侯。细考汉阳诸姬之分布地域,不论是杨东晨、杨建国在《汉阳诸姬国史述考》一文考得汉水、淮水南北流域的11 个姬姓诸侯国[6],还是杨宽等学者确定的随、唐二国属于汉阳诸姬[7](P388),抑或于薇认为“汉阳诸姬”是“淮阳诸姬”的讹传[8],均不妨碍这些淮汉流域的封国与“二南”中所涉及的汉水、汝水在地理位置上相互重合的事实。 包括名震一时的曾侯乙之墓,即同样位于汉水之畔。 由此而言,“二南” 的诗作者就很可能是在周初之时,从宗周向南方迁徙的姬姓贵族。 唯有此,才能够解答“二南”之中看似互相矛盾的南北名物。
诸诗作者原生中原, 故多有对中原地区的记忆,黄河、终南山会出现于“二南”诗篇之中本自寻常。 而且,西周素有“小有述职,大有巡功”[1](P4434)的传统,这些南方诸侯皆为周室同姓,与王室自然交流密切,如《何彼襛矣》描述齐侯之子往周室求娶周王之女的场景,即有可能是南方贵族随诸侯向中央述职时所亲见。 在作诗者并非生于南土的情况下,才可能导致“二南”中既多有南方名物,却又记录了周朝核心地区事物的现象。
由此,“二南”作诗者的身份与地域已可获得解答,但“二南”既为南方周室贵族所作,为何又以“周”“召”为名?事实上,周公、召公与南方之间的关联于史记载不多,但仍有证据证明,周公、召公曾有征伐南国、经营南方的事迹。《荀子·王制》载:“故周公南征而北国怨。 ”[9](P173)《乐记》言《武》乐所载周初事迹时,同样提到:“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郑玄解释“南国是疆”之语曰:“四奏,象南方荆蛮之国侵畔者服也。”[1](P3343)《乐记》之言明确指出,武王伐纣后南还期间,又有平叛南方、分封南土之事[1](P3343)。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一南征事迹之后,周公、召公才被委以重任、分职而治,则周公、召公在南征中的作用大可推致而知。
近年的出土材料进一步佐证了周公、召公征伐南方的史实,如柞伯鼎明确记载了周公曾“广伐南国”[10]。 由此证实,南方诸国确实是周公、召公耗费大量精力所平定、征服的区域,而淮汉诸姬多是在平定南方后所逐渐分封的同姓诸侯。以此史事作为参照,《周南》 便是周公征伐的南方区域中所封贵族所写诗歌,《召南》则是召公平定南土中贵族所作篇目。
另外,《诗经》文本本身多有对周、召二公经营南土事迹的歌颂。 从“二南”的记述中可以发现,南土为周、召二公曾经亲至之所,南国贵族对二公多所缅怀,如《甘棠》即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1](P604)正由于以上原因,“二南”遂被冠以“周”“召”之名。
(四)“二南”为淮汉诸姬所作的师法依据
以周、召南营江汉的历史事件解释“二南”的来源似无前说,或悖于经典《诗经》师法。 但在笔者看来,此说非但不与《毛诗序》的经典解释冲突,反而更能清晰地阐发《诗序》所谓“南,言化自北而南”的意涵:自北而南之化指的并不仅仅是抽象地歌颂文王之道远及南方,更是周公、召公实际意义上平定南方并施行周政的事件。
以往学者往往不能明“二南”出于淮汉诸姬之史事,遂仅将“化自北而南”理解为在文化层面上的事件,如陆德明曰:“南者,言周之德化自岐阳而先被南方。 ”[1](P561)竟使这一层周人经营南方的政治事实隐而不显,“化自北而南”成了并无“行事”的歌功颂德之语。 其实,如以周公、召公南征定国之事视之,《诗大序》所谓的“《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言化自北而南”[1](P569)实际均非“空言”,它们指的正是在周公、召公平定南方后,封于南国的周室贵族作“二南”之诗,以彰显周、召二公安定南方、奠定周室太平之基的不朽功业。
当然,证无三不立,以上仅是从诗文本内部名物的角度进行论证,固不足为“二南”出于淮汉诸姬之铁证。但如对“二南”写作时间加以考辨,发现“二南”之诗当作于周初之时,周、召南征故事正是“二南”唯一可能的时代背景。
二、论“二南”作于周公、召公主政时期
(一)论“二南”不为东周时诗
对于“二南”的写作年代,学者多将其定为周初时诗,但在确定其为文王时诗还是康王时诗有些许分歧。 至于近代,翟相君《二南系东周王室诗》一文以《何彼襛矣》一诗中提及的“平王之孙”作为主要证据,将“二南”定为东周时诗[11]。 马银琴又补充了《史记》中“周室衰而《关雎》作”这一说法,则试图论证“二南”是东周畿内之诗[12]。
然而,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来看,将二南看作东周时诗问题颇多。 首先,《秦本纪》记载:“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 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 ”[13](P179)东周之初,岐周故地、西周王畿大半土地皆为秦土。 “二南”之中,属于岐周故地的“周南山”履见,如“二南”为东周时诗,则俨然应称“秦南”而非“周南”“召南”。 其次,自周昭王末年以来,南方诸国已渐不服于周,昭王末年楚国先叛,《左传》有“昭王南征而不复”[1](P3891)之说。 宣王时淮汉诸夷多有不服,《大雅》乃有《江汉》《常武》之诗。至于东周,僖公二十年“随以汉东诸侯判楚”[1](P3930),则春秋初淮汉诸国已多归附楚国; 至于僖二十八年,晋栾贞子更有“汉阳诸姬,楚实尽之”[1](P3961)之说。 “二南”为国风之首,并且后来都被用作仪式用乐,断无采自楚国势大并与周朝抗衡时期的南方诗歌的道理。因此,唯有周初楚子仍为周臣,汉阳诸姬以藩屏周之时,“周南”“召南”之名才有可能。
除此之外,“二南” 为东周时诗说的几项关键证据仍值得商榷。 对于《何彼襛矣》“平王之孙”一句,郑玄、孔颖达等人皆释“平王”为“德能正天下之王”[1](P617-618),唯朱熹引时人之说云:“或曰:‘平王,即平王宜臼。 齐侯,即襄公诸儿。 事见《春秋》。 ’”[2](P16)翟相君则认为“平王”为东周平王宜臼。 此说对“二南”周初说确为一大挑战,然考齐襄公时嫁于齐之王姬,《公羊传》曰:“秋,七月,齐王姬卒。 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 录焉尔。 曷为录焉尔? 我主之也。”[1](P4832)则按《春秋》书法,王姬非嫁齐侯之子,直嫁襄公而为夫人也。 又《礼记·檀弓》曰:“齐穀王姬之丧,鲁庄公为之大功。 ”[1](P2815)如王姬仅嫁于齐侯公子,鲁侯无为服大功之理,郑玄亦用公羊之义,以王姬为襄公之妻。且齐人迎周王姬于鲁,如“齐侯之子”为襄公,则《召南》竟为《鲁风》。 其实,周人对天子多有“明王”“圣王”之称,“平王”于构词法上与之无异,作为代指周初之王的美称实无不妥。
至于《史记》“周室衰而《关雎》作”一句,亦不指东周之衰。 司马迁所学原为鲁诗,然鲁诗实以康王时为周衰。同传鲁诗的刘向即曰:“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关雎》豫兴,思得淑女以配君子。 ”[14](P90)王充《论衡》亦针对鲁诗家,引鲁诗之论曰:“彼将曰:‘周衰而诗作,盖康王时也。 ’”[15](P562)《史记》之“周衰”,亦不过谓康王德衰而已。且司马迁又以《甘棠》之诗为“民人思召公之政”[13](P1550)所作,则《召南》亦去召康公之时不远。 由此而言,《史记》并不能成为东周说的佐证。
(二)论“二南”不作于周宣王时
部分学者认为,“二南”中部分诗篇当出于西周宣王时期。 如程俊英、蒋见元之《诗经注析》及陆侃如、冯浣君之《中国诗史》,均以为周人以“召公”专称康公,以“召伯”专称穆公,则《甘棠》之“召伯”为召伯虎[16](P38)[17](P68-69)。 但是,这一论述同样存在无法解决的问题。
首先,近年出土器物纷纷可证“二南”不为宣王之诗。 季旭升从青铜器铭文出发,已明确《甘棠》之“召伯”更可能是召公奭,未必为后来之穆公[18](P19-29)。而《卷耳》有“我姑酌彼金罍”之语,吴晓峰指出,罍仅多见于周初, 至西周中后期已非常见器物[19](P215-222)。此皆前人成论,固不必复加申说。
其次,宣王时期的时代背景与“二南”全然不合。召穆公为宣王南征功臣,诗史皆有其证,但没有任何记载可以表明宣王时的周公曾参与南征事宜。如“二南”为宣王时诗,则但当有《召南》而已。 即使有《周南》之篇,周公之功亦远不及召公,其诗固当置于《召南》之后,不宜为十五国风之首。 且季札称“二南”为“始基之矣”[1](P4356),宣王为西周中兴之主,后期又国势转衰,何以得称“始基”?
再次,如以“二南”为召穆公所平南方之诗,无法解释“二南”中出现的北方名物。淮阳诸姬大多皆封于周初,宣王虽平南夷,但封申伯“登是南邦”而已。则宣王之时,南国诸姬大多生长于南方封地,难有北人南视视角,完全无法解释“二南”名物的地理特殊性。
就此而言, 东周时说与宣王时说皆存在困难。比起此类仅从文本内部望文生义的新说,存在大量传世史料相证的西周初期说更值得信服。因文武成康时期的时势不尽相同,“二南” 具体写作何时,仍需要进一步的确定与澄清。
(三)“二南”作于周、召主政时的师法依据
如按上文之论,“二南”与周初贵族迁徙南方事迹正合,则其应为武王至成王时,周、召二公主政时期的诗篇。但鲁诗将《关雎》为首的“二南”诗定为康王时诗。 郑玄则将“二南”定为文王时诗,如《汝坟笺》曰:“是时纣存。 ”[1](P593)《行露笺》曰:“此殷之末世。 ”[1](P605)在郑玄诗学中,“二南”写作之时殷纣尚存,当为文王时诗。如此,鲁诗与郑玄的说法虽然都将“二南”定为周初,却都不与周公南征、南封诸姬的时间相吻合。
考郑玄《诗经》之学,原主韩氏,后转毛学,其说解多杂韩诗他说, 未必能达毛公本意者比比皆是,胡承珙、马瑞辰等清儒已有详论。 至于定“二南”之作为文王时,郑氏实亦本于韩诗之说,未必能解《诗序》原意。 郑说本韩诗之证,见于刘良《文选注》中《兔苴》 诗解:“殷纣之贤人退于山林, 网禽兽而食之。 ”[20](P708)刘良素来多本韩学,“二南”为殷纣时诗这一说法固亦可以系于韩氏。如仅从《毛诗》家法出发,《诗序》始终将“二南”定为周公、召公行政之时的诗篇,其篇目亦大多确实作于武王、成王之时。
首先,在毛诗的解释下,《周南》《召南》紧密系于周、召二公,如《甘棠序》曰:“美召伯也。”[1](P604)《行露序》曰:“召伯听讼也。 ”[1](P605)而从现存史料来看,文王之时,周公、召公尚未成为至重之臣,如《史记》载:“帝纣乃囚西伯於羑里,闳夭之徒患之。 ”[13](P116)文王时期,周室主事之人仍以宏夭、散宜生等异姓大夫为主。至于武王即位以后,方有重用同姓之事:“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脩文王绪业。 ”[13](P120)武王即位,作为武王兄弟的周公、召公乃初掌权势,成为周室的辅弼重臣。至于成王即位以后,周公成为摄政大臣,即《史记》所谓“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召公为保,周公为师”[13](P132)也。当此之时,周公、召公方才位更居公望等文王时期重用的异姓大臣之上, 成为周室的头等权臣。因此,如将《甘棠》《行露》定为美召公之诗,则“二南”自当作于成王即位前后,周公、召公主政之时。
其次,更明确的内证则是《诗大序》所言:“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 《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 ”郑玄受韩诗影响,默认“二南”为文王时诗,故而注曰:“先王,斥大王、王季。 ”[1](P569)但是,考察之后的《诗序》所提及的“先王之道”,皆毫无疑问地指称“文王之道”,《汉广序》即曰:“文王之道,被于南国。”[1](P592)《汝坟序》曰:“文王之化行乎汝坟之国。”[1](P593)俱以文王为先王,而无一处提及大王、王季。且如《摽有梅序》曰:“召南之国,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时也。”[1](P612)如作诗为文王之时,召公未受重用,无称南国为“召南”之理,则“文王之化”非谓文王自身经营南国,当指召公南播文王之道,使南国得化。 唯《江有汜序》言“文王之时”, 似以此诗作于文王在世之时, 然细观毛序之意,仅是表明文王之时的江沱地域“有嫡不以其媵备数”,至作诗、采诗之时,已是多年后的“媵遇劳而无怨,嫡亦自悔也”[1](P614),则作序者亦未必以此诗为文王在世之时所采。 总体而言,在毛诗体系中,“二南”皆视文王为先王,作诗、采诗之时文王早已作古,所谓“文王之化”“文王之道”往往仅指周、召二公继承文王之道,以文王成法治理二南之国。 这一观点,便与之前的考证完全吻合。
因此,以“二南”为周初南国诸姬所作之诗恰最合《毛诗序》本义。 而在几家经典诗说的合理性上,毛氏之说同样显得更为合理,于时于地完全可与诸多史料互证。 鲁诗之说,王充即已疑之曰:“二王之时皆衰,夏、殷衰时,诗何不作? ”[15](P563)韩诗之说,亦别无依据。唯有从毛之旨,将“二南”确定为周公、召公南伐后分封的淮汉周室宗亲所作之诗,方才能化解来自文本内部、外部的一系列矛盾,达成时间与空间上的融贯性真理。
事实上,《左传》中所载“季札观乐”之事已经很好说明了东周时人对于“二南” 成书年代的定位:“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 ’”[1](P4356)季札已经明确指明,“二南”为周初奠定始基时所出现的诗篇,而按本文所论,季札所谓“勤而不怨”指的正是周公、召公苦心平定南方、封建亲戚的事迹。
三、“二南”诗作的“偃武修文”性质
不过,“二南” 中的诗篇并未过多叙述周公、召公用武力平定南方之事,反而多言嫁娶之事,如《关雎》思以贤女配于君上,《葛覃》颂妇德、妇功,《汉广》求汉之游女,《鹊巢》叙娶妻之事,《行露》斥娶妻无礼之男,《摽有梅》《野有死麕》等诗亦多劝男女嫁娶得时、娶妻不逾于礼。究其原因,周公征伐之功业均已系于《豳风》,如《七月》《鸱鸮》为周公东居自作之诗,《东山》以下则为美周公功业之作。 而“二南”往往专用于房中之乐,郑玄《仪礼·燕礼》即注“遂歌乡乐”句曰:“《周南》、《召南》,《国风》篇也。 王后、国君夫人房中之乐歌也。”[1](P2128)二南之演奏对象往往为后妃、夫人,如《豳风》中“周公东征,四国是皇”[1](P850)之句即显不合时宜,故“二南”多取能够凸显南方女子嫁娶不失于礼的诗篇,从而强调后妃、夫人的妇德、妇功。
比起《豳风》的歌颂武功,“二南”更能体现周王朝偃武修文之德。克殷以后,武王即“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虚,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也”[13](P129),周公更有“治天下六年,朝诸侯於明堂,制礼作乐”[1](P3224)的不世之功。 周室素重文教,周公、召公平定南方以后,必然同样会用怀柔的方式巩固南国,因此“二南”多见周人对汉水等地南方女子的求娶事迹,亦颇为强调嫁娶不失于礼。 正是这种太平气象,遂使“二南”成为列于《诗经》首篇的正风,所谓:“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1](P562)“二南”天下太平而夫妇可正的意涵可为天下楷模,故“二南”于礼经中不止为房中之乐,更可为用于邦国之乡乐。
由此而言,周人之所以如此重视“二南”,并将其广泛用于各种礼乐场合之中,即可得到理解。《诗序》正是在偃武修文的背景下理解“二南”的,“后妃之德”“夫人之德”均未必出于作诗者之本意,但成于淮汉的“二南”诗篇作为南方诸姬“正婚姻”的直接体现,恰是教化后妃、夫人,乃至风化天下的最佳榜样。 《诗序》曰:“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1](P565)此之谓也。
综上, 本文以历史名物的特殊性作为出发点,结合周公南征、封建淮汉的事迹,将“二南”确定为周公、召公经营南方时分封贵族所作之诗。 又通过对“二南”作于周初的时代论证,加强了论证的可靠性。 这与传世《诗序》相合不悖,不仅使“二南”本义得到澄清,亦能令《诗序》原意得到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