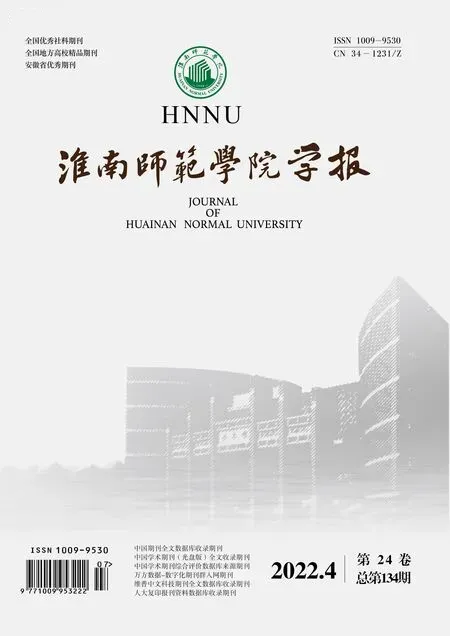黑暗与光明的交织:《八月之光》中的异托邦建构
卜立进,刘 娟
(淮南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南 232038)
《八月之光》 是20 世纪美国文学巨匠威廉·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的核心作品之一。作品以美国南方传统守旧的杰弗生镇为背景,铺呈丽娜和乔·克里斯默斯两位主要人物的叙事线索。丽娜未婚有孕,挺着大肚子,长途跋涉来到杰弗生镇寻找孩子的父亲。 当她来到小镇后,另一位主人公乔·克里斯默斯的悲惨人生徐徐展开。 克里斯默斯从一出生便因身上一脉莫须有的“黑人血统”被排斥在黑白两个种族之外,身心倍受折磨,最终因杀死白种情人而被白人种族主义者残忍杀害,沦为种族博弈的牺牲品。
目前,国内研究者大多运用叙事学、结构主义、存在主义、女性主义、心理分析、神话原型等批评方法,探讨该小说在叙事艺术、人物塑造,及种族和宗教等方面的艺术成就及主题。及至最近10 年来,国内学界开始关注小说中的叙事空间问题,且主要集中在空间隐喻和空间叙述形式两个方面。 而关于《八月之光》的异托邦,即异质空间研究,目前只有2013 年周文娟发表的一篇论文。 周文娟认为,福克纳作品中存在很多异质空间书写形式,具体到《八月之光》, 则体现在“人物生存空间叠加异质结构空间”[1]。 作家在杰弗生镇这个场景中同时并置了代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海托华、克里斯默斯和丽娜的故事, 这种将过去和现在生存空间的并置叠加,形成了小说叙事结构的异质性, 极大地延展了小说所凸显的主题倾向。
本文将借助福柯的异托邦理论, 进一步探讨《八月之光》中的异质空间书写形式——明暗交织、互为对照的异托邦建构,及其背后的空间隐喻。 以期更深入了解福克纳小说叙事的空间诗学,了解文本中的异托邦建构如何凸显和深化了小说主题,并加深对福克纳人文主义思想的认识。
一、福柯的异托邦理论
异托邦是福柯哲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福柯将其定义为“在所有文化中,在所有文明中,都存在着这样一些真实的场所、有效的场所,它们被书写入社会体制自身内, 它们是一种反位所的场所,它们是被实际实现了的乌托邦, 在这些场所中,真实的位所,所有能在文化内被发现的其他真实的位所被同时表征出来,被抗议并且被颠倒;这些场所是外在与所有的场所的,尽管它们实际上是局部化的。 因为这些场所全然不同于它们所反映,它们所言及的所有位所,所以,与乌托邦相对立,我称它们为异托邦。”[2](P22)据此,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异托邦的内涵。
一方面,和乌托邦不同,异托邦是一个真实的、局部的位所, 是在社会体制内获得认可的现实场所。另一方面,如同镜子能够映照出周围的一切,异托邦也能映照出文化范围内的所有其他真实位所。人在镜子的映照下可以意识到自身以及自身所处空间的真实性,并观察、思考、重组自身。 文化范围内所有其他真实位所在异托邦的参照下,也可以反观、思考并重组自身。 例如,相对于红尘俗世,寺庙就是个异托邦,它就像一面镜子,让人们更深切地意识到自己身处的红尘俗世的存在,并通过寺庙的安静和清心寡欲认识和反思俗世的喧嚣和人心浮躁。 寺庙的空间秩序不同于俗世的常规秩序,甚至抗议、否定、颠倒世俗常规秩序。 因此说,异托邦能够反映、呈现、甚至抗议或颠倒在文化内被发现的其他常规空间。
为了更准确阐释和定义异托邦,福柯还进一步描述了异托邦的六个原理: 异托邦的文化普遍性、异托邦的文化同步性、空间并置与叠加、异时异托邦、禁区式异托邦、异托邦与其他空间的关联性,而且只要满足其中之一便可构成异托邦空间。
根据福柯的异托邦理论,《八月之光》中的两位主人公丽娜和克里斯默斯的生活空间就明显构成了一明一暗、互为对照的异托邦空间,前者充满光明和温暖,具有抚慰人心的力量;后者却满是苦难折磨,暗黑无光,震撼人心。
二、克里斯默斯的生活空间:黑暗的异托邦
(一)偏离性异托邦
福柯在描述异托邦第一个原理时明确指出,异托邦在人类所有文化中是普遍存在的,而且“显然采取了极其多样的形态”[2](P23)。 其中,“危机异位”因为与一些特权性、 神圣或禁忌性的古老场所有关在当今社会逐渐消失,“它正在被所谓的偏离(deviation)所取代:在这些偏离中的个体,就与中庸或被要求的常态的关系而言, 其行为乃是偏离性的。”[2](P23)可见,“偏离性异托邦”指的正是游离于主流文化所规定的常态之外,能够表征主流文化空间,但与主流文化形式相偏离甚或相对抗的“他者”性的空间形式,它“凸显着人的不同群体之间在文化规范、社会思想或者风俗习惯方面的鸿沟,它在一个文化的内部划分出属于这个文化中的特殊群体的空间”[3]。 小说中伯顿小姐家的大宅正是这样一个偏离性异托邦。
伯顿家大宅是克里斯默斯成为伯顿小姐的情人后经常出入的地方,是他最后一段人生历程中主要的生活空间,它的偏离性异托邦属性从它的物理空间就可窥见一斑。
伯顿家大宅虽然在杰弗生镇上,但却离镇中心半英里远,孤零零地矗立在一片小树林中,只露出一根烟囱,周围零散地分布着一些黑人小木屋。 远离镇中心, 暗示了它与杰弗生镇在空间上的疏离,位于以白人为中心的杰弗生镇的“边缘”位置,是以杰弗生镇为代表的白人主流文化空间的“他者”。之所以成为“他者”,用杰弗生镇上的白人的话说,就是“她是一个支持黑人的美国佬”[4](P32)。 伯顿小姐的先辈是南北战争后的重建时期从北方迁过来的,坚持废奴主义,她祖父和兄弟也因支持黑奴在州政府的选举权而被一位前农奴主杀害。 年过40 仍单身的伯顿小姐每天处理的也都是与黑人有关的教育、法律事务等,因此受到附近“有色乡亲们”的照顾,来拜访她的也只有黑人妇女。在奉行白人至上的美国南方小镇上,支持和帮助黑人就是对主流文化形式的一种“偏离”,甚至“对抗”,这就使得伯顿家大宅拥有了“偏离性异托邦”属性。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与黑人生活空间的重合,相反,大宅和周围的黑人小木屋之间也总隔着小树林和浓密的灌木丛。屏障的存在清楚地表明了大宅与黑人文化空间的距离感。这是因为从家族继承的清教种族主义观念让伯顿坚信黑人是上帝施加在白人身上的诅咒,对她来说,所有的白人,“已经出世的和没有出世的……都被钉在黑色的十字架上”[4](P178),因此,她认同父亲的观点:“你必须斗争,站起来。为了站起来,你必须把黑影一同举起。 不过你永远也无法将它举到和你一样的高度”[4](P178)。
由此可见,作为一个游离于“白人至上”主流文化形式之外的“偏离性异托邦”,伯顿家大宅既是白人主流文化空间的“他者”,又排斥黑人文化空间,暗示了伯顿家族在对待黑人问题上的矛盾之处。伯顿小姐帮助黑人也不是发自内心的同情和支持,而只是为了消除白人身上的黑人诅咒。 “尽管自称是帮助黑人的废奴主义者,伯顿从未摆脱潜意识中白人的种族主义偏见。 ”[5]因为意识到这一点,克里斯默斯和她在一起觉得自己“像被无底的深渊吞噬了一样,……此刻,他所看到的还是那条寂静、荒芜、凄凉的道路”[4](P184)。 克里斯默斯口中那条“道路”指的正是“一次对无种族主义困扰的‘乌托邦’地带的苦寻,也是对最终内心宁静的矢志追求”[5]。 可惜的是, 虽然克里斯默斯来到了这个看似敢于抵制、反抗“白人至上”主流文化空间的异托邦地带,但早已渗透其中的清教种族主义让他的追寻再次陷入更加黑暗的深渊。 所以,当伯顿小姐要求他上黑人学校时,他一生都在不断进行的对自我种族文化身份的追寻彻底幻灭,最终,克里斯默斯杀死了伯顿小姐,并放火烧了整个大宅,也因此被白人种族主义者枪杀并阉割。
(二)禁区式异托邦建构
除了伯顿家大宅,小说中提到的克里斯默斯的重要生活空间还有孤儿院和养父母的家。
这三个生活空间算是克里斯默斯拥有的最接近“家”的地方,但可惜的是,对克里斯默斯来说,它们都是他无法真正融入的“禁区式异托邦”空间。
福柯的异托邦第五原理指出:“异位总是假定了一个开放的和关闭的系统,这个系统使异位孤立起来,并使之同时具有可渗透性”[2](P26)。 可见,异托邦并不是一个可以自由出入的空间,它可能会被设定成一个“禁区”,不被允许进入或者是有条件被允许进入,正如福柯所提到的军营、监狱或宗教圣地。军营和监狱之所以构成异托邦,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们都具有“禁区”的性质,是人们不被允许进入的空间,而宗教圣地虽然有时可以进入,但必须遵从某些“仪式或净身”[2](P26)。
如果此处福柯所说的异托邦是一种完全关闭或者一种看似关闭的“禁区”——因为实际上往往有允许进入的条件,因此有开放的可能性,那么福柯随后提到的就是一种看似开放,但实际上却是无法真正进入的“禁区”式空间。 这样的异托邦具有“一些奇特的排斥……。 任何人都可以进入这些异位的位所,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幻觉:他相信自己正在走进去,正是由于这一进入,他也就被排斥在外了”[2](P26)。 福柯认为巴西或南美大农场中一些有名的房子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些房子可供任何陌生的路人或旅行者推门进去休息,但因为它们远离全家起居的中心屋子, 是远离家庭核心的边缘所在,因此,进入这些房子同时也就意味着无法接近家庭核心,始终是家庭核心的“他者”。 对克里斯默斯来说,孤儿院、养父母的家和伯顿家的大宅正是这种看似开放,但其实却总是让他成为“他者”的“禁区式异托邦”。
孤儿院是克里斯默斯有记忆以来第一个“家”,但在他的记忆中,孤儿院始终是一个“长期处于混乱、 冷清状态的大房子”,“房子外暗红色的砖墙被……熏得乌黑、惨淡;屋外铺满炉渣的空地寸草不生”[4](P83)。 “混乱”“清冷”“乌黑”“惨淡”“寸草不生”暗示了克里斯默斯在孤儿院里始终缺乏温暖和关爱。 他在孤儿院里总是一个人待着,不和其他孩子一起玩,因为他们总是喊他“黑鬼”。 虽然年幼的孩子尚不知道“黑鬼”的准确含义,但显然隐隐的不安让克里斯默斯逐渐远离其他孩子。 不仅如此,由于克里斯默斯无意中撞到年轻女营养师与情人的“奸情”,为防止克里斯默斯泄密,女营养师对他进行疯狂的报复,并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故意向孤儿院女总管透露他是“黑鬼”。 女总管一得知这个消息,便“果断而决绝”地说:“我们得处理他,立即处理他”[4](P95)。 显然,克里斯默斯成为了孤儿院中必须被“立即处理掉” 的 “异类”。 如果说孤儿院是一个“家”,那克里斯默斯因为莫须有的“黑鬼”身份,始终无法成为这个“家庭”中的一员。
克里斯默斯被孤儿院“处理”的结果是很快被麦克依琴夫妇收养,但孤儿院隐瞒了他可能是“黑鬼”的真相。 麦克依琴先生是一个严厉地近乎冷酷的清教徒,如果年幼的克里斯默斯没有背出《长老教会要理》的相关内容,或者没有达到他的要求,就会遭到一顿毒打。克里斯默斯和麦克依琴夫妇虽然共同生活了十几年时间,但他却无法真正融入这个家, 他与麦克依琴先生始终处于一种敌对的状态,对麦克依琴太太也充满恨意。 究其原因,首先是麦克依琴的冷酷,不仅让自己和克里斯默斯始终处于对立的两端,还让从小就没有获得过温暖和关爱的克里斯默斯无法回应麦克依琴偶尔流露出温暖和关爱, 当麦克依琴太太小心翼翼地试图表达对他的关心和爱护的时候,“他对她的恨意比对那个冷酷决绝的男人还要强烈”,就是因为他觉得“她千方百计想把我弄哭”[4](P118)。其次,“黑鬼”身份是阻止他融入这个家的更深层原因。他十分清楚一旦“家人”——尤其是养父——知道他可能有黑人血统后的反应。这就是为什么他为了报答麦克依琴太太对他的关心曾经想说出真相, 然后打算永远不再出现的原因。对克里斯默斯来说,养父母的家表面上对他是开放的,但实际上却是“可能是黑人”的他永远无法真正进入的“禁区式空间”。刚成年的克里斯默斯无数次从楼上的窗口借助绳子偷偷溜出家的行为正是隐喻了他对这个“家”的逃离。最后他无意中杀死养父并从此四处流浪更是彻底脱离了这个“家”。
伯顿小姐家的大宅是克里斯默斯最后一个重要的生活空间。 虽然他经常出入大宅,但都是在晚上偷偷溜进去,他自己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从没有真正收到过她的邀请进入那幢房子里”, 而且他总是“觉得自己像个小偷、强盗,甚至当他爬上楼梯, 走进她等候的卧室时, 他一直都是这样的想法。”[4](P164)他们即便是情人关系,但因为伯顿小姐的清教种族主义观念, 他们之间似乎只有肉体的交流,而无思想的共鸣,更无内心的归属,克里斯默斯更是觉得“这不是我的生活,我不属于这里”[4](P182)。因为黑白种族冲突的存在, 克里斯默斯始终无法、也不愿真正进入大宅。 最后,克里斯默斯杀死伯顿小姐并烧毁整座房子更表明了他与“大宅”的决裂。
从孤儿院到养父母的家再到伯顿家大宅,代表了克里斯默斯从童年到青年再到中年的整个人生历程。 但无论在哪一个“禁区式异托邦”,克里斯默斯无法真正进入的原因归根结底都是其身上可能的黑人血统。而造成克里斯默斯悲惨一生的最初推手就是他的外祖父老海因斯先生。老海因斯先生是一个狂热的近乎疯狂的清教种族主义者,对于清教妇道观和种族观念有着无比强烈的执念,认为女性的“放荡”和黑人血统都是对上帝的亵渎,是必须被消除的魔鬼般的恶行。 因此,只因女儿的情人可能带有黑人血统就将其枪杀, 并放任女儿难产而死,之后更是把尚在襁褓的外孙扔在孤儿院门口,自己也来到孤儿院工作,替上帝监视在人间行走的“魔鬼的种子”,并在上帝选定的“合适的时机”采取“恰当的行动”。可以说,老海因斯的极端行为直接影响了后来克里斯默斯悲惨的人生走向,其养父助推了他人生的悲剧。 可见,通过这些“禁区式异托邦”建构, 福克纳将美国南方清教种族主义推到幕前,通过展现它对人性的摧残对之展开尖锐的批判。
无独有偶, 作家在描述这三个重要生活空间时,出现的最多的修饰语都与“黑”有关系:孤儿院里被烟囱“熏得乌黑、惨淡”的砖墙,“晦暗的墙壁”,玻璃上雨水冲刷成的“黑色的泪痕”; 养父母家中“朦胧灰暗的栅栏”,里面有一个等待交媾的黑人女孩的“黑乎乎的”刨木棚,附近“黑黢黢的丛林”;伯顿家掩映在树林中的大宅也是“黑乎乎”“阴暗”的,他们幽会的丛林“半明半暗”,连附属与大宅的小木屋也是“一片漆黑”“光线全无”等等。这一切仿佛都在暗示,从出生开始,带着一脉可能的黑人血统的“混血儿”克里斯默斯在奉行“白人至上”的主流文化空间、在清教种族主义根深蒂固的美国南方必将承受充满苦难与磨难的生命之重。
三、丽娜的生活空间:光明的异托邦
如果说,福克纳通过叙述克里斯默斯生活空间的黑暗深刻地揭露了南方清教种族主义对人性的无尽摧残,凸显作家的种族关怀,那作家对小说中另一主人公丽娜的生活空间的“船舶式异托邦”构建则展示了作家对人类美好人性的自信和期盼,体现了作家的人文主义情怀。
福柯的异托邦第六原理指出:“异位有一种与其他空间相关的功能。这种功能散布于两个极端之间。 ”[2](P27)这两个极端分别是幻觉性异位和补偿性异位。 根据福柯的阐释,幻觉性异位可以让人身处其中而感受不到真实空间中各种常规社会规约的束缚,可以让人暂时摆脱真实社会空间中的常规秩序,一如妓院;补偿性异位却可以创造出一个比紊乱不堪的现实空间更加完善和严密、更加秩序井然的近乎完美的空间,就像某些“殖民地”。 而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空间状态就是船舶。 “船舶是一个浮动的空间,一个没有处所的处所,……同时又驶在一望无际的大洋上,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从一个轮班到另一个轮班,从一个妓院到另一个妓院,一直抵达殖民地, 去探寻在花园里留待发现最珍贵的宝藏,……而且是想象力最伟大的宝库。 ”[2](P27-28)
这类独特的“船舶式异托邦”是一种没有固定位所的流动异托邦,而且连接了幻觉性异托邦——妓院和补偿性异托邦——“殖民地”,因此,具备以下特征:首先,它可以像“妓院”一样让人暂时进入常规社会秩序不复存在的梦幻之地,此时异质秩序得到肯定,常规空间秩序被抗议和颠倒;其次,没有船舶,就无法抵达殖民地,而殖民地隐喻了近乎完美的理想空间。也就是说,只有船舶才能“将人们带到可以建造理想的圣经秩序的殖民地”,因为它“连接了未知、冒险和新秩序的可能”[6](P145)。 再次,船舶是“从一个妓院到另一个妓院,一直抵达殖民地”,因此,“妓院”是起点,而“殖民地”才是最终目的地。也就是说,通过幻觉性的梦幻空间来表征、抗议或颠倒常规空间秩序只是“船舶式异托邦”的一个特质,其最终的目的是构建一个与混乱的现实空间相对立的秩序井然的理想空间。小说中丽娜的生活空间就是这样一个“船舶式异托邦”。
丽娜的生活空间具有“船舶式异托邦”属性的首要原因就是小说中的她“一直在路上”。 年轻的丽娜未婚先孕,负心汉卢卡斯·伯奇早已逃之夭夭,但她执拗地相信:“他会来接我,他说过会来接我。”[4](P3)在耐心而忠贞地等了很久之后,她挺着大肚子走上了寻找孩子父亲的寻亲之路。 就像船舶一样,她没有固定的位所,或步行,更多时候是搭乘一辆又一辆从身旁经过的马车,从阿拉巴马州一路走来。 来到杰弗生镇时,她遇到了平凡、善良并真心爱她的拜伦。在拜伦的帮助下,丽娜平安生下了孩子,也见到了她一直寻找的卢卡斯。但卢卡斯的再一次逃跑让她只好重新上路,只不过这次和她一起上路的除了新生的婴儿还有拜伦。当然更重要的是,丽娜的“在路上”还起到了连接幻觉性异托邦和补偿性异托邦的作用。
一方面,丽娜本人是一个单纯、善良的美丽姑娘。 她一路遇到的也都是陌生而又善良的人,正是因为这些热心人的帮助她才能从阿拉巴马州一路走到杰弗生镇。 其中需要特别提出的是,虽然在传统男权文化和清教妇道观盛行的美国南方,女人的“贞洁”成了女人最好的品质,但一路上,丽娜从未故意对帮助她的人隐瞒或撒谎她未婚怀孕的事实,说起孩子的父亲,“她好像从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并坚信“上帝一定会保佑她全家团聚的”[4](P16)。不仅她自己从未感到自卑或自怜, 在大家眼中,她身上也总有一种纯洁而坚定的气质,并不因为失去“贞洁”而变得卑贱,反而很坚强、美丽、优雅,“固执中透着一丝温柔、一种内心的澄明和宁静,不理智中透着一种超然”[4](P12)。 这与孤儿院里的女营养师和克里斯默斯的母亲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三位女性都是传统意义上失去“贞洁”的女人,但是女营养师却因为接受了清教妇道观思想而对自己的 “淫贱”怀有深深的罪恶感和恐惧感,以至于变得邪恶和疯狂,而克里斯默斯的母亲更是因为生下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相比之下,丽娜所到之处,一切都是那么的温暖和美好,人与人之间充满善意,没有歧视和偏见,大家总是热心互助。 进入丽娜的生活空间,似乎让人忘却了现实空间的各种残酷、不公和黑暗。于是,丽娜的生活空间具有了幻觉性异托邦特质,它的善意、 温暖和美好揭示了现实空间的黑暗和丑恶,从而抗议和颠倒了现实空间。
另一方面,丽娜的一路前行,如果说之前是为了寻找孩子的父亲,那从杰弗生镇与孩子、拜伦一起出发就不再只是寻亲之旅了。 在小说的最后,就连仅捎带了他们一程的家具修理工都能看出来:“我想她只是在旅行。 我觉得她并不在乎自己在找谁,她似乎从来就没有目标,……我觉得她只想走远些,尽可能多看些风景。”[4](P353)丽娜已经不仅只是一个人物形象,而是“一个隐喻符号,一个来自尘世之外的光”,她“用她沉静的心灵、天使般柔和的眼睛衬托这个世界的阴暗和浑浊,并用一个新的生命为通往未来世界的路上送来希望之光”[7]。 因此,从隐喻意义来看,他们再次上路寻找的应该是更美好的事物,也许正是克里斯默斯用一生在追寻的没有种族歧视和偏见、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美好“乌托邦”之地。可见,丽娜的生活空间就像一个“船舶”,引领人们抵达“可以建造理想圣经秩序的殖民地”,因而具有了一种抚慰人心的力量,让人们尤其是身处黑暗现实中的人对未来充满希望。
四、结 语
由克里斯默斯的生活空间构建的偏离性和禁区式异托邦, 揭露了现实空间中的残暴和丑恶,而由丽娜的生活空间构建的船舶式异托邦,却梦幻般展示了一种异质性秩序的美好和温暖,从而引导人们去追寻一个更完美的理想空间。福克纳通过这一明一暗、一美一丑的差异性异托邦建构,不仅深刻批判了美国南方的清教种族主义、妇道观等传统观念,还表达了作家对美好人性的信任和对人类美好未来的期盼。这就像在一间暗黑无光的屋子里打开了一扇窗,旋即几缕阳光驱散了无尽黑暗,让身处其中的人们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没有这份光明,黑暗显得过于沉重;缺少这份黑暗,光明不会如此珍贵。 也许这就是福克纳把这部小说的书名从《黑屋子》改成《八月之光》的原因吧。对此,福克纳曾解释说是因为故乡八月之初有几天阳光特别柔和,宛如圣灵降临一般。 无疑,小说中的丽娜就是八月的那缕阳光,带来了光明、温暖以及希望。这再一次验证了福克纳的人文主义思想内核,就像他在诺贝尔获奖致辞中所说:“我相信人不仅仅会存活,他还能越活越好。他是不朽的,……因为他有灵魂,有能够同情、牺牲和忍耐的精神。 ”[8](P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