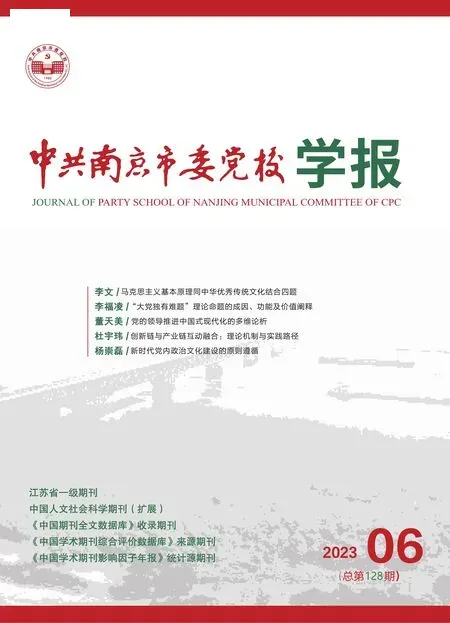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四题*
李 文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1]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百年历史,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第二个结合”的过程中取得了丰富的经验,深入挖掘和探究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 结合的文化心理基础: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
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实践问题,更是一个文化心理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探讨两者的结合问题不仅要从理论的契合性角度去加以深入的理论分析,从现实的实践角度去探讨两者结合的实践指向,更要从坚定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文化心理角度去加以理解和把握。回顾中国近代历史,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探索历程,在器物和制度层面探索失败之后,在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看来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主要还是一个自身传统文化落后的问题。因此,他们在对传统文化开展激烈批评的同时,极力主张向西学或者向东学。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古法实在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以至陷入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泥沼不能自拔。究其根源,就是我们对于自身的传统文化和历史的不自信。就此意义而言,在新的征程上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就必须要坚定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可以说,这种历史和文化自信是对近代以来文化自卑心理的一种彻底批判和反思,也是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文化心理根基。
历史和文化自信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和强调的一个重要理论和实践范畴。从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传统文化的历史角度而言,对文化自信的强调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那么,什么是文化自信呢?从学术界对文化自信内涵的分析而言,一个普遍性的观点是文化自信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这一内涵而言,文化自信本身就是一个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文化自觉过程,也是一个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问题。换言之,文化自信的前提条件是我们要对身边的文化有一个理性的审思。我们要思考:我们身处的文化是什么?由哪些要素构成?这些构成要素中有没有可以值得自信的东西?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都离不开文化自觉的过程,同时也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理性认知。就历史逻辑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所创造的文化的提炼。就现实逻辑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在文化领域的反映和写照。这启示我们,深入理解和把握文化自信的内涵和价值,也要遵循历史和现实的双重逻辑,既要从中华民族文化传承和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的“大历史”角度加以理解和把握,也要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角度加以理解和把握。
首先,从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历史角度来看,五千多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的底气。文化自信并不是一种无根的臆想,之所以有这种自信是因为我们悠久的历史文化中有许多优秀的文化遗产。毛泽东就曾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2]533-534他还说:“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2]622打开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画卷,从先秦的诸子百家到两汉经学,从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从宋代儒学到明清实学,这些思想流派无一不在思想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面对这一份历史遗产,我们是完全有理由自信的。当然,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农业文明,其自身有不足之处。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方面,毛泽东认为要坚持历史的辩证的客观理性态度,既要看到传统文化的好的一面进步的一面,也要看到其中的不足和局限性。在新的历史时期,习近平继承了毛泽东对待传统文化的这一基本态度,对传统文化给予了历史的辩证的客观评价。其一,习近平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其中蕴含的丰富的思想资源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实践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启发作用。其二,在具体的方法论层面,习近平也强调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对传统文化加以观照。比如,他也认为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去认知传统文化中的不足和消极因素。他还说:“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3]313不难看出,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在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上具有继承性。在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方面,两者都给予传统文化以客观理性的评价,认为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中既具有许多珍贵的东西,同时受到历史的局限性影响,也有许多糟粕性的东西。因此,我们强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是建立在对自身传统充分了解的前提之下的一种自觉和自信。
其次,从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奋斗历史来看,其所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文化自信的底色。1949年,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指出:“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4]1516
虽然毛泽东这里并没有明确指出他所说的文化具体是什么,但是我们不难看出,他在这里强调的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另类文化形态。换言之,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孕育了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习近平在强调要充分重视和发掘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同时,也强调对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近年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大搞历史虚无主义,歪曲党的历史,丑化矮化革命年代的英雄人物,借此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针对历史虚无主义这一错误思潮,习近平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与此同时他进一步强调要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教育。通过“四史”教育和学习,坚定对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
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文化自信的物质基础。毛泽东在阐述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时就曾开宗明义地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2]694文化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受到一定的物质经济条件制约。也就是说,新时代我们强调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有其现实的物质经济基础,离开了这一物质经济基础,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就只能是空中楼阁和无根之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我们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可以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迎来了光明的前景。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提出并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制定一系列具有全局性意义的区域重大战略,我国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5]8比如,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增长到114万亿,经济总量占世界的18.5%,提高7.2%,稳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39800元增加到81000元。制造业规模、外汇储备稳居世界第一。再如,十年来我国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不断加强,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载人航天、探月探火、卫星导航、大飞机制造、超级计算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发展壮大。这些成就无疑成为坚定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坚实物质前提和基础。
二、 结合的内容:精髓和精华融通起来
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5]18,这一论述为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锚定了方向。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获得有根性,不仅仅要被赋予中国人所喜闻乐见的外在语言形式,更要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而要获得这种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就必然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有机融合和汇通,也只有如此,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地融入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世界,才会成为中国人日用而不觉的价值理念。
首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实现了从形式、内容层面的结合到强调价值理念层面深度结合的转变。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最初的形式是语言形式层面的结合。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西方外来的文化形态,要在中国传播、被中国人所接受和认知,首先面对的问题就是语言形式的转化。就此而言,我们就不难理解最初的中国知识分子基于自身固有的传统文化背景,从我们熟悉的传统文化中找寻同马克思主义相类似的概念范畴去比附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当然,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步传播和中国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语言形式层面的结合显然已不能满足中国革命的现实需要了。换言之,现实的革命实践要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在更深层的内容层面实现有机的结合。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所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朴素认识论和朴素辩证法学说的结合就是这一层面结合的典型代表。
另一方面,从结合的主要内容角度而言,新时代两者的结合更加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就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5]18这启示我们要实现两者在价值理念层面的深度融合首先必须充分发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契合性。值得强调的是,以往我们在探讨两者的契合性时主要侧重于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层面挖掘两者的价值契合性。二十大报告则特别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契合性,这显然是一个全新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也就是说,新时代推进两者在价值理念层面的结合有了不一样的目标指向,如果说毛泽东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主要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朴素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有机融合,那么,新时代两者结合的目标指向就是要努力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与之相契合的价值理念的深度融合。
其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要融入现实生活中,建构一种新的生活样式。在当前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个结合”价值目标研究中,不少学者仍然把两者的结合解读为在现实实践的基础上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以转化和发展,以此建构出一种新的理论或者全新的概念为现实实践服务。笔者认同这种观点,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价值旨趣自然不是书斋里的理论纯思和重构,而是一种基于现实问题导向的“实践本位的结合”。但是,对新时代两者的结合我们又不能仅仅局限于此,两者的结合不仅仅要为现实的实践提供新的理论,也要回归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世界。正如二十大报告所强调的那样,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时也要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如此才能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有学者在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和意蕴时,曾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区分为政治层面的中国化和学术层面的中国化问题,政治层面的中国化主要侧重于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实践,并把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的经验上升为理论;学术层面的中国化则主要侧重于在学术层面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学术层面的中国化主要是知识分子的责任。这一区分或许还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是也触及到了马克思主义如何回归现实生活世界的问题。也就是说,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逻辑关系而言,新时代推进“第二个结合”不仅仅是为“第一个结合”提供思想理论资源,同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价值目标就是要回归现实生活,建构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这一新生活样式的进一步提炼就是一种中国式的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
最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一个“三位一体”的过程。新时代推进两者的结合着重强调价值理念层面的深度融合并不是要否定、忽视形式和内容层面的结合。换言之,新时代两者的结合应是形式和内容层面的结合,更应该是价值理念层面的结合。不论是形式层面的结合,还是内容层面的结合亦或价值理念层面的结合,其最终的价值目标都是为了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宗派主义了。不但宗派主义的问题可以解决,其他的许多问题也都可以解决了。”[6]858他还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4]1515这两段论述启示我们,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既要解决现实实践发展的理论问题,同时也要回归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世界。
总之,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经验而言,用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去比附和解释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个有利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基于深厚的民族情感的文化认同问题。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概念范畴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改造和转化不仅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而且基于现实的中国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不仅为“第一个结合”提供了思想理论资源和精神动力,而且在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建构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样式。这一全新的生活样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实生活根基和内在文化基因。
三、 结合的目标: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如果说坚定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文化心理基础,那么,在实践过程应如何具体推进两者的结合呢?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为我们提供了目标指向。问题的根本在于在现实的实践中如何具体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呢?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百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两个结合”的过程中取得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无疑是一笔宝贵的思想遗产。在此,以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为例具体探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现实路径问题。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同时也是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典范。在笔者看来,《实践论》和《矛盾论》在形式、内容和价值理念三个层面很好地做到了对传统文化的推陈出新和转化发展。
首先,形式层面的推陈出新,即立足于用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阐述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赋予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中国语言形式。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的西方文化形态,要在中国传播、生根、发芽、开花和结果,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要实现语言形式的转化。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过程中,当时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就已经敏锐地意识到要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语言和思想宝库中找寻与马克思主义相对应的概念去比附和解释马克思主义。比如,梁启超就认为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共产主义理论在中国古已有之,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与共产主义学说存在诸多的契合性。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那么,这里的民族形式又是什么呢?他进一步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谈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534毛泽东这里所强调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显然蕴含着中国的语言形式。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毛泽东为了阐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矛盾论的基本原理就大量运用了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名言典故。比如,用“吃一堑长一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来说明实践对认识发展的作用;用《山海经》中的“夸父追日”、《淮南子》中的“羿射九日”、《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七十二变等典故作为反面事例来证明矛盾转化是现实的具体的。毛泽东不仅在理论上倡导要用鲜活的中国语言形式去阐释马克思主义,更是在实践中身先士卒率先垂范。
其次,内容层面的推陈出新,既借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概念形式,同时又赋予其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内涵。如果说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概念、典故形象地解释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一种外在的推陈出新,那么,内容层面的推陈出新则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内容转化和发展。比如:毛泽东在《实践论》的标题后面加上“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这一副标题就颇为耐人寻味。众所周知,知和行以及知行关系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固有概念和话题,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则把主要强调伦理道德践行的朴素知行观发展为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这是毛泽东对中国传统知行观推陈出新的具体表现。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借用“相反相成”这一概念来阐释矛盾的斗争性和统一性问题。他说:“‘相反’就是说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相成’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结起来,获得了同一性。”[7]333在这一论述中,毛泽东借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概念,同时又赋予其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内涵。回顾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推陈出新,这方面的事例还有很多。毛泽东对古代实事求是学风的改造和转化、对仁义忠孝的理解、对中庸思想的新解、对智仁勇的新解等都属于这一类内容层面的推陈出新。
最后,价值理念层面的推陈出新,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理念的深入融合和汇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不仅是在形式层面用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去比附和解释马克思主义,也不仅仅是在内容层面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和改造,更应该是一种价值理念层面的深度融合。就两种文化交流互鉴的一般性规律而言,只有实现两者在价值理念上的深度融合,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地融入中国人的精神理念世界。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价值理念层面的结合方面无疑也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和启发作用。《实践论》中对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视“习行”价值理念的转化和发展,《矛盾论》中对中国传统“尚变”价值理念的推陈出新都堪称范例。当然这方面的事例还有很多,比如:毛泽东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相结合发展为我们党的群众路线;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强不息精神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相结合发展为我们党的独立自主精神。值得强调的是,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提出也很好地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的价值理念同马克思主义全人类情怀这一价值理念的有机结合。生态文明思想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价值理念同马克思主义生态理念的有机融合。人民至上的思想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同马克思主义鲜明的人民立场的有机融合。可以说,这些全新的价值理念和理论范畴是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新典范。
四、 结合的关键:明体达用,体用贯通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既是“体”又是“用”,是“体”和“用”的统一。新时代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关键在于明体达用,体用贯通。
首先,明体方可达用。“第二个结合”在理论上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命题的认识,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更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其一,“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进一步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规律性认识。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毛泽东强调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这个具体实际自然包括中国传统文化。这一认知倾向我们可以从毛泽东后来在《改造我们的学习》《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等文章中的相关论述得到印证。也就是说,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已经触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问题,但是从理论高度明确提出“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理论贡献。其二,“第二个结合”也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正如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1]不难理解,“第二个结合”理论命题的提出,其重要指向就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文化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何而来?没有5000年中华文明,哪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是中国式的?没有5000年中华文明,哪里又有中国式现代化。我们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种和平主义的特质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平主义文化基因关系密切。其三,“第二个结合”更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指出:“中国知识线和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便是第二次。”[8]4432我们暂不论梁启超的评价是否客观,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在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的每一次思想大爆发都离不开不同思想文化间的融合创新,反之,如果一方拒斥文化的交流互鉴,则必然滞碍文明的进步和发展。概言之,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告诫我们交流互鉴则文明兴,拒斥封闭则文明蒙尘。明体方可达用,这个“体”就是要在结合中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和中华文明发展的规律。
其次,在“达用”中“明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9]57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其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不能囿于书斋式的纯理论阐释和建构,更应该直面鲜活的社会实践,求解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一言以蔽之,两者的结合要解决实际问题,产生实践效力。比如,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1]不难理解,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互成就一方面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则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在场。也就是说,“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很好地解决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古今中西”之争问题。再如,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还指出:“‘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其本身就是“两个结合”的典范。通过对马克思主义这一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根脉的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在实践过程中必然产生一种固本强源的文化免疫效果,这种文化免疫既体现为对西方外来文化糟粕的免疫,也体现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糟粕的免疫。这种文化免疫能力的获得势必又会达到巩固文化主体性的作用。毫无疑问,“第二个结合”产生的实践效力是全方位的,这方面的事例还有很多。值得强调的是,“第二个结合”发挥的实践效力,反过来又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第二个结合”的理论认知和感悟。
最后,基于实践本位的体用贯通。“明体”中“达用”,“达用”中“明体”,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明体”与“达用”的统一呢?回答则是实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实践具有客观实在性,实践是人类改造世界的客观物质性活动,它虽然是人类有意识的行为,但本质上是客观的、物质的活动。实践的客观实在性是理论和实践统一的中介和桥梁。具体而言,“第二个结合”要体用贯通必须坚持实践本位的结合观,在现实实践需要的基础上既接着马克思主义说,又接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所谓实践本位的结合观,即现实的实践为两者的结合提供了现实场域,这一场域蕴含着两者结合的时代背景、物质基础、感性材料、问题指向和检验标准等。就两者结合的时代背景而言,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力量对比和全球格局正在经历深刻演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国际关系民主化潮流势不可当。但是,逆世界潮流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依然存在,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人类发展何去何从?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在这一时代大背景之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应运而生,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问题的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本身又是“第二个结合”的范例,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全人类情怀这一价值理念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和”这一价值理念的有机融合。如前所述,我们以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为例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目标和内容,同时我们也知道毛泽东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并不是书斋里的纯思,而是为了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从理论上彻底批判教条主义,为党确立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一思想路线的确立反过来又极大促进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就此而言,要实现“明体”和“达用”的统一必须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既为新时代两者的结合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也为两者的结合提出了现实的问题指向,更为两者的结合效力提供了检验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