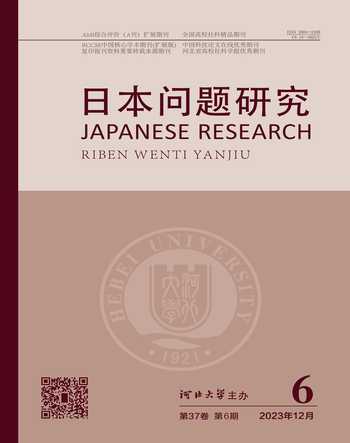互鉴与对话:泉镜花与中国古典文学
孙艳华
摘 要:作品译介是文学互鉴与对话的重要路径,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文学影响力的主要尺度。目前,学界对于日本近代翻译、改编中国文学典籍的整体把握与个案挖掘尚有待提升。日本近代作家泉镜花的13篇译作及翻案作品共涉及38个中国古典文学文本。毋庸置疑,这些译作及翻案作品为日本民众阅读、接受、传播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扩大其影响起到促进作用。作为文学互鉴与对话的个案之一,细勘泉镜花翻译、翻案作品对于完善明治、大正时期的中日文学交流状况不无裨益。
关键词:泉镜花;翻译;翻案;中国古典文學;近代
中图分类号:G115;I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23)06-0062-10
DOI:10.14156/j.cnki.rbwtyj.2023.06.007
引 言
文学交流与作品译介是不同国家文学间相互影响与传播的重要路径。就中日两国而言,近代之前,无论是数量,抑或是影响力,中国远高于日本。转至明治时期,“这一时期是中日文学交流较为活跃频繁而又颇为错综复杂的时期。这是日本文人作家的汉文学教养空前普及和提高、中国文学的影响空前多样化、曲折化的时期,同时也是日本文学转向西洋世界,中国文学的影响逐渐式微的时期。”[1]中国文学的影响虽式微,但文学交流并未中断,中日近代的典籍文化交流“时刻处在一个流动的模式和状态”[2]45。
然而,在日本,作为考量近代中国文学影响力的汉籍日译状况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甚至有漠视、淡化的倾向。以文学翻译为例,《明治期翻译文学综合年表》中统计的报刊杂志上登载的翻译文学共4 509项,均为欧美文学[3]。《明治、大正、昭和翻译文学目录》中收录的2 860项也都是欧美文学的翻译作品[4]。这种做法有失偏颇,因为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也是日本近代文学翻译的组成部分之一。为准确勾勒中日文学间互动与互鉴的全貌,需要围绕日本近代,尤其是史料记载译作数量较少的明治、大正时期中国文学的翻译状况进行深入的个案挖掘,以史料来还原历史语境。本文拟在中日两国文学互鉴与对话语境下,将泉镜花明治、大正时期的小品文及杂记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翻译、翻案中国古典文学典籍的情况。
一、近代中日两国的文学互鉴与对话
(一)文学交流
关于明治、大正时期中日两国文学的交流,学界普遍认为近代以前中国向日本的单向输出发生逆转,
中国文学的影响已由“显”变“隐”,竹内实的观点受到推崇:“明治以后,日本人的智慧的关心,智慧的、审美的价值基准,从以前的倾向于中国,发生了急剧的转换,但是,所谓的‘汉学却是牢固地存在于担负草创近代文学的文学者的教养根基之中的。”[5]301
学者们针对日本近代不同时期中国文学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开掘,认为明治初期对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和所谓的“新文学” ——政治小说的创作都离不开中国古典文学[6,7]。关于政治小说与汉学的关系,日本学者也持相同观点:“日本明治初期,一时盛开的政治小说的背面深藏的文学观,莫不如说更近于传统的中国思考。可以说,现实主义的政治小说意识,诞生于汉学的气氛之中。”[8]
王晓平则一语道破明治前期和后期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所产生影响的差异:“在明治前半期,中国文学是以其修辞和文体与日本文学发生联系,到后半期则逐渐出现了潜藏于修辞和文体深处的思想联系。”[5]301
关于大正时期,“日本文学(包括日本翻译的西方与俄国文学)良莠混杂地不断被介绍到中国来,而当时的中国文学却极少有日本人注意,只有一些作家,回过头去寻觅那遥远的古代。大正时代的作家和明治时代的新文学草创者不同,没有接受过日本化的中国古典的熏陶,他们对中国文学的理解和兴趣与森鸥外、幸田露伴等已不尽相同。他们所利用的,是中国悠久的历史和充满东方情调的题材”[5]368。
作为深受中国文学浸润的明治、大正时期的作家,森鸥外、幸田露伴、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长与善郎、武者小路实笃、菊池宽等名列其中[9]。
另一方面,有学者以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驻日使馆官员、旅日文人与日本汉学界的诗歌应和为例,力证明治二三十年代迎来了日本汉文学史上的第四次繁荣[10]。
(二)作品译介
作品的翻译和翻案对于他国文学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从王晓平的论述中可以得到印证:“在中日文学交流史上,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某些日本文学作品是中国文学的‘翻案或改作,这些作品不仅将中国文学的影响引入到日本文学的传统之中,给日本文学带来某些新的内容,而且因为作者的创造,在某种程度上使原作日本化,所以较之原作有更广泛流传的可能,甚至不胫而走,名噪一时。我们把这称作中国文学的第一次影响,或间接影响。这种改作,并不是影响的终结,而是影响的驿骑。后世作家从中受到启示,又创作出崭新的作品。”[5]306概言之,文学交流只是对接受过汉学教育、具备汉学素养的知识分子产生影响,而作品的翻译或翻案对于中国文学作品更广范围的传播及作品的大众化所做的贡献远非文学交流所及。
中国的文学典籍传入日本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饱受汉学浸淫的日本文人借助标注训点的训读法阅读、理解中国典籍,并不需要将其翻译成通俗的日语。至近世,日本印刷技术的发展与町人阶层的崛起、阅读阶层的平民化,使翻译、翻案中国古典小说的需求不断扩大。以文言小说《剪灯新话》为例,浅井了意的假名草子《伽婢子》(1666年)对《剪灯新话》中的18篇作品进行了改头换面式的改编,开翻案中国小说之先河。《剪灯新话》的翻译作品最早见于1687年刊行的假名草子《奇异杂谈集》,其中收录了3篇作品——《金凤钗记》《牡丹灯记》《申阳洞记》的译作。
“江户时代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二个高峰,汉诗汉文自不待言,明清白话小说也倾倒了上至公卿贵族下至市井百姓的广泛读者,并引发一股模仿创作的热潮。”[11]随着中国白话小说的大量涌入,“江户前期以林罗山为代表的日本文人,对中国小说的兴趣在于文言小说、尤其是志怪,至元禄以降始逐渐转向白话小说,而这一转向背后,实际隐含着日本社会文化和文学风尚的历史嬗变”[2]34。日本近世文人文学兴趣点的转移,加之为阅读古汉语而发明的训读法无法高效地实现阅读白话小说的功能,于是,白话小说的翻译、翻案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况。以1689—1692年面世的翻译作品《通俗三国志》为嚆矢,对白话小说的翻译一发而不可收拾,共诞生了43部译作[2]965-967。素材采撷自白话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的译作《小说精言》(1743年)、《小说奇言》(1753年)、《小说粹言》(1758年)被称为“日本三言”。白话小说的译作通常被冠以“通俗”之名,如《通俗忠义水浒传》(1757—1790)、《通俗西游记》(初篇1758年刊,续篇1784年刊)、《通俗醉菩提全传》(1759年)等不一而足。对中国古典小说进行翻案的近世文人也不在少数,都贺庭钟、曲亭马琴、上田秋成的影响最大。中国古典小说的流入、翻译、翻案、传播在叙事范式和小说文体等方面对日本近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文学典籍通过翻译、翻案对日本近世文学及读者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这种单向、封闭的模式进入明治后发生变化。明治二十一年至大正五年(1888—1916)翻译的中国典籍仅为9部,且多为古典文学[12]57。此间,受到“言文一致运动”的影响,出现了用现代日语翻译的译作,如1903年国木田独步译《聊斋志异》中的4篇作品——《竹青》《王桂庵》《石清虚》《胡四娘》,载于《东洋画报》。另一方面,至明治中期,日文典籍汉译的状况也令人堪忧。其后,骤然变得异常活跃。明治八年至二十七年(1875—1894)仅为4部,明治二十八年至三十七年(1895—1904)飙升至348部[12]56。中国留日学生亲眼目睹日本为“脱亚入欧”所付出的努力及取得的长足进步,以日本为窗口,将介绍日本及欧美先进文化的典籍進行翻译并积极引进到中国。之后,日译汉作品的数量一直远高于汉译日作品的数量。
转至大正中期,日译汉籍成果显著,呈现出新特质。大正六年至十五年(1917—1926)、昭和元年至九年(1926—1935)的20年间,日译汉籍由之前的个位数分别上升至42部、49部,除19部为文学语言类外,还有宗教、哲学、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教育、社会、实业等类,几乎涵盖各个领域。前10年间,除对文言小说进行重译外,国民文库刊行会发行的40卷本《国译汉文大成》(1920—1924)的付梓,标志着日本翻译中国古典典籍的最高峰。该丛书系日本首套汉籍翻译的集大成之作,分为经子史部和文学部,各20卷。
进入昭和时期,中国的新文学、新文化受到关注。1927年井出季和太译胡适的《先秦名学史》(书名胡適の支那哲学論);同年,武者小路实笃编辑的《大调和》上登载了鲁迅《故乡》的译作。1928年,《上海日日新闻》登载井上红梅译《阿Q正传》《社戏》;同年,《世界戏曲全集》第40卷收录柳田泉译丁西林作品《一只蜜蜂》。之后,鲁迅的《鸭的喜剧》《上海文艺一瞥》等作品的译作陆续出炉。1931年鲁迅作品的翻译集亦面世。其后,迎来日本翻译中国现代文学的小高潮,多部翻译合集悉数登场。
上述不同时期翻译或翻案的作品逐渐融入日本文学及文化之中,为各类文艺创作提供了素材,产生了二次、甚至三次影响。泉镜花曾一度大量翻译、翻案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作为文学互鉴与对话的个案之一,细勘其翻译、翻案作品,对于完善明治、大正时期的中日文学交流状况不无裨益。
二、泉镜花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
据查,泉镜花藏书中,汉籍共59部333册。从藏书量上看,鬼怪神魔传奇类(206册)约为诗集及评论类(70册)的3倍,总体上说,镜花受稗官小说等俗文学的影响要大于正统的经史诗文的影响,镜花翻译、翻案的中国作品均属于志怪小说或记载奇闻逸事的杂俎类也佐证了这一论点。
(一)“翻译”与“翻案”之辨
在划分翻译作品与翻案作品之前,有必要对“翻译”与“翻案”的概念加以甄别。文学意义上的“翻译”系指将某种语言的作品变换为另一种语言文本的行为。相对而言,“翻案”的定义较宽泛,例如《大英国际大百科事典小项目事典》将其定义为:在移植外国文学时,相对于忠实原作的翻译而言,“翻案”是指保持原作的脉络、事件,将地名、人名、风俗人情置换为本国的样式。《日本国语大辞典》《新汉语林》也将“更改地名、人名等”作为衡量翻案作品的标准。
关于日本的翻案作品,沼野充义认为:“明治时代结束了闭关锁国,在以迅猛的势头移植、消化西欧文化的过程中,日本对于外国文学常常大胆地使用‘翻案的方法,细言之,借用原作的脉络和内容,将地点替换为日本的地名,人名变为日本式的,‘脱胎换骨为其他作品”[13]。在此,也将变换人名或地名定为翻案作品的条件之一。
相对于前述宽泛的概念界定,永田小绘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划分。“在文学中作为目标语言文本的翻译作品(TT,Target Text)需保持的源文本(ST,Source Text)要素有如下4点:
(1)原作中包含的作者欲表达的信息;
(2)源文本中所指示的出场人物、事物(构成要素)及各构成要素间的关联;
(3)原作的文体与风格;
(4)原作的体裁(儿童文学、时代小说、现代小说、推理小说、科幻小说等)。
从忠实原文到一定程度自由翻译,译文有很大的差别,源文本的(1)和(2)在目标文本中被改编则可视为翻案,未满足(3)和(4)条件的可视为‘创作性翻案[应为“创作性翻译”之误。因为前后文中未曾出现“创作性翻案”一词。]”[14]61。永田小绘以白居易的《卖炭翁》为例,指出:“将汉诗翻译成口语体的散文是创作性翻译”[14]62,换言之,若改变了原作的文体即为“创作性翻译”。
依据上述概念审视泉镜花作品的话,翻译和翻案中国文学的作品各有5部小品和1篇杂记。此外,有1篇杂记中部分内容涉及对中国文学的翻译。
(二)翻译概况
泉镜花5部小品和2篇杂记的翻译涉及29篇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如果对照泉镜花藏书目录的话,主要出自《新齐谐》《琅琊代醉篇》《耳食录》《酉阳杂俎》《列仙全传》《搜神记》《秘书廿一种》中的《续齐谐记》等志怪类汉籍以及假名草子《新语园》。浅井了意著《新语园》是中国古典训诫类故事和奇闻逸事的翻译集。镜花的译作译自以下作品:
《术三则》(1906年)译自《琅琊代醉篇》十八之《羿》《颜息》《飞卫》。三则故事分别出自《帝王世纪》《左传·定公八年》《列子·汤问》。
《道听途说》(1907年)以传闻的形式“直译式”地转述了7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出自《新语园》卷一之八《李白祝子诗》、之九《东坡洗儿诗》以及《琅琊代醉篇》卷十八中的《地狱变相》《刘褒》《曹再行》《殷蒨》《徐景山》。据《琅琊代醉篇》记载,《刘褒》出自《博物志》,《徐景山》出自《齐谐记》,其他未标注出处。
《假装知道》(1907年)中穿插了两个泉镜花翻译的故事,即《续齐谐记》之八《阳羡书生》和《旧杂譬喻经》卷上之十八。
《花间文字》(1908年)的開篇至韩湘子返江淮部分,主要译自《酉阳杂俎》卷十九《广动植物》之十九《牡丹》及韩湘子《言志》诗,其余部分译自《列仙全传》卷六之《韩湘子》的后半部。
《鉴定》(1911年)译自《耳食录》卷一之《樊黑黑》。
《一景话题》(1911年)中《甲胄堂》的部分内容译自《搜神记》卷五《蒋山庙戏婚》。
《唐模样》(1912年)选取《新语园》中的10篇故事进行了二次翻译。《丽姬》取自卷三之二《丽娟回风舞》,原典出自《洞冥记》卷四。《勇将》中的两个故事分别节选自卷三之二十五《被斩首不死》和二十六《丧首盥马》。《被斩首不死》共讲述了5个故事,无头太守贾雍的故事最后出场,文中标注原典出自《录异传》之二。《丧首盥马》被标注出自《天中记》,行简禅师的故事则出现在《丧首盥马》的后半部。《愁妆》节选自卷三之三十一《容态学佗》,译作中讲述的寿阳梅妆、愁眉、远山眉、清黛眉在《新语园》中标注的是分别出自《事物纪原》、《后汉志》、《西京杂记》卷二、《西京杂记》。《捷术》出自卷四之七《肉飞仙》,原载于《隋书》卷六十四。《骄奢》是卷四之二十《魏世王侯之富》和二十一《晋石崇富荣》合体而成,前者出自《洛阳伽蓝记》之八,后者源于《晋书》。《空蝉》译自卷五之四十七《杨知春》,原载于《博异志》。《人妖》译自卷六之二十一《无足妇人》,出自《玉堂闲话》。《少年僧》译自卷二之三十二《少年僧以诗得妇》,出自《留青日札》。《魅室》译自卷六之三十九《令史妻魅疾》,出自《广异记》。《良夜》译自卷五之三十六《王积薪闻暗棋》,出自《集异记》。
从年代来看,泉镜花翻译中国文学的时期集中在明治三十九年至四十五年(1906—1912),即明治末期。这既有大环境的陶染,也有个人因素的催发。
明治初期,作为了解西方的手段之一,兴起翻译西方文学的热潮,明治二十年代(1887—1896)达到隆盛。包括文学家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投身到翻译西方文学的潮流之中。森鸥外、坪内逍遥、二叶亭四迷、田山花袋、森田思轩、井上勤、上田敏等人自不待言,恩师尾崎红叶和同门小栗风叶的活跃对泉镜花“刺激”不小。尾崎红叶在明治二三十年代翻译了格林、莫里哀、左拉等人的作品,小栗风叶则在1905—1906年发表了多部莫泊桑作品的译作。
另一方面,1907年泉镜花与登张竹风共译的德国剧作家盖尔哈特·霍普特曼创作的《沉钟》(5幕剧),由于反响不佳,仅连载两幕便夭折,并因长谷川天溪的批评而引发了与镜花的论争。对于未曾留洋,也未进入高等学府的镜花来说,在北陆英和学校所学的英语也仅能达到阅读的程度,至于翻译西方文学作品似乎难度较大[15]。换言之,西方文学也并未引起镜花更大的兴趣。1900年,镜花凭借《高野圣僧》一炮走红,奠定了神秘、怪异的文学基调。中国的志怪小说和记载奇闻逸事的杂记更能吸引他的眼球,翻译起来也更得心应手。周围环境的刺激、翻译西方作品的挫败以及镜花的兴趣点是促使他明治末期集中翻译中国古典作品的诱因。
(三)翻译策略
1.作品名的拟定。
从作品名看,除《甲胄堂》外,泉镜花的6部翻译作品均重新拟定了题名。这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将内容相近的数篇作品收进一部翻译作品时,在译作中不显示原作名,而是重新命名译作,如《术三则》《道听途说》《假装知道》《花间文字》,镜花翻译中国古典文学的最初阶段都是采取这种形式;另一种情况是直接将原作改名,如之后翻译作品《鉴定》《唐模样》中的10篇。
《术三则》讲述的是后羿、颜息、纪昌三位射手的故事,可以说《术三则》这个题目恰当地体现了主题。《道听途说》是以传闻的形式翻译介绍中国的作品,所以取名《道听途说》。《假装知道》是将《续齐谐记》、《旧杂譬喻经》和《天方夜谭》中的3个故事翻译,并加以比较,以《假装知道》为名是为了避免留下“卖弄学问”之口实,表明自己谦逊的态度吧。与原作名《牡丹》《韩湘子》相比,《花间文字》更具浪漫情调。
为译作重新取名,体现了泉镜花的审美情趣。与《樊黑黑》相比,《鉴定》更凸显了为证实自己所言属实竟然让其他男子与自己妻子同房的愚昧,具有诙谐讽刺的意味。《唐模样》中10篇作品的题名——《丽姬》《勇将》《捷术》《骄奢》《愁妆》《人妖》《少年僧》《空蝉》《魅室》《良夜》,可谓用心良苦。《丽娟回风舞》等原作名淡而无味,毫无美感,而镜花所起新名更像是小说的题目。10个作品名除《少年僧》外,都是两字词,对仗工整。其次,“丽、勇、捷、愁、妖、空、魅、良、骄、奢”等修饰词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突出了主题。
2.对原作的删减、增补与改写。
泉镜花在翻译时会根据自己的审美标准和作品需要对原作内容进行取舍,并在译作中不时添加评论或日本元素。按照前述永田小绘所下定义分类的话,《术三则》《道听途说》《唐模样》中的10篇短文基本是对所选内容的逐字逐句对译,加写的地方少且精,属于翻译。《花间文字》《鉴定》《假装知道》中译自《阳羡书生》的部分、《甲胄堂》中译自《蒋山庙戏婚》的部分则是创作性翻译。
《假装知道》将《续齐谐记》、《旧杂譬喻经》和《天方夜谭》中内容相近的3则故事进行比较,夹叙夹议。针对《旧杂譬喻经》卷上第十八的翻译基本为直译。相比之下,译自《续齐谐记》中《阳羡书生》的部分则改动较大,内容有增有减。例如:将许彦相的身份改为卖斗鸡[斗鸡:日语为“军鸡”,江户时期从泰国传入的品种。]的,该身份设定对于日本读者来说具有亲近感;加入大量对人物及大鹅音容笑貌的细致刻画,如书生“像是买给小孩子玩儿的不倒翁”,“仿佛从底部钻出来”一样出笼,“连簪子都不拔,便将美女的黑发吸入口中,红衫缠绕牙齿,仿佛叼着松叶牙签”,“化作夕阳下的云彩”,书生吐出的美女“娇滴滴的声音”“抛着媚眼”“微醺时吐出可爱气息”,大鹅“也不拍打翅膀,规规矩矩、泰然自若地呆在笼子里”。除详细刻画外,为便于日本读者理解,泉镜花还适时地加入说明,为原文中未表部分做出合理解释。故事中又插入了镜花对儿时读过的该故事的翻案作品的回忆。省略“美少年又吐出一女子”的情节,避免了重复,略去最后交代许彦相高升等无关紧要的部分,使情节更紧凑。如此大幅度的改动,可视为创作性翻译。
《花间文字》堪称精美的小说。与原文相比,加写多达13处,姑举两例。原文中对韩昌黎责备韩湘子的场面并未着墨,泉镜花则如下点缀:“韩湘子诚惶诚恐,像是啃指甲般嚼着手中的东西,与日本嚼豌豆的样子相仿。昌黎厉色训斥道:怎么回事?夺下一看,形状似有平糖的糖瓣儿,非也,是美丽的桃花花瓣,一落掌,簌簌地散落至膝盖上。时值冬令,不会是小阳春的‘桃开二度,怎会弄到花瓣呢?昌黎一脸严肃地盯着韩湘子”。刻画细腻、唯美,还加入了“有平糖”“日本的豌豆”等日本元素,拉近了与读者的心理距离。又如,韩昌黎被贬官赴潮州时,原文仅以“途中遇雪”一笔带过,而在镜花的笔下,一幅“高山风雪图”展现在读者面前:“晦冥阴惨,云冷风寒,征衣微墨发忽白。岭遮天,关锁地,马不前。马不前,雪碎孤影。濛濛中,唯见云一簇,霏霏现薄红。风吹飘渺到眼前,日暮下,岂是夕阳落影?疑似红泪染雪。卷袖拂面,遥见云中现韩湘”,蕴含汉诗的韵味;又时而以“吾今见仙葩”,与前引韩湘诗相呼应,增添了小说的元素。概言之,镜花的加写或浪漫,或细致,或添加小说要素,或增强逻辑性,更具文学色彩。
此外,泉镜花将结尾进行了改写。原文为:湘辞去,出药一瓢与公御瘴毒,公怆然,曰:“此后复有相见之期乎?”湘曰:“前期未可知也。”平淡无奇。镜花将其改为:“韩湘子安慰道:勿悲伤,吾知公无恙,且不久朝廷必会重新重用。分别时捧雪赠昌黎,曰:此物能除潮州的瘴毒,叔父多保重。昌黎于马上接雪入袖,白雪散发芬芳,即刻化为花片。”比原文更具神韵。首先,以“吾知公无恙,且不久朝廷必会重新重用”突出韩湘子的“神性”。其次,将“药”换作“雪”,“雪”又化为“花片”,既浪漫又突出了“花”,前后呼应。镜花的独创部分占相当大的篇幅,若人物和地點换做日本的人名和地名的话,则是一篇地地道道的“翻案”作品。
《甲胄堂》中也有类似情况。人名、地名、故事情节均按原文如实翻译,但加入一些细节描写和日本元素,例如:为方便日本读者理解,补充说明了蒋山的身份——土地爷;写木像的女子白皙,女性肌肤白皙是镜花眼中美女的必备条件;详尽描写了三个公子哥在庙中大吃大喝及调戏女像的细节。对蒋山神第二次入梦的描述具有强大的冲击力,包含的信息量远超出原文。首先,蒋山神的装束是“身着银色盔甲,胯下如雪白马,身负白羽箭,手持白鞭”,一副仙风道骨的模样,与其神仙的身份相吻合。这里需注意“白羽箭”的文化蕴含。据日本自古以来的传承,寻找祭祀用少女的神仙会在选中的人家屋顶上插上白羽毛的箭作为标记。“白羽箭”既承载了日本几代人的记忆,也预示着三个公子哥即将成为祭品的结局。其次是蒋山神话语中所包含的文化寓意,如“把我女儿当成什么了,又不是‘海老茶”。这里的“海老茶”极具日本色彩。“海老茶”在日语中原本指略带灰色的暗红色。明治中后期女学生穿着的裤裙流行“海老茶”颜色,因此诞生了“海老茶式部”一词,用以指代明治三十年代(1897—1906)的女学生。这里的“海老茶”暗指当时接受高等教育的女学生,也是泉镜花不喜欢的一类人。话语中透露出对女学生的嘲讽。
《鉴定》的最大特点是将原文的平铺直叙改为泉镜花擅长的对话体,文体发生了变化,应归入创作性翻译之列。同时,以“当下流行的厢发”和众人皆知的日本绝代美女“小野小町”来讽刺屠户新婚妻子的容貌,符合日本人的审美观;将“两股之间有香气袭袭扑人”表现为“满屋充溢兰花和麝香的芬芳”,避免了低俗和直白。
3.译者的艺术趣味。
从作品名的拟定和内容的改动,可看出泉镜花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策略及其艺术趣味。
从题材选择方面看,泉镜花喜好神怪,崇尚技艺。选择怪异题材体现了镜花尚奇、好神秘的趣味。自室町时代,日本人就喜好中国的奇谈。江户时代,中国志怪小说和唐传奇的翻译和翻案作品大量面世,上田秋成的《雨月物语》便是镜花的喜读书之一。镜花赞叹秋成的作品才是真正地鬼气逼人[16],在《汤岛之恋》中让主人公神月梓朗诵《雨月物语》,可见其对秋成作品的喜爱程度。崇尚技艺则与镜花的出身相关。镜花之父是金泽小有名气的金属雕刻师,母亲出身于艺术之家,镜花自幼便对“有一技之长”的人充满敬意。
综观泉镜花所选汉文的叙述方式基本为平铺直叙。镜花在翻译时会将“叙述”转为幽默诙谐的“对话”,打破了汉文所特有的拘谨严肃的氛围,以《鉴定》最具代表性。镜花深受《东海道徒步旅行记》为代表的滑稽小说影响,深谙其精髓,幽默的对话也成为镜花文学的一种样式。其诙谐的风格在题目的拟定上也可略窥一斑,如《鉴定》。
从其行文、全知型叙事方式可看出说书对泉镜花的影响,最典型的是作者经常在文中“露面”,品头论足,如《术三则》《道听途说》《丽姬》《愁妆》《捷术》《人妖》《良夜》等,比比皆是。镜花自幼喜欢听评书,远赴东京后,也经常光顾说书场[17]。说书对泉镜花影响之深从其翻译作品中也可略见一斑。
泉镜花在作品中善用大量的定语和状语等进行人物描摹与情节刻画。如《勇将》中,将行简禅师“手捧头颅安于颈上,追赶匪贼如飞”描述为:“将被斩下的头颅如纸糊的面具般捧在手中,‘砰地扣于颈上,张开大手,追赶逃窜的数十匪贼,如鹫般健步如飞。”以状语“如纸糊的面具般”“‘砰地”“如鹫般”形容“捧”“扣”“健步如飞”等动作;在“匪贼”前添加定语“逃窜的数十”以营造气氛;以“张开大手”打造视觉效果。刻画情节时镜花格外重视美感,如《空蝉》将原文中的“指中出血,如赤豆汁”中的“如赤豆汁”改为“如丝”。这种唯美的情绪在《花间文字》中达到顶点。
《道听途说》将白獭喻为“如妖妇入浴般美丽可爱”,《魅室》中“妻子微醉的面庞妖艳无比”,《假装知道》中书生吐出的女子“娇滴滴的声音”“抛着媚眼”“雪白的酥胸如李子花随风摇曳”,从中可看出镜花喜好在文学世界里刻画妩媚而性感的女性。
《旧杂譬喻经》《耳食录》《新语园》中的部分作品是以道德上劝戒他人、惩恶扬善为目的的。泉镜花翻译时有意淡化故事的“功利性”,增加文学色彩。如《空蝉》将原文的“大不仁。有物不能赎,卒断其指”省略,以“痛哉”一言以蔽之,更突出了痛感。《鉴定》和《假装知道》也如法炮制,略去文末的说教。
上述翻译作品虽然对人物形态和情节大肆着墨渲染,但对原文中的人名、人物身份、地名、故事的发展主线等基本不做改变,以保持“原汁原味”,使日本读者感受到异国情调。
三、泉镜花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翻案
泉镜花的6部翻案作品为《聪明的女人》《妙龄》《画里》《捣麦》《人参》《三片柏叶》,涉及9篇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分别出自镜花藏书目录中的《新齐谐》《阅微草堂笔记》《搜神记》《耳食录》。
被归入杂记类的《聪明的女人》(1907年)是对《旧杂譬喻经》第二十五个故事的翻案。全篇采用说书人的口吻,随处可见说书人对人物心理的揣摩。比原文更具故事性,情节也更丰富,加入了心理描写和外观描写。前半部和后半部均采用了倒叙的手法,增加悬念,引人入胜。开篇即言“丈夫不知为何开始怀疑妻子”,吊起读者的胃口。接下来写夫妻吵架,约定妻子去神树前发誓。于是二人进入斋室以净身,此时琢儿[原文为琢银儿。]方才登场。与原文开门见山“妇值青衣作地窟。与琢银儿相通。夫后觉”的写法相比,更符合逻辑,也更有趣。后半部寫夫妻二人去神树途中妻子突然被“疯子”抱住倒地,丈夫在神树前解释并非妻子之过,妻子得以幸存,最后揭开谜底是妻子与琢儿密谋所为。通过倒叙的手法,极大增添了故事的趣味性。原作欲传达给读者的信息是“妇人奸诈”,而泉镜花却为作品起名为《聪明的女人》,并将女子描写得美若天仙,这里反映了镜花的审美观和女性观。文中对后悔与妻子赌气但又欲罢不能的丈夫的刻画惟妙惟肖。故事中还插入了韩非子《内储说下·六微(十八)》之《李季浴矢》的故事,与前述故事形成互文关系。
《妙龄》(1908年)取材于《旧杂譬喻经》卷上十七,对原作的翻案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1)叙事结构:原作以“昔有妇人生一女”这一民间传说文学特有的方式开篇。新作则设定了释迦牟尼讲故事以教诲弟子的场面,在其中插入《旧杂譬喻经》卷上十七的故事。故事结束后,愚钝的周利槃特向释迦牟尼请教“以树叶为被的男女所说的情话”时,释迦牟尼苦笑,答曰:不知。这一结局滑稽诙谐,令人忍俊不禁。
(2)地点:加入了“大萨摩峰”“富士河”“华严瀑布”等令人联想到日本的元素。
(3)主题:《旧杂譬喻经》卷上之十七是以国王欲娶一美貌女子,用尽心机终未果的故事告诉世人:命运是不可逆转的。原故事本无题目,泉镜花将其命名为《妙龄》,文中极尽能事渲染女孩之花容月貌,在故事结尾以“外面如菩萨,内心如夜叉”概述故事主题,可知其主题聚焦于美丽女子,通过作品欲传达给读者的信息已发生变化。
(4)情节:改编之处较多。原文中“呼道人相后中夫人不。道人言。此女人有夫。王必后之”,仅寥寥数语,而新作洋洋洒洒700余字,不仅惟妙惟肖地刻画了高僧的举止样态及国王的神态,还对高僧的禀奏进行了详细加工,增添了真实感;将“我当牢藏之”变为“国王听后哈哈大笑,你当我是谁呢。你的放大镜或许没有看错,但我是能号令草木的大王啊,虽然无法让她重回胎里,但是凭借金钱的力量和权利可以轻松将女子藏起来,现在就让你检验一下”,增加了国王对自己能力的夸耀,与结局形成巨大反差,获得的阅读效果更佳。原作未表男子登场的契机,新作写的是“天空中坠落一颗星星,化作卵石从上游漂下来,紧随其后的是一支支树叶繁茂的桂树枝,蓝中泛着绿,打着旋儿漂来。接着是一美少年,不知从哪里掉入河中的。好像是从华严瀑布岩底冒出来,和岩石块及碎藻一起从云中掉落的。”原作将男子描述为俗众,新作中的男子是非凡脱俗的美少年。日语中有“桂男”一词,指的是中国神话中在月宫砍桂树的吴刚。“星星坠落”“桂树”“从云中掉下来”与月宫中的吴刚形象叠加在一起,暗示了美少年所具有的神性。
(5)人物:作品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是隐藏少女的动物,在原作中是“鹄”,泉镜花将其改为“鹤”。日本人对“鹄”并不熟知,而对于“鹤”则情有独钟。“鹤”被视为灵鸟,是长寿的象征,“仙鹤报恩”的故事流传至今。
《画里》(1910年)的蓝本为清乐钧《耳食录》卷四之《画师》。取名《画师》是为凸显画师的高超技艺,而《画里》更强调了画里之景、画里之人,故高潮出现在众人目睹徐群夫小妾裸体、使徐当众受辱的部分。泉镜花借用该故事的框架和部分内容,以达到讽刺权贵的目的,并为此作了精心的铺垫:将徐群夫的身份设定为村里的土豪,在作品中直呼“徐土豪”。画者为流浪画师,求见徐土豪,徐一副傲慢、不屑的态度,而当徐受辱恼羞成怒,欲向画师发泄时,画师潇洒地消失在画中,教训了这个自以为是的土豪。作品中一大段为意译,而非直译,有镜花“添油加醋”的成分,语言诙谐,徐土豪的形象丰满生动,已超越翻译的框架,属翻案范畴。
《捣麦》(1910年)翻案自《新齐谐》卷二十三之《风流具》。与《风流具》相比,取名《捣麦》去掉了低俗的趣味,月夜下蒋公子独自捣麦子的画面呼之欲出。
《捣麦》基本保留了原作品的主线,但将女主人公的名字“珠团”改为日本常见的名字“お玉(たま)”;地点做了部分移植,如“先在城边的新宿大木户旁转悠一圈儿”,这里的“新宿大木户”指的是人尽皆知的“四谷大木户”,系进出江户的关卡;加入了日本元素,如将“坐在大火炕上”改写为“坐在大广间正中足有两张榻榻米大的大火盆前”;“16号是‘釜日”则体现了日本的风俗,江户时代以后将每月带“1”和“6”的日期定为节假日、研习日、聚会日等,“釜日”系指茶道老师用“釜”烧水,让弟子演习茶道的日子;“惣领甚六”是日本的谚语,“傻老大”之意;“公认的‘送狼”中的“送狼”一词原本诞生于日本传承文学,经常出现在俳谐、洒落本和人情本中,为日本人所熟知,加入该词,更便于日本人接受。同时,《捣麦》用定语、状语或原因从句对人物的衣着、神态、品性、动作等进行了极为细致的刻画。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增加故事情节的合理性,作者还会加以解释。
《人参》(1911年)由两则故事构成,取材于《新齐谐》卷二十三的《骗人参》和《偷靴》。《偷靴》基本上忠实原文,《骗人参》改动较大。将京城批发人参的老字号张广号以“银座之首”形容其规模之大;对于不谙人参价值的日本读者,泉镜花用江户时代的名妓——高尾、薄云、芳野的身价相当于1两人参来进行说明;将故事发生的舞台改为筑地宾馆。银座、筑地、日本的名妓等,导入了日本读者熟知的元素,做了改头换面式的移植,但并未达到脱胎换骨的程度,翻案的色彩并不浓郁。
《三片柏叶》(1914年)由3篇短篇构成。其中,《旷野》源自《新齐谐》卷五之《洗紫河车》,《被卖女子》源自《滦阳续录》之四,《狐》源自《耳食录》卷二之《胡好好》。
《旷野》对《洗紫河车》进行了大刀阔斧式的改写。将主人公丁恺的名字改为“丁隶”,符合主人公衙役的身份。原作未表丁隶亡妻的外观与性格,泉镜花将其刻画为姿色颇佳、对前夫有情有义的女子。原作中的牛头鬼“眉目言笑,宛若平人”,在镜花笔下则化身为“色白细面,梳着分头的时尚好男儿”。原作的意图是向读者讲述怪诞之事,而镜花的兴趣点似乎在于一女嫁二夫的感情纠葛上,将原作改编成了活脱脱的“人情本”。丁隶得知亡妻改嫁牛头鬼时的嫉妒和怨恨心理,亡妻对前夫虽旧情尚存但鉴于已为他妇的身份,当被前夫拽住衣袖时的羞涩与在意外人眼光的心理,牛鬼头的宽宏大量等,随着情节的展开而逐渐展现在读者面前。镜花将原文中三人共饮,牛头鬼用计使丁隶重回人界的结尾省去,以“他有恩于我,我岂有不救之理……”收场,在三人达成和解的高潮处戛然而止,也正符合“人情本”的套路。
泉镜花不仅着重刻画了三人微妙的感情变化,还不时地加入一些调侃的因素。品味一下丁隶的话语,便可嗅出“滑稽本”的味道。例如,“也太夸张了,写什么‘阴阳界啊,这不等于在妓院大门上写‘色欲界吗?”“破蜘蛛也对阎王爷敬而远之,只在他手下人的脸上织网——虽说是木雕像,也会郁闷啊,太可怜了。”“洗什么怪东西呢?是鬼奸夫的肚兜吗?”语言幽默诙谐,使读者不禁联想到镜花的大作《歌行灯》。
泉镜花对原作的叙述方式做了部分改动,采用倒叙的手法,而且以其特有的幽默对话[在此是自言自语。]开篇。原文的叙事是直线型的:过鬼门关→见石碑→至古庙,在新作中变为:古庙→鬼门关→见石碑。新作比原作更增添了小说的要素,例如对丁隶在庙中及在旷野中奔走时的胆怯心理、听到亡妻改嫁后的嫉妒心理和丁妻乍见前夫时的复杂心理的描述。加写部分很多,信息量是原作的数倍,如河上的小桥、对人物神态和举止的细节描写等。在传承文学中,“桥”起到境界线的作用,在此暗示小桥的对岸是阴间。“丁隶看到对岸女子在洗外形似菜的物件,心想:是什么菜呀,故意咳了一声,以引起对方注意。女子这才意识到有人,抬起头。黄昏下,眉毛的影子和发鬓虽有些凌乱,但眼睛和鼻梁清晰可见,是一位颇有姿色的女子。丁隶一看,大吃一惊,跌坐在地,竟是前年过世的妻子。”这种方式比原文的“谛视渐近,乃其亡妻”更具戏剧性。
《被卖女子》的故事在《滦阳续录》中是为了告诫那些妄想成仙得道之人,而泉鏡花欲借该故事表达对被卖女子的同情。镜花在文中两次直言被卖女子可怜,并省略了原文结尾处的训诫之词。《被卖女子》在叙述方式上延续了镜花擅长的以对话开篇的形式,人物语言呈现江户市井百姓的风格。同时,镜花改变了人物身份。原文中被卖的是妇人,镜花将其变成姑娘,更引人怜悯;将“道人”变为“讨厌的和尚”和“仙人”,并加入村医的角色。原来的平铺直叙在镜花的妙笔下变得鲜活,改写、加写了许多内容,注重故事的铺垫和趣味性,更具小说的特点。原文中的“云初彼买时,引至一人家。旋有一道士至,携之入山”在镜花笔下竟然变成千字文,以渲染女子的可怜境遇。同时加入一些景物描写以烘托女子的忐忑不安和恐惧心理,而被吸血的细节描写更细腻。
《狐》对原作的结构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原文的叙述顺序是:①何生邂逅胡好好,在别宅密会数月→②何生归宅,见一年少书生进入内室,冲进卧室,发现躺在床上的是胡好好→③胡好好捉弄何生夫妇后恢复狐形逃走→④说教。新作的顺序是②→①→③,更加曲折。从叙述时间来看,采取的是倒叙和插叙的手法,比原文结构更复杂。此外,运用伏笔的手法,开篇以“新情人两天未回别宅”,为胡好好的出现埋下伏笔。同时,对人名、时间、情节进行改写,如:佣人的名字“权平(ごんぺい)”系日本常见的人名;称胡好好为“お好ちゃん”;何生与胡好好邂逅的时间从“清明”改为“春天”,不言而喻,春天比清明更适合谈情说爱;改写了猥亵的场面,加入“手枪”这一近代的要素以及对书生和何妻的细致描写。
结 语
泉镜花以9篇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为蓝本改编成6部作品,从叙事结构、主题、人物和地点、情节等方面进行翻案。细言之,采取倒叙的手法改变原作中的平铺直叙,以增加故事的曲折离奇和趣味性;改变主题以淡化原作的功利性;将姓名和地点置换为日本式的,便于日本读者接受;以诙谐幽默的语言一扫古汉语的凝重气氛;对情节的改变主要体现在增加细节刻画和对人物心理的揣摩,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景物描写更加出神入化,增加小说的元素。
泉镜花的翻译作品助推了中国古典小说在日本平民百姓间的传播。其创作性翻译作品富于文化蕴含,文学色彩浓郁,充分体现了镜花美学的去“庄”入“谐”,化“简”为“繁”,唯美,浪漫,妩媚。
泉镜花翻译、翻案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时间集中在明治三十九年至大正三年(1906—1914),恰好是日译汉籍青黄不接的时期。毋庸置疑,这些作品对于日本民众阅读、接受、传播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扩大其影响起到一定作用。同时,也以事实有力地反击了无视日本近代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史实的做法。作品译介是国家间文学相互影响的途径之一,对于日本近代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个案挖掘及整体状况的爬梳与准确把握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王向远.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的中日文学比较研究概观[J/OL].(2017-10-17)[2023-03-10]. http://cll.newdu.com/a/201710/17/31572.html.
[2]周健强.中国古典小说在日本江户时期的流播[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3]川戸道昭,中林良雄,榊原貴教.明治翻訳文学全集新聞雑誌編別巻1 明治期翻訳文学総合年表[M].東京: 大空社,2001.
[4]国立国会図書館.明治·大正·昭和翻訳文学目録[M].東京: 風間書房,1972.
[5]王曉平.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M].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
[6]马兴国.近代中日文学交流述略[J].日本研究,1992(2):55-61.
[7]任卫平.中日文学交流史略谈[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1):92-93.
[8]鈴木修次.中国文学と日本文学[M].東京: 東京書籍,1987:17.
[9]熊鹰.“中国题材”的政治——中日左翼文学交流中的《我的母国·作为日本文学课题》[J].文学评论,2017(6):127-133.
[10]高文汉.步入近代的中日文学交流——以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为中心[J].外国问题研究,2009(1):4-10.
[11]勾艳军.日本近世戏作小说的中国文学思想渊源[J].日本问题研究,2012(2):55-60.
[12]実藤恵秀,小川博.日本訳中国書目録:日中友好の一つの礎石として[M].東京:日本学生放送協会,1956.
[13]沼野充義.小川公代,村田真一.文学とアダプテーション——ヨーロッパの文化的変容[M].東京: 春風社,2017:8-9.
[14]永田小絵.芥川龍之介の翻案に見る受容化の方策[J]. Mathesis universalis : bulletin of the Department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2018(1):57-84.
[15]蒲生欣一郎.もうひとりの泉鏡花[M].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990:55.
[16]泉鏡花.旧文学と会談[N].時事新報,1909-12-27.
[17]延広真治.鏡花と江戸文芸——“講談”を中心に[A]//東郷克美.泉鏡花 美と幻想.東京:有精堂,1991:163-164.
[责任编辑 孙 丽]
Interchange and Dialogue: Izumi Kyoka and Chinese Literature
SUN Yanhu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iyin Normal University, Huaian, Jiangsu, 223300, China)
Abstract: The introduction of works is an important path for literary exchange and dialogue, as well as a primary measure of assessing the literary influence of a country. Currently,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the overall understanding and individual case excavation of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into modern Japan. Thirteen translated and adapted works by Izumi Kyoka, a modern Japanese writer, involve a total of 38 texts from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Without a doubt, these translated and adapted works play a promoting role in enabling the Japanese people to read, accept, and disseminate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ry works, thereby expanding their influence. As one of the cases of literary exchange and dialogue, a detailed examination of Izumi Kyokas translated and adapted works would undoubtedly contribute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literary exchange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during the Meiji and Taisho periods.
Key words: Izumi Kyoka; translation; adaptation;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mode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