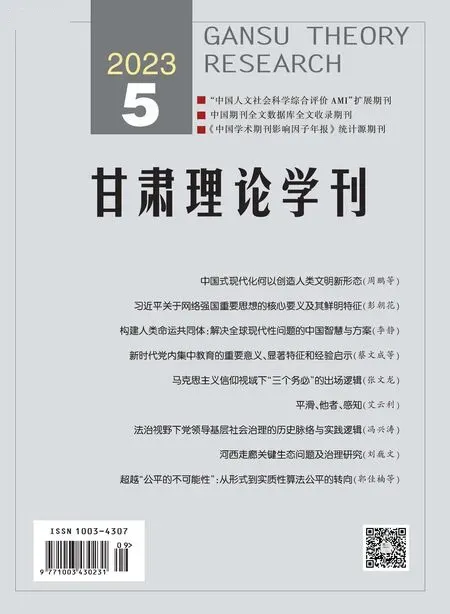平滑、他者、感知
——论韩炳哲的免疫美学思想
艾云利
(南昌大学 人文学院,南昌 330036)
对于差异、他性的关注构成法国当代理论的显著特征之一,萨特、梅洛·庞蒂、列维纳斯、德里达、拉康、布朗肖等人都对其有过一定的理论探索。韩裔德国学者韩炳哲,其哲学美学理论不同于德国古典学院派,反而是更靠近法国理论。通过对“他者”和“平滑”的分析批判,韩炳哲成为“法国差异哲学美学”家族的一员。韩炳哲借助埃斯波西托的免疫理论,从认知逻辑上将免疫学和美学进行关联,认为其本质都在于一种“他者性”,由其共同的核心逻辑演绎出姑且称之为“免疫美学”的论述。
一、 感知的复制与梗阻:平滑及“平滑美学”
从康德的先验感性论开始,到黑格尔的“理念感性论”、鲍姆嘉通的“感性学”,再到梅洛·梅洛庞帝的“感知”思想、阿列西·艾尔雅维奇的“审美革命”、朗西埃“艺术审美体制”,甚至是斯蒂格勒广泛意义上的“感觉”,一种“普遍意义上的感觉性”[1],都在暗示当代美学研究正在重返感性经验场域,感知问题被重新研究,并与政治问题和社会批判紧密联系,日益成为重要的美学议题。不同于艾尔雅维奇,朗西埃认为当今美学的主要问题在于“艺术的丑闻”和“美学的欺骗”两个方面。现代艺术将“随便什么”的日常物件和生活图像都接纳到审美领域,不遗余力地追求某种反讽的思想深度,其形而上的持续挞伐实际上破坏了美学“歧感”力量的生产与运作,并非是一种先锋性的审美革命。在随之而来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浪潮中,美学被赋予了革新生活却无法兑现的承诺,最终在与力比多经济、资本市场的合谋中迷失了自身。
除此之外,现代主义美学的拼凑、置换、日常生活化和先锋性,是立足对主体感知的短暂性和突发性影响下的完全形而上的思想艺术,实质上忽略了美学最初“感性学”的内涵维度。所以,在现代主义美学与西方政治革命忽隐忽现的暧昧关系下,随着政治革命的结束,现代主义美学最终寿终正寝。大众和美学没有否定“侵略者”,而是随着“侵略者”的否定一起走向灭亡。德国韩裔学者韩炳哲正是看到了现代主义美学的问题所在,由此回归到感知层面上来探讨美学问题,进一步考察现代大众美学的平滑性问题,试图提出自己的审美救赎方案。
韩炳哲考察了当今时代的美学标签,苹果手机具有自愈功能、几乎无损的屏幕触感,杰夫·昆斯高度抛光的艺术雕塑,巴西热蜡脱毛下的光滑身体,以分享和点赞为主的“赏心悦目”的人际交流,作为知识色情形态的透明信息等,“平滑”正作为整个时代的审美要求被全面嫁接到个体感知中,它表征了愉悦、圆润、光洁、轻盈、无阻、顺从、快速等一些积极性属性,其所蕴含的绝对肯定意义披着美学的华丽外衣被堂而皇之地售卖消费。具有超前先锋性的现代艺术,打破、颠覆一切传统束缚,最终沦为“观看作品的人或许只会发出一声简单的哇哦”[2]3,这一切极具讽刺意味。在“美的感性化”现代历史中,“美被完全禁锢在其纯粹的积极性之中”[2]21,从而形成一种“平滑美学”。那么,“平滑美学”的盛行,究竟是一种现代主体内在于自身的自发感官需求,还是一种外在消费意识的强制移植呢?
“平滑美学”主要指向主体触觉所带来的美感体验。触觉最初称“肤觉”,“肤觉是全部的躯体感觉,在其他感觉之首”[3],指向主体的感官想象和知觉综合。福柯认为“比起其他所有感觉,触觉更能激发快感”[4],并提出触觉是作为所有感觉的普遍形式起作用的。触觉作为沟通主体内外的光辉地位由来已久,但在近代艺术理论领域却并不受宠,甚至被一度贬斥。黑格尔将艺术感性限定于理论上的视觉和听觉(绘画、建筑和音乐),认为诸如触觉此类(嗅觉、味觉)是物质本身直接具有的感官属性,触觉平滑带给人的是舒适的感觉,并非真正的审美体验,从而直接否定了“平滑艺术”及其美学合法性。罗兰·巴特在《神话学》中论述雪铁龙新款DS系列,提出其完全无缝精密的组装,带来了一种触觉强迫,而触觉正是消除神秘的感官,其平滑带来的完美感和轻盈感在触碰的瞬间消失。与之相对的视觉与听觉,则保持距离和神秘。巴特认为美学评判以存在默观距离为前提,变相质疑了“平滑美学”的合理性。黑格尔将“平滑”所带来的触觉剔除于美感机制之外的做法,韩炳哲并不完全同意,他认为触感也是产生美感的感官功能之一。尽管触感如巴特所说,触感会消除审美距离,降低美学效果,但本质上并不会取缔审美体验的瞬时生成。真正的问题在于,“平滑艺术”仅仅停留在单一的触感(舒适感和平滑性),并将其推崇为美学的至高价值与唯一意义。最后的结果是,现代大众文化美学重点关注主体触觉,并从视觉、嗅觉、听觉、味觉、性觉等全方位去营造“平滑感”。在商业运作机制和消费者心理的共同协作下,将美感仅仅塑造为一种绝对积极性、肯定性、愉悦性,导致了美学自身的扁平化。“平滑”通过营造一个绝对愉悦性的世界来展现平滑艺术的救赎维度,最终导致美学的庸俗化倾向。“平滑美学”在现代资本市场和消费社会能够大行其道,与“人”的一路高歌前进不无关系,其理论正肇始于自启蒙以来主体性的抬升与膨胀。
英国经验美学家埃德蒙·柏克在《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中,首次将作为美学范畴的“崇高”与“美”区别开来,提出美的本质是不同于崇高的“平滑性”,美是一种充满肯定性的欢愉。康德将美等同为认知过程,提出崇高是面对自然界无限力量想象力受阻下激发的自身主体理性,是审美想象超越主体感性限制的结果,促进了主体认知力的协调互动。康德这无疑是在“……用积极的理智能力去限制消极的感觉物质性”[5],其批判最终导致了美学的主体化倾向。无论是柏克将崇高排除于美学之外,还是康德从认知层面将崇高统合进美学,都是企图将美限定在单一的积极性范畴内。伯克的排除、康德的转化无疑都服膺主体性的权威之下,难怪阿多诺将其斥为“自我意淫性美学”。韩炳哲批判自启蒙以来,美学作为主体思想革命的形式被完全悬置于物质材料之上的方式,同样也反对现代大众文化美学为取悦主体感官满足,将感知架构为单一的平滑欢愉。韩炳哲试图取消凌驾在消极性之上的积极性的优先地位,认为内核同质的“平滑美学”在审美实践的感性体验只能形成单一的感知模式,主体也并没有从其“平滑性”中克服自身物质的惰性而摆脱沉重存在的压迫,并最终造成“审美无产化”的后果。何谓“审美无产化”?斯蒂格勒将“无产化”定义为知识的失去,“审美无产化”即是审美的去知识化、去他异性,美感成了单一快感。“平滑美学”的欢愉性和积极性倾向是美学无缝衔接资本市场的工业文化产物,“通过感知的复制和疏导装置,导致了消费者的感性的无产阶级化”[6],审美由此成为一种简单的文化消费和感官经济,也正是在这种感知的复制与梗阻中,美学成为一种同质化和积极性的主体快感和自我娱乐。
现代文化产业通过对可感物的控制深刻影响了主体感知,美学成为一种核心的经济功能,个体的日常生活由资本市场和大众媒体共同控制。“平滑美学”与主体感官需求、身体欲望无疑是同轨并行的,其单一的欢愉要求生产重复叠加的自我快感。“平滑”从感官维度上来说,清除了褶皱、凸起、缝隙、断裂等所有异质性感知,貌似是在审美实践中对主体感知进行疏导,实则在主体与美学之间建立了一种局部流通机制,将市场批量生产的美感直接运输至主体感知场域,最终致使主体感知流通的结构固化和同质覆盖。由此,美仅仅成为一种单向的自我感知,从而与他者无关。“平滑美学”在消除异质性审美体验可能性的同时,只能在主体内部循环单一快感,最终将主体的存在掏空。韩炳哲提出,“感知”的根本性问题在于对象性,斯蒂格勒也认为“感知他者”是文学艺术的重要问题。“平滑美学”在消费社会和资本社会控制下,感知的对象由他者完全转向主体自身,美感成为单一快感,美学由此成为一个“彻底去他异性”的自我感知问题,“感知”从根本上失去了原初意义。不同于朗西埃关注“感知分配”在运作过程的内部机制问题,韩炳哲强调勘察内嵌于主体性视域中感知的投射对象和范围问题,关注“审美感知流通”的问题,认为现代“平滑美学”在流通领域尚未进入美学经验的运作进程,被现代主体全部反向吸收,内化为大面积的自我感知,阻断了“感知”流通的“他向性”进路以及随之而来的“他者性”反馈,失去了感知流通的交互性体验和关系生成的可能性,“他者”所表征的差异与多元也在感知领域和审美实践中慢慢消失。
二、重构他者:自然、遮蔽、创伤、灾难
韩炳哲在当代批判理论语境下聚焦于“感知”问题,通过对“平滑美学”的历史分析和有效批判,洞察了现代主体同质化审美取向形成的深层因素,即他者的消失。由此,韩炳哲开始关注近现代美学主体压抑下的异质性层面的审美重塑,赋予美学“他者性”特点,试图呈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审美范式的可能性。针对“平滑美学”出现的种种变体:“数字化之美”“透明性之美”“娱乐化之美”“后免疫性之美”等大众美学现象,韩炳哲提出“自然美学”“遮蔽美学”“灾难美学”“创伤美学”这类日渐消失的审美维度,来对抗“平滑美学”带给人类的否定性的无能和日渐衰微的意志力。
(一)自然美学和数字化之美
从康德开始的观念美学到谢林的艺术哲学,老生常谈的自然美学逐渐在所谓更高的领域被扬弃,这种“美与日俱增委身与分析”[7]106的做法受到了阿多诺的谴责,他认为“真正的审美经验并不是主体能够享受重识自我的满足,而是主体对其有限性感到震惊或者领悟”[2]32,自然与主体感知交互下的一种否定性审美体验,崇高美即属此类。受阿多诺的启发,韩炳哲批判自康德以来的“自淫性主体美学”,提出正是主体的过度侵凌导致了对自然美的破坏,它“惯于毁坏所有不受主体操控控制的东西”[7]95。韩炳哲认为,自然美并非指美丽的自然风景,而是一种“……向盲目而无意识的感知开放的”[2]32自然环境与氛围,一种沉默并留待调试的尚未存在者的代码。韩炳哲认为,正是艺术对自然美的模仿,使得沉默的自然美本身得以显现。由此,自然美被赋予一种“谜语气质”,包含着一种否定性的生成、非同一性的参与、不可界说的多维可能性。“作为不确定的东西,自然美敌视所有一切界说”[7]111,它用自己的特性正在对抗主体感知的同一人格化,并通过一种彻底的否定性方式来使主体摆脱自我意淫的牢笼。所以,唯有将自我的有限性展示出来,才能理解自然美,成功避开了主体的利用与消费的崇高美学。由此,主体对自然美崇高部分的愉悦是独立于对其使用和消费的任何预期占有,其本质上是一种未被自足主体所捕获的他性美,有“未然的已然”的时间性和“非同一性”的相异性特征。
与之相对的“数字化之美”,一种现代信息社会中“平滑美学”的数字高级配置模式,它致力于信息图像、人际交流的快速畅通,拒绝任何阻碍和断裂,是人为制造的虚拟代码。“数字化之美排除任何否定性,标志着不加任何否定的满足”[2]33,营造了一个完全同一性的平滑空间,主体在绝对数字化的世界中感知自我。“数字化世界似乎是一个人们用自己的视网膜就能将其尽收眼底世界,这个被人为联网的世界将导致永久的自我镜像的形成,网络编织的越密这个世界就会彻底地包会自己不受他者与外界的影响,数字化的视网膜将世界变成显示器与控制屏。”[2]35“数字化之美”没有时间维度上的过往和未来的现在时,消除了所有非同一性的否定性,具有一种以消费为目的的伪多样化差异。在数字化的人类视觉空间,只有主体感知的不断复制。
(二)遮蔽美学和透明性之美
韩炳哲提出“遮蔽的美”和“透明的美”,并指出美本质上是一种遮蔽,而“透明的美”是一种矛盾的说法。现代大众文化审美在数字信息社会的影响下对透明性尤为推崇,甚至逐渐将其簇拥为美学的重要标准。韩炳哲利用“色情”和“情色”隐喻了“遮蔽的美”和“透明的美”的区别。色情图像中的赤裸肉体是身体的一种透明状态,透明性的身体都是雷同的,性器官被局部突显。这些图像的特点:无遮掩、无秘密、简单直接,从而快速刺激了主体的感官反应。“梅普勒索普通过近距离拍摄内裤布料,把他的性具特写从色情变成了情色”[2]38,将其关注的主要事物由性具转向内裤,将次要事物提升到主要位置,分散审美的注意力,使得美自身不被直接触及,遮蔽、延迟和分散成为“遮蔽美学”的时空策略。美不是遮蔽物,也不是被遮蔽物,而是遮蔽下的物。因为正是通过这种遮蔽,美才得以生成于事物中。歌德诗歌中“被彩色玻璃折射后的光所遮蔽的内在空间”“《托拉》中躲藏的情人形象”“人物化的漂亮外衣覆盖下的《圣经》”[2]39都是对于“遮蔽的美”的诠释。韩炳哲借助圣经的注释阐释学,提出对于原文本的不断注释本质上是一种遮蔽技术,在最大限度上增加了人们对于原文本的阅读情欲。正是在这种注释下,若隐若现的原文本所形成的某种微弱缝隙、断裂和缺口,其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所造成的“他者性”将“色情”转化为“情色”,赋予原文本无穷魅力,读者在遮蔽中受到诱惑和牵引,不断寻求注释与重新阐释,从而脱离主体的自足自满,走入一种他异性。
除此之外,信息、数据、图像等事物的透明性同样是一种现代美学原则,它们的本质即是可见与展示。在透明社会中,主体行为、语言、事件、性等等成为可计算、可控制的透明性存在。可以说,作为现代信息社会的一种系统性强制行为,透明性席卷了所有社会领域和事物发展进程,包括人类自身,并由此发展为一种新型暴力。“女人在裸露的一刹那,就失去了性的特征”[8]106,正是性的透明最终成了暴力毁灭了性自身。不同于传统的排斥性暴力,“消除门槛、消除差别和界限导致各种形式的过度增值和社会循环的过度肥胖”[9]143,透明性是一种将所有东西调整为同类的扩张性暴力。“完全的透明性”将主体降格为一个数字化发展的优化项目,主体在完全的照明中无限扩张自我,最终灼伤自己,引起某种神经性疾病,这就是透明性的暴力。“我赖以生存的是我身上那些不为人知的部分”[9]146,而现代功绩主体正在通过一览无余的自我展示来将自己功能化和市场化,从而丢失自己的独异性,成为社会系统中的调配元素,最终主体“……不再遁于黑暗之中,而是消失在过度照明和过度曝光之下”[9]150。“透明的美”依靠可计算的数字化来具体呈现自己,是对一系列遮蔽物的全面撤销,用虚拟的数字化符码来代替事物的实体状况,将一切“他异性”的欲望、幻象、梦和意识转化为可控制的数据展示和系统调节。这种透明性的数字曝光是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常用策略,没有否定性的遮蔽物,只有等待处理优化的障碍物。“透明性美学”的发展终极是“遮蔽美学”的死亡,更是文学艺术的衰落。
(三)灾难美学和娱乐化之美
无论是康德的主体理性,还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某种程度上都是对外在消极性、完全他异性的一种变相否定。“心中的道德律令”是主体理性的结果,“头顶上的星空”也并非指向外在的自然法则,而是主体理性中无限延展的内在性。这种被充分肯定的内主体性是“没有灾星”的,因为主体诉诸理性力量,能够将其逐渐内化。把一切外在事物都引入主体内部是康德思想的定言令式。黑格尔用“千眼阿格斯”隐喻主体的这种内化行为,并将其视为“艺术的任务”。将可见外表上每一点所显现的形象都变成眼睛,而这“眼睛”正是主体内在性中无限的绝对精神。不同于康德“星空”闪耀明亮的主体之思,韩炳哲提出一种“灾星”形象,表征一种消极、否定、异质、外在,它不是“星从式”的主体内在性,而是一种“打开精神内在性的外在”[2]57,是不受主体照管的一种异质性存在。布朗肖的“空洞天空”与“灾星”一样,是与“满天星空”相对立的“完全他者”,“一种无法内在化的外在的特应性”[2]57。由此,韩炳哲提出一种“灾难美学”,其本质上是“事件美学”,它并不涉及美感与道德感的关系,是指主体的某种突发性的事件性,“一个将自我掏空,让自我失去内在性、失去主体性,却因此而让自我感到快乐的空洞事件”[2]58。这里的“灾难”是对于主体而言,因为那是自我意淫主体的死亡和消失。波德莱尔的《恶之花》、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都显示出灾难、可怕、致命之物的消极性,却成为美的重要基础,韩炳哲正是认识到这压倒一切的主体同一性的恐怖之处,从而提出打破主体性的“灾难美学”。
韩炳哲批判了“娱乐化之美”作为寻求感官快乐和自我满足的主体原则,这种“娱乐的纯粹无意义性与耶稣受难的纯粹无意义性是相似的”[10]4。韩炳哲将其隐喻为“甜蜜的十字架”,即“受难者为了福佑将自己的幸福抵押出去”[10]4,这种悖论式交换也正是“娱乐化之美”的核心逻辑。现代主体为了获得感官娱乐而将主体感知抵押给资本市场操控,从而失去了真实的审美感知能力。当今时代一切事物呈现泛娱乐化趋势,教育、游戏、信息、图像、辩论,甚至恋爱情感、婚姻家庭都在娱乐化,著名综艺《奇葩说》《非诚勿扰》《爱情保卫战》等电视节目的流行都是“娱乐化之美”的典型混合制作模式。现代娱乐的无处不在正是娱乐美学的绝对化,他们如同一种快适艺术,“……没有被赋予形而上学的潜力”[10]155,是直接短暂、转瞬即逝的,甚至成为现代功绩主体夺取自我和时间的假象存在,一种疯狂的报复性娱乐,如节假日的疯狂出游、熬夜成瘾的沉浸式娱乐等。在这种“丝毫不晃动精神”的感官娱乐中,主体正在被慢慢榨干,疯狂萎缩成一种毫无“事件性”的娱乐人,所以说“娱乐的世界是伪装成天堂的地狱”[10]49。
(四)创伤美学和后免疫性之美
罗兰·巴特谈到爱情,提出“创伤情色论”,即恋人是无皮汉。这种“去皮性”隐喻了主体自身的敏感性、易损性和脆弱性,是一种渴望在某种关系中深度感知彼此,从而让渡一部分自我来承受他者异质性的方式。“去皮”是对于自我中他异性的创伤和痛苦的交代与袒露;“去衣”的裸体则是为了完全透明性的自我展示,作为一种色情诱惑和身体兜售,“她们的技巧作为衣服替她们穿上了”[8]108。脱衣舞从表面上来看,主体尽褪衣饰,甚至局部放大性器官,却从自身内部形成一个不容置疑的自足主体遮盖物,消除了所有创伤性和消极性的可能性存在。“去衣者”避开了“去皮性”可能带来的对于主体自身的损伤,从而避开了任何消极性感知,回归主体本能的自我需求感知模式。除此之外,巴特在摄影中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研点和刺点。韩炳哲将研点总结为一种包含随意的欲望、兴趣、嗜好等的辽阔的信息场域;刺点犹如偶然地“……从照片的场景里像箭一样射出来,射中了我”[11],是惊讶、悲伤、错愕下的视觉盲区,一种隐藏、无法陈述的具有抵抗性的余留之物。研点被称为主体的场域,主体在其中欣赏、破译,带有实行主权的意味;刺点则是“将我刺穿”的打乱、干扰、错愕,由细节开始占满整张照片,潜藏着扩张的力量。“将我刺穿”也就是“将主体刺穿”,“它很有穿透力,能钻进我为之我的一个不确定的区域”[2]50,其所产生的裂缝就是他者的隐藏点。韩炳哲将罗兰·巴特关于摄影的理论总结为一套“创伤美学”。
里尔克在《布里格手记》中,将“看”描述为一种创伤,韩炳哲将其阐释为“使自己完全遭遇侵入自我未知区域的事物”[2]46。这种“看”意指一种主体不自觉的遭遇。人逃离主体的完全掌控,从而敞开自身,具有“易损性”的“看”承载了“他者”的出现,从而激发了异质性的视觉感知。“没有创伤就没有真相”[2]46,创伤使得“看”这一行为攫取住存在所具有的否定性,使得主体获得关于存在的完整感知。在千篇一律的审美感知模式中,主体面临的并非是真实,而是感官需求和市场资本创造的娱乐幻象。这种“创伤美学”意味着主体自身的敏感性和易损性,只有这样主体才能摆脱完全自我从而体验“他者”,在这种痛苦的“否定性”中,他者存在的相异性得到揭示。
与“去皮”“刺点”“看”的“创伤美学”不同,现代主体从生物学角度崇尚“后免疫性之美”。免疫学作为生命科学的前沿学科和医学基础学科,对人体健康的预防保健具有重要意义。免疫分为自体免疫和体外免疫,自体免疫是人自身产生抗体,从而维护机体内部环境平稳。外体免疫则是事先将一个无害的病原注射到人体内,从而促使人体产生抗体。当人体再次接触了病原,就会快速大量产生抗体,抗体和抗原的特异性结合,杀死病毒从而抵抗疾病的侵袭。现代主体依靠免疫学,试图抵御各类特异疾病,从而不断优化人体生长发育。韩炳哲从象征意味上提出这种“免疫”保护主体的同时,也筛选优化了主体的最终样式,因其为主体排除了各类病原影响的同时将制造千篇一律的健康模式。“什么也没有被禁止:你只是被告知了一个因果联系”[12]94。“他者”与“否定性”正是在与主体所谓的因果联系中被知识逻辑判处死刑。也正是在这种伦理价值的指导下,主体对自身注入少量否定性,在遭遇否定性的同时将其转化为一种过量的肯定性,从而消灭否定性自身存在,他者性与陌生之物彻底消失。这种“永久性免疫”被韩炳哲称为“后免疫范式”,其从医疗领域到审美领域,身体完全健康的同质化幻象正在勾连精神始终欢愉的单一性美梦,数字化、透明性、娱乐化正是人类感知免疫下的审美需求,一种“后免疫范式”的审美实践。
三、免疫美学:审美感知的流通
同罗兰·巴特一样,韩炳哲的美学思考似乎也蕴藏着寻求对立概念的热情。“就像魔术师的手杖,概念,尤其是成对的概念,催生了一种写作的可能”[13],这些对立概念作为“说出某些内容”的生产修辞,是一种美学异质性层面的观念重构。韩炳哲提出自然与数字、遮蔽与透明、灾难与娱乐、创伤与后免疫等一系列对立美学范畴,作为一种抵抗自启蒙主体美学到现代“平滑美学”的手段策略,本质上暗合了20世纪免疫学范式的内涵逻辑。
韩炳哲追溯了20世纪的免疫学范式,包括内外、友敌、攻击与防御、自我与他者等一系列对立边界问题。在美苏冷战话语与军事规则控制的氛围笼罩下,这种免疫学范式从生物学领域逐渐蔓延至整个社会层面,主体开启防御模式,对于他者等一切陌生之物的盲目攻击逐渐成为其特点,最终导致后免疫学时代的来临。后免疫美学指向以“平滑美学”为中心的数字化、娱乐化、透明性等一系列美学诡计,它为了拯救表层感官和肉体娱乐牺牲了完整自我,“通过自我毁灭来拯救自己的灵魂”[14],韩炳哲则试图修正免疫范式的条件逻辑以期将其重新运用到审美实践中来挽救现代大众文化美学的困境。
“免疫”一词最初作为一个生物学和医学用词,指的是生物内部所拥有的一套抵御外界侵害的反应系统。经过德里达、哈拉维、埃斯波西托等人,“免疫”逐渐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哲学概念开始汇入到由福柯开启的生命政治学的研究路径中。从德里达到哈拉维,是一种由否定性视角的自体免疫到肯定性维度的外体免疫的转变,埃斯波西托在吸收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接续性地将其视为一种对于个体与共同体关系及其边界的重新思考。“免疫”一词的概念滑动和范式流变使得“免疫范式”拥有着活跃的理论阐释空间。埃斯波西托从生物医学和政治司法双重层面定义了免疫的基本范畴,从面对疾病身体自发产生的抗体到暂时性或决定性的责任豁免,暗示了免疫范式作为知识经验和固态模式存在于主体生产和社会系统中,从其关于保存生命的客观起源走向了一种外部分析的理论阐释。它涉及疾病与健康、肯定与否定、保护与毁灭等一系列二律背反的内在逻辑,“免疫成为生命保护的一种否定形式”[15]。
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中分析了埃斯波西托的免疫理论模型,认为埃斯波西托的理论假设条件在现代社会并不成立。埃斯波西托援引大量案例,例如20世纪美苏两国的冷战模式、东德西德的柏林墙、攻击和防御的军事化行动、非法移民的壁垒加固等,说明其免疫学范式的根本性原则——他者性,其“免疫学范式”可以横向剖析不同的独立话语,但最终都汇集到同一个意义视域:“面对危险侵袭时的保护反应”[16]6。韩炳哲指出这种免疫学范式在当代理论应用的根本问题,即“危险侵袭”的事实性发生。埃斯波西托始终是从身体之维来思考免疫范式如何在生命政治框架中建构共同体的问题,忽视了直接的身体冲突被日益严格的社会规范和政治司法所制约,社会战场由外部逐渐转移到主体内部,一种精神冲突正在愈演愈烈,由此异质约束和自我约束交替崩溃。
随着20世纪冷战结束和全球化经济进程,以埃斯波西托的“免疫理论”为基础的诠释模型近乎衰落,无法解释当今免疫范式的重大转型,一种由医学生物领域向审美感知层面的转移悄然而至。主体不再面对“危险侵袭”的事实性和“全然他者”的陌生性,而是预防式主动地对于自己施加少许暴力,由此触发身体内部的免疫反应,由此产生抗体,从而获得“永久性免疫”,完全避免未来的不确定威胁,走向一种后免疫时代。这种由否定之否定最终走向一种过量的肯定性,彻底消除了“他者性”和“否定性”,在过量的肯定性中不断吸收和同化,主体的“知觉过敏”能力消失殆尽。韩炳哲分析了21世纪以抑郁症和倦怠综合症为主的精神类疾病,认为其正是由一种完全缺乏否定性的过量肯定性导致的,从精神之维指出了免疫学范式的问题及其重新应用的价值前景。
免疫学的基本特征是一种否定辩证法,“免疫学上的他者是否定的,侵入自我个体并试图否定它。如果自我不能够反过来否定侵略者,它将在他者的否定下走向灭亡”[16]7。主体正是通过这种否定之否定,从而完成自我持存。虽然这种否定之否定最终导致一种肯定结果,但是这种否定之否定本质上不是负负得正,即否定的叠加使得自身成为一种肯定。在后免疫学范式中,“将否定性本身进行前所未有的肯定化”[12]114,这种否定之否定由此丧失了本质性,最终也丧失了自身逻辑的批判性和辩证性。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后免疫学不是一种免疫学,而是一种非免疫学的排斥反应,利用机体惯性盲目排外,精神疾病中的自我拒绝和内心冲突、主体的抑郁倦怠和窒息感即属此类,最终导致主体自身的毁灭。这种后免疫学中的负负得正逻辑,蕴藏着一种过剩的肯定性,正是一种缺乏他性的主体精神的逻辑暴力,也是一种关于肯定和自我的极权主义。
韩炳哲对埃斯波西托从身体之维所阐释的生命政治和共同体建构下的免疫范式进行了时代修正,指出伴随着“他者”和“否定”的消失,这种诠释模型自身的衰落,由此导入21世纪的后免疫范式的出现,尤其是“平滑美学”的大行其道,“否定”作为一种他者失去了自身的本质存在和独立性,而被纳入肯定的范畴。除此之外,免疫范式由外到内的转变,使得主体内在承载着不断超载的肯定,过度的生产、超负荷劳作、普遍的信息化和过量的交流等,正是在这种情境下,主体审美感知趋向麻木,其审美体验在资本市场和虚假自我的双重操纵下趋向复制性的同一。主体在繁复同质的审美体验中,被外在事物所控制却将其视为自发行为的同时,感知由内到外的流通性面临大面积梗阻状态。韩炳哲通过自然、遮蔽、灾难与创伤等一系列“他者”对主体感知进行免疫注射,并保护这些“他者”的“否定”能力的独立性以此发生触敏反应,激活主体感知的他向流通性,并在这种斗争逻辑中维持主体感知系统的持续运转以达到自我保存的结果。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自然、遮蔽、灾难和创伤美学正是一种预防主体知觉麻木的免疫注射,企图挽救后免疫美学下主体感知系统的瘫痪问题。基于现代主体在数字化、透明性、娱乐化、后免疫化中走向感知的梗阻与瘫痪,韩炳哲试图借助自然、遮蔽、灾难与创伤等范畴在完善美学自身内涵范畴的同时,指出其对于唤起和维系主体感知系统的重要作用,通过不同美学范畴的彼此勾连,重新激活美学过度平滑性所造成的感知梗阻,从而实现审美感知的流通。
四、结语
韩炳哲的美学思想,其核心逻辑吸收了埃斯波西托的免疫理论,以对于平滑美学的分析批判为中心,立足于主体审美感知问题,围绕自然与数字、遮蔽与透明、灾难与娱乐、创伤与后免疫等范畴,形成了姑且称之为“免疫美学”的思想命题。“免疫美学”思想揭示了美学自身的多重性内涵,在对感知流通和免疫反应的理论映照和逻辑互动进行探究的同时,力图恢复审美感知的流通,一种由他异性所形成的复杂化、多样化的感知体验,这也是韩炳哲《美的救赎》一书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