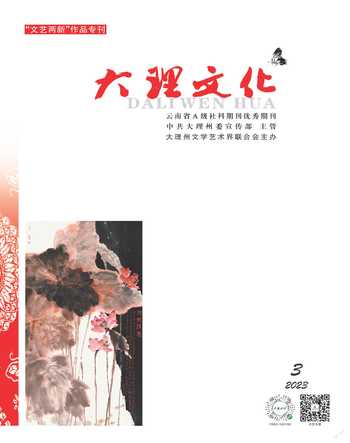三河情
施亮池


三河行政村毗邻丽江九河,俗称剑川县的“北大门”。这里有极富民族特色的白族服饰(也称喜鹊装),因此被命名为“剑川三河白族服饰文化村”。下辖河东、河北、河南三个自然村分布于214国道两侧,隔路相望,其中,河南、河北在路西,河东则紧挨国道。
原计划,由一位来自河东村的高中同学带领我寻访三河。几近中午,我如约抵达,同学已在家门口等候。房屋遮蔽,阳光稀薄,厨房内飘来的煮鱼香味在清凉的空气中四处弥漫。寻访之前,我在她家吃午饭。一大锅汤白肉嫩的清水煮鱼置于厨房中央的餐桌上,在一片似白非白的颜色包围下,乳白色的鱼肉和黄白色的芹菜并非无从分辨。一股白气缓缓上扬,不断变幻着姿态,一会儿清晰一会儿朦胧。厨房之内,温度较屋外高些。同学细心无比,特意端来一碗色彩斑斓的豌豆凉粉,碗里有香菜与葱花的翠绿、凉粉的浅黄、辣椒粉的鲜红、花生末的红白,吃完还驱走了热意。鱼乃剑湖野生鱼,凉粉乃剑川白族人喜闻乐见的夏季消暑小吃。碗筷之间不断交叠的碰撞声,无不折射饭菜的可口与我的意犹未尽。一温一凉,恰如其分抵消了二者的饮食界限。吃罢,小憩一会,既无意料之中的大汗淋漓,也非意料之外的凉意四起。出门时,同学临时有事,唯我踽踽独行。
穿越国道,向西径直而去,我此行先前往河北村。一条水泥大道延绵不绝,房屋居两旁,但大多集中在路右边,随山坡的陡势逐渐攀升,其间古木参天,疏落有致,山体裸露在阳光下,褐黄相杂的土壤平添出一番古朴粗犷之美。路左,原野辽阔无垠,有一条水泥小径弯弯曲曲从中穿过,跨过一座石拱桥,又曲曲折折幻化成土路抵达另一个村落,那便是河南村。
河北村多为土木结构的老房子。早年间,来自丽江等地的商人常来此收购老式门窗。相较于剑川坝区的村落,以河北为代表的三河村依旧延续着传统的生活方式,现代化气息似乎鲜见。
我很快就见到一间小卖铺。身穿“喜鹊装”的老媪倚靠着小卖铺的铁门,漫不经心地拍了拍坐垫,挪躲在阴凉一角,阳光灿烂,令人睁不开眼。我眯眼略见铺内黯淡无光,近前细细一窥,才觅得里头的货什商品不多。我买了一瓶矿泉水,顺便坐在铺子前的木墩上休息,与老媪聊天。
“我们三河人每逢喜庆节日、新婚嫁娶、起房盖屋或农闲之余,男女老少身着盛装,三五成群相约至村寨旁、村中广场或田头边的空地上,围成一圈或数圈,举行打歌活动。大伙儿情绪饱满,动作流畅大方,情感真挚热烈,从无什么定式,随心所欲,尽情挥洒,歌唱生产和生活。”老人慢条斯理地说着,却难掩激动之情。
“当然,每个群体,都有属于各年龄阶段的服饰要求,我们老年人,不似少女那般色彩鲜艳,也不浓妆艳抹,会被笑话的。”老人继续说道。
“若抛开色彩层面,服饰从少至老未有改变么?”我突发好奇。
“少女时期,所戴头巾色彩艳丽,包层较少,顶部扎制成喜鹊尾状,但结婚以后直至去世,就变成了多块相叠、颜色深沉的头巾。”她边说边比划。
“我们有好几套服饰,均是自制,一年四季,不论严寒酷暑,从少女到老年,陪伴终生。旧了坏了又重缝新装。不过——”
她顿了顿,接着说:“冬天还好些,若是夏天,天气酷热,也得穿这厚实的服饰,风俗传统自古如此,须耐得热,长年累月便慢慢适应了。”
“现在老了,身体不如从前喽,气温稍凉便觉不自在,而今身穿传统服装饶有好处。”老人面色清和,笑容可掬,仿佛成了一个纯真稚童。
由历史记载可知,至少自元代始,剑川毗邻丽江,北境便达三河村,延续至今,几不变迁。由于地理位置特殊,三河村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常遭兵燹之厄。譬如南宋淳佑四年(1244年),蒙古军一部南下云南乘革囊横渡金沙江,欲以丽江攻克大理,至九河遭宋代大理国民族政权将领高禾(和)部奋力抵抗,战斗极为惨烈。此役对南宋王朝鼓舞极大,特派专使至大理吊祭高禾将军,并在九河建立纪念塔,俗称“白王塔”。
这里除了是战略要地外,还有南来北往的商贸活动、民族文化交流等,共同塑造了三河地区独特的历史人文景观,而这一现象在“三河式”服饰上尤为突出。它融合了白族与纳西族妇女的服饰特色,整体保持白族风格,背饰七星白羊皮披毡却类似纳西族款式,在很多方面反映了三河白族的历史文化内涵、风俗习惯及审美观念。
“三河式”服饰也称“喜鹊装”,以妇女服饰为代表,一般采用靛蓝、天蓝、紫红、粉红、纯白、黑色等颜色的优质布料缝制,分中老年装和少女装。大体包括头巾、上装、下装、背披、围腰、挂巾6大部分。中老年妇女头巾常用黑色、靛蓝布料,边挑白色花线,多块相叠制作而成。少女服饰色泽鲜艳,靓丽大方。头巾色彩艳丽,包层较少,顶部扎制成喜鹊尾状,配以鲜红或五彩绒线垂肩缨穗;上装内衣、外衣颜色不同,外衣袖筒置精细袖圈,外着无袖领褂,内外衣均前短后长;下装宽裤口大裤裆,并系精绣围裙,显得潇洒明快,干净利落;背披为千层布纳制,下摆为白色绵羊皮,由于与丽江接壤,亦有加缀披星戴月形式的环形装饰;挂巾为配戴饰物,由10余块颜色艳丽的须边方巾相叠而成,方巾上挑有精细图案,一角系于腰前领褂布扣,下摆自然垂至腰部,别进围裙。三河服饰别具一格,含有吉祥幸福的寓意,充满独特浓郁的文化气息。
有人恰好來买东西,老人起身进屋,找她零钱。这人皱纹满额,年逾古稀,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三河白族老妇人。天上,原先闭目养神的太阳开始发力,阳光尤烈。树梢间,鸟声清丽鸣啭,似在抱怨毒辣的烈阳。我被邀请入屋小憩,两位老者此时已坐在方凳上。我们的话题旋即再续。
“再过十几年,或许我们这一辈人都将离世了。”
“活得太长寿,未必是好事,倘若自顾不暇,只会给子女平添负担,也活得痛苦。”她们若无其事说着,但一丝不易察觉的愁容在两人眉宇间掠过。
“您们大概是属于最后一代坚守传统的人了吧。”我的问题似是而非。
“我的女儿、儿媳和孙女们识书认字,紧跟时代潮流,逢年过节打跳时,她们身穿传统服饰,活动结束便可换回现代装束。而我们成了最后一代人——终年与传统息息相关。”她们听懂我所表达的意思。
我继续寻访,她们建议我去村中古井那儿(文化广场背后)看看,旁边有一群老太在纳凉,据说,其中有很多人曾到縣上多地跳过舞。
未久,我便抵达古井那儿。2019年时,这里被修葺一新,名曰“万古清泉”,古井碑记有一古诗,为河北村教师段鸿年所作:
河北村心有清泉,万年古代一井水。畜肥人健谁家慰,子孙万代用不完。冬温夏凉这股水,下雨天旱不增减。通年四季长清秀,未识水源何处来。
石碑立于1991年3月立夏。
古井东边,有一空地,石凳上仅坐着老太三五人。在中国广大的乡村,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大多为老人,集于村口、村中央、一切宽敞明亮的地儿,倚靠墙根、排排坐石凳边晒太阳边闲聊。而有趣的是,老头和老太们似乎互不合群,或无共同话题,两群通常“井水不犯河水”,各有地盘。我想坐下,老太们递予我一块坐垫,非常热情。寻访过程渐入佳境。
老太们告诉我,除节日外,人家来请,她们便应邀参加。来邀请的会提前打招呼,大伙事先排练,然后,大伙就组成成竹在胸的队伍出发了。石宝山歌会、剑川木雕文化节,她们都参加过。她们的舞蹈有时自创、有时仿跳,更多时候,只要音乐一响,每个人都会沉醉在优美的旋律中,信马由缰地跳着,不拘泥于某种定式,每个生命都绽放出璀璨的光芒。
以前,夜幕降临,村中广场满是人流,大家载歌载舞,不知不觉中就几近深夜。而今,年老体迈,不复当年,只能出来散散步,活动一下躯体,现在舞台上的主角基本属于年轻的一辈。生命潮起潮落,进场与退场的方式亘古不变,只是曾经鲜活的沧海一粟,珍贵而独特。
我又前往另一个村落——河南村。
田间水泥小径歪歪扭扭,犹如一条长鞭挥出,直至石拱桥。桥下有一条小溪悠徐流淌着,声音很小,将道路拦腰折断,于此出发,另一端成了尘土飞扬的土路,迤逦至山脚,尽头是河南村,与河北村相差无几,不过新房较多了些。
靠近村落,土路开始变窄,继而化作蛛网状,朝四周分散,四通八达,我犹如无意闯入一座迷宫,找不到出口,就这般稀里糊涂走着。此时正值中午,村民大多在田中劳作,好不容易逢遇一人,经他指点,我才踉踉跄跄寻着活动广场。一群中老年男人在凉亭内休憩,柳枝随风摇动,树叶轻颤,那风儿打东边吹来。从凉亭这里可俯瞰整个河南村。村庄鳞次栉比,呈阶梯状依山而居,狭长分布。
周三与周六是河南村的赶集日,四处跑街的小商贩来此摆摊,尽管规模很小,但对远离集市的村落而言,实属难得。我也终于回到了水泥大道,一垄垄小麦一碧万顷,如浪般从这头翻卷至那头,窥不透,飘扬的麦穗究竟是沉醉不醒的惬意抑或是被迫裹挟的忧郁。目光穿过小麦田,可眺望东边的河东村,规模倒比河南、河北村小些。
公路上车流依旧,对面又见一群老太,肤色暗沉,皮肤松弛;时而望望呼啸而过的大车,时而无力地垂首,五彩斑斓的服饰宛如一股强光,越集越密,在无数的空气中脱颖而出,射入我的瞳孔。揉揉眼睛,她们身后的红褐色土墙有些斑驳。
闻言,三河人有出色的经商才能,他们走南闯北,铸造一段段不同凡响的人生经历,或辉煌,或荒凉,或唏嘘……
我自来熟地在她们旁边坐下,欲打听一些这里的事。起初,颇想聊聊取得重大成就或荣耀乡里的典型人物。她们的回答莫衷一是,或干脆表示孤陋寡闻。
然而瞬间柳暗花明,很大原因源自我目光的下移,我逢遇一段波澜起伏的缩影。她不动声色地说起过往,却又满心澎湃。
河东村的段新开老人已78岁。1951年开始入学,1961年初中毕业后,当了7年民办教师,在此期间结了婚。因一些原因无法转正,无奈赋闲在家,为养活子女,只得另谋生计。识文断字的她购来裁剪书籍,最终无师自通,成为远近闻名的裁缝。当然,学习过程并非坦途,初次缝纫时效率低下,一天内竟缝不完一条围腰,但终于在无数次实践中渐渐得心应手。
其缝绣之物以三河、丽江的传统服饰为主,因气候差异、风俗习惯等原因,此种衣饰格外适合居住在金沙江沿岸的少数民族。多年来,她的足迹几乎遍布丽江、迪庆的各个角落,诸如石鼓、黎光、巨甸、维西、香格里拉等,有时也至兰坪金顶。每至一处,背篓里的缝制品很快就被抢购一空,生意颇好,与她炉火纯青的技艺息息相关。
何时何地赶何街,她自是熟悉。彼时,从剑川到丽江仅有两趟班车。凌晨四五点,她如往常一样去村口搭车,待到街市卖完东西,再乘车抵家已是半夜一两点。隔些日子,她会出一趟远门,出发前,在家中花费几昼夜赶制服饰,一趟行程少则几天多则十来天,沿金沙江一路穿行,逢街摆售,转六七趟车是常有之事。
同她一起远行的人来自附近村落。她们的落脚处极其简便,人常在半夜冻醒,白天,可能会吃到集市上隔夜的凉稀豆粉,以致上吐下泻。那会儿,金沙江沿线的山路崎岖不平,弯多坡急,汽车行驶其间,稍不留神,便会葬身江底。除面对险恶的自然环境外,还得时刻提防沿途中猝不及防的拦车抢劫:一群游手好闲之人想方设法逼停汽车后,面目狰狞地从车窗翻入,将司机与车内乘客全身搜遍,企获不义之财。
多年来,正是凭借这股敢闯敢拼的干劲儿,才含辛茹苦养活了5个子女,久而久之,便有了如雷贯耳的名号——女丈夫。后来,她母亲去世后,儿女亦陆续结婚,各自忙碌,家里似乎无人看管,渐渐地,不复东奔西走做生意,仅接些附近的活儿。从三十多岁始,几近四十载的裁缝生涯里,经年累月的久坐引发了肥胖、颈椎病、腿脚不便、视力下降等诸多问题,对此情形,老人依旧一脸喜悦。原来,在无数个昼夜辛劳中,她常常苦中作乐,算是找到一些生活的乐趣。
此乐趣便是她所擅长的山花词白曲创作演唱。其创作的一些脍炙人口的山花词曾在“夕阳红兰亭文艺杯”全国老年(大学)文艺大赛中荣获银奖,本人则被授予“中华夕阳红文艺先锋人物”荣誉称号。作品多次刊载在《剑川景风诗社》期刊。当然,她也是景风诗社社员之一。
她的山花词通俗飞扬,音律和谐,意蕴十足。譬如这首颂扬三河服饰:
我是白族一星宿,我民族服装都做;我身衣服缀红花,我无师自绣。我做女围腰带子,我从手工变机绣;我现绘画配电脑,我画电脑绣。白族服装真漂亮,白长衣裳红褂褂;白绣花鞋黑裤子,白围腰系上。白红绣球亮晶晶,白银金玉耳上挂;白线蓝布绣包头,白花皮披上。小小姑娘更漂亮,小白兔耳冲天笑;小黑辫子绕外边,小花发尖挂。小花巾一飘带子,小蝴蝶结腰边挂;小姑娘像花喜鹊,小线鞋配上。老年服装很朴素,老年包头花不做;老年绣球太阳紫,大花带系后。老爱大折边围腰,老用长蓝带围住;老人带须挂两边,黑鞋子走路。
老人领我到她家里坐坐,距离不远。走上二楼,步入里屋,泛出一股年代久远的书籍味儿。环顾四周,墙上挂了几张尺寸颇长的合影,多是文艺活动,一身醒目的民族服饰令她在人群中一眼可辨。她从一摞蒙尘的书中拾出一沓,递予我,有些是发表的刊物,有些是作品打印,有些是字迹模糊的创作手稿。
捧起手稿,她嘴中吐出富有音乐般诗意的白语,横竖撇捺的汉字霎时活了,在屋内飘荡、回响。手稿文字分两部分,前部为汉语直译,后端是汉字记音(类似汉字记英语单词)。我在旁边录音。某些山花词或因创作已久远,以及先观汉字,再转白语,读之,时常停顿,很不流畅。也许别有他途,倘若借新白文之力呢?1958年,徐琳、赵衍荪等语文专家拟定了以拉丁型26个字母为形式的《白族文字方案》。1982年对原方案进行了修订,简称“新白文”。近半个多世纪的新白文,很多白族人甚或未闻其名、知其形,妄谈熟练的书写运用了,由此可窥普及路途之艰巨。
老人告诉我,有两个愿望:将所写的山花词结集出版;再寻一写作者,记录她颠沛流离又异彩纷呈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