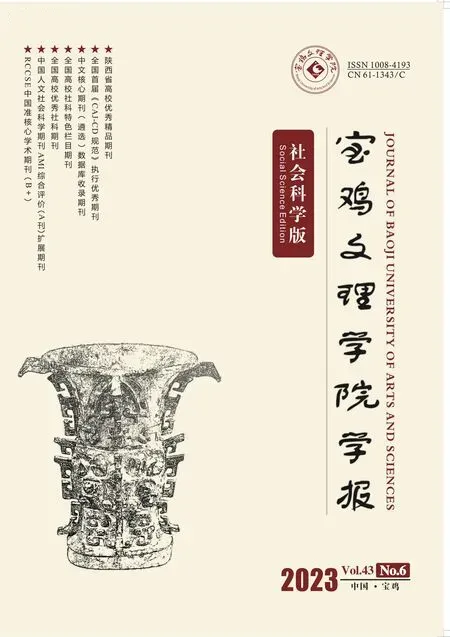嵩山《大唐天后御制愿文碑》与《大云经》问题考略*
姚彬彬
(武汉大学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2)
嵩山少林寺现藏武则天“御制碑”两通,其一为《大唐天后御制诗书碑》,另一通为《大唐天后御制愿文碑》,前者保存完整,但因所书内容尚保留在《全唐诗》和《全唐文》中,题为《从驾幸少林寺》和《赐少林寺僧书》,故原碑的史料价值相对有限,且清人王昶《金石萃编》卷六十中亦对其进行过著录和考证。《大唐天后御制愿文碑》残缺,文字短少而难读,虽有人对其进行过初步释读,但错误相当严重,目前学界亦尚未从史料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关注。笔者近期从少林寺方面得到了该碑的高清拓本和相关资料,初步厘清了其文字情况,并意外发现,此碑残留内容,对于学界争议已久的武曌与《大云经》关系问题提供了重要证据线索。
一、《大唐天后御制愿文碑》残碑碑文考释
《大唐天后御制愿文碑》出土于1980年,高79厘米,宽62厘米,厚19.5厘米,立于唐高宗永淳二年(683)。目前仅见汪鹏《从少林寺〈大唐天后御制碑〉谈武则天的孝亲与尊佛》一文对碑文进行了释读,其文为:
窃以觉路,冲玄理于宝偈,义在难闻,大云而写润庆洽。先考工部尚书,荆一升荣,鹤鼎燮理。先妣忠烈太夫人,擅于寰中,响蔼丹怀,弥切濡霜践路。尊灵少申迷恳。近先慈往昔,托想禅人,此寺奉为法鼓,载惊逸响,均供而严净莲台,降弘斯福,祜奉翊□。净居而宴坐,永□行经,咸归圣果,□盖闻堵山万仞,□云列砌,石镜将□,□切茹茶,时既□仙驾敬览,招提□□,用虔诚净剥,广各一铺,凭兹胜善般若之舟同践菩。[1]
可惜的是,对照高清拓本细研,可知这段释文讹字、阙字、衍字极多,这也许是因为作者所依据的图片不够清楚造成的。但其释读的断句亦大多有误,则应是误将残碑当做整碑看待所致,这一错误可能源于嵩山有关资料对此碑的介绍:“碑身右侧下部与碑阴右侧下部损,碑阳右侧下部损两行字损缺,碑首左上部掉块残缺。”①拓本如图1(见 23页):

图1 《大唐天后御制愿文碑》拓本
认为此碑有下部“两行字损缺”,这个看法并不正确,因为此碑与保存完整的《大唐天后御制诗书碑》为同时营造,款式、纹饰均基本一致,因此其原高度亦应大体接近。《大唐天后御制诗书碑》每行26字,如图2:

图2 《大唐天后御制诗书碑》拓本
现存《大唐天后御制愿文碑》则每行最多8字,因此笔者推断,《愿文碑》早已被毁,现存者仅为原碑的上部的一部分,高度约为原碑的三分之一左右。对此亦可通过碑文所书内容得到“内证”。首先,若假定尾部仅缺1-2行字,全文显然读不通;其次,更明显的情况是,碑文有武则天追忆其“先考”武士彟,“先妣”杨氏的事迹,其文字长度依理而论,断非现存之三言两语可及。再次,碑文末尾落款仅存“永淳二”三字,而《大唐天后御制诗书碑》所书者为“永淳二年九月廿五日司门郎中太孙咨议王知敬书”,《愿文碑》原文的落款显然亦应近于此。
据此,笔者对此碑进行了重新释读:
(第一行)窃以觉路冲玄,理绝……
(第二行)于宝偈,义在难闻,故……
(第三行)大云而写润②,庆洽人□③……
(第四行)先考工部尚书,荆州……
(第五行)一,升荣鹤鼎,燮理……
(第六行)先妣忠烈太夫人……
(第七行)擅于寰中,响蔼丹……
(第八行)怀弥切,濡霜践□④……
(第九行)尊灵,少申迷恳……
(第十行)先慈往昔,托想……
(第十一行)今此寺奉为……
(第十二行)法鼓载惊,逸响均……
(第十三行)供而严净,莲台降……
(第十四行)弘斯福祐,奉翊……
(第十五行)净居而宴坐,永……
(第十六行)深经,咸归圣果……
(第十七行)盖闻山耆山万仞……
(第十八行)云列砌,石镜将……
(第十九行)情切茹荼,时既……
(第二十行)仙驾,敬览招提……
(第二十一行)□⑤用虔诚,净刹广……
(第二十二行)各一铺,凭兹胜善……
(第二十三行)般若之舟,同践菩……
(第二十四行)永淳二⑥……
第三行所言之“大云”当即是后来为武曌改元称帝(天授元年,690年)提供了“合法性”支持的《大云经》。理由如下:
其一,天授二年(691)三月,武则天发布《释教在道法上制》诏书,文谓:“朕先蒙金口之记,又承宝偈之文,历教表于当今,本愿标于曩劫。《大云》阐奥,明王国之祯符;方等发扬,显自在之丕业。”[2](P79)文中同时提到了“宝偈”与“大云”(此“大云”指《大云经》无疑义),《大唐天后御制愿文碑》的第二行与第三行也均提及“宝偈”与“大云”二词,若以碑文中之“大云”非特指此义,恐无此巧合,可证此“大云”当指《大云经》。
其二,从《大唐天后御制愿文碑》残存文字看,第十六行“深经,咸归圣果”,所谓“深经”是佛典中的常用语,多用于赞颂某种佛经意蕴深邃;第二十二行“各一铺,凭兹胜善”,所谓“一铺”,应该是绘制经变画,从现存敦煌经变画看,“‘铺’是佛画的量词,造像题记上往往写着造什么佛‘一铺’”[3],有可能此《愿文》即是武曌在少林寺供奉了几幅经变画(或包括以《大云经》为主题者在内),希图以功德回向其父母的记录。
《大唐天后御制愿文》书于永淳二年(683),此时唐高宗李治尚在世,由《大唐天后御诗文碑》中诗的首句“陪銮游柰苑”⑦可知,武曌这一次是随驾来少林。因此,这是以往未被有关学者发现的、武曌本人最早提及《大云经》的文字。
二、关于武曌与《大云经》问题
据《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长安志》等诸多史籍记载,载初元年(690)七月,也就是在武曌正式登基称帝的两个月之前,薛怀义和法明等上《大云经》,言经中有女主受命之符,为武曌称帝提供了合法性依据。若《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载:“有沙门十人伪撰《大云经》,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制颁于天下,令诸州各置大云寺,总度僧千人。”《新唐书·武皇后传》亦载其事。《旧唐书·薛怀义传》:“怀义与法明等造《大云经》,陈符命,言则天是弥勒下生,作阎浮提主。唐氏合微,故则天革命称周……其伪《大云经》颁于天下,寺各藏一本,令升高坐讲说。”此事亦载于《通鉴》卷二百四。此外,《长安志》卷十载:“武太后初,此寺沙门宣政进《大云经》,经中有女主之符,因改为大云经寺,遂令天下每州置一大云经寺。”[4](P155)
不过,因《大云经》为佛典文献中之旧有典籍,其即北凉昙无谶所译《大方等无想经》之别名。正史言其为“伪撰”,可能是因为作者不谙佛典且厌憎薛怀义辈所致,故宋僧赞宁在其《大宋僧史略》中提出:“观《新唐书》言《大云》是伪经,则非也。此经晋朝已译,旧本便云‘女王’,于时岂有天后耶?盖因重译故,有厚诬加,以挟薛怀义,在其间致招讥诮也。”[5](P248下)宋僧志磐《佛祖统纪》记:“载初元年,勅沙门法朗九人重译《大云经》,并封县公,赐紫袈裟银龟袋。”[6](P369下)二书皆以之为“重译”。宋僧祖琇在《隆兴编年通论》亦考及此事谓:“《新唐史》极恶《大云》之妄,然其后菩提流志、不空三藏、清凉国师诸公皆未有考其所以来而黜绝之,今是经犹列于藏中,迹其真妄固未易详也。”⑧[7](P177下)对其真伪表示存疑。
这一关于《大云经》真伪问题的疑案,直至20世纪初中日学者在敦煌文献中发现了《大云经疏》才得到了答案。目前已发现的敦煌本《大云经疏》,有藏于大英伦敦博物馆的编号为S.2658及S.6502的两个残卷,最早的发现者是日本学者狩野直喜,至1924年,罗福苌根据狩野直喜所录,将之收入《沙州文录补》,这一文献始为中国学界所知。最早进行研究者是王国维,为其写了一篇跋语《唐写本大云经跋》,他通览《大云经疏》后提出了基本判断,对武曌与《大云经》关系问题进行了澄清,文谓:
此卷亦狩野博士所录,前后阙。以文义观之,盖武后载初元年所作《大云经疏》也。卷中所引“经曰”及“经记曰”云云,均见后凉昙无谶所译《大方等无想经》。此经又有竺法念译本,名《大云无想经》(此本已佚,上虞罗氏藏六朝人所书一卷,系第九卷,亦阙前半),昙公译本中亦屡见“大云”字,故知此为《大云经疏》也。……后凉译本之末,固详说黑河女主之事。故赞宁《僧史略》谓此经晋代已译,旧本便曰“女王”,于时岂有天后,云云。颇以《唐书》之说为非。志磐《佛祖统纪》从之,故于武后载初元年书敕沙门法朗九人重译《大云经》,不云伪造。今观此卷所引经文,皆与凉译无甚差池,岂符命之说皆在疏中,经文但稍加缘饰,不尽伪托欤?[8](P423-424)
王国维所言“黑河女主”事,即《大云经》(《大方等无想经》)经文中所述及蒙佛授记的南天竺的一位女王,经文原文为:
善男子!汝今谛听!我当说之。以方便故,我涅槃已七百年后,是南天竺,有一小国,名曰无明。彼国有河,名曰黑闇,南岸有城,名曰熟榖,其城有王,名曰等乘。其王夫人,产育一女,名曰增长,其形端严,人所爱敬,护持禁戒,精进不惓。其王国土,以生此女故,谷米丰熟,快乐无极,人民炽盛,无有衰耗、病苦、忧恼、恐怖、祸难,成就具足一切吉事。邻比诸王,咸来归属。有为之法,无常迁代,其王未免,忽然崩亡。尔时,诸臣即奉此女,以继王嗣。女既承正,威伏天下,阎浮提中所有国土,悉来承奉,无拒违者。女王自在,摧伏邪见,……教导无量一切众生,说《大云经》以调其心。[9](P1107上)
《大云经》中关于南天竺女王的记载,《大云经疏》的作者们将之当做佛陀对武曌应登基称帝的预言。《大云经疏》中录此段经文:
大云密藏菩萨问曰:“唯愿如来,为诸众生,说是天女未来之事。”佛言:“我以方便故,示涅槃已,七百年后,是南天竺有一小国,名曰无想,彼国有河,名曰黑河,南岸有城,名曰熟榖,其城有王,名曰等乘。其王夫人,产生一女,名曰增长。……”
《大云经疏》中所录经文与昙无谶译本原文文意基本一致,仅有文字表述上的简繁出入。但其重点在于“疏”的部分利用当时流行的图谶来进行解释,把对“女王”的表述处处都引向武曌,若其诠释“黑河”谓:
经曰“彼国有河,名曰黑河”者,但生死名“河”,烦恼称“黑”,即显神皇菩萨慈悲化生,于大河中除烦恼故。又窃惟武氏羽姓,在于北方,北方色黑,羽又为水,故曰“黑河”。又黑水成姓,即表黑衣,与《孔子谶》相符,名黑河也。伏承神皇幼小时已披缁服,固惟黑衣之义也。又并州太皇陵侧,旧有一井,俗称武井。先来有水,后遂干枯。隋末已来,微似有水。自国家之后,水便满井。至于今日,其水大流,阔数丈,流入汾水。故隋日童谣云:“猷水竭,武井溢,此中当有圣人出。”即明水流之义,本应神皇,非关人姓刘也。[10](P5)
由此可见,《大云经疏》中所录之《大云经》经文本身,可以断定当非伪作。但其“疏”的部分,皆以图谶妄加附会于经文,正如王国维所说,其“附会穿凿,无所不至,怀义等所修自当如此。”[8](P424)故薛怀义等所献者即此《大云经疏》,而非《大云经》本身。“新旧《唐书》等所说伪造《大云经》当为伪造《大云经疏》之误。矢吹庆辉就曾指出:《大云经》下当补一‘疏’字”[11]。
1935年,陈寅恪先生发表《武曌与佛教》,亦对此问题详加辨析,认为《大云经疏》的经文部分,既非伪作,亦非改译,其真实情况应是:“观昙无谶译《大方等大云经》之原文,则知不独史籍如《旧唐书》等之伪造说为诬枉,即僧徒如志磐辈之重译说亦非事实,今取敦煌残本,即当时颁行天下以为受命符谶之原本,与今佛藏传本参校,几全部符合,间有一二字句差池之处。而意义亦无不同。此古来书册传写所习见者,殊不能据此以为有歧异之二译本也。又因此可知薛怀义等当时即取旧译之本,附以新疏,巧为傅会。其于昙本原文,则全部袭用,既不伪作,亦非重译。”何以如此,“盖武曌政治上特殊之地位,既不能于儒家经典中得一合理之证明,自不得不转求之于佛教经典。而此佛教经典若为新译或伪造,则必假托译主,或别撰经文,其事既不甚易作,其书更难取信于人。仍不如即取前代旧译之原本,曲为比附,较之伪造或重译者,犹为事半而功倍。”[12](P364-365)陈寅恪之分析较之王国维所说显然更合乎情理,后来学界从之者亦更多。今人林世田基于陈寅恪之论断,并详考《大云经疏》之文本,论定《大云经疏》之成书时间,其上限应在垂拱四年(688)已着手撰写,下限为载初元年(690)成书,期间经薛怀义等十人多次补充。[11]
由此可知,书于永淳二年(683)的《大唐天后御制愿文碑》中提及《大云经》的情况,早于《大云经疏》的写作起点至少五年,这个时间点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吾人至少可以据此作出以下三点论断。
1.关于新旧《唐书》等史籍认为《大云经》是伪作的问题,实于敦煌本《大云经疏》重见天日后已基本得到解决。如果仍要坚持“伪作”之说,那除非只能认定收入藏经的《大方等无想经》全文及其相关记载都是薛怀义等伪造的,这种可能性显然微乎其微。不过,宋僧祖琇在《隆兴编年通论》中倒是确实提出过这种怀疑,谓“今是经犹列于藏中,迹其真妄固未易详也。”——《大唐天后御制愿文碑》的情况显示,在唐高宗李治还在世时,武曌已然对《大云经》十分推崇,而那时候薛怀义还没有登上历史舞台,故史载《大云经》为薛怀义等伪作之说,据此可以进一步彻底否定。
2.学界于《大云经疏》所引用之经文,王国维、汤用彤等主张出于改作重译。[13]既然《大唐天后御制愿文碑》证实了武曌早已读过《大云经》并发生信仰,对其经文自然相当熟悉,薛怀义等也自然没有重译或刻意改写的必要。由此可证,陈寅恪批评王国维之说“尚有未谛”,《大云经疏》“其于昙本原文,则全部袭用,既不伪作,亦非重译”[12](P365)之推断应是正确的。
3.既然武曌推崇《大云经》之事早已书于碑文,这一情况在当时自应早已被普遍知晓,故不少学者认为《大云经疏》为“武则天授意命薛怀义等所炮制”[11]之说未必为确论。这是因为武曌平生为政得失、道德人品自然可以见仁见智,但她对佛教信仰的虔诚性是不必怀疑的,这从其家族出身的情况和平生与同时代高僧们交往的情况均可得到印证,正如任继愈先生所说:“武则天享有威凌天下的权势,同时又内心有所不足,祈求神佛保佑的软弱、怯儒的一面。政治权力并不能满足一个精神生活有欠缺的中国妇女的要求,于是,不得不到宗教中求安慰找一个安心立命的境界。身为帝王,不同于一般人可以抛开家室,出家求道。她一生追求政治权力,同时又要求得到一种精神上的满足,投靠宗教是唯一的途径。”[14](P130)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主动授意别人去炮制一本经典虽然不能说毫无可能(因为她毕竟还是个政治野心家),但恐怕还是断定《大云经疏》为薛怀义等揣摩其意图、投其所好而作更为合理一些。
武曌归心于《大云经》当始于何时,根据《大唐天后御制愿文碑》的证实,自应在永淳二年(683)之前,也就是还在她当“天后”的阶段。揆诸情理,武曌之所以重视《大云经》,肯定与经中所记黑河女王事直接相关。自麟德元年(664)始,武曌正式执掌朝政权柄,“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生杀,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资治通鉴·唐纪十七》)史称“二圣临朝”。女性摄政,舆论的阻力当然很大,于是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祥瑞”来为其营造合法性。“时因二圣临朝之故,乃有奏称祥瑞与二圣有关的,如曾有奏谓白龙见于玉山宫西南王谷,是天皇、天后之应;或者径有直谓是为了武后而出现的,如芝草生于东都太原寺含利塔下,太子以为是‘天后化含万物,训正六宫,天下被涂山之音,海内仰河洲之教’所致。祥瑞是天意对人君的表示,如今天意嘉及皇后,可见武后有人君的象征,其来有自。”[15](P270)因此,若在此阶段,有人投其所好,向武曌推荐《大云经》,应当适逢其时。
注释
① 未出版资料。
② 碑文现作“写润”,“写”字似有残损,疑当做“泻”。“泻润”,谓雨水倾泻滋润,多用于比喻帝王下施恩泽。
③ 当为“天”,《寺沙门玄奘上表记》:“泽及幽显,庆洽人天。”见《大正藏》第5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第820页中。
④ 当为“露”。刘禹锡《唐兴元节度使王公先庙碑》中有“濡露践霜,谁无永怀”语,此外,《大唐天后御制诗书碑》中又有“悲践露而愈悲”句,可证。
⑤ 此字漫漶,似“是”字。
⑥ “永淳二”,据《大唐天后御制诗书碑》落款“永淳二年九月廿五日”,当亦在此时间前后。
⑦ “柰苑”系佛教语,为佛寺的别称。《全唐诗·卷五》收录此诗作“禁苑”,误。见《武则天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71页。
⑧ 又见《卍续藏》:第二编乙,第3套,京都:藏经书院,1905-1912年,第280页中;又见《卍续藏经》第130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第559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