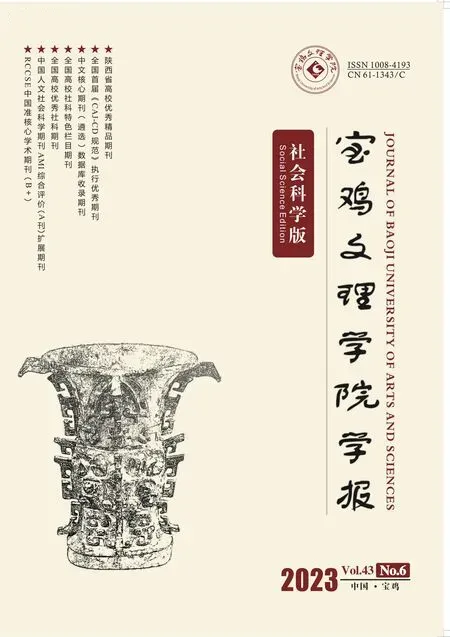《史记》人格遗韵与魏晋南北朝游侠诗*
苏悟森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1400)
司马迁首次在史书中为游侠立传,并极力歌颂他们的美德:“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戹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1](P3685)《史记·游侠列传》颠覆了历来对游侠态度的惧憎传统,挖掘出游侠在身具破坏性的同时,也拥有救人于危难的高贵品质。这种急人之困的品质,蕴含着司马迁感慨身世遭遇的隐衷,是其理想人格的映照,故而章太炎说“史公重视游侠,其所描写,皆虎虎有生气”。[2](P361)司马迁对游侠的赞美态度,以及《游侠列传》对朱家、郭解等人事迹的书写,促成游侠诗在魏晋南北朝的崛起与繁荣。魏晋之际,《史记》在士人群体中传播较广。《三国志》就记载曹丕“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3](P90)的阅读经历;曹植也在《与杨德祖书》中表明对“成一家之言”理想的向往:“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于名山,将以传之于同好。”[4](P228)南北朝时期,《史记》进一步传播,为其影响诗歌创作奠定了基础。魏晋南北朝诗人也正是通过对前朝当代各类游侠事迹的吟咏,重现了《史记》中游侠形象的人格光辉,拓展了游侠群体的思想内蕴。
一、“生从命子游,死闻侠骨香”:嫉恶如仇的复仇游侠诗
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详细描述了数位游侠嫉恶如仇的复仇事件,可见复仇往往是体现游侠重诺品质的标志与核心。受《史记》影响,魏晋南北朝诗人也多通过歌颂复仇来彰显游侠的侠义本性,从而再现了司马迁笔下游侠形象的人格光辉。司马迁描述过朱家“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的心性,也描述了郭解“少时阴贼,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的行为,即使“及解年长”,在“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的同时,也“自喜为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阴贼着于心,卒发于睚眦如故云”。[1](P3868-3870)这些复仇事件所彰显的正是游侠“为死不顾世”的美好品质,它们在魏晋南北朝的复仇游侠诗中得到了很好的继承。
少年复仇和女性复仇是魏晋南北朝复仇游侠诗中并行不悖的两大主题,而曹植正是这两大主题的开创者。其《结客篇》一诗即是对少年游侠复仇勇气的歌颂:“结客少年场,报怨洛北芒。利剑鸣手中,一击而尸僵。”[4](P798)少年本是意气风发的人生阶段,年少之人最容易做出惊世骇俗之举,司马迁在叙述郭解事迹时,即强调“少年慕其行,亦辄为报仇,不使知也”的现象,由此可知少年所独具的冲动、朝气本性。《结客篇》正是通过对少年复仇行为的吟咏,展现了游侠蓬勃凌厉的生命意气。而曹植《精微篇》则歌咏了女性游侠的复仇事迹:“关东有贤女,自字苏来卿。壮年报父仇,身没垂功名。女休逢赦书,白刃几在颈。俱上列仙籍,去死独就生。”[4](P493)诗歌叙述了苏来卿壮年复仇、身死名传以及秦女休为宗报仇、恰逢赦书的故事,展现了游侠英勇无畏、视死如归的人格魅力。女性本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女性复仇的侠义行为,往往更能激起人们心中的敬畏之情。曹诗正是通过对女性侠义行为的吟咏,强调了游侠复仇给人带来的心灵震撼。
曹诗开辟的女性复仇题材,在左延年、傅玄笔下呈现出更为丰富生动的细节。左延年《秦女休行》详细叙述了女休复仇的全过程:
始出上西门,遥望秦氏庐。秦氏有好女,自名为女休。休年十四五,为宗行报仇。左执白杨刃,右据宛鲁矛。仇家便东南,仆僵秦女休。女休西上山,上山四五里。关吏呵问女休,女休前置辞:“生为燕王妇,今为诏狱囚。平生衣参差,当今无领襦。明知杀人当死,兄言怏怏,弟言无道忧。女休坚词为宗报仇,死不疑。”杀人都市中,徼我都巷西。丞卿罗列东向坐,女休凄凄曳梏前。两徒夹我持刀,刀五尺馀。刀未下,膧胧击鼓赦书下。[5](P563)
诗人通过“左执白杨刃,右据宛鲁矛”的动作描写,活脱脱地刻画出一个英姿飒爽的女侠形象;通过“女休坚词为宗报仇,死不疑”的慷慨陈词,传达了主人公誓死报仇的决心。虽然女休“杀人都市中”的复仇行为本“不轨于正义”,但最终还是得到世俗的谅解,获得“刀未下,膧胧击鼓赦书下”的可喜结局。全诗以生动的笔墨、戏剧化的情节,展现了女休“为死不顾世”的侠义人格。西晋傅玄《秦女休行》一诗则借左延年诗题抒写庞氏妇复仇故事:“白日入都市,怨家如平常。匿剑藏白刃,一奋寻身僵。身首为之异处,伏尸列肆旁。肉与土合成泥,洒血溅飞梁。”[5](P429)诗中的描写充满血腥,它在展现庞氏妇刚烈勇猛的同时,甚至流露出作者快意恩仇心理。诗中“一市称烈义,观者收泪并慨忼”以及“县令解印绶,令我伤心不忍听。刑部垂头塞耳,令我吏举不能成”的侧面烘托,更加渲染了庞氏妇义薄云天的光辉人性。
少年复仇题材在魏晋南北朝游侠诗中也有着进一步发展。张华《博陵王宫侠曲·其二》即是对少年游侠传统的复归:
雄儿任气侠,声盖少年场。借友行报怨,杀人租市旁。吴刀鸣手中,利剑严秋霜。腰间叉素戟,手持白头镶。腾超如激电,回旋如流光。奋击当手决,交尸自纵横。宁为殇鬼雄,义不入圜墙。生从命子游,死闻侠骨香。身没心不惩,勇气加四方。[5](P612)
原本曹植《结客篇》只记录了少年“利剑鸣手中,一击而尸僵”的精彩瞬间,而张华却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多方延伸:既铺陈了少年游侠的装束,又描摹其不凡的身手,更展现出其“宁为殇鬼雄,义不入圜墙”的精神境界和“生从命子游,死闻侠骨香”的凌凌风骨。张华塑造的游侠形象,对后来的游侠诗创作影响极深,李白“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以及王维“纵死犹闻侠骨香”之句,就是脱胎于此。此外,张华《博陵王宫侠曲·其一》还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揭露出游侠杀人的现实根源:“岁暮饥寒至,慷慨顿足吟”的贫困生活导致“收秋狭路间,一击重千金”的杀人勾当,这里的游侠消褪了“身在法令外,纵逸常不禁”的不羁色彩,呈现出匍匐于生活脚下的无奈姿态。
南北朝时期,少年复仇主题在鲍照和吴均诗中也有所延续。鲍照《代结客少年场行》的诗题就表明对曹植《结客篇》的模拟,全诗不仅叙述了少年复仇故事,还展现了游侠平生行踪:
骢马金络头,锦带佩吴钩。失意杯酒间,白刃起相雠。追兵一旦至,负剑远行游。去乡三十载,复得还旧丘。升高临四关,表里望皇州。九衢平若水,双阙似云浮。扶宫罗将相,夹道列王侯。日中市朝满,车马若川流。击钟陈鼎食,方驾自相求。今我独何为,坎怀百忧?[6](P192)

游侠的复仇行为,虽展现出急人之困、一诺千金的美好品质,但毕竟对社会稳定构成了威胁。除了乱世呼唤游侠之外,升平之世的统治阶级对游侠多采取打压政策。《史记·游侠列传》就记载了“景帝闻之,使使尽诛此属”的事实,武帝也多采用充军发配的方案削弱游侠势力,历代统治者对游侠的态度大同小异。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复仇游侠诗的创作也就变得十分谨慎。相比于复仇题材,魏晋南北朝诗人更愿意置游侠于边塞,使之在杀敌报国的行为中提升自我;或置游侠于市井,使其在斗鸡走狗、谈笑风生的行为里,展露无伤大雅的任侠情怀。
二、“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尽忠还恩的报国游侠诗
司马迁在《史记》中描绘的游侠具有急人之难的美好品质,但这种品质主要局限于报仇还恩的个体自觉,也具有“以武犯禁”的社会危害。因而魏晋南北朝报国游侠诗,则通过对《史记》中将军形象的借鉴,将游侠置身于战场,使之在民族战争的洗礼中实现由报恩到报国的心理转变,从而提升了游侠形象的思想境界,也完成了对《史记》游侠人格的内涵拓展。
曹植《白马篇》较早完成了对游侠形象的改造。诗中“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的少年游侠,在“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的民族战争洗礼下,萌生出“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爱国情怀。曹诗塑造的游侠形象,不再是睚眦必报的复仇少年,而是胸怀大义的民族英雄。屈原在《国殇》中也塑造了一群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但他们是英勇无畏的战士,不是潇洒豪迈的游侠,曹诗将游侠与战士合二为一,塑造出“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的潇洒英雄形象,导引了魏晋南北朝的游侠诗走向。而这样的英雄形象同时也是对司马迁笔下游侠和将军的形象合体。
魏晋南北朝出现《白马篇》系列拟作,展现出游侠由复仇走向报国的曲折历程。南朝袁淑《效曹子建白马篇》讲述了游侠从戎的委婉心曲:“义分明于霜,信行直如弦”的性格,使得游侠“一朝许人诺,何能坐相捐”,因此“飘节去函谷,投珮出甘泉”,也正由于经历了战争的磨练,游侠逐渐蜕变成“心为四海悬”的沙场英雄。袁诗既展现了游侠的蜕变过程,又挖掘出促成蜕变的内在原因,即在于游侠一以贯之的正义本性。全诗通过对游侠正义品质的书写,揭示出游侠群体崇高的人格内蕴。鲍照《代陈思王白马篇》则反映了游侠从戎的复杂心理:主人公对“埋身守汉境,沈命对胡封”的边塞生活忿忿不平,发出“丈夫设计误,怀恨逐边戎”的悔恨之音,然而“去来今何道,卑贱生所钟”的现实命运逼迫他守土边疆,以求“但令塞上儿,知我独为雄”的心理补偿。鲍诗中的游侠儿虽也投身战场,但并无多少爱国激情,更多的是感伤自身的暗淡命运。孔稚珪《白马篇》则重现了少年游侠的沙场雄风:诗歌首先交代出“少年斗猛气,怒发为君征”的内在原因,接着又展示了游侠“雄戟摩白日,长刚断流星”的高超武艺和“左碎呼韩阵,右破休屠兵”的赫赫战绩。孔诗中少年英雄的杀敌报国,并非完全出于爱国之心,更多的还是彰显勇武之气,这从“县官知我健,四海谁不倾”的得意神情中即可窥见一斑。沈约《白马篇》中的游侠形象则呈现出知恩图报的被动心理:一方面“冰生肌里冷,风起骨中寒”的边地环境折磨得他痛苦不堪,另一方面“唯见恩义重,岂觉衣裳单”的报恩思想又迫使他勉为其难地投入战斗,最后主人公在“本持躯命答,幸遇身名完”的惊魂甫定中惨淡地收束其边塞生涯。其后,王僧孺《白马篇》书写了游侠渴望“豪气发西山,雄风擅东国”的豪迈心志,徐悱《白马篇》展现出上郡少年由“剑琢荆山玉,弹把隋珠丸”的纨绔子弟转变为“占兵出细柳,转战向楼兰。雄名盛李霍,壮气勇彭韩”的常胜将军的心路历程。
隋朝君臣也创作了《白马篇》同题之作。隋炀帝杨广塑造的游侠形象不再是怒发冲冠的武夫,而是“英名欺卫霍,智策蔑平良”的智勇双全之士;游侠从戎也不再是爱国或名利的单向驱动,而是有着“本持身许国,况复武力彰”的双重目标。辛德源和王胄塑造的游侠形象又各具特点:辛诗着力铺陈游侠“金羁络赭汗,紫缕应红尘。宝剑提三尺,雕弓韬六钧”的华丽装束,对于从戎之事只是一带而过,可见其旨在追忆边塞驰骋的潇洒意态,而非游侠从戎的报国情怀。王诗中的少年游侠虽有“良弓控繁弱,利剑挥龙泉。披林扼雕虎,仰手接飞鸢”的不凡身手,又有“前年破沙漠,昔岁取祈连。折冲摧右校,搴旗殪左贤”的过人胆气,但其报国行为只是“志勇期功立,宁惮微躯捐。不羡山河赏,谁希竹素传”的心理诉求的真实反映。
除了《白马篇》系列之外,魏晋南北朝还有很多边塞报国游侠诗,塑造出性格各异的游侠群像。王僧达《和琅琊王依古诗》讲述了少年游侠守卫边疆的报恩思想,何逊《学古诗》展现了“长安美少年”从戎报国的豪迈之气。吴均更有多首诗歌,都是对游侠报国精神的反映:《雉子班》叙述了“幽并游侠子,直心亦如箭。生死报君恩,谁能孤恩眄”的重诺品质,《城上麻》展现出“少年感恩命,奉剑事西周。但令直心尽,何用返封侯”的凌凌风骨。游侠“取予然诺”的报恩行为,前提是受到对方的尊重和理解,如此他方能“为死不顾世”,借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报国是报恩的提升,本质还是为了还报君王的知遇之恩,因此游侠报国一旦得不到君王认可,就会流露挫败之感、苦闷之情。吴均《酬别新林》就是这种苦闷心理的反映:
仆本幽并儿,抱剑事边陲。风乱青丝络,雾染黄金羁。天子既无赏,公卿竟不知。去去归去来,还倾鹦鹉杯。气为故交绝,心为新知开。但令寸心是,何须铜雀台。[5](P1735)
诗中的幽并健儿经历过风里来雾里去的边陲人生,但他们历尽苦辛却得不得天子公卿的欣赏和肯定,“但令寸心是,何须铜雀台”的宽慰之语也难掩字里行间的抑郁之情。
边塞报国的游侠形象在南朝甚至还沾染上纨绔习性。例如刘孝威《结客少年场行》:
少年本六郡,遨游遍五都。插腰铜匕首,障日锦屠苏。鸷羽装银镝,犀胶饰象弧。近发连双兔,高弯落九乌。边城多警急,节使满郊衢。居延箭箙尽,疏勒井泉枯。正蒙都护接,何上惮险途。千金募恶少,一挥擒骨都。勇馀聊蹴踘,战罢暂投壶。昔为北方将,今为南面孤。邦君行负弩,县令且前驱。[5](P1869)
诗歌开头极力铺陈少年玩世不恭的游侠气质,接着表明其远赴边城的报国决心,并通过蹴踘、投壶的细节捕捉表现游侠举重若轻的无畏心理。萧绎《紫骝马》与之相似:“长安美少年,金络铁连钱。宛转青丝鞚,照耀珊瑚鞭。依槐复依柳,躞蹀复随前。方逐幽并去,西北共联翩。”[5](P2033)诗人对少年装束着墨尤多,对从戎报国轻描淡写,即使是暗示游侠从戎的最后两句,传达的也并非紧锣密鼓的沙场氛围,而是轻松愉悦的游戏态度。
历史上统治者以充军方式削弱游侠势力的举措,以及乱世之中游侠从戎并获成功的先例,加速促成了魏晋南北朝游侠诗创作的转型。魏晋南北朝诗人通过报国游侠诗的书写,实现了对游侠形象的改造,丰富和完善了游侠群体的思想蕴含。
三、“宝剑值千金,被服丽且鲜”:任侠使气的市井游侠诗
虽然司马迁主要通过趋人之急、取予然诺的行为来塑造游侠的仗义,但他也不忘通过流连市井、游戏人间的行为来体现游侠的豪情,例如其笔下的剧孟就“好博,多少年之戏”。魏晋南北朝的市井游侠诗正是通过将游侠置身于市井,使之在斗鸡走狗的生活中展现任侠使气的个性,从而消解了游侠群体与生俱来的破坏性,并完成对《史记》游侠形象的深化与补充。
市井游侠诗的创作,在魏晋南北朝也呈现出欣欣向荣之态。曹植《名都篇》是较早展现游侠市井人生的作品: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宝剑直千金,被服丽且鲜。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驰驱未能半,双兔过我前。揽弓捷鸣镝,长驱上南山。左挽因右发,一纵两禽连。馀巧未及展,仰手接飞鸢。观者咸称善,众工归我妍。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脍鲤臇胎鰕,炮鳖炙熊蹯。鸣俦啸匹侣,列坐竟长筵。连翩击鞠壤,巧捷惟万端。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云散还城邑,清晨复来还。[4](P721)
诗中的京洛少年成日里过着斗鸡走狗、宴会豪饮的放浪生活,任凭岁月蹉跎不改其初。这里的少年形象,与其说是急人之困的游侠,还不如说是不务正业的纨绔,只不过其举手投足还遗留着一丝半缕的任侠气质,借以表明对循规蹈矩之平庸人生的突破,对纵横驰骋之英雄梦想的追寻。但这种追寻充其量不过是对游侠行为细枝末节的模仿。嗣后,阮籍在《咏怀·其五》中就追悔了这种年少无知:
平生少年时,轻薄好弦歌。西游咸阳中,赵李相经过。娱乐未终极,白日忽蹉跎。驱马复来归,反顾望三河。黄金百镒尽,资用常苦多。北临太行道,失路将如何?[7](P222)
宴乐豪饮、一掷千金的少年时期,回想起来后悔莫及,可见市井任侠生活的浮华本质。张华《轻薄题》就全面反映了“末世多轻薄,骄代好浮华”的社会风气,诗歌结尾“念此肠中悲,涕下自滂沱。但畏执法吏,礼防且切蹉”的感慨,也隐约传达出诗人对轻薄儿违礼犯法行为的担忧。至此,《史记·游侠列传》所歌咏的游侠品质已所剩无几,市井游侠诗所呈现的游侠形象,与救人之急、不吝其趋的侠义人格相去甚远,只留下挥洒使气的游侠躯壳。
南北朝的市井游侠诗创作尤为繁荣。刘苞《九日侍宴乐游苑正阳堂诗》即描绘了“六郡良家子,幽并游侠儿”立乘争饮、侧骑竞驰、奏琴吹箫的热闹场景,只有末尾“取效绩无纪,感恩心自知”两句约略涉及游侠的报恩品性。何逊《拟轻薄篇》也描写了城东少年“走狗通西望,牵牛亘南直”的游乐生活。甚至是秉持传统审美趣味的萧统,也在《将进酒》中吟咏了游侠的享乐人生:“洛阳轻薄子,长安游侠儿。宜城溢渠盌,中山浮羽卮。”[5](P1972)由此可见南朝市井游侠诗的奢靡之状。只有王筠《侠客篇》一诗流露出些许阳刚之气:“侠客趋名利,剑气坐相矜。黄金涂鞘尾,白玉饰钩膺。晨驰逸广陌,日暮返平陵。举鞭向赵李,与君方代兴。”[5](P2010)王诗中的侠客虽也装饰华丽,但并非终日沉溺于歌舞美酒,而是在策马驰骋的纵横意气里展现出疏阔人生。北朝游侠诗总体上透着与王诗相似的豪壮气息。温子昇《白鼻马呙》一诗即描绘了少年颐指气使的任侠景象:“少年多好事,揽髻向西都。相逢狭斜路,驻马诣当炉。”[5](P2220)王褒《游侠篇》也叙述了京洛豪侠“斗鸡横大道,走马出长楸”的生活图景。庾信《侠客行》一诗则融合南北,描摹出侠客豪纵享乐的市井画卷:“侠客重金镳,金鞍被桂条。细尘鄣路起,惊花乱眼飘。酒醺人半醉,汗湿马全骄。归鞍畏日晚,争路上河桥。”[8](P386)
此外,梁陈之际还兴起“刘生”系列拟作,成为市井游侠诗的集中代表。萧绎《刘生》是系列中较早的一篇:“任侠有刘生,然诺重西京。扶风好惊坐,长安恒借名。榴花聊夜饮,竹叶解朝酲。结交李都尉,遨游佳丽城。”[5](P2034)萧诗展现了刘生重诺传名、饮酒遨游的潇洒人生。其后张正见通过“金门四姓聚,绣毂五香来。尘飞玛瑙勒,酒映砗磲杯”的描写,补充说明刘生的豪贵身份。徐陵《刘生》另辟蹊径,借“任侠遍京华”的刘生故事抒写“高才被摈压,自古共怜嗟”的不平之情,而这正好从侧面说明刘生具有可贵的才情和品性。其后,江总着力表现刘生“干戈倜傥用,笔砚纵横才”的文武双全,江晖则精心刻画刘生“唯当重意气,何处有骄奢”的美好品性。甚至,陈叔宝和弘执恭还分别塑造了刘生“羞作荆卿笑,捧剑出辽东”和“纵横方未息,因兹定武功”的报国形象。当然,报国并非“刘生”主流,大多数诗作还是对其市井人生的吟咏,但这也从侧面表明“刘生”所具有的丰富包孕性。通过拟作的持续输出,“刘生”形象俨然被塑造成梁陈文人心目中的游侠理想:身世显赫、风流倜傥、重诺守信、文武双全,补充和发展了史迁塑造的游侠形象。
相比于复仇主题和报国主题而言,市井游侠诗创作在六朝蔚然大宗。毕竟复仇的血腥会招致世俗和礼法的压制,报国又需要过人的胆识和决心。因此,披着任侠使气的外衣醉生梦死的富家少年,便成为六朝诗人的首选。六朝市井游侠诗正是通过对这帮少年的不倦吟咏,传达出士人群体对不顾世俗、蓬勃凌厉个性的无限神往,对摧毁循规蹈矩之压抑人生的殷切渴望。
综上所述,司马迁在《史记》中为游侠立传,并深情赞美他们急人之困、一诺千金的高贵品质,对后代诗人产生了深远影响。自曹植创作大量游侠诗以来,复仇、报国和市井成为魏晋南北朝游侠诗的三大主题。魏晋南北朝诗人通过少年复仇和女性复仇事迹的描写,重现了《史记》中游侠形象的人格光辉;通过将游侠置身于边塞和市井,在杀敌报国和斗鸡走狗的活动中,完成对游侠破坏性的消解,为游侠群体增添了尽忠怀国、潇洒不羁的精神品质,从而拓展了《史记》游侠形象的人格内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