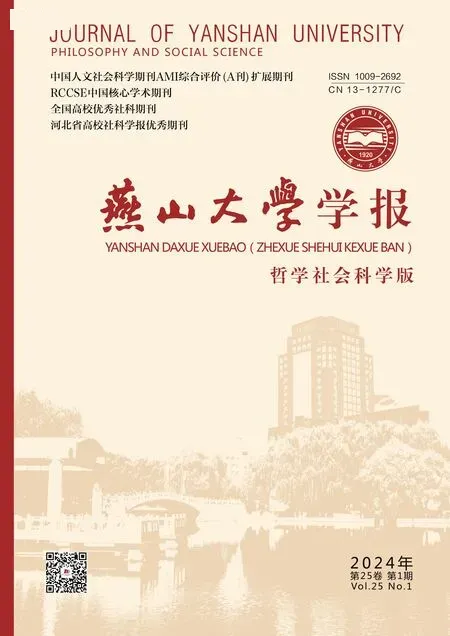解构与重构
——庞德汉诗译作在美国的经典化
姚成贺,崔 放
(1.北京师范大学 外文学院,北京 100875;2.河北环境工程学院 基础部,河北 秦皇岛 066102)
对于诗歌翻译,翻译界存在的争论最多,同时也有不少学者认为诗歌是不可译的。对于在英汉这两种不同语系间进行的诗歌翻译,难度似乎不言自明。然而庞德(Ezra Pound,1885—1972)的汉诗译作似乎超脱了语言与文化的障碍,《华夏集》(Cathay)在美国广为流传并被奉为经典。T.S.艾略特(T.S.Eliot)称:“庞德是我们时代中国诗的创造者。”[1]特威切尔(Twitchell)认为:“在庞德之前,中国没有与好的名字相称的文学流行于说英语的国家。”[2]90在庞德之前,也曾有众多学者进行过汉诗英译,其中既有外国学者,也有中国本土学者,然而从影响力看,似乎都不如庞德译作的影响力大。“很多诗集的编辑、诗人及翻译家将《华夏集》奉为英文诗经典,甚至以之为创作灵感的源泉。”[3]有学者认为翻译文学经典有三重含义:“一是翻译文学史上杰出的译作;二是翻译过来的世界文学名著;三是在译入语特定文化语境中被经典化了的翻译文学作品。”[4]很明显,庞德的汉诗译作既是杰出的译作,更是在特定文化语境中被经典化了的译作。庞德译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原作的解构与重构,在中国读者看来,这种解构与重构是对原作的一种偏离,甚至是一种歪曲。但庞德提倡翻译精神(translation of spirit),“译者能体验并传达出原作的精神,尤其是‘现代精神’,翻译不应该是语文学的,应该是阐释性的。”[5]那么,这种现象为何会促成其汉诗译作在美国的经典化?这需要对这种解构与重构背后的含义加以解读。同时,其他的因素,如赞助人(patronage),也助推了其汉诗译作的经典化。
一、解构:对自身诗学的实践
在传统翻译观中,原作与译作,原文作者与译者间普遍存在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在翻译过程中,普遍奉行“原作中心论”原则。而庞德的译诗在很大程度上挑战着这一原则。在很多中国学者看来,其汉诗译作乃是一种不忠,甚至是一种扭曲,因此庞德被冠以东方主义者的称号。然而,在西方学者看来,其译作也并没有归化为严格意义上的传统诗体。简言之,庞德的译诗“是一种对目标规范的异化,也是对原文的异化,是一种双重异化”[6],或者说是一种“双重解构”。学界普遍认为庞德的诗学可以称为“翻译诗学”,“庞德的译学与其诗学同步发展,其诗学的每一步重大发展都得益于其翻译作品的文化影响。”[7]21因此,对庞德的翻译诗学有所认知,也便对庞德的个人诗学有了一个概括性的了解。总的说来,庞德的翻译诗学主要表现在三方面:(1)抛弃维多利亚时代矫揉造作的翻译措辞,进行语言革命。(2)将历史照进现实,借助翻译实现对现实的关照。(3)通过文化互鉴,实现自身的反省与变革。
首先,20世纪初欧美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巨大变革使文艺复兴时期确立的文化体系难以为继。作为意象主义诗歌运动的领导人,庞德对维多利亚式冗长、陈腐的诗风发起挑战。他注重意象,认为“意象是在瞬间呈现出的一个理性和情感的复活体”[8],并于1913年明确提出意象主义三原则:(1)直接处理主客观事物。(2)不用无助于表现的词。(3)提倡音乐性短句的反复演奏。因此,句子的简洁明快乃是题中之意,有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甚至要牺牲传统的句子规约。基于这三项原则,庞德强调诗的散文价值,形式规整简约的汉语诗则为庞德提供了灵感源泉。在他看来,“文学艺术作品的意义会随着语言的变化而变化,语言本身具有一种活力。”[9]语言的适应与变异能力决定着对语言的解构可使一首诗获得新的意义。在早期翻译实践中,庞德将刘彻《落叶哀蝉曲》的最后一句“望彼美之女兮,感余心之未宁”译为“She the rejoice of the heart is beneath them:A wet leaf that clings to the threshold.”这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创译,符合庞德的意象主义理念。最后一句突出了“wet leaf”这一意象,似乎是一个镜头,余音袅袅,回味无穷,同时给译诗增添了超脱丧偶之痛的一丝新意。在《华夏集》的翻译实践中,庞德借助“文学实验(experimentalism)”,进行了彻底的意象主义语言革命。庞德虽不懂汉语,但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翻译反而“给他探索自由诗结构以最大的自由。结果《华夏集》的语言在他所有译文中最简朴、最不受古语影响。换言之,它的语言最当代化”[2]89。汉语诗注重意象,而多数汉语诗甚至有意象密集并置的特点,为了展现意象,庞德有时甚至直接将汉语诗中密集并置的意象平移过来,典型的一例便是李白《古风五十九首(其六)》的翻译,其中的“惊沙乱海日,飞雪迷胡天”一句,庞德直接译为“Surprised.Desert turmoil.Sea sun.Flying snow bewilders the barbarian heaven.”[10]31类似的还有《胡关绕风沙》中“Desolate castle,the sky,the desert(荒城空大漠,边邑无遗堵)”[10]16的翻译。这种翻译并不仅仅是对陈腐奢靡的维多利亚式辞藻的挑战,更是对长久以来的英语语言规约的挑战,第一句中没有任何的介词与连词,“大胆地切断了诗行与诗行或是诗节与诗节间的逻辑联系,对占主导地位的传统语言规约做了最彻底的反叛。”[11]这是对其意象理念的生动实践。这种做法“推动了中国式英语诗的发展以及美国诗句法的中国化”[12]88,在欧美社会迅速形成了一种新诗风,推动了语言朝着现代性方向的革新。
其次,在庞德看来,“翻译不具有历史性,而具有当代性,具有超越时空的特点。”[13]210在庞德眼中,翻译即是创作。“过去可以成为变革现实的活的因素,古代作品的译作从现代角度来看乃是旧作。”[7]21由此,让历史照进现实,通过现实的视角重新审视历史。“翻译的方式乃是诗歌批评的途径之一。”[14]有意识地选择翻译题材恰恰成为了将译作赋予独立意义的重要途径。不难发现,《华夏集》中的诗歌均表达战乱苦、离愁怨、别恨痛这类主题。这类主题,一来构建了一个与西方不同的东方社会的形象,二来抒发自己的情感,表达对战争的控诉。“庞德以当代的观念审视解读原作,悬置了原作的历史和语言背景,造成译作有别于原作。”[15]正如之前探讨的《落叶哀蝉曲》,最后一句的创译加强了主旨的表达。这样一种解构将单纯的怀念变为了永久的伤逝,可以演变为世间的任何一种离别之情,具有更加恢弘的题旨,成为战乱中众多生离死别的生动写照。《采薇》一诗的开头“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庞德译为“Here we are,picking the first fern-shots/And saying:When shall we get back to our country?”[10]5原诗采用了“兴”的手法,庞德在翻译时将此消解,直抒胸臆,表达对战争的厌倦、对家乡及亲人的思念。《玉阶怨》的翻译也是典型一例。庞德在翻译时将原诗的第三人称改为第一人称,拉近了与读者的情感距离,加强了“怨”的表达,同时以注解的形式描述了诗作的背景及主人公的身份,借历史之口言说现实,以异域民族的情感激起本民族的共鸣,使译作成为了具有新内涵的一种创作。另一例是《青青河畔草》中“荡子行不归,空床独难守”一句的翻译,庞德译为“Who now goes drunkenly out/And leaves her too much alone.”[10]7这样一种夸张式的翻译,超越了单纯的闺怨之情,具有更为强悍的情感震慑力,“成功地激起了人们的情感共鸣,战争给所有人带来了痛苦:不管是前线作战的男人,还是留守家庭的妇女。”[12]86利用增补的手法表达感情在译诗中也时有发生,如“代马不思越,越禽不恋燕”一句,庞德译为“The Dai horse neighs against the bleak wind of Etsu,The birds of Etsu have no love for En,in the North.”[10]31第一句的翻译为明显的增译,直接对战争场面之壮烈加以渲染,将作者内心的情感态度表露无疑。而这样一种翻译式批评,既站在西方人的审美立场上,对原诗进行符合西方口味的革命与升华,又打破了维多利亚时期翻译家们所奉行的愚忠原则,给翻译理论及实践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对此,解构主义代表人物本雅明(Benjamin)认为:“翻译不太像文学作品,更接近批评或者文学批评。”[16]由此可见,庞德的理论之中已经透出了一个新时代的曙光。
最后,对庞德来说,“中国诗意味着一种完整有序的帝国文化。庞德关心的是整个文化的范式。”[13]211如《华夏集》题目所表现的那样,“它的魅力主要在于异国情调,让人想起充满诗意的虚构国度。”[13]211在“文化大同观”的基础上,庞德主张发掘人类情感中相通的成分,以这样一种相通来发现、认识自我。早年,庞德在参观大英博物馆时接触到东方文化,并产生浓厚兴趣。馆员比宁(Binyon)的东方艺术讲座更是把庞德拉进了东方文化的殿堂。不能否认,中国画技法及哲学理念对庞德的诗歌翻译及创作产生一定程度影响。随着对中华文化了解的不断加深,庞德在其中发现了一种与西方社会黑暗腐败迥然不同的景象,认为“在中国发现了一个新希腊”[17]。因此,庞德的翻译,一方面运用异域文化,翻译文化本身;另一方面,通过翻译传递新的价值观,翻译文化之精神,推动西方社会之变革。在《送孟浩然之广陵》的英译中,庞德将“故人”直接音译为“Ko-Jin.”①[10]28对不懂汉语的外国读者来说,Ko-Jin似乎成了一个具体人名,既增添了译诗的异域情调,又拉近了与读者的心理距离。“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二句的英译“His lone sail blots the far sky./And noe I see only the river,/The long Kiang,reaching heaven.”[10]28更是对原作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解构,译诗用“blot(弄脏;使模糊)”一词巧妙地将孤帆幻化为一个墨迹,而“天”则成了留白,可以认为庞德将中国画的散点透视法运用于诗句,使作为时间的诗歌超脱空间的局限,以遐想会意为补充,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同时,“blot”作“模糊”之意讲,可认为正是由于泪水模糊了双眼,因此使人无法看清远方的天边,惜别之情溢于言表。最后一句的“天”,庞德译为“heaven”,而非“sky”,因为“heaven”在西方文化中除了“天”的含义,还指“天堂”。在乱世中构建人间天堂正是庞德毕生的理想,也是贯穿其著名作品《诗章》(Cantos)的主线,此处颇有一语双关之意。此外,通过翻译实现对西方社会每况愈下的世风的批判与反讽,也是庞德力图实现的目标。庞德将《古风·天津三月时》最后一段的“功成身不退,自古多愆尤。黄犬空叹息,绿珠成衅仇。何如鸱夷子,散发棹扁舟。”译为“For them the yellow dogs howl portents in vain,/And what are they compared to the lady Riokushu,/That was cause of hate!/Who among them is a man like Han-rei/Who departed alone with his mistress,/With her hair unbound./And he his own skiffsman.”[10]15原文用典频繁。李斯、石崇因痴迷于权力、欲望,未能功成身退,最终招致个人与家门的不幸;而范蠡却选择退隐江湖,可以说是功成名就的典范。对于典故翻译,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按照原文直译,然后加注说明;另一种是将原文的含义直接翻译,牺牲掉一些文化意象。而庞德此处的翻译介乎二者之间,既将原文的隐喻直接加以阐释,同时又保留一些意象,且未加注说明。这样做一来对于西方读者达到陌生化效果;二来直接阐明态度,对西方社会长久以来的重商主义、竞争社会等传统价值观加以批判,“That was cause of hate”实则表明庞德思想中揭示的道德腐化之根源。总而言之,“《华夏集》的用语有很多可以称为‘文明’的微妙之处,这与其说是民族或个体的忠诚行为,不如说是一个井然有序的帝国的社会价值观。”[13]211
“庞德的翻译激励并加强了他的诗歌创作,而诗歌创作又反过来引导促进了他的翻译。庞德的诗学基本上是翻译诗学,他为20世纪诗歌翻译的本质和理想重新下了定义。”[13]204庞德的翻译诗学借用翻译对汉语诗歌赋予新生,既对原作形成一种批评,又给欧美社会传统诗风带来挑战。同时产生的效应并不仅仅局限在翻译与语言层面,通过这样一种翻译诗学,庞德思考着时代及社会的提问,以另一种文化对其加以解答,推动了文化间的交流互鉴。庞德通过对原诗的解构,按照自身的翻译诗学进行文学实验,即一种“写作式翻译”,而这样一种文学实验无论是从行为本身还是从内容上都与社会的大潮同向而行,甚至助推了社会大潮的滚滚前行,既是一种顺从,更是一种服务,因此成为其汉诗译作经典化的因素。在其背后需加以探讨的,是隐藏在个人诗学背后的另一大因素——社会诗学。
二、重构:对社会诗学的顺应
所谓重构,是指庞德按照社会诗学的要求,建构起一种符合其要求的翻译体系,在这一体系里,既有翻译策略上的建构,又有翻译内容上的建构。庞德所处的时代,社会诗学主要包括三大方面:一是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将历史照进现实,从历史中寻求现实的答案;二是不同文明的交汇与融合,主要是东西方文明间的冲突与共存;三是对欧美社会自身的反省与变革。这三大方面分别体现在译诗题材的选择,汉诗英译时如何调和不同的文化要素,以及对传统诗学发起挑战。其中第三方面最为重要,因为庞德的个人诗学恰恰建基于社会诗学,也就是说,其个人诗学与社会诗学相结合。这种结合或许可以称之为一种顺应,而这种顺应恰恰体现在庞德的重构活动之中。
就第一方面的内容来看,庞德提倡“以现代的角度反映历史真实,以现代的眼光看过去,把尘封的历史当作活生生的现实来认识”[7]21。这一点类似于新历史主义倡导的“历史的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有学者认为:“庞德的诗学与新历史主义批评展现出了高度的亲缘同类性,具有相同的文化诗学观。”[18]庞德翻译《华夏集》时,欧美社会日益腐朽,一战的枪声已经打响。因此,建构一个与西方截然不同的理想社会,帮助西方发现自我,同时反对战争,这样的主题成为了社会的主流诗学,在这样一种大的社会背景影响下,庞德译诗自然选择了那些描绘离愁别恨、战争祸乱的诗篇。《华夏集》中的19首诗无一例外,都属于此类题材。庞德的友人布尔泽斯卡(Brzeska)在给庞德的回信中称“这些极妙地刻画了我们现在的状况”[19]。第一首诗《采薇》直接描绘了周宣王出征的史实,这一史实为庞德反战思想的表达提供了素材。其中的“戎车既驾,四牧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驾彼四牧,四牧骙骙”,庞德译为“Horses,his horses even,are tired.They were strong.We have no rest,three battles a month.By heaven,his horses are tired.”[10]6原文的“既驾(tied栓)”改为“tired (劳累)”,“一月三捷”变为“一月三次战斗”,又添加了“By heaven”(天啊),直抒胸臆,反战之情溢于言表。另一首经典译作《长干行》,庞德在翻译时将标题改为TheRiverMerchant’sWife:ALetter(河商之妻的一封信),通过一种书信的形式将情感视角加以重构,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在具体翻译上,“坐愁红颜老,感此伤妾心”一句庞德直接译为“They hurt me,I grow older.”[10]12如此一来,庞德似与作者融为一体,直接诉说出其内心的情感。在对该诗最后一部分的翻译中,这种“译者现身”特征十分明显,将原诗那种隐约的闺怨之情变为了对战争的直接控诉,情感表达直指人心,不失为原作的一种“新生”。此外,庞德把《送友人》最后一句的“萧萧班马鸣”重构为“Our horses neigh to each other/as we are departing.”[10]29将友人间的互道珍重变为了马儿间的嘶鸣,在人与物间构建了一种隐喻,突出别恨痛。对庞德而言,翻译意味着“把原文重置于当今的审美情感之中,即通过译者把原文置入后来的某一历史时代,从而以看似谬误的方式达到对原文的历史理解”[13]217。
就第二方面的内容来看,庞德提出了“文化大同观”,提倡构建一种“世界性文化”,“一个抛开时代、国界的普遍标准——一种世界文学标准”。[20]庞德所处的时代既是欧美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也是人类文明交融的新时代。西方迫切地需要了解东方,既是殖民活动的需要,也是挽救其自身社会危机的呼唤,渴望于另一个世界中“发现另一个自我”。而东方在种种侵略与殖民危机之下开始向西方求索。此时的战争与冲突将文明间的交流推向了高潮。庞德的诗歌译作无疑充当了这种文明交流的媒介。其诗歌译作重构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东西方文化与价值观的交汇融通。“庞德的译文维持了原诗的古雅风格和异国情调,这主要是通过保留原诗中的意象成分和中国地名获得的。”[21]比如,将“直至长风沙”直接译为“As far as Cho-fu-sa.”[10]12糅合进西方因素的典型一例便是对《长干行》中“十五始展眉,愿同尘与灰”一句的翻译,庞德将其译为“At fifteen I stopped scowling,I desired my dust to be mingled with yours.”[10]11其中dust一词的翻译超脱了原诗中的“尘”的含义,更多地与《圣经》文化相连。《圣经》中有表达类似含义的名句“For dust thou art,and unto dust shalt you return”(来自于尘,终归于尘)。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一用法拉近了西方读者与译诗间的距离,使他们产生了艺术共鸣。既具备了西方的审美特质和文化内涵,又没有牺牲原文的意象。”[22]类似的用法还有“绕床弄青梅”中“青梅”一词的翻译,庞德将其译为“blue plums”,用“blue”代替“青”,在西方文化中,“blue”含有忧郁之意,用这一词汇将全诗“怨”的主题表达出来,暗含着全诗的情感基调。另外,庞德将李白的《江上吟》与《侍从宜春苑奉诏赋龙池柳色初青听新莺百啭歌》两首诗进行重构,合二为一,变为一首《江上吟》②。原来的《江上吟》一诗表达对功名利禄的鄙夷,另一首则表达对权贵的奉承,主题与感情色彩截然相反。庞德巧妙地对第二首诗的标题进行重构,变为“And I have moped in the Emperor’s garden,awaiting an order-to-write!/I looked at the dragon pond,with its willow-colored water/Just reflecting the sky’s tinge,/And heard the five-score nightingales aimlessly singing.”[10]9实现视角的转换,将奉承之举变为一种无奈,一种对过去的回忆。如此一来,两首诗尽管基调全然不同,却紧密衔接,似浑然天成,在一首诗内形成鲜明的对比,加强了主题的表达和对西方社会深刻的道德批判。总而言之,“《华夏集》通过陌生与熟悉的辩证互动要求西方读者通过移情重新构建中国诗的社会和道德情况。”[13]211
就第三方面内容而言,也是需要明确的,就是前两方面的内容既是社会自身运动与发展之要求,也是社会自身变革的必然结果。而庞德自身的诗学是建基于社会这个大的诗学之上,社会诗学为其自身的诗学理念提供了建构基础,同时其自身诗学又需服务于社会诗学,为其注入活力,推动其不断发展。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庞德的个人诗学观与社会诗学观存在着众多的交叉之处:庞德的意象主义诗歌运动之理念与要求文学变革的呼声和理念不谋而合;文化大同观与文明间的借鉴与交流不期而遇;重新定义历史与现实间的关系,用历史来观照现实。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探讨的庞德翻译诗学的三个层面与社会诗学的三方面间并非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而是互相渗透、互相包含,存在诸多交叉点。我们可以按照语言观、历史观、社会观三方面,对二者加以比照,具体如表1所示。在文人、学者看来,庞德所处的时代,欧美社会处于一种大变革与大调整的时期,民众之中存在着一种物质与精神间的巨大落差。这种落差迫切要求文化上的变革,文化上的推陈出新成为了一种大势、一种新的社会诗学,而庞德恰好经受了这种新诗学的洗礼,这种新诗学为庞德提供了灵感之源,庞德则在这样一种宏观背景之下,建构着个人的诗学理念。而个人诗学理念之价值恰恰因服务于意象主义诗歌运动而存在,这一运动则推动了欧美文学界的变革,使其风气焕然一新。纵观庞德的汉诗译作,莫不体现着一种个人诗学与社会诗学的融合。一首首的汉语诗以意象主义的视角呈现,而背后的主题与诗性之思莫不与时代紧密相关,可以说庞德将个人与社会重构于一首首获得新生的汉诗译作之中。庞德之所以伟大,其译作之所以经典,就在其译作并非是个人牢骚满腹的发泄抑或是自说自话,庞德译诗始终将自身置身于宏观的社会视野之中,因此能够获得一种更为恢弘的气度与更为强大的气场,其译作方可包罗万象、历久弥新。庞德始终在以个人的翻译诗学抒写着社会之思,回答着时代的发问,承载着历史的记忆。

表1 庞德个人诗学与社会诗学之比照
如果放到翻译领域,社会诗学亦可以理解为一定意义上的接受者因素。格尔兹(Geertz)认为:“一群人的文化乃是文本的总和。”[23]因此,读者的期待视野既是社会诗学的构成,也推动着其变革。而翻译活动恰恰是建基于特定的读者群之上,庞德的重构乃是受接受者因素作用之必然,也必定要符合读者的期待视野。庞德的行为虽然并不能界定为严格意义上的翻译,但正是因为引入了读者期待的重构之目标,其挑战传统诗学的解构之策略才具有了发生的意义。由此观之,解构与重构并非两种泾渭分明的行为。所谓的解构正是为了重构之目的而存在,一切的解构行为也就是一定意义上的重构活动。正如个人诗学与社会诗学之调和那样,庞德将社会诗学融入了个人诗学之中,在个人诗学之中体现了对社会诗学的关照。
三、经典化的途径与助推因素
勒弗菲尔(André Lefevere)[24]在操纵论(Manipulation Theory)中,提出了操纵翻译活动的三要素:意识形态(ideology)、诗学(poetics)、赞助人(patronage)。任何一种翻译活动都难以摆脱这三要素的干预,同时这三要素对于翻译活动的顺利开展也具有重要影响。在庞德的译诗活动中,除了意识形态的体现,以及自身诗学与社会诗学相结合并付诸实践外,赞助人因素在其汉诗译作的经典化道路上也起到重要作用。此处,赞助人因素主要包括:费诺罗萨及其妻子、出版商及一些重要刊物的发行、文学界对庞德的推崇、学术界对庞德作品的评价与研究、一些作品的收录等。
庞德开始其汉诗英译活动的一个最重要的赞助人便是已故东方学家费诺罗萨(Earnest Fenollose)的妻子。费诺罗萨由于疾病突然离世,留下数百首汉语诗歌作品尚待翻译完成。在他的妻子看来,完成这项任务需要一位既具有诗学素养又对东方文化感兴趣,同时具有最新的文学理念的人。庞德便成了完成这一任务的不二人选。在不通汉语的情况下,庞德利用词典开始了他的翻译工作。在庞德看来,这些汉语诗歌恰恰为其文学实验提供了最新的理念以及创作的灵感。因此得到费诺罗萨的遗稿可以说是庞德翻译生涯,乃至整个意象主义诗歌运动的一个重大转折。
出版商及一些重要刊物的发行成为庞德译诗经典化的主要途径。庞德在欧洲漂泊期间结识了《英语评论》(TheEnglishReview)的主编F.M.福特(F.M.Ford)。《英语评论》为当时最具权威的文学评论刊物,而主编福特先生亦为现代派运动的领导人物,他认同庞德的诗学理念,认为应对维多利亚式旧体诗风加以革新,使文学服从服务于大众。此后,福特先生便在其主编的刊物上刊登庞德的诗作,这对于推广庞德的诗学理念及其诗歌作品,提升其文学影响力的作用自然不言而喻。另一位重要人物是《黄面志》(TheYellowBook)期刊的编辑埃尔马修斯(Elkin Mathews),此人为英国著名的出版商和书商。他对庞德向传统诗学发起挑战的行为大加赞赏,并帮助庞德发表了一系列诗作。得知《华夏集》完成时,他决定出版此书。凭借其在出版界的影响力,《华夏集》一书迅速发行开来。在美国,H.门罗(H.Monroe)创办了《诗刊》(Poetry),该刊物成为美国文学现代化运动的阵地。庞德则成为该刊物的海外代表。利用这一刊物及其海外代表的身份,庞德既将自己的诗作发表于其上,又将与之具有相似理念的友人的诗作加以刊登。发表在《诗刊》上的很多经典作品都经过庞德修改而成。《自我主义者》(TheEgoist)在促进英美现代主义诗歌刊物成长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庞德应主编马斯登(D.Marsden)的要求担任该刊物的编辑一职,通过这一职务庞德刊登自己及他人的现代主义作品,成为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另一阵地。
文学界对庞德的推崇对经典化功不可没。在英国期间,庞德加入了由休姆(T.E.Hulme)、斯托勒(E.A.Storer)等人创办的“诗人俱乐部”,与成员一道,共同谋划发起诗坛革命。加入这一组织既提升了庞德的诗学视野,又增强其在文学界的影响力,为其后来诗歌译作的出版与发表铺平了道路。“利用自己的声望和朋友关系推荐青年诗人作品发表或出版,并亲自撰文评介新人作品,提升和扩大他们的影响是庞德促进英美现代主义诗歌发展的重要方面。”[25]其中最著名的一例是帮助T.S.艾略特修改《荒原》(TheWasteLand)一诗,而修改后的诗作一经发表,便成为经典,被奉为现代派诗歌的开山之作。经庞德帮助和提携的诗人不胜枚举,著名的有W.C.威廉斯(W.C.Williams),W.B.叶芝(W.B.Yeats),R.弗罗斯特(R.Frost)以及E.M.海明威(E.M.Hemingway)。这些人无形中构成了一个赞助人集团,他们既得到了庞德的帮助,又对庞德的诗歌作品及译作大加赞赏,大大提升了庞德在文学界的地位及影响力。海明威在获得诺贝尔奖时甚至认为将奖项授予庞德更为合适。他们将庞德当做文学现代化运动的核心与领导者,呼唤庞德身体力行,为文学革新运动带来更多经典的富有启发意义的作品。这激励着庞德进行更深入的探索,汉诗英译恰恰成为了探索的工具,探索的产物顺应了变革的潮流,因此其经典化乃大势所趋。
学术界对庞德作品的评价与研究助推了经典化。《华夏集》一经出版便引发了一系列关于翻译、诗歌以及美学的讨论。“几乎所有的现代主义者都称赞它的清新、优美与简约。”[26]在美国,休·肯纳(Hugh Kenner)于1951年出版了《埃兹拉·庞德的诗歌》(ThePoetryofEzraPound),开庞德研究之先河,并引起学界广泛关注。二十年后出版的《庞德时代》(ThePoundEra)则产生了新的轰动。J.H.爱德华兹(J.H.Edwards)于1953年出版了《埃兹拉·庞德作品初步核对表》(APreliminaryChecklistoftheWritingsofEzraPound),并称“这是一种将庞德作品经典化的尝试”[27]。到50年代中期,庞德已成为学界热衷研究的对象。60年代,G.S.弗雷泽(G.S.Fraser)出版了《埃兹拉·庞德》(EzraPound)一书,在书中对庞德诗歌译作以高度评价:“他的作品从头到尾都有无可挑剔的悦耳效果,他是重要的创新者,诗歌技术的大师,天才般的探索者。”[28]在英国,唐纳德·戴维(Donald David)于1965年出版了《埃兹拉·庞德:作为雕刻家的诗人》(EzraPound:PoetasDculptor),在英国掀起庞德研究的热潮。如今的庞德研究已遍及世界,各种讨论及学术会议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庞德诗歌译作朝经典化方向迈进。
一些主要译作的收录最终确定了其经典化地位。《华夏集》中的一些作品被收录到美国的一些重要诗选中,反复吟诵,不断流传。如《长干行》于1954年被奥斯卡·威廉斯(OscarWilliams)收录到《袖珍本现代诗》(APocketBookofModernVerse)中,另一本书《主要美国诗人》(MajorAmericanPoets)中亦收录了此诗。1976年出版的《理解诗歌》(UnderstandingPoetry)一书中再次将该诗收录,此后,该诗又先后被《美国诗歌五十年》(FiftyYearsofAmericanPoetry)、《美国名诗101首》(101GreatAmericanPoems)、《诺顿美国诗选》(NortonAmericanPoetry)等文集收录。这一系列的收录及再版活动无不确定了庞德汉诗译作的经典化地位。
由此观之,庞德在文学界的一系列活动,如投身文学革命,宣扬诗学理念,帮助扶持诗界新人,参与文学刊物的创建与发展,成为其译诗活动隐性的赞助人;出版界及文学界对其诗歌译作的肯定与赞扬,学术界对其译作的研究与积极评价,以及国家层面不断的收录与再版行为,则成为了显性的赞助人。然而更需清楚的是,正是由于将个人诗学与社会诗学相结合,庞德的汉诗译作才具有了经典化的本质内核,因经典而经典,赞助人因素只是因其具备了成为经典的条件,才能够成为一种助推的力量。
四、结语
纵观庞德汉诗翻译活动及其译作在美国的经典化,可以清楚地发现,个人诗学与社会诗学相结合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庞德汉诗译作的经典化。通过对原作的解构,庞德将个人诗学付诸于实践活动中,推动了意象主义诗歌运动的发展及对时代与社会的反思;通过重构,庞德的翻译活动努力与社会诗学相协调,同时使自身的诗学服从服务于社会诗学的发展。除了这两大主要的推力,赞助人等一些具有操纵性质的因素也助推了其译作的经典化。需要明确的是,所谓经典化,其实是一种被动的建构过程,是要经过种种时空的考验,才能够被定义为经典。个人诗学与社会诗学相结合,使庞德的汉诗译作具备了成为经典的内核,能够经受住时间的检验,历久弥新。赞助人因素一方面建基于此,另一方面也助推了其译作的经典化。其实,庞德汉诗译作更是一种翻译文学,因其译作“在译入语文化中具有长久的文学审美价值和普遍的社会价值,同时其译作语言达到了文学语言的审美标准,给今后的文学翻译活动带来借鉴意义”[29]。其汉诗译作的经典化过程对我们的译入及译出活动也会带来一定的思考与启发。
注释:
①此处的音译不太可能是由于庞德不懂汉语造成,因为费氏在其译本注中已标明“old acquaintance”。对这种译法的详细分析可参见:T.S.Eliot (eds.)LiteraryEssaysofEzraPound.New York:New Directions,1968.
②长久以来,学界认为这是庞德犯的一个“愚蠢错误”,因为庞德误把第二首诗的标题当做内容,从而将两首诗合二为一。有关这一问题的详细探讨参见:Wai-lim Yip.EzraPound’sCatha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9,pp.148-158.
-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其它文章
- 论秦国墨者的逻辑学贡献
- 数字普惠金融对黄河流域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 TTDI框架下国际旅游竞争力优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