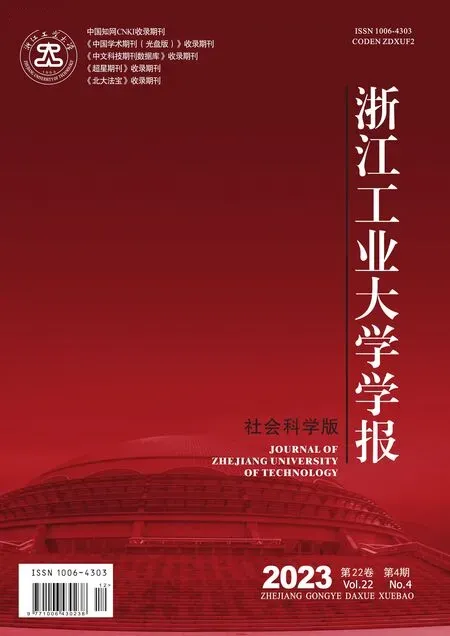清末民国杭州城市聚落变迁
——以《浙江省城图》《杭州市街及西湖附近图》为中心的考察
项文惠
(浙江工业大学 之江学院,浙江 绍兴 312030)
对杭州历史地图的利用表现在整理且出版地图集[1-3]。研究则集中在三个层面:地图历史,阙维民将杭州历史地图分为杭城古图和杭州旧图两部分,对其存佚、种类、绘制进行研究[4];钟翀考察了《浙江省城全图》的形成背景、变化脉络、消失原因[5]。地图复原,日本梅原郁提出用近代实测地图可以复原城市空间形态要素[6];陈吉以《杭州市第一都图》(1931—1934 年)为底图,分类、统计、复原《浙江省垣城厢图》中清光绪初年的城市空间形态要素[7];地图利用,李建以杭州旧城为例,对从古代地图中提取的空间要素进行量化分析和叠合研究[8];龚缨晏通过中世纪的“世界舆地图”,介绍了杭州的地理位置[9]。
聚落(聚居地)作为人类聚居和生活的场所,分城市聚落、乡村聚落,它的发展得益于人口、建筑的集聚,同时又制约着街巷修筑、设施建设、土地利用等,尤其是对城市规模、扩展方向的影响至关重要。但到目前为止,对近代以来杭州城市聚落变迁的研究并不多见,原因之一是既往的讨论几乎依赖于文字资料,很难截取聚落记录的时间断面,但在大数据时代,通过区别于传统舆图、以实测技术为基础的城市地图,在复原不同时段聚落的基础上,可以获取杭州城市空间变迁的信息。论文拟采用清末民国两个时段的城市地图,考察近代以来杭州城市聚落的数量及其分布演变的特征。
一、数据处理
(一)时空讨论
1.在时间上。杭州城市地图并非稀缺罕见,最早可追溯到《开元沙州都督府图经》《乾元西州图经》(残卷),以及《祥符杭州图经》等,但因均余“志”而无“图”,一般仍以南宋潜说友所簒《咸淳临安志》较详尽和具有代表性,其卷一、卷一二附图13 幅,包括《府治图》《京城图》(2 幅)、《浙江图》《皇城图》《九县山川总图》《西湖图》(2 幅)及余杭、盐官、富阳、新城、临安、於潜、昌化七县《县境图》,迄今,仅公开出版的即有百种之多,但干净、平整、清晰只是采用最基本的条件,若从数字化的角度来看,能进行处理的并不多,选取了其中的两种,分别是《浙江省城图》[10]《杭州市街及西湖附近图》[11]。前图是杭州最早直接采用西方近代测绘技术绘制的城市地图,方位上北下南,无比例尺,城门、运河、荡、车站、铁道、山、河、街道、桥、水门、闸11种图例(图面自称凡例),右有《杭州省城图说》,1 000 余字,叙说城形、面积、“城中水道”、上下两张宣纸拼接,97×58 厘米,浙江图书馆藏,在清光绪十八年(1892 年)诞生后,多年垄断杭州地图市场,直到民国三年(1914 年)实测地形图推广后才被取代,展示内容虽有一定增减,如清宣统二年(1910 年)再版时,增加了铁路和火车站,但仍以清末杭州城市空间格局和形态特征为主体。后图绘制于民国十七年至十九年(1928—1930年),原有艮山门、庆春门、清泰门、武林门、新市场、吴山、凤山门、松木场、岳坟、三潭印月、净慈寺、闸口、海潮寺、江干、湖墅15 幅,现仅存前12幅,方位上北下南,比例尺1∶5 000,200 多种图例,涉及明确记载的地理信息2 491 个,彩印,46×36 厘米,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藏,后编著为《90 年前的杭州——民国〈杭州市街及西湖附近图〉初读》,2020 年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是杭州历史上最为详尽、最为实用的城市地图。在表面上,仅采用这两种城市地图,时间跨度有些漫长,但这恰恰是杭州城市空间变迁较明显的时期,而两种城市地图作为清末、民国杭州城市地图的典型代表,蕴藏着丰富的地理信息,对于复原杭州城市聚落具有重要意义。
2.在空间上。作为塑造杭州城市空间形态特征的两大关键因素,城墙、河道是“不变”的代表性景观,前者促成了格局、规模、城形等外部形态,后者影响着街巷走向、街区布局、桥梁构筑等内部形态。故应充分考虑杭州城市所具有的这一特殊性,在分析杭州城市聚落变迁时,把空间范围确定在城墙之内,以别于城墙之外的乡村聚落,且以《浙江省城图》勾勒的城墙为重要参考系。另外,有河道就有桥梁,在杭州尚未开始拆城筑路之时,河道走向及其众多桥梁依旧,遂以119 座桥梁和十大城门为基本控制点(图1)。同时,以上述现存12 幅图为蓝本,拼接为整幅的《杭州市街及西湖附近图》,为下述杭州城市聚落空间分析的底图。
(二)数据处理
采用WGS1984坐标系,基于ArcGIS软件中的ArcMap 工具,在图1、拼接图上定位打点聚落要素,因城市化带来的沧海桑田,一些聚落要素已发生很大演变,采用WGS1984这类现代地理坐标系定位打点,与当时的实际情形存在一定偏差,但也因采用了相同的坐标系,从而确保聚落要素在两个时段之位置的相对一致性。换言之,就是确保了打点在图1 上的聚落要素,在拼接图上位置的精确度,为下一步空间分析提供了可靠依据。
(三)研究方法
1.核密度(Kernel density)分析法。亦名Parzen 窗(Parzen window)。其原理为通过计算一定窗口范围内的离散点密度,且将其作为该窗口中心值,从而得出研究对象空间分布的密度变化图层,显示核心集聚区及其相应的影响范围,核密度值越高,说明要素分布越密集;反之亦然,采用该方法可以较直观地看到杭州城市聚落在空间上的分布和集聚趋势。
2.标准差椭圆(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分析法。这是一种能够精确揭示点数据空间分布特征的常用统计方法。其原理为通过以中心、方位角、长轴、短轴为基本参数的空间分布椭圆来定量描述研究对象的空间分布特征。椭圆空间分布范围表示空间分布的主体区域,其中,中心表示地理要素在二维空间分布上的相对位置;方位角反映其分布的主趋势方向;长轴表示地理要素在主趋势方向上的离散程度,代表了最大的分布方向;短轴代表了最小的分布方向。如果长、短轴的比值越大,表示方向性越明显;反之,表示方向性越模糊。此方法主要用于分析杭州城市聚落分布的方向和范围。
二、聚落变迁
如上所述,聚落只有在人口、建筑的集聚达到一定规模时,才会发生街巷修筑、设施建设、土地利用等,进而为建成区。但对杭州城市聚落而言,以盐桥河(今中河)、菜市河(今东河)、外沙河(今贴沙河)“三河并立”水网体系为核心而形成的街巷,不论其始筑、名称还是长宽、走向等,均是聚落整体布局的主要构成要素,也就是说,这些街巷既是人口、建筑最集聚的空间,更是经济、社会活动的集中指示器,它们在数量、布局上所发生的演变,是聚落及其空间变迁的主要表现,将折射出杭州城市化的进程。
因此,以街、巷、弄、里等所谓“道路”为统计单位,且对此类线状要素,只取其“名”而略其“形”,基于ArcGIS 软件中的ArcMap10.3,分别在图1、拼接图上定位打点,予以标注,再经统计,得出图上有街巷274 处,拼接图上有街巷499 处,相对图1,几近一倍。由此可以推断,在民国以来道路修筑持续进行的背景下,随着街巷的不断增加,杭州城市聚落的数量或规模得到了同步增加或扩大。
(一)聚落分布的核密度分析
为直观地展示杭州城市聚落在空间上的分布和集聚趋势,分别对两种城市地图上的聚落要素进行核密度分析。同时,为了方便对聚落分布演变特征的把握,特将图1 上的聚落要素转移至拼接图上,由此形成两幅不同时段的核密度分析图(图2,3)。从两幅不同时段的核密度分析图来看,在图2 上,杭州城市聚落主要集中在城西,形成一个高密度核心集聚区,且呈犄角态势向东延伸,与东北、东南方向的次密度核心集聚区接壤,从而形成高密度核心集聚片区,相当于以御街(今中山路)为轴线且向东、向西扩展的区域,“城市内主要街道上大部分是商店和货栈,其中许多规模之大不下于伦敦同类栈房。

图2 《浙江省城图》聚落核密度分析
纺织的商店最多,也有不少毛皮和英国布匹商店”,尤其是集中在清湖河(今浣纱路)一带[12],符合杭州居民沿河、依街聚居、生活的实际;在图4上,聚落已经遍布杭州全城,形成五个高密度核心集聚区,尤以城西偏北片区、城东带状片区最为突出,相当于新市场、火车站一带。
相对于图2,在图3 上,杭州城市聚落分布的高密度集聚区更多,核密度值更高,说明在空间布局上,聚落已由单核为主体的集聚片区向多核心、多片区、高数值的方向演变。相应的,其核密度分析的影响范围明显扩大,说明在聚落分布高密度集聚的同时,其分布范围也更加广阔,几乎遍及整个城市,且越来越接近城墙,成为杭州城市空间扩展、基本格局演进的表现和预示。

图3 杭州市街及西湖附近图
(二)聚落分布的标准差椭圆分析
为了对杭州城市聚落分布进行标准差椭圆分析,以黄、蓝两种颜色,分别表示两个时段的聚落,由此形成一幅标准差椭圆分析图(图4),用来显示聚落分布的方向和范围。

图4 聚落标准差椭圆分析
从标准差椭圆的长轴分布方向看,两个时段的聚落分布均呈“南—北”方向,其空间布局与杭州南北修长、东西狭窄的“腰鼓城”城形基本符合。椭圆空间分布范围表示空间分布的主体区域,相对于清末,民国时期聚落椭圆范围更广,相应的,其主体区域随之扩大。进一步的,聚落分布中心稍有演变,即朝西南方向略有偏移,但与清末的分布中心仍然保持一致。由此可以推断,历经数十年,无论在数量还是范围上,聚落均发生了演变,但分布的方向、中心几乎不变。
综上,从清末至民国,杭州城市聚落变迁的特征为:第一,就数量看,大量增加,几近一倍,规模随之扩大,从单核向多核、成片发展,直至覆盖整个城市。第二,从布局看,南北方向、御街中心的特点基本不变,但朝西南方向略有偏移,说明会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发生演变,却难以摆脱对自然环境、历史基础的依赖,而表现为兼具顽强的依赖性和一定的适应性。
三、原因分析
从上述对杭州城市聚落变迁的复原及其分析看,其意义不仅在于近代化进程中聚落数量的增加或规模的扩大,更重要的是,短短数十年,在空间布局发生演变的基础上,促进了城市化的进程,而产生这一聚落空间布局变迁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一)拆城筑路
吴越国三次筑城,奠定杭州“腰鼓城”及其“城东—湖西”的基本格局,且千余年不变。即使元至正十九年(1359 年)张士诚东扩、北缩城市空间,杭州城市聚落依然集中在以御街为轴线的东、西两侧。清顺治七年(1650 年)在西北隅建“旗营”,“环九里有余,穿城径二里”,共计一千四百余亩,相当于城内面积的十分之一[13],但系军事特殊用地,除官署、寺庙、营房等建筑,余皆农田、植被、荒地,对聚落分布的格局并无影响。
刺激杭州城市聚落变迁的动力,首推改旧旗营为新市场的“拆城”。这一进程始于清末浙江省谘议局第一届常年会议“拟就旗营空地兴辟市场”的议决,旨在振兴商务、名胜西湖[14],实施则在辛亥革命后。随着旗营城墙的拆除及其筑路27 条,“杭州新市场的街道宽得很”“都种了树”,“干净得很”“平坦得很”“行路的人闻不到臭气”。新市场内大量的空地、便利的交通,产生了吸引力,使之转化为商、住合一的大型城市公共空间时,若以平海路为界线,大致呈“南商业、北居住”的格局,商业主要分布在延龄路(今延安路)与迎紫路(今解放路)构成的十字轴上,至少在几百家以上;居住分石库门、墅园两类,石库门在长生路、蕲王路、学士路、孝女路、菩提寺路,其中,湖边邨、大庆里业已完工,劝业里、思鑫坊、星远里、天德坊、九星里、萱寿里、承德里等已经或即将开工,墅园分散其间,尤其是集中在圣塘路(今圣塘景区)濒西湖一带。
除了拆城的原因外,筑路尤其是铁路穿城而过,带动了沿线多种城市要素的汇集,使之由城乡交错景观转变为城市景观,对杭州城市聚落变迁影响深刻。这其中又以城东一带为最。从艮山门经庆春门至清泰门的城东,分布着大大小小“七十二荡”,地旷人稀,清幽宁静,菜圃桑畦、竹篱茅舍间夹杂着大量寺院,颇有一番“小天竺”的景致。随着江墅、沪杭、杭甬、杭江等铁路的先后开通运行,除了成为城市交通轴线外,火车站作为客运、货运的节点,带来了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聚集,迅速成长为城市建成区。在杭州城内、外所设闸口、南星桥、清泰门、艮山门、拱宸桥五个站中,清泰门站(今杭州站)凭借总站的优势,不论客运还是货运的规模均排序第一,如民国二十年(1931 年)的营业收入935 708 元、进出站旅客1 191 793人,而艮山门站仅77 215元,211 356人[15],分别是前者的8.25%和17.73%。清泰门站周围筑路13 条,整齐划一,分布着旅馆、商铺等服务设施,“此外如城站之迎宾、武林第一楼、模范剧院、益智社等处,每到晌午,竟有人满之患,其热闹可以想见”。
(二)人口增长
清末,杭州进入到一个政局相对平稳的时期,经济恢复带动社会发展,作为浙江省治所在之地,很快成为东南地区农产品的集散地、工业品的中转地,对周边甚至外省产生了吸引力,人口大量内移,清宣统二年(1910 年),浙江省进行了第一次人口调查,得出以今解放路为界的仁和、钱塘两县共约44 万人,但考虑到两县的四至范围,西南的钱塘县(东:清泰、望江两门为止;南:富阳县庙山界七十里;西:余杭县长桥界四十五里;北:德清县导墩界七十里;东南:萧山县西兴界二十八里;东北:仁和县义和坊四里;西南:富阳县分金岭为界六十五里;西北:余杭县西溪界四十里);东北的仁和县(东:海宁州上舍泾为界六十里;南:绍兴府萧山县渔浦界二十八里;西:钱塘门抵城界;北:德清县五林村为界四十五里;东南:萧山县西兴界二十八里;东北:石门县横溪界一百二十里;西南:西城脚下钱塘界;西北:德清县导墩界七十里)[16],十分明显,只有其中部分空间位于城墙之内,由此可以推断,杭州城市人口远在此数之下,以上聚落分布之图似可佐证。
即使如此,由就业、收入等造成的城乡差距,构成人口要素“乡→城”流动大于“城→乡”流动的态势,如民国十八年至二十年(1929—1931年),杭州人口内移共计297 500人,外移225 000人,净内移72 500 人[17]。而其中的90%以上为省内和外省的“移民”,省内“因为天灾人祸的缘故,不得不搬到省会来求生活”,外省“因为浙江比较的安定,比较容易找机会,也搬到浙江来”,尤其是“政治中心的杭州”[18]。杭州人口不断增长,如民国十六年(1927 年)计38 万人,民国二十年(1931 年)达52 万人,增长率为36.8%,如果按《杭州市经济调查》的面积650 平方公里来计算,得出1931 年12月的人口密度为805 人/平方公里[19]。这可从高密度集聚区增加、成片的趋势中一窥其详。同时,大量的省内和外省“移民”并不能完全为主体区域所消化,其外缘或分布范围也在不断地扩展之中,成为杭州城市聚落散布全城的重要驱动力。
(三)都市设计
杭州城市聚落变迁源于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但毋庸置疑的是,不同权力的介入发挥了导向性的作用。地方政府所采取的城市发展战略,指引着杭州城市聚落变迁的方向。这其中又以若干的“都市设计”为最。
先是以“拟就旗营空地兴辟市场”议决为基本思路的新市场计画得到实施,这是一个以追求街道卫生、公园花草为主旨之一的“都市计划”,明显带有英国霍华德(Howard)“田园城市”理念的痕迹,“自旗营新辟市场后,湖滨草地安设长椅,西曝日光,既温而暖,远望南北诸峰,屏列如障,而西园及湖山其一楼等茶馆新创,又足供游客之休憩,故每日午后裙屐争集,若不知为冬令者,亦杭城之新气象也”。这是杭州城市聚落分布中心朝西南方向略有偏移的原因之一。
在地方政府所采取的杭州城市发展战略中,以现代意义上的、重在功能分区的“都市设计”最具代表性。从民国十六年(1927 年)至抗战全面爆发的十年时间里,杭州市政府拟定了“行政计划纲要”,《杭州市区设计规则》《杭州市分区计划》《杭州新都市计划》,这些“都市设计”的内容已超出本文范围,但它们确定的四至范围始终处在扩展之中。从“行政计划纲要”中,东南沿海塘至钱塘江闸口一带,西至天竺、云栖。北至笕桥及湖墅、拱宸桥[20],经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勘定新的界限,“其西南界线,自之江文理学院西面江口大路起,循路之曲折,蜿蜒达于狮子峰之顶,跨天竺山,斜趋石人岭、石头山,循路由美人峰至北高峰,横贯桃源岭,由椅子山出秦亭山至古荡,以与旧界相会;西北角界线,由汽车路洋桥入河,过和睦桥,沿周家桥,侧折转严家桥,循河至汽车路,出拱宸桥,与运河为界;北部界线,由长桥起,经永安桥折向北,循河直趋至河流转弯处,折东经镇梁桥至施行桥,又折南过金典桥,随河流曲折至严家桥,以与旧界相会”,到《杭州新都市计划》再次划定杭州市与杭县的界限,“由梵村西约1公里之留芳岭,直上山冈,经百子尖、任家坞、象鼻尖、竹竿山、琅珰岭,至石人岭、白云峰,与市区原界线连接,悉以山之分水线为界,界东梵村、徐村、云栖、梅家坞、五云山、狮子峰、白沙坞及大刀沙一带之山丘平地,尽行划入市区。现全市面积,共计250.835平方公里”[21]。不宁唯是,民国二十五年(1936 年),浙江省政府、杭州市政府又先后提出“钱江南岸新商区计划”“开辟西兴区计划”,虽因抗日战争即将全面爆发,只做了选址和测量,但其规划的理念、设想尤其是扩展方向,颇具前瞻性,而为后来的城市规划所借鉴。
“都市计划”关于四至范围的动态调整,使杭州城市聚落空间布局发生了一系列的演变,其中,扩展方向尤著。在聚落四散分布到整个城市的趋势中,越来越近城墙,而城墙不仅是一处线状建筑,还是一个独特的空间,即城乡的结合部或过渡带。围绕这一空间,不论该段城墙是否拆除,均进行了设施建设,或在城墙基址筑“环城马路”,或建市场、辟公园,或设火车站、筹建工厂,是设施建设、空间扩展、格局演变最早、最快、最集中、最明显的区域,更是城市化进程中由乡村向城市转化的先遣。
聚落作为人类在聚居土地上安顿自己的方式,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始终处于动态变迁之中以杭州城市聚落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这一要素在《浙江省城图》《杭州市街及西湖附近图》上的复原,来解析清末至民国时期杭州的城市化进程。在这数十年的短暂时光里,杭州城市聚落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布局上均发生了演变,但这一演变绝不孤立,更割裂不了与过去、未来的种种联系。既是过去聚落的某种延续,也是未来聚落形成的基础,更在于从过去、现状、未来之间找到了相应的平衡点,它们在折射出近代以来杭州城市化进程的同时,也将为新时代城市在健康、持续的道路上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1949 年后,尤其是五六十年代见缝插针建工厂、改革开放以来用“拆旧建新”方式推进旧城改造、由“拆改留”到“留改拆”转变、党的“二十大”报告“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历史曲折,更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