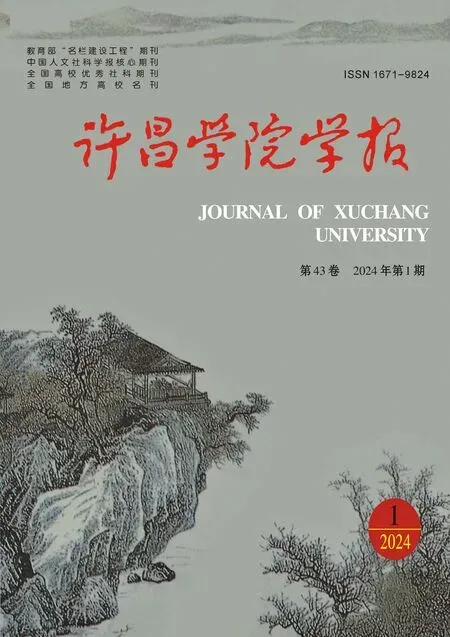百花齐放与多途发展:由新出简帛文献看战国史学的多样化编纂特征
刘 承
(许昌学院 文史与传媒学院,河南 许昌 461000)
战国史学,历来被划到先秦史学的框架中而被视为中国史学发展的童年阶段。由于年代久远所带来的思维定式,加之样本的单一、史文的缺失、伪书的混杂,我们对于战国史学形态似乎形成了固有的印象,那就是单一、粗疏、零散、不成体例。近四十年来大量简帛文献的整理和公布,促使我们有必要修正这个传统的观点。在这些涉史类简帛文献中,既包含“事语类”这种故事体史书,又包含“纪事本末类”的史事汇编,还有天文、地理、世系、礼仪类等专门性史学文献。其编纂类别之多样、历史观念之丰富、思想见解之深刻,令人叹为观止。将这些“真”文献作为研究对象,对战国史学的编纂成就进行整体考察,对于重新认识这一阶段史学发展的真实镜像,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事语类”史书占据半壁江山
在涉史类文献中,“事语类”史书数量最为丰富,反映出“记言”“记事”已成为春秋以来史书编纂的主流趋势。记录言行,是史官的基本职责所在。《礼记·玉藻》称:“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1]778由此形成的原始档案就成了事语类史书的主要史料来源。事语类史书,一般以特定的历史主题或事件,加以辑录汇编。内容多涉及春秋战国史事,少数涉及夏、商、西周古史(由战国时人追忆而成)。其编纂方式通常是以事为枢,以言为要,言行并记,记行事之原委,载言谈之语录[2]。这类史书的大量出现,多集中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与当时列国交往频繁有着很大关系,反映了人事、人谋在推动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有专家认为,“在早期的史书各体中,故事类(事语类)的史书却特别活跃,数量十分可观,其实是最突出的一种”[3]288。从清华简、上博简、马王堆帛书等已公布的资料来看,情况确实如此,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如下几个小类。
一是类似于《国语》的以记言为主的古书,主记“邦国成败,嘉言善语”[4]594。如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整理者张政烺先生指出该篇应属于楚大夫申叔向楚庄王建议教育太子“九艺”之一的“语”。全篇16章文字,“每章必记一些言论,所占字数要比记事多得多,内容既有意见,也有评论,使人一望而知这本书的重点不在讲事实而在记言论”[5]。有学者列举例证,认为该书是“《国语》的一种选本,其内容是古本《国语》有,后来散失了的”[6]。不论这个结论是否成立,但可以肯定的是,《春秋事语》当是先秦贵族接受历史教育的一种课本,“突出特点是每章必记言论,寓理于史”[7],属于典型的春秋时期的语体史书。此外,还有北大简《周驯》,是以“训语”的形式来记载古史。全篇共14章,以周昭文君与共太子对话的形式,回顾了尧、舜以来至秦献公古代王侯的故事,借以阐述治国为君之道。该简犹如贵族的家训,“它以直接的形式,揭示了先秦讲说故事的一个重要功能,即以史为鉴,于事喻理,化启心智”[8]。它是先秦“训体”文本的一种,也是语体史书的典型代表。
二是以记事为主体的具有专题性质的史书。这类史书往往围绕具体的思想主旨展开叙述。一种是记治国理政措施。如清华简《越公其事》,全篇分11章,讲述吴越夫椒之战至越灭吴的故事,重点描写了越王勾践实施“五政”,渐致富国强兵的过程。这篇简文的编纂特点是记事与政论相结合,“对于越国兴起的过程与经验没有采用君臣问答或单纯叙述的方式,而是进行了分类总结和概括,再以时间的次第分别叙述,既有政论的特点,又不失记事的大体”[9]。还有一种是追忆古先圣王往事。如郭店楚简《唐虞之道》讲述上古唐虞时代尧舜禅让的故事,通过赞美舜的美德阐述了尊贤政治的重要价值。上博简《武王践祚》记周武王向太公望垂询治国之道和铸铭以自戒之事,体现了战国史家熔古今史影为一炉的编撰方式[10]。上博简《成王既邦》记周公教导成王如何行“天子之正道”一事,反映了战国学者对于“重光其昌”这一理想国的探索。
记史类史学文献当中还有很多是具有国史档案性质的文献。它们多为各诸侯国史官的原始记录,以单篇或短章形式专记某一历史事件,内容集中在春秋时期。如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郑文公问太伯》《子产》述郑国史事,前两篇主记武公、庄公史事,对于考察两周之际郑国东迁和春秋初期郑国小霸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子产》主记改革家子产的政治思想,简文提到的“郑刑”“野刑”,可以补充《左传·昭公六年》子产作刑书的记载。清华简《子犯子馀》《晋文公入于晋》《赵简子》都是记晋国史事,对晋文公称霸和卿族势力崛起的原因有着比较深入的分析。上博简《成王为城濮之行》《柬大王泊旱》《庄王既成》《申公臣灵王》《平王问郑寿》《平王与王子木》《陈公治兵》等都是记楚国史事,涉及晋楚城濮之战、邲之战等争霸事件,但更多地讲述了楚国公族贵族间的政治残杀,反映了春秋中晚期楚国复杂的政治局势。此外,还有清华简《管仲》和上博简《竞公虐》记齐国史事,清华简《子仪》记秦国史事。这些事语类史书基本上可看作当时人说当时事,内容比较集中,史料价值很高。
三是以诸子百家语的“语”形式出现。这类文章“今多视为政论,但在古代,却是私家之史乘”[3]299。如上博简《鲁邦大旱》《举治王天下》《史蒥问于夫子》等篇以尧、舜、禹、汤、文王等圣人之治来阐发议论,反映了战国儒家浓厚的崇圣观念,其历史观中的厚古薄今思想倾向非常突出。清华简第八、九辑收录的《邦家之政》《邦家处位》《治邦之道》《心是谓中》《天下之道》《虞夏殷周之治》《治政之道》《成人》等篇,则是一组风格相类的有着很强逻辑性的政论文章。这些简文大致从修身、重德、任贤、恤民、轻刑、反战、崇礼义、睦外邻、和诸侯等内政外交方面阐述政治理念,语言通俗而典雅,思想丰富且深刻。其思想归属不宜简单以后世的学派观念来套用[11],可视之为楚人“杂学”[12]。文中多用“昔者”“今者”作对比,带有强烈的以史为鉴意识,史论特征十分明显。
上述以记言、记事为主体的史学文献已经突破了官书、国史的限制,既不像诗书类文献那样古朴深奥,也不再像编年体国史那样拘守于周礼,而是更多地表现出重视人事的发展和历史人物对社会变动的认识[13]21。事语类史书代表了春秋战国以来私人历史撰述的繁荣,为后世纪传体史书的编纂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二、清华简《系年》——纪事本末体的滥觞之作
作为一部有着纪事本末体特征的史书,清华简《系年》开启了以宏大叙事为主的历史书写方式的样例。这部文献由138支简组成,共3875字,分23章,各章相对独立,内容上采取详近略远的述史方式,由武王克商开始,直到战国早期三晋与楚大战结束。全篇以晋、楚争霸为主要叙事线索,具有统一的谋篇布局,“是一篇经过作者精心构思,主题突出、脉络清晰的史学作品”[14]。《系年》的面世,堪称中国史学史上的重大发现。它的出现,“就像曾侯乙墓编钟改变对音乐史的认识一样,也会改变我们对先秦史学的认识”[15]。
《系年》的编纂有三个显著的特征。
第一,《系年》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纪事本末体史书,但它在体裁上具备了明显的纪事本末体的特征。纪事本末体作为一种史书体裁,其编纂特点是“以类排纂,每事各详起讫,自为标题”和“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16]437。而《系年》从内容和形式上来看,就大体符合这两个特点。如第2章记述道:

此章完整讲述了两周之际的政治动荡,记载了幽王废长立幼,平王奔西申,骊山之战,携、平二王并立,晋文侯杀携王,平王东迁,诸侯掌权等一系列史事,深刻揭示了周王室内部、内诸侯与外诸侯之间的政治矛盾。作者相继用“逐”“走”“围”“亡”“杀”“徙”等字眼,生动刻画了王室贵族血缘亲情的冷漠和政治杀戮的残酷,还用“周亡(无)王九年”来陈述周王朝权力真空的窘境,表达出对周代王权日薄西山的感叹。该章以两周之际局势变迁这一重大事件作为叙事主线,用幽王、携王、平王纪年来标注事件发生顺序,叙事虽简,但前后始末一目了然,符合“每事各详起讫”“每篇各编年月”的纪事本末撰述要素。《系年》的编纂,“反映了历史学家要求在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掌握影响最大的主要历史事件,明了其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的新认识”[18]45,表明了作者“带有理性的进步史观,更多从人的活动方面来考察,表现出尊重客观实际的倾向”[19]。因此,说《系年》是纪事本末体的滥觞之作,当不为过。

第三,《系年》作者不虚美、不隐恶的直笔原则。作者从楚人的角度叙史,从不掩饰楚国先王的过失。如第15章讲楚庄王以平陈国内乱为借口伐陈,杀夏徵舒,掳其妻少孔(夏姬),致使楚大夫申公巫臣反目,逃晋通吴,最后导致吴人侵入,使楚在对吴战争上疲于奔命。第18章讲楚灵王背弃第二次弭兵之会,伐徐、吴、陈、蔡等江淮诸侯,并杀蔡灵侯,虽然战功赫赫,最终也落得个“见祸”的下场。第23章则用“无功”“宵遁”“犬逸”如实描绘楚军溃败奔逃的狼狈状,毫无隐晦之意。这正如专家所说:“篇中不为楚人遮丑,有时措辞颇为严厉……作者即使确是楚人,他的眼光则是全国的,没有受到狭隘的局限。”[23]“著者通过这种史实的陈述,似乎是想告诉其所教育的对象——战争即使是胜利,带来的也是灾难。”[24]
总之,《系年》称得上是战国史学编纂中的一部旷世之作。它的史料来源于王室旧档和各国史记,不可谓不真实。它吸收了书体、语体、编年体等史体的长处,开创了以“事件”为中心的具有纪事本末特色的历史编纂方式,不可谓不用心。它的叙事严密紧凑,情节生动,不可谓不考究。它用“焉始”“至今”诉说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充溢着深沉的忧患意识,不可谓不深刻。《系年》是东周史体分衍与融合的产物[25],是展示战国史学成熟气质的重要表现之一,其颇具前瞻性的编纂方式,也为后世的历史书写赋予了更多的启示。
三、“天文、地理、礼仪、谱系”类各具特色
涉史类简帛文献还存在一些涉及天文、地理、礼仪、谱系等专题性质的史书,反映了战国史家撰述视野的拓展。它们都是先秦思想文化长期积累的结晶,也是先秦史学编纂多样性的一种反映。
2021年11月刊布的清华简(第十一辑)中有一篇名为《五纪》的简文,是一部罕有的天文类佚籍,堪称最早的《天文志》。这篇简文规模宏大,凡130支简,存4463字,篇幅超过《系年》。整理者黄德宽先生总结说:“该篇始于历数,终归人事,结构严整,层次丰富,对于古代天文历数、国家治理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26]89
《五纪》的编纂带有强烈的专制主义思想。简文开篇就提纲挈领地说:
隹(唯)昔方有港(洪),奋洫(溢)于上,权其有中,戏其有德,以乘乱天纪。后帝、四干、四辅,乃耸乃惧,称纕(攘)以图。后帝青(情)已,攸(修)鬲(历)五纪,自日始,乃旬简五纪。五纪既敷,五算聿度,大参建尚(常)。天地、神祗、万貌迥(同)德,有邵(昭)明明,有港(洪)乃弥,五纪有尚(常)。[26]90
五纪,就是日、月、星、辰、岁。它是“后帝”用来统摄宇宙秩序和人间“常法”。这种将天道与人事相连的构想,被作者赋予了神圣且永恒的意味。一是强调“天”与“人”的紧密结合与统一。作者认为人事行用务必与天象运行保持高度一致,不相悖乱,才能达到“天地、神祇、万貌同德”的和谐景象。二是强调“后帝”至高无上的地位,体现出鲜明的等级意识和专制思维。简文中的“后帝”(天帝)居于中天,将“群神十有八”“群祇二十有四”“二十八宿”、南门、北斗等神置于四荒、四忱、四柱、四维等方位中,对各级神祇拥有至高无上的支配权。而天地神祇则奉后帝之命各有所司,行使执掌尘世万貌的相应职责[27]。《五纪》篇的这个安排,与《史记·天官书》围绕北极星将二十八宿及各区域星座分布于东官、南官、西官、北官的记述如出一辙,都是在构建一个虚幻的天帝朝廷。“这种机械的比附,本身并不科学,但却是一种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思想在天文观测上的反映。”[28]126三是设立以“五纪”为纲领的法则和秩序。“五纪”不仅统领“五数”“五算”“五时”“五色”“五气”等自然法则,还对应“五音”“五章”“五德”等人间秩序。举凡岁时月令、风雨雷电、道德条目以及人的感觉器官等等,都纳入“五纪”体系当中,而且都合于“五”这个数目,为的是体现天经地义、不可违逆的常理。例如礼、义、爱、信、忠这“五德”,作者称其为“天下之正”。它与儒家的“五行”(仁、义、礼、智、圣)不同,“作者只择用了其中顺从统治的部分……为的是以训导民众循规蹈矩”[29]。《五纪》的天文思想与后世正史《天文志》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在营造“普天之下”的专制一统观念。尽管作者可能不是一个史学家,尽管他的思想归属比较庞杂,兼及阴阳、儒、法各家,但作者旨在创建大一统国家永恒法则的历史构想对后世史家产生了强烈的启示。董仲舒的天道合一说、班固的承天统理和一统尊君的历史观,都能从《五纪》中找到类似的影子。因此,从历史观的承接上来看,《五纪》的神意史观对当时及秦汉以后史学的影响是不容小觑的。
地理类著作中较典型的是上博简《容成氏》。该篇主述尧、舜至文王等上古三代古帝王的传说,含有浓厚禅让思想,当是战国时期热衷于托古改制的儒生所作。文中有相当篇幅记述大禹治水、分九州的故事,所载九州之名除徐、荆、扬、豫外,其余五州名称均为首次出现,这说明《容成氏》中的九州“完全可以视为自成一系的古老传说”,该九州传说发生的地域“最大可能在黄河下游的山东一带”[30],也就是齐地。齐国在战国大多数时间里一直处于一等强国行列,也具备统一的资格,《容成氏》的地理观念或许就是齐人九州一统观念的另一种表达。
礼仪类文献亦即礼书。先秦礼书大多出自史官的非正式的礼制载录[31],后由儒家七十子后学编辑成册。这类礼书多保存于上博楚简中。如《天子建州》篇,主要论述周代大飨礼的饮食礼规及礼与仪、礼与刑的关系。特别是篇中“豊(礼)之于宗庙也,不腈(精)为腈(精),不美为美”一句,体现出文质兼具、和谐相济的礼学观念[32]。《君子为礼》和《弟子问》“当是颜氏之儒所传,反映了颜氏之儒所受孔子之教的某些侧面”[33],前者记载了大夫“容礼”的若干细节,可与传世文献《礼记》《新书》的记载互相补充;后者则通过孔子答弟子问的方式,介绍了君子言行应注意的一些礼节。礼书从先秦历经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发展,至隋唐时形成了所谓的仪注学,归属于史部。不过先秦礼书所体现的正纲纪、别尊卑、区贵贱的专制主义意识形态,依然贯穿于后世礼书的撰述和修订中。这也正是仪注类史书备受专制统治者重视、长期处于显学之位的原因。
谱系类文献的代表当属清华简《楚居》。《楚居》是一篇记载楚国先祖世系及迁徙情况的古史文献。学者推测该篇“或者是在《梼杌》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作者应为楚国史官,很有可能就是清华简墓主人[34]。《楚居》的特点是按世系衍生叙述历史,以楚公楚王的谱系为经,以居处迁徙为纬,附载楚王求偶经历、后妃相貌、生子情况等,目的是体现楚王世系的连续性和正统性。《楚居》与《世本》《帝系姓》《春秋历谱牒》等均属于同一类作品,基本契合了《周礼·春官·小史》“小史掌邦国之志,奠世系,辨昭穆”的要求,都是先秦氏族政治在历史编纂上的反映。谱系类史书编纂到了南北朝隋唐时期形成了所谓的谱牒之学,甚至一度位居显要,并细化成士族、谱籍、世胄、世官、谱学、谱局等著录小类。但无论怎样细化,它们在推世系、辨亲缘、定姻亲的编纂主旨上与先秦“氏姓之书”是一致的,说明先秦谱系类史书也为后世的谱牒之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简言之,上述天文、地理、礼仪、谱系类等涉史类文献的编纂,是战国史学分化的具体反映。这些史学专篇并非偶然出现,而是战国史家根据时代变迁和政治需要精心构造的产物。它们看似不言政治,实则与现实政治密不可分,体现出“史之为用,其利甚博”[35]303的社会功用,更是反映了史家经世致用的著史动机和政治情怀。
四、史学成“家”:战国史学编纂多样化形成原因探论
历史编纂是主观进行的,其执行者就是那些具备深邃历史思维的历史学家们。英国学者柯林武德曾说:“历史知识就是历史学家正在研究的那些思想在他自己心灵里的重演。”[36]213所以,历史学家也是历史的创造者。所谓“心灵里的重演”,实际上就是历史学家执行社会责任、参与现实的历史创造活动。而这个创造活动,就是史学编纂工作。
战国史学编纂之所以能够展现出成熟的气质和多样的面貌,得益于战国“史家”这一家派的贡献。以往提到先秦各家各派,我们往往想到的是在思想领域作出卓越贡献的诸子百家。实际上,史学领域也有“家”,那就是“史家”。史家脱胎于商、周史官,但与早期史官仅限于记录官书和史诗的职事不同,春秋以后的史家已经走出了学在官府的藩篱,开始大规模编纂国史、家史及其它专门性史籍,以适应“治”的需要。春秋战国各种历史撰述的出现,显示出史学已经进入到勃然生长的阶段。这一时期的史学编纂群体,如同儒、墨、道、法一样,卓然成为一“家”。他们有着共同的编纂宗旨,就是“王道备,人事浃”[21]509;有着清晰的书写原则,那就是“书法不隐”[37]663;有着明确的撰述目的,那就是采善贬恶、彰往察来;更有着广阔的历史视野、完善的史学思想和深刻的历史观念。战国史家已经具备家派的学术特征,其鲜明的个性意识和多样化的表达足以令它成为与诸子百家并称的“史家”。恰恰正是其个性、多样的特质,才使得战国史学形成百花齐放与多途发展的现象。因此,考察战国史学编纂多样化的形成原因,需要从战国史学的成“家”这一角度入手。
首先,王官失序致使史官向史家转变,促进了国史修撰的繁富。《孟子·离娄下》载孟子语:“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38]572说明西周时期用史诗来颂扬王化意义的述史形式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展现霸权雄姿的列国国史的编修。王官下移为国史编纂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一是各国史家(指那些具有历史意识的史官、卿相、士大夫等)可利用大量积存的官书档案作为史料来源,采取灵活多变的方式,编纂出适合本国历史形势的史著,如春秋、梼杌、乘、书、志、微等。二是历史编纂从内容到形式更加系统化,如从体裁上看,就有事语体、记体、训体、编年体以及带有纪事本末特征的历史撰述。很多史著往往围绕一个史体,兼蓄其它史体特点,融会贯通为一体。三是出现了史书以外的各种撰述类别,如礼、乐、兵、刑等具有典制体性质的史书以及天文、地理、谱系等专门性史书。国史编纂的日渐繁富更好地反映了春秋战国的历史变革,为中国史学的多样发展奠定了很好的根基。
其次,私人历史撰述蔚然成风,为战国史学的多样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春秋末年,孔子据鲁国国史修撰成《春秋》,开启了私人历史撰述的先河。至战国,私人修史蔚为大观,出现了多种形式的历史撰述:有关于春秋时期的编年体史书和文献汇编,有解释《春秋》的史书,有关于战国时事的辑录,还有萌芽形态的通史性质的著作[13]20。传世文献中的《春秋》三传、《国语》《战国策》,出土文献中的事语类史学文献,基本上都是私修史著。它们的作者,大多数并非史官,但并不妨碍其成为优秀的史家。这些史家能够取得如此高的成就,原因种种:一是出于王命,供统治者览观所需;二是补史官之阙,以丰富史实;三是出于发展史学的自觉意识;四是史家自身敏锐的洞察力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致。战国时期私人历史撰述彻底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开创了属词比事、约文去繁、征信、求真等历史编纂的优良传统,促进了战国史学领域的活跃和创新。
再次,春秋战国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突出了史学的资治效应。史学社会功用价值的扩大和史学重要性的提升,是造成战国史学编纂成就丰富多样的重要原因之一。汉代史家司马谈在他的《论六家要旨》这篇学术史文献中,开篇便提纲挈领说:“《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21]3289这段话总结出先秦诸子的学术宗旨在于“务为治”,即服务于当前政治,亦即常说的经世致用。战国史家作为百家中的一家,在经世致用方面,较之诸子,有过之而无不及。史学经世致用的涉及面是很广的,上及治国理政,下及人生修养。因此,出于“致用”这个目的,战国史学编纂在数量和种类上骤然提升。如在治国理政方面,《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记载有《左氏春秋》《铎氏微》《虞氏春秋》《吕氏春秋》,出土文献中有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银雀山汉简《晏子春秋》、清华简《系年》《越公其事》、上博简《鲁邦大旱》等等。这些史书,都是战国史家对于春秋这个距离他们最近的时代的历史经验和智慧的总结,充分表达了资治这个编纂宗旨。除此之外,记载夏、商、西周和战国当代史的史学文献亦不在少数。在人生修养方面,战国史家早已注意到“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39]243的意义。《左传》《国语》以及清华简、上博简中的很多史料,都是通过记录前代人物的言行,来阐述忠孝、仁义、礼乐、圣智的社会作用。这也正是当时史家以史为鉴、以人为鉴的用意所在。
最后,战国史家内部的学术创新和融合,为战国史学的多样发展提供理论指导。战国史家总结了很多史学理论方面的成果。如在史笔方面,战国史家创立了采撰、实录的信史原则。在史家修养方面,孟子提出了事、文、义三原则,指出史家必须具备记事、文采、历史认识这三个基本理论素质。在史识方面,战国史家运用了通识的历史认识方法,开创了中国古代史学的通史家风。通识有纵通和横通两种。纵通有《左传》《竹书纪年》、清华简《系年》、帛书《春秋事语》、云梦秦简《编年记》、荆州胡家草场汉简《岁纪》等,都是以时间为序体现历史发展的连续性。横通如《国语》、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等,则是通过地域或人物言行来把握历史的横断面。无论哪一种“通”,都是编纂者整体性历史眼光的表达,体现了史家群体以古律今的历史意识。此外,战国史家在史法、史评、考据等史学理论上,在天命、时势、通变等历史观念上,都颇多创见。正是基于这些理论成果,战国史学才形成了系统的、连续的、多层面的历史撰述。
五、结语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40]121战国史学的创造自然也是以它已有的“条件”为依据的。这个“条件”,就是它正处于中国思想文化的“轴心时期”,也就是由神道主义发展到人文主义、由道术一尊走向道术分裂的思想飞跃时期。这一思想背景,促使战国史学走出了单一的以《诗》《书》载史的模式,分化成不同类型并具备一定体例的专史,产生了丰富多样的史学成果。多样化,正是战国史学整体面貌的突出特征。这个特征显示出战国时期的史学已经褪去童年的稚气,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总之,战国史学编纂不仅为秦汉以后的史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也对中国古代史学的连续性发展和中华文明的传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应予以充分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