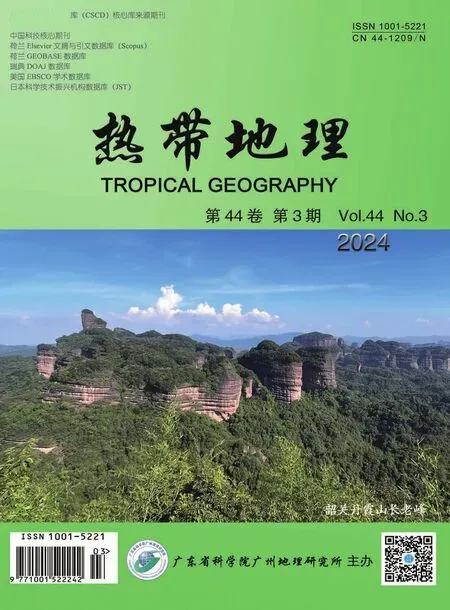人口城镇化视角下中国流动人口住房阶层研究
龚 岳,曹吉阳
(1.武汉大学 城市设计学院城乡空间治理中心,武汉 430072;2.澳门理工大学 人文与社科学院,澳门 999078;3.北京大学 城市规划与设计学院,广东 深圳 518055)
流动人口长期处于住房市场边缘,难以进入城镇 住 房 保 障 体 系(Logan et al., 2010;田 莉 等,2019)。第七次人口普查公报显示,2020 年中国流动人口规模达3.76亿,新市民的住房问题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李国庆 等,2022)。在城镇化的背景下,流动人口住房阶层(即住房拥有状况的分层)正发生变化。一方面,2012—2017年,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自购住房比例从12.3%升至25.2%(杨菊华,2018)。另一方面,流动人口内部出现明显的居住状况分化:农业户籍流动人口大多居住在宿舍或城中村等的半城市化地区,部分非农户籍流动人口有更多机会进入城镇住房市场(李强,2009;方长春,2020;王宇凡 等,2021)。国家对流动人口住房问题愈加重视,2021年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2021)将城市新市民与青年群体面临的住房问题提至国家政策层面,旨在帮助新市民与青年群体顺利进入城镇住房市场。因此,研究流动人口住房阶层,对于制定住房政策、推动流动人口新型城镇化以及改善其城市住房状况有重要意义。
住房阶层是一种社会分层,住房参与者由于消费经验与市场机会等方面的差异(魏万青 等,2020),处于阶层冲突中,形成以住房为表征的阶层与空间分化(魏万青 等,2020;曹吉阳 等,2021)。已有研究多从社会经济和制度变迁考察住房阶层及其影响因素。国外研究发现,拥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社会成员,更有可能住在自有产权住宅中(Martin et al., 2013)。种族差异是家庭进行住房选择的关键驱动因素(Ibraimovic et al., 2018)。在欧洲住房价格上涨的环境下,产权住房与住房保障是反映住房不平等的最重要的2个方面(Filandri and Olagnero, 2014)。针对中国住房分化的实证研究也证明社会经济和制度是住房阶层的重要影响因素。如在中国住房分化时期,户籍、职位与单位性质,对城镇居民拥有产权住房产生显著影响(Huang and Clark, 2002)。户主的受教育程度、出生序列、户籍性质、职业、行业等因素,可能影响家 庭 住 房 状 况(Bourassa, 1995; Pamela and John,1997)。
作为分析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重要视角,住房阶层研究存在几点不足。第一,多依据是否拥有住房以及住房产权类型划分住房阶层,忽视住房的空间性,即不同城镇乡住房资产价格存在较大差异,不能简单划分为同一阶层;第二,多关注城镇居民,较少关注流动人口内部阶层分化,以及这种分化与流动人口城镇化和住房的关系;第三,中国人口城镇化从省际迁移转向省内迁移,呈现新的迁移结构(林李月 等,2021),可能影响流动人口购房决策以及住房阶层,需进一步分析。鉴于此,本文以住房阶层为切入点,采用人口城镇化空间视角划分住房阶层、选取控制变量,探讨流动人口内部住房阶层的特征、空间格局、影响因素与机制。以期从人口城镇化视角拓展中国社会分层研究,为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制定提供实证支撑。
1 住房阶层理论和划分依据
居住社区的空间本质决定住房阶层的划分带有空间性,因为居住在不同社区或者是获得不同类型住房所有权都表征划分的空间标准。如Rex(1968)在住房阶层的划分中,按照令人满意的社区和不太令人满意的社区来区分居民类型。中国城镇乡的社区环境和住房资产有明显差异。一方面,城市房价高于村镇房价,级差地租的规律也说明城镇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房价越高。另一方面,城镇化率较高的地区提供给流动人口进入住房市场的机会较少(穆学英 等,2022 a)。这反映中国城镇化率较高的大城市中高房价和购房难的问题,以及在大城市中购买住房的流动人口拥有更多的资产和更高的购买力。因此,本文从人口城镇化的视角,结合传统拥有住房等划分标准,按照城镇乡的空间维度划分住房阶层。这一方面能在一定程度上表征流动人口的住房资产,另一方面能反映流动人口的城镇化程度。
社会经济因素和制度因素是影响住房阶层的主因,是市场转型与权力维续理论的外在体现。Blumstock和Szelenyi(1983)认为非权力阶层的利益在市场机制中能得到更好的保障与提升,Nee(1989)进一步指出再分配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意味着资源配置模式与社会分层秩序的改变。在中国市场转型的过程中,收入、受教育程度、出生序列、职业特征等社会经济因素也可能影响城市住房状况(Pamela and John, 1997)。而权力维续理论认为,中国城市的制度背景与历史具有延续性,在人力资本和企业家回报上升的同时,政治权力仍在影响资源配置,还是阶层分化的重要因素(Bianand Logan, 1996)。户籍、住房等制度的变迁影响社会成员的住房阶层。改革过程中,在市场化转型与权力资源再分配的作用下,流动人口依旧难以享有城市公共住房,而城镇本地居民仍保持住房资源占有的优势(谢霄亭 等,2015)。
从人口城镇化的视角看,人口的流动模式和区域不平衡发展可能通过住房过滤影响住房阶层。住房过滤是将住房供应与中低收入群体住房机会相联系的框架,市场或政府的住房供给过大时,低收入者有可能获得中高收入者放弃的住房(Xing and Zhu, 2018)。《中国房地产统计年鉴2017》(国家统计局,2017a)显示,2010—2020 年,中国人口增加0.7 亿,商品住房竣工面积从25.13 亿m2上升到62.77 亿m2,同时政府也大力提供公租房等保障性住房,城市住房总量增幅明显大于人口增长。基于迁移地域的住房供给状况,流动人口有可能获得住房。此外,当大城市住房紧张、中小城市住房供给远大于其人口增长时,流动人口可能更容易在中小城市获得住房,实现阶层跃迁。因此,本文基于市场转型和权力维续理论选取社会经济和制度因素,同时选取迁移和区域等空间因素,拓展住房阶层影响因素的研究。
2 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数据包括2016 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数据A 卷、城镇与住房数据。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样本为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不含港澳台地区)8 450个样本点中,非本区(县、市)户口、且在流入地居住1 个月以上的15~59 周岁流动人口,2016年样本总量16.9万人,问卷中问题303询问“您家已在哪里购买了住房?”,提供流动人口自购住房及其城、镇、乡的位置信息,这反映本文采用的住房数据主要为商品房,不包括不能买卖的农村自建房。2016年全国房价数据来源于禧泰数据库①禧泰数据.https://www.cityre.cn/;城镇数据来源于各省统计年鉴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7》(国家统计局,2017b)。
2.2 关键变量选取
城镇乡空间差异,决定流动人口住房选择带有等级特征(林赛南 等,2021;穆学英 等,2022b);住房成本差异,影响流动人口迁移决策(张海峰等,2019)。为厘清流动人口的潜在类别,将流入地特征、不同城镇化地区住房占有情况作为潜在变量,描述流入地住房限制,揭示住房群体的空间属性。住房支出占总收入的比例是消费分层的重要指标(张传勇 等,2020),因此将其作为潜在变量,反映流动人口的住房成本,揭示住房群体的经济属性。
在“社会-空间”系统中,资源和机会的稀缺与分配之间的矛盾,重塑社会阶层并推动城市空间发展。一方面,城镇空间占有是一种阶层“再生产”的机制,空间机会的结构性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群体的住房结果(穆学英 等,2022a)。另一方面,中国住房增值对生活机会的影响,会显著超过职业收入对生活机会的影响(魏万青 等,2020)。因此,选取购房地城镇化水平,表征流动人口在不同等级城市中的空间机会;选取城镇乡地区住房保有量,代表流动人口在不同城镇乡空间中的生活机会。最后,通过构造住房阶层地位量表,表征流动人口住房阶层。
基于已有研究(Bourassa, 1995; Bian and Lo
gan, 1996; Pamela and John, 1997; Huang and Clark,2002),本文将影响流动人口住房阶层的因素分为制度要素、社会经济特征要素和迁移要素。制度要素中,户籍、党员身份、单位性质与中国城乡二元体制及制度改革紧密相关,住房公积金与失业保险反映流动人口的抗风险能力。此外,流入地城镇住房保障制度差异,可能促使流动人口形成不同的购房决策。社会经济特征要素包含婚姻与受教育程度等,反映流动人口的个人特征。迁移要素包含累计流动时间、流动范围与流动区域,反映流动人口迁移的空间性及资本积累能力。
2.3 研究方法
1)潜在类别模型 针对随机偏好差异,潜在类别模型能将流动人口划分为多种类别。其优点为判断类别之间是否具有显著差异、分类是否有意义,避免人为武断确定样本分界点(王灿 等,2015)。本文模型外显变量为流入地特征、不同城镇化地区住房占有情况和住房消费,将外显变量分别记为A,B,C后,潜在类别模型表示为:
式中:i,j,k分别表示外显变量的趋势;πABC ijk表示外显变量的联合分布概率;πx t为观察的数据属于某一潜在类别变量x的特定类别t的概率;πAˉx it表示属于第t个受测对象,在流入地特征变量上为第i种反映的条件概率;πBˉx it表示属于第t个受测对象,在不同城镇化地区住房占有情况特征变量上为第i种反映的条件概率;πCˉx it表示属于第t个受测对象,在住房消费特征变量上为第i种反映的条件概率。
2)多项Logit 回归分析 利用多项Logit 回归模型,分析流动人口住房阶层分化的影响因素。公式为:
式中:p(Y=i) 为特定住房阶层的概率;i=1,2,3,4,……,n,表示流动人口的住房阶层;α1为常数项;β1~βn为回归系数;X1~Xn社会经济要素、迁移要素及制度与社会保障要素等解释变量。
3 流动人口住房阶层结构及特征
3.1 流动人口的住房阶层
不同住房群体,其经济属性与住房的空间属性存在显著差异(李强,2009)。住房资产是流动人口资本积累的表现(吴开泽,2019),描述流动人口的生活机会;而购房地城镇化水平,反映流动人口进入城镇空间的机会。首先,利用潜在类别模型分析,从类别数1的基准开始,逐步增加潜类数目并检验拟合优度,选出拟合优度值最小,且能较为准确地描述流动人口住房地位群体的分类(Julie et al., 2018)。检验显示,当类别为7 时,模型的拟合效果最好。其次,利用住房阶层量表(表1),结合住房群体的特征,将流动人口的潜在住房群体分为5类住房阶层(图1)。最后,为验证住房阶层与住房群体的联系,将住房阶层与住房地位群体进行交互分析。结果表明,流动人口住房阶层与住房群体划分呈现同步趋势,具有较强的相关关系(表2),说明将住房群体分为5类住房阶层较为合适。

图1 流动人口住房群体与住房阶层关系Fig.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grants housing group and housing class

表1 流动人口住房阶层量化信息Table 1 Migrants' housing class scale

表2 住房群体与住房阶层交互Table 2 Housing group and housing class interactive
从人口城镇化的视角,中国流动人口可以分为“三阶五层式”的住房阶层,呈现“土”字形的结构(图2-a)。其中,多房阶层、一房阶层与户籍地城镇有房阶层占总体样本的37.63%,较为接近中国2016年41.2%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能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中国的城镇化趋势,即流动人口在城镇中的购房行为,与人口城镇化进程趋同。

图2 流动人口(a)和分户籍流动人口(b)住房阶层结构Fig.2 Housing class structure of migrants(a) and migrants by Hukou(b)
3.2 流动人口住房阶层的主要特征与空间格局
1)社会经济特征 流动人口呈现出生序列靠前、受教育程度越高、收入越高,无房阶层占比越低,有房阶层占比越高的特征(表3)。1950年以前出生的流动人口中,7.16%在城镇拥有多套住房,而57.59%的“90后”流动人口尚未拥有产权住房。小学及以下学历流动人口无房阶层占比55.93%,远高于其他学历流动人口,且多房阶层占比最低。大学专科以上学历流动人口,村房阶层与无房阶层占比最低,分别为6.52%与35.03%。在收入方面,月均工资收入低于2016年全国人均最低工资标准的流动人口②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各地区月最低工资标准情况》(截至2016年12月)。,无房阶层占比最高、多房阶层占比最低。月均收入5 600 元以上的流动人口,多房阶层、流入地一房阶层、户籍地城镇有房阶层占比高于其他收入的流动人口,且无房阶层占比最低(图3)。

图3 流动人口住房阶层收入特征Fig.3 Income characteristics of migrants

表3 样本基本特征Table 3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samples %
2)迁移特征 在迁移范围方面,跨省迁移流动人口尚未拥有产权住房的比例为51.7%,市内跨县迁移人口尚未拥有产权住房的比例为45.02%。在迁移区域方面,东部地区流动人口无房比例最高(54.86%)。在累计流动时间方面,流动人口住房阶层呈流动时间越长无房阶层占比越低,有房阶层占比越高的特征。
3)制度特征 农业户籍人口无房阶层居多,非农户籍人口流入地一房阶层居多(图2-b)。农业户籍流动人口无房阶层占52.74%,显著高于城镇多房阶层与户籍地城镇有房阶层,其中租住公共住房的农业户籍人口的比例仅为1%,仍难以享有城市公共住房福利。与农业户籍流动人口相比,非农户籍流动人口无房阶层仅占30.36%,流入地与城镇有房阶层占比达65.62%。党员身份流动人口在城镇拥有多套产权住房比例相对较高(5.66%)。在国企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流动人口,城镇产权住房比例相对较高(3.69%),尚未拥有产权住房的流动人口比例较低(36.49%)。
4)空间格局 中国流动人口住房阶层呈现南北差异(图4)。流入地与户籍地多房阶层主要集中分布于北京、上海与部分中小城市(图4-a),成渝、珠三角城市群多房阶层较少。相较于其他大城市,北京、上海的多房阶层流动人口呈现非农户籍与高学历的特征,其住房支付能力与城镇适应能力较强(林李月 等,2016)。流入地一房阶层较少分布在东南沿海、京津冀与成渝城市群,而较多分布在内蒙古、东北三省(图4-b)。户籍地城镇有房阶层多集中于中西部(图4-c),以回迁购房为主。户籍地村房阶层并未形成具有明显特征的空间格局(图4-d)。而无房阶层流动人口呈沿东南部集聚的空间格局(图4-e)。

图4 住房阶层空间格局(a.流入地与户籍地多房阶层;b.流入地一房阶层;c.户籍地城镇有房阶层;d.户籍地村房阶层;e.无房阶层 )Fig.4 Housing class spatial pattern of multiple houses in inflow and Hukou areas(a), one house in the inflow area(b),one or multiple houses in Hukou areas(c), village houses in Hukou areas(d), and the houseless class(e)
4 流动人口住房阶层分化的影响因素与形成机制
4.1 流动人口住房阶层分化的影响因素
首先,共线性与拟合分析发现回归模型容差均<0.1、VIF均<10,不存在共线性问题。在此基础上,通过Logit 回归(表4),分析影响流动人口住房阶层的因素,并探讨流动人口住房阶层分化的机制。

表4 流动人口住房阶层分化基础模型Table 4 Multiple logit regression of housing class
1)社会经济要素 模型结果显示,住房负担能力较强、出生序列靠前、受教育程度高的流动人口,更有机会成为多房阶层。此外,婚姻与就业身份也是影响流动人口住房阶层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房价收入比越高,流动人口成为户籍地城镇有房阶层的概率,比成为多房阶层的概率高1.145倍,比成为流入地一房阶层的概率高1.113 倍。出生序列能测度流动人口社会资本累计时长。随着年龄增长,流动人口持续不断积累社会与经济资本,进而有机会进入流入地商品房市场,提升自身的住房地位,但年龄增加到一定程度后,流动人口住房地位又呈现下降趋势(王丽艳 等,2018)。本文模型显示,与1950年以前出生的流动人口相比,其他出生序列流动人口更倾向于成为户籍地城镇有房阶层。有研究认为,国内房价高企,北上广与天津四座城市之中高学历青年推迟购房,无法在迁入地拥有多套住房(Chen et al., 2017)。与前人研究不同,本文发现全国尺度下高学历流动人口可在户籍地和迁入地购买住房,更有机会成为多房阶层。教育仍是住房阶层的重要影响因素,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流动人口成为多房阶层的概率是小学以下学历流动人口的3.48倍,且成为无房阶层的概率仅为小学以下学历流动人口的1/2。此外,在婚、雇主或自雇就业的流动人口,更有机会成为多房阶层。
2)迁移要素 地理空间先赋因素影响流动人口住房阶层(穆学英 等,2022b)。分析发现,流动人口流动距离越短,维持流出时自身住房阶层的概率越高,越容易保持与流出地相似的住房阶层。与跨省流动人口相比,省内跨市与市内跨县流动人口,成为多房阶层的概率,比成为户籍地城镇有房阶层的概率高1.368与1.533倍。值得注意的是,与跨省流动人口相比,省内跨市与市内跨县流动人口,成为无房阶层的概率比户籍地城镇有房阶层的概率高1.495与1.639倍。迁移距离越短,流入地与流出地社会经济状况、城市住房政策越相似,流动人口更有可能维持其流出前住房阶层。在累计迁移时间方面,时间越长,流动人口越容易成为多房阶层。与流动时间2 a以内相比,流动3~9 a的流动人口成为多房阶层的概率高1.598 倍;累计流动10 a的流动人口比2 a高2.035倍。在流入区域方面,西部地区的流动人口,成为多房阶层的概率,比成为户籍地城镇有房阶层的概率高1.184 倍。此外,与东部地区的流动人口相比,东北地区的流动人口成为户籍地城镇有房阶层的概率比成为无房阶层的概率高1.242倍。
3)制度要素
在单位性质方面,国企员工的制度优势得以延续。与已有研究不同(Ho and Kwong, 2002;王丽艳 等,2018),分析发现,国企就职的流动人口,成为多房阶层的概率比外资就职的流动人口高1.508倍,比私营与个体流动人口高1.577倍,国企单位在多房占有方面仍保持其显著优势。户籍仍是影响流动人口进入城镇住房市场的最重要因素,非农户籍流动人口仍具有其制度优势。与农业户籍相比,非农户籍与居民户籍流动人口,成为多房阶层的概率高2.080与2.173倍,非农户籍与居民户籍流动人口尚未购买住房的概率仅为农业户籍流动人口的1/3,验证了已有研究(蔡禾 等,2013;杜本峰等,2014;Chen et al., 2017;王丽艳 等,2018)。已有部分研究认为,党员身份的制度优势正在减弱(Huang and Clark, 2002;蔡禾 等,2013);但也有研究认为,党员身份显著影响居民住房阶层(刘祖云 等,2012;毛小平,2014)。本文发现,与党员相比,非党员成为多房阶层的概率为党员的85.4%。党员身份在住房阶层分化中仍具有一定优势,体现政治资本在流动人口社会阶层分化中起作用。与拥有住房公积金的流动人口相比,未拥有的流动人口成为多房阶层的概率不足80%。与本地拥有失业保险的流动人口相比,没有流入地失业保险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成为户籍地城镇有房阶层而非多房阶层,其概率高1.471 倍。可见,住房公积金与流入地失业保险,也会影响流动人口住房阶层分化。
4.2 流动人口住房阶层的形成机制
制度与机制变迁促使社会产生结构性变化(Wu and Xie, 2003),市场和国家制度变迁是流动人口住房阶层分化的根本原因。直到1998年的住房制度改革前,中国城市一直实行住房福利分配,没有产生明显的住房阶层。福利房时期,单位主导城镇住房分配,同一单位内部具有较强的一致性,职务与工龄是影响阶层分化的主要因素;而不同单位间的差异化福利政策会导致个体住房状况分异。住房制度改革后,在市场转型和制度变迁的共同作用下,个体的社会经济状况发生较大改变,住房改革的受益者多是拥有制度资源与社会资本的单位职工(Huang and Clark, 2002)。不难发现,占据优势资源的国有企业,其福利政策的延续,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住房阶层的持续分化。而流动人口并不拥有本地户籍,同时较难进入当地单位工作,无法汲取当地住房改革的红利,加之收入较低,往往处在住房阶层的底层。
户籍和单位制度仍是影响住房阶层主要因素。同时,收入和教育这2个反映市场作用的因素显著影响流动人口住房分层,而户籍身份强化了农村流动人口在住房阶层分化中的劣势。在制度与市场2种力量的作用下,低收入农村流动人口较难进入住房市场,农民工和流动儿童难以得到城市住房保障。而有高等教育背景或城市流动人口,有较多的资本购买商品住房,也较容易得到城市住房保障。如近年来大规模的公租房建设,就是针对受过高等教育的新移民和青年群体。因此,当大量农村流动人口仍停留在住房阶层的底部,一部分高学历或城市流动人口在向上流动,使得流动人口的住房阶层产生分异。制度和市场的共同作用使得流动人口住房阶层进一步分化。
流动人口的迁移特征也影响其住房阶层,其原因可能在于地理空间先赋因素的差异与区域不平衡发展。迁移时间越长,流动人口能在流入地积累更多资本,帮助实现阶层跃迁。在迁移距离方面,与长距离流动者相比,短距离迁移的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社会经济背景相类似,流入地与流出地社会经济特征相似,较少受到劳动力市场的排斥,越容易保持在流出地时的住房购买决策,更容易实现住房自有,维续原有的住房阶层;迁移距离越长,尤其是迁入东南部地区的流动人口,更容易完成资本积累,并回迁购房。另一方面,区域之间的不均衡发展持续影响流动人口的迁移选择,并与住房过滤一起推动流动人口住房阶层结构分化。中国东、南部地区以及大城市的住房市场较为发达,房价相对较高,土地供应相对稀缺、购房限制措施严格,而中西部、北部地区以及中小城市住房供应与政策较为宽松、房价较低,推动一部分流动人口倾向于集聚在有利于获得住房资产、改变住房阶层的中西部、北部或中小城市。在这种住房过滤作用下,形成中西部城市一房和户籍地城镇有房阶层居多、东南部大城市无房阶层居多的空间格局。简言之,在制度和市场变迁之外,迁移时空特征和区域发展不平衡是流动人口住房阶层变化的空间机制。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分析中国流动人口住房阶层的特征与空间格局,揭示流动人口住房阶层分化的影响因素和机制。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群体形成三阶五层“土”字形的住房阶层结构。农业户籍流动人口在无房阶层中占比较高,多处在住房阶层的下层,城镇化程度很低。非农户籍流动人口较多拥有户籍地城镇和流入地住房,多处在住房阶层的中上层,并且少数的非农户籍流动人口能够跃迁到最上层的流入地和户籍地多房阶层,表征其较高的城镇化程度。流动人口住房阶层形成南北差异的空间格局,城镇多房和一房阶层多分布在北部和中西部,且多聚集在中小城市,而户籍地城镇有房阶层与无房阶层多分布在东南部和南部,且多聚集在大中城市。
社会经济和制度依然是影响流动人口城镇住房分层的主要因素,流动人口在产权住房的层级特征上,与其社会、经济、政治地位存在高度一致性,户籍、单位制度、党员身份仍是影响流动人口住房阶层分化的重要因素。市场转型使得流动人口的收入和教育程度发生分异,进而影响其住房阶层的分化。在市场化和制度变迁的背景下,户籍、单位制度改革并不彻底且相对滞后,不仅拉大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的差距,同时分化流动人口内部的住房阶层。城镇化和城镇住房保障不均衡发展使非农户籍流动人口更有机会进入城镇住房市场,农业户籍流动人口则多遭遇市场和户籍制度双重挤压,较易被排除在市场和住房保障之外,加剧流动人口住房阶层分化。当前的房地产通过价格、户籍、教育和工作稳定性等因素构成进入市场的门槛,排斥农民工等流动人口进入城镇住房市场。另外,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对象主要是本地户籍居民中的困难群体或引进人才,不包含低学历、低收入的流动人口群体。各大城市在“抢人大战”中,更应将保障性住房分配给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如公交司机和环卫工人,使其突破户籍限制融入城市,弥合流动人口内部的住房阶层分化。
流动距离等空间因素也影响住房分层。流动距离越短,流入地与流出地的社会经济属性越相似,流动人口更有可能维持其原本住房阶层。随着城市规模扩大,非国企流动人口的劣势被强化,农业户籍与非农户籍流动人口之间的阶层分化加剧。不同区域的城市,不仅住房市场存在差异,政策制度也有所不同,影响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使得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在北部和中西部购房以及在中小城市购房,产生按南北地域和城市等级的住房过滤,形成中国流动人口住房阶层南北差异的空间格局。
对于未来的人口城镇化,以住房促流动人口市民化是一条有效路径。流动人口户籍地城镇住房阶层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流出地城镇化的发展,也能推动中西部和中小城市就地城镇化进程。而大力推动流动人口流入地住房阶层的壮大,才能促进流动人口在大城市的异地城镇化,推动住房公平。因此,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存量住房消解与新房建设,必须考虑流动人口住房的空间配置及其住房阶层分化特征,以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
综上,对新型城镇化与住房保障提出政策建议:1)加快户籍和单位制度改革,以较快促进农村流动人口获得城镇产权住房,推动其市民化进程。2)当前的保障房建设应基于地域和城市规模。东南沿海是流动人口无房阶层集聚的区域,应大力建设公租房、安居型商品房和公有产权房3类保障性住房,在取消住房申请户籍限制的同时,针对环卫、交通等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分配保障性住房,缓解农村流动人口的住房困难问题,促进其市民化进程。对于北部和中西部的中小城市,有较多的一房或多房的流动人口,要控制其房地产业的发展,避免经济泡沫;也要谨慎建设保障性住房,主要针对在流入流出地都无房的流动人口提供公租房,并保障较高的居住质量。
此外,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由于数据限制,对不同区域流动人口的住房资产仅做了粗略的描述,未能对产权住房和市场价格进行精确匹配,住房阶层未能完全体现住房资产的市场价值,未来可基于更为精细的数据,将住房价格数据纳入模型分析。其次,数据包括现流入地城镇、流出地城镇、户籍地村与其他地区购房,但不包括流动人口在其他地区的购房信息,东西部地区的村房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与价格不明确等问题,未来可在获取更为丰富数据的基础上,展开进一步研究。
——以北京市2005年和2014年数据的实证分析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