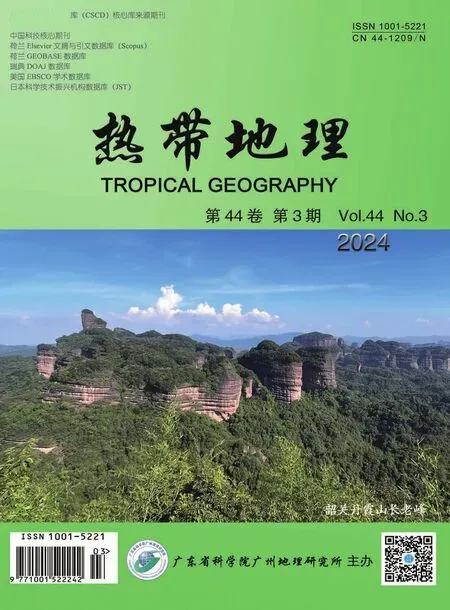基层治理的地域领域化与阶级生命政治的变迁
——以珠海市A镇产业园区为例
李辉霞,陈世熠,胡珏滢,林锦标
(1.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广东 佛山 528000;2.中山大学 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广州 510006;3.云南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昆明 650000)
伴随中国城市化发展模式由空间增量的发展模式向空间存量的治理模式的转向,如何构建有效的现代化治理体系以提高基层治理能力,是当前国家-社会共同体面临的棘手难题(戴欢欢 等,2022)。当前中国城市化模式主要是人口在城市中聚集形成区块,导致城市问题与城乡分异、阶级分化耦合,为城市领域的治理带来诸多难题(王祯等,2022)。
同时目前国内关于微观区域治理的研究,在内容上主要聚焦规划层面上的社区功能构成分析(侯璐璐 等,2020)、管理层面上的空间哲学思考(蓝江,2022)、及治理层面上的经验模式探讨,但仍缺乏对现有规划、管理及治理框架运转过程中的政治逻辑,特别是其背后的国家-社会关系的阐释,导致领域化研究中的政治性不足。在研究方法上,当前仍以“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式探索为主,缺少对地域内主体行动逻辑的理论探讨,造成理论创新能力局限于描述而难以于造成微观区域治理困难的“全能主义”转型对话。
因此,本文从政治下的空间视角出发,首先阐述对领域政治和生命政治、社会资本和领域空间的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社会资本—空间生产—生命政治”的分析框架;继而以珠海市A镇工业园区为例,运用定性分析方法对城市基层地域管治为何出现生命政治嵌入领域化的现象进行剖析;最后结合案例研究结果,对基层地域管治政策提出展望和建议。
1 领域空间中的生命政治
1.1 生命政治中的空间与空间领域中的政治
领域作为一个拥有多重外延的概念,在不同学科中有不同的解释(刘云刚 等,2015a)。在地理学上,领域指现代民族-国家管辖的领土、领海、领空等实体空间(Taylor, 1994)。在文化概念和人类学上,领域是集体身份构建的文化空间,是独特的人类现象(Johnston, 1991)。在政治学上,领域是权力与社会关系交集下的表现体(Cox, 2003)。而萨克认为领域除了具备宏观的国家政治属性外,更存在个人的社会关系调整、权力变化等微观属性(Sack, 1986)。
生命政治的空间视角是关注领域化中主体生命政治的塑造过程,即各主体围绕领域结构的空间竞争机制。刘云刚等(2015b)认为领域的政治化可细分为领域化、再领域化和去领域化3种形式。领域化是政治主体划分边界和生产领域,即规训客体的过程;再领域化是政治客体服从或者策略性抗争的过程。这种形式是依靠政治主体修改空间的权力结构,掌握空间实体来实现的。在城市建设、治理过程中,国家和地方政府塑造空间,实施城市规划、调整行政区域便是自上而下地的领域化(马学广,2010a)。但随着公民社会的扩大,城市空间的开发、修缮、治理也逐步出现公民团体(吴结兵 等,2022)、社会资本(徐苗 等,2010)、民间组织(刘云刚 等,2011)等参与实现再领域化。
在生命政治的理论中,领域化应包含无形的权力生产关系(米歇尔·福柯,2012),即领域化并非韦伯权力观中主体对客体的规训,而是福柯理论的渗透(王鸿宇 等,2021)。这意味着在领域化过程中,资本家、政府等社会强势主体建立领域化的过程都受到历史客观规律的影响,而非自我意识的绝对支配(米歇尔·福柯,2018)。这种学术路径强调领域化是从身份作为起点,即普通群众先成为公民、人民后,主动参与或被动参与到工厂、居委会的治理中。因此,本文认为理解领域理论需引入国家-社会关系,讨论生命政治如何受到空间分布的影响。
生命政治下的领域理论应包含国家-社会关系的渗透、标准化、结构运转和去结构化4个部分(图1)。领域化理论的开端是国家向基层延伸完成渗透能力建设的过程,即现代国家城市化完成基层控制能力的过程(安东尼·吉登斯,1998)。在初步领域化中,国家作为绝对强势的政治主体,以资本密集型或强制密集型的现代国家构建模式赋予群众以公民身份,由此公民从政治客体转化为国家共同体的主体(蒂利,2012)。这使领域化的过程存在显像性和隐像性(肖滨,2021),即微观视角下个体力量的抗争具有巨大作用;但在宏观环境下,“机制”对这些主体力量有明确的建构作用,主体并非随完全的自我意志而行动。

图1 生命政治视角下的领域化理论Fig.1 Theories of domaining in a life-political perspective
在完成上述的渗透过程后,国家面临如下问题:公民通过公民权利、义务获得一致的生命起点,但身份的赋予并无法使普通群众具有行使身份的能力。如何通过标准使个体的生命历程符合国家统一的构建,而不是个体脱离国家,就需要标准化的过程(摩根索,2006)。因此,国家在领域边界内的治理不仅需要通过渗透完成下沉,更需要构建标准意识形态,才能在后续进行结构运转中实现国家共同体的保持。
在国家完成了超大范围的渗透和标准化后,则存在超大型国家统一性与地方多样性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代表公民处在不同地域必然经历不同的生命政治,必须完成微观自治,从而降低超大型国家的常态化成本,避免国家权力的内卷化(周雪光,2019)。于是国家建构“结构”后,区域内部需展开后续领域化的工作。结构奠定了社会资本—空间关系—生命政治三方耦合互动机制的基础(斯考切波,2007)。在后续领域化中,强势方通过暴力、强权、政商关系获取社会资本的优势,成为空间塑造中的强势方。强势方依照资本密集的生产逻辑,塑造对其有利的空间格局,并管理弱势方生产、生活的空间。这种管理模式使弱势方由国家建设的主体转为社会建设的被动方,弱势方对权力的获取能力也逐渐减弱,最终影响个人生命政治。
再领域化,即弱势方反对社会主体争夺的过程(Lefebvre, 2021)。弱势方通过国家的财政、政策支持得以改善空间生产关系中的劣势局面。在公民权利的影响下,获取社会资本对自身生命政治加以改善。再领域化是弱势方在政治体制内完成的,其并未跨越标准化制造的框架。最后,去领域化是弱势方以革命形态破坏原有的领域内附属的权力关系(安东尼·吉登斯,2000),借助社会资本的重塑再次打造不同的生命政治,改变上层建筑形态,从而重塑生命政治,再次成为共同体中的主人。
1.2 社会生产关系与空间领域化治理的历史演变
社会生产关系是以社会资本为基础构建的物质生产、意识形态的生产关系(丰子义,2022)。社会资本是集体或者个体嵌入社会网络获取社会资源,从而获得回馈的构造物(Knight and Yueh,2008)。强势方通过社会资本产生的社会网络在“结构”内对弱势方进行生命政治的统治。而社会资本的创造与个体的人际行为有重要关系,即影响生命政治(李晓光 等,2022)。
社会生产关系对生命政治与空间生产的领域化关系研究的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社会生产关系的分析方式在宏观上决定主客体需遵从生产力的发展规律,在微观上揭示个体行为背后的必然性规律。因此,在进入对具体场域领域化前,必须对中国空间领域化过程是如何受到社会生产关系影响的问题进行梳理。
建国初期,中国需要完善对领域“渗透”“标准化”从而实现现代国家建设的任务,更需要以这两个任务的完成推动工业化的发展。这一背景使“单位制”的推行符合“资本密集”对空间生产关系的要求:以计划方式调动人力来弥补社会资本的不足。因此计划性的生产关系促使领域管理体制的单位制和人民公社体制改革,以实现国家制定的“一化三改”的目标(温铁军 等,2019)。同时,由于“鞍钢宪法”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用于治理工厂生产和社区管理,使塑造共同体关系需要依靠单位社会的封闭性实现。“单位社会”形成独特的共同体(施雪华 等,2021),既满足人衣食住行的需求,也由此完成社会的稳定控制(马学广,2010b)。
20 世纪90 年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改变了生产关系,这使单位制的力量逐渐削弱。资本生产的机制同样以人口密集的方式协调资本密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作,此时劳动生产需要工人在衣食住行方面做出一定改变。于是工人的生命政治轨迹也从原本的“单位主人”,转变为对工厂宿舍的依附(汪晖,2014)。值得注意的是,单位制的减少并不代表国家初步领域化的失效,现代国家的基础构建仍存在,这也是各式社区依旧存在封闭性,同时中国司法、行政、党建的力量能深入基层也是很好的证明。这种削弱主要来源于国家能力与交易治理成本的考量,而腾出的空间产生社会主体竞争(周黎安,2022),有了完整的领域化构建。于是,伴随着地方政府逐渐公司化,社区制度的建设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地方政府退出社区的基本治理,转而交由社区-居委会-物业等社会资本的强势方完成基层的日常形态治理(杜洁 等,2017;沈洁 等,2021)。这种空间领域化的完全完成,也正式标志公民生命政治活动由主体化向专业客体化转变,政治事务的管理转变为行政-理性事务的关系(高天驹,2022)。
但街居体制与社区制并未有特殊的耦合反应,同时也未促成公民社会的快速发展,反而在国家管治的基本单元上衰落,致使社区制徒有其表(肖林,2011)。在人员的管理上,社会组织也出现借以公共权威治理社区或者基层地域单位的权威转让现象。权威转让的产生致使阶级的管理方式由上述经济依附转为彻底的依附关系。但权威转让造成处理紧急公共事件或监管、治理常态化时,容易出现社会组织或非行政单位“越位”现象,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周雪光,2011)。
从领域化的过程看,中国的基层社会的治理是以单位制带来的国家能力(Mann, 1986)为基础的领域体系。如图2所示,行政机关在基层社会的治理主要是依靠单位制带来的初步领域化,从而实现经济帮扶、司法保障、政治稳定等效能。而完全领域化的实现是在初步领域化的基础上,由社会组织、半官方单位、市场主体完成的,这些领域化的区域主要包括商业设施、商品房住区、工厂厂区等。这些社会强势主体在斗争中借助社会资本的优势完成对空间生产的优先权,成功塑造独特的碎片化管辖区域(You-Tien, 2010)。而弱势群体也从空间的主体性中抽离变成空间中带有依附性的客体。最后,在碎片化与地方政府公司化的背景下,社会主体完成再领域化,弱势群体从依附性客体转变为完全性客体(Hsing, 2012)。弱势方不仅接受行政机关在领域化中建构的治理,也需要在强势方再领域化构建的场域接受管理。

图2 中国空间领域化的变迁Fig.2 The changing face of spatial domaining in China
2 珠海市A镇产业园区的领域化
本文以珠海市A镇的A产业园区为例,详细解析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领域化过程和不同阶级的生命政治变化。其中领域化过程可看作是国家完成领域化,市场主体再领域化,国家介入与公众参与下的再领域化和去领域化。
2.1 案例地及调查概述
A产业园区借助金湾区的产业政策,以及借助大湾区的区位条件、完善的基础设施、及相关政策条件,成功吸引众多企业入驻。据工业园区管理机构统计,园区总人数约980 余人,目前累计进驻数十家实体企业。A产业园区是较为典型且大型的产业园区。园区内不仅拥有先进的生产设备和管理设备,还包含了居住设施、生活设施等,由此可构建出领域化过程。
笔者于2022年进入A镇开展扎根调查,分别于2022 年6—7、9—10、11—12 月共3个阶段对该A 镇A 产业园区(图3)以及周边工厂的产业发展状况和工人生计展开定性研究:第一阶段,与珠海市相关市政府部门和镇政府进行座谈;第二阶段,对A产业园区内的3个居民社区中部分企业的工人进行访谈,以了解基层管理状况和工人生计现状;第三阶段,针对A产业园区和周边企业的工作人员展开无结构式访谈,此后根据38 组无结构访谈的结果设计半结构化访谈的问卷,再有针对性地展开半结构化访谈。通过系统抽样,对128人展开半结构式访谈,其中访谈有效资料为114份,有效率达89.06%。在此基础上,形成对珠海市A 镇产业发展区域的领域化和生命政治变迁的综合认识。访谈问卷调查样本和访谈对象基本信息见表1、2。

表1 访谈问卷调查样本基本信息Table 1 Survey questionnaire samples

表2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Table 2 Survey interview samples

图3 珠海市A产业园地理位置Fig.3 Location of the A Industrial Park in Zhuhai
以工资收入、工作场域内地位为基本划分依据(埃里克·奥林·赖特,2008),根据调查样本工资收入的分布特征确定阶级划分标准,对128个访谈者的阶层身份进行划分(表3),其中低收入阶层68人、中等收入阶层43人、高收入阶层27人。

表3 阶级划分标准Table 3 Survey interview samples
2.2 以政府为主体的领域化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以土地改革和集体经济建设的方式完成领域层面的渗透和标准化。初步领域阶段建立了以人民公社为基础的领域化,并且完成了基础的司法、行政控制,实现了国家对基层的控制(陈国涛 等,2022)。“广东省国营A 镇机械农场”的正式建立也标志国家以集体经济制度的方式渗透A镇产业的领域化初步完成,国家在产业区域内管理工人的生活资料、生产资料,工人的教育、社会保障、文化等方面都以“合作主义”的方式被纳入国家建立的人民公社中。该时期,国家在领域内具有极强的存在感和控制力。
“我们当时全部都是有组织,像看病呀、吃饭呀上面都分配好了,我们平时参与表决。像日常的管理运转,(生产队)队长会搞定。”
——PS2209-03普通工人
初步领域化的过程中,有大量的知青参与到A镇农场的建设中,在该过程中,A镇机械农场逐渐成为全国著名的甘蔗生产基地。同时,A镇糖厂也完成了建设,村民由农民转为工人。A镇糖厂的建设得以将更多村民的管理纳入国家初步领域化的过程中,村民形成了工厂—村民、党组—村民、政府—村民等3 种联系状态。在1978 年后,“广东省国营A镇机械农场”改名为“A 镇华侨农场”,同时,A镇糖厂的管理权也逐渐收归地方政府所有。同时,国家大规模的管理基本退场,初步领域化留下的基础性成果,被地方政府和乡镇企业收揽。
“当时厂里就没怎么分配东西了,以前有很多“福利”,后来就没什么了……管理当时换了人,没有大队呀那些组织了,但大家当时都还是在那工作只不过厂子里没提供那么多东西了。”
——PS2208-01工人
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珠海市经济特区的建立使得珠海市政府进入了公司化模式,并且在领导班子的决定下,珠海市推动全市土地国有化。地方政府加入社会主体竞争,并完成土地的全面国有化,使得土地在集体和个人身上的功能效用减少,这也致使珠海市出现政府作为强势方的第一次再领域化的形式。
“我们用地的时候政府存在感一直很强,像什么建新房报批都要和他们报备,所以我们也很难建新房,不像佛山那些城市一样。”
——PS2210-05村民
2.3 以资本为主体的再领域化建设
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推进,A镇的产业从原有的国有企业、市属企业向社会企业转变,这也标志工人生命政治归属的变化,但这些都是基于国家完成领域化的基本结构所产生的。领域的资本化进程与A 镇产业多样化的建设是同步的,如船舶、电子、家电等。而产业园的布置在生活和经济上重新提供务工者劳动的机会,工人的生产所需都在产业园的内部完成。这一部分可被认为是再领域化,港澳侨商、存有资本的商人成为社会生产关系的强势方。强势方在国家退出基层直接管制时,通过地方政府对资本的需求影响产业园、地块用地、公共设施等的选择,同时也形成对工业园的管理。
调研中发现工业园实际以低成本的内部运作和管理逻辑取代政府的日常管理形态。除了违法犯罪、法律援助等司法问题,大多数工人的日常活动是在产业园内展开,而工人也因产业园提供宿舍、伙食等条件,需要承担执勤、打扫等职责。这些通过交易的形式提供生活服务等,营造出以市场为主体的权力空间。有一位工人在采访中表示:
“我们平常就待在园区里面,也比较少出门,很多事情都是老板定好的规矩,我们照做就是了……老板说在这住的,大家一起打扫一下卫生、看一下大门安全。”
与本科类中外合作办学相比,专科层次的中外合作办学往往在办学定位等方面十分尴尬,许多报考高职中外合作办学的学生都是因为在国内没有学校可以上或者是想留在较发达地区就读,很少有人能真正出国留学,真正奔着留学目的的学生几乎是凤毛麟角,而实际上有意愿报考此类项目的考生往往在语言能力和经济实力等方面比较尴尬,这就使得当前不少高职院校开办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沦为鸡肋”,有名无实,难以得到学生、家长乃至社会的认可。
——LL2210-05普通工人
受到新集体经济的影响,A镇建立了资源资产公司对全镇的“二级市场”进行管辖和调整。资源资产公司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弱势方被纳入庞大集体,可以借助谈判、协商等方式对广场、村落绿化、生产设施等宏观上的布置进行调整,而不是完全随着资方投资的计划走。因此,资源资产公司的创建可认为是政府通过注入资本,赋予弱势方社会资本,使其能拥有改善空间关系的可能,从而构建更为优良的环境,以实现个人生活的提升。
“政府创建资源资产公司以后,我们有机会参与A镇各个项目的决策,到底怎么建、建什么我们有了知情权。虽然我们可能没他们有文化,但起码我们可以提一下大多数人的意见。”
——HP2209-02 村民
资源资产公司的创建确实有助于提升推动再领域化,实现更为公平的公共空间分配,达成初步平等的生命政治。但资源资产公司是基于直接收集资源形成的“二级市场”,由于“一级市场”的缺乏以及资源资产公司的市场属性,依旧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在利润面前,人民再次回到弱势方的可能。
总结以上历史变迁可发现,A镇产业园的社会生产关系实质是从早期工人—村社—政府的三重主体关系向工人—厂区—政府的关系转变。在该关系下,工人在生活和生产领域依赖厂区塑造的空间,而政府则提供公共服务设施、社区服务设施等。工人的生命政治也主要嵌入于厂区所营造的生产空间中,工人—厂区—政府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纵向关系,只有在厂区无法提供时才会出现工人跳出厂区空间诉求于政府的情况。相比之下,由于土地国有化的全面实施,社会群体缺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与厂区抗争,因此并没有出现以社会弱势方通过改变空间生产关系实现的再领域化,更不可能存在弱势方借助土地生产走出原有结构的去领域化。
3 珠海市A 镇产业园区生命政治的变迁
基于生命政治视角下的领域化理论(见图1),本文认为领域化主要表现为空间生产关系改变-社会资本争夺-生命政治变迁的过程逻辑。通过对A镇产业园区领域化过程的梳理,着重介绍在国家完成领域化后,以市场为主导的再领域化力量如何改变社会资本的积累和生命政治的变迁。
3.1 社会资本的地缘积累
整理问卷和访谈资料,将工人、中层员工、高层董事的相关信息绘制成图。如图4所示,随着产业园区内职工的阶层不断提升,居住点与产业园区的距离不断增大。工人通常在产业园区分配的宿舍或周边社区居住,而中层员工和高层董事居住地点离产业园区距离则相对更大。这种悬殊的空间关系扩大了社会资本分配的不平均,然而这并非是强势方有意识地规划设计,而是社会斗争中形成的以资本为中心框架的必然结果(见图4)。

图4 珠海市A产业园区不同阶层的生活点分布Fig.4 The distribution of living points of different classes in A Industrial Park, Zhuhai
这种框架下的社会资本分配使得工人在教育、医疗以及生活体验上的不同,这种不同也塑造了层级之间很难产生交互性的社会资本。同时这种社会资本实质只可能在阶级内部运作,社会资本出现了地缘上的积累差异。

图5 珠海市A产业园区不同阶层周末外出的距离(a)和频率(b)Fig.5 The distance(a) and frequency(b) of different classes going out on weekends in Zhuhai A Industrial Park
这表明在一定程度上阶层与周末生活的丰富性有线性的相关性,大多数普通工人的周末生活更为单调或者缺少周末社会交际活动。同时,在出行距离上,普通工人也远低于另外2 个阶层的人群,即他们的周末更多是在工厂宿舍中度过的。值得关注的是,普通工人中不同交往人群和带来的生命体验的不一致也造成社会资本积累的断裂,即随着阶层的逐渐向下,同个阶层的社交活动逐渐减少、社交活动所创造的的社会资本也逐渐减少。
当然并不是所有普通工人周末都在宿舍居住,也有年轻人尝试突破地缘边界,周末常在市区内部活动。但这为他们的生活带来较高的社交成本,导致生活压力上升。这些活动更多也是以消费的形式存在,但并没有将参与活动的年轻工人拉入市区的生活,反而因为参与了大量活动后,日常生活更加拮据。因此,来自不同领域的生命主体在尝试对其他领域的公共服务或社会服务展开体验后,便容易回到更穷迫的困境中,从而更难以维系社会网络。有一位年轻的工人边说道:
“我周六日也很常到市区找朋友玩或者去看看电影什么的。但市区消费太高了,而且离我们住的地方很远,来回就要花上很长时间。这种活动方式开销太大了,像我们这种工人的工资根本撑不住多久,就没钱了。”
—— SK2301-02普通工人
而领域政治产生社会资本积累方式的地缘化分异,带来不同区域以阶级为特征的领域化过程。不同的阶层在以资本累积作为驱动力的城市中被自觉地分化到不同的“社群”,“社群”的交互网络带来不同社区内部关系的不一致,也影响不同阶层在“结构”中对意识形态和自我认识的看法。这种领域化外部的差异比领域化内部的结果影响更为明显,而这种差异更为深刻的影响是推动不同阶级生命政治角色的变迁。
3.2 生命政治角色的变迁
在社会资本积累和空间关系的影响下,不同阶级的生命政治角色产生主体性变化。在国家后续领域化的过程中,“国营A 镇机械农场”和A 镇糖厂是以工人作为生产阶级在厂区内活动的,虽然工人需要依靠“三重依附”的关系才能完成领域内的活动,但工人可以依靠“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实现在场内的自我决定与参与厂内生产事务。有一位在厂内工作的老工人说:
“当时大家都是把厂子当家看,虽然不在那里住,但是都很有感情……当时厂子里面做决定会开会,把大家都叫来一起决定要不要做。不管你是技术专家、工人还是队长,那都一样的,大家就像整个厂子里的主人。”
——PS2208-01普通工人
这种“主人翁”的生命角色实质上依赖于国家初步领域化的建设,工人被赋予共和国公民的平等角色。而“结构”的框架跳跃出资本运转的“市场逻辑”使得工人的主体性得到增强,同时全体职工的平等劳动和“单位社群主义”体系(李怀印 等,2017)使社会资本出现互惠现象,工人实质上无需依赖于其他客体,即可成为自身的“决定者”。除此之外,工人通过参与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参与基层治理,是为数不多的中国领域化治理中出现社会群体作为强势方的时期。
“工会还有职工会(即职工代表大会)都是大家选出来的,每年又给我们争取很多福利……他们也可以帮我们和领导提意见,工会也总有办法让领导听我们提的意见。像附近(指周围的村)出了事,工会就会组织我们去帮忙,帮一些老乡修一下房子,收(甘蔗)的时候帮帮”。
——PS2208-02普通工人
在20 世纪80、90 年代后,农场和糖厂的经营转交给不同的分管单位。随着地方市场公司化的进程,两者回到“市场逻辑”,工人从生活、政治、经济的归属转变为对工厂的经济依附。工人不再作为主体存在于工厂的运作逻辑中,这也意味者工人需要依靠外部关系来获取社会主体性的存在意识。因此,社会资本的获取不再是工人的工会、代表会议,而是需要依靠对外的社交。
不过在该时期,工厂的员工更多是本地人为主,因此当自身劳动和经济价值不再代表主体性地位时,工人的身份能在村中获得认同和尊重,由此在村内的基层选举或者事务管理中起主体作用。
“那时候厂里工会倒还是有,只不过职工会(即职工代表大会)没了,普通工人的话确实说不上什么话了,毕竟管理还是他们那些有知识的人更在行嘛……”
——PS2209-03普通工人
“我们虽然在村里面说不上什么话,但是我们回到村里面很受人尊敬的。而且当时在搞乡镇企业,我们这些在有工作经验的老工人可以参与村里面事务的管理,像有个工人就被选成了村长,我以前也干过村干部”。
—— PS2208-02普通工人
A镇产业园区的第一次再领域化便是在这种环境下进行的,地方政府受到分税制和发展绩效的鼓动,推动产业园的管理从行政领域走向市场管理。再领域化的推动与上述材料所述相似,生命政治的诉求外化,工人的生命政治开始出现断裂,在经济上依赖于工厂的赋予成为客体,而政治上通过村内认同依旧保存着主体认知。
随着地方政府公司化和产业竞争的加剧,A镇糖厂和农场都退出了A镇产业园区的舞台,转而代之的是其他更具规模效应的其他企业。产业的变化在工人身份也出现了其他特征,即产业规模增大,吸收了更多的外地工人。这给工人的生计活动带来不一样的变化:以纯经济为纽带的社群关系逐渐替代了原地缘关系等为纽带的社群、团体关系。
而这种变化带来的是工人的经济、生活、管理全方位都在厂区内部完成活动,特别是大多数普通工人外出活动频次低的情况下(见图5),工人的生命政治从经济依附状态转向全面的依附。工人的全面依附意味者中层管理者对普通工人的全面管理。但第二次的再领域化是在初步领域化形成的“结构”中实现的,企业不可能尝试推翻国家对标准化的建设,自我建立执法、行政事务。因此,作为强势方的资本对区域的领域化都是以隐形的“权威转让”实现的。
企业需要对工人活动的直属管理权,而地方政府作为行政发包体制中的管理方希望降低行政成本(Vafai, 2005),这种“交易成本理性”(Oliver,1985)促使双方完成产业园区隐形的领域化。产业园需要对工人生活、行径量化管理,从而降低企业经营管理的成本,地方政府希望借助产业园减少下渗基层的成本,于是地方政府转交部分管理权威给企业,从而达成“权威转让”。而这种转让在疫情期间格外明显。
“当时(疫情期间)很少能够出门,厂里面不让我们出去,有个厂听说有在外面住的员工也被主任要求回宿舍住不能外出”。
——JQ2210-01普通工人
“企业当时要求我们上报所有行程还有每次出入都要检查粤康码的状态,如果不去做核酸就要扣钱或者被开除”。
——SW2210-01普通工人
工人的生命政治也被权威转让的方式纳入工业园区中,即阶级内部很难跨地缘产生社会资本。同时,工人以社会运动的方式只改变了原有的空间生产关系,并未改变资本运作的“再领域化”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弱势方实现去领域化的可能性较低。在工人完成“全面依附”的生命政治历程中,区域的领域政治也完成了“政治强力-资本经营”的第二次再领域化。资本借助政治强力的权威转让实现了对特殊区域的管理,这种管理与波兰尼的经济、社会的“嵌入关系”相似(Bandelj, 2020)。资本嵌入社会过程影响了社会的其他方面,而工人也从早期的经济依附转化为全面依附。当这种现象越明显,公民社会的成长性越弱,自然也不存在社会团体参与公民治理的可能性,这也是为何在相似的领域内,社区建设失败的原因。
综上,在国家逐渐褪去“全能主义”的色彩后,地方政府获得了相当大的剩余控制权。在激励与压力的背景下,地方政府推动了土地财政,使得地理分异影响了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的分布。更高昂的地价便包含了更昂贵的公共服务,地方政府在国家构建的初步领域化上对照土地价格完成了第二次的领域化。而需要大量廉价土地的工厂,自然被分隔至土地价格便宜的地区,形成与昂贵地区不相同的领域。其次是管理方式的嬗变,从技术手段上构建了工人在领域化过程中的地位。这使得工人居住在工厂的生活与那些非工人居住在其他地区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背后扭曲了工人原本应该具有的基本服务和社会参与热情,改变了工人的生命政治历程。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工人生命政治变迁和社会资本变化2个视角引入领域化过程的分析,并基于中国基层治理的现实情况建立了社会资本—空间关系—生命政治三方耦合互动的领域政治框架。从生命政治的视角看,以国家主导的领域化过程,为工人带来主体身份上的认同;而后续地方政府公司化带来的资本密集型的城市化,导致出现第二次的再领域化,产生权威转移的现象。以上认识在珠海市A镇的产业园区研究案例中得到印证。不同年代的工人经历了“自我主体-经济依附-全面依附”的生命政治历程,伴随全面依附关系的形成,空间关系也形成了“政治强力-强势方(资本)经营”的领域化图景。而这种图景实质是经济嵌入社会过程中的“反噬”,带来公民社会的羸弱。这也是本文认为同样的理论可以用于解释社区制度建设失败的原因。
本文为理解城市空间正义和工人生计演变提供了地理论视角,不同阶层的生命政治具有空间特征,而领域在不同的阶段具有可分性,不同阶层的领域受到土地、公共服务等多重方面的影响。另外,国家与社会视角的切入让人们认识到任何阶层都是在“结构”的框架内依照标准化的意识行动的,在资本为中心的现行生产力条件下,最符合资本密集和推动生产的空间结构也正是以工人“全面依附”为代价实现的。而实体化的个人只是作为领域化过程中推动的具象主体而非意识的发生者。而这种过程的发生是带有资本发展的必然性的,这也是A镇的产业园区能为研究基层治理中领域政治如何影响空间生产关系这个科学命题提供案例借鉴的原因。
因此,在国家能力允许的情况下,应对工人生命政治的主体性进行恢复。一方面,国家应搭建好基层治理的框架,让主体的任何一方都可以通过空间关系改善实现领域结构的改造,使得阶级冲突和空间冲突得以内化。如推动工人组建权益维护类的组织,并为组织提供活动基金、确定其合法地位、权利范围和搭建政府—企业—民间组织的渠道。因此将现代国家的“参与”“分配”制度完善是深化改革治理体系的重要方向。特别是空间规划中的公众参与机制,政府应该加强权责统一,完善不同层级体系的任务分管,从现行空间政策混乱管辖者的局面中走出来,让各级政府有更明确的定位。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应注重以人为本的空间生产关系,推动弱势方的生产关系在政治领域的平等化。诚如,政府与外界社会组织提供相应的法律、经济的援助,并对弱势方单独召开相关规划的讨论会议等。以此,才能培养公民社会的力量,完善国家-社会的耦合体系。
本文也存在部分不足:1)研究过程中未考虑企业类型对空间关系和工人生命政治的影响,本文选取企业都是实体产业而并未考虑以服务为主要业务的企业。2)本文重点关注的是城市内部的空间生产关系变化,对当前发展型政府带来的“绩效效应”关注不足。受到地方政府公司化影响,产业同质竞争可能压缩基础设施,导致工人生计问题更加严重,加剧空间不正义;也有可能推动地方政府实施产业转型政策,推动工人生活改善。未来可从产业类型、城市竞争关系和其他行业的格局演变等方面拓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