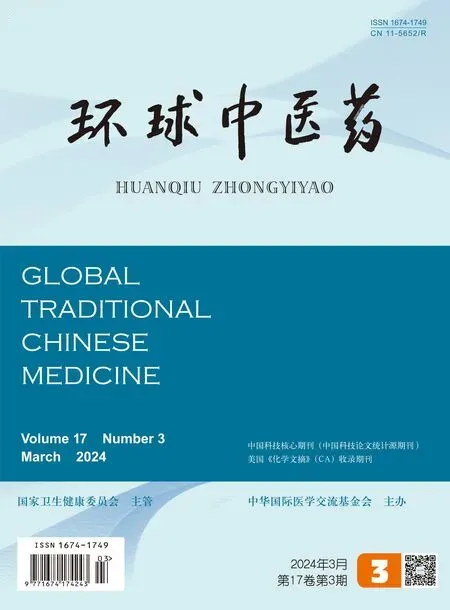基于中医理论结合药理探讨《伤寒论》中的麻黄发汗禁忌
练志润 张家蔚 何剑峰 赵子珺 杨保林
麻黄药性峻烈,发散阳气,耗伤津液,服之有致虚、化热、动风(令人筋惕肉瞤)诸弊,禁忌症及不良反应多。纵使张仲景著书惜墨如金,亦不厌其烦地记录下关于“不可汗”诸条文30余条,关乎生死,不可不重视。其中“淋家”“疮家”“亡血家”“少阴病”“少阳病”不可汗等告诫,皆另有深意,乃阴阳寒热虚实的笼统解释所不能窥及。本文结合现代医学及药理学知识,与临床经验、中医文献记载互参,以落到实处的精神对张仲景“不可汗”诸条文进行重新解读,归纳出在临床具有可操作性的麻黄发汗禁忌,讨论其中的内在规律。
1 《伤寒论》中关于麻黄发汗禁忌的条文归纳
本文将《伤寒论》“不可汗”的条文分为麻黄禁忌症、麻黄慎用症、伤寒鉴别症三类(详见表1~3)。

表1 《伤寒论》麻黄禁忌症归纳表

表2 《伤寒论》麻黄慎用症归纳表

表3 《伤寒论》麻黄相关伤寒鉴别症归纳表
(1)麻黄禁忌症:麻黄禁忌症是指建议避免使用麻黄的情况,若使用麻黄有较大概率导致相对严重且不易挽回的医疗不良事件甚至死亡。
(2)麻黄慎用症:麻黄慎用症是指有机会使用麻黄,但麻黄在该个体出现不良反应的风险增加,使用时需予警惕的情况,建议适当配伍,积极观察及随访,必要时及时停药。
(3)伤寒鉴别症:伤寒鉴别症是指形似伤寒(有发热、恶寒、无汗、头身痛等证),但实际上属于其他感染性疾病且不可用麻黄发汗的情况,需与伤寒进行鉴别。
2 麻黄“耗伤津液”及有关禁用汗法的条文释义
2.1 发汗利尿是麻黄“耗伤津液”的主要药理学基础
中医理论认为麻黄性刚燥,过用、误用皆易耗伤津液,其药理学基础主要包括麻黄可发汗、利尿两部分。麻黄具有发汗作用,其发汗主要有效部位为挥发油及醇提部位[6]。发汗过程中阳气、津液皆受损,如《伤寒论》在大青龙汤方后注载“若复服,汗多亡阳,遂虚,恶风,烦躁,不得眠”,又如“复发汗,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人体体表存在约200~400万个汗腺,每小时排汗量最大可达2升,蒸发这些水分需要每分钟大于18 kcal的能量,为人体提供散热功能[7]。故麻黄在发汗退热的同时,亦可能导致体液流失,严重的时候可能导致有效循环血容量不足而休克,故张仲景反复强调“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脉微弱,汗出恶风者,不可服之,服之则厥逆”。另一方面,麻黄具有利尿作用,研究表明0.5~1.0 mg/kg的d-伪麻黄碱可令麻醉犬尿量增加2~5倍[1],可进一步加大体液丢失相关的风险。
2.2 脓毒性休克病系少阴,不可发汗
脓毒症指机体对感染反应失调所致的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碍,脓毒性休克被定义为脓毒症合并出现严重的循环障碍和细胞代谢紊乱[8]。考虑到《伤寒论》的少阴病涉及恶寒、息高、吐利、小便难、眩冒、躁烦等心、肺、消化道、肾、脑等多脏器功能障碍,脉微细,但欲寐、肢冷等循环障碍,有理由相信脓毒症及脓毒性休克是《伤寒论·少阴病篇》论述的核心问题之一[9]。少阴病的本质为机体水火两衰, 真水耗竭无以充盈血脉,真阳衰微无以鼓动血脉,故见脉微细,阴阳亏虚无以养神,故见但欲寐[10]。张仲景多次强调了少阴病不可发汗的临床经验,如“少阴病,脉细沉数,不可发汗”“少阴病,脉微,不可发汗”,其原因在于麻黄发汗会进一步耗伤本已殆尽的真水元阳;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看,“脉细沉数”“脉微”已提示血容量不足、循环障碍,属于休克或休克前期,再投麻黄发汗利尿无异于抱薪救火。故张仲景仅仅在少阴病初期真水元阳尚未竭尽之时使用麻黄附子细辛汤等方解表,且不强调温覆取汗。
2.3 低血容量性休克属亡血亡津液,不可发汗
低血容量性休克是指有效循环血容量丢失所致的休克,常见病因为失血、吐泻、脱水等,从中医理论角度讲乃亡血亡津液。津血本是同源,所谓“夺血者无汗,夺汗则无血”,津血任意一方的严重耗伤皆不可再用麻黄进一步耗散津液,否则容易加重循环障碍,故仲景有“亡血家不可发汗,发汗则寒栗而振”的告诫。
3 麻黄“发越阳气”及有关禁用汗法的条文释义
3.1 交感神经兴奋作用是麻黄“发越阳气”的重要药理学基础
麻黄碱是麻黄的主要有效成分之一,具有类似肾上腺素的交感神经兴奋作用,是麻黄“发越阳气”的重要药理学基础。麻黄碱在机体内可直接激动肾上腺素受体,间接促进去甲肾上腺素神经递质释放,继而产生心率增快,心输出量增加、皮肤及腹腔血管收缩,血压升高、胃肠运动减弱,消化液分泌减弱、膀胱逼尿肌舒张,尿道内括约肌收缩、汗腺分泌增多等一系列作用[3]。麻黄碱的类肾上腺素药作用是产生麻黄不良反应及相关禁忌症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包括心律失常、心衰、高血压、腹胀便秘、排尿困难、汗出等[1],与张仲景所言“不可汗”条文有密切关联,例如“脉浮数……身重心悸者,不可发汗”“汗家不可发汗”等。在上述情况下使用麻黄可能加剧原本的病理过程。因此经典的交感、副交感神经系统理论是临床使用麻黄或麻黄制剂时的重要参考。
3.2 麻黄可诱发或加重心衰,急性心力衰竭患者不建议使用
麻黄碱作用于α受体、β1受体,导致外周血管阻力增高,心脏负荷、心肌耗氧量增加,继而可能诱发或加重急性心力衰竭,对于有基础心脏病或老年患者尤当注意,急性心衰患者建议避免使用。《金匮要略》载“青龙汤下已,多唾口燥,寸脉沉,尺脉微,手足厥逆,气从少腹上冲胸咽……小便难”即是在描述服用青龙汤(即麻黄类方)后出现急性心力衰竭的情况。张仲景在小青龙汤方后注中提到“若喘,去麻黄加杏仁半升”,《千金》认为是避麻黄发越阳气之弊端,追其根源可能与麻黄可加重心衰有密切关系。
4 关于虚证与麻黄之间关系的讨论
4.1 “虚证不用麻黄”的观点过于笼统,限制了麻黄的使用
麻黄是否适用于虚证历来存在争议[11],历代医家及当今释本多倾向于虚证(包括阴虚、阳虚、气虚、血虚)不用麻黄[12-13],且《伤寒论》亦有相关条文佐证。笔者认为,张仲景所说的“里虚”“阴阳俱虚”“亡阳”等不可汗条例皆有特定范围、特定所指(如前所述),不可简单归纳为“一切虚证皆不可用麻黄”。“虚证不用麻黄”的观点因过于笼统而没必要地削减了麻黄的适用范围,导致许多医者不敢使用麻黄,或不考虑使用麻黄,严重限制麻黄的使用。实际临床中,在合理配伍的前提下麻黄可广泛用于多种虚证的治疗[11],如《伤寒论》的麻黄附子细辛汤、麻黄升麻汤等方即是明证。
4.2 虚证有机会使用麻黄,但相关风险增加
鉴于少部分虚证患者的确对麻黄反应敏感,但又不应简单将虚证列为麻黄的禁忌症,笔者将“虚寒、虚弱、高龄患者”列为一组代表体质偏羸弱但未满足重度虚劳的标准的患者,将其归为麻黄慎用症,表示这类患者使用麻黄时相关不良反应发生风险相对增高,临床需予警惕。但这并不意味着麻黄在这类患者中无用武之地,相反是在建议若病情需要可试用麻黄。对于严重虚劳的患者,已属于张仲景所言“阴阳俱虚”者,遵张仲景意不予“汗吐下”之法,列为麻黄禁忌症。年轻、体质壮实者对麻黄多耐受良好[14],可放心使用。
5 伤寒鉴别症的本质不是外感表证,不建议用麻黄发汗
广义伤寒是外感热病的总称,属于感染性疾病,《难经》将广义伤寒分为中风、伤寒、湿温、热病、温病五类。《伤寒论》使用大量的篇幅谈论太阳伤寒与其他外感热病的鉴别,多以“……不可汗”“发汗则……”的形式表达,如“少阳不可发汗,发汗则谵语……胃不和,烦而悸”等。这类不可用麻黄发汗的伤寒类似症,主要包括温病、热病、阳明病、少阳病、疮家、淋家等,细品其文义,这类“不可汗”更多是针对疾病本身的鉴别,而非禁忌症这种否定性的条件。这类伤寒类似症的共性为皆属于感染性疾病,具有与伤寒、太阳证、麻黄证相似的临床表现(如发热、恶寒、身痛等证),但都不宜使用麻黄类方发汗,若发汗则或治疗无效,或使病情传变增剧。例如裴永清先生认为,淋家(包括泌尿系感染等)、疮家(包括毛囊感染、多发性疖肿、丹毒、创伤后感染等)疾病本身即可出现发热、恶寒、身痛等证,但这些症状不可归为外感病而治以解表发汗之法,而当视为鉴别之法[4]。
6 麻黄发汗禁忌在临床运用中的讨论
6.1 外感伤寒与内伤杂病用麻黄的态度不同
6.1.1 外感伤寒使用麻黄宜“中病即止” 伤寒乃外邪来犯,发病急骤,易于传变,若邪气内陷,脏腑伤损,阳气、津液耗伤,则变证迭出,若错过发汗时机,或在不正确的时机发汗,或发汗太过,皆可导致坏病。对于外感伤寒疾病而言,麻黄的发汗时间窗相对较窄,使用麻黄时建议做到“中病即止”“证变转方”,尤其是对于麻黄使用指征存疑、存在风险的情况,建议每次处方不超过2~3剂。
6.1.2 内伤杂病用麻黄可“守方服用” 相对于外感伤寒疾病而言,内伤杂病病程相对较长,病机亦相对稳定,不易传变,故临床使用麻黄时可予守方服用。如《备急千金要方》载治疗中风使用续命汤时若“风大重者,相继五日五夜服汤不绝……如其不瘥,当更服汤攻之,以瘥为度”“勿计剂数多少,亦勿虑虚”[15],可见治疗内伤杂病时,麻黄的使用远没有治疗伤寒外感疾病时那般保守、谨慎。究其原因在于,内伤杂病不若外感伤寒疾病那般变化多端且迅猛,对人体正气、津液的消耗亦不如伤寒外感疾病那般快速。一般而言,在避开禁忌症、辨证准确、剂量合理的前提下,使用麻黄治疗内伤杂病(除外危重症)较少出现严重耗气伤津乃至亡阳的情况,亦较少出现坏病,故可放心使用。笔者常用小续命汤(麻黄用10~15 g)连服1~2周治疗脑卒中、面神经炎、横贯性脊髓炎、关节炎等疾病,甚少见因发汗而出现严重不良反应者。故对于内伤杂病而言,掌握麻黄禁忌症是使用麻黄类方的重大前提。
6.2 有是证未必用是方,辨证需与辨药物禁忌症合参
方证相应思想是经方思想的灵魂,是经方辨证的尖端,古往今来的善用经方者,包括柯韵伯、王旭高、刘渡舟、胡希恕等,无不秉持着“有是证,用是方”的用方原则[16-17]。笔者认为,方证相应诚然重要,但并非唯一的标准。临床上常常可遇到有是证用是方而无效甚至加重者。影响疗效的因素很多,其中药物禁忌症是中医辨证论治过程中重要但又相对重视不足的因素。《伤寒论》中关于提示药物禁忌症的记载十分多见,例如“柴胡不中与也”“不可与桂枝汤”“不可发汗”“不可下之”等,可见张仲景深明辨药物禁忌症对疗效及预后的影响。辨药物禁忌症是寻找否定该方药使用的依据,在此过程中,某些不同于方证所提示的病机得以判断,是辨证论治的重要环节。辨方证不辨药物禁忌症,可能导致治疗无效甚至病情加重。
7 麻黄误汗导致坏病的医案举例
7.1 脑干出血患者肺部感染误汗亡阳虚喘案
患者,男,75岁,主因“嗜睡、言语不利4天”于2020年8月31日由东直门医院周围血管科转至神经内科。患者4天前行糖尿病性坏疽截趾术后突然出现嗜睡,言语不利,饮水呛咳,头晕,左侧肢体无力,小便失禁,头颅CT提示“脑干出血,出血量约10 mL”,遂转至脑病科。查体:嗜睡,混合性失语,左上肢肌力2级,左下肢肌力3级,左侧巴氏征(+)。舌淡嫩红,水滑,脉浮缓。本病属于中风范畴,患者阳气不足,脉络空虚,风邪挟痰浊客阻脑窍而为病,予小续命汤加菖蒲、茯苓(麻黄用10~15 g)治疗后意识转清,肢体肌力、言语皆明显改善,2020年9月10日复查头颅CT:脑出血灶基本完全吸收,继续予原方治疗。
2020年9月11日,患者不慎受凉后出现发热,最高体温37.9℃,次日出现呼吸困难,短气,喘憋,端坐呼吸,咯黄痰及粉红色泡沫样痰,汗出,腹胀满,储氧面罩吸氧,氧流量>10 L/min,血氧在81~91%之间。查体:嗜睡,双肺呼吸音粗,可及广泛湿啰音,心率87次/分,律齐,心音低钝,辅助检查:(2020-09-13)白细胞计数17.2×109mmol/L,中性粒细胞百分比68.9%,淋巴细胞百分比22.7%,C反应蛋白128.4 mg/L,肌钙蛋白0.125 ng/mL,B型钠尿肽893 pg/mL,血气pH 7.461,氧分压61.3 mmHg,二氧化碳分压25.5 mmol/L,实际碳酸氢根 18.4 mmol/L,诊断为肺部感染、急性充血性心力衰竭、1型呼吸衰竭等,予抗感染、化痰、解痉平喘、抗炎、利尿等对症治疗。中医辨为支饮,予小青龙汤加石膏、茯苓合葶苈大枣泻肺汤温肺化饮。
经治疗后患者仍嗜睡,喘憋、短气好转不明显,腹胀满,双下肢凹陷性水肿。辅助检查:(2020-09-15)B型钠尿肽994 pg/mL,舌淡水润,苔薄微黄,脉缓弱涩,左关尺沉微。脉证相参,乃阳气衰微欲脱之象,阳虚水饮不化,《金匮要略》言“短气有微饮者,当从小便利之”,予真武汤合苓桂术甘汤温阳、化气、行水,具体处方如下:桂枝30 g、生白术30 g、茯苓30 g、生姜20 g、黑顺片15 g先煎、白芍20 g、生甘草10 g。一日一剂,水煎服,每日2次。
经中西医联合治疗后,患者神转清,诸证好转,生命体征稳定。辅助检查:(2020-09-20)白细胞计数9.2×109mmol/L,C反应蛋白48.98 mg/L,肌钙蛋白0.067 ng/mL,B型钠尿肽413 pg/mL,氧分压100 mmHg,二氧化碳分压33.6 mmol/L,顺利于2020年9月22日出院。
按 本例患者高龄,有糖尿病病史,感染前用小续命汤治疗脑出血得效,虽连用麻黄10余日,却未见麻黄刚躁误事。但肺部感染后未及时更方,甚至再用小青龙汤发汗,诱发心衰,该证属于虚喘范畴。麻黄增加心脏负荷乃其病因之一,正如《伤寒论》载“发汗后,饮水多必喘,以水灌之亦喘”。
7.2 白血病(虚劳)患者伤寒误汗咳而遗尿案
患者,女,24岁,主因“咳嗽1周”于2017年1月7日就诊,患者天冷不慎受凉后出现咳嗽,咳嗽频繁,影响睡眠,咯泡沫样痰,微挟黄色,二便调,余无他症。既往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病史,经骨髓移植术后幸存。舌淡红薄小,水滑,肌肉松软,面白,脉弦弱。审证不细,以为乃外寒内饮,予小青龙汤原方。患者服后咳嗽更加剧烈,咳而小便自出,腰酸痛,牙龈出血,神疲,面白,两脉弦弱,两尺沉微而涩,乃少阴肾咳。张仲景言“不可发汗……尺中迟脉微,此里虚,须表里实,津液自和,便自汗出愈”,乃予黑地黄丸补肾、散寒、止咳治疗:熟地30 g、干姜10 g、五味子10 g、细辛5 g、苍术5 g、紫菀12 g、款冬10 g、炙甘草5 g。4剂,每日1剂,水煎服,分温2服。
患者服后咳嗽及遗尿明显缓解,增咽痛一证,予蛇胆陈皮口服液,口服数日而告愈。
按 本例患者本属虚劳虚寒患者,用麻黄类方宜慎,所幸换方及时,未酿成大祸。《伤寒论·辨不可汗篇》载:“咳而小便利,若失小便者,不可发汗,汗出则四肢厥逆。”
7.3 颅内感染(风温)误汗头痛、神昏谵语案
患者,男,66岁,因“头痛、四肢乏力、发热2天”于2022年7月13日就诊于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患者2天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头痛,四肢乏力,发热,最高体温38.4℃,伴怕冷,无汗,大便干结,舌暗红,苔黄厚,脉浮滑数略紧。既往高血压病史、左股骨头坏死病史。辅助检查:血常规(五分类)+CRP:白细胞 10.13×109/L,单核细胞数1.32×109/L,单核细胞百分比13.0%;电解质四项:钠124.9 mmol/L,氯89.2 mmol/L;脑脊液压力为230~250 mmH2O,颜色清亮;脑脊液常规:白细胞282×106/L;脑脊液生化:蛋白1051.0 mg/L,葡萄糖5.50 mmol/L,氯7.6 mmol/L;脑脊液细菌培养、抗酸染色、新型隐球菌涂片阴性。病原微生物检高通量测:主要病原为EB病毒。胸部CT:右肺下叶少许炎症;头颅磁共振平扫:双侧侧脑室旁白质小缺血、变性灶。诊断为病毒病脑炎,予抗感染、激素消炎、脱水降颅压等治疗,好转不明显。
中医方面考虑为太阳阳明合病,予葛根汤加半夏、黄芩。患者服中药当天出现头痛、四肢乏力、发热加重,胡言乱语,对答不切题,四肢不自主震颤,言语不利,嗜睡,汗出,纳差,眠可,大便干结,数日未解,小便可,舌暗红,苔黄厚,脉浮滑数略紧。专科查体:嗜睡,言语不利,对答不切题,查体不合作,粗测四肢肌力4级,脑膜刺激征(+)。考虑本为风温,病属阳明,误汗后火热更甚,腑气不通,火郁不散,立即予大柴胡汤合升降散通降阳明,发散郁热治疗,具体处方如下:柴胡40 g、黄芩15 g、姜半夏15 g、生姜15 g、大枣15 g、甘草15 g、生大黄12 g、 僵蚕12 g、 蝉蜕12 g、姜黄12 g、 天竺黄20 g, 3剂,每日一剂,水煎分2次内服。
服药后患者头痛、四肢乏力明显好转,神清语利,对答切题,无四肢震颤,一般情况可,续服3剂,病情稳定后予办理出院。
按 本例乃风温误认为伤寒予葛根汤发汗的案例,临床上被诊断为病毒性脑炎,与《伤寒论》中“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若发汗已,身灼热者,名风温。风温之为病,脉阴阳自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语言难出……若被火者,微发黄色,剧则如惊痫,时瘈瘲”的描述如出一辙。伤寒温病治疗不同,温病尤不宜用麻黄发汗,温病学家对此论述已多。
8 小结
本文探讨了《伤寒论》中“不可汗”的条文内涵,归纳了麻黄的禁忌症、慎用症及伤寒鉴别症。本文一再强调麻黄用之错谬可导致坏病,意不在驳斥麻黄在临床中的重要地位,相反是为了更清晰地从负面角度描述麻黄的药性特点,尽可能避免相关不良事件的发生,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