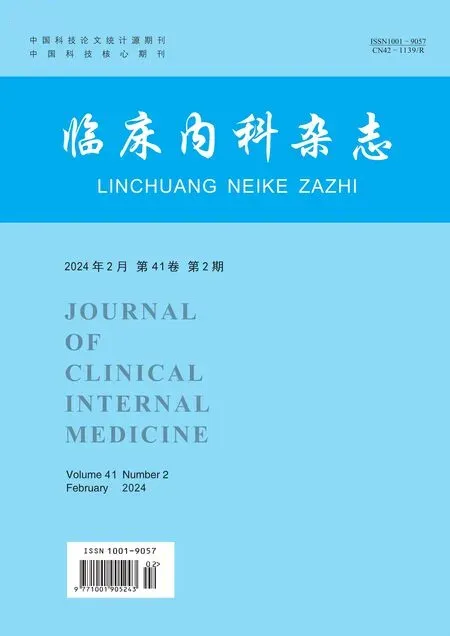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合并骨髓增殖性肿瘤临床特征分析
刘雯 刘亚楠 赵磊 刘尚勤 吴三云 何莉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是一种主要发生在中老年人群中的成熟B淋巴细胞克隆增殖性肿瘤[1],是西方最常见的慢性白血病类型。骨髓增殖性肿瘤(MPN)是一组克隆性造血干细胞疾病,经典的费城染色体阴性的MPN包括真性红细胞增多症(PV)、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ET)及原发性骨髓纤维化(PMF)。JAK2V617F作为MPN的一个重要诊断依据,在绝大多数的PV患者和约50%~60%的ET及PMF患者中均可检测到JAK2V617F突变[2]。MPN和CLL罕见共存于同一患者,有研究提示两病可能存在遗传相关性,但目前MPN和CLL共患病的发病率仍较低,两者的关系仍需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本文通过总结既往病例,讨论两病共存可能的发病机制及临床特点。
对象与方法
1.对象:查询PubMed、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回顾性纳入2000年~2020年世界范围内报道的CLL合并MPN患者112例,另纳入本院CLL合并MPN患者1例。检索策略为主题词和自由词结合的方法,数据库检索条件分别如下:PubMed:(“Polycythemia Vera”OR“Thrombocythemia,Essential”OR“Myelofibrosis”OR“Myeloproliferative Disorders”) AND (“Leukemia,Lymphocytic,Chronic,B-cell”OR“Lymphoproliferative Disorders”)。中文数据库:(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OR真性红细胞增多症OR骨髓纤维化OR骨髓增殖性肿瘤)AND(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纳入患者需先后或同时诊断为CLL及MPN(包括PV、ET、PMF)。根据MPN类型将所有患者分为PV合并CLL组(35例)、ET合并CLL组(53例)及PMF合并CLL组(25例);根据JAK2V617F突变情况将已知突变情况患者95例分为JAK2V617F阳性组(66例)和JAK2V617F阴性组(29例);根据疾病诊断顺序将所有患者分为先MPN后CLL组(60例)、同时诊断组(27例)及先CLL后MPN组(26例)。
2.方法:收集所有患者临床特征资料,包括性别、诊断年龄、两种疾病诊断间隔时间、疾病诊断类型、JAK2V617F突变情况及其他类型突变情况、治疗及转归情况、存治状态、生存时间、MPN类型、疾病诊断顺序。描述本院诊断的1例CLL合并MPN患者诊治经过,使用一代测序及定量PCR对其JAK2V617F进行分析,由Sequencing Analysis 5.1.1软件进行一代碱基测序,PCR扩增和检测在ABI 7500系统中进行。

结 果
1.不同MPN合并CLL组患者临床特征比较:3个MPN合并CLL组中共患病以ET合并CLL最为常见(46.9%)。3组患者JAK2V617F突变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PV合并CLL组JAK2V617F阳性患者比例明显高于其他两组(P<0.05)。PV合并CLL组患者CLL诊断年龄最大(P<0.05)。3组患者中均以男性居多,但3组患者性别、MPN诊断年龄、两种疾病诊断间隔时间及生存时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不同MPN合并CLL组患者临床特征比较
2.JAK2V617F阳性组及阴性组患者临床特征比较:113例患者中JAK2V617F阳性66例(58.4%),阴性29例(25.7%),未提供突变情况18例(15.9%)。JAK2V617F阴性组CLL诊断年龄小于JAK2V617F阳性组,两种疾病诊断间隔时间长于JAK2V617F阳性组(P<0.05)。两组患者性别仍以男性居多,但两组间性别、MPN诊断年龄及生存时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JAK2V617F阳性组及阴性组患者临床特征比较
3.不同疾病诊断顺序组患者临床特征比较:先MPN后CLL诊断是最常见的共患病诊断顺序(60例,53.1%)。先MPN后CLL组患者生存时间最长,同时诊断组患者生存时间最短,先CLL后MPN组两种疾病诊断间隔时间高于先MPN后CLL组(P<0.05)。3组患者性别、初病诊断年龄、JAK2V617F突变情况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表3 不同疾病诊断顺序组患者临床特征比较
4.MPN存在其他突变类型患者的临床特征分析:JAK2V617F阴性组29例患者中以男性居多(男性18例,女性3例,性别不详者8例),其中5例存在CALR阳性,1例存在MPL阳性;上述6例患者平均初病诊断年龄(56.17±3.31)岁,中位两种疾病诊断间隔时间13.55(10.02,16.25)年,其中5例(83.3%)患者进行了相应治疗,平均生存时间(13.82±4.42)年。部分患者临床资料见表4。

表4 MPN存在其他突变类型患者临床特征分析
5.治疗及转归情况:在治疗方面,39例患者未达CLL治疗标准,仅治疗MPN,平均存活时间(8.16±5.78)年;11例患者仅治疗CLL,平均存活时间(9.01±6.59)年;CLL与MPN均行治疗的患者14例,平均存活时间(10.09±6.77)年,30例患者截至文献报道时未行特殊治疗,平均存活时间(7.00±6.90)年;另有19例患者治疗方案不详,平均存活时间(8.10±3.72)年。各治疗方案中,以两病均行治疗的患者存活时间最长,但各治疗方案间患者存活时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105例患者截至文献报道时为存活状态,8例患者死亡,其中6例患者死亡原因不详,2例患者因白血病进展及肺部感染死亡。
6.本院CLL合并MPN患者的诊治经过及JAK2V617F突变情况分析:患者,男,64岁,既往有高血压病史,2012年8月于外院同时诊断有脑梗死和ET,血常规结果示PLT计数615×109/L,Hb 120 g/L,WBC及淋巴细胞计数均正常,经羟基脲治疗后PLT计数降至正常。2017年4月,患者外院复查血常规结果示WBC计数15.5×109/L,其中淋巴细胞占48.3%,骨髓穿刺可见成熟淋巴细胞增多,骨髓细胞流式免疫分型结果示淋巴细胞占全部有核细胞51.1%,其中90.3%的细胞表达CD5、CD19、CD23、BCL-2,弱表达CD20、CD22、κ。流式免疫分型结果提示淋巴细胞占有核细胞的51.1%,异常成熟小B淋巴细胞占有核细胞的46.1%,影像学结果提示肝脾淋巴结无肿大,诊断为CLL Binet A/Rai 0期,随访观察。2020年12月患者至我院血液科就诊,体检发现多处淋巴结肿大,脾肋下3指。患者外周血WBC计数29.3×109/L,其中淋巴细胞占78.1%,Hb 120 g/L,PLT计数200×109/L。骨髓穿刺结果提示淋巴细胞比例增高,以成熟小B淋巴细胞为主。流式免疫分型结果提示淋巴细胞占有核细胞的73.2%,其中91.9%为异常成熟小B淋巴细胞。基因检测提示JAK2V617F突变负荷4.38%。有IgH、IgK基因单克隆性重排基因片段,荧光原位杂交(FISH)结果提示13q14.3缺失阳性,染色体核型正常。诊断为CLL Binet B/Rai Ⅱ期,予以减量CVP方案(环磷酰胺400 mg×3 d、长春地辛2 mg×2 d、地塞米松20 mg×3 d)预化疗后,患者开始接受泽布替尼联合利妥昔单抗治疗CLL,1个月后复查血常规提示WBC计数2.6×109/L,淋巴细胞计数1.2×109/L,Hb 71 g/L,PLT计数71×109/L。骨髓象提示淋巴细胞比例下降,流式免疫分型提示淋巴细胞占有核细胞的17.2%,异常成熟小B淋巴细胞降至有核细胞的7.1%,JAK2V617F突变负荷升至13.88%,评估疗效部分缓解,治疗过程中患者有轻度肺部感染及皮下出血,对症治疗后Hb及PLT计数回升,后至血液科门诊规律复诊。
讨 论
MPN与CLL均是起源于多能造血干细胞的疾病,两病共患的实际概率远超其理论概率,提示两病共患现象并非偶然。有研究表明MPN患者相较于普通人群有更大可能发展成淋巴细胞增殖性疾病,尤其是CLL,有超过12倍的风险[3]。然而,CLL与MPN均为慢性隐匿性疾病,其在人群中的发病率也有被低估的可能,从而影响统计学的判断。
现有针对共患病发病机制的主要假设如下:一是认为有髓系-淋巴系造血祖细胞的存在。细胞早期阶段发生的触发打击使多潜能祖细胞的基因趋向于不稳定,之后特异的分子事件导致髓系或淋巴系一系或多系克隆性增殖[4]。二是认为两系细胞在不同的微环境下发生遗传学改变,独立地引起淋巴系和髓系克隆增殖。在CLL或MPN的骨髓环境下,慢性炎症等导致的微环境变化使两者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5-6]。肿瘤引起的免疫监视功能缺陷也可促进第二肿瘤的发生与发展[7]。此外,MPN治疗药物如芦可替尼[8]、羟基脲等的使用,也可能增加淋巴增殖性疾病的发病率,但具体机制尚未阐明。
本院共患病患者治疗CLL后,评估治疗效果达部分缓解,但治疗后JAK2V617F突变比例升高,该突变负荷的增加与高白细胞、巨脾、血栓形成等不良事件相关,且使MPN进展为骨髓纤维化及转化为白血病的风险升高,该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提示ET疾病进展[9]。该患者曾使用羟基脲行降PLT治疗,但目前对羟基脲可致第二肿瘤发生存在争议,Wang等[10]对4 023例MPN患者进行回顾性研究,发现使用和不使用羟基脲的患者继发实体肿瘤或血液肿瘤的累积发病率相似,该结论也能在瑞典的一项研究中得到印证[11]。考虑我院患者规律使用羟基脲,且治疗时间短,继发CLL为羟基脲引起的第二肿瘤可能性较小,推测该患者淋巴系和髓系的恶性克隆来自于不同的造血祖细胞。
既往研究表明,JAK2V617F突变会增加患血液系统肿瘤的风险,包括MPN(HR:161)、淋巴瘤(HR:5.7)。JAK2V617F突变在男性、女性间发生风险比约为1.3(0.3~5.4)[12],而本研究中JAK2V617F阳性的患者也以男性居多。分析共患病患者JAK2V617F突变与患病顺序关系发现基因突变阳性比例在先诊断MPN后继发CLL的患者中最高,在先诊断CLL随后诊断为MPN的患者中比例最低,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这也与Marchetti等[13]的研究结果一致。这可能意味着JAK2V617F突变不是共患病发生发展中所必需的分子改变。两病同时诊断的共患病患者存活时间最短,且与另两组患者存在显著差异,可能与个体的肿瘤易感性及免疫功能损伤相关。另外,CALR、MPL阳性患者与JAK2V617F阳性患者相比,其初病诊断时间提前,诊断间隔及生存时间延长,提示这两种突变相较于JAK2V617F突变可能有更惰性的临床过程,与MPN单病时一致。
在疾病的治疗方面,共患病的治疗尚无统一治疗方案,疗效及不良反应尚不明切。既往病例中,39例患者使用羟基脲、放血、抗凝、切脾、免疫调节剂等疗法治疗MPN,其中11例采用苯丁酸氮芥、氟达拉滨、苯达莫司汀、伊布替尼等化疗或靶向方案治疗CLL,14例患者进行了针对两病的治疗。本研究中不同治疗方案组间生存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可能与病例随访时间不足有关。此外,引入BTK抑制剂、BCL-2抑制剂等治疗方式的改变也对患者生存时间产生了影响。就目前病例总结,作者认为共患病的治疗可参照单发肿瘤分别进行针对性治疗,过程中可适当使用免疫调节剂等方法减缓疾病进展。
综上所述,MPN及CLL共患病与两病单发时有相似的临床特征,但其发病机制、治疗及预后情况仍不明确,局限于既往文献报道内容不全面,患者治疗过程中血细胞计数、不良事件发生、疾病转归等情况仍有不详之处,难以进行系统研究。多中心、大样本基于分子水平的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将有利于进一步明确MPN及CLL共患的内在机制及发展过程,更好地指导治疗及评估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