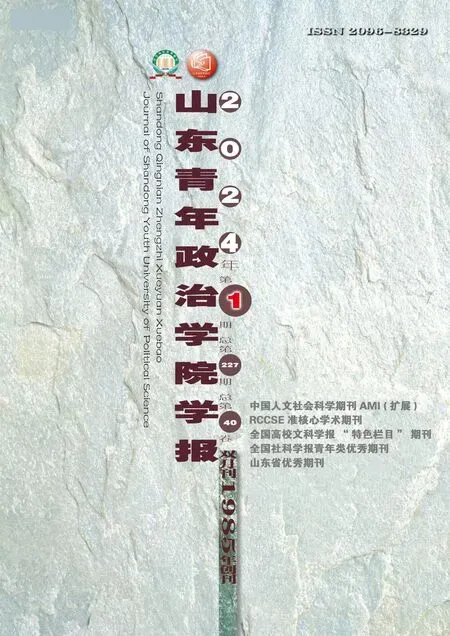老舍在山东史料零拾三题
刘子凌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济南 250014)
老舍与山东可谓缘分颇深。从1930年下半年受聘至济南的齐鲁大学任教,到1937年因投身“抗战”而从青岛赶赴武汉,他前后在山东度过了七年的寓居时光。在此期间,他既教书、创作、翻译,也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迎来了一个收获丰硕的人生阶段。
关于老舍在山东的生活与工作情况,学界已有系统的梳理和总结。(1)比如说,张桂兴在其所著的《老舍资料考释》(修订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0)中,以《老舍在齐鲁大学考》《老舍在山东大学考》《老舍与齐鲁文化名人》《老舍的结社及任职考》《老舍主编及参与编辑的刊物考》等章节,较为系统地钩沉了老舍在山东的行迹;相关成果,也反映在其所编撰的《老舍年谱》(修订本)(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中。另外,如五卷本《老舍青岛文集》(文物出版社,2014)全面收录了老舍在青岛创作的作品、在青岛时期发表的作品和在异地写作或发表的与青岛直接相关的作品,对展示老舍的青岛生涯而言,也是一部很有特点的专题资料汇编。但因为时间跨度较大,加之文献分散,这一领域应该还有值得致力之处。笔者在翻阅相关书报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与老舍有关的史料,对于了解这位作家在山东的思想与交游细节,或不无小补,特在此略加钩沉。
一、一篇演讲残稿
学界公认,老舍不仅拥有一枝生花妙笔,口头表达的功力也相当出色。在“国语”尚未普及但又被普遍看重的年代,他的一口北京话,“大家听得懂,听得省劲儿”,再加上他的演讲“简练明了,幽默生动”,自然邀请者纷至沓来,以至于“讲演成为了他创作的一部分”——整理者至少“发现 170多次有记载的讲演”。(2)舒济:《后记》,载舒济编《老舍讲演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第210-211页。这一数字肯定早被突破了,近年来,在老舍的佚文发掘方面,似乎也是与演讲,尤其是抗战时段的演讲有关的文献最有成绩。(3)相关成果略举数例:解志熙:《“献上我们的智与力”——老舍抗战及40年代诗文拾遗》《“风雨八年晦,贞邪一念明”——老舍抗战及40年代佚文校读杞记》《文学史的“诗与真”——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赵曰茂:《老舍在国立山东大学的讲演<怎样作文章>》(《新文学史料》2019年第4期);郭国昌:《抗战时期老舍在兰州的两次演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2期);李莹:《老舍青岛讲演佚稿<怎样作文章>考释——兼谈老舍讲演与新文学写作、传播的互文性》(《文艺争鸣》2020年第4期);凌孟华:《抗战时期老舍在重庆的演讲活动钩沉与补正》(《创作评谭》2021年第6期)。
笔者发现的老舍演讲,题为《老舍的演讲(续)》,题目下署“灰云记述”,刊于《国民日报》的“团圆周刊”第16期(1934年3月13日)。初步翻阅《老舍全集》,没有找到与此接近的篇目。这一时期的老舍年表,也没有给出相关信息。所以,这是老舍的一份佚失的演讲记录稿。先照录原文如下:
所以我们应预备,这再次的世界大战。
因此你应该把宗教观,放在事上去作事,不要事和宗教分别,所以就得根本去作,去实行,不要受任何的限制和支配。现在世界情形是这样,设若将来再次的世界大战,我们这些作基督徒的,都抱定了已定的宗旨,凡是这种惨忍的战争,无论如何,我们不去参加,那恐怕这次世界大战,或因之而停,或永不会,有这种战争的事。总说一句:凡若是世界基督徒,真能努力去照样作去,我想一定能减少了这战争的力量!
所以是在现在的基督徒,从意识上要认清现在的社会,从思想上要认清现在的世界,是如何的现劳(“劳”或应作“势”——引者),努力去作。在原先以为无论何人,无论他信教的忠实否?只要他是个好人,就算是个好基督徒,这只是局部的,我们要把宗教作用,不限得如此小,就以现在中国说吧!先不要说世界,中国的人,可以比作一个拉磨的驴,一切不管,只是瞎着眼在转磨,一切都不去管,因此中国的事,无一件办明白办清楚了的,无论什么问题,解决了的很少,多一半是未解决。那基督教,因环境的关系,所以这宗教的问题更不用说了,还是没弄明白,只是瞎着眼转,结果没有一点的用处,所以是你得看清楚去作,并不是人说什么,你就作什么,人家不说你就不作,这不是成了一部死机器了么?!但是你也不能说作,就不顾一切去做,至于计划也得有的才行。
标题中的“续”字表明,这篇讲稿有前文;而且,这期刊物上揭载出来的部分,也似乎没有完篇。遗憾的是,由于报纸不全,这次演讲仅存上文的残稿。但因为它只是他人的“记述”,严格来说,不能算是老舍的佚文。
关于《国民日报》,很难查到更多的信息。目前只知道它是国民党历城县党部主办,1929年创刊,1935年停刊,负责人为郝家骅。(4)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山东省志·报业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132页。这份报纸的报头是戴传贤题写的。而据罗腾霄在《1934:济南大观》(齐鲁书社,2011)中的记载,郝家骅时为历城县国民党党部委员。“团圆周刊”在刊头左侧标注“葡萄社主编”,也不清楚“葡萄社”是个怎样的社团。这一期刊物上的一则《编后》,留下了一个通信地址:“东关青龙街一八三号”——可能是“葡萄社”的社址,在济南。因为仅见这一期,刊物的其他情况均不可考,不过基本能够断定,这是济南本地性比较强的一份副刊。考虑到老舍此时是齐鲁大学的教师,他的演讲刊布于此,合理的推测是,这次演讲应该就是在他执教齐鲁大学期间进行的。可惜,“掐头去尾”的残稿无法给出更准确的时间。
更多的疑问接踵而来:老舍的这次演讲,讲给谁听?主题是什么?演讲记述者“灰云”又是何许人也?此人的记述,有没有经过老舍的校订?能不能准确反映老舍的思想?这些问题又在“老舍的演讲”这一标题前碰壁。读者只能就现存的文本做出一些大致的推测。
首先,这份残稿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其极为浓厚的宗教色彩。“我们这些作基督徒的”云云的措辞,更透露出老舍的演讲乃是在某次宗教活动场合中,或某一教会组织(或教会学校)内进行的。众所周知,老舍是正式受洗加入教会的基督教徒,但他却又很少正面阐释自己的宗教思想。朝戈金《老舍关于宗教的佚文》列举了5篇“老舍关于宗教方面的文章、译文和讲演录”(5)《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2期。,刘涛此后补充了一篇题为“以善胜恶”的演讲(6)舒舍予讲,单伦理笔记:《以善胜恶》,《河南中华圣公会会刊》第5卷第5期,1932年10月5日。考证文字见刘涛:《老舍的基督教信仰与救世观及其他——从最近发现的三篇老舍佚文谈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2期。。《国民日报·团圆周刊》上这份演讲残稿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再一次为人们理解老舍的宗教观提供了旁证材料。
总起来说,这份残稿可以划分为两个层次:一是面向国际关系的讨论,一是针对中国社会的思考。在一般的印象里,老舍并不是一个以敏锐的政论头脑著称的作家。所以,残稿开头的一句话就十分让人惊讶。关键不在于老舍是基于怎样的理由而预感到了“再次的世界大战”,而且他的预感又是怎样很快地被世界历史的展开过程所证实,就他的观察本身而言,那种宏阔的地缘政治眼光便展示出他的思想里少为人知的一面。至于绝不参战的立场,基于宗教的博爱观念,反倒显得不是多么突兀了。有迹象表明,这一时段老舍对国际形势保持着一种密切的关注。在《以善胜恶》的演讲中,他也表达了对“世界的潮流”的某种隐忧,那就是“人所欲解决的,不是别的,只有经济问题”,“宗教则置之度外”。(7)舒舍予讲,单伦理笔记:《以善胜恶》,《河南中华圣公会会刊》第5卷第5期,1932年10月5日。
这种“世界的潮流”,自然会折射到中国社会中,老舍的批判足够犀利——“只是瞎着眼在转磨,一切都不去管”。与此相反,他主张“你得看清楚去作”。当然,怎样才是“看清楚”,这在简短的残稿里没有能够展开,读者无从悬想。可细味文意,在他看来,人之所以能“看清楚”,只能归之于“宗教作用”。但他又没有把“宗教”限定得非常狭隘,而是体现出一种相当宽松的姿态,不以“信教的忠实否”“好人”“好基督徒”为断,警惕这些“只是局部的”标签,其结果反而把“宗教作用”说小了。
从这样的理路看,老舍的宗教观带有相当的超越性。“宗教”在他这里,主要是某种精神资源的表征,它的意义不体现于信不信教等外在的形式,而是要充当一种价值观、人生观的指引。如果与这一时期辞气完足的《以善胜恶》对读,可以确认老舍之于这种思想的一贯性,也可以确认《国民日报·团圆周刊》上这份演讲残稿应该是较为真实地反映了老舍这一时期的思想状况。(8)从语体上说,这份残稿也大致保留了老舍演讲的一般特征:“多使用短句,言简意赅,句句连贯,并在段落之间加以过渡,因此讲演的整体结构一目了然。”(李莹:《老舍青岛讲演佚稿<怎样作文章>考释——兼谈老舍讲演与新文学写作、传播的互文性》,《文艺争鸣》2020年第4期)
遥想当年留日时的鲁迅,就是一手批判“金铁国会立宪”(9)“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奚事抱枝拾叶,徒金铁国会立宪之云乎?”(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47页),一手主张“迷信可存”(10)“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30页)。历史迤逦来到“五四”,老舍事后追认他此时受到的影响,“首先是:我的思想变了”(11)老舍:《“五四”给了我什么》,《老舍全集(修订本)》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第636页。。不得不说,老舍对“宗教作用”的重申,内在于中国近现代知识人艰苦的思想探索传统之中。
二、在山东大学的日常
1934年下半年,老舍辞去在济南的私立齐鲁大学的教职,经过一番犹疑和试探,最后接下了位于青岛的国立山东大学的聘书。老舍在青岛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学界利用现有材料,已经呈现出了较为清晰的轮廓。笔者拟以黄际遇日记为基础,对老舍的日常交游情形作一些补充。
黄际遇何许人也?现代文学研究界对其人其事知之不多。老舍入职山大时,他是文理学院院长,排在校长赵畸(赵太侔)、秘书长皮松云、教务长杜光埙之后的学校四号人物(杜光埙公务、家事繁忙,其教务长职务多次由黄际遇代理)。在所有教职员中,他的入职时间(1930年5月)也最早,那个时候山东大学的前身青岛大学还在酝酿组织之中。所以他是不折不扣的“老人”。
文理学院在当今的大学里,确实是很少见到的建制。当时的山大,文理学院下设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12)《民国二十四年国立山东大学一览》,国立山东大学出版课,1935,第7、273页。以一位数学家而管理文科专业,当然有“外行领导内行”的危险。但黄际遇却胜任愉快。后来在中山大学,此君一面为理学院、工学院讲授“微分几何学”“连续群论”,一面在中文系开设“骈文研究”“《说文》研究”,即此一点,已可想见他的学科跨度。丰厚的古典文学修养与丰富的留日、留美研习数学的经历,使黄际遇与文理学院这一建制实现了完美的契合。
黄际遇的日记也很有特点,“全是以文言文写成,文章有时简约畅练,有时骈散兼备,有时更是全篇流丽典雅的骈文”(13)黄天骥:《<黄际遇日记类编>序》,载黄小安、何荫坤编注《黄际遇日记类编 国立山东大学时期》,中山大学出版社,2020,第2页。。他的日记经常会留下同事把日记借走阅读,或劝其录副以传世的记录,他自己也曾起意“庸吏抄胥”,“印如讲义”,分赠各方(1935年10月19日日记(14)黄小安、何荫坤编注《黄际遇日记类编 国立山东大学时期》,中山大学出版社,2020,第363页。下文引用日记,同此版本,简便起见,只随文括注页码,特此说明。)。盖其日记不仅为纪事,也是修身、自励的一种学记。(15)1935年11月6日日记云:“人事纷蕴,两日未亲一书,勉以日记自课而已。”(第370页)尤可见出他对日记的定位。
老舍与黄际遇在青岛的初次见面,是1934年9月11日:“怡荪偕舒舍予来”。怡荪即张煦,时任中国文学系教授兼系主任。老舍经他陪同访问黄际遇,显然是新同事入职、拜见上级领导的礼节之举。人情之常,无需多论。有意思的是,黄际遇并没有记下他对老舍的印象,缘故何在?或许是因为二人此前有过共事之举,并非初见——同日日记,黄氏留下了一笔:“舍予前尝在历城典试同阅国学试卷。”
“历城典试”,这似乎是老舍履历中人们不曾知道的内容。查黄际遇日记,时间是在1933年6月29日。但他当时没记老舍也参加了同一活动的事。根据这个日期,很容易查到报纸上的相关新闻,如《鲁普高检定考试昨在齐鲁大学举行》(16)《益世报》(北京),1933年6月30日。,这个考试场所,又是黄际遇日记没有写入的。
南京国民政府设置的检定考试,“是为甄拔一批无力升学而自学成才的人取得任命人员或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应考资格的考试”。(17)房列曙:《中国近现代文官制度》下册,商务印书馆,2016,第545页。老舍参与其中,或许是基于“地利”之便。考场所处的齐鲁大学,正是他的供职机关。
黄际遇虽不守旧,对新文学也并不隔膜(18)黄际遇1932年10月8日日记就自己直接接触的同事沈从文发挥了一大段,还评价《阿丽思中国游记》“不像鲁迅专以尖刻,郁达夫专以颓废为拿手戏的”。(第56-57页)可见他对新文学作家并不陌生。,但肯定算不上一名热烈读者。山大文科教员中,与他过从最多的游国恩(泽丞)、姜忠奎(叔明)等,都不是新文学名家。不过黄氏性格豁达,兴趣广泛,兼之酒量甚佳,雅好交际,所以与老舍的交往,逐渐也就多了起来。
兹将黄际遇日记中与老舍有关的文字摘录如下(省略号均为摘录者所加):
1934年10月1日:夜访舒舍予谈。(第277页)
1934年10月5日:少侯约同柬招太侔夫妇、洪浅哉、唐凤图、李仲珩、舒舍予、水天统、毅伯、达吾、仲纯诸友七日晚饮于寓庐。(第279页)
1934年10月7日:席阑茶熟,围坐高谈,老舍浅哉,尤烂剧理,其谓左嗓子不能唱正中调,证以发音机关构造之图,言菊朋之以老生见长,参有青衫行腔运调之处。又谓小生唱法其妙处在以宽嗓窄嗓间互运用。均属深入浅出之论。尤于说理时随举剧词,曼声拍唱,高山流水,实移我情,而低调之难于高调更可见也。(第280页)
1934年10月23日:晡仲纯来共杯杓,同舍人聚话,复招舒舍予与会。(第285页)
1935年1月5日:午舒舍予夫妇约饮私宅,为之盘桓竟日。(第310页)
1935年3月8日:老舍来小谈。(第314页)
1935年3月24日:早访少侯话足疾,少侯曰不麻不振,恐是北人所谓寒腿之症。诣老舍证之而益信,丐得北京广生堂药膏以归(虎骨熊油追风活血膏)。(第318页)
1935年3月28日:老舍来答访。(第321页)
1935年4月27日:夜应舒舍予约饮于春和楼,坐有陈季超,老友健拳,遂为之尽欢鏖战。(第330页)
1935年5月5日:舍予馈药,柬谢之。(第332页)
1935年6月25日:日景尚高,雇车践涤非厚德福酒家之约。叔明先至,舍予、少侯、泽丞、啸咸、贺祖篯、李保衡歱接而来,仲纯、怡荪后焉。……坐甫定,酒行数巡,意兴都豪,余即攘臂盘马,訇髦而呼。客皆弹指藏弦,闻声起舞。(第351页)
1935年10月10日:舍予来面约十三日汤饼之饮。……入席间,得舍予张其军,亦极盘马弯弓之能事,嘉宾破戒而尽觞。(第360页)
1935年10月13日:驰赴舒宅汤饼之会。坐有陈季超盘马弯弓故善战,久阔之下劝杯倍勤。(第361页)
1935年10月14日:日入少侯、太侔骞至,飞柬舍予来驱,驱之在市之肆曰“百花村”者,……大言无碍,小饮亦佳,戟指藏钩,娄添酒筹,兴之所之,遂不成醉。(第361页)
1935年10月29日:晚少侯招饮登州路精舍,太侔夫妇、浅哉、老舍、仲纯、康甫早集,当炉炰羔,莼羹皆韵,醇醪盈罍,色香并佳。此会在比来不可多得矣。(第387页)
1935年11月5日:又面约仲纯、康甫、舍予往太侔寓夜饮,酒由宁氏馔,则寡人谈侣酒俦,大半在是,流连尽晷,乐乃无央。(第369页)
1935年11月26日:偕舍予阴雨中访少侯,已不可支。(第379页)
1935年12月3日:偕舍予过访少侯闲坐片时,稍摅一日之劳,不知何故,乡思悠然。(第381页)
1935年12月21日:晚偕君复应舒舍予酒约,一坐多拳酒胜流,比因戒杯,少饮而止。(第387页)
1935年12月30日:夜约消寒之会,太侔未晡过谈。浅哉、少侯、仲纯、舍予、咏声,怡荪、达吾先后而来(毅伯辞以疾)。……曾几何时,而肴酿俱有难继之状,兴到酣时,一斗不醉,非屠沽市远,今夕诸君大有再接再厉之势也。乐不可极,酒不可纵,撤馔易茶,甘苦同之。西隅半斗书室之间,今文坛健者洪深、老舍、赵少侯诸子,方放高谈。(第391页)
1936年1月20日:今日舒舍予都讲文艺中典型之人物,出口有章,隽语叠出,极博佳评,舍却人生无文学之论者也。(第400页)
1936年1月22日:晡承佑约少侯、舍予、仲纯会于蔽庐,亨羊炰羔,举酒属客。……须臾肉尽,纵谈于室,同心之言,酒醇不醉,鲁酒不薄,齐谐无伤。舍予引亢以高歌,少侯依声而应节。一曲未已,昆乱间出,予亦悉索所有,拾响效颦,但资哄堂,宁惭屋漏。亦以余力应敌丁丁。正是炉香茶热时,不知今夕何夕,人间天上。(第401页)
可以看出,在黄际遇的日记中,老舍的形象是多面的:这位同事懂“剧理”,还能“引亢以高歌”,来上一段——这为老舍与京剧的关系,增添了旁证;这位同事有可信的生活经验,“寒腿之症”可以在他口中取得确认,也可以从他得到对症的药物;这位同事善于演讲,是谈笑风生的“文坛健者”;这位同事更是相当投契的酒友,豁拳叫嚷,酒酣耳热,其乐未央。这些记录,提供了老舍以及山大教师群体日常生活的生动画面。
如果长时段地看,1934年下半年的国立山东大学有一种由盛转衰的趋势。黄际遇经常在日记中流露出杨振声任校长时代“酒中八仙”盛况不再的感慨。(19)“酒中八仙”的雅事,因梁实秋的多次渲染,广为人知。参见其《谈闻一多》(载《梁实秋文集》第2卷,鹭江出版社,2002,以下各卷版本相同),《忆杨金甫》《方令孺其人》(均载《梁实秋文集》第3卷),《酒中八仙——记青岛旧游》《记黄际遇先生》(均载《梁实秋文集》第4卷)诸文。时局的动荡,也猛烈冲击着这所年轻的高等学府。1936年1月10日,黄际遇听说山东省政府给学校的协款三万金“二十四年底以后不再拨给”,深觉“帝业未成,一朝断送”,便萌生了去意(第397页)。当年寒假,他拒绝挽留,离开了这所曾服务将近六年、付出相当心力的学校,赴老家广东,任教于中山大学。他与老舍的交游,也就中断了。
三、未曾实现的定居青岛计划
黄际遇离职,老舍也只在山大多逗留了一个学期。1936年暑假,他也跟这所学校脱离了关系。次年,因为抗战全面爆发,青岛局势危殆,他先是重回济南的齐鲁大学就聘,然后艰难地只身赶到那时的抗战中心武汉。也就是说,他也跟青岛告别了。在大后方,老舍主持“文协”大局,发挥的巨大作用自不待言。但抗战胜利后老舍曾经有过的一个定居青岛从事创作的计划,似乎不甚为人注意。
张桂兴在《老舍资料考释(修订本)》和《老舍年谱(修订本)》对此事有所介绍。前书谓:“1945年9月,老舍曾带着抗战胜利的喜悦致信王统照,托他在青岛购买一所小房,预备返回青岛过他的写作生活。结果房子未买成,老舍也未能赴青岛,而是应邀赴美国讲学去了。”(20)张桂兴:《老舍资料考释》(修订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0,第403页。后书则在1945年9月项下记:“致王统照信。”据王统照《忆老舍》说:“他在日军初降时,高兴之至——九月间写了一封信,托我为他在青岛购置一所小房子,预备仍返故处,安安逸逸的过他战后创作生活。”(21)张桂兴编撰《老舍年谱》(修订本)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第488页。如此记述的史料依据相同——1946年2月8日青岛《民言报》。
张桂兴毕竟不是要专门处理这个话题,故他的介绍失之简略。但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其他人加以展开,有待解释的疑点至少包括:老舍为什么选择青岛为胜利后的定居之处?他为什么委托王统照买房?房子又是为什么没有买成呢?这些疑点,王统照的文章其实都给出了说明。但因为这篇文章不曾收录于《王统照全集》,刊布的报纸又不容易获读,所以也就影响了其传播的范围。借此机会,笔者将王统照的这篇《忆老舍》全文辑录如下:
当年,老舍离开北方,流亡南去,他是从青岛走的。正当芦沟桥战事紧急之时,全国同愤,风云变色。本市是日人专力经营投资集中,日侨繁多的要地。他们的军舰,三三五五已在胶州湾中游弋,预备随时登岸,——或随时开火。那时,本市居民纷纷走避,知道这里终有一场剧战。我在沪上忙于文字,也正在眼望着全国文艺界函电抗争,准备为国家共尽微力。因为本市人心惶惶,家人无策,电催归来。在匆忙中,我由津浦路连夜到青,小住七八日。一面预备同家人南下,一面抽空会晤亲朋,——为的这次空前抗战,时日多久,困苦多大,都难说定,与他们见见即作长别!
老舍先生住在黄县路上某号一所二层楼的第一层内。(他早已不在山大教书,专写小说约有二年了。)自然,见了两回。他说,本愿与我同行,无奈他的夫人即将分娩,正住医院,非迟几个礼拜不克动身。或者战事一时尚不至“波及”青岛,能够从容出走;即已“波及”,也只好另做打算。
“那儿去呢?回老家,干吗?总得南下,南下!”
谁晓得?看光景,北方准是先被炮火,长江流域或能稍晚?……
可是变化奇突,八一三因虹桥事件,日本兵便先从淞沪下手,青岛战事反而晚下去,直到过年以后,方才实行他们的登陆计划。
老舍先生与那年秋间尚留寓本市的几位文艺朋友,也在上海抗战极剧烈的期间,九十月内,从容离青他去。
我正在周围炮火,日夜空战的沪上,写文,讲演,他们却已由铁道或起旱,经过鲁南,转向西南各方去了。
从是时起,算到现在,整整八年有半!
老舍连年为“文协”如何尽力,如何写作,如何清苦自持,这些话都不须多提。他现在正将赴美作一年勾留。为传播我们新文艺的消息;为沟通两国(中美)的文化;为使世界人士真实认识我们的创作者,他与曹禺君此行,当有重大影响。
他在日军初降时,高兴之至!九月间写了一封信,托我为他在青岛购置一所小房子,预备仍返故处,安安逸逸的过他的战后创作生活。他想的十分平正,十分合乎情理。以为,经过这次以前未有的胜利,日本人在青岛留下了多少大小建筑物,除掉公家需用者外,定有许多所小楼房,能以廉价出售。他知道我先回此,地方熟悉,所以趁此时机,想买下所小巧住房,以供晚年——就说是晚年罢!反正他比我还大几岁,——读书安居之用。虽然他没有财力,但以想象中的廉价,他在可能范围内拮据集凑,也还可以。
太平直了!太坦然了!那能料到“事实”,“事实”,如是,如是。不但用廉价买日人剩下的小房无从说起,就连那封信到沪后,经友人代寄青岛,(那时还没有青沪航邮)你想怎么样?今年一月中旬我方收到。在途中,或搁置在邮局之中总逾百天!——还能讲“甚么”其他?
也好!他暂时并不来青,到“新大陆”上看看战后的盟邦。采风问俗,自由谈说,交几个文艺朋友;若有便能往南美逛逛,更为有趣。
也许,一年之后他可重来青岛?纵然无法买到一所小房,我若在此却能给他预备间比较适宜的住室,再过过我们当年饮“苦露”,走沙滩,豁快拳……的生活。
希望如此!光阴迅过,即使再聚,也未必还能提起当年的豪兴。但:
“一枝好烟,一杯醇酒,一声凄叹,一霎相对的回忆,一些不易谈数的言语。——斑发皱颜,彼此在苦痛,忧悒,幽愤,岑寂中熬练过的心情,还可交换一下?”
明年夏日,盼望能够同他在海滨公园小亭子里,指点沧波,东谈西扯,眼望着上下飞鸣的海鸥自由翔集。
三十五年,二月四日。
抗战胜利后惨淡的现实、文化人可贵的友谊、普通民众的无奈与苦涩,一切尽在王统照的这篇不长的文字里展露无遗,毋庸辞费。需要补充说明的只有两点。第一,这篇文章的确切出处是青岛的《民言报》副刊“潮音”第21期,作者署名剑三,这是王统照的字,也是他最常用的笔名之一。曾广灿、吴怀斌所编的《老舍研究资料》(22)曾广灿、吴怀斌编《老舍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在“老舍研究资料散见篇目索引”部分准确著录了相关信息。第二,王统照此文中“一枝好烟,一杯醇酒,一声凄叹,一霎相对的回忆,一些不易谈数的言语。——斑发皱颜,彼此在苦痛,忧悒,幽愤,岑寂中熬练过的心情,还可交换一下?”这一句话,清清楚楚地是放在引用符号,即“「」”——这是民国时期繁体竖排文字的印刷习惯——之内的。仔细体会其语言风格及其上下文,这句话很有可能是从老舍的信中摘出的。诚如是,则可视为老舍的一段佚文。
青岛对于抗战胜利后的老舍而言意味着什么?写于1941年的“话剧歌舞混合剧”《大地龙蛇》早就留下了一个颇富深意的安排。这部带有未来与“空想”色彩的剧本第三幕,时间延伸到“大中华民国五十年春”,地点设置便是“青岛”。但有意思的是,作为这一幕的主题的“和平节”,并未在老舍的笔下得到正面的展示。众人口中反复谈论,乃至在这“没有斗争,没有戏剧”(23)老舍:《大地龙蛇》,《老舍全集》(修订本)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第360页。的一幕里造成小小“斗争”的,其实是赵立真任馆长的水族馆开幕典礼。围绕这个活动,赵立真的妹妹赵素渊遗憾地放弃了陪学生参加和平节大游行,赵立真的族弟赵明德表达了对“国家派大哥养着那些鱼”(24)同上书,第413页。的不解,但最后也期待当“小鱼馆”的馆长,印度友人竺法救也赶着典礼来送标本做礼物……凡此种种,为这一幕场景平添了喜剧的氛围。
《大地龙蛇》第一幕里,赵立真还是“一天到晚净弄小鸟和毛毛虫”(25)同上书,第363页。,二十年过去,怎么就转而管理起了水族馆?在老舍笔下,这些生物学研究都表征了一种科学主义的改造世界的想象。用赵立真自己的话说,“拿各处送来的标本为题”,他就可以“说明世界上的人已经知道了注重科学,爱护科学;也就是知道了拥护真理,支持真理;也就是开始创造和平,扩大和平”,“全人类要是都同舟共济的征服自然,开发自然,大家就不必彼此争夺而有吃有喝,就足以消灭自然加给我们的祸患”……(26)同上书,第417页。
诚然,老舍在剧本前的“序”中明确提出“第三幕设景青岛,亦因取景美丽,无他用意,也可以改换”。(27)同上书,第360页。可是从剧本的思想脉络观察,青岛恐非只是因为“美丽”而被老舍选中。相反,因为这里有一座水族馆,青岛这一“装置”构成了一个关键的叙事框架和结构性要素,不能被轻易取代。
当然,“美丽”也不是不重要。第三幕的布景,老舍介绍赵立真兄弟的小园,就是在“青岛市郊,面碧海星岛,茅亭一间,环以花木”,而且“园与海之间有马路,夹路青桐,隐隐可见”。(28)同上书,第407页。如果说水族馆代表了“真”——就像它的负责人的名字赵立真所显示的那样,世界和平、族群大同蕴含了“善”——比如剧本中的日本人马志远干脆入了“华籍”,那么青岛在老舍笔下显示出来的“美”,则为他的这份理想加上了不容缺失的一个维度。从这个意义上说,老舍致王统照的信中寄托于青岛的,既有他在这座城市的真实生活体验,更有他对未来光明世界的热切梦想。
——An Idea From "Etudes Metro"—the Work of Pierre Schaef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