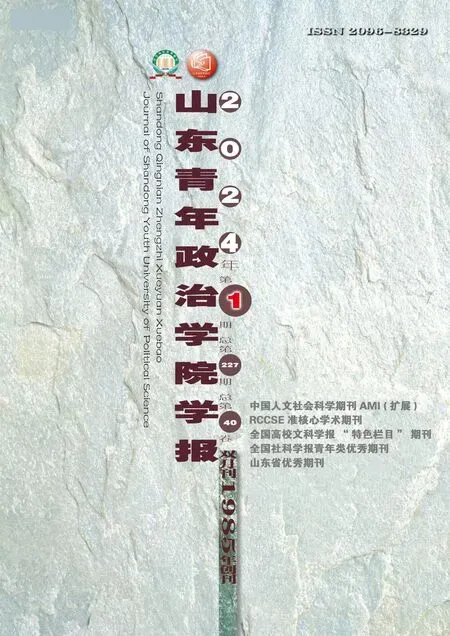1949年之前关于鲁迅古籍整理的研究述评
马慧慧
(聊城大学 文学院,聊城 252059)
古籍整理工作,贯穿鲁迅生命的始终,是鲁迅学术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探寻关于鲁迅整理古籍工作的研究,有益于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一个总体全面的认识,并对长期以来被人们忽视的“学者鲁迅”的形象有所补充。所谓鲁迅古籍整理的研究,主要指的是对鲁迅古籍整理工作的学术成果、治学理念和方法、学术贡献的介绍和评价。关于鲁迅古籍整理研究的综述不多,比较重要的是石祥的《鲁迅辑校古籍研究述评》。他将研究成果按照集部古籍、小说文献、子史典籍、乡邦文献以及鲁迅与文献学、古籍整理关系五类逐一加以述评,并指出现有研究存在选题冷热不均、缺乏阐发学术史意义以及研究深度和密度都有待提高的问题。(1)石祥:《鲁迅辑校古籍研究述评》,《图书情报工作网刊》2012年第9期。这篇论文不仅总结了关于鲁迅古籍研究的现状,而且对现有研究的问题作出说明,但缺乏对1949年之前关于鲁迅古籍整理研究的观照。此外,鲍国华《“小说史家鲁迅”研究的历史回顾》对各个时期鲁迅小说史研究作出全面回顾,并结合研究者的学术理念和学术环境,考察其理论得失及其学术史价值,其中1949年之前的小说史研究也涉及鲁迅古籍整理的方面(2)鲍国华:《“小说史家鲁迅”研究的历史回顾》,《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2期。,但篇幅不多,对鲁迅古籍整理未能详细介绍。1949年之前的研究包括对鲁迅古籍整理情形的回忆性记述和古籍具体内容的分析,本文将着眼于主要的研究者及其观点,展现1949年之前鲁迅古籍整理的研究状况。
一、关于鲁迅古籍整理情形的回忆性记述
周作人、蔡元培以及许寿裳和鲁迅在生活中都有过密切交往,他们对于鲁迅整理古籍的具体工作情形有过近距离的观察和了解。周作人作为鲁迅整理古籍的助手,帮助整理《会稽郡故书杂集》《古小说钩沉》和《小说备校》,参与查书、抄写、校对和出版等过程。蔡元培早年和鲁迅同在教育部任职,对其整理古籍有所了解,并且关注到鲁迅整理古籍与清代学术传统之间的联系和超越。许寿裳对鲁迅在日本留学和绍兴会馆这段时期整理古籍的情况有较多了解。通过他们的记述,可以了解鲁迅早年整理古籍的情形。此外,1938年《鲁迅全集》出版后,编者在回顾的文章中也有关于鲁迅整理古籍的记述。
周作人出于记录“鲁迅的学问与艺术的来源”(3)知堂:《关于鲁迅》,《宇宙风》1936年第29期。,写下《关于鲁迅》这篇纪念文章,希望“事虽细微而不虚诞,世之识者当有取焉”(4)知堂:《关于鲁迅》,《宇宙风》1936年第29期。。在此文中,他将鲁迅的工作分为两大类,甲类是搜集、辑录、校勘和研究,乙类是鲁迅的创作。周作人这样列举:
甲部
一,《会稽郡故书杂集》。二,谢承《后汉书》(未刊)。三,《古小说钩沉》(未刊)。四,《小说旧闻钞》。五,《唐宋传奇集》。六,《中国小说史》。七,《嵇康集》(未刊)。八,《岭表录异》(未刊)。九,汉画石刻(未完成)。
乙部
一,小说:《呐喊》,《彷徨》。二,散文:《朝华夕拾》,等。(5)知堂:《关于鲁迅》,《宇宙风》1936年第29期。
在周作人列出的甲部中除了《中国小说史》(即《中国小说史略》)和《汉画石刻》,其他都属于鲁迅古籍整理的工作,可见他认为这在鲁迅的学术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
周作人认为鲁迅的治学和创作有其独特的地方,他评价道:“这些工作的成就有大小,但无不有其独得之处,而其起因亦往往很是久远,其治学与创作的态度与别人颇多不同,我以为这是最可注意的事。”(6)同上。所谓治学的不同,主要是鲁迅整理古籍的兴趣偏重古代小说、乡邦文献和乡人著作方面。据周作人描述,鲁迅自日本归国到为《新青年》写稿之前这一段时间内,“一面翻古书抄唐以前小说逸文,一面又抄唐以前的越中史地书”(7)同上。,辑书的成绩包括《会稽郡故书杂集》(凡八种)、《古小说钩沉》和谢承《后汉书》。
周作人认为鲁迅对于古籍特别是乡邦文献的整理,是受清代文献学家张澍辑录《二酉堂丛书》的影响。《二酉堂丛书》收录36种古籍,其中21种辑录唐代以前有关凉州地区(今甘肃、宁夏地区)的文献。鲁迅受其影响,开始收集乡邦古籍,后来刻印成《会稽郡故书杂集》以传承故土文化。他在《会稽郡故书杂集》的序中曾有提及:“幼时,尝见武威张澍所辑书,于凉土文献,撰集甚众。笃恭乡里,尚此之谓。而会稽故籍,零落至今,未闻后贤为之纲纪。乃创就所见书传,刺取遗篇,絫为一袠。”(8)鲁迅:《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35页。可见鲁迅对于家乡古籍散落现状的不满,出于传承文化的考虑,开始着意搜集会稽古籍。
此外,周作人还说明《会稽郡故书杂集》和《古小说钩沉》是鲁迅的成果,而不是自己的成果。他回忆道,《会稽郡故书杂集》曾使用周作人的名义刊行,《古小说钩沉》因资财受限,最终未能出版,但《<古小说钩沉>序》还是使用周作人的名义发表。鲁迅选择署名周作人而不是自己的名字,一方面周作人在鲁迅整理古籍的过程中曾帮助搜集和抄写材料、校对和刊印全书(9)顾农:《周作人——鲁迅整理古籍的重要伙伴》,《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2期。,兄弟齐心合作,不分彼此,鲁迅甘愿退居人后。另一方面如周作人所说鲁迅此举是“不求闻达”(10)知堂:《关于鲁迅》,《宇宙风》1936年第29期。。他说:“这就是证明他做事全不为名誉,只是由于自己的爱好”,“实在只如上文所说不求闻达,但求自由的想或写,不要学者文人的名,自然也更不为利”。(11)同上。可见鲁迅是抱着不计名利的态度来整理古籍,希望借此保留传统文化的精华,可以“用遗邦人,庶几供其景行,不忘于故”(12)鲁迅:《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35页。。
此外,还有两则在鲁迅逝世后采访周作人的新闻,都提到鲁迅整理古籍的情形。两则分别用白话文和文言文写成的新闻,分别由《大晚报》和《时事新报》发表,在诸多细节呈现互文关系,笔者推测是同一人所写。前者这样记述周作人的话:“在文学方面,他对于旧的东西,很用过一番功夫,例如:古代各种碎文的搜集,古代小说的考证等,都做得相当可观,可惜,后来都没有出版,恐怕那些材料,现在也都散失了,有人批评他说:他的长处是在整理这一方面,我以为这话是不错的。”(13)《鲁迅先生噩耗到平——周作人谈鲁迅》,《大晚报》1936年10月22日,第1版。另一则新闻与之相比增加了不少细节,这样记述道:
先兄治学,首本注重旧籍。南行后,因环境关系,遂不能展其所长。最初致力搜集旧籍,如《太平御览》,逐条分类而加以考据,但外间尚鲜知者。民初辑得绍兴过去之史实地志等材料甚多,用木版刊数十部名《会稽郡古书杂集》(《会稽郡故书杂集》,笔者注),在绍兴仅售出一部,其余赠送亲友,及各图书馆,自己仅留一二部。民国八年回家接眷北上,误书版为试版,遂被焚毁,至为可惜。又对古代文献极有兴趣,将唐代以前散佚小说汇集成篇,名曰《古小说钩沉》,凡四部:第一部为《汉书·艺文志》著录之书,第二部为《隋书·经籍志》小说类著录之书,第三部为《新唐书·艺文志》小说类著录之书,第四部为虽不见于史籍,而汉唐人却已引用者。(14)《苦雨斋中——周作人谈鲁迅往事》,《时事新报》1936年10月23日,第3张第1版。
笔者推测这篇新闻是作者在了解有关鲁迅的生平资料后,根据采访记录写成。因为篇末对《古小说钩沉》的介绍出自许广平《鲁迅先生撰译书录》,此文收入于1926年台静农所编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一书中。根据这一则新闻,可知鲁迅早年整理古籍先是从《太平御览》等类书中做资料整理工作,收集了《古小说钩沉》和《会稽郡故书杂集》的一些材料。
蔡元培纪念鲁迅的文章《记鲁迅先生轶事》,同样发表在第29期的《宇宙风》上。蔡元培提到以前鲁迅编辑古籍的情形:“先生进教育部以后,我们始常常见面。在南京时,先生于办公之暇,常与许君季茀影抄一种从图书馆借来的善本书。后来先生所发表的有校订本魏中散大夫《嵇康集》等书,想就是那时期工作之一斑了。”(15)蔡元培:《记鲁迅先生轶事》,《宇宙风》1936年第29期。在鲁迅逝世后,蔡元培曾有挽联,其中提到鲁迅学术工作的成就:“著述最谨严,非徒中国小说史。”(16)鲁迅纪念委员会主编《鲁迅先生纪念集》,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1937,第21页。此外,他后来在1938年出版的《鲁迅先生全集》的序言中称赞鲁迅“为新文学开山”,其工作“方面较多,蹊径独辟,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17)蔡元培:《鲁迅先生全集序》,载《鲁迅全集》第1卷,鲁迅全集出版社,1938,第1页。。他从学术、翻译和创作三个方面来总结鲁迅的毕生成就。其中在学术方面,他总结鲁迅的成就为辑录古籍,编汉碑帖、六朝墓志目录和六朝造像目录,古代小说研究,木刻和笺谱的整理。蔡元培指出鲁迅在治学态度和方法方面“受清代学者的濡染”,而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不为清儒所囿”。(18)同上书,第1页。“不为清儒所囿”体现为鲁迅的学术兴趣不是清代学者关注的经学,“而对作为经学附庸的小学和史学旁支的金石、方志则兴趣盎然”(19)陈平原:《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载王瑶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第87页。。
1938年《鲁迅全集》的编者在出版全集后,对鲁迅的生平和著作作了全面回顾,其中有对鲁迅整理古籍的记述。首先,他谈及《岭表录异》和谢承《后汉书》未能收入《全集》的原因,在于当时没有看到这两本书的原稿。其次,作者将鲁迅的学术工作与清代学术传统联系在一起,“认为鲁迅早年跟随章太炎学习,受到清代朴学严谨的治学精神的熏染。”他指出鲁迅对于古籍的辑校工作具有“精密深刻”的特点,“一字一句的异同,都不肯轻易放过”,胜过清代王谟《汉魏遗书钞》、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和黄奭《汉学堂丛书》等辑佚书籍,显示出鲁迅在整理古籍方面受清代学术重视考据和实证的深刻影响。(20)《‘鲁迅全集’发刊缘起》,《文艺阵地》1938年第1卷第3期。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是应许广平的请求所写关于鲁迅的回忆录,先后在《民主》和《人世间》杂志上连载,后来于1947年10月由峨嵋出版社在上海出版。许寿裳是鲁迅在日本留学时认识的好友,他们的友谊深厚,相识三十五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21)许寿裳:《鲁迅的思想与生活》,台湾文化协进会,1947,第1页。。在这些回忆文章中,许寿裳记载了一些关于鲁迅整理古籍的情形。比如他记载鲁迅在教育部公事之余常常钞写古书,有《沈下贤集》《谢承后汉书》《嵇康集》等。又有鲁迅1912年5月来到绍兴会馆第一天,就借走了许寿裳之兄许寿昌一本《越中先贤祠目序例》。那时鲁迅正热心于整理乡邦文献和乡人古籍,因此对于乡邦先贤的著作格外注意。这些回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鲁迅早年整理古籍的情形。
二、关于鲁迅古籍整理具体内容的研究
除了关于鲁迅古籍整理情形的回忆性记述,还有关于鲁迅古籍整理内容的研究。这些研究在关注鲁迅小说史的研究成就时,也关注到其所整理的小说古籍的成绩,包括《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和《古小说钩沉》。
(一)许广平:早期对鲁迅古籍整理工作的介绍
1926年7月台静农编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由未名社出版,内收由许广平撰写、鲁迅校订的《鲁迅先生撰译书录》。其中介绍鲁迅所做的古籍整理工作,包括第三部分“纂辑”目录下的谢承《后汉书》辑本、《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和《小说旧闻钞》以及第四部分“校订”目录下的魏中散大夫《嵇康集》十卷和唐刘恂《岭表录异》三卷。这份鲁迅著作目录不仅记录书名,还介绍作品的概况,其中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许广平在谢承《后汉书》辑本的简介中,介绍鲁迅辑本超越前人之处:“自云搜采考订,视姚之骃,孙志祖,汪文台诸家较为详密。”(22)景宋:《鲁迅先生撰译书录》,载台静农编《关于鲁迅及其著作》,未名社,1926,第119页。其次,提供弄清《古小说钩沉》编次和目录的重要材料。《古小说钩沉》在鲁迅生前未能整理出版,因为他认为“重行整理,又须费一番新功夫”(23)鲁迅:《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427页。,而且从以往整理的古籍出版情况看,读者很是寥落,因此鲁迅没有整理《古小说钩沉》,这本书始终处于未完成的状态。这本书不仅缺少序跋和作者,而且编次缺少条理。后来林辰根据许广平在书中提到的《古小说钩沉》“凡四部”体例和鲁迅手稿《小说钩沉目录》,提出《古小说钩沉》应当由五部分组成(24)林辰:《鲁讯计划中<古小说钩沉>的原貌》,载《林辰文集》第2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10,第148页。,这个推断被学界所认可。第三,详细介绍《岭表录异》的内容。许广平这样介绍《岭表录异》:“以永乐大典本为主,校以唐宋诸书所引用,补正脱误甚多。末附补遗一卷,皆大典本所无;又札记一卷,说明所据以改正之根据。”(25)景宋:《鲁迅先生撰译书录》,载台静农编《关于鲁迅及其著作》,未名社,1926,第121页。1932年,鲁迅在许广平整理的书目基础上,重新整理一份作品目录,对《岭表录异》的介绍删减了很多细节,他写道:“以唐宋类书所引校《永乐大典》本,并补遗。”(26)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184页。虽然鲁迅所写更简洁,但我们通过许广平的介绍可以了解《岭表录异》更多的细节。
(二)赵景深:关注鲁迅小说史料的整理工作
赵景深对古典戏曲和小说颇有研究,著有《小说戏曲新考》《小说论丛》《小说闲话》《中国小说论集》等。他关于鲁迅整理古籍的文章有《中国小说史家的鲁迅先生》《评介鲁迅的古小说钩沉》《读鲁迅<古小说钩沉>》《古小说钩沉补遗》。另外他对鲁迅的研究著作《中国小说史略》也有著述,有《中国小说史略勘误》(27)赵景深:《中国小说史略勘误》,《小说月刊》1940年第7期。和《中国小说史略勘误补》(28)赵景深:《中国小说史略勘误补》,《小说月刊》1940年第9期。。
赵景深在《中国小说史家的鲁迅先生》中介绍鲁迅对小说古籍的整理,包括《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和《古小说钩沉》。首先,他认为《小说旧闻钞》主要是为了“辅翼《中国小说史略》而行”(29)赵景深:《中国小说史家的鲁迅先生》,《大晚报》1936年10月22日,第5版。,与近代蒋瑞藻的《小说考证》相比,《小说旧闻钞》专注“小说考证”材料的收集而不滥收像戏曲等其他方面材料;此外注重材料来源的原始出处,根据原书校正字句。这些都是《小说旧闻钞》胜过蒋氏《小说考证》的地方。其次,他称赞《唐宋传奇集》“分辨伪作,考证源流,用力极勤”(30)同上。。一些唐代传奇存在作者错讹的问题,“经鲁迅考订以后,方才拨云雾而见真相”(31)同上。。第三,他认为《古小说钩沉》“对于中国小说史的研究上,必有很大的贡献”(32)同上。,将其与邓嗣禹《太平广记篇目及引书引得》相比,认为相比邓嗣禹《引得》“只以《太平广记》为本位而‘钩沉’”,而《古小说钩沉》是“以小说为本位而作横的辑集的”(33)同上。,肯定了鲁迅搜集广博、学识独到的优点。
赵景深特别关注鲁迅《古小说钩沉》的研究,他说:“《古小说钩沉》是常在我怀念中的一部书”,“并且也时常念念不忘于《古小说钩沉》”。(34)同上。他的《评介鲁迅的古小说钩沉》总结《古小说钩沉》的优点和缺点,例证丰富。他指出鲁迅所做的学术工作是先有搜集积累、后有阐述研究。《古小说钩沉》“辑录唐以前的小说,恰与《唐宋传奇集》相衔接,并与《中国小说史略》相辅而行,为其轮翼”(35)赵景深:《评介鲁迅的<古小说钩沉>》,《宇宙风》1938年第77期。。他认为《古小说钩沉》有四个方面的优点:首先是采辑审慎,“凡是类似的书名而不能断定的一概不收”;其次是搜罗宏富,“不仅注明某书者照收,即使注明甲书,而其中文字实引乙书者,也收到乙书一堆去”;再次是比类取断,“凡遇误注书名或不甚清晰者,均据他书断定”;最后是删汰伪作,“凡是与作者时代不合的,一律删汰不录”。(36)赵景深:《评介鲁迅的<古小说钩沉>》,《宇宙风》1938年第77期。
在缺点方面,首先赵景深认为《古小说钩沉》在编列方面存在条理不清晰的问题:
此书不注作者姓名和时代,且不完全按照《中国小说史略》所说先后排列(虽然略会分类),使人读起来颇为不便。前面似乎还缺少一个编列;不,最好像《唐宋传奇集》那样也来一篇详细的《稗边小缀》。大约这是鲁迅未竟之业,所以也只得如此了。(37)同上。
此外,赵景深还谈到四个方面具体的“小缺点”,并举出详细的例子。一是误记卷次,他推测一些误记可能是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校对者将《古小说钩沉》收进全集时出现的疏忽错误;二是辑逸未周,他认为“此点最为重要,但漏了的并不多”,并举出几条鲁迅在《太平广记》中遗漏的片段;三是辑录错误;四是臆测书名。除了这些,赵景深认为隋代杜宝所著《水饰》也不应该放进《古小说钩沉》,虽然这是研究戏剧史的宝贵材料,但放在隋以前的《古小说钩沉》中似乎不妥。最后他对鲁迅的《古小说钩沉》进行总结,认为“虽然有几个小缺点,究竟是优点多于缺点的,并且是学术界的大贡献”。(38)同上。
赵景深后来将这篇文章收进自己关于古代小说研究的《银字集》,并作了一些修改。他对于《古小说钩沉》优点的评价基本未变,在缺点方面,删去了“误记卷次”这一条,还有《水饰》不应该收入《古小说钩沉》这一建议也删去了。他在原来的结尾处加上了这一句:“因为遗辑者自己不曾整理过,疏忽之处是难免的”(39)赵景深:《银字集》,永祥印书馆,1946,第129页。,但依然认为这是一部优点大于缺点的学术著作。“遗辑者”指的是鲁迅,可见赵景深对于《古小说钩沉》未能尽善尽美的遗憾。
赵景深对于鲁迅古籍整理的研究还有《读鲁迅<古小说钩沉>》(40)赵景深:《读鲁迅<古小说钩沉>》,《文艺春秋》1946年第3卷第4期。和《古小说钩沉补遗》(41)赵景深:《古小说钩沉补遗》,《涛声》1946年第1期。。前者是一篇读书札记,补充一些《古小说钩沉》中疏忽遗漏的材料,并作简单评点。后者记载《古小说钩沉》中没有收录的材料,在文章结尾处赵景深称自己的工作“只是做一个开路的马前卒罢了”(42)同上。,可见作者的谦虚作风。
总之,赵景深在广博知识的基础上,往往能够阐发细微,对鲁迅的古籍整理工作作出确当的评价,并指出一些疏忽遗漏的地方。这种“不虚美不隐恶”实事求是的态度,使赵景深对鲁迅的古籍整理作出客观的评价。
(三)阿英:重视鲁迅小说研究与整理的事业
阿英在20世纪30年代对晚明和晚清时期古代小说的研究用力极深,著作有《晚清小说史》《中国俗文学研究》《小说闲谈》《弹词小说评考》等,编著有《晚明小品文库》等。
阿英的《作为小说学者的鲁迅先生》发表于1936年11月,和赵景深的《中国小说史家的鲁迅先生》一样,都是为纪念鲁迅而写的文章。由于他们二人都对古代小说有所研究,因此关注到鲁迅在古代小说研究与整理方面的成绩。在古籍整理方面,首先,阿英提到《古小说钩沉》始终未能出版的缘由,在于鲁迅认为还有修订的必要。其次,他认为《小说旧闻钞》在材料的选择上优胜于蒋瑞藻的《小说考证》,尽量选择原本誊抄,体现了鲁迅谨严的编选材料的态度。再次,他认为鲁迅的《唐宋传奇集》考证详实,“于各篇所据本子,作家事略,可以互发的考证补充资料,无不详及”(43)张若英:《作为小说学者的鲁迅先生》,《光明》1936年第1卷第12期。,而且《唐宋传奇集》在编辑体例、材料选择和校勘方面都十分严谨,“与通行之唐宋小说辑本,迥然不同”(44)同上。。
阿英对鲁迅的中国小说研究与整理工作评价很高,他说:“中国的小说,是因他而才有完整的史书,中国小说研究者,也因他的《中国小说史》(《中国小说史略》,笔者注)的产生,才有所依据的减少许多困难,得着长足的发展。”(45)张若英:《作为小说学者的鲁迅先生》,《光明》1936年第1卷第12期。又说:“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是一部对中国小说研究极重要的书……特殊是关于古代的钩沉部分”,“鲁迅先生,作为一个小说学者看……替我们在为蒙茸的杂草所遮掩的膏腴的地域里,开拓了一条新的路,替我们发掘了不少的宝贵的珍藏”。(46)同上。此外,阿英称赞鲁迅整理小说古籍严谨的态度,认为他“以历史的,同时又是考据的态度,来从事整理,成‘史’而又可‘信’,这是在方法上最见卓识的地方”(47)同上。。
此外,阿英还指出由于一些小说古籍材料发现较晚,鲁迅未能对这些古籍进行充分的整理和研究。这些小说资料,有《玉轩新纂古今书目》和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东京大连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新发现的元明话本《警世通言》《鼓掌绝尘》《清平山堂话本》,还有辑录许多小说史料的《金瓶梅词话》。
(四)郑振铎:鲁迅治学不以考据和校订为止境
郑振铎写了《鲁迅先生的治学精神——为鲁迅先生周年纪念作》《鲁迅的辑佚工作——为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而作》来纪念鲁迅,特别指出鲁迅学术工作的成绩。
在第一篇文章中,郑振铎提到鲁迅的古籍辑校工作。首先,他认为鲁迅的小说史研究与小说材料的整理密不可分。《中国小说史略》材料的充实和考证的严密,很大一部分得益于鲁迅前期整理的《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以及《小说旧闻钞》。其次,他指出鲁迅整理古籍不以考据和校订为止境,有“尖锐的考察,精密的分析,而以公平的态度下判断”(48)郑振铎:《鲁迅先生的治学精神——为鲁迅先生周年纪念作》,《申报》1937年10月19日,第5版。。在搜集材料和考证的基础上,鲁迅以科学的态度和眼光去考察,然后作出自己的学术判断,这是他超越古代学者的地方。从郑振铎的观点可以看出,鲁迅与古代学者学术目标和方法有所不同。古代以辑佚和考证为重,鲁迅则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并以此来统筹材料,但他在辑佚和考证方面下的功夫也不逊于前代学者。
在第二篇文章中,郑振铎称“鲁迅先生的辑佚工作,和他的创作及翻译是‘三绝’”(49)郑振铎:《鲁迅的辑佚工作——为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而作》,《文艺阵地》1938年第2卷第1期。,肯定鲁迅古籍整理工作的重要性。郑振铎称赞鲁迅的古籍整理有许多胜过前人的地方,比如《古小说钩沉》的许多小说材料是清代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中所没有的,两者重合的辑佚书目只有八种,而在这八种中,鲁迅所辑的材料也比马国翰的丰富,可见“鲁迅的辑佚工作的细密有序”(50)郑振铎:《鲁迅先生的治学精神——为鲁迅先生周年纪念作》,《申报》1937年10月19日,第5版。。诚如郑振铎所言:“鲁迅所见的书并不是什么冷僻罕见的书。只因为他较精细,较谨慎,故便抓搜得更多了。”(51)同上。还有《唐宋传奇集》扫清《唐人说荟》等伪书的迷惑,使唐代小说的真正面目重现于世。同时,郑振铎也指出鲁迅的辑佚工作的不足。比如他对《古小说钩沉》的未完成之处就表达了遗憾:
在鲁迅先生的辑佚工作里,《古小说钩沉》最为重要,却可惜是未完成之作,虽经写定清本,却未及著作序跋,说明每一部辑出的古佚书的作者及原书卷帙、搜辑经过,像他在《会稽郡故书杂集》所著的序跋一样。这是我们所最引为遗憾的;因为没有了这些序跋,便不易见出他艰苦搜辑的经过。(52)同上。
1938年版的《鲁迅全集》只收录《古小说钩沉》,而《<古小说钩沉>序》一直到1946年唐弢的《鲁迅全集补遗》出版,才得以重新面世。序文最初发表于民国元年二月的《越社丛刊》第一集上,随着时间流逝,逐渐被人们遗忘,以致郑振铎误以为鲁迅没有为《古小说钩沉》撰写序文。
(五)台静农:集鲁迅小说史料整理研究之大成
台静农关于鲁迅古籍整理研究的文章有三篇,分别是《鲁迅先生整理中国古文学之成绩》《<古小说钩沉>解题》和《鲁迅先生的一生——在重庆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的一个报告》。
1939年台静农发表《鲁迅先生整理中国古文学之成绩》,全文篇幅很长,举例丰富,主要介绍鲁迅的小说史研究和小说史料的整理工作。编者在文后有附志:“原文有尚《会稽故郡杂集》(《会稽郡故书杂集》,笔者注)和《嵇康集》两章,因限于篇幅,祗得割爱,特向作者与读者致歉意。”(53)孔嘉:《鲁迅先生整理中国古文学之成绩》,《理论与现实》1939年第1卷第3期。由此可知,台静农的原文还涉及《会稽郡故书杂集》和《嵇康集》的分析,可惜现在没有机会看到全文。
关于鲁迅小说研究与史料整理的关系,台静农这样形容:“兹以《中国小说史略》为首,而以《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附之。因此三书皆为《中国小说史略》之副册”(54)同上。,指出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台静农认为鲁迅前期整理的古代小说资料,是完成《中国小说史略》不可缺少的准备工作。这些史料的积累使鲁迅了解关于古代小说的资料,发现一些流传已久的讹误,并对此作出确当的考订。他认为把《唐宋传奇集》的《稗边小缀》和《中国小说史略》对读,最能看出鲁迅谨严的考证态度:“两书同属考订,然一为长编,一为定文,凡定文中所引所略,益见匠心,而《小说史》的谨严史例,亦于此见之。”(55)同上。在对比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在《中国小说史略》和《稗边小缀》中的不同表述后,他认为前者“史笔重简核,故不铺陈”(56)同上。,而后者可以了解“先生搜讨之勤,与夫取舍之精审也”(57)同上。。
具体到鲁迅整理的小说史料成果,台静农首先介绍《古小说钩沉》,他认为《古小说钩沉》“用功至勤,搜罗最富,魏晋六朝散佚的作品,可说尽于此矣”(58)同上。,而且纠正清代学者重经史不重小说辑佚的风气。另外,他对《古小说钩沉》前面没有原书卷帙的介绍感到遗憾,这与赵景深、郑振铎的想法一致。因此,他根据《中国小说史略》和各史书的艺文志,代拟36种小说源流的序文,希望“是虽未见先生之序文,于此亦可以互见其大要,今移置于此,以供读者之参考”(59)同上。。由于当时是抗战时期,一些资料难以获得,这篇小序并不完整。台静农说:“山居不易得书,俟后补入之”(60)同上。,但这毕竟是早期对《古小说钩沉》补充完整的尝试。他后来写的《<古小说钩沉>解题》比这一篇更加完整和丰富,综合考察许多材料后撰写完成。其后林辰、顾农等人继续这一工作,根据鲁迅手稿等新材料撰写小序,使《古小说钩沉》趋于完整。
其次,台静农认为《唐宋传奇集》的考证“将一切纷误,廓面清之”(61)同上。,考证的方面涉及“撰者之生平”“撰人之误题”“篇名之误题”和“关于故事之渊源及后来之影响”,详细介绍鲁迅整理《唐宋传奇集》的经过。
再次,台静农认为《小说旧闻钞》不只是名字所显示的小说搜集整理的应有之义,“实有总结旧闻,考证旧闻之意,使人读其书并知其渊源与演变”(62)同上。,并详举其例,显示了鲁迅考证的精到之处。他这样介绍《小说旧闻钞》及其分类:
是书分类为:(一)以小说为纲,得四十一部;(二)源流;(三)评刻;(四)禁黜;(五)杂说。末附以引用书目。计引用书有七十六种,其未通观全部者,仅王坼《续文献通考》止阅其《经籍考》而已。(63)同上。
台静农的这篇文章系统介绍了鲁迅古代文学整理与研究的成绩,论证充分,概述全面,林辰评价这篇文章“是关于鲁迅整理古籍方面的较早的一篇名作”(64)林辰:《怀台静农先生》,载《林辰文集》第3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10,第282页。。
《<古小说钩沉>解题》是台静农1946年接受台湾大学中文系的聘请赴台后所写,发表在《台湾文化》上。台静农详细地介绍了《古小说钩沉》的36种小说中的29种,内容较之前只是参照《中国小说史略》和各种《艺文志》的序文更加丰富。值得一提的是,台静农在正文之前还写了一篇序文,对《古小说钩沉》评价甚高:
鲁迅先生之《古小说钩沉》,仅有一总序,民国元年假其二弟作人之名,载于《越社丛刊》。全书合魏晋江左作者,得三十六种,虽坠简丛残,难复旧观,然治小说史者,欲考古说,舍此莫由。顾先生生前,未及一一叙其源流,读者殆莫窥其端绪。兹检旧籍,略为解说,其无可考者,仍付阙如。至辑录之勤,校完之精,则非浅学所能知也。(65)台静农:《古小说钩沉解题》,《台湾文化》1948年第3卷第1期。
另外,台静农还有一篇《鲁迅先生的一生——在重庆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的一个报告》(66)台静农:《鲁迅先生的一生——在重庆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的一个报告》,《抗战文艺》1938年第2卷第8期。,解释鲁迅整理《嵇康集》的原因,认为是其借整理古籍寄寓他面对黑暗现实的苦闷情绪和无法尽情抒怀的忧思。
(六)其他研究
除了以上这些研究,还有一些零散的研究。如唐弢对鲁迅《<古小说钩沉>序》的发现,钧相《<小说旧闻钞>读后记》(67)钧相:《<小说旧闻钞>读后记》,《中国商报》1940年7月17日,第5版。和斯文《<古小说钩沉>探源》(68)斯文:《<古小说钩沉>探源》,《天津华北新报》1944年12月18日,第3版。。
唐弢对于《<古小说钩沉>序》的发现,弥补了《古小说钩沉》没有序的遗憾。唐弢在《<鲁迅全集补遗>编后记》中提到:
《<古小说钩沉>序》发表于民国元年二月的《越社丛刊》第一集上,是戴望舒先生借抄的。……本文与《儗曲序》一起,用周作人的名义发表。周作人《关于鲁迅》一文中说:“其辑录的古小说逸文也已完成,定名为‘古小说钩沉’,当初也想用我的名字刊行,可是没有刻板的资财,托书店出版也不成功,至今还是搁着。”序文借署,自属无疑。兹姑从发表年月,定为一九一二年,但其撰作日期,恐怕要较早于此的。(69)唐弢编《鲁迅全集补遗》,上海出版公司,1946,第386-387页。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唐弢考证鲁迅佚文谨慎细密的态度,不从孤证,多方求证,保证佚文的真实可靠。他后来继续辑佚鲁迅作品,将搜集到的《<中国小说史略>再版附识》和《小说备校》收录在《鲁迅全集补遗续编》一书中。
钧相在《中国商报》上发表一篇《<小说旧闻钞>读后记》,分两期登载完成。他首先指出《小说旧闻钞》胜于蒋瑞藻《小说考证》的地方:一是只收小说材料,其他材料不收;二是使用原书材料;三是文章“力汰重复”,行文简洁。其次,他认为鲁迅不仅提供小说资料,而且对这些材料进行考证辨伪,使读者受益匪浅。再次,他指出《小说旧闻钞》没有将晚清几部著名的小说收入,不够完备,如韩邦庆《海上花列传》、李汝珍《镜花缘》、刘鹗《老残游记》和曾朴《孽海花》。
斯文《<古小说钩沉>探源》对《古小说钩沉》辑录的先秦至隋代古小说三十六种的作者进行考证。除了一些佚文的作者已不可考外,他还根据陆侃如《中国文学史简编》、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辞源》等书撰写十六位作者的小传。值得一提的是,这篇文章发表在1944年12月的《天津华北新报》上,该报是日伪当局为了加强华北地区的报纸管控所创办。在此,作者为了规避检查,将《古小说钩沉》的作者写成“周树人”而不是“鲁迅”。
三、这一时期研究的意义与不足
如上所说,这时期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鲁迅古籍整理的回忆性记述,研究者作为和鲁迅同时代的人,在回忆和总结鲁迅生平成就时,关注到他在古籍整理方面的成就。二是对鲁迅古籍整理内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小说古籍方面,肯定他对小说整理和研究的开创之功。
总的来说,这时期的研究作为鲁迅古籍整理研究的开始阶段,研究者多从史料层面评价鲁迅的成绩,肯定他搜集全面和治学严谨的优点。一些研究者如蔡元培、郑振铎和台静农等人还关注到鲁迅在治学兴趣、研究方法和观点方面具有现代学术新质。这时期研究也有一些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主要关注鲁迅的小说古籍整理工作,而对其他乡邦文献、集部古籍和子史典籍关注较少。因为鲁迅整理的小说古籍与其他古籍相比出版较早,所以研究者的目光也多聚焦在这一方面。关于鲁迅整理古籍在1949年之前的出版情况,《百喻经》《会稽郡故书杂集》《小说旧闻钞》和《唐宋传奇集》在其生前出版,《古小说钩沉》和《嵇康集》1938年被收入《鲁迅全集》。其中《百喻经》是鲁迅1914年为庆祝母亲六十生寿托金陵刻经处所刻印,《会稽郡故书杂集》1915年以周作人名义发行,鲁迅后来很少提起这两部书。在1932年鲁迅编订的译著书目上,在整理的古籍方面,他列举已经出版的《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以及未出版的《岭表录异》《嵇康集》《古小说钩沉》和谢承《后汉书》。此外,鲁迅晚年曾打算集印“三十年集”,前后列出两种不同的编目。在第一种中,只列举《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和《小说旧闻钞》等小说古籍,与《中国小说史略》一起构成小说史研究体系,鲁迅为这个系列起名为“说林偶得”。在第二种编目中,鲁迅只列举以上三种古籍,不再提“说林偶得”的名字,除此之外,他还增加“起信三书”(70)鲁迅:《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519-520页。。据许广平回忆,这三书指的是《嵇康集》《岭表录异》和谢承《后汉书》。(71)许广平:《许广平忆鲁迅》,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第141页。这两种编目以小说古籍为主,这些作品问世较早,且出版时间相距不远,与《中国小说史略》“构成‘史料-史论-文本’相结合的完整的中国小说史研究体系”(72)鲍国华:《作为方法的史料——重读鲁迅<小说旧闻钞>》,《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因此受到研究者的青睐。除了《嵇康集》1938年随着《鲁迅全集》的出版受到关注之外,其他古籍因为没有出版,也就难以进入这一时期研究者的视野。
其次,与同时期关于鲁迅创作、思想等方面的研究相比,关于古籍整理的研究数量较少,起步时间较晚,而且缺少系统深入的研究。与《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新文学作品一问世即引起讨论和关注相比,鲁迅生前出版的《小说旧闻钞》和《唐宋传奇集》等辑录古籍受到的关注较少,以致鲁迅不愿将《古小说钩沉》交付北新书局出版,原因在于他认为“看的人一定很少,折本无疑”(73)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413页。。
第三,研究者没有充分认识到鲁迅古籍整理这一学术工作的意义,以及古籍本身所呈现的鲁迅治学方法和眼光方面的独特价值。比如,这一时期,一些关注鲁迅小说史研究的学者往往将鲁迅整理的小说古籍看成史料的准备,但鲁迅所整理的小说古籍在材料的选择上,同样可以反映鲁迅治学的方法与特点。
总之,1949年之前关于鲁迅古籍整理工作的研究具有开创性,为后来研究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由于研究者们所处的时代和自身的特点,这时期的研究还处于发轫阶段,对鲁迅古籍整理的研究还不够全面深入,有待后来研究者的继续开拓。
——盐业古籍整理新成果《河东盐法备览合集简注》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