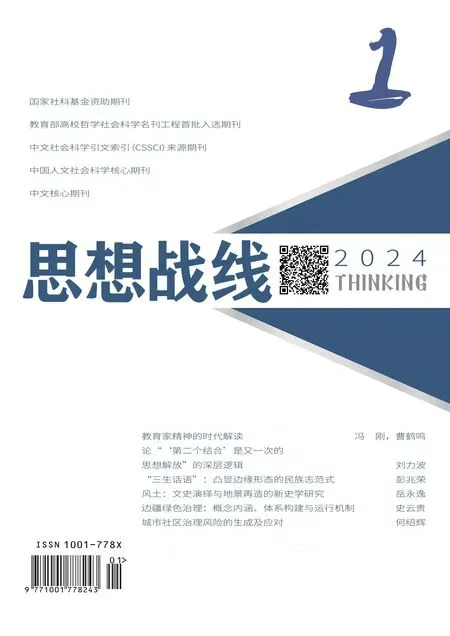风土:文史演绎与地景再造的新史学研究
岳永逸
一、引 言
作为一个具有界碑意义的学术事件,顾颉刚1924年对孟姜女故事的研究,(1)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的转变》,《歌谣周刊》第六十九号(1924年)、第七十三号(1924年)。让当时远在巴黎的刘半农叹服不已,将之誉为“二千五百年来一篇有价值的文章”!(2)刘复:《通讯:颉刚先生》,《歌谣周刊》第八十三号(1925年)。在孟姜女故事研究的基础之上,顾颉刚将章太炎、梁启超、邓实、王国维等人倡导的新史学的范围进一步拓展到“全民”与“全域”。(3)岳永逸:《终始:社会学的民俗学(1926—1950)》,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127-130页。不仅如此,在揭示出孟姜女故事日趋繁杂的历史化、社会化、民间化和地方化进程的同时,该研究还赋予了孟姜女这个“箭垛”式的故事以学术生命,(4)胡适:《胡适文集》4,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33页。使之成为百年来中国学界一个常青的话题。
新近,李志生和黄小峰对唐代虢国夫人这个历史人物的探析,一个是史学的偏重读文,一个是艺术学的偏重看图。学科不同,二者却明显有着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暗流的影响。从历史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日渐受儒家伦理道德规训、支配的文人心性的角度,黄小峰通过大量的图文考辨和对虢国夫人住宅在长安宣阳坊的还原,明确指出:两《唐书》《明皇杂录》《杨太真外传》和张祜《集灵台》《邠王小管》,薛逢《开元启乐》,郑嵎《津阳门诗》等后生的关于虢国夫人的史、文、诗的叙事,明显有有意为之或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的污名化品质,即大抵是“欲望”(色欲、贪欲、穷奢极欲)的“黑历史”。(5)黄小峰:《虢国夫人游春图:大唐丽人的生命瞬间》,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23年,第41-69页。与黄小峰对虢国夫人的“还原”止步宋代不同,李志生对虢国夫人的文本和日常生活的细读延伸到了清代。其对虢国夫人从唐到清文本衍进的梳理、对这些文本内在旨趣从“祸首”到“花仙”演进的耙梳,都意在揭示日渐成镜渊(mise en abyme)之象的虢国夫人这一历史人物的生死辩证法:肉身的从生到死,精神生命的从生到死再到生,后人叙写——神化的死(祸首)、生(花仙)之间的转换。(6)李志生:《唐虢国夫人:文本与日常生活》,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2年。
同是历史人物,杨贵妃(贵妃)的丰富性、复杂性明显胜于因她而一度风光、富贵的虢国夫人。杨贵妃,开元七年(719年)生于蜀地,幼年早孤,叔父玄珪养之。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十一月,她归于寿邸,为寿王妃。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十月,她从寿邸出,度为女道士,号太真,天宝四载(745年)七月册为贵妃。(7)《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178页;《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493页;乐史:《杨太真外传》,丁如明辑校:《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31页。原本寿王妃的杨玉环,通过入道观度为女道士从而过“关”以改换身份、象征性地“新生”。这与唐代道教和政治、权力、性别以及才能之间的复杂关系密切相关,有着必然性。参阅贾晋华:《唐代女道士的生命之旅》,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21年。与两《唐书》将杨贵妃明确称为“祸本”“贼本”稍异,唐代诗文传奇、笔记小说等言说、书写的主线大致是杨贵妃与唐明皇之间或浓烈或凄婉、或铺天盖地或遗世独立的真“情”,而非被污名化后的虢国夫人长期单一对标的“欲”。虽然不像虢国夫人在元、明、清时化身“花仙”,对让唐明皇痴迷而对历史走向有着更大影响的杨贵妃,自唐以来的文人似乎因为“情”而有着更多的认可和包容,恍若有着不能已的“了解之同情”。(8)陈寅恪:《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279页。至少,在不知不觉、身不由己中流露出的“情”不逊色于“理”。这从光绪三年(1877年)将此前对贵妃和明皇书写一网打尽的胡凤丹(1828—1889)《马嵬志》、1942年人们在重庆排演音乐家黄自(1904—1938)的清唱剧《长恨歌》,可见一斑。
在相当意义上,正史中要谆谆告诫后世的“贼本”“祸本”——红颜祸水,因为文人士大夫集团中相当一部分人心心念念的“情”,而具有了不同的意义。要明了将杨贵妃视为“情”之化身的这一历史心性、文人心性、接受美学和这一“情”所左右的凭吊、言说、叙事与地景再造、圣化,就必须有更广阔的视野。
宋人洪迈曾感慨今天被归类到文学且“无讳避”的唐诗的真实性或者说历史性的一面。他不无羡慕地写道:“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词咏寄,略无隐避。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9)洪迈:《容斋续笔》,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68页。其实,不仅唐诗,唐代士人的笔记、传奇也多有此特征。而且,诗文所述,两《唐书》也多有化用。尽管本文不拟讨论历史的“诗”性,也不拟厘清诗文的历史性,却会将同时兼具“诗”与“真”的构拟的历史(10)何兆武:《历史理性批判论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2-55页。和相关诗文记述相提并重。
二、话把儿,文史中的本末
无论生前还是身后,作为一个确实存在过的历史人物,而且是貌美多才又与圣文神武皇帝、开元盛世、安史之乱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历史人物,杨贵妃一直都在生成过程之中,不停地被跨时空也是各有心思的人言说、书写、表达与塑造。在唐代,杨妃故事,时人就“本所乐道”。(11)鲁迅:《鲁迅全集.9》,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78页。陈寅恪亦言:“唐人竟以太真遗事为一通常练习诗文之题目,此观于唐人诗文集即可了然。但文人赋咏,本非史家纪述。故有意无意间逐渐附会修饰,历时既久,益复曼衍滋繁,遂成极富兴趣之物语小说,如乐史所编著之《太真外传》是也。”(12)陈寅恪:《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12页。
在《周秦行纪》这一文人的演绎中,已经位列仙班的贵妃根本不记恨自己的被赐死,对她的“三郎”忠贞不渝,还给落第的牛僧孺吟诗一首:“金钗堕地别君王,红泪流珠满御床。云雨马嵬分散后,骊宫不复舞霓裳。”(13)牛僧孺:《周秦行纪》,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3317-3319页。要说明的是,基于假小说以施诬蔑、排谄、攻击人的前在认知,鲁迅认为《周秦行纪》的作者不是牛僧孺,而是其政敌李德裕的门客韦瓘。参见鲁迅:《鲁迅全集.9》,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74、323、96-97页;《鲁迅全集.10》,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22-125页。就“牛李党争”,也有人通过二人的赏石进行了别开生面的呈现,参阅黄晓,刘珊珊:《辞采与门第:唐代赏石的牛李之争》,《读书》2023年第12期。一如既往,在这个文本中发声的杨贵妃是被代言的。在文人士大夫不断叠加的演绎中,杨贵妃始终是“失声者”。
1、貌美如花
杨贵妃未进宫前,不缺美色的明皇是任性的,后宫也是热闹的。明皇自己常和妃嫔玩“随蝶所幸”的游戏。他让妃嫔养花插花,自己亲放蝴蝶,看蝴蝶停歇在哪个妃嫔的鲜花上,就由那位妃嫔侍寝。为了争得皇帝的临幸,妃嫔自己也玩投钱赌侍明皇寝的游戏。(14)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丁如明辑校:《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68页、第92页。在这个原本你追我逐、“其乐融融”的局面下,杨贵妃能获得“六宫粉黛无颜色”的专宠,肯定不仅仅是其丰满的娇无力,光彩焕发、转动照人的美貌。与美貌一体的才艺、气质,在音律与舞美等艺术上的相通应该同样是关键所在。
《新唐书》言,姿质天挺的贵妃“善歌舞,邃晓音律,且智算警颖,迎意辄悟”。(15)《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493页。《旧唐书》言,太真“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智算过人。每倩盼承迎,动移上意。宫中呼为‘娘子’,礼数实同皇后”。(16)《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178页。虽是演绎,陈鸿《长恨传》所言同样是有力的佐证:有意冶其容、敏其词、婉娈万态的贵妃,“非徒殊艳尤态,独能致是;盖才知明慧,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容者焉”。(17)陈鸿:《长恨传》,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3298页。
天宝二年(743年),欣承诏旨、奉命填词的诗仙李白拟就的《清平调词三首》,经常被后人释读出婉讽的微言大义,但其主旨显然是贵妃的美貌和玄宗在美貌前的痴迷。李白“奉旨填词”的创作情境、现场“巨星天团”的歌唱、琴瑟和鸣的欣赏和接受效果,主要根据李濬《松窗杂录》(18)李濬:《松窗杂录》,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1308页。所载,《全唐诗》编者写就的“题注”都有交代。云:
天宝中,白供奉翰林。禁中初重木芍药,得四本红紫浅红通白者,移植于兴庆池东沉香亭。会花开,上乘照夜白,太真妃以步辇从。诏选梨园中弟子尤者,得乐一十六色。李龟年以歌擅一时,手捧檀板,押众乐前,欲歌之。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遂命龟年持金花牋,宣赐李白,立进《清平调》三章。白承诏,宿酲未解,因援笔赋之。龟年歌之,太真持颇梨七宝杯,酌西凉州蒲萄酒,笑领歌词,意甚厚。上因调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将换,则迟其声以媚之。太真饮罢,敛绣巾重拜。上自是顾李翰林尤异于(他)学士。(19)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703页。
对此,与李昉同时期的宋人乐史的《杨太真外传》也有记述。(20)乐史:《杨太真外传》,丁如明辑校:《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36-137页。让皇上兴起鸣笛媚妃,而妃意厚笑领的歌词具体又是怎样的呢?挥洒自如、驰思泉涌、语由信笔的李白,朦胧而又清晰地将人视——自视、旁观、情人凝视/对视——与物视的太真婉腻动人、羞花闭月的美貌一一道来: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一枝秾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21)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703页。
实际上,诗仙的这三首《清平调》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多少有着事实的依据。至少可以说,一度出入宫廷的他确实对贵妃明皇的生活日常多少有着了解。天宝年间,禁中沉香亭培育木芍药(牡丹)的成功——诸多异象在《开元天宝遗事》有载:“初有木芍药,植于沉香亭前,其花一日忽开一枝两头,朝则深红,午则深碧,暮则深黄,夜则粉白;昼夜之内,香艳各异。帝谓左右曰:‘此花木之妖,不足讶也。’”(22)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丁如明辑校:《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72页。
“云想衣裳花想容”“一枝秾艳露凝香”“名花倾国两相欢”既是抒情,也是写实。《开元天宝遗事》“助娇花”有言:“御苑新有千叶桃花,帝亲折一枝插于妃子宝冠上,曰:‘此个花尤能助娇态也’。”相信牡丹醒酒的玄宗,一次与贵妃在桃树下宴饮时认真地说:“不独萱草忘忧,此花亦能销恨。”(23)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丁如明辑校:《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74页,第86页,第78页。鉴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开元天宝遗事》采自遗民之口,“委巷相传,语多失实”的总体评价,晚生的王仁裕是根据李白诗意而敷衍成这些宫中逸史也不一定。
2、动移上意
贵妃迎意辄悟、倩盼承迎、动移上意。两《唐书》皆有载,贵妃在天宝五载(746年)、九载(750年)因忤旨而先后两次被送归外第。(24)《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179-2180页;《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493-3494页。前一次,聪颖的她回宫后“伏地谢罪”,给足了原本因谴她出宫而茶饭不思、喜怒无常的玄宗面子,恩宠如初。后一次,贵妃则引刀剪发一缭附献,以示以死相报明皇的恩情、爱情。其以死谢罪的诚心与真心,再次赢得明皇的欢心,恩宠愈隆。后边这一次情感危机之化解,早于两《唐书》的《开天传信记》的记述亦活灵活现,值得参考:“太真妃常因妬媚,有语侵上,上怒甚,召高力士以辎軿送还其家。妃悔恨号泣,抽刀剪发授力士曰:‘珠玉珍异,皆上所赐,不足充献,唯发父母所生,可达妾意,望持此伸妾万一慕恋之诚。’上得发,挥涕悯然。遽命力士召归。”(25)郑綮:《开天传信记》,丁如明辑校:《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9页。
在《杨太真外传》中,乐史也详述了贵妃两次忤旨而遭外放。就第二次外放,乐史串写了《旧唐书》和唐诗的相关记述,演绎出更多细节,尤其是批判贵妃行为的不端、杨国忠的奸诈权谋、明皇对贵妃的迟疑不舍和贵妃的机警务实。原文丰富曲折,娓娓道来,如作者亲见亲历:
九载二月,上旧置五王帐,长枕大被,与兄弟共处其间。妃子无何窃宁王紫玉笛吹。故诗人张祜诗云:“梨花静院无人见,闲把宁王玉笛吹。”因此又忤旨,放出。时吉温多与中贵人善,国忠惧,请计于温。遂入奏曰:“妃,妇人,无智识。有忤圣颜,罪当死。既蒙尝恩宠,只合死于宫中。陛下何惜一席之地,使其就戮?安忍取辱于外乎?”上曰:“朕用卿,盖不缘妃也。”初,令中使张韬光送妃至宅,妃泣谓韬光曰:“请奏:妾罪合万死。衣服之外,皆圣恩所赐。惟发肤是父母所生。今当即死,无以谢上。”乃引刀剪其发一缭,附韬光以献。妃既出,上怃然。至是,韬光以发搭于肩上以奏。上大惊惋,遽使力士就召以归,自后益嬖焉。又加国忠遥领剑南节度使。(26)乐史:《杨太真外传》,丁如明辑校:《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33-134页。
《酉阳杂俎》中贵妃观弈的小故事(27)张仲裁译注:《酉阳杂俎》,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7-19页。,同样体现了贵妃的倩盼承迎。观弈时,杨贵妃带着她那只来自康国的宠物狗。在看到玄宗可能要输时,贵妃故意把小狗放在座位旁边。会意的小狗爬上棋盘,呆萌地搅乱棋局。这让玄宗高兴不已。晚些时候,王仁裕重写了这个故事,并以“猧子乱局”名之。(28)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丁如明辑校:《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00-101页。
贵妃的乖巧,还表现在其用语奇警,比象可爱。一年冬至大雪。雪停时,后宫独处的贵妃,让侍儿敲下房檐所结的冰条玩耍。晚朝视政后,明皇回到后宫。当他问贵妃玩啥时,贵妃以“冰筯”应之。明皇对左右说:“妃子聪惠,比象可爱也。”因此,明皇将贵妃比作其“解语花”。(29)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丁如明辑校:《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90页、第96页。当然,动移上意的贵妃更是多才多艺。
3、舞掩千古
贵妃善舞,有着满满的自信,自认为“《霓裳羽衣》一曲,可掩前古”!在明皇眼中,贵妃舞又如何呢?一次,明皇与诸王在木兰殿宴饮。虽然木兰花开,明皇的心情则不是太好。乖巧的贵妃醉中舞了《霓裳羽衣曲》。结果,龙颜大悦,评说道:“方知回雪流风,可以回天转地。”(30)乐史:《杨太真外传》,丁如明辑校:《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37页、第135页。
善舞的贵妃还善琵琶,且弟子众多。《明皇杂录·逸文》有载:“贵妃每抱是琵琶奏于梨园,音韵凄清,飘如云外。而诸王公主洎虢国以下,竞为贵妃琵琶弟子,每奏曲毕,广有进献。”(31)郑处诲:《明皇杂录》,丁如明辑校:《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7页。《杨太真外传》亦云:“诸王、郡主、妃之姊妹,皆师妃,为琵琶弟子。每一曲彻,广有献遗。”(32)乐史:《杨太真外传》,丁如明辑校:《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36页。但是,对于刚进宫贫穷但善舞《凌波曲》的新丰女伶谢阿蛮,贵妃则当场赏赐了“红粟玉臂”。此外,或者与其曾在道观为女冠的这个“过渡仪礼”(the rites of passage)(33)Arnold van Gennep,The Rites of Passage,translated by Monika B.Vizedom and Gabrielle L.Caffee,Chicago;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9.有关,贵妃还善击磬。《开天传信记》言其拊摶之音,“泠泠然新声。虽太常梨园之能人,莫能加也”。(34)郑綮:《开天传信记》,丁如明辑校:《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8页。
如同赏赐初次见面的舞者谢阿蛮一样,对于善舞的同行,杨贵妃不吝赞誉之辞。《全唐诗》中收录的她唯一的一首诗《赠张云容舞》,就是赞叹其侍女张云容舞姿的。身为杨贵妃的侍女,张云容同样擅长霓裳羽衣舞。杨贵妃写道:“罗袖动香香不已,红蕖袅袅秋烟里。轻云岭上乍摇风,嫩柳池边初拂水。”(35)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4页。从诗中,我们看到的是杨贵妃对动人舞姿的沉醉和赞美。写人又仿佛是在写己。曼妙舞姿、动人舞者、现场观感、恰切的通感比拟,都不仅仅是一个舞者自身的体验,没有细致的观察和才情,没有对“艺”的推崇礼敬,没有可爱的比象,是难以写出这首“舞诗”的。《赠张云容舞》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起那首成为太上皇的唐玄宗晚年常常欷歔独吟也是自况的《傀儡吟》:(36)郑处诲:《明皇杂录》,丁如明辑校:《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4页。“刻木牵丝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须臾弄罢寂无事,还似人生一梦中。”(37)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42页。《傀儡吟》还有“咏木老人”“咏窟磊子人”之名。其作者除唐明皇之外,《全唐诗》还有天宝年间的梁锽之说(《全唐诗》,第2116页)。就该诗展现的才情、性情、顿悟与大彻大悟的哲思而言,我更愿意相信它是亲手缔造了大唐盛世又亲手将其消解而经历了大起落、大悲欢、大无奈、大孤独的玄宗所作。参见岳永逸著:《明皇打鼓,贵妃跳舞》,《读书》2023年第10期。
显然,贵妃这首“唯一”的诗与《傀儡吟》有着心灵的默契和跨时空的对话与呼应。甚或说,原本各自独立的两首诗完全是互文。合体品读时,才明白它们道出了大唐的盛衰、人生的荣枯、短暂与永恒的悖谬、生离与死别的悽惋。真人与傀儡(真假)、云容与老翁(男女)、罗袖与鸡皮(肥瘦/老少/荣枯)、舞与弄(软硬)、风柳与刻木(动静)、轻云与牵丝(刚柔)、红蕖与鹤发(浓淡)、袅袅与须臾(快慢)、动香与寂梦(虚实)、不已与一梦(长短)、云容与贵妃/老翁与明皇(观演)、贵妃与明皇(戏里戏外),等等,因为贵妃和明皇两位知音天人两界的“四手联弹”、高歌浅吟和凝视观想,观演得以自然转换。“人生一梦”的飘忽,人生苦短而捉摸不定如秋烟般的春愁,人生迟暮的不可逆转、苍凉,及时行乐、沉醉当下的苟且和迷思,都溢于言表。
无论真情、才情、性情,还是爱情,以三八虚龄缢死在马嵬坡前的贵妃,终究定格在弱柳扶风而香不已的嘉年华,以“太上至道圣皇天帝”之尊号长眠在龙盘凤息的泰陵的明皇,则定格在那位鸡皮鹤发的傀儡老翁。
三、异文,徐贤妃与孟才人
在唐代,从(主动或被动)殉情抑或“殉葬”皇帝夫君的意涵而言,还有贵妃的“前世”“来生”。那就是唐太宗的贤妃徐惠(627——650)和唐武宗的孟才人(一说王贤妃),尽管时人和后人对她们的演绎要远少于贵妃。
与后来的杨贵妃和孟才人相较,两《唐书》中的徐惠绝对是一个贤良淑德,正能量满满的“全人”与“完人”。《旧唐书》言:徐惠出生后五个月能说话,四岁能诵《论语》《毛诗》,八岁能文。因手不释卷、遍涉经史,她文思泉涌、挥翰立成、词华绮赡。在被太宗纳为才人后,徐惠很快晋升为婕妤,再迁充容。旋即,《旧唐书》的编撰者引用了徐惠劝诫太宗且让太宗“善其言”的长篇疏谏,佐证其才与德。在这篇传世疏谏中,有这样的金句:“有道之君,以逸逸人,无道之君,以乐乐身。”尤其让史官称善的是,太宗崩后,徐惠追思顾遇之恩,哀慕愈甚,发疾不自医。重病垂危中,她对亲人诉说了自己早日殉情(葬)太宗的真心诚意:“吾荷顾实深,志在早殁,魂其有灵,得侍园寝,吾之志也。”这样,因为一心求死,永徽元年(650年),逝于芳龄廿四的徐惠获得贤妃封号,陪葬在昭陵的石室。(38)《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167-2169页。
《新唐书》列传中的“徐贤妃”直接是对《旧唐书》中“贤妃徐氏”的缩写与改写。为显其才,当然也是殉情夫君和陪葬皇帝的宿命,编撰者增加其父孝德让贤妃拟《离骚》而成的《小山》的具体内容:“仰幽岩而流盼,抚桂枝以凝想。将千龄兮此遇,荃何为兮独往?”与此同时,编纂者也改写了其矢志陪侍园寝的誓词:“帝遇我厚,得先狗马侍园寝,吾志也。”(39)《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472-3473页。在这次改写中,徐贤妃自比“狗马”,更显出宋儒想彰显的皇权、男权与夫权和在皇权、男权、夫权支配下,作为女德典范的徐惠高度的“文化自觉”。
然而,或者是因为太过“正点”,因彰显妇德而被史官书写出的这个完美的徐贤妃,很少被后来的士人和凡夫俗子念想。与汗牛充栋的对贵妃和明皇的书写相较,徐贤妃和太宗的相知相遇、生同床死同穴的相濡以沫俨然被遗忘。同是“真情”,何以至此?同样值得玩味的是,在诗文基本“无讳避”的唐代,文人骚客还演绎出了一个“小号”的贵妃明皇,即以灭佛而著称于世的唐武宗李炎和他善歌的孟才人。
对于贵妃明皇旖旎雄浑、大胆张扬而风生水起、满朝风雨的情事,白居易《长恨歌》和元稹《连昌宫词》无疑在这一情事的书写史、叙事史和传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以这一“双子星座”为轴和主体,陈寅恪探究了唐代士人之间的交往习气,描摹、渲染出了那个年代以精英男性为主体的士风、礼俗。(40)陈寅恪:《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大致与元、白二人同期的诗人张祜,以“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十字赢得生前身后名。这十字出自其《宫词二首》,云:“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河满子,双泪落君前。”“自倚能歌日,先皇掌上怜。新声何处唱,肠断李延年。”(41)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5834页。
这两首宫词,究竟是广景概写还是微距特写,历来意见不一。因为那声河满子,因为双泪垂君前,因为皇帝掌怜,因为肠断,人们多数会将这两首宫词与张祜《孟才人叹并序》连带释读,认为张祜咏叹的是善歌而被武宗宠幸的孟才人。《孟才人叹并序》的正文是七绝,序则不短,交代了该诗的史实、消息的来源、传播过程和哀兴叹的创作动机。云:
武宗皇帝疾笃,迁便殿。孟才人以歌笙获宠者,密侍其右。上目之曰:“吾当不讳,尔何为哉?”指笙囊泣曰:“请以此就缢。”上悯然。复曰:“妾尝艺歌,请对上歌一曲,以泄其愤。”上以恳许之。乃歌一声河满子,气亟,立殒。上令医候之,曰:“脉尚温而肠已绝。”及帝崩,柩重不可举。议者曰:“非俟才人乎?”爰命其榇,榇至乃举。嗟夫!才人以诚死,上以诚命。虽古之义激,无以过也。进士高璩登第年宴,传于禁伶。明年秋,贡士文多以为之目。大中三年,遇高于由拳,哀话于余,聊为兴叹。
偶因歌态咏娇嚬,传唱宫中十二春。却为一声河满子,下泉须弔旧才人。(42)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5849-5850页。
在《新唐书·本纪第八》中,只述这首诗“序”提及的主角唐武宗的帝王业,未言及任何妃嫔事。(43)《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39-245页。诗序所言的唐武宗与孟才人在深宫不为人知的生死相依的情事本传于禁伶,稍后由懿宗朝重臣高璩带出宫外。这个诚死诚命的深宫情事,就是高璩亲口也是满怀伤感地讲给张祜的。《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二》中,有高璩的传。这篇短传记述了高璩是高元裕之子和历任官阶。不知是不是高璩四处叨叨武宗与孟才人情事的关系,抑情主理且要讽谏的宋儒编撰的这篇短传,还特意提及在高璩身后太常博士曹邺对他的品评:“交友丑杂,取多蹊径,谥法‘不思妄爱曰剌’。”(44)《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86-5287页。在武宗过世不久,其在深宫实践的情事很快在宫廷内外传播开来,成为禁中、文人士子茶余饭后闲谈、感慨、嚼舌头的“话把儿”“话根儿”。因为张祜的吟唱,唐末康骈(軿)《剧谈录》就“复写”了孟才人这个动人的故事,且直接以“孟才人善歌”为目。(45)康骈:《剧谈录》,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37-38页。
在《新唐书·列传第二》中,殉情武宗、生死同穴的并非孟才人,而是死后才由即位的宣宗嘉其节、赠“贤妃”的王才人。列传言,善歌舞的王才人是邯郸人,身世不详,所谓“失其世”。她十三岁入宫,性机悟,成功阴助武宗上位。其貌与为求长生不老而常年服用丹药的武宗相像,“状纤颀”,以致苑中游猎时,外人分不清都穿锦袍骑骏马的两人。因服丹药而身体恶化,武宗感到时日不多,就向陪伴在侧的王才人惜别。王才人当即表示一旦驾崩,“妾得以殉”。在武宗驾崩后,王才人如言“自经幄下”。(46)《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509页。诗文中孟才人和史书中王才人的不同,引起了比主持编撰《新唐书》的欧阳修稍晚的沈括的兴趣。沈括注意到武宗重用的朝臣李德裕《文武两朝献替记》的记述。即,有专房之宠的王妃娇妒忤旨,日夕而殒,这造成群臣对上位成功的武宗喜怒不定的惊惧。而且,李德裕言王氏为妃久矣,并非宣宗即位后的追赠。进而,沈括认为:《新唐书》所载的王妃殉情事,“疑其孟才人也”。(47)沈括:《梦溪笔谈》,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216页。
与贵妃明皇情事在其生前就成为天下事不同,徐妃与太宗、孟才人与武宗都仅仅是个人事、帝王私事和后宫事。毕竟,只有杨贵妃才让唐人感叹“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并有“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是门楣”的时谣。(48)乐史:《杨太真外传》,丁如明辑校:《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34页。毫无疑问,杨贵妃的显赫、张扬与恓惶落幕,触及时人的价值观、情感世界,甚至是泪点。虽然杨贵妃不得不身死马嵬,但其波澜诡异的生命历程所承载的意义却被文人骚客反复吟咏和铺陈,并在华夏大地上蔓延开来,直至漂洋过海,不论正反都长命不绝衰。这也使得墨客骚人对孟才人以及徐惠的叠加叙写,一直笼罩在潜存演绎的多种可能性的贵妃情事的阴影里。
四、锦靿,遗物的资源化
到宋代,对贵妃明皇的再写作,劝诫、讽喻、警醒的特色日浓。《新唐书》如此,比《新唐书》早的《梅妃传》《杨太真外传》同样如此。《梅妃传》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尚无定论。从留存文本及文本生成后的传播而言,它都是站在正统道德家立场,哀“穷独苟活”的明皇:“晚得杨氏”的他“变易三纲,浊乱四海,身废国辱”;梅妃淑雅温顺,是值得爱的,贵妃俨然河东狮吼的悍妇,是不该爱的;因为该传“咎归杨氏,故词人喜传之”。(49)佚名:《梅妃传》,李剑国辑校:《唐五代传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364页,第1367页。
《杨太真外传》则是串写了《明皇杂录》《开天传信记》《安禄山事迹》《长恨歌传》《唐国史补》以及《酉阳杂俎》等书中关于贵妃明皇事。就该书旨趣,作者自云:“今为《外传》,非徒拾杨妃之故事,且惩祸阶而已。”不但围绕“紫玉笛”对贵妃与宁王的关系捕风捉影,该书还隐晦地叙写了贵妃与安禄山的不同寻常,云:“交趾贡龙脑香,有蝉蚕之状,五十枚。波斯言老龙脑树节方有。禁中呼为瑞龙脑,上赐妃十枚。妃私发明驼使(明驼使腹下有毛,夜能明,日驰五百里)持三枚遗禄山。妃又常遗禄山金平脱装具,玉合,金平脱铁面椀。”(50)乐史:《杨太真外传》,丁如明辑校:《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46页,第140页。当然,这是对《唐国史补》“安禄山心动”(51)李肇:《唐国史补》,李肇等:《唐国史补 因话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8-19页。的继续演绎也不一定。对因杨贵妃而荣耀一时的杨家兄弟姊妹的荣华富贵、飞扬跋扈、糜烂日常的渲染,也是该书的主旨之一。不言自明,这些负面信息的增多与总体呈现,都是要婉讽太平天子。宠幸贵妃后,绝逆耳之言、恣行燕乐、衽席无别,还数次欲“私幸”虢国夫人的明皇实在不堪,甚至可以说昏聩。这在该书对安禄山的刻写中表现得明白如话。(52)乐史:《杨太真外传》,丁如明辑校:《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42页,第141页。
在贵妃缢死马嵬之后,不仅是对于“苟活”的三郎,对于睹物思人、垂垂老矣而泪点较低、动辄泪涕的明皇(当然不排除“眼泪政治学”的表演嫌疑)而言,香囊、头巾、玉磬等贵妃遗物和遗物指陈的贵妃之间,已经实现了生死转换。(53)《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181页;张仲裁译注:《酉阳杂俎》,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7-19页;郑綮:《开天传信记》,丁如明辑校:《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8页。而且,在骚人吟唱、文人写作和好事者的“口耳”之学中,在贵妃明皇和与之相关物之间,均有着镜渊之效:物被人化,人被物化,人物互化,人人互化,物物互化;我死你在,人死物在,物销香在,香散神在,神散诗在,诗亡情在,情在人在。凡夫俗子虽然没有文人骚客那么多的神游八荒,但他们却实实在在、直白甚至是粗粝地用自己的行动、实践演绎着贵妃明皇的情事,让贵妃明皇成为他们自己的。《唐国史补》“百钱玩锦靿”有载:“玄宗幸蜀,至马嵬驿,命高力士缢贵妃于佛堂前梨树下。马嵬店媪收得锦靿一只。相传过客每一借玩,必须百钱,前后获利极多,媪因致富。”(54)李肇:《唐国史补》,李肇等:《唐国史补·因话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9页。
与两《唐书》不同,“百钱玩锦靿”明言,在马嵬驿,是玄宗命令高力士在佛堂前的梨树下缢死了贵妃,而非贵妃一了百了的自缢。贵妃死后,当地一开店妇人——马嵬店媪,“获得”贵妃的一只锦靿——袜子。此消息不胫而走。好奇的路人争相前来赏玩,所谓“过客每一借玩”。应接不暇的“得宝”店妇,不但明了贵妃遗物这一“文化遗产”的价值,还有着经济头脑。居奇货的她,明码标价,“百钱一观”。前后获钱无数的店媪,实现了从文化经纪人向资本家的转型,终成富人。
不论贵妃如何死、自缢还是他缢、真死还是假死,值得玩味的是作为贵妃遗物的那只锦靿!在李肇目的明确的这一“补”写中,无论真品还是赝品,作为贵妃遗物的锦靿已经不是明皇思妃的专利品,而是民众观想、“借玩”,从而神圣自我表证、展现它自己的显圣物(hierophany)。(55)[罗马尼亚]伊利亚德:《神圣与世俗》,王建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序言第2页。在对其络绎不绝的借玩中,好奇、伤悲、慨叹或占有欲得到(虚假)满足的过客,实现了自己与高高在上、才艺双绝却肉身不在的贵妃的神遇和交际。如同其只有香如故的香囊,通过其原本穿在脚上、踩在地上的锦靿,已经香消玉殒的贵妃的气息真切地得以传接。对于当时那些“借玩”锦靿的过客——俗人而言:玉环这个杨家女子死了,杨贵妃还活着;或者说,杨贵妃死了,玉环这个杨家弱女子还活着!
在唐代,无讳避的诗文,互补也互现!“百钱玩锦靿”应该不是李肇无中生有。与李肇大致同期的喜欢“采风”的诗人刘禹锡,写有《马嵬行》一诗。诗中,根据自己从“里中儿”访得的信息,刘禹锡提及待圣驾车远,里巷窥觑场景和爱踪迹的驿站邮童私手解鞶结、传看万千而凌波袜香不歇的“口述史”。当然,在明显同情心更胜的这一口述史中,多少是延续杜甫《北征》“中自诛妺妲”将贵妃暗喻为妺喜、妲己和褒姒的这一婉讽写技(56)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404-405页。,贵妃有着“妖姬”的别名。而且,贵妃不是缢死,而是被逼吞金自尽。她“牵帝衣”“转美目”的倩盼承迎,不再具有效用。原诗如下:
绿野扶风道,黄尘马嵬驿。路边杨贵人,坟高三四尺。乃问里中儿,皆言幸蜀时。
军家诛戚族,天子舍妖姬。群吏伏门屏,贵人牵帝衣。低回转美目,风日为无晖。
贵人饮金屑,倏忽舜英暮。平生服杏丹,颜色真如故。属车尘已远,里巷来窥觑。
共爱宿妆妍,君王画眉处。履綦无复有,履组光未灭。不见岩畔人,空见凌波袜。
邮童爱踪迹,私手解鞶结。传看千万眼,缕绝香不歇。指环照骨明,首饰敌连城。
将入咸阳市,犹得贾胡惊。(57)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963页。
五、故冢,马嵬的圣地化
基于博览的诗文和对自己所处时代的不满、责任与担当,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对大唐遍布各地的官方建筑——驿站馆舍进行了想象性的复原。对他而言,与街道、官树、桥梁、水利、河渠等并列的“馆舍”,是驿舍以及官寺、乡亭等遍布州县的体面、弘敞、雅致、舒适和惬意的园林式官方建筑。馆舍可能有池、沼、鱼、舟、林、竹,融山水、万物与城郭为一体。其诗情画意,足以慰藉、安放羁客士子身心,使之相忘于江湖,而且“天下州之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弘敞”。(58)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642-643页。
目前,尚未看到唐代马嵬驿建置的具体研究以及描述。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中,对京兆府兴平县马嵬故城的记载只有寥寥数语:“马嵬故城,在县西北二十三里。马嵬于此筑城,以避难,未详何代人也。”(59)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金陵书局光绪六年(1880年)刻本,卷二第1页。危难之际,能够让明皇圣驾停留、三军与之博弈的马嵬驿,应该不会太过简陋。至少,元和年间颇有盛名的李肇,在《唐国史补》提及马嵬驿有佛堂、有梨树。亦即,与当时众多的驿站一样,马嵬驿应该是一片可以“返景入深林”的栖居之地,至少是可以一晌贪欢、喘气歇息之所。重要的是,因为贵妃之死,因为这只贵妃锦靿和最初埋葬贵妃尸身的故冢,马嵬驿不再仅仅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自然空间,也不再仅仅是大唐一个基址弘敞的驿站,而是一个在后世文人眼中充满诗情画意的人文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双重意义上的关键景观。作为贵妃的魂断之处,原本早已存在的马嵬这个地方获得了新生。反之,并非此前的马嵬,而是因断魂贵妃、贵妃冢而新生的马嵬成为后来者的圣地。
光绪三年(1877年),浙江永康人胡凤丹《马嵬志》问世。该书缀集旧闻、网络轶事,征引了从唐至清的247种文献,(60)胡凤丹:《马嵬志》,光绪三年(1877年)永康胡氏退补斋藏板,卷首“引用书目”第1-8页。计16卷,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再现与贵妃明皇捆绑一体的马嵬的唯一的志书。它以古迹、事实、词曲金石、图画服饰饮食、珍宝音乐、花卉果木、禽兽昆虫、评论和艺文为纲目,对既有相关诗文进行了耙梳汇集,洋洋大观。尤其是古迹、词曲金石二卷,更加鲜明地说明在与贵妃明皇帝有关的沉香亭、华清池、骊山等众多地点中,距离长安和洛阳都不近的马嵬是如何脱颖而出,成为关键的人文地景,而被世人念想的。
该书卷首有《骊山图》《马嵬图》和《杨贵妃小像》三幅手绘图和胡凤丹的题诗。作为舆地图,《马嵬图》标识出了马嵬坡、马嵬驿、马嵬、杨贵妃冢、马嵬山和马嵬佛寺等标志性景观。贵妃小像所绘的贵妃体态丰美,仪容鲜艳,神逸妩媚,华贵意远。在差不多一个半世纪前,有别于在精英间有限流转的关于贵妃的宫廷画和文人画,《马嵬志》中这些应该受众更广的图与像,仿若当下的VR(Virtual Reality)、AR(Augmented Reality)。它将景、人直观化、一体化,完美互现,培育着读者的视觉美感,激发着受者的超常体验、臆想与神游。
其实,仅从乾隆年间《兴平县志》卷七“明皇帝贵妃杨氏故冢”并不是太长的记述,尤其是乾隆丙戌进士,时任兴平县知县顾声雷《重修马嵬故冢记》就可知,地方人士不时重修、维护与陪护的杨妃故冢,始终在为马嵬的圣地化添砖加瓦和助燃。(61)顾声雷修,张埙撰:《兴平县志》,光绪二年(1876年)刻本,卷七第10-13页。换言之,作为地方的文化资源、名胜古迹,马嵬杨妃墓一直都是往来使者、骚人、逸士登眺、吟唱和勒石立碑的所在。而究竟讽喻还是称颂,怨恨或者同情,都无关紧要了。如是之故,马嵬驿在相当意义上不再是世俗的,不仅仅是世俗的,而具有了神圣性。甚至可以说,马嵬驿不但是窥觑、把玩锦靿之过客——凡夫俗子的圣地,更是千百年来咏物抒怀的文人骚客——另一种过客——心中的圣地。因为香消玉殒的贵妃,因为贵妃当初完好的尸身,因为其遗物锦靿,凡夫俗子和文人骚客对贵妃或猥亵或圣洁、或怨恨不已或哀伤同情的念想,都汇聚、熔铸到马嵬驿这个地方和“马嵬”这两个书写符号上。
光绪二年(1876年),胡凤丹为《马嵬志》写就了“自序”。与乐史在《杨太真外传》卷末的自白大同小异,胡凤丹编志本旨是意在劝诫。然而,情涌动于中,情大于理与智的《马嵬志·自序》开篇的一段话,不但将历代文人书写马嵬、杨妃的盛况说得清清楚楚,还将原本平凡的马嵬转型成为圣地的过程描画得明明白白。前往凭吊的文人骚客不但进行着绵延不绝的悲、慨、愤等一系列语言建构,还前赴后继地通过寻、拾、俯仰等肢体动作,在马嵬这个地方进行着“锄禾日当午”和“上穷碧落下黄泉”式的身体书写。原文如下:
马嵬,一坡耳,驿耳。非有豪杰崛起于其乡,仙佛栖灵于其地也。徒以美人黄土,埋玉此间。千百载后,骚人韵士,过而凭吊流连。寻坠履于荒烟,拾遗钗于蔓草。悲狐狸之拜月,慨鼯鼠之啸风。相与俯仰其间,魂驰魄感,惝怳怅惘,仿佛若睹其人于尺组之下。郁为淫思,倡为艳曲。寄厥闲情,传彼好事……(62)胡凤丹:《马嵬志》,光绪三年(1877年)永康胡氏退补斋藏板,“自序”第1页上。
怜香不尽千词客!每一次书写、吟诵与寻觅、凭吊,都是将杨贵妃“激活”,都是对杨贵妃的再发现、再制造与再编码。每一次朝拜,都使得当下、眼前的马嵬,回到佛堂梨树下缢死贵妃的那个瞬间的马嵬、过去的马嵬、原初的马嵬,也是对马嵬的再一次圣化与加持。
对马嵬的“恋地情结”(topophilia)(63)段义孚:《恋地情结》,志丞,刘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和对贵妃的“自我化”也就水乳交融。贵妃明皇、佛堂野草、瓣瓣梨花、三尺孤坟、为尘轻骨、锦靿香囊,相互滋养、相得益彰,都是千古词客吟诵、书写的对象与意象!原本是交通中转站、歇息站、加油站的马嵬驿,也成为不同阶层、不同时代、各色人等的心灵交换器、离合器,甚至是大功率的情感涡轮发动机。这也是在贵妃身死后对其的海量写作中,总是与马嵬捆绑一起的心理学抑或说心灵学动因,及至衍生成为众说纷纭、纷繁复杂、不绝如缕甚至浓厚的“杨贵妃文化现象”。(64)王炎平:《评历代咏马嵬诗——兼议杨贵妃文化现象》,《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其实,与其说“杨贵妃文化现象”,还不如直接说“贵妃情结”。在相当意义上,中国古代的士人集团没有西方古典的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但一直有着浓厚的贵妃情结,甚或说自恋(narcissism)进而自我封圣、志得意满的情结。当然,这里的“贵妃”不仅仅是杨贵妃,而是对以身试/护法也是以身效/祸国的所谓中国古代四大美女(其实是悲剧美女)——西施、王昭君、貂蝉和杨贵妃——的概称。这些集红颜、祸水、才艺与智慧于一身、对家国、历史都重要莫名的“贵妃”,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想左右自己,又身不由己。如误撞蛛网的飞虫,其左右手互搏的人生困境,实乃同样随时都不得不左冲右突的士人集团的群像、镜像。这在明清时期,失意文人为了强调自己的忠孝而群体性对节烈女性的推崇、塑造与颂扬达到了极致,(65)田汝康:《男性阴影与女性贞节:明清时期伦理观的比较研究》,刘平,冯贤亮译校,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终致群体性地形成了对镜贴花黄式的踌躇满志、顾影自怜的“影恋”。(66)潘光旦:《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上海:新月书店,1929年。
我手写我口,写我心!与清末民初落魄、心不甘又孤芳自赏、自怨自艾的文人对老北京天桥艺人的吟唱一样,(67)岳永逸:《空间、自我与社会:天桥街头艺人的生成与系谱》,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231-233页。历代士人集团对“贵妃”的涂抹、无奈、叹惋和凭吊,对不得不如此且只能如此的悲壮美的颂歌、挽歌与暮歌,为他们自己的生存状态也赋予了想象中的合情合理性。不难理解,在中国历史的书写中,在古中国的诗、词、歌、赋、文与画中,这种贵妃情结都挥之不去,凝聚在指端、笔尖,散布在字里行间与留白处。诅咒也好,歌颂也罢,婉讽也好,叹息也罢,如影随形,如鲠在喉。
事实上,虽然义存炯戒,要讽一劝百、挖空心思地要为“终不失为明也”(68)胡凤丹:《马嵬志》,光绪三年(1877年)永康胡氏退补斋藏板,“自序”第2页上。的明皇找补,《马嵬志》同样是对贵妃爱恨夹杂而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一种表现。而且,胡凤丹费心费力地为一坡耳、驿耳,无豪杰仙佛,仅有贵妃埋葬其间的黄土马嵬树碑立传写志,实则在无意中从另一种层面夯实、强化了马嵬驿的重要性和后生的凭吊者/朝拜者络绎不绝的圣地属性。或者,经过千年传递与沉积,生活在风雨飘摇的晚清的江南文人胡凤丹,对马嵬有着更多的恋地情结,也比任何人有着更多的贵妃情结!虽然他给《杨贵妃小像》的题跋少了文人的矜持而近于辱骂,(69)胡凤丹:《马嵬志》,光绪三年(1877年)永康胡氏退补斋藏板,卷首“图”第6页。但给《马嵬图》的题诗则道出其内心的纠结与小九九。诗云:
国门才出妃子死,生生世世今若此。香魂一缕土一堆,惨雨愁云呼不起。
桓桓敢怨陈玄礼,三郎枉自称天子。伉俪不庇庇六军,佛堂尺组伊谁使?
人亦有言拾敝履,夜半私誓犹在耳。生前恩不念床笫,南内相思空入髓。
梨花带雨泪如洗,化作坡前呜咽水。(70)胡凤丹:《马嵬志》,光绪三年(1877年)永康胡氏退补斋藏板,卷首“图”第4页下。
六、野野史(71)在本文中,“野史”是与两《唐书》等传统意义上有专门史官和机构修订“正史”而言,是在中国社会传衍的杨贵妃的传说故事。但是,如本文所呈现:正史同样有着主观性、时代性,有着对坊间里巷的遗闻、诗文记叙的抄录、改写。“野野史”则是相对“野史”而言,主要指在日本因杨贵妃而生成的遗迹、图像、仪式实践和口头叙事等。,漂洋过海的名实
当然,也可以残酷地说:与顾左右而言他的士人集团抑或说踌躇满志、总觉郁郁不得志的文人不同,原本弱势的黎民百姓,不但同样消费、再造着贵妃,还借贵妃锦靿,了然无痕地侵蚀着明皇的至高无上、大唐的辉煌和士人的脸面。
在《太平广记》中,或者因为时过境迁,或者故意要吸引人眼球而找一噱头,“百钱玩锦靿”这则逸史没有采用刘禹锡的“凌波袜”,而是直接易名为“杨妃袜”。与两《唐书》不同,“杨妃袜”保留了玄宗、力士、马嵬、佛堂、梨树、店媪、锦靿、过客等核心要素。表述更简洁的“杨妃袜”如下:“玄宗至马嵬驿,令高力士缢贵妃于佛堂梨树之前。马嵬媪得袜一只。过客求而玩之,百钱一观,获钱无数。”(72)李昉等:《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2709-2710页。别有风味的是,张扬“道德”的《杨太真外传》将《唐国史补》“百钱玩锦靿”缩写成了更短的两句话,廿七字,云:“妃子死日,马嵬媪得锦靿袜一只。相传过客一玩百钱,前后获钱无数。”(73)乐史:《杨太真外传》,丁如明辑校:《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46页。
落墨成蝇!盛唐气象有了更多或真或赝、或美或丑的斑斑点点。这让人欲说还休!元人张可久《落梅风·天宝补遗》就戏谑道:“姮娥面,天宝年,闹渔阳鼓声一片。马嵬坡袜儿得了看钱,太真妃死而无怨。”在贵妃身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其书写还出现了创新性传承与创造性转换,诸如杨妃茶、杨妃菊、杨妃井、杨妃墓,以及贵妃脚是三寸金莲等与时俱进的岔路、枝丫。当然,还有始于唐的众多图画及其题诗。贵妃明皇事不仅是其身后诗文创作的灵感之源,也是宫廷画、文人画的母题,并在诗画之间形成了联动互现的回还。在《马嵬志》卷十三中,辑录的从宋到清给相关贵妃绘画的题诗就有90首之多。这些图包括贵妃春睡图、出浴图、调鹦鹉图、洗儿图、上马图、午困图、霓裳图、夜游图、玩月图、醉归图、病齿图,等等。在绘画史中,杨贵妃的形象也是唐代理想女性形象的典型,并在10世纪成为辽代贵妇墓室壁画醒目的一部分。(74)巫鸿:《中国绘画中的“女性空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167-205页。
就贵妃马嵬坡死状,《杨太真外传》叙写无疑最详。如同事无巨细的全景航拍,历历在目的贵妃死依旧延续了《唐国史补》玄宗“命高力士缢贵妃”的基本情节,并写出了其复杂性。乐史先是将与虢国夫人乱情的杨国忠说成是武则天男宠张易之的儿子。在六军以“杨国忠与番人谋叛”为名杀死杨国忠及其子暄之后,明皇责问为何六军依旧不前时,乐史写道:
高力士对曰:“国忠负罪,诸将讨之。贵妃即国忠之妹,犹在陛下左右,群臣能无忧怖?伏乞圣虑裁断。”(一本云:“贼根犹在,何敢散乎?”盖斥贵妃也。)上回入驿,驿门内傍有小巷,上不忍归行宫,于巷中倚杖欹首而立。圣情昏默,久而不进。京兆司录韦锷(见素男也)进曰:“乞陛下割恩忍断,以宁国家。”逡巡,上入行宫。抚妃子出于厅门,至马道北墙口而别之,使力士赐死。妃泣涕呜咽,语不胜情,乃曰:“愿大家好住,妾诚负国恩,死无恨矣。乞容礼佛。”帝曰:“愿妃子善地受生。”力士遂缢于佛堂前之梨树下。才绝,而南方进荔枝至。上睹之,长号数息,使力士曰:“与我祭之。”祭后,六军尚未解围。以绣衾覆床,置驿庭中,敕玄礼等入驿视之。玄礼抬其首,知其死,曰:“是矣。”而围解。瘗于西郭之外一里许道北坎下。妃时年三十八。上持荔枝于马上谓张野狐曰:“此去剑门,鸟啼花落,水绿山青,无非助朕悲悼妃子之由也。”(75)乐史:《杨太真外传》,丁如明辑校:《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42页。
正是这一起承转合皆具、严丝合缝的微距特写,也是口头文学惯有的一波三折“三叠”式的细腻铺陈,进一步为贵妃漂洋过海的跨国社会化提供了充要条件。虽然以陈玄礼为首的六军验明正身了,但乐史代玄宗说的“此去剑门,鸟啼花落,水绿山青,无非助朕悲悼妃子之由也”,却此地无银三百两。白居易《长恨歌》书写史实,“诗多于情”,却有着人本主义(humanism)的特色,渲染了人类共通的“性格”“情绪”。(76)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117-118页;《中国大历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3页。因此,吟唱、渲染该情事的《长恨歌》不翼而飞。有早已在东瀛传播的《长恨歌》的加持,作为“完美”文本的《杨太真外传》这一小纰漏,再加之其后有的蜀地道士杨通幽为太上皇“绝大海,跨蓬壶”而觅得“玉妃太真院”,(77)乐史:《杨太真外传》,丁如明辑校:《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45页。又进一步助力促生了明皇和高力士合谋用丫鬟调包贵妃,并将贵妃送往海外仙山避难逃生的“野野史”。
野野史又并非纯粹是无稽之谈!时至今日,日本的山口、热田等地,不仅有着系列的杨贵妃传说在讲述,还有着杨贵妃的故居、墓地、塑像,有着对杨贵妃一系列的敬拜实践和与之有关的生活文化。(78)加藤蕙:『楊貴妃漂着伝説の謎』,东京:自由国民社,1987年;渡瀬淳子:「熱田の楊貴妃伝説:曽我物語巻二「玄宗皇帝の事」を端緒として」,『日本文学』54(2005),pp.21-29;近藤乃梨子:「楊貴妃伝説で村おこし―山口県の小さな漁村にある真言宗寺院の住職を中心に始まった取組み―」,『集団力学』第30巻(2013),pp.196-235;相田満:「楊貴妃日本に渡る:遺跡と遺物と伝説と」,『東洋研究』214(2019),pp.49-74。这即异域的马嵬,或者说马嵬在异域的再生、活化。毫无疑问,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和一个文化符号,曾经活色生香的杨贵妃这个人的“社会化的延展性”(79)岳永逸:《脱离与融入:近代都市社会街头艺人身份的建构——以北京天桥街头艺人为例》,《民俗曲艺》2003年第142期;《空间、自我与社会:天桥街头艺人的生成与系谱》,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296-301页。抑或说生死辩证法,是历时的,还是跨地域、民族与国别的,是超时空的。如同镜渊,重重叠叠、生生死死、无穷匮也。
在信息时代与视频社会,历史同样成为一个时髦而被反复咀嚼和消费的东西。“大话××”“戏说××”“水煮××”,你方唱罢我登场。在听说我在写杨贵妃时,“你会写李白、宁王、安禄山与杨贵妃的情事不?还有高力士?”这样的发问,已经遇到数回。虽然有些荒诞,但好在人们还是将“贵妃”定格在“情”与“欲”的人的本色层面。在这无父无母的单调性的“青少年文化”、(80)甘阳:《通三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65-77页。荡涤掉孕育着生命力的粗粝的“萌文化”(81)刘文嘉:《别无选择》,《读书》2022年第2期。支配一切的时代,普罗大众对历史的奇妙想象,也是另一种意义上对杨贵妃及与她合欢、一体的明皇的社会化,是“贵妃/明皇”这个箭垛式的历史人物不得不面对的“社会化的延展性”。
由此,有必要在《离骚》《洛神赋》《长恨歌》《莺莺传》《西厢记》《唐明皇秋夜梧桐雨》《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红楼梦》《浮生六记》《边城》《围城》《倾城之恋》《柳如是别传》《受戒》《废都》《白鹿原》这一长时段的男欢女爱的情感书写流中,理解作为常人、良人的贵妃明皇的情事,理解对这一情事的书写实践史和传注疏笺史。也有必要放在《蒹葭》《上邪》《有所思》《孔雀东南飞》和孟姜女、梁祝、白蛇传与牛郎织女等口头诗学的传统中,理解作为非常人和艺人的贵妃明皇的情史。
七、非地点与常人
不得不看到,在出行速度、信息传输速度日新月异的后现代社会,此前被精英发明出来的“旅游”(82)黄微子:《旅游的发明:一段从精英到大众的旅程》,《读书》2023年第6期。已经成为普罗大众标榜自己小资、中产、文明、优雅的一种生活方式,形成阶级属性明显的“区分”(distinction)。(83)[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刘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这使得本质意义上的“体认”和传统意义上因体认而生的时空观、地方感发生巨变。离地、离土的工业革命、现代文明反向促生的“恋地情结”正在退潮。故乡不再令人魂牵梦绕,家乡如异乡,本土即异域。(84)[德]赫尔曼·鲍辛格:《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户晓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0-134页。带有温度、情感,甚至某种情结的地方成为一个个扁平、同质、单向度的空间。指向“香火”也好,指向“星火”也罢,圣地不再具有神圣性,更不神秘。(85)赵树冈:《星火与香火:大众文化与地方历史视野下的中共国家形构》,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4年。具有一统性、同质化的地点不再具有归属感、关系性与历史性,成为“非地点”(Non-Lieux)。(86)[法]马克·奥热:《非地点:超现代性人类学导论》,牟思浩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76页,第108-161页。
如今,千年前的马嵬、旧京杂吧地儿天桥,(87)岳永逸:《老北京杂吧地:天桥的记忆与诠释》(修订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369-425页。如同一个个星罗棋布的高速公路服务区、高铁站、飞机场、旅游景点、超市和连锁店,它们仅仅是行色匆匆的人们穿越、眨眼而过的无差别的一个网格状化的庸常时空点,仅仅是“到此一游”打卡、刷脸的所在。这些非地点,不再是有着归属感、关系性与历史性的驿站、馆舍之类的地点、地方,亦不再是融城市、乡镇、山林和江湖一体的中国社会(88)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205-220页。,而是扁平的空间——笔直、空无一物、无始无终的单行道。这些摄像头——天眼密布的扁平空间,无关枯藤老树昏鸦,无关古道西风瘦马和夕阳,无关“寂寞开无主”的梅花,无关祠堂庙宇、断垣残壁、荒冢废墟,更与嘹亮清越的《紫云回》、苍凉慷慨的《凉州》、回肠荡气的《雨霖铃》无涉。
当下的社会,已不全然是闲暇时间去剧院、电影院、博物馆或在家看电视、看书的“景观社会(La Société du spectacle)”。(89)[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它正在向与视频等移动图像相依为命的媒介社会、网络社会全方位让渡。在虚拟也是令人眼花缭乱的网络社会,人们足不出户,就可坐地日行万里。远方、世界、他者和自我,仅仅是一帧帧一闪而过的图像。这个时代,不是指鹿为马、白马非马,而是宝马(BMW)非马!速度远胜于祖先白马的四轮宝马,让人们将祖先四蹄腾空的“宝马”抛之脑后。由此,人,不再具有地方感,也不再具有地点性,无故无乡。人活着,不是一列列在轨道上飞驰的高铁,就是一辆辆在高速公路上疾驰的宝马,不是一架架穿云而过的飞机,就是一艘艘在茫茫大海上漂泊慢移的游船。(90)于一爽:《船在海上》,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22年,第1-26页。与盛唐连带一体浓得化不开的贵妃情结,正被疾驰的后现代社会、闪烁的视频社会抛离。如同当下大多数人与在人类社会演进史上长相厮守的马和丰产的大地绝缘一样,陕西人不知马嵬驿、北京人不知杂吧地儿天桥,都稀松平常。在拥有种种技术手段的当下,文化保存非难事,但直击心灵、融入生命的文化传承反而并非易事。
总之,如果对关公形象的真切理解必须回到中国文学的“生活现场”,(91)李永平:《对戏剧及宝卷中关公形象的跨文本研究》,《思想战线》2023年第5期。那么对挥之不去的贵妃情结的释读得率先将杨贵妃视为一个与你我他一样活生生的有着生命尊严也必然是过客的人。在其生前身后海量的诗、文、史以及绘画、墓葬中反复出现的杨贵妃,首先是一个常人,是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的杰出艺人,其次才是身不由己、倩盼承迎、动移上意的贵妃,才是所谓的“贼本”“祸本”与“妖姬”。无论叹惋还是诅咒,作为一个文化符号与意象的杨贵妃,更多指向的是人人挥之不去又向往的“情”,甚至是男女之“至情”,而非已经被污名化的“欲”。抛离爱恨夹杂且“自我化”的贵妃情结所支配的文史叙事诗学的瘴雾,杨贵妃的常人和艺人面相也就呼之欲出。作为一个雅俗共有、共享且历久弥新的消费对象,贵妃的遗物完全摆脱了唐明皇的专利属性。传闻其遗失在马嵬并引过客争相观瞻的锦靿与静默的贵妃冢,犹如显圣物将马嵬圣地化,也在一定意义上支撑了贵妃在海外安家落户的这一“野野史”。
八、结语:史地中的情理辩证
其实,马嵬驿有无佛堂、佛堂有无那棵梨树、贵妃真缢还是假亡、那只锦靿是否贵妃遗物、贵妃冢是否被看护、是否在他邦安营扎寨,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贵妃和她的明皇确实来过马嵬,确实在此生离死别。历史从此处拐弯,情感在此定格,并被文学唠叨、艺术点染。历史因此更加厚重、深沉,更耐人咀嚼、寻摸,更容易被人一本正经、秉笔直书地涂抹。换言之,与理性一样,情感不但成就了文学、艺术,它也塑造着历史,且情感本身也有历史。只不过与文艺创作中情感的张扬、热烈不同,历史写作中的情感是内隐的,时常穿着理性的马甲。其实,正因为情感的介入,随着时间的后移,孟姜女故事本身及其所承载的历史也才越来越“厚”,并使得承载了历史的乡土有了种种关系,成为散发着光晕(Aura)、(92)[德]华特·班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班雅明精选集》,庄仲黎译,台北:商周出版,2019年,第25-69页。具有膜拜价值而不可替代的故土。
无论历史(杨贵妃)还是文艺(孟姜女),好的叙事,都是情感与理性、“诗”与“真”的高度辩证统一。歌德自传《诗与真》、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盛誉的《史记》、有“诗史”之称的杜诗如此,白居易《长恨歌》、刘禹锡《马嵬行》、张祜《孟才人叹并序》、韦庄《秦妇吟》亦如此。好的抒情诗原本就自带历史性。在抒情诗中,由情感抒发产生的叙事交流主要以呈现历史空间的空间意象叙事方式进行,因从个人经验走向更广大的空间,与带有历史意味的时代、社会、大众的情感融合,个人情感也就具有了普遍性,从而唤起不衰的共鸣。(93)谭君强:《论抒情诗的历史空间呈现》,《思想战线》2022年第3期。这也是本研究对诗、文、史同等视之的缘由所在。因为,与其说本研究在意的是杨贵妃的情感,还不如说在意的是对贵妃情感的情感史。
吊诡的是:在旅游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今天,与个体真情实感基本没有关联的马嵬,已经成为一个不再具有归属感、关系性和历史性的非地点。反之,非遗运动的加持,使与孟姜女故事相关联的不少地点俨然赢得新的生机。原本乡土性的景致转型为文化遗产景观实践,多少有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意味。(94)桂榕:《文化遗产景观实践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思想战线》2023年第1期。而顾颉刚1925年带队研究的北京郊区的妙峰山(95)顾颉刚编著:《妙峰山》,广州: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1928年。,如今已经是学科、花会、泰斗、信仰、休闲等多重符号叠加的“箭垛之山”。(96)岳永逸:《朝山》,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13-122页。无论对于孟姜女故事流传地还是妙峰山,原本意在革新史学,“使中国人认识中国”“使中国人知道自己是中国人”(97)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三卷1933—1937》,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第376页。亦可参阅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237页。的顾颉刚,也化身一个文化符号,发生了从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让渡,成为地方/历史有机的组分,寄托着言说他的不同主体的情与理。
或者,风土,抑或说文化,不是别的,就是在史地——时空连续统,亦即融城市、乡镇、山林和江湖于一体而持续互动演进的中国社会中,不同心性的行动主体情与理的对撞、共谋、交融——辩证,和基于此的具象化的生产实践——文史演绎和地景再造的循环再生!简言之,文史演绎,即风;地景再造,即土;风土的回环流转,亦即中国社会与文化。在此意义上,本研究不仅是新史学的,它也有着历史社会学、文学人类学、人文主义地理学与民俗学的意味。
谨以此文致敬顾颉刚(1893—1980年)先生1924年的宏文《孟姜女故事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