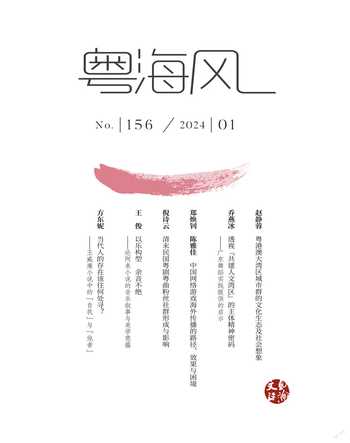清末民国粤剧粤曲粉丝社群形成与影响
倪诗云
摘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我国粤剧粤曲史上粉丝活动十分活跃的时期。本文结合历史描述和理论分析,探讨粤剧粤曲粉丝社群基本面貌、形成原因和功能影响等。研究发现:1.清末民国的粤剧粤曲粉丝从自发的个人行为逐渐发展至规模化的社群组织,并划分了不同派别,即从松散化向组织化、派别化转变。2.粤剧粤曲粉丝社群是基于戏曲活动的集体性、个体内在需求和社会环境外力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3.他们由于体制不成熟和派别斗争成为了当时社会不稳定因素,但在文化认同、产业发展和制度完善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是推动粤剧粤曲文化前进的重要杠杆之一。粤剧粤曲粉丝社群至今活跃在社会生活中,我们应当重视粤剧粤曲粉丝社群的构建与发展,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影响力,进而助推粤剧粤曲文化发扬光大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粤剧粤曲 粉丝社群 形成机制 影响
一、概念界定和问题提出
20世纪初,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粤剧粤曲在批判与改良声中不断成长,其粉丝社群活动亦相当活跃。粉丝是英文“fans”的音译,美国学者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1958—,美国)指出,所谓粉丝即为“狂热地介入球类、商业或娱乐活动,迷恋、仰慕或崇拜影视歌星或运动明星的人”[1]。粉丝是伴随着商品经济和大众娱乐文化的发展而孕育形成的,早已有之。粤剧粤曲粉丝不仅仅是单独行动的个体,他们由于共同的戏曲爱好、价值观念和社会活动等,逐渐建立起亲密关系,进而形成具有凝聚力的社群。“社群”是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对Community一词的译释。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腾尼斯(Ferdinand Tonnies,1855—1936)首先对“社群”这一客观现象加以描述,认为其是由拥有共同习俗、价值观念以及情感一致的同质人口组成的、密切联系的生活群体。[2] 社群具有一致性和边界性,粉丝社群亦是如此。粤剧粤曲爱好者聚集形成的小团体,具有典型的社群特征,他们趋于相似的戏曲兴趣和偏好,通过彼此之间共同的活动参与和在此基础上衍生的人际互动,构建起同质的粤剧粤曲爱好者关系网络,进而形成特定的粤剧粤曲粉丝社群。本文采用粤剧粤曲“粉丝社群”这一概念,而没有使用戏曲界的习惯称谓,如“捧客”“票友”“票房”或“票社”等,是由于这些习惯称谓具有丰富历史内涵和情感色彩,各个概念间既相互区别,又有交错重叠之处。而“粉丝”和“社群”则相对具有广义性,能够更好涵盖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为便于分析论述,本文使用粤剧粤曲“粉丝社群”的概念和表述方式。
粤剧粤曲粉丝社群,近年来曾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但纵观其已有研究成果,一则多流于描述他们的演剧现象,二则多将他们视为职业演员、专业院团的“附属品”,总体上疏于深层理论的研究,缺乏对粤剧粤曲粉丝社群的系统性讨论。事实上,戏曲粉丝社群是以文化传播和情感互动为纽带的群体建构,是推动戏曲发展的重要社会力量。一般而言,粉丝社群的形成和发展受到粉丝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和所属阶层的社会属性等因素影响。本文选取的是清末粤剧粤曲向城市中心转移到七七事变前这一时间段,来考察粤剧粤曲粉丝社群的形成与影响。清末至民国时期是粤剧粤曲实现由农村向城市、由草台向剧院发展的重要时期。清末,随着清廷对粤剧的弛禁,粤剧本地班活动日益兴盛,并在与外江班的竞争中逐渐取得优势,成为广州省城剧坛之雄霸,为粤剧粤曲粉丝社群的形成奠定了文化基础。民国时期,广州城市政治、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粤剧省港班相继办起,粤剧粤曲粉丝社群队伍壮大,造就了城市粤剧粤曲之昌盛。至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社会动荡,人员星散,原先的粤剧粤曲发展进程一度被打断,随着粤剧粤曲界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而进入了新的阶段。清末民国的粤剧粤曲粉丝以生活在广府地区、说粤方言为主的广府人为主,他们拥有相似的文化习俗和生活习惯,重要节庆、婚丧嫁娶、迎来送往等活动均离不开粤剧粤曲的参与。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构成了粤剧粤曲粉丝社群形成的重要社会文化背景。同时,粉丝群体所属阶级、阶层的社会属性会影响粤剧粤曲粉丝社群的建构。清末民国粤剧粤曲粉丝社群的发展,体现了传统秩序失范后群体通过消费行为表明文化身份的认同,亦展现粤剧粤曲在社会转型时期中释放的活力与生机。
那么就具体而言,清末民国的粤剧粤曲粉丝社群是如何形成的?组织特点和功能是什么?对当下粤剧粤曲粉丝社群治理有什么启示?以上问题关乎个体娱乐福祉,又与粤剧粤曲发展振兴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息息相关。基于以上三个问题,对清末民国“粤剧粤曲粉丝社群”进行历史描述和理论探讨,为粤剧粤曲的传承保护提供参考。
二、从个体到集体:
清末民国粤剧粤曲粉丝的基本面貌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孕育和发展的粤剧粤曲粉丝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随着粤剧粤曲的日渐繁盛,其粉丝从自发的个人行为逐渐发展至规模化的社群组织,即从松散化向组织化转变。粉丝社群与群体以外的人群保持着明确的界限,并以阶级、阶层等划分了不同派别,各派别斗争激烈,这不仅是审美上的差异,更体现了当时突出的阶级矛盾和身份认同危机。
(一)自发的粤剧粤曲粉丝个人行为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处于以报纸、杂志等印刷品为主要媒介的一个单向传播的机制中,受众多为被动的信息接收者,粤剧粤曲粉丝尚未形成大规模的群体性力量。此时期粉丝活动多属于自发的个人行为。《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2月14日的《歌坛燃犀别录(六)》中记载了名为矮仔樊的粉丝追随女伶的情形:
矮仔樊,高才三尺,面如乌烟,而性好猎艳,尤醉心于女伶,尝在某校修业,组织剧社,粉墨登场,饰鸨母,惟妙惟肖,而做工之余,兼善丝竹。迨夫剧社歇閉,于是专意歌坛,初迷苏影,凡影度曲,必为之掌板,藉献殷勤。后苏影为程某所获,樊遂销声匿迹,不履歌坛者数月,近又静极思勤,旧路重寻,闻颇迷于梅影,但以矮仔樊之材(身材)之貌,其不蒙青盼,毋待龟卜矣。
SX君曰:矮仔樊,固堂堂专门学生也,以讨好女伶故,而不惜与弦索手为伍,矧未受教育之二世祖与无业游民乎?[3]
此条记载虽颇具调谑意味,但生动体现了当时粤剧粤曲粉丝在追寻明星艺人之事上的情感投入和时间投入情况。《歌坛燃犀别录》还记载了迷于白玉梅的乙友梅、成为女伶工会书记的桃某等粉丝故事,从中亦可看出这些粤剧粤曲粉丝被大众媒体污名化的现象,粉丝被视为特殊的受众,与普通戏曲观众之间存在着厚重的壁垒。
(二)有组织的粤剧粤曲粉丝社群派别
虽然大多数属于粉丝自发的个人行为,但并不意味着没有社群。当时粉丝追捧明星艺人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派别,可看作是松散的粉丝社群的初步形成。同时,粉丝社群之间存在差异,同一社群内部也存在层级结构。刊物《珠江》1928年第16期刊载了元元的文章《谈捧角》,说明了广东捧角之风的源起:
北京之两大捧角家,皆粤人,一为捧梅(兰芳)之冯幼伟(耿光),一为捧程(艳秋)之罗炎东(惇融)……吾粤捧角之风始于梅(林绮梅即苏州妹)李(李雪芳)两党,两党对峙,各有所好,试一翻阅当时两党竞争之报纸,未尝不哑然失笑也。泊梅李脱却歌衫,嫁人为妇,党魁既失,党员星散,捧角之风,沉寂数年…… [4]
在20年代初全女班兴盛之时,“梅李争春”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继梅李之后,渐有新的歌伶取代其地位,形成了新的捧角风潮。《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7月14日载有文章《茶楼捧客之派别》,其列举了其中规模较大的几个捧客党派:
1. 郭湘文之党。“原为苏影咏裳两党之党徒,今乃改组为郭党,党员约有卅余人。众推某军参谋柳某为领袖,某报记者董某为宣传,其余一律为党员。然其党员中有所谓金仔项仔亚李等,或是某大学学生,或是某军职员,或为某公署之三等书记,某厅之录事,声势颇大,无论郭伶在河南北度曲,党人皆追踪而至。每逢郭伶一曲度终,一声暗号,齐呌好嘢之声不绝。而该党领袖柳某,则洋洋得意,顾盼自豪,郭伶以目逆送之,立与交谈,其亦许党人与郭伶谈话,以示利益均分之意。惟不得过五分钟,否则以猖獗论罪,党人群起逐之。故茶楼中时起打架者,皆此辈之对付党人猖獗之故云。现闻柳某因事失职矣,党人亦渐星散,此郭伶之不幸也。”
2. 公脚秋党。“此党完全以工人为中坚,参以商界,党员大约与郭伶相等,然实力无郭伶之伟大。因郭党友新旧国华报评剧栏为之宣传,柳某时时暗怀凶器,预备作外交之后盾云。”
3. 白燕仔党。“此党以某中学教员温某为领袖,势力甚为薄弱,党员只十余人,然其足以号召者,赖有温某咸诗颇佳也。其余如大连影、梅影、慧珠、文武耀等辈,亦有党徒。但党微人稀。殊不足与郭秋燕诸党相颉颃,故不备载,阅者谅之。”[5]
从“捧客之党派甚多,几至不能枚举”中,足见当时追捧伶人风潮之盛。一些粉丝社群还体现出对偶像的无比执着和忠诚,比如只看自己所捧艺人的表演。《天趣画报》1928年第2期的《郭湘文燕燕之我评》一文中说“余曾于某夜听湘伶于南如楼,该伶一曲既终,座客即如排山倒海而下,虽有别伶继唱,亦决无留恋。”[6] 纵观此时期的粤剧粤曲粉丝社群,可以总结如下特征:
1. 粉丝社群内部存在单层次的层级结构。上述女伶有着专门的曲迷会,为了方便管理,还推选出了“领袖”。这些粉丝社群虽然松散,但也具备了初步的层级关系,有领袖统领成员活动,有专职宣传,成员的入选亦有一定的门槛。这里的“领袖”可谓是核心粉丝,相较于普通粉丝,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和更强的号召力、影响力,并为此投入更多的时间、金钱和情感。在他们的带领下,形成了核心粉丝主导和普通粉丝参与的单层次社群结构。一些核心粉丝还通过一些特殊规定表明自己与普通粉丝的区别,如郭伶一党领袖柳某规定其党人与郭伶交谈时间不得超过五分钟等。
2. 不同派别的粉丝社群有大有小,展现了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粉丝群体的差异,其中认同差异是粉丝群体类聚和群分的心理根源。郭湘文、公脚秋和白燕仔粉丝主体职业不同,郭湘文粉丝有大学生、军职人员和公署书记等,成员社会地位高、资本相对雄厚;公脚秋粉丝则以工人和商界为主体,实力相对较弱;白燕仔粉丝包括中学教员等。“粉丝—明星”是这些党派的表层关系,实际上反映了粉丝在不同社会关系中获得的归属感,即价值上的认同。价值认同包括个人认同、群体认同和社会价值认同。个人认同是指粉丝在开展社会活动时关于自我的认识,群体认同是粉丝在粉丝社群活动中的内归属感和外群异质感的结合,社会价值认同是关于国家、民族、职业等主流价值观念与粉丝社群價值观念在粉丝心理层面中的交汇和平衡。上述郭湘文之粉丝,活动频繁,交往密切,积极为郭湘文宣传,甚至“拉踩”其他伶人,“柳某时时暗怀凶器,预备作外交之后盾云”。这些行为一方面是获得自我尊重和情感满足的需要,将个人价值的实现与明星价值相统一;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社会不同阶层、阶级间的思想、资本等方面的差异和斗争。
3. 运作的非正式性和功能的不完善性。此时期粤剧粤曲粉丝社群虽然有领袖的领导和管理,但在实际的活动运作中是非正式制度在发挥作用,并没有明确的规章制度作为保障。同时,粤剧粤曲粉丝社群主要是发挥了粉丝的消费者功能,并没有满足粉丝作为生产者在粤剧粤曲创作和参与等方面的需求。此外,粤剧粤曲粉丝社群内部和粉丝社群之间交流互动机制十分有限,社群冲突和成员星散问题时有发生,不利于社群的可持续发展。
三、多因素协同:
清末民国粤剧粤曲粉丝社群形成原因
清末民国粤剧粤曲粉丝社群的形成是多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主要包括戏曲活动本身具有的集体性、社会个体内在需求构成的心理动力源以及制度变迁、观念变化、技术变革等组成的环境外力。特别是民国初年,粤剧粤曲在市场化的运作中一度引领了时尚风潮、吸引观众眼球,传播范围进一步扩展,为粉丝社群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粤剧粤曲艺人价值地位的观念变化、政商合作举办粤剧粤曲明星选举活动以及印刷传媒时代带来新机遇,成为粤剧粤曲粉丝社群发展壮大的重要助推力。
(一)逻辑基础:戏曲的集体天性
戏曲是集音乐、舞蹈、表演等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具有集体性的特征,它的主要功能包含祭祀、娱乐和休闲,是集体创作的结果。绝大多数戏曲表演都是群体性的活动,具有高度的配合性,既需要创编者、表演者的相互配合、共同创作,又需要观演者的集体反应和积极参与。可以说,戏曲艺术是群体心理外化的表现,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创造的成果。大量戏曲作品是在充满集体色彩的氛围中产生的,每个参与者都能在这种空间和氛围中感受群体精神和社会力量的感染而在其中实现自己的价值追求。在这个持续性的参与过程中,成员之间逐渐形成了情感的纽带,产生了社群认同和社群意识,甚至发展出高层次的社群认同,对社群的团结起了重要作用。
粤剧粤曲亦是如此,从明代中后期的“广班”到清代的“广府戏”,再到民国初年的“粤剧”“粤曲”,都是广府人民智慧的结晶。广府人民不断吸收、融合弋阳腔、昆腔、梆子、二黄等外来戏曲声腔,并在木鱼歌、龙舟歌、南音和粤讴等本土民间艺术形式基础上,以粤方言表演,创造出具有鲜明广府特色和丰厚文化内涵的粤剧粤曲表演形式。粤剧粤曲构成了广府民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存在于广府人民经济生产、商贸活动、人际交往、民俗祭祀以及休閑娱乐等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亦是广府人民自我认同的文化符号和情感联系的重要纽带。总之,粤剧粤曲艺术本身就具有的集体性,构成了粤剧粤曲粉丝社群形成演化的逻辑基础,推动着社群的不断发展。
(二)心理动力源:个体的内在需求
聚集是人的本能选择。个体的生存过程,往往受到各种规则的约束和社会变迁带来的刺激,为了满足身心健康、个人发展以及社会交往的内在需求,可以选择参与休闲的戏曲活动,暂时摆脱家庭、工作等带来的紧张和压力,寻求自我缓解、自由舒适的戏曲娱乐世界,建构起个体存在的生活意义。
清末民国,社会制度发生了巨大改变,社会信仰的多元化伴随着儒家价值体系的崩解与商人群体的崛起,传统知识分子面临被边缘化的危机。科举制度的废除,破解了传统文人依附关系的存在基础,使其获得了人格独立和职业自由;同时他们失去了原有的政治保障,从四民之首、社会中心走向边缘,在失衡的社会中遭受现实的残酷压抑。在此期间,粤剧粤曲演出市场愈加繁荣,粉丝社群逐渐兴盛起来。其参与者上至王公贵胄,下至市井百姓,通过会串义务戏、组织堂会戏等方式,或是打发时间,或是寻求过去士绅感觉,或是缓解和摆脱现实的紧张残酷,粤剧粤曲社群组织成为他们寻求内心平静的娱乐空间。此外,新兴的社会统治阶级如资本家、军阀等,为展现社会地位、资本实力以及满足声色之欲,亦成为当时戏曲粉丝社群的重要一支。
正如前文提及,社群的形成受到粉丝从属的阶级、阶层的影响,体现出一种“类同一性”。“类同一性”指的是不同数量、不同特征的个体之间的共同属性特征,它为社群的人际吸引、价值认同、文化认同等提供连绵不绝的内生动力。在从事粤剧粤曲活动中,相同阶级、阶层的人或群体有着相似的属性和需求,他们往往会相互吸引。在时间的推移中,其群体规模逐渐壮大并趋于稳定,进而发展出具有共同的惯例仪式、共享的价值观念之集体意识和集体行为。于是,在“类同一性”法则的作用下,个体的自娱自乐转化为集体的狂欢,粤剧粤曲粉丝社群形成并派生出具有差异性的不同组织。
(三)传统观念转变:粤剧粤曲艺人地位的提升与合法化
粤剧粤曲艺人地位的提升与合法化是粉丝社群形成的前提。清末民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原有的阶层贵贱之分在制度和观念上逐渐被打破,梨园行也顺应时代发展不断改良,艺人地位逐渐由“贱民”走向“平民”。
首先,西学东渐推动了关于戏曲、优伶的观念转变。优伶自古以来地位卑贱,俗语曰“梨园不是当家郎”。清末民初,西学东渐带来了对于戏曲、优伶的新观念。北京《顺天时报》1904年刊登的《伶部改良策(续昨稿)》文章中说:“欧美日本之名伶皆有教育思想,其人不敢妄自菲薄,国家视之亦甚重,从无以贱类目之者。”[7] 陈独秀1905年《论戏曲》一文中说“戏园者,实普天下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之大教师也。”[8] 近代的启蒙运动将戏曲艺人推向前台,伶界自主意识觉醒,戏曲的社会功能被重新发现,知识分子与艺人们共同推进粤剧粤曲艺术的繁荣。盛行一时的以移风易俗、激励爱国为宗旨的志士班便是知识分子和粤剧粤曲艺人合作的例子。
其次,新出台的法规制度再次明确了粤剧粤曲艺人职业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民国初年,广州市政治公所(当时的广州市政府)将作为城市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粤剧粤曲等纳入市政管理和市政建设中,采取了一系列的管理措施,包括征收和调节戏捐、限定票价、成立戏曲管理机构、出台相关法规章程等。针对戏班和艺人管理,1924年3月13日广州市财政局拟办理戏班商业牌照,并由教育局负责戏曲艺人执业凭证的颁发,“所有拟将省河各戏班之商业牌照发给权,收归职局,及将省河各戏班之优伶执业凭证发给权,收归教育局各缘由,理合备文呈请察核,如属可行,乞即分别咨厅饬局办理”[9]。同年6月12日,市财政局拟制定各家茶楼酒肆清唱女伶牌照。[10] 1930年,广州市政府正式出台法规《广州特别市娱乐场所戏班及艺员登记规则》,要求在市区内营业的娱乐场、戏班和艺员到社会局登记注册,领取执照,并每年按时更换执照。[11] 这些法规制度进一步明确了艺人职业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粤剧粤曲行业更加规范,社会接受度和尊重度日益提高。在各类官方的赈灾筹款活动和庆典活动中,主办方经常邀请粤剧粤曲艺人进行表演,让艺人体会到职业地位的提升和社会责任的担当。在法规制度的推动下,粤剧粤曲艺人的社会地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一批批优秀的“名伶”不仅跻身社会上层,还成为众人羡慕和追捧的“明星”。
最后,粤剧粤曲艺人收入的增加有助于社会地位的提升。经济收入是衡量社会地位的重要指标。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市场化的经营下,粤剧粤曲演出的发展思路从依赖整体戏班转向依赖名角,名角挑班制出现。此时期名伶的艺术声望不仅仅是通过内行对其舞台表演水平来判断,更多是由内外行结合其表演水平和叫座能力来决定,名伶身价水涨船高。1932年,粤剧红伶薛觉先身价已达年薪六万元,兼任班主的名伶廖怀侠年薪四万元,名花旦肖丽章年薪四万元…… [12] 这种高额的经济收入为普通民众所艳羡,加上角色滤镜和商业包装,一些名伶呈现出高雅且富有的“浊世佳人”形象。一些名伶还积极投身慈善事业,乐善好施,为社会所称道。《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10月24日刊登一条《伶人乐善》的新闻,称赞了出价最高的伶人靓少华:
国民党此次筹款赈济三江灾民,在第一公园开会演戏,其大戏一部,购名誉入场券者,人数极多,至出价最高者,首推伶人靓少华,以三百元购入场券,如该伶者,亦可谓有心人矣。[13]
可见,粤剧粤曲艺人们将世俗追求名利与文人推崇高雅和社会责任融于一体,化身为某种文化符号,成为大众争相追捧的明星。
(四)商政合作与价值再发现:粤剧粤曲明星选举活动的举办
伴随着整个社会的城市化、工业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粤剧粤曲艺人选举和竞演活动逐渐出现并发展。在各类竞演平台中,艺人、观众和主办方、政府等多个主体间的互动和联系得以强化,戏曲艺人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亦得以突显。
20世纪20年代,广州公园游艺会中常举办女伶选举大会。第一次女伶选举大会以观众票选为主,由于缺乏权威性而遭舆论界非议。第二次的游艺会女伶选举会设置了听选会,并由专家评选和观众票选两部分构成,评判员由著名戏曲前辈刘海东(即子喉七)、陈铁军、黎凤缘、冯辑伍、梁子安、林寿朋、瑞意师娘等七人担任。一些医院为筹集款项,也会举行女伶选举活动。《香花画报》1928年第1期载有广告:“筹款报效,方便医院特开广州市之歌伶选举,详细章程请到九如茶楼取阅。”[14] 选举活动吸引着粤剧粤曲粉丝的关注和捧场,成为了主办方筹集款项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提升了粤剧粤曲市场的活力
(五)印刷传媒时代新机遇:报纸刊物的宣传造势
20世纪以来,经济发达之城市如京、穗、港、沪等印刷传媒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些报刊中不乏关于优界的报道和评论文章,一些以明星花边新闻为主要内容的娱乐小报也逐渐兴盛。印刷传媒的发展,使大众得以从更多视角和途径了解戏曲艺人,为捧角风潮提供了平台,给粉丝社群及其活动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随着名角制的兴起,人们不仅仅满足于戏曲表演方面的资讯,而是将更多的目光投向这些成名艺人的私人生活领域,报刊为此提供了极佳的渠道。在对戏曲明星的追踪式的报道中,艺人们的曝光率得到提升,社会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报刊亦借明星光环畅通了销路,还满足了人们对明星私生活的好奇。刊物《开麦拉》就有多则关于粤剧名伶薛觉先的报道,例如1932年第109期的《章非东山再起,薛觉先改名章非:再由章非改原名薛觉先,再度来沪跃跃欲试,五万元够他活动》[15];1923年第125期的《薛觉先决定排戏、白金龙原来是粤剧、女主角是自己老婆……外国人收音》[16] 和《薛觉先被控案》[17];1932年第134期的《薛觉先被控昨判无罪,唐爱妃着黑色旗袍出庭:当庭判薛觉先无罪,第二被告冯瑞庭处罚四十元以儆》等。其中第134期的《薛觉先被控昨判无罪》新闻中,记录了薛觉先和友人冯瑞庭与舞女唐爱妃发生纠纷,当庭对峙的情形。舞女唐爱妃指控薛觉先主使冯瑞庭对其进行殴辱,薛觉先则力证清白,机智应对,甚至引起了“哄堂大笑”,报道者评论道:“盖在沪粤人,多闻薛名而未及观其戏剧天才,今得机会一聆薛君之有趣对白,且态度表情之认真,亦仿如演剧,是不得不莞尔失笑”。[18] 可见,薛觉先的形象不仅局限在戏剧演出中,而在这些日常报道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丰满。
1935年广州优游出版社发行的刊物《优游》是戏曲电影娱乐刊物,内容包括戏剧界、电影界、体育界、舞女优伶等的花边新闻和照片,粤剧名伶如马师曾、白玉堂、白驹荣、桂名扬等八卦新闻在其上就有较多登载。一些刊物还设有戏曲艺人的专号,例如刊物《天文台》1937年第46期刊登《华南歌剧电影领袖紫罗兰专号:紫姑娘的作品及其墨迹》,该专号内容丰富,既有紫罗兰的照片,又有紫罗兰“读《复活》”的感想及笔记,还有其活动情况及出版书籍的广告,其中也不乏社会各界人士对紫罗兰的钦慕溢美之词。关于紫罗兰的粤剧,有人评论道:“讲到粤剧的各项,就要安紫姑娘为第一人了。”[19] 此外,一些戏曲艺人亦借助报纸刊物等刊登自传文章,社会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例如薛觉先1940年在《影迷画报》第8期发表了文章《我的奋斗》等。[20]
一方面,报纸期刊的发展,突破了粤剧粤曲以往面对面的舞台观看、口耳相传和日志笔记的人际传播方式,拓展了粤剧粤曲传播的深度和广度。观众和读者能通过多种渠道和不同视角获取粤剧粤曲讯息,粤剧粤曲艺人因此揭开了神秘的面纱,以更为亲民的方式展现在大众视野中。另一方面,报纸期刊构建起粤剧粤曲的“舆论”空间,成为粤剧粤曲营销推广的阵地。其通过设置议题和内容生产,以广告、信息、照片、评论等多种方式,为戏曲及艺人“造势”,引发大众及粉丝社群的关注,为粤剧粤曲的发展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
四、功能与反思:
清末民国粤剧粤曲粉丝社群的影响
社群不是简单的人群集合体,而是个体的有机结合,社群的力量远大于个体之和。粤剧粤曲粉丝社群是粤剧粤曲及艺人的坚定追随者,在追随过程中由于一些粉丝的不理智行为造成了当时社会的不稳定和艺人的困扰,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但不可否定的是,粉丝社群是粤剧粤曲发展的坚实群众基础,在粤剧粤曲发展史上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民国初年粉丝斗争现象时有发生,争风行为不仅仅体现在报刊媒体上的舆论暗战,还有枪战恐吓等物理领域方面的激烈对抗。这些狂热的、不理智的粉丝斗争行为,往往置艺人于不顾,使其遭受损失,还造成了社会的动荡。《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5月1日的《总之女伶累事》中说:“本市各茶楼,自复准女伶演唱后,一时港澳佛梧各女伶,均联翩归来,初为茶楼度曲时,尚无何等怪状,距日来竟有女伶党争,及公然在茶楼上争风之事发生,其中人物,有机关职员者,有法界、军界,亦有学界,此种怪状,不一而足。”[21] 该新闻还具体记载了两界人物为争邀女伶而拔枪示威之事,虽无人员受伤,但茶楼损失茶费等最终由女伶承担。
针对粉丝的盲目跟风、厚此薄彼以及争风行为,当时的一些批评家就发出了严厉批判。如1922年8月陈大悲就在《晨报复刊》剧谈一栏中发表文章《捧角家是戏剧艺术之贼:捧角家底丑态,旧戏底艺术化》,其对戏曲表演者带有偏见,对捧角者更是无情指摘。他认为“所谓捧角家者,其中固然有几个是‘恩客,或是‘老斗,其余的无非是‘恩客‘老斗底食客或是走狗”[22]。讽刺了那些附庸风雅、不懂装懂之人。苏重威1923年在《戏剧周刊(苏州)》第5期发表《无谓之捧角》一文中指出一些捧角者“赞之若无与伦比,而他伶人则无以足道”[23]。批判了这种厚此薄彼的捧角行为等。在社会众人对“捧角家”的批判和讨伐声中,也有人看到积极的一面,并进行理性的发声。孙绮芬在文章《韦尘梦先生捧角怪物论书后》中认为:“捧角常事也,亦正经事也。歌艺可取,喝彩叫好,文字揄扬,褒之以鼓其行,奖之以励其艺,雅人深致。名士闲情,何足病焉。”[24] 他认为不可将捧角者视为洪水猛兽。署名“慎行”者在其文章《演员与捧角》中说:“我不反对捧角,因为这种心理是每个人都有的,所不同的,不过明显不明显罢了……只要有一技之长,能够迎合观众或听众的心理,他就具有被捧的资格,这些人多半能以自己真实的本领,获得观众的欢心,不管他们与观众是属于同性也好,属于异性也好。”[25] 其将捧角行为看作是人类正常的心理行为。粤剧粤曲粉丝社群在推进粵剧粤曲发展中也发挥着积极作用。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强化了粤剧粤曲文化的群体认同
随着地区间人和人的交流日益频繁,文化同质化趋向日益严重。在此情况下,粤剧粤曲粉丝社群通过共同观看表演、发表评论和组织剧社等集体仪式,强化其身份认同和群体凝聚力,从而在理解、尊重和支持等方面得到满足,提升了其社会适应水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中国乃至世界各地的粤剧粤曲粉丝社群层出不穷,例如上海有岭南鉴社、粤侨工会新剧部、俭德储蓄会粤剧部等;京津地区有广东音乐会、津钟音乐会、韶韺乐社等;美国有叱咤社、侨声音乐社等。这些粤剧粤曲粉丝社群构成了海内外粤籍人民身份认同及情感联系的重要纽带。同时,在粉丝社群的宣传和活动下,粤剧粤曲表演艺术的独特性也得以突显,并获得越来越多的了解和关注。粤剧粤曲影响力的深度和广度得以拓展。
(二)促进了粤剧粤曲文化产业的繁荣
粤剧粤曲粉丝社群除了社交层面的价值认同,还带来了经济层面的价值认同。粉丝社群通过集体活动证明所捧粤剧粤曲艺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有利于艺人获得更多的商业资源;资本方由此增加对艺人的投资,加大粤剧粤曲文化产品和相关话题的产出,例如戏曲刊物、戏曲电影、名伶唱片、名伶广告等推陈出新,为粉丝社群不断注入新的消费动力,并获取经济红利。在粤剧粤曲粉丝、艺人和资本的共谋中,粤剧粤曲文化产品的繁荣得到刺激。由此,商业特性日趋显著的粤剧粤曲成了当代社会市场经济的重要支柱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三)推动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融合发展
粤剧粤曲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其本身蕴含的精神因素得以传承,并在口耳相传、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人们的文化心态、知识结构乃至价值观和世界观。一方面,粉丝社群作为当时重要的文化现象为社会舆论所关注,代表精英文化的知识分子对其的口诛笔伐或辩证批判,同时促进了学术界对于戏曲艺术功能和发展道路的思考,粤剧粤曲文化产业由此发挥了政治宣教、意识形态的作用。另一方面,粉丝社群是当时粤剧粤曲文化产业的重要支持力量,其需求亦代表了当时大众文化市场之需求,即要求放松、娱乐和调节身心。还有不少文人为粤班制造声势。《李雪芳》一书中记载了李雪芳1919年初到上海演出,获得同乡康有为书法题字宣传之情形:“雪芳初次到申之时,南海康有为,为书斗大之告白字,极龙蛇飞舞之妙……印刷万张,彩色绚烂,炫人眼帘,命张诸通衢,一时李雪芳之芳名,万人争称,识与不识,皆赞书法之妙,而雪芳之声名,亦从此雀起焉。”[26]
为拉动大众的消费,粤剧粤曲文化的发展往往需要迎合其需求量身定制,力图多元化、通俗化和娱乐化,满足更多群体的喜好,促进粤剧粤曲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其中通俗易懂并不意味着不能启迪人们的智慧,一些粤剧粤曲剧目蕴含着丰富的教育和审美资源,侧面弘扬着真善美,推动着大众文化的健康发展。
(四)加快了粤剧粤曲相关法规制度的完善
在粤剧粤曲粉丝社群的集体造势下,政府及相关部门深刻感受到粤剧粤曲文化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并有意识地规范粤剧粤曲文化市场,优化其生存发展的外部环境,例如设立戏剧审查会、教育局改良戏剧研究会,出台《广州市特准清唱女伶牌照章则》《取缔市内瞽姬办法》《广州市取缔戏院章程》等,促进粤剧粤曲相关法规制度的完善。
结语
粤剧粤曲粉丝社群的兴起,可视为粉丝对自身社会属性和需求、戏曲活动的集体性以及所面临的社会文化环境的一种自然回应。清末民国时期,伴随着广州城市化的发展,粤剧粤曲表演不断以更亲民、更日常的方式深入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促成了粤剧粤曲史上最繁荣兴旺的阶段。此時期以粤剧粤曲为代表的大众文化显示出鲜明的商业性和世俗性,其以娱乐休闲的方式进入大众消费领域,受众进一步扩大。同时,歧视戏曲艺人的传统社会观念发生转变,粤剧粤曲艺人地位不断提升,明星效应初显端倪。个体的、松散的追星行为向有规模的、有组织的粉丝派别发展,形成一批围绕粤剧粤曲明星的粉丝社群。
粤剧粤曲粉丝社群既吸收和融合了社会主流文化的精髓,又在粤剧粤曲传播传承过程中进行创造和更新,成为推动粤剧粤曲文化前进的重要杠杆之一。虽然由于当时社会的特殊性和局限性,粤剧粤曲粉丝社群出现了诋毁、斗殴、争风等社会行为失范问题,但仍以群体力量深刻影响着粤剧粤曲市场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发展进程。作为居民参与社会文化娱乐活动微观组织的粤剧粤曲粉丝社群,至今依然存在,并在粤剧粤曲文化传播传承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应当关注当代粤剧粤曲粉丝社群的发展,重视群体的力量,通过优化内外协同治理等方式,更好地发挥粤剧粤曲粉丝社群的积极影响力,促进当代粉丝社群的规范化、法制化,进而推动粤剧粤曲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为广州市社科规划项目“粤剧粤曲结社研究”(项目编号:2022GZLW0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注释:
[1] [美] 亨利·詹金斯、杨玲:《大众文化:粉丝、盗猎者、游牧民-德塞都的大众文化审美》,《湖北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2] [德] 斐迪南·腾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3]《歌坛燃犀别录(六)》,《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2月14日,第9版。
[4] 元元:《谈捧角》,《珠江》,1928年,第16期。
[5] 老焰:《茶楼捧客之派别》,《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7月14日,第4版。
[6] 香江客:《郭湘文燕燕之我评》,《天趣画报》,1928年,第2期。
[7] 剑雪生:《伶部改良策(续昨稿)》,《顺天时报》,1904年7月30日。
[8] 三爱(陈独秀):《论戏曲》,《新小说》,1905年,第2期。
[9]《财政局欲办戏班牌照(提交财政委员会讨论)》,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3月13日,第3版。
[10]《唱女伶增月饷》,《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6月12日,第9版。
[11]《广州特别市娱乐场所戏班及艺员登记规则》,《广州市市政公报》,1930年,第351期。
[12] 张方卫:《三十年代广州粤剧盛衰记》,转引自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粤剧春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6页。
[13]《伶人乐善》,《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10月24日,第7版。
[14]《筹款报效》,《香江画报》,1928年,第1期。
[15] 维太风:《章非东山再起,薛觉先改名章非;再由章非改原名薛觉先,再度来沪跃跃欲试,五万元够他活动》,《开麦拉》,1932年,第109期。
[16] 慕维通:《薛觉先决定拍戏,白金龙原来是粤剧,女主角是自己老婆……外国人收音》,《开麦拉》,1932年,第125期。
[17]《薛觉先被控案》,《开麦拉》,1932年,第125期。
[18] 舞客:《薛觉先被控昨判无罪,唐爱妃着黑色旗袍出庭:当庭判薛觉先无罪,第二被告冯瑞庭处罚四十元以儆》,《开麦拉》,1932年,第134期。
[19]《华南歌剧电影领袖紫罗兰专号:紫姑娘的作品及其墨迹》,《天文台》,1927年,第46期。
[20] 薛觉先:《我的奋斗》,《影迷画报》,1940年,第8期。
[21]《总之女伶累事》,《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5月1日,第10版。
[22] 陈大悲:《捧角家是戏剧艺术之贼:捧角家底丑态,旧戏底艺术化》,《晨报副刊》,1922年8月31日,第3期。
[23] 苏重威:《无谓之捧角》,《戏剧周刊(苏州)》,1923年,第5期。
[24] 孙绮芬:《韦尘梦先生捧角怪物论书后》,《小说日报辉订》,1923年,第219期。
[25] 慎行:《演员与捧角》,《三六九画报》,1941年,第00010期。
[26] 我佛山人:《李雪芳》,上海:东亚书局,1920年版,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