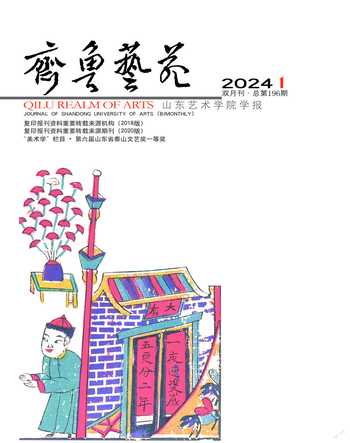齐鲁文化视域下的电影创作泛论
刘璐 吴岳
摘 要:从齐鲁文化的思想特质入手,全面梳理其文化渊源及发展流变,本文以儒家思想是齐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认知为前提,将其核心即仁学本体学说进行全面归纳,并与电影叙事相结合展开论述。从剧作层面来检视内蕴儒家思想品格的中国电影作品的叙事方法与策略,进一步探讨具有仁学思想的文艺母题在情节叙事与人物塑造方面的方法运用,看其如何将人性表达作为贯穿剧作结构的始末,让仁学本体思想融入人物构设的过程,又怎样通过影像故事让观众真正去体认儒家思想和中国智慧,为指向未来的中国电影创作,提供更广阔的思维理路。
关键词:齐鲁文化;儒家思想;仁学叙事;人物塑造
中图分类号:J90-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236(2024)01-0027-06
在全球化拓展与全媒体传播的影像时代,电影作为最具表现力的艺术形式,已成为公众认识社会、宣扬文化价值观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如何利用影像故事弘扬传统,以全新的叙事讲述方式承继民族精神,并赋予其当代意义,是我们需要思考和面对的问题。
一、齐鲁文化与儒家思想
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齐鲁文化,在悠远的历史长河中,曾发挥重要意义。“齐鲁”二字源自于西周初期的两个诸侯国,齐国与鲁国,在史前文明时期,他们同属于一个地域文化圈——即中国古老文明的东夷文化[1]。在先秦的典籍中齐鲁二字的连用并不多见,西周封邦建国后,由于其地理环境不同,齐、鲁两地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受多重因素影响,原本并不相同的两种系统,逐渐发展成为统一的地域概念——齐鲁文化。齐、鲁地域相近,就有了“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2](P89) (《论语·雍也》)的说法。“齐、鲁之故,吾子何不闻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执事也。”[3](P1260)《荀子·性恶》篇中开始将齐鲁二字连用,甚至将齐鲁与礼仪、仁义之道联系在一起:“天非私齐鲁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于父子之义,夫妇之别,不如齐鲁之孝具敬父者,何也?”[4](P522)直到春秋战国之际,二字逐渐连用指称齐、鲁两地所在区域所共有的命名,秦统一六国后,齐鲁走向融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地域和文化概念,而齐鲁之地与今天的山东省区域大致相似。齐国灿烂文化的缩影——稷下学宫,以道家、法家为主要流派;而鲁文化的繁荣孕育了以儒家、墨家为代表的思想流派,使之在春秋战国时期成为显学,即“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5](P724)。“齐鲁文化上承夏商周三代,直攀史前东夷文化,下启秦汉,直至于今,将中国数千年文化连为一系,发展不断。”[6](P2)儒、墨、道、法为代表的齐鲁文化相继融合于儒家,形成了外儒内法的精神特质。
儒家思想源自于齐鲁地域中的鲁文化,魯文化的根基就是周代的礼乐文化,而礼乐的根本在于对人性的塑造。礼乐是一种根本的规范,其在人际关系中形成。礼乐传统弥漫于各个阶级群体,渗透在人们的一切社会活动之中,起到的是约束与调和的作用。礼乐制度所建立的是天地人一体的道德中国状态,在这个体制中,人人本分行事,维护整个秩序的稳定,意图达成孔子在《论语》“为政”篇提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7](P14)的理想境界。这也就成为了周以德而得天命的伦理合法来源,成就了孔子所念念不忘的精神世界——重视道德使人心真正归服,形成稳定的政治伦理。礼是作为人与人交往的基本规范而存在,是国家安定繁荣的基石,所以才有“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8](P15)的关于德行的中国根基,正如礼乐文化的核心精神“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9](P28)。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这是周代礼乐的核心精神,也是孔子希望构建的完美社会秩序。
齐鲁文化浸润下的儒家思想,经历代学者的加工与改造,最终凝结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家思想体系所建构的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完整人文世界,它以人为思考一切的中心,并以其核心概念“仁”学本体与具体生活实践相结合,来改善人的生命状态,所以会有“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10](P32)(《论语·八佾》)这种仁是以人的自觉来与世界建立关系,用以强调如何关切他人、与人为善、与民同乐和实现自我的价值问题之问。
二、齐鲁文化精神与电影故事创作
齐鲁文化融合下的儒家思想,重在对人性的阐释,而关于人性表述的仁学思想,则可作为电影主题引领进行演变与探索。孔子从不去追问不可知的形而上,儒家所探讨的都是对人世间处世之道的具体实践,是对人生如何通向正确道路的哲理探索。所谓智、仁、勇,也是通向人生正确之路的方法,其归于儒家的“性本善”之论。所以电影主题对人性情感的探讨,可以哲学思维为导向,进行主题探索。孔子的一生都在践行“礼乐”制度包含的德行理想,《礼记》中把“仁”定义为己之性德,将人与天贯通,突出了仁的宇宙论意义,体现了把“仁”通向超越面的一种努力[11](P16)。孔子以“仁”为核心要义,以“义”为行为标准,以“礼”为行为方式,来界定人心与天命之间的相互关系,所以,孔子之道就是仁学之道。儒家思想向来倡导朴素的生活态度,将价值观问题与具体实践相结合,从不自高标榜,立异竞速。儒家思想与历史积淀的社会心理较为一致,它所实践的是一种永恒的理想,这个永恒的理想是接续传统,永续前进。儒家思想所反映的是一个社会的整体意识和文化倾向体系,它被统治阶级尊崇与提出,它重视个人对国家的责任,在中华民族共同文化与群体心理的塑造过程中,其影响更是意义深远。
孔子以“仁”作为思想的核心,来解决普泛的人生问题,以仁释礼、孝悌为仁、忠恕为仁,认为每一种美德都是仁的必要条件。李泽厚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对孔子进行过再评价,对“仁”的含义给予自我理解的阐释,并从血缘、心理、人道和个体人格分别论述。孔子对“仁”的解释,有明确的释义“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12](P107),表明孔子所主张的“仁”具有自发性的特点,是人内在的德行与价值,所以在颜渊问“仁”时,孔子的回答是“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13](P174)(《论语·颜渊》)。“克”是一种能够的表达,在孔子看来,自己做主去实践礼乐的要求,才是真正的人生正途。对仁的思想的强调在于内在之鉴定,所以会有“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14](P136)(《论语·子罕》)。孔子对仁之道的坚持是一以贯之的,仁者成就他人,也成就自己,“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5](P93)(《论语·雍也》),所以在儒家看来以“仁”作为改善生命的起点,仁者才是真正道德高尚的人。
成为一部优秀电影作品的基本条件首先是通俗易懂的故事内容,其次是生动有趣的人物形象。对于电影故事情节的构设搭建来说,以先进的哲学思想为引领,将自古以来最具普遍意义的真理价值讲述清楚,无疑艺术创作成就自我的基础。儒家思想的践行路径是经由世俗世界中的人类活动而得以通达,所以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创作,更適合承载中国传统精神价值。将仁学思想于仁义礼智信方面的具体阐释与电影叙事相结合,是传讲新时代中国故事的关键要素。在电影故事的营构中,将人物塑造和思想动机融入传统文化精髓,通过人物形象让观众进一步认识儒家伦理内蕴的精神品格,是以真理之光激活中华文明基因目标得以实现的必要前提。优秀的故事创作再生产,才能体现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
三、仁学思想与电影叙事逻辑
所谓电影叙事,是指在银幕上由创作者讲述的一个故事,其运用艺术处理方式叙述的事件,会伴随着一定的观念和情感产生,而故事最终呈现在画面上,给观众了解事件全部过程的这个空间,又被称作叙事空间。“这个空间”包含讲述的内容和如何讲述的问题。电影语言作为一种表意系统,在叙事层面更关注如何叙述以及讲述的角度;而对电影叙事而言,故事作为叙述的产物,侧重于事件的选择及立场问题,所以,故事就是电影叙事的核心。
以仁学为母题的电影创作,为电影主题的选择提供了明确目标,高尔基曾为主题下过全面的定义:“主题是从作者的经验中产生、由生活暗示给他的一种思想,可是它聚集在他的印象里还未形成,当它用形象来体现时,它会在作者心中唤起一种欲望——赋予它一个形式。”[16](P296)主题的选择来自生活,与现实密切相关,所以会有在生活中发现主题的说法。处于中国传统文化大背景中的儒家思想,其仁学本体的道德与行为,呈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以仁学为导向的主题创作,可为电影叙事表达衍生多样化的变体。就像作家铁凝说的“无论对于小说还是电影,懂得艺术来源于生活并不困难,但要明白无中生有对小说和电影的意义,就似乎不太容易,而我所说的无中生有,恰恰是指作家对生活和生命本身深层次的总体把握与判断”[17](P105)。所以,从生活中发现主题,进而通过无中生有去开发主题十分重要。
“仁学”母题就是关于生命意义的探讨、人性的探讨以及价值观问题的探讨,仁学视域下的叙事逻辑,就是多元包容性的文化形态。伊朗电影《小鞋子》对人生希望的表述,体现了一个为了卑微心愿,即为妹妹赢得一双属于自己的球鞋,宁愿放弃第一名而拼命争夺第三名的孩子身上闪耀的光芒;《巴别塔》《撞车》中不同民族文化的沟通;《圣女贞德》中所探讨的爱与救赎问题;《勇敢的心》在电影背后是价值观的辩护;在对人性的探讨中,英剧《黑镜》第一季对当代媒体网络极其犀利的讽刺,对民众与人性的批判也极为尖锐。将现代观念和现代元素融入传统文化之维中进行创作,在儒家仁学思想浸润下进行“仁学”母题的影像表达,是开创极具中国特质的电影类型的核心要素。
儒家思想中有关于“仁”的学说,即推己及人。作为儒家正统的孟子,将孔子“仁”的观点发展为“仁政”,以人为本的思考,建立了“性本善”的学术论断。好莱坞有大量关于人性思考的作品,卓别林的影片,虽然以滑稽喜剧著称,但是其所塑造的流浪汉夏尔洛的形象与故事的讲述,都是围绕人性表现的深刻写照;《阿凡达》这部影片中潘多拉星球的灵魂之树,与人纯净的心灵相通,以展示人性的善良与纯真,其情节设定,也是为了讨论人与自然的关系;《秋菊打官司》对于“理”的探寻,是秋菊对正义和真理的执着追求;这些关于人性的具体呈现,都可以用儒的仁学本体赋予影像诠释体现。
布莱克·斯奈德的《救猫咪——电影编剧宝典》,按照电影自诞生以来的时间线,对故事类型进行详细分类说明。大卫·波德维尔在《好莱坞的叙事方法》中,也对多线叙事的框架进行专章分述,运用人物命运聚合、网状叙事等手段进行事件和时序的编辑,即一个事件被另一个事件打断,但他们之间却存在着某种联系,这种联系随着剧情的发展逐渐紧密,最后,几个小事件汇集在一处,让影片达到高潮。[18](P112-114)百家争鸣的战国,是中国古代文化最灿烂的时代,而观点创造冲突,是故事写作最核心的部分。黑格尔主张悲剧的本质并不在于一个人物是“对”的,而其他人物都是“错的”,也不在于善良与邪恶的对抗,而是双方人物都是对的,把故事变为“正确对抗正确”的设定,并带向其合乎逻辑的碰撞才是最新吸引人的。[19](P129)用矛盾冲突阐明影片的主题,是建构故事危机的前提,矛盾达到一定形势后,节奏和危机感才会同时增强,以进入故事真正的高潮部分。其实,人们对电影创作的关注点,更多在于人物性格心理的具象化表达,而如何通过动作演绎人性的深邃,构设符合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人性逻辑,是需要用中国哲学理念的思考贯穿始终的。就此而言,儒家思想中的仁学本体演变与阐发就变得尤为重要。
四、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理念
古希腊时期的“摹仿说”是现实主义创作的基石,所谓现实主义就是呈现社会人生的客观性真实状态。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最早阐述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并进一步发展了摹仿说,他认为其并不是对现实消极的抄袭,而是要反映在现实世界中最具有普遍意义的创造。“真正的差别在于历史学家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诗人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诗比历史是更哲学、更严肃的,因为诗所说的多半带有普遍意义。”[20](P465)具有现实主义意义的摹仿说所揭示的是现象的本质和规律,莎士比亚对其进一步发展,他认为戏剧的目的在于反映人生,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所以莎士比亚式的创作总是最大限度地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最终给出现实主义创作以权威指导的当属恩格斯,他认为“照我看来,现实主义是除了细节的真实以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21](P20)。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能否写出特定历史时期的典型环境,揭示这个环境中真实的阶级关系,在整体上符合历史真实,是判断历史剧是否达到艺术真实的客观标准。”[22](P204)就像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一江春水向东流》,就是运用了典型化的原则创造出的高水准现实主义力作,其致力描摹的是中国社会历史之兴替变迁,书写的是反映民族性格和精神倾向的轮回往复。我们可以学习借鉴好莱坞,创建具有本民族特质的类型模式,如具有美国式英雄主义特质的类型——西部片,类似《关山飞渡》《原野奇侠》等作品。电影创作应积极挖掘本民族的文化基因,选取与民族、时代密切相关且意义深远的事件,加入仁学思想体系,赋予儒家文化以划时代的价值,为当下社会发展指出新的方向。
五、仁学思想与人物塑造
儒家以人为一切价值的基础,孔子的“道”主要是人之道,礼乐的根本在于对人性的塑造,礼的规范在人际关系中形成,不了解礼的规范,无法在社会立足,这也就是“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的根据所在。在儒家看来,理想人格就是拥有一颗真诚的心,它是一切外在规范的基础,其最终指向的是对“君子”形象的想象。就剧本创作的核心部分——人物塑造而言,令观众印象深刻的人物,是作品成功与否的关键。一部作品最终可以形成一个怎样的故事,核心也在于人物塑造。涉及人物的创作,需要通过动作、语言、心理加以通盘考虑。叙事过程中,人物的戏剧性需求是设定事件的前提。所谓戏剧性需求是贯穿整个故事的线索,即你的人物想要获得什么。随着事件不断发展,人物的戏剧性需求会发生变化,而变化才是叙事中最吸引观众的部分。故事的讲述是通过事件来决定人物,在人物的戏剧性需求中建构人物关系,通过人物行为衍生事件。人物创作取决于其思想、感觉、情绪所决定的行为,电影是通过画面讲故事的艺术形式,动作就是人物。[23](P124)观众往往可以通过人物动作来认识人物,辨认其在作品世界中的身份,了解他们的价值观,明确其思想。动作就是人物的自证。
电影创作者需要将现实本身中的人物形象呈现在銀幕上,塑造生活的典型。运用儒家思想中的“仁”的观念,来塑造具有对应品行的人物,是弘扬其主张的精神主旨的路径。“仁”作为孔子学说的中心观点,对电影人物创作同样具有启发性,不仅仁者爱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种具有独立品格的思想,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呈现。
齐鲁文化滋养下的人物品格,是电影人物创作的关键,齐鲁特色人物的创作是电影的灵魂。齐鲁文化融合的儒家思想,更是将其主要关怀,聚焦于人类社会的人际关系,而提出“仁”的思想——人的本性就是“仁”,是人性与道德的统合体。仁是统摄诸德的本源,是无条件的绝对本源。[24](P127)“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就是对于道德的高度赞誉之意,所以民本思想一直是古代中国的根本,高明的道德表述,更是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途径。讲述人物传记故事,通常也是为世界介绍中国,但如何让一个人物身上凝聚的思想体系清晰呈现,就需要电影剧作的努力。一方面编剧要具备历史与哲学思想底蕴,要充分了解自己所写人物的背景,回顾人物的人生轨迹,只有完全深入这个人物中时,才会捕捉到人物的“本质”,就像王阳明“格竹顿悟”的那一刻,决定了他真正“心学”的方向;另一面也要具备将人物思想贯穿于事件之中,去支撑故事弧线的编排能力——可以按照任意需要,在时间脉络中穿插事件,表现情节中心内容。
六、人物塑造的道德理念
儒家思想的乐观有为、重视道德价值、重视历史经验的优良传统,为中国文化的传承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儒家倡导以“求善”为目标的伦理型文化,其政治原则是从道德原则中推导出来的,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在孔子的思想范畴中,常用道德来替代宗教,因为儒家思想望向的是入世的思想,探究的是人在现实中的生存哲学,即以人类关系为出发点,以入世进取心理为基础,以礼教名分道统为中心,以人文主义为内核,极少涉及宗教色彩的文化精神传统。“未知生,焉知死”,他并没有否认鬼神的存在,但不求助于鬼神。崇尚道德论,是从人与人的现实关系中,来确立道德,儒家所重视的是对现实生活的态度,“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智矣”[25](P88)(《论语·雍也》)。这是孔子教诲弟子提高道德觉悟的方法论,敬畏神灵、敬而远之,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
影视作品的创作重心在于写“人”,可以用可视化的影像突出人物形象,通过语言来塑造人物的性格,呈现人性的外在;也可通过画外音的表述形式,透视人物的心理世界。就像《阳光灿烂的日子》,画外音中马小军的讲述在全片贯穿,牵动观众的情绪,最终使作品与其产生情感共鸣,使观众会重新回看过去的时代;又像是《天云山传奇》在人物刻画时的内心独白使用,凸显了人物的心理世界。儒家核心思想之“仁”,“仁者爱人”是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教育世人做好自身去影响他人,而且“仁”的思想是在强调主体自主性,而不是被动境遇。通过这种仁学本体的“人之爱”进行变体的人物塑造,来叙事故事,才是阐释传统文化的有力体现。仁者就是能克制自己,自己做自己的主人,在仁义礼智信中实现真正的自主。电影作品“宣扬人民性,让人民成为作品的主角”(《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提到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着重描写人物命运及思想的变化,将具有表现功能的镜头运用其中,用以传达人物的内心情感。让人物在动态发展中进行渐次积累式的性格塑造,使观众了解人物、理解事件讲述的关系,也是电影创作的核心。人物塑造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生活中真实存在人物为原型进行艺术创作,二是典型化的艺术形象,将生活的普遍本质意义熔铸在人物身上进行书写。在表现真实环境中的人物时,对于底层生存困境与内在情感需求的关注,具有社会现实意义。如李睿珺的影片创作,大部分都是在呈现伤痕累累的乡土生命状态,《隐入尘烟》中所展现的正是两个被各自家庭所抛弃的孤独个体的故事:日复一日、相濡以沫的生活细节中,镌刻着农村底层夫妇从相知到相守的心路历程。
七、齐鲁文化的当代价值
新时代的中国电影创作,要探索在现代化文明的背景下,如何让中国传统之思寄予故事讲述之中的方法。以民族文化之内核作为故事的发展曲线,在电影故事的内部结构中融入其精髓,用影像来表现中国人对理想家园的完满建构,或许是一种便捷的通道选择。在张岱年先生看来,“文化的核心是哲学思想,弘扬中国文化中的优良传统,首先要弘扬中国古典哲学中的优良传统”[26](P321)。 理解人性,是掌握真正生命途径的方法。赋予优秀传统文化加成的中国电影作品,可以让世界看到重德贵义的中国精神。用哲学思想指导电影创作,对于真正中国故事的讲述,将具有重要意义。
儒家思想倡导温故而知新,继承与发展传统文化,赋予传统以当代意义,实现价值观念和民族文化精神的全面更新,是时代课题。在全球化传播时代,通过最具表现力的电影媒介,将中国哲学主题融入剧本创作,在剧情设置中以传统思想唤醒沉睡的古老文明,重塑美丽中国的集体记忆,重拾难以释怀的乡愁美学,是提升现代化中国精神面貌的必经之路。如何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思想进行影像化表达,将独具地域特色的中国文化向世界输出,让世界看到多元的中国故事,是每一个电影人的当代使命。
结语
齐鲁文化强调对人内在生命的关注,追求自由的齐文化和崇尚德行的鲁文化,共同构成了具备儒家传统特质的齐鲁大地。通过电影故事创作彰显具有仁学思想的文化智慧和中国故事,才是唤醒属于我们自己的民族意识,重塑美丽中国的集体记忆,提升當代中国精神面貌的必经之路。
参考文献:
[1]李伯齐. 也谈齐鲁文化与齐鲁文化精神[J]. 管子学刊,1999,(4).
[2][7][8][10][12][13][14][15][25]杨伯峻译注. 论语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06.
[3]李梦生译注. 左传译注(下)[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4][清]王先谦撰, 沈啸寰,王星贤点校. 荀子集解(下)[M]. 北京:中华书局,2013.
[5]高华平,王齐洲,张三夕译注. 韩非子[M]. 北京:中华书局,2010.
[6]郭墨兰主编. 齐鲁文化[M]. 北京:华艺出版社,1997.
[9]戚汝庆主编. 齐鲁文化基础知识[M].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20.
[11]陈来. 仁学本体论[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16][苏]高尔基. 高尔基选集:文学论文选[M]. 孟昌,曹葆华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7]铁凝. 共享好时光[M]. 北京:群众出版社,1994.
[18][美]大卫·波德维尔. 好莱坞的叙事方法[M]. 白可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9][23][美]悉德·菲尔德. 电影剧作问题攻略:悉德·菲尔德经典剧作教程3[M]. 钟大丰,鲍玉珩译.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
[20]桂青山. 影视剧本创作教程(第4版)[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21]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22]陆贵山,周忠厚编著. 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第三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4][德]卡尔·雅斯贝尔斯. 四大圣哲[M]. 傅佩荣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
[26]张岱年. 中国古典哲学中的优良传统[M]//张岱年全集(第7卷).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叶 凯)
收稿日期:2023-10-31
作者简介:刘 璐,女,博士后,山东农业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电影史论与文化批评。
吴 岳,男,釜山大学亚洲电影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文化产业与艺术管理。
项目来源:本文系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齐鲁文化与当代电影创作研究”(L2021Z07070175)的阶段性成果。
doi:10.3969/j.issn.1002-2236.2024.0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