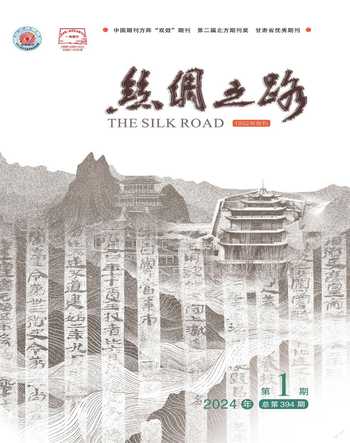5-15世纪中亚音乐文化述论
马茜
[摘要] 5-15世纪中亚音乐以宫廷和城市音乐文化为代表,呈现多元性、科学性、实用性及诗歌一体性特征。波斯音乐奠定了中亚音乐的专业基础,阿拉伯音乐的融入确立了其体系特征,萨曼王朝学者的研究促成了中亚音乐科学的形成。突厥系王朝重视音乐治疗功能,帖木儿帝国展示了社会音乐的多样性。
[关键词] 5-15世纪;中亚;音乐文化
[中图分类号] G1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5-3115(2024)01-0107-10
“中亚”(Central Asia)作为一个具有内陆亚洲地理特征的自然区域,其范围虽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情况下有一定的变动和伸缩,但不外乎广义和狭义两种说法。广义之说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最为权威,即中亚地区涵盖阿富汗、伊朗东北部、巴基斯坦、印度北部地区、巴控和印控克什米尔、中国西部地区、蒙古和苏联的中亚地区,即“中央亚细亚七国”之说;而狭义中亚则包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五国[1]。本文研究聚焦5-15世纪中亚五国,以其历史文化演变为背景,阐述萨珊波斯王朝至帖木儿帝国时期主流音乐文化发展样貌,并归纳、揭示这一时期音乐文化特征。
国内中亚音乐文化研究主要聚焦于西域及丝绸之路音乐研究领域,诸多学者从区域国别研究视角关注中亚五国的音乐研究,如金文达教授的《中亚地区的音乐》一文首次概述了中亚各国的音乐历史发展,阐释了其形态结构特征[2]。金溪、王小盾教授则对西方学界有关中亚音乐研究的成果进行了部分梳理[3][4]。近来,王小盾与孙可臻还对中亚丝路音乐研究的基础资料及研究成果进行了一定的考察[5][6][7][8]。侯越、洛秦教授对美国学者西奥多·莱文(Theodore Levin)教授所做中亚乐器及图像学研究成果进行了翻译介绍等[9]。然这些研究大都为整体概括性叙述,未能对5-15世纪中亚音乐发展进行阶段性的细致描述和考察,也缺乏对主流音乐文化特征的详细讨论。我国中亚历史通史类著作均包含了中亚各时期文化发展概述,其中不乏音乐相关描写,但内容较少。加之国内学者对俄语及中亚本地语言音乐研究的丰硕成果译介较少,本文主要利用中亚音乐相关俄语及当地语言研究资料,结合中亚历史文化研究成果,以中亚历史文化演变为主线及背景,試图展示5-15世纪中亚音乐文化主流发展,梳理重要音乐家及其理论贡献,揭示、总结其音乐文化特征,借以推进我国中亚历史文化研究进程,丰富国内丝绸之路中亚段音乐文化研究成果。
一、萨珊波斯王朝的专业音乐发展
中亚音乐文化的历史可追溯至数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岩画中描绘了人们狩猎的场景及仪式性的舞蹈,某些物品类似于打击乐器。音乐伴随着人们的狩猎及劳作,原始的节奏和曲调循环往复,最具实用功能。公元前1000纪至公元2世纪,中亚人民音乐文化的突出特征为口头音乐和诗歌创作的出现,主要为神话题材的英雄传说。史诗般的歌声体现了勇敢的中亚人民为战胜敌人、保卫家园而战斗的生动情节。例如英雄史诗《萨克斯》展现了牧羊人西拉克为人民自由而牺牲的英雄主义气概[10]6。此外,音乐与生活密切相关,在宗教仪式、节日庆典及军事活动等社会各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曾记载波斯阿契美王朝时期①,波斯人在宗教仪式上咏唱赞美诗;希腊作家色诺芬则提到波斯人与亚述人的交战中也高唱英雄赞歌。希腊作家普鲁塔克讲述了帕提亚人使用打击乐器铜铃与鼓震慑罗马军队并赢得胜利的故事②。
公元3世纪,贵霜帝国进入衰落期,崛起于伊朗高原的波斯第二帝国——萨珊王朝统治了中亚西南部(今土库曼斯坦)。作为古波斯文化的发展巅峰,其音乐文化对中亚音乐体系及乐器的形成发展具有显著影响作用。萨珊王朝(224—651)时期,城市生活的发展带动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在各种节日及宫廷服务中产生了专门从事音乐艺术的表演人员,从此专业口述音乐传统被纳入到创作过程,加速了音乐表演的专业化。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才华横溢的音乐家,如拉姆汀、巴姆沙德、纳奇萨、阿扎德与巴尔巴德等。其中,巴尔巴德的音乐创作代表了萨珊王朝音乐艺术的顶峰。巴尔巴德曾在宫廷任职,是歌手、音乐家、作曲家和伟大的音乐理论家,他对萨珊王朝人民的音乐遗产进行了概括和系统化,创作了影响几代音乐学家的思想理论并进行实践。在他的创作中体现了古代宇宙科学及占星术意象,他曾创造一套与萨珊历法相对应的音乐体系,包括“7种君王用乐调式、30种分调式以及360种旋律等”[11]。这一时期抒情歌曲《雅资达·奥弗里德》《欧伊娜·贾姆希德》表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思想情感;《阳光》《美丽的一天》等歌曲体现了自然的变化及季节变迁;主要的英雄歌曲有《苏鲁迪·帕拉瓦龙》《苏鲁迪·马赞丹龙》和《库鲁索尼》等[12]15。
自公元前1世纪,波斯人创立琐罗亚斯德教(祆教),此后成为中亚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宗教。萨珊王朝时期,琐罗亚斯德教用于传教的诗歌被编撰成书,成为波斯圣书《阿维斯塔》。根据《阿维斯塔》记述,琐罗亚斯德教徒必须修读的科目包含音乐教育和音乐文化。在其宗教拜火仪式中,教徒围在尊师周围点燃圣火并演唱或演奏音乐。人们相信拜火仪式具有治愈疾病的特殊作用,在神话《沙阿纳姆》传说中,当演奏鼓和弦乐器时,产生的声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病人的头痛[12]11。《阿维斯塔》中还记述了琐罗亚斯德教徒庆祝纳乌鲁斯节的欢快场面③:这天撒马尔罕和周围村庄的居民在日落之后点燃篝火,唱起赞颂节日的欢歌,弹奏民族乐器。在手鼓伴奏下,人们举行火炬游行,随后跳过篝火到河里沐浴,祈求丰收及免受邪灵侵扰[10]9。
考古资料也提供了萨珊王朝时期乐器的相关信息,在塔克·伊·波斯坦遗迹的浮雕和萨珊王朝银器的雕刻上,生动地描绘出波斯人所使用的乐器,如钱格(波斯立式弯形竖琴)、巴尔巴特琴(短颈琉特琴)、鲁巴卜琴(双共鸣体琉特琴)、锵(扬琴)、奈依、唢呐以及手鼓等[13],这些乐器流行于整个中亚地区,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
二、粟特音乐舞蹈与隋唐音乐文化的双向交流
自公元4世纪起,中亚的奴隶制逐渐被封建制度所取代。6世纪,突厥人在中亚建立统治后,为中亚注入突厥文化的新鲜血液。“6世纪,在葱岭(帕米尔)以西,波斯以东,大雪山(兴都库什山)以北,楚河以南的地区形成了诸多以城邦为中心的国家,中国史书称这些国家为昭武九姓国,或胡国。”[14]41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河中地区称为粟特,即中亚索格底亚那。西突厥汗国统治时期,昭武九姓与中国隋唐王朝往来增多,除派使臣朝贡外,民间商业交往也空前频繁。至7世纪中叶后,唐灭西突厥汗国,昭武九姓正式成为唐朝属国,中原文化与中亚粟特文化广泛交流。据《新唐书》记载,粟特地区的昭武九姓有:康、安、曹、石、米、何、史、火寻、戊地。中亚今撒马尔罕地区为康国,今布哈拉地区为安国,今塔什干一带则为石国。
公元6-7世纪中亚音乐文化相关记载多见于我国史书,其次见于我国与中亚国家考古文物发现。根据乌兹别克斯坦考古资料记载:“在阿芙拉西奥卜④中发现了许多演奏长笛、乌德和多伊拉的陶俑雕塑,还有一种类似于短颈琵琶的乐器,琴身为圆形,琴头向后弯曲,两到五根弦。这些小雕像证明了音乐在河中地区及撒马尔罕城市生活中的重要性。”[15]27此外,角形竖琴及琉特琴也常见于粟特地区出土的纳骨瓮上奏乐图像,这些乐器是粟特本土常见的样式,反映了粟特地区的音乐特征[16]。有关粟特在前伊斯兰时代留下的文字记载十分有限,存留的文字反映了当地波斯文化传统与希腊、印度和其他文化传统的融合[10]9,这种融合也同样体现于中亚的音乐舞蹈艺术中。
隋唐时期,大量粟特人入华移民、经商,粟特文化逐渐东渐,粟特乐舞《胡旋舞》与《柘枝舞》风靡宫廷与民间,常在节日庆典、宴饮娱乐及祭祀仪式等日常生活中演出。《胡旋舞》主要出自康国、史国和米国等,节拍鲜明,奔腾欢快,舞者随音乐节拍旋转蹬踏,故名“胡旋”。伴奏音乐以打击乐鼓点为主,与其快速的节奏、刚劲的风格相协调。《柘枝舞》出自石国,舞者穿红紫五色罗衫,锦靴、腰带银蔓垂花,头冠绣花卷檐虚帽,帽上饰以金色铜铃。舞姿矫健,节奏多变,大多以鼓伴奏,最初为女子单人舞,后发展为双人舞。此外,粟特康国乐、安国乐还是隋唐宫廷《燕乐》的重要组成部分,粟特音乐家在我国音乐历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例如康国的琵琶高手康昆仑曾在唐宫廷任职,号称“长安第一手”;曹国的曹婆罗门、曹僧奴和曹明达祖孙三代皆擅长琵琶弹奏;粟特歌手与乐师在隋唐宫廷技压群芳,更是涌现了如何满子、米嘉荣等著名歌手。
中亚粟特音乐文化对中国隋唐音乐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同时,中原音乐文化也传入中亞。考古资料显示:“在阿芙拉西奥卜的宫殿中发现了一幅壁画,描绘了中国妇女和音乐家的画面,她们手中的乐器从演奏方式和外观都类似于中国乐器琵琶。在琵琶演奏者的前面,另一位音乐家弹奏的是筝。”[15]36此外,“在泽拉夫善河上游,距撒马尔罕70公里处的片治肯特Ⅵ号遗址42居室中发现了属于8世纪的壁画,其中有唐装女乐形象,在同遗址13号室发现了乐人手中所持的排箫,排箫起源于中国内地,它的发现表明在胡乐对唐朝音乐文化发生重大影响的同时,中亚音乐也吸收了中国音乐的成分”[17]。考古发现中的粟特文化遗存,体现了这一时期中原音乐与中亚粟特音乐的互动与双向交流,中亚音乐在波斯、希腊、突厥、印度及隋唐中原音乐文化的互动中形成了多元的音乐文化格局。
三、萨曼王朝中亚音乐科学的形成
自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创立伊斯兰教,早期伊斯兰教义禁止一切音乐享乐,其后在诵读《古兰经》中加入音乐的吟唱。7世纪阿拉伯人占据中亚后,直至8世纪中叶以前,伊斯兰文化在中亚并没有取代其本土文化[14]116。反而是旋律优美委婉且富有浪漫飘逸诗意色彩的波斯音乐深受阿拉伯人喜爱,阿拉伯音乐受到希腊、罗马及波斯音乐的广泛影响。在阿拉伯帝国初期,波斯风格的阿拉伯音乐曾风靡一时。伊斯法哈尼的《诗集》也被称为《歌曲之书》⑤,收集了中亚人民的诗歌和音乐,其中记述了许多阿拉伯人都在使用中亚音乐旋律。例如阿拉伯歌手穆萨吉曾去中亚学习多种音乐旋律,并以此为基础创建了歌曲演奏系统;另一位歌手伊本·穆克里兹也曾学习中亚歌手的演唱并创作了阿拉伯经文歌[18]。
8世纪下半叶,随着阿拉伯人在中亚完全确立了统治,阿拉伯语言、文字与宗教强势侵入,对中亚本土文化发展产生巨大影响。阿拉伯阿拔斯王朝时期(750-1258),其政权吸收了大批波斯人,形成了阿拉伯贵族与波斯贵族的联合政权。统治者既重视波斯古老文化传统,也注重吸收希腊、罗马和印度文化精髓。阿拔斯王朝后期,中亚地区诞生了三个波斯王朝,尤其在萨曼王朝统治时期(872-999),河中地区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中亚大部分居民改信仰伊斯兰教,波斯文化的复兴与阿拉伯文化的吸收进程加快,形成一种新的伊斯兰—波斯文化。这种多元文化的融合促进了包括音乐在内的中亚艺术的高度发展,随着波斯音乐与阿拉伯音乐文化的相互借鉴,大批科学家、诗人、学者和音乐家推动了这一时期音乐从感性经验向理性认知的实践过程。
10世纪生于中亚的著名哲学家、阿拉伯音乐家法拉比(870-950),为认识论、逻辑、数学、物理学、形而上学、政治理论、心理学和音乐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据学者研究,“法拉比采用柏拉图人文科学划分,将音乐与算术、几何学和天文学一起归为数学科学。后又将其归为四等分,通过对音程、音阶进行系统的数值分析来研究音乐,并探讨了它们在弦乐器上调音和定位的实际应用”[19]18。他在阿拉伯音乐四音列基础上,发展了乐器律制,将其律数由9增加到17,并区分为两类:按传统四度相生法所得的正律和根据中立音程所得的变律。
法拉比将音乐科学分为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理论科学涉及音乐的基础知识和研究方法。他认为在任何理论科学中,要达到完美就需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掌握其基本知识;第二,能够从该科学的基础上得出必要结论;第三,了解其他科学家的意见,并能够纠正本科学中的错误。在其音乐理论科学研究中,他强调应始于对声音的物理特性研究,因而法拉比在各种乐器的示例中说明了乐音的声学特性,振动体的音量与声音的音调之间的关系,并说明了以数学方式表示链接数量的因素[20]。在音乐实践科学中,法拉比分析了节奏,描述了当时流行的乐器,并指出乐器根据其声音的性质将起到各种不同作用:“有专为战斗而设计的乐器,声音高昂而锐利。有用于盛宴和舞蹈的乐器,其声婉转而飘逸;用于举行婚礼和欢乐聚会的乐器欢快而热烈,而用于情歌的乐器声音是忧郁且充满哀怨。”[10]11法拉比继承发展了古希腊音乐美学思想,进一步探讨了音声关系、音乐的社会功能及其与事物的普遍秩序联系。
法拉比的音乐思想集中体现在《音乐大全》《节奏分类法》及《音乐的类型》三本音乐著述中,其中最重要的《音乐大全》一书明确了音乐的基本概念,阐释了音乐的物理和生理学原理,并对曲谱进行了详细分类,记述了各种樂器的演奏方法。该书的研究范围和系统严谨性启发了之后一系列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写作的数学家,特别是穆罕默德·花拉子密和伊本·西纳这些伟大的哲学家和音乐理论家的作品,为此后研究马卡姆系统理论及阿拉伯音乐理论、伊斯兰音乐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19]18,将音乐的研究提高到独立学科的水平。
11世纪中亚最伟大的医学家、诗人、哲学家、自然科学家伊本·西纳(980-1037),拉丁语名阿维森纳。作为百科全书式的著名学者,他一生写作了99部书,研究内容涉及医学、哲学、天文学、几何学、教义学、艺术及语言学等众多领域。其中多部作品都包含音乐的物理特性、音乐品格和节奏基础等相关信息。在《治疗之书》和《救赎之书》中,伊本·西纳发展了音乐科学的声学方面,在《知识之书》中推进了前任法拉比在律学方面的成就,确立了中三度和中六度音程为特征的阿拉伯—波斯乐律体系[21]。此外,伊本·西纳在他的著述中概括了音乐的内部结构和感知规律,其音乐美学观念在于“音乐作为人类活动的产物,是一种有效的交流手段,不仅应通过经验,而且还应通过科学思维来鼓励音乐的发展”。他认为旋律的美感和内在本质归因于成比例的质(重音)量(长度),旋律及节奏的质量是音乐中的重要因素,因此,诗词和音乐的质量分配是完美音乐的最重要条件,应该特别关注节奏的质量问题以取得音乐和诗词的自然和谐[22]。伊本·西纳会演奏多种乐器,但他认为人声是最完美的乐器,并将其他乐器与之进行比较。伊本·西纳继承和发展了法拉比的音乐思想理论,其著述是研究中世纪中亚音乐文化的最重要来源。
10-11世纪,新波斯语伊斯兰文学在中亚呼罗珊和河中地区兴起,产生了一批如鲁达基(850-941)、菲尔多西(940-1020)等世界著名作家,他们同时也是宫廷诗人及音乐家。这一时期作品的主要类型是赞美执政者的诗歌,其序言部分伴随着乐器的演奏,舞蹈与乐器弹奏分开进行。除此之外,社会上还出现了表达进步观点和情绪的寓言歌曲,其内容揭露了官员的贪婪,蔑视神职人员的伪善和偏执。通常,在这种嘲讽背后隐藏着对自由的追求及呼吁。这样的歌曲迅速在大众中传播,获得广泛的欢迎和喜爱[10]11。鲁达基被誉为“波斯文学之父”,是塔吉克—波斯古典诗歌的奠基人,同时也是一位传奇音乐家。他的诗歌创作体裁多样、题材丰富,首创了四行诗及颂诗,抒情诗风格朴实明快、寓意深刻,充满民歌风味。其哲理诗言简意赅,富有教诲和训诫意义。他亦是一位音乐奇才,不仅“擅长弹奏琵琶、竖琴、琉特琴等乐器,还亲自改进了琉特琴的制作和演奏方法,创作了‘塔鲁纳(tarona)和‘舞珐丽(ufar)两种古曲调”[23]。
萨曼王朝时期,出现了基于两个押韵诗句和11个音节的专业英雄史诗。10世纪中亚最伟大的诗人菲尔多西基于中亚人民的史诗传统及神话传说,创作了他的叙事史诗作品《列王纪》。在作品中,诗人再现了古代波斯英雄,追忆了波斯28位帝王时期的历史事件,并对当时的音乐生活和乐器进行了丰富的描述。例如在对宫廷宴会场面的描绘中,诗人写道:“音乐家弹奏竖琴及琵琶,宾客饮酒享乐直到午夜。”[12]29除此之外,音乐也广泛运用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宗教礼拜、节庆仪式和婚丧嫁娶中不可缺少的内容,这些都成为诗人们诗作中重要的描述对象。这一时期中亚的乐器种类繁多,主要的弦乐器有竖琴、琵琶、乌德琴、琉特琴和扬琴等,管乐器有奈依、双簧管、长笛和小号等,打击乐器有手鼓、小铃和卡锛等[14]344。
萨曼王朝时期,宫廷诗人音乐家的诗歌作品不断丰富,学者的理性研究也推动乐器律制及其演奏方法的深入开发,最终促使中亚音乐科学的形成。
四、突厥系王朝时代中亚音乐的治疗功效
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欧亚草原发生了一次游牧民族自东向西的迁徙运动。在此后的200多年间,喀喇汗、伽色尼、塞尔柱三个突厥系王朝瓜分了萨曼王朝遗产,开启了中亚地区突厥化、伊斯兰化的重要时期。喀喇汗王朝,随着突厥—伊斯兰文化的形成,出现了一批突厥—伊斯兰文学学者,形成了喀什噶尔和八拉沙衮为代表的两个文化中心⑥。在著名学者马哈穆德·喀什噶里编著的《突厥语大辞典》中,提供了史诗作品的样本歌曲和节选;法赫雷丁·米巴拉克沙赫的《历史》,也记述了突厥诗歌及其音乐信息。音乐是对听众进行道德影响的重要手段,旋律甚至被用作治疗的工具,这在当时社会是一种普遍的观点[10]12。
“巴赫希”(bakhshi)一词在中亚文化中具有两个主要功能,即萨满巫师(治疗师)和音乐家(史诗歌手)。早期,史诗歌手与萨满巫师并没有区别,两种功能同时存在。随着时代发展,现今“巴赫希”一词在中亚突厥人群中具有单独含义。例如在吉尔吉斯人和哈萨克人中,巴赫希仅是治疗师,他们在神灵的帮助下进行治疗仪式,既不唱史诗歌曲,也不弹奏乐器。而在乌兹别克人和卡拉卡尔帕克人中,巴赫希的主要功能从早期的治疗师变为史诗歌手[19]50。
突厥王朝时期,巴赫希的治疗力量对于中亚草原游牧区人民尤为重要。作为萨满巫师,音乐是他们用于与神灵沟通及进行巫术治疗疾病的手段。在治疗过程中,巴赫希通过击打手鼓等乐器并念诵咒语驱除邪灵,仪式中涉及“迁移、归来”等程序[20]46。巴赫希通常用三种方法进行治疗,而可治愈的疾病都被认为是恶魔起源,因此,治疗也是驱魔的过程。在治疗前一天,巴赫希会咀嚼一块山羊皮,梦中神灵将告诉他选择哪种治疗方法。第一种方法:当巴赫希念动咒语并抚摸病人脑袋,邪灵被迁移到火炬而焚灭。第二种方法:巴赫希给病人施法念咒语,病人随之背诵咒语直到他被治愈,期间巴赫希会用乐器给病人捶打身体,用以驱逐邪灵。第三种方法:巴赫希吟唱灵歌或演奏乐器,与神灵沟通并请他们相助。这种治疗将经历几个不同阶段,音乐也涉及简单的旋律及节奏变化。期间,巴赫希可能会停止演奏,起身并开始用他的乐器击打病人,或者当巴赫希进入一种恍惚状态时,可能会发出口齿不清的低吟和哭声,这或是因他受到“善”的精神感召,亦或是他正与邪灵作战。最后,巴赫希将邪灵从患者的身体转移到其自身或牺牲动物的器官。这一过程中还可能涉及咒语、喊叫、腹语及各种禁欲习俗,包括自我鞭笞,踩锐刀或手持炽热铁块等行为[24]。当巴赫希结束这种状态时,往往又开始演奏他的乐器并返回到灵歌的原始旋律。三种治疗方法中,第三种用时最长,甚至会持续整晚。
随着时代的发展及现代医疗技术的进步,中亚巴赫希音乐的治疗功能更多地被民间史诗艺术家所取代,巴赫希用丰富的表情伴随乐器弹奏讲唱生动的史诗故事情节,并与听众广泛互动,成为中亚乌兹别克人智慧和創造力的代表——达斯坦(史诗说唱)艺术。
五、帖木儿王朝中亚社会音乐多样性
13世纪,随着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军队的入侵,整个河中地区被摧毁,许多科学家和艺术家因战乱而死亡,文化艺术的发展近乎中断。13世纪70年代后,中亚大部处于察合台系蒙古人建立的察合台汗国统治之下。14世纪下半叶,西察合台汗国突厥贵族帖木儿统一中亚⑦,并建立中央集权国家。帖木儿帝国时期(1370-1507),中亚经济大力发展,来自不同国家的工匠、学者、歌手和音乐家为撒马尔罕、赫拉特等城市文化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中亚文化开启了名为“帖木尔文艺复兴”的繁荣昌盛时期[25]。
这一时期,音乐广泛运用于人们的社会生活。鼓手在日出、晌午和日落时击打节奏,以明确时间。在斋月中,使用打鼓来唤醒斋戒的人们。作为统治者,帖木儿非常重视音乐的军事价值,他认为音乐是一种精神因素,可以将军队的战斗精神保持在较高水平,并为军队的发展做出贡献。帖木儿用三样东西来奖励英雄:骄傲的喊叫声、一面旗帜和一面鼓[26]。由此,乐器不仅是一种精神象征,更是军事实力的象征、勇气的象征和战士荣誉的象征。帖木儿的军乐队由各种打击乐器组成,使用了在中亚地区流行的各种鼓及喇叭和号角。由这些乐器演奏的军乐不仅可以使士兵振奋精神、提升战斗力,还可以起到威慑敌人,使其溃败的效果[12]23。
帖木儿本人重视音乐及艺术家,他对待音乐及音乐家的态度也影响了他的子孙。在他的继任者沙哈鲁统治期间,中亚音乐艺术进一步发展,风格多种多样,并广泛开展了音乐的国际化交流。如1404年夏,历史学家哈菲兹·阿布鲁在描述沙哈鲁在撒马尔罕庆祝节日时,提到来自七个国家的音乐家演奏不同音乐的场景。他用“塔里哈”(tarīqa,方法、道路)一词表征波斯风格,用突厥语“约孙”(yosun,风俗)表征突厥风格,蒙语ayalghu(歌曲、旋律)代表蒙古风格。他还通过使用不同的阿拉伯术语“方式”和“规则”等来区分诸如伊朗、阿拉伯、中国和阿尔泰山脉等其他国家音乐家的风格,强调其多样性[27]。沙哈鲁之子兀鲁伯是中亚著名的天文学家,建造了天文台,编成了《兀鲁伯天文表》。在他统治期间,经常鼓励诗人和音乐家进行创作,这一时期民间元素越来越多地渗透到文学和宫廷音乐中。撒马尔罕的诗人和音乐家经常受到其他城市贵族及富商邀请前去表演,社会音乐活动频繁。然而也正因为兀鲁伯重视学术、爱好科学和崇尚文艺,引起了宗教界的不满,最终被宗教极端分子杀害。至15世纪下半叶,中亚地区文化艺术中心已转移到赫拉特⑧。
15世纪塔吉克诗人、学者贾米(1414-1492)是波斯古典诗坛最后一位著名诗人,因而被誉为“末代诗圣”。其诗歌创作题材广泛,以叙事诗、抒情诗、训言诗和颂诗为主。内容主要宣扬苏菲主义观点,阐述宗教伦理,赞颂安拉及先知穆罕默德、颂扬君主、描述爱情故事等,语言精炼,寓意深刻,充满哲理且富有浪漫色彩。他在15世纪下半叶创作了《音乐手册》,发展了法拉比和伊本·西纳的音乐理论。《音乐手册》中的诗歌内容简短,但意义非凡,旨在强调音乐的神圣品性,从而调和了当时音乐与宗教体系之间的突出矛盾。贾米还致力于专业口头艺术——马卡姆艺术的研究,他将主要音阶分为17级,认为该音阶的基础是七度音阶,对应于乌兹别克音乐固有的混音调。此外,贾米强调“节奏是声乐和器乐作品旋律线出现的基础,其各个部分都应与诗歌的韵律相吻合”[28]。贾米在其著作《关于音乐的论文》中对基本节奏公式进行了阐释,并进一步指出节奏是连接诗歌和音乐的手段。在诗歌中,主要元素是字母,由它们的组合来形成诗节。在音乐中,节奏犹如字母在诗歌中的作用,而重音是节奏的基本因素。诗歌的节奏韵律与音乐的旋律互为影响,相辅相成[29]。贾米的作品普遍包含宇宙观的阐释,据此音乐表达了自然和谐与社会道德基础。在许多方面,他虽然重复了法拉比和伊本·西纳的音乐思想,但又不同于其中流行的数学方法,诉诸于音乐家的“自然健康感觉”,从而在理论与实践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10]17。
15世纪,中亚伟大的诗人、学者和思想家阿利舍尔·纳瓦依(1441-1501)以其丰富和卓越的文学创作成为乌兹别克文学的开创者与奠基人。他出生于赫拉特,自幼接受了良好的教育,饱读诗书。青少年时期不断研习突厥、波斯和阿拉伯语言文学以及历史、哲学、天文、算法等学科知识,在绘画和音乐方面颇有造诣。其诗作广泛运用突厥语、波斯语及察合台语,写作文学著述30多部,贯穿了其人道主义思想,高扬真善美、鞭笞假恶丑。在他担任苏丹·侯赛因的大臣期间,经常出资保护诗人、音乐家和艺术家进行创作。纳瓦依本人是优秀的音乐鉴赏家,也从事音乐作品的创作,他认为音乐对社会的影响力巨大,而好的音乐应该是清晰且有效的,并与人民现实生活密不可分[20]39。纳瓦依喜爱民间歌曲,在他的专著《诗歌大小的尺度》中,他指出乌兹别克和塔吉克诗人使用的诸多语汇都来自于民间歌曲。
5-15世纪中亚学者的音乐理论著作中并没有专门介绍民间普通百姓的音乐生活,但毫无疑问的是,在宫廷和城市中丰富发展的音乐艺术及诗人音乐家的创作实践,都是在民间音乐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发展起来的,严格的作曲规则很大程度上是对民间音乐进行创造性思考的结果[10]17。经过帖木儿王朝统治者与宫廷诗人、艺术家的不懈努力,撒马尔罕和赫拉特成为15世纪穆斯林世界的音乐中心,其艺术及宫廷音乐对16世纪周边国家及其民族音乐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六、结语
5-15世纪中亚主流音乐文化以宫廷和城市音乐文化为代表,在不同历史文化特质的封建王朝更替中延续其发展,呈现出多元性、科学性、实用性和诗歌一体性特征,具体如下:
首先,5-15世纪中亚音乐文化的多元性体现为以波斯音乐为基调,加以阿拉伯音乐理论构建其体系,以突厥—伊斯兰音乐文化、波斯—伊斯兰音乐文化为表征,具有明显的地域风格差异,呈现草原游牧音乐文化与绿洲农耕音乐艺术的混合发展特征。这一时期中亚乐器的形成与发展,体现了历史上各统治政权的生产方式、文化特征及其与周边国家音乐交流的相互影响。随着政权的更替,音乐体现了异质文化的融合、继承与发展,从而造就了音乐文化的多元性特征。
其次,5-15世纪在众多中亚学者、诗人和音乐家的普遍关注及研究下,促成了中亚音乐科学的形成及发展。研究领域主要为两个方面:其一,音乐声学、律制和调式结构等本体方面。如法拉比、伊本·西纳将音乐划归为数学科学,利用数值分析进行音律计算,并将其运用于弦乐器的调音、定调;贾米研究诗歌韵律与节奏、重音之关联,创制节奏公式等。其二,音乐美学、伦理价值等理论方面,如音乐的宇宙观、自然和谐论、音乐治疗论的阐释等。中亚音乐科学的创造者大都在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多个领域饶有建树,对于音乐的思考严谨且理性,并创作了具有影响力的音乐理论著述,体现了这一时期音乐文化的理性思维及科学性特征。
再次,5-15世紀中亚音乐文化的实用性体现于音乐的多种社会功能,近代考古发现突出显示了早期音乐的政治交往功能和宗教仪式功用。中期以后,学者和音乐家更加重视音乐的美育及社会道德教化功能、音乐治疗功效。晚期,帖木儿重视音乐军事作用的发挥,其子孙也将音乐的国际化交流视为一种政治外交活动。诗人的诗作广泛展现了音乐家在宴会中弹唱乐曲的场景,突出了音乐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娱乐功效和审美功能。
最后,强调诗词韵律与音乐节奏的协调,即诗歌一体性特征是5-15世纪中亚音乐文化发展的动力之源。诗人即是歌手,文学作品在特定的节奏与旋律模式进行中抒发对真主的赞美、对君主的颂扬、对人事的劝寓、对爱情的向往。旋律多取材于民间歌曲,依据诗词节律及重音规则即兴创作,蕴含了对生活的诗意表达。
[注 释]
①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0年至公元前425年),古希腊伟大作家、历史学家,著有《历史》一书,被尊称为“历史之父”。
②普鲁塔克(约公元46-120年),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作家、哲学家、历史学家,以《比较列传》(又称《希腊罗马名人传》或《希腊罗马英豪列传》)一书闻名后世。
③纳乌鲁斯节有着悠久的历史,起源于古代波斯,在波斯语中,“纳乌鲁斯”是“新的一天”的意思。纳乌鲁斯节与古波斯的太阳历有关,在3月20日或者21日这一天,白天和黑夜的时间长度相等,春天终于来临,新的耕种季开始,是农民劳作和孕育希望的时期。伊朗和中亚各民族自古就有纪念春分日的传统,最终形成了纳乌鲁斯节。中亚国家中,乌兹别克斯坦率先恢复纳乌鲁斯节,并将其作为国家节日。
④阿芙拉西奥卜:撒马尔罕古城,古代粟特城址。北部建于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4世纪被希腊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军队占领;古希腊人称此地为马拉坎达。至撒马尔罕城北,此城为粟特地区最大的政治经济中心。
⑤伊斯法哈尼:阿拔斯王朝诗人、历史学家。
⑥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古城;八拉沙衮:今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境内的托克马克。
⑦帖木儿(1336-1405),帖木儿帝国创建者,中亚著名军事家、政治家。
⑧赫拉特:阿富汗西北部历史名城,帖木儿帝国后期都城,文化艺术中心。
[参考文献]
[1]李琪.历史记忆与现实侧观:中亚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6.
[2]金文达.中亚地区的音乐[J].音乐研究,1993,(01):54-61.
[3]金溪,王小盾.西方世界的中亚音乐研究:中亚各地区篇[J].音乐研究,2016,(04):54-69.
[4]王小盾,金溪.西方世界的中亚音乐研究:中国关系篇[J].音乐研究,2016,(03):24-38.
[5]王小盾,孙可臻.关于中亚的丝路音乐研究:概论篇[J].音乐文化研究,2019,(01):6-14.
[6]孙可臻,王小盾.关于中亚的丝路音乐研究:相关成果篇[J].音乐文化研究,2019,(02):6-20.
[7]孙可臻,王小盾.关于中亚的丝路音乐研究:基础资料篇(上)[J].音乐文化研究,2019,(03):5-12.
[8]孙可臻,王小盾.关于中亚的丝路音乐研究:基础资料篇(下)[J].音乐文化研究,2019,(04):6-14.
[9]西奥多·莱文著,侯越、洛秦译.中亚音乐研究(二)——乐器分类、制造及其图像学研究[J].音乐文化研究,2021,(02):7-14.
[10]Соломоновой Т.Е. История узбекской музыки[M].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узыка. Москва. 1979:6.
[11]俞人豪,陈自明.东方音乐文化[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3:228.
[12]Madrimov Bahrom Xudoynazarovich. O‘zbek Musiqa Tarixi[M].Toshkent: Barkamol fayz media, 2018:11.
[13]朴玉敏编.世界各国音乐简述[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5:60.
[14]蓝琪,赵永伦.中亚史(第2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41.
[15]Alexander Djumaev. Musical heritage of Uzbekistan in collection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M]. Uzbekistan Today, Zamon Press Info. Toshkent, 2017:27.
[16]吴洁.粟特纳骨瓮上的音乐图像释读[J].黄钟,2021,(04):149-152.
[17]蓝琪,苏立公,黄红.中亚史(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398.
[18]Вызго Т. C., Карелова И. Н., Кароматов Ф. М. История узбекской советской музыки (1917-1945) [M].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имеии гафура гуляма.Tашкент. 1972:29.
[19]Theodore Levin, Saida Daukeyeva., The Music of Central Asia[M].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6:18.
[20] Abdullayev R.S. O‘zbek Mumtoz Musiqasi[M]. Toshkent: Yangi Nashr. 2008:66.
[21]Абу Али ибн Сина Математические главы. 《Книги знания》[M] (Донишнома). (О математических главах 《Книги знания》 Ибн Сины и комментарии Умарова С.М. и Розенфельда Б.А.). Душанбе: 《Ирфон》, 1967:180.
[22]Зокиржон Тоирович Орипов.Шарк Мусикий Манбашунослиги (X-XI Асрлар)[M]. збекистон Давлат Консерваторияси. Ташкент.2008:41-44.
[23]M.S.阿西莫夫,C.E.博斯沃思主编,华涛译.中亚文明史(第四卷上)[M].北京:中译出版社,2016:78.
[24]Beliaev, Viktor M. Central Asian Musi[M]. Trans. Mark and Greta Slobin. Middletow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75:294-295.
[25]蓝琪,刘刚.中亚史(第4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233.
[26]Temur tuzuklari. Т., 《SHARQ》[M] NMAK bosh tahririyati, 2005:77
[27]M.S.阿西莫夫,C.E.博斯沃思主編,刘迎胜译.中亚文明史(第四卷下)[M].北京:中译出版社,2016:641.
[28]Трактат М.Джам и Абдурахман[M].Toshkent:1992:105.
[29]Абдурауф Фuтрат .Узбек классик мусиаси ва унинг тарихи[M].Фан,наш Dиёти,Toshkent: 1993: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