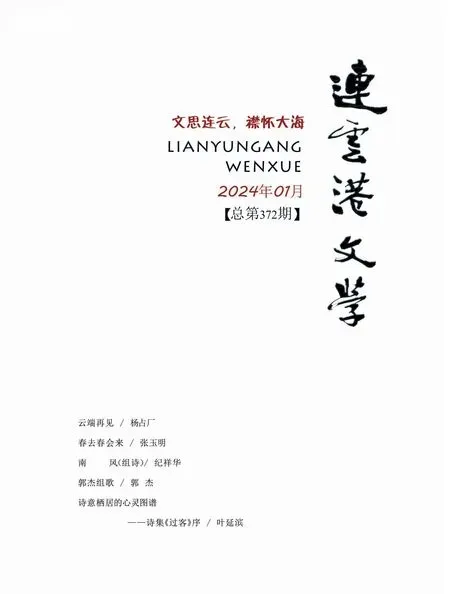吃肉坨子
吴明忠
听说“盐城八大碗”进入全省非遗目录,我一个在外地工作的盐城人很是高兴。其中一道菜“红烧糯米圆”,老家叫“肉坨子”,是我孩提时代的最爱。几十年过去了,吃肉坨子已经不是什么难事,可它给我留下的乡村生活记忆却没齿难忘。
四五十年前,海边人家生活条件普遍不好。除了逢年过节之外,吃上一顿肉都是很大的奢望,更不要想吃肉坨子了。在农村只有遇到红白喜事的时候,主家才请厨师做肉坨子。因为这是一道硬菜,请客吃饭,桌上如果少了肉坨子,是要被亲友抱怨的。
比起扬州名菜“红烧狮子头”,盐城“红烧糯米圆”制作工艺不是特别复杂。肥瘦适中的新鲜五花肉,到集市上买上三五斤,拿回来后用温水清洗干净。厨师先用锋利的刀子把肉切成小块丁子,放上点葱姜,然后双手并用,在砧板上把肉丁剁成肉泥。这个过程很有看头。水平高的厨师双刀飞舞,真有点像现在乐队的司鼓一样,很有节奏地把个砧板剁得砰砰带响,弄得左邻右舍个个晓得某人家要做大事情了。
就在厨师开始切肉剁肉的时候,其助手要按三斤肉一斤米的比例,把糯米饭做出来,装出锅,放在边上晾一会儿。为什么肉坨子里面要放糯米?我想也许是肉比米贵,很多人家买不起那么多肉,肉不够,糯米凑。离开老家后,我吃过用萝卜、山药、荸荠拌肉做的肉坨子,甚至还有用老豆腐和肉做的豆腐坨子,问其缘由,大都是过去老祖宗饥荒时代传下来的。这就进一步印证了我的猜想。但是,今天的红烧糯米圆之所以保留放糯米这道工艺,我想应该是逐渐富裕起来的人们发现,肉泥中放进适量糯米饭,恰恰起到荤素搭配、吸油解腻的特殊效果,而吃纯肉做的肉坨子反而吃不出那个味了。肉剁好了,糯米饭晾好了,接下来就是和馅。除了把肉泥和糯米饭按照一个方向搅拌均匀到一起,还要敲三五个草鸡蛋进去,再放点生粉,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味道更鲜,二是考虑增加结构力。
肉坨子做得好不好、水平高不高,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食盐有没有放得恰到好处。因为肉泥是生的,水平高的厨师一般不会用舌头去舔尝肉的,否则就要被别人笑话。他就凭着自己多年经验,看肉馅多少放适量食盐,拌匀后挑出一小块,用鼻子嗅嗅,凭着加盐以后的肉泥散发出的气味轻重,就能断定咸淡是否适中。一般来说,偏淡一点更好。因为一旦加重了,再想把咸味拔出来很难,而如果放淡了,后期在红烧阶段,可以通过加入食盐或者酱油来弥补咸味的不足。
经过前面几道工序后,要将拌好的糯米肉泥搁在盆里醒两三个钟头,让食盐在肉米之间充分融化。接下来就要下油锅煎炸了。这里面也有几点讲究。一是要等菜籽油烧开后,不能用冷油,否则就会把肉坨子炸老了。二是肉坨子要个头适中、大小均匀,通常和一个鸡蛋差不多。太大了,不好煎,太小了,容易糊。厨师先用一只手从肉泥中抓上半把,再用两只手来回抟几下,松软的糯米肉坨子雏形就出来了。
轻轻往热油里一放,肉坨子四周很快就泛出滚开的油花,肉香味也随之飘了出来。这里有第三个注意事项,就是半熟出锅,一般不把坨子炸熟了。因为后面还有一道工序,就是用淡淡的酱油汤煨一煨。如果前面炸得太熟,后面再煨,整个肉坨子就很容易煮烂,肉也吃起来不嫩。等到糯米肉圆在油锅里开始往上漂的时候,就可以起锅了。看起来黄灿灿,闻起来香喷喷,外酥内软、半生不熟的糯米肉圆出了油锅,经过计数,被装到大瓷盆里一装,就随时准备着二次下锅。
如果说前面的絮絮叨叨只是说明了糯米圆子制作过程的话,接下来就是“红烧糯米圆子”整个加工流程的最后一环——红烧。
农村大席,有的是几十桌同时开饭。这就对厨师统筹每道菜的加工时间提出了很高要求。按照传统的规矩,肉坨子是第三道菜,前两道是烩土膘、大鸡抱小鸡。但是几十桌上百个肉坨子要同时出锅,必须在开席之前先要把糯米肉圆下锅。工艺倒不复杂。先是把大锅烧热,往里面倒点菜籽油,然后放进适量的红酱油,再加水。把水烧开后,放进糯米肉圆,用大火烧开后改小火,慢慢地煨,让鲜美的酱油味道逐渐渗透到肉圆中去。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根据油汤的咸淡决定是否补一点食盐进去。农村人口味大多比较重,太淡了,吃不出味来,所以厨师会稍微多放一点食盐。旁边准备好切碎的小葱或者蒜苗。
等到第二道菜“大鸡抱小鸡”一端出去,这边厨房里的师傅就要起锅装肉坨子了。因为又经过红烧这个环节,糯米肉圆已经非常松软,所以起锅装盘要特别小心,不能弄得破皮烂肉,装出来要有型,最好从四周往中间堆,堆出一个小山的样子,寓意主人家有金山银山之意。还有一个注意事项一定不能搞错。农村老规矩,一桌坐八个人,每人是三个肉坨子,总共二十四个,一个不能多,一个不能少。
等所有的肉坨子全部装到碗里后,厨师会在每一碗上撒上少许葱末或者蒜末。葱蒜自然的香气就随着碗里的热气往外挥发。随着传菜的一声喊,“得罪,碰啊!”一碗碗个头饱满、有汤有货、香飘四溢的红烧糯米圆子,就这样登堂入室,走上了大席,掀起八大碗的第一个高潮。
每每想到这里,有一个画面时常浮现在脑海。昏黄的汽油灯下,人声嘈杂,热气腾腾。在农村平时吃不到什么好东西,碰到谁家做事情,父母亲会带上一两个孩子一起去吃酒席。因为人多席少,有时候能把大人安排上桌子,就顾不上小孩子。小孩子就只能眼巴巴地等在门外,或者就在附近玩。一到红烧糯米圆子上桌子的时候,整个酒席上就像炸开锅似的。凡是带小孩来的父母,都要用调羹装上第一个肉坨子,开始朝外喊。“小二子”“小三子”此起彼伏,很快在外边玩疯了的小孩立刻停下来,一个个和小鸡找母鸡一样,迅速溜到自家大人的身边,麻溜接过调羹。脸皮薄的,不好意思当那么多大人面吃,端出去干。也有脸皮厚的,一到手里,三下五除二,一个鸡蛋大的肉坨子眨眼间就滑下了肚子,还眼巴巴地看着桌上的大碗。带两个孩子来的,分给了小的,还要再分一个给大的,父亲和母亲有时自己只能吃一个。平时邻里关系不错的,或者有亲戚关系的,有时会主动把自己的三个肉圆计划拿出一两个来,分给那些站着不肯走、吃了还想吃的孩子。
说到吃肉坨子,还有一种情况蛮有意思。有时候家里大人无法出席,让小孩子来参加。有的人就爱捉弄孩子,等到红烧糯米圆子上来时,就跟这个孩子说,肉坨子一人四个,事事如意。如果这个孩子真一口气吃下四个圆子,他就哈哈大笑起来,暗地里说这个孩子没有家教。所以,不少家长在孩子临出门前都要和他们讲,上桌子,吃圆子,一个人只能吃三个,不能多吃。也有的孩子不好糊弄。如果哪个大人叫他吃四个圆子,他就说,“你先吃四个,我就吃四个”,人小心眼多,大家全都哈哈大笑起来,直夸他真聪明。农村的这些老规矩,就在这些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代代相传。
胃是有记忆的。在外三十多年,虽然现在衣食无忧、吃穿不愁,但还是经常想吃家乡的红烧糯米圆。每次回老家,母亲和其他的亲戚都要想方设法搞点让我一饱口福,临走的时候还要带上几十个。自从大舅舅、大舅妈从老家搬迁到连云港来,和表弟他们一起生活,只要叫我过去吃饭,不用说,一定少不了红烧肉坨子。虽然我爱人没觉得盐城肉坨子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她更爱淮安山药坨子,但她晓得我偏好这一口,十几年前从母亲和大舅妈那里学会了怎么做盐城的红烧糯米圆,现在已经完全出师,而且学习扬州狮子头的做法,对工艺进行了改良,放进了荸荠,做出来的红烧糯米圆,软中有硬,香中带脆,别具一格。家有贤妻,厨有美食,夫复何求?
二〇一七年春节,我在美国耶鲁大学访学,第一次一个人在国外过年,父母到连云港陪我爱人、孩子一起团聚。通过微信视频见面,问候了家人。老母亲一句话,说今年过年你吃不到妈妈做的肉坨子了,说得我热泪盈眶。挂掉电话,一个人面向家乡的方向号啕大哭一场,取经万卷,来此异邦,不远万里,背井离乡。当天下午,一群留学生和司马懿老师相约聚餐,每人带上一个菜。我凭着自己的印象,现场做了几十个肉坨子,让大家品尝品尝我家乡的味道,赢得了一致好评。虽然品相离正宗的盐城红烧糯米圆还差了一些,但是这一道黄海边上承载着盐民们苦难记忆和美好向往的美食,也终于有机会跟着一个盐城后裔漂洋过海,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马克思说过,地方的,就是世界的,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