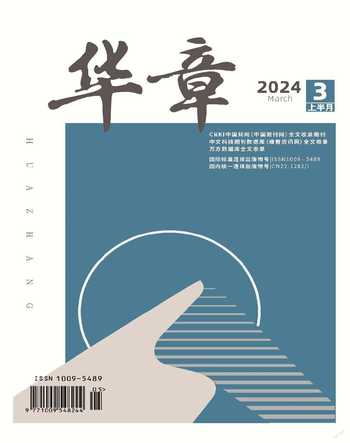刑事审判中常理的适用研究
[摘 要]常理是广泛适用的概念,内涵丰富,它是社会共同生活的基础,也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认知与共同价值追求。常理影响每个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也会形成一个人的司法潜见。最高人民法院的(2016)刑再3号刑事判决书将常理适用于刑事审判实践,充分运用了常理裁判理念,使常理融入刑事审判。审判实践中常理的运用有赖于法官将自己主动置于社会存在,尽可能地用与社会共性相一致的个性进行判断。刑事审判中运用常理对犯罪者的定罪量刑是社会存在及其规律的内在要求。
[关键词]刑事审判;常理;正当性
在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的(2016)刑再3号刑事判决书(简称:最高法刑再3号刑事判决书)首次将“常理”运用到判决书中。法官对卷中证据的排除或者确认,除了原有的司法手段,还运用了“常理”。事实上,刑事审判中的常理是一种观念,也是一种思维方法。刑事审判的定罪理念是入罪必须讲究国法,即是否符合犯罪构成;出罪应遵循合理,即是否合乎常理常情。在刑事案件诉讼过程中,无论是侦查人员、检察人员还是审判人员,不仅要考虑犯罪之中的事实,还要考虑犯罪背后的深层次因素,即犯罪之前的事实和犯罪之后的事实。不仅要分析犯罪原因,还要确定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这些刑事审判过程中影响性要素的判断,离不开基本的人类朴素情感,朴素的常理。也就是说,聂树斌案件原审有关重要证据缺失的情况下,充分运用了“常理”这个重要的裁判理念,并多次使用“不合常理”表述。更重要的是最高法刑再3号刑事判决书中存在显而易见的常理,正是普通老百姓都懂得、普遍认同的道理,是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观,是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试金石。
一、常理的基本概念
常理并不是物质性的有形体,而是以理念、信念、观念的形态存在于语言,并为人们所表述。通过语言运用使得常理具有物化为实指。但是,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不能违背人民的意愿,要依据人们日常遵循的常理;法官在判案、定罪处刑时,要依据自己的良心,也要依据常理;法学家在解释分析法律时要依据常理,形成的法学理论不能违背常理。因此,当人们尝试运用常理时,就应当先理解常理的语境及其表述。那么,何谓常理,《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常理的定义为通常的道理[1]。常理是公众认同的基本道理,是人们通过对常识的理解和运用,以及对常情的理性判断所得出的道理,是人们公认的道理[2]。依据词典释义,“常理”之“常”具有不同维度内涵,“常”意味着一般、普通、平常,“常”还有客观规律之意。常理之“理”,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3]。常理不是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而是经过人民群众长久的实践检验而逐渐形成的人与人之间共通的基本经验、基本道理和基本感情[4]。
常理与法理、法条、审判等司法理论和实务呈现若即若离的关系。一方面,常理被人们所认可而融入法理、法条、审判等之中;另一方面,法学教义、司法实践、审判实务等运行过程中,又要探究背后的常理,检视刑事审判是否违背常理。实践之于常理而言,常理属本原性要素,刑事审判应当遵循常理。
二、刑事审判中常理运用情形
科学研究起源于问题,实践是问题的源泉。德国学者阿图尔·考夫曼指出:问题的方向由其对象决定,因其只有从具体事物入手,故问题的提出直接与具体事物相连[5]。事实上,刑事审判中作为司法人员认定案件事实的基本逻辑是通过搜集固定的证据链,进行回溯性的呈现。案件事实认定过程中,证据的证明力大小问题,关键证据不足或缺失,卷中证据矛盾冲突等问题不同程度存在。常理作为人类社会共同价值,体现在人们潜意识中,作为司法判断者对卷中证据问题分析判断及采信,发挥着重要的功能。
以最高法刑再3号刑事判决书为例,在聂树斌案件中法官的常理运用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聂树斌供述审查、运用中的常理。在最高法刑再3号刑事判决书的说理中,卷中证据显示聂树斌对关键事实的供述,不仅前后供述矛盾,而且内容反复不确定。关于作案时间、何时去掉被害人内裤、被害人的自行车型号,以及作案动机、死者的年龄、死者衣物即穿连衣裙质地特点等关键事实和主要情节,卷中显示的聂树斌供述相互矛盾。根据卷证据中分析,聂树斌的态度具有双面性,一方面认罪,另一方面对基本事实不清楚,这种矛盾和反复不合常理。二是相关证人证言审查、运用中的常理。在聂树斌案件的原始审卷宗内,没有证人证言的情况,存在两种不同的解释。第一种,当时的办案人员解释称在对案件排查过程中是用笔记本记录,只对侦破案件有必要的证据材料才整理入卷,对案件侦破没有必要的材料就不再整理,故没有入卷;第二种,当时的办案人员在办案过程中没有装订侦查卷的规定,办案人员把案件材料送给预审科,由预审科挑拣甄别,对案件没有关联的材料直接剔除,所以证人证言缺失,很有可能是被预审剔除后存入副卷,后来搬家副卷遗失,这明显不符合常理。三是作案工具审查、运用中的常理。卷中证据的现场勘查笔录显示,死者颈部缠绕一件短袖花上衣,原审判决将该情形作为聂树斌杀人犯罪工具。事实上,案发时聂树斌经济条件较好,而且聂树斌有工作,每月有几百元的固定工资,有自己的山地自行车,生活条件好,不缺吃,不缺穿,卷中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聂树斌具有不良嗜好,没有证据显示其迷恋女士衣物,因此聂树斌供述称其为了自穿偷一件破旧的、短小的女式花上衣,不合常理。同时,卷中证据显示聂树斌供述称偷取花上衣的具体地点不明,也不能确定,存在有多种说法,供述又出现反复且相互矛盾,不合常理。事实上,裁判者遵循法律规范的刑事审判,是确保社会生活的安定性的前提。审判中常理的运用有助于法官从纷繁复杂的法律现象中把法律关系,刑事审判规则恰当地适用具体个案判断。认识和理解常理并在刑事审判运用,才能更接近对法律的真知,更好地服务审判实践。审判实践中常理的运用,依靠的是法官直觉指引,需要法官具有丰富的审判经验和生活经验做积淀。
三、刑事审判中常理运用的理性反思
常理不是规范性法律用语,任何人都可贯以常理名义解释其实施行为的合理性、正当性,也不管其实施的行为是否真的体现常理。常理作为一种理论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哲学根基。刑事审判中常理实践与现代法治状况、法治教育、法学的整体水平有关。知法不知常理,受到的教育越高、法律知识越高对基本道理、常理的背离可能性越大。解决这些迫在眉睫的问题是每一位有责任感的法学家所必须面对的,特别是受过高等法学教育的人对最基本道理的尊重和认同,促使人们思考。实践中,人们可以通过法律、规则、条文、法理等认识常理,但很难倾尽常理的现实存在。刑事审判是法律实践,属于社会存在,常理構成我们世界的一部分,常理的存在不在于人之外,是人的存在本身。然而,常理并没有在刑事审判中获得应有地位,人们把刑事审判归属于法律规范及法官,事实上刑事审判是人类社会之常理的表征形态。
常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马克思哲学观明确,任何事物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柏拉图说过:人不能同时踏入一条河中。也就是说,世间万物事瞬息变化的,试图找到永恒的、不变的事物是不符合自然规律的。老子的《道德经》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人世间没有千古不变的道理,今天的道理虽然在称谓上与昔日的道理相同,但是其内涵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从生产力角度看:生产力落后的古代,匮乏的物质生活资料,不能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条件,人类生存面临极大威胁。为了能够生存而与自然界斗争,在这种状况下生存并实现种族繁衍,是人类所遵循的基本常理。从生产关系角度看:社会是人群集体,是自己与他人的共同体,人的本质属性社会性体现在与他人的交往关系中。不同地区、不同地域的人们由于他们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文化传统、民族习性各异,人与人之间理念及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社会各方面存在着差异,这样不同地域就有不同的常理。所以司法裁判者的水平、能力、经验以及知识背景、生活经历、感情好恶、价值取向,均影响常理的运用。
法作为调整人们行为的规范,就刑事法律而言,它是规定何谓犯罪及如何进行处罚的规范,这一规范也是人们行为的基本准则,这一“准则”的形成来源于两个方面。其一,立法者把人们普遍认可的基本道理进行抽象的概括归纳总结,通过一定的形式上升为所有人必须遵守的普遍的准则,这一准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是良法;其二,少数立法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好恶,随意推测人民的意志,把自己的意志好恶强加给广大民众,并把这一意志通过一定程序上升为所有人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如果这些普遍的准则与人们所遵循的基本常理相悖逆,则存在是遵守法律还是遵守人们普遍认同的道理的两难选择。因此,审判实践中常理的准确运用依赖于基本法规范、依赖于法官将自己主动置于社会存在,并尽可能地用与社会共性相一致的常理进行判断。
四、刑事审判中常理的运用具有正当性
从犯罪产生角度看,刑事审判中运用常理具有正当性。常理是人类社会的客观现象。社会是矛盾的聚合体,有人类社会就有矛盾冲突,有冲突势必产生犯罪,在此种意义上讲犯罪是社会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换言之,犯罪是一种常态化的社会现象。虽然犯罪是固有的社会存在,但是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犯罪的产生、发展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意大利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认为,犯罪是社会中的正常现象,而不是病态的现象。犯罪是社会所固有的现象,犯罪产生于社会相互作用。迪尔凯姆强调犯罪是社会本身所固有的,犯罪在任何社会中都存在着,并且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这是因为消灭了犯罪的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社会组织的基本条件合乎逻辑地包含着犯罪[6]。台湾学者林山田认为,犯罪乃是自从有人类社会以来,即一直存在于人类社会,而且是无法完全禁绝的行为实施与社会现象[7]。在治理犯罪的行动中,最具体而有效的做法,就是制定刑事法,并建构刑事司法体系,使刑事司法机关依据刑事法的规定与其意旨,追诉与审判犯罪,以对于犯罪行为人施予刑事制裁与处遇。由此可见,刑事审判、对犯罪者的定罪量刑应当遵循常理。
从刑事法律规范角度看,刑事审判中运用常理刑事法律的内在要求。构建和谐社会也是刑法的终极目标。特别是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不公现象突出,贫富差距较为明显,多重社会矛盾交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冷漠、亲情友情观念淡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强化法律手段,是必要而迫切的,但是,如果一味强化法律作用,不考虑社会环境及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不审视行为人所处的环境及实施危害行为可能性的大小,是不能解决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也无法构建和谐社会。“法律不强人所难”,我国古代的亲亲相隐制度,大陆法系的期待可能性理念,及英美法系的可以宽恕的抗辩事由,从不同角度确认维护人性基础,并在一定程度确认了常理的理念。具体到刑事审判而言,常理在刑法体系中的位阶很难把握,它是刑法的灵魂又是标准,它在犯罪论体系中与犯罪构成关系如何也存在紧张关系。保护社会与保障人权是统一的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人权必然是有保障的社会;反过来能有效保障人权的社会,也必然符合社会常理。
从司法角度考虑,法官在定罪时可以依据常理去判案,而这些常理是在每一个法官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容易造成相同的案件出现不同的结果,同时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定上显得苍白无力。刑事审判中的法官判断、思维方式、直觉是一种认知机制,是个体在与社会环境互动中获得的。法官之所以能够理智地分析问题、运用概念、识别规则,能够有意识地解决问题,并能清楚地觉察和表达自己如何处理问题,是其长期职业习惯的影响下,形成的某种人格化心理和行为倾向。换言之,人的思维并非单纯的理性思维,而是理性思维与非理性思维的统一与融合。
结束语
总之,在刑事审判中,法律规范是理性认知的对象,司法程序是理性目标的手段。实现良法善治,常理应当贯穿于刑事审判法律体系之中,穿梭于法治运行的各环节。常理并非作为理论工具在解释法律中实现其价值,常理的思维、内在价值不仅关注权利义务合法性问题、法官裁判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程序问题,还检视刑事法律规则的运行行为及结果的可接受问题,是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问题。因此,刑事审判中常理的适用有利于促进司法文明。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42.
[2]陈忠林.常识,常理,常情:一种法治观与法学教育观[J].太平洋学报,2007(6):11-17.
[3]王夫之.张子正蒙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5:168.
[4]王斌.期待可能性之理论与实践研究[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10.
[5]考夫曼,哈斯默尔.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M].郑永年,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7.
[6]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88-89.
[7]林山田,林東茂.犯罪学[M].台湾:三民出版,2020:88-89.
作者簡介:查了源(2001— ),男,汉族,河南郏县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在读硕士。
研究方向:法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