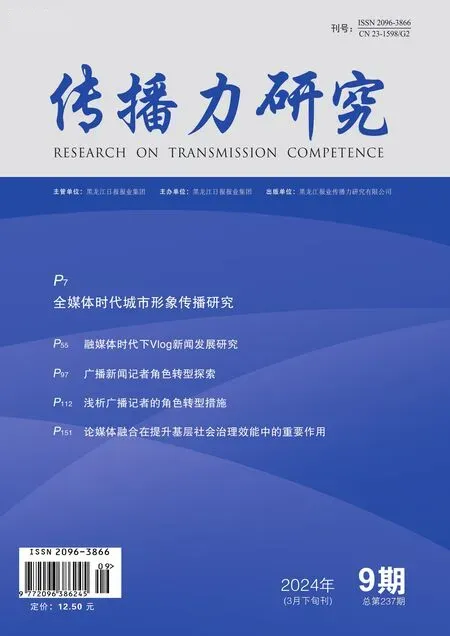新媒体语境下新闻业内部控制体系的困境与重构
◎王子晨
(兰州财经大学,甘肃 兰州 730000)
一、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控制研究作为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其主要研究目的是考察和分析各种制度和制度因素在大众传播活动中的作用。对于新闻从业者而言,只有建立健全的内部控制机制,才能使职业新闻工作者将被广泛接受的新闻价值准则作为选择的判断依据,并以公认的新闻伦理原则为基本的道德规范,以确保新闻制作的专业性和独立性,同时保障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以及新闻最根本的使命——为公众服务。
同时,随着新媒体设备的普及和新媒体技术的成熟,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而在新媒体语境下,诸如算法、大数据等新媒体技术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新闻生产,并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新闻业的内部控制体系,导致其面临着一系列的困境[1]。
综上所述,考虑到建构新闻业内部控制体系的意义,以及该体系正面临解构的事实,本文将结合案例对新闻业内部控制体系所面临的困境进行分析,并从“转向”的角度出发,尝试寻找重构这一体系的方法。
二、文献综述
(一)国内研究现状
郭庆光提出“考察传媒机构的内部制度对信息的生产、加工和传播活动的制约”属于控制研究的一部分。学者陆晔和潘忠党在他们的著作《成名的想象》中阐述了“新闻专业主义”,这一概念包括了一套界定媒体社会职能的信念、一系列规范新闻从业的职业道德准则、一种遵从政治和经济权力之外更高层面权威的精神以及一种以自觉的态度为公众提供服务的意识。以展江、彭桂兵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将包括中庸之道、绝对命令、功利主义、无知之幕在内的四种伦理理论加以综合运用,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效地分析争议性的媒体伦理议题。
以上学者的研究建构了新闻业内部控制体系的四个向度。而在进入新媒体时代后,学者刘丹凌在《困境中的重构:新媒体语境下新闻专业主义的转向》一文中提出,新媒介技术背景下的新型新闻传播撼动了传统意义上的新闻专业主义。另外,学者常江在他的著作《规范重组:数字媒体环境下的新闻伦理体系建构》中提出将社会责任、人本主义和美德原则作为数字新闻伦理体系的三大核心理念支柱。
总之,针对新媒体语境下内部控制体系面临的困境分析和重构探索,国内学者所广泛关注,并似乎已经达成了一个学术共识,那就是在新媒体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新闻业内部控制体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而针对各类新媒体技术的具体特征,探索建立可为全行业普遍遵守的新控制规范是重构这一体系的重要工作[2]。
(二)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同样有所研究,特别是进入算法和数字新闻时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探究算法技术的工具理性与人类记者的价值理性之间的冲突。例如Carlson 在“Automating judgment? Algorithmic judgment, news knowledge, and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一文中提出,固有的算法判断对以新闻专业主义为基础的人类记者的新闻判断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并进一步影响了新闻本身的质量和合法性。而在新闻伦理方面,国外学者呈现出乐观与悲观的两种不同态度:Aviles 在“Online newsrooms as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exploring digital journalists applied ethics”中指出,新闻从业人员对自身的美德有明确要求,不管新闻机构的类型有何差异,新闻从业者都应具备足够的能力,以应对当前各种伦理挑战,这并不会因机构类型而有本质性的变化。与之相反,Spinello 在“Morality and Law in Cyberspace”中指出,由于数字新闻机构存在盲目追求效率、技术崇拜的倾向,长期在这种环境下工作的新闻记者,其职业道德会逐渐淡漠以至消失,甚至他们本身的存在也会受到轻视。
综上,国外学者对于新媒体语境下新闻业内部的控制体系也进行了一定量的研究,并且能够发现,有相当部分的国外学者也对这一体系在数字新闻时代的建构表示了担忧。
三、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使用案例分析法、内容分析法进行研究,通过对新闻业真实案例的分析以及对大众传播内容的分析,来揭示新媒体语境下新闻业内部控制体系面临的困境,并提出重构角度。同时,由于笔者有媒体工作经验,因此本文将采用自我民族志的方法,从个人视角出发进行分析和研究。
四、新闻业内部控制体系面临的困境
(一)职业角色:记者异化为操作者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不断发展,媒体内容的呈现方式变得更多元化,除了文字、视频、音频之外,VR 等新技术也开始逐步为新闻呈现服务。比如,在2021 年全国两会期间,新华社推出了一款沉浸式虚拟现实(VR)新闻,名为《听会》。该新闻通过重新构建人民大会堂的新闻场景,使用户能够与大会现场的参与者一同参与全国两会的热门议题。这些新技术丰富了受众的接收体验。另外,随着新技术的入场,新闻业从业者的身份也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异化。
传统的新闻工作者只需要将精力和工作重心放在对生产内容质量的把控上。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对于记者的要求变得更加多元,不仅仅要求记者能够做到采编一体,而且还期待记者能够熟练运用新媒体技术以使内容的呈现方式变得更丰富[3]。在这种情形下,许多科班出身的记者不得不花费更多时间成本去学习新媒体技术,且在这个过程中,新闻工作人员的价值理性存在逐渐被工具理性取代的风险,产生“技术至上”的思维,从而降低对内容本身的要求。久而久之,记者就会异化为技术的操作者,这在数字新闻机构中体现得尤其显著。
(二)机构危机:从“科层式”到权力分散
学者鲁曙明和洪浚浩在《传播学》中指出,传统的新闻由层级分明的新闻机构制作,其商业模式基于广告和发行。这意味着媒体向公众提供必要的新闻信息,吸引公众的注意力,然后将这些注意力出售给广告主。然而,在新媒体环境下,新闻的生产和传播权力正在不断分散。在现实中,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参与新闻的生产,内容由公众提供,盈利方式也在进一步变化。以抖音为例,个人和组织制作内容为平台吸引关注,平台将这部分注意力售卖给广告主,并将所得利润与内容制作者进行分成。在这种情形下,公民内容生产更加重视对话、协作、平等而不是利润,是一种民主下放的运作模式[4]。显然,这种模式更贴合一般受众的需求,对专业新闻机构是一种巨大的冲击。
(三)专业主义:“守望者”退场,“混淆者”登场
新闻专业主义是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精神、职业原则和专业要求的总和,它要求媒体尽可能承担起环境“监视者”的责任。在这一价值要求下,新闻媒体应主动贯彻新闻的真实、客观等原则,为公众提供能够消除不确定性的信息。但进入新媒体时代,媒体必须想方设法维持自身“活跃度”,以营造一个永远新鲜的“前台”形象,而维持这一形象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在“后台”用满足受众多样化需求的信息填充版面,这就可能导致更多无意义、真实性不能保证的信息进入公众视野,进而混淆公众视听。
(四)道德规范:功利主义趋势责任旁落
功利主义由英国经济学家边沁创立,简单来说,它是一种“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处事经验。随着媒体发展进入新媒体时代,功利主义越来越多地影响到了媒体新闻的生产过程,造成了新闻业责任的旁落,致使新闻伦理中的理性向度遭到侵蚀,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新闻视角产生偏倚。近年来各种“门”事件层出不穷,它们的共有特点在于利用猎奇信息来博人眼球,而对于新闻媒体来说,它们都能够在短时间里为媒体吸引大量目光,这就导致在功利主义驱使下,部分媒体将更多注意力放在报道劣质新闻上,英国的《太阳报》就是其中的代表性媒体。
其次,虚假新闻泛滥。新媒体环境有一个隐性逻辑,那就是针对同一事件,第一个报道的媒体能够获得最高的关注度,这就会导致媒体为了更多利益而不断抢发新闻,忽视对新闻内容本身的审核,进而导致虚假新闻的泛滥。
最后,知识产权难以保证。脱胎于复制、粘贴功能的“洗稿”被更多商业媒体使用,这种方式更加便利,也更容易满足前文提到的“活跃度”要求,但是这种新闻生产方式不可避免地会侵犯原作者的知识产权。
五、重构新闻业内部控制体系
(一)身份重构:回归“参与者”的新闻职业观
约半个世纪前,Cohen 对记者进行了二分,即“中立者”和“参与者”,其中“中立者”主张客观报道新闻,尽可能中立地反映现实;“参与者”要求记者积极参与到社会运动中,推动社会进步。在当下的新媒体时代,由于信息爆炸和非理性化网络环境,面对非常态、触发性社会事件,不仅普通网民难以第一时间做出正确判断,甚至相关责任主体也难以及时有效地处理事件,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记者以“参与者”的身份入场,通过建设性新闻的实践,来引导各方对事件进行正确反映。例如《纽约时报》在疫情期间发布的报道《互动:全面了解冠状病毒的种族不平等》,指出黑人和拉丁裔冠状病毒病例的发生率更高,同时在数据收集的过程中,发现美国疾病监测系统缺乏透明度,并提起《信息自由法》诉讼迫使该机构发布信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公共卫生官员做出更适当的决定。
(二)行业转型:重塑权力的深度融合
在新媒体语境下,新闻业内部控制体系的重构应该以新闻行业的全面转型为出发点。实现这种转型的首要任务是充分利用多种媒体的优势力量,重建更具专业水准的组织结构,以实现职业权力的深度融合[5]。具体而言,这一过程包括以下方面。首先是“内容融合”,即将非专业的草根新闻信息与专业的媒体生产内容充分交叉,以创建更为多元化的新闻矩阵。其次是“形式融合”,即将文字、图片、视频等多媒体传播形式融合在一起,打破传统的单一报道模式,创造全景式新闻体验。最后是“媒介组织融合”,即建立各种媒体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专业媒体组织应该联合起来,构建多媒体工作模式,从独立运营转向联合运营,特别是在信息采集、生产和分发方面实现协同作业,以最大限度地降低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并最终提高新闻产品的质量。
(三)标准重建:构建更高要求的专业主义
在新媒体时代,新闻业不仅要求做公众的“守望者”,同时也不能成为产生妨碍作用的“混淆者”,这就要求新闻业需要构建要求更高的专业主义,即在真实客观的原则之上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内容高品质。专业新闻机构所生产的新闻应该是“高品质”的新闻,以其内容和形式的高要求来体现专业性,更好地满足受众的需求。二是互动性增强。强调增强新闻的交互性,一方面能够吸引受众,更好地传播内容,另一方面也能为受众提供交互平台,直接接收受众的反馈,以进一步对后续内容生产做出改进。三是新闻制作的全时化。根据杜俊飞教授的解释,“全时化”是比“及时”更为高层次的要求,它主要体现在快速发布、高频更新、有效重复等方面,也就是按照受众的现实需求和心理需求提升新闻产品的效率。
(四)伦理转向:事实与人文关怀并重
以“事实”和“人文关怀”的并重来治愈功利主义对新闻伦理产生的伤害,是新媒体语境下重构新闻业伦理的可行之道。一方面,事实能够体现新闻业理性和责任的向度;另一方面,新媒体环境本身就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环境,主体意识觉醒和能动性的解放都不断重复作为普通人价值的重要性[6]。就重建的角度来看,新闻业不仅需要在内部重新确立并践行专业理念、知识、技能和自律精神,还需要从外部接受一般公众的监督,并接受正确的新闻职业教育的引导。
六、结语
总而言之,在确定新闻业内部控制体系具有重要规范作用后,我们应该正视这一体系在不同层面遭受到的不同程度的冲击,致使新闻业构建内部体系面临着一系列困境。在这些困境的影响下,新媒体时代下的新闻业生产内容无法满足公众需求,并存在对公众产生一定程度的误导的风险,同时也对新闻从业人员自身的职业精神和原则造成了损害。因此,重构新闻业内部控制体系,在新媒体语境下具有现实急迫性。
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完成对这一体系的重构,应从职业角色、权力架构、专业主义、伦理规范四个向度入手,通过实践建设性新闻与媒体深度融合,从行业内部进行改革,并以更高标准的新闻专业主义和带有人文关怀的新闻伦理作为新闻业生产内容的规约。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新闻生产的专业与独立,贯彻新闻的真实与客观,回归新闻的基点——公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