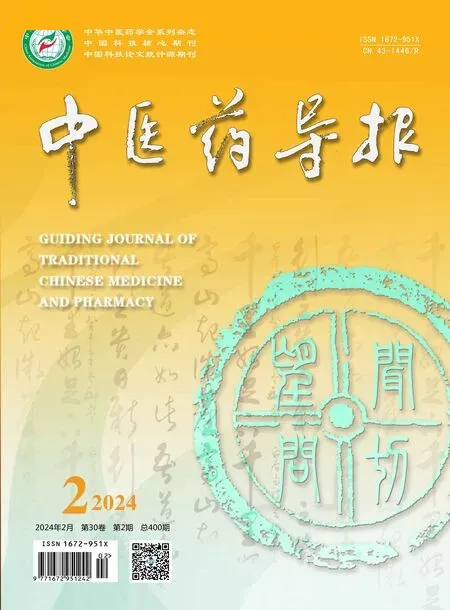邢佳从痰论治郁病经验*
屠芳源,邢 佳,孟得心,周光玮
(1.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北京 100020;2.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北京 100078)
郁病是由于七情过极,情志所伤,进而导致肝失疏泄,气机郁滞,脾失健运,心失所养,从而引起脏腑阴阳气血失调而形成的以心情抑郁、情绪低落、胁肋胀痛、易怒易哭或自觉咽中如有异物梗塞等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病证。中医学郁病的症状主要可见于抑郁症、焦虑症及双相情感障碍的抑郁状态之中。郁病作为现代临床常见病,可导致患者出现失眠、乏力、耳鸣、心悸、咽部不适、头晕等躯体症状[1]。有报告[2]称,我国抑郁症患者中约有60%出现躯体化症状。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社会心理功能,严重者甚至使患者丧失工作能力,出现社会适应不良甚至自伤自杀行为,这严重影响了人们的心身健康。
在临床治疗中,大多数医家注重从肝气郁滞的病机论治郁病,着重疏肝解郁、调畅气机。邢佳,副主任医师,师从首都名中医郭蓉娟教授,从事中医情志病的诊疗与研究十数年,对中医治疗郁病颇有心得。邢佳总结多年诊治郁病的临床实践经验,并翻阅大量古典医籍,发现郁病初起或单纯以气郁病机为主,然气郁日久则痰阻,而痰阻则气滞愈甚,恶性循环,坏证频生。而郁病多起病隐匿,随着病情迁延日久,病机也愈加复杂,躯体症状也更为多样,此时单以理气解郁治疗或收效甚微。笔者师从邢佳,曾数年跟随其左右学习中医诊治情志病相关思路。现为进一步研讨相关理论及思路,特将从痰论治郁病的理论依据及具体治法加以梳理,总结如下,以供各位同道参考交流。
1 痰与郁病的关系
许多古代医家均认识到痰与郁病关系匪浅,并曾有过关于痰在郁病病机中所起作用的论述。如朱丹溪曾在《丹溪心法·六郁》中将郁病分为气郁、血郁、痰郁、火郁、湿郁、食郁等“六郁”,首创“痰郁”之说,这表明朱丹溪已注意到痰在郁病病机中的重要作用。而在后世,朱丹溪的“痰郁”思想被进一步继承发展,产生了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见解,如虞抟在《医学正传·郁证》中论述了痰郁与其他五郁之间互为因果的关系:“热郁而成疾,痰郁而成癖,血郁而成癥,食郁而成痞满,此必然之理也。又气郁而湿滞,湿滞而成热,热郁而成痰,痰滞而血不行,血滞而食不消化,此六者皆相因而为病者也。”这表明痰郁可与其他五郁互相影响,合而为病。戴思恭进一步补充和发挥了朱丹溪的“六郁”学说,其在《金匮钩玄·六郁》中说:“郁结,结聚而不得发越也。当升者不得升,当降者不得降,当变化者不得变化也。此为传化失常,六郁之病见矣。”这表明戴思恭认为气机升降失常是导致郁滞不通的关键。同时,戴思恭对朱丹溪提出的“凡郁皆在中焦”做出了进一步阐明,认为六郁中最易出现中焦气机的郁滞,再加上饮食、痰饮、寒湿等的影响,故“中焦致郁多也”[3]。而亦有现代医家认为,饮食失调,痰湿饮食停滞于胃,会导致脾胃运化失调,气机不畅[4],影响气机升降而出现郁病[5]。痰饮停于脾胃而至中焦气机升降失常进而引发郁病的病机与朱丹溪“凡郁皆在中焦”的理论不谋而合,进一步佐证了痰饮在郁病发生发展中的重要推动作用。
许多明清医家亦对“郁痰”有详细的描述。如《症因脉治·卷二》言“郁痰即结痰,顽痰”,并指出郁痰之证的表现包括“胸满饱胀,九窍闭涩,懊憹烦闷,或咽中结核,睡卧不宁,或肠胃不爽,饮食有妨,或气逆不利,倚肩喘息”等,这与郁病患者的临床表现一致。《杂病源流犀烛·痰饮源流》云:“郁痰即火痰郁于心肺间,久则凝滞胸膈,稠粘难咯,多毛焦,咽干口燥,咳嗽喘促,色白如枯骨。”《证治汇补·痰症章》谓痰“留于胃脘,证见吞酸嘈杂,呕吐少食,噎膈嗳气,名曰郁痰”,“猝受惊恐,心虚停痰者,亦称郁痰,证见惊惕心跳,甚则欲厥等”。由以上论述可知,火与痰结,郁于心肺,或痰留胃脘,或心虚停痰均可形成郁痰之证,其内涵甚广,病位较多,涉及有形与无形之痰,临床症状复杂。治宜祛结痰以行滞气,如《杂病广要·痰涎》云:“病患原有痰积,其气因痰而结滞者,岂但理气而痰能自行耶。必先逐去痰结,则滞气自行,岂可专主一说。”其不仅提出了痰为先、气郁为后的理论,而且阐明了对于痰积导致气结之证,宜先祛痰结,痰结祛则滞气自行的道理。
痰由内生,阻滞气机,患者可出现身体沉重、疲乏无力、精力减退之症,这些症状与现代医学中抑郁症患者疲乏懒动、精力不足的躯体症状十分类似。反之,气郁亦可导致痰由内生,如《杂病广要·痰涎》所言“盖以人之七情郁结,气滞生涎,聚为痰饮”,清楚地论述了七情郁滞,气不行津,涎聚为痰饮的病机。由此可见,痰可致郁,郁亦可致痰,二者互相影响、共同致病的情况并不少见。如《古今名医汇粹·痰饮门》中所言:“七情之方,虽有多门,原其本标,半因痰病,盖亦有因病而生痰者也。”其指出痰与七情之病互为因果,既可因痰致郁,亦可因郁致痰。
对于由痰所致之郁,其总体治则不外理气化痰开郁,但当其病机涉及不同脏腑及兼证时,亦应注意分证论治。如《景岳全书·痰饮》云:“郁痰有虚实,郁兼怒者,宜抑肝邪;郁兼忧者,宜培肝肺。”其指明在郁痰兼怒、兼忧这两种情况下宜采用的治法治则,宜偏重的不同脏腑病机,表明当不同脏腑与痰及郁病病机相关时,应辨清病机,分证论治。有现代关于抑郁症的数据挖掘研究表明,抑郁症的22种中医证候中,有7种证候涉及痰浊的病机[6]。现代医家如王亚丽认识到痰的病机对郁病的重要影响,对于痰郁者常用陈皮、竹茹,半夏、石菖蒲等药对[7]。杨小娟等[8]也意识到痰与郁互生互因,“痰”不只是病理产物,也是致郁之因,痰浊不解则生郁。
2 各脏腑与痰及郁病的关系
痰是人体津液失于运化的病理产物。《诸病源候论·痰饮候》认为,“痰饮者,由气脉闭塞,津液不通,水饮气停在胸腑,结而成痰”,“诸痰者,此由血脉壅塞,饮水积聚而不消散,故成痰也”。可见三焦气化不利,水饮凝结于胸腑或血脉壅塞,饮水停积不散均可导致痰的产生。人体津液运化过程涉及诸多脏腑,如脾、肾、肺、三焦等。由此可见,不仅肝气郁滞会致津行不畅生痰,诸多脏腑功能失常均会导致痰的产生,从而诱发或加重郁病病情。
2.1 肝与风痰及郁病的关系 肝为风木之脏,若肝风内动,与痰相合,则结为风痰。《泰定养生主论·痰证》云:“风痰者,因感风而发,或因风热拂郁而然也。此皆素抱痰疾者,因风、寒、气、热、味而喘咯咳唾,非别有此五种之痰。”其指出素有痰者若感风可结为风痰。《医学入门·内伤》曰:“动于肝,多眩晕头风,眼目瞤动昏涩,耳轮瘙痒,胁肋胀痛,左瘫右痪,麻木蜷跛奇证,名曰风痰。”其描述了风痰会产生眼目昏涩、胁肋胀痛等躯体化症状。《杂病广要·痰涎》云:“夫痰之源不一……有因风而生者……风痰成瘫痪,大风眩乱,暗风闷乱。”其阐明了风痰可出现肢体瘫痪及目眩等症状。《医宗必读·痰饮》云:“在肝经者,名曰风痰,脉弦面青,四肢满闷,便溺秘涩,时有躁怒,其痰青而多泡。”这表明风痰之证可能出现的临床表现既包括四肢满闷等躯体症状,又包括时有躁怒等情绪症状,这提示风痰内蕴可能与患者情绪变化密切相关,可能是引发郁病的病机之一。
反之,气郁日久亦可化生痰涎。如虞抟《医学正传·郁证》云:“气郁而湿滞,湿滞而成热,热郁而成痰,痰滞而血不行。”即指出气郁可逐步发展为痰滞[9]。又如《张氏医通·郁》所言“郁则津液不行而积为痰涎”,阐明了气机郁滞,津行不畅,最终留而为痰的病机。肝在疏泄气机、调畅情志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肝失条达,气机失于调畅,则气郁为患。而体内津液的运行需赖气以推动,若气郁日久,推动无力,津液易停滞为患,留而为痰饮。综上,内生风痰可致郁,郁亦可反过来加剧痰的产生,二者相互促进,相因为病。
2.2 脾与湿痰、食痰、酒痰及郁病的关系 脾在志为思,思虑过极则伤脾,而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而气血为情志活动的物质基础,脾气伤则脾失健运,这一方面导致了情志活动的物质基础——气血的生化不足,使得人体应对外界不良情志刺激的自我调节能力下降;另一方面导致了津液运化无力,停聚为痰,留而为患。正如张从正在《儒门事亲·饮当去水温补转剧论》中所说:“脾主思,久思而不已则脾结,故亦为留饮。”《景岳全书·杂证谟·非风》亦云:“脾气愈虚,则全不能化,而水液尽为痰也。”《医学入门·卷五》云:“生于脾,多四肢倦怠,或腹痛、肿胀、泄泻,名曰湿痰。”《景岳全书·杂证谟·痰饮》中说:“盖脾主湿,湿动则为痰。”《杂病源流犀烛·痰饮源流》云:“在脾曰湿痰,其色黄,滑而易出,多倦怠,软弱喜卧。”以上医家的论述表明了在脾之痰的性质为湿痰,且具有色黄质滑的特点,同时湿痰证患者会有倦怠喜卧等表现。这与抑郁症患者常常出现的懒动、乏力等表现类似。有研究[10]表明,肝郁脾虚证是抑郁症患者中常见的临床证型。王永炎院士认为气虚湿阻是抑郁症的病机之一,认为抑郁症患者的低动力症状符合气郁湿滞证的症状表现,并注重运用燥湿醒脾、化湿行气之法调畅情志[11]。而代君等[12]医家也认为,继肝气郁结之后发生的脾气亏虚、痰湿为患是郁病发生的重要因素,并注重以健脾化痰法治疗郁病。这表明脾的相关病机在痰饮的产生及郁病的发生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除情志过极损伤脾气,导致痰饮产生、积聚外,饮食不当及过劳过逸亦可伤脾而致痰饮内生。如饮食不节,暴饮暴食,或饮食不洁,食用腐败变质食物,或过食生冷甜腻,损伤脾胃,运化功能失常,湿浊便易蓄积生痰[13]。若恣食肥甘厚味或甜腻之物,酿生痰浊,或饮酒过量,湿热内蕴,均可直接导致体内痰湿的产生与蓄积。正如《景岳全书·杂证谟·痰饮》所言:“痰涎之化,本由水谷,使脾强胃健,如少壮者流,则随食随化,皆成血气,焉的留而为痰。”叶天士在《临症指南医案·湿》中提到:“湿从内生,必其人膏粱酒醴过度,或嗜饮茶汤太多,或食生冷瓜果及甜腻之物。”这些记录进一步说明了痰饮的产生与脾胃功能是否强健以及饮食是否适度有重要关系,若饮食不当,酿生痰浊,阻滞气机,则会增加郁病发生风险。有研究表明,快餐饮食模式和肉类饮食模式会增加抑郁症状的发生风险[14],以过多摄入甜食和过低摄入乳制品为特征的不健康饮食模式与焦虑、压力和抑郁显著相关[15],这些现代研究与中医所讲的过食肥甘厚味、甜腻之品酿生痰浊,阻滞气机而生郁病的观点不谋而合,也进一步佐证了饮食失宜会增加郁病发生风险。而古代医籍亦有许多饮食生痰的相关记载,如《证治汇补·痰症》曰:“生于脾,多腹痛膨胀,或二便不通,名曰清痰,或四肢倦怠,或久泻积垢,或淋浊带淫,名曰湿痰,若挟食积痰血,内成窠囊癖块,外为痞满坚硬,又名食痰。”其又言:“若因饮酒,干呕嗳气,腹痛作泻,名曰酒痰。”这表明因脾所生之痰除了湿痰外,还有食痰、酒痰等,且其病机与饮食失当或饮酒伤脾密切相关。古代医籍也曾提到,形体肥胖之人体内较之形体正常之人更易蓄积痰湿。如《仁斋直指方论·火湿分治论》曾指出:“肥人气虚生寒,寒生湿,湿生痰……故肥人多寒湿。”清代医家陈士铎的《石室秘录·肥治法》中也曾说道:“肥人多痰,乃气虚也。虚则气不能营运,故痰生之。”这些中医古籍的记录都说明了形体肥胖之人更易生痰。同时,有现代研究表明,心理疾病患者常有肥胖等营养问题[16],且肥胖会增加罹患抑郁症的风险[17]。这些研究表明肥胖之人更易罹患郁病,这可能与肥胖之人体内痰湿过多有关。
2.3 肺与气痰及郁病的关系 肺为娇脏,易为邪侵,且肺喜润恶燥,若人体外感燥邪则易伤肺,日久炼液为痰。而肺易为痰邪所侵,《证治汇补·痰症》云“肺为贮痰之器”,可见体内痰邪易停于肺,肺中停痰易与七情郁结之气相结,形成气痰之证。《证治汇补·痰症》云:“七情过多,痰滞咽喉,咯之不出,咽之不下,胸胁痞满,名曰气痰。”其不仅明确地提出了气痰的概念,并且指出气痰是由过极的七情与痰相合而形成的。其他医籍亦常可见气痰的相关描述,如《医学入门·内伤》曰:“七情痰滞咽膈,多胸胁痞满,名曰气痰。”其又曰:“七情郁成,咯出不出,咽之不下,形如破絮,或如梅核。”其论述了痰与郁结之气相搏形成气痰之证的机理,以及气痰之证可出现胸胁痞满等症状表现。
古代医家早就认识到肺与人体的情志有密切的关系。一方面,肺为气之主,肺在协调气机升降、使人体气机运行通畅中起着重要作用[18],正如《王氏医案释注·卷八》所言:“治节不行,一身之气皆失其顺降之机。”另一方面,肺在志为悲忧,悲忧由肺精肺气所化生,正如《素问·举痛论篇》所言“悲则气消”,过度忧伤哀愁则肺气受损[19],肺气受损则导致机体应对外界不良情志刺激的能力下降,更易产生悲忧的情志变化;若痰饮留肺,阻滞肺气,肺气不利,甚或受损,则可导致人体对于外界不良情绪刺激的耐受力下降,使人更易产生悲伤忧愁的情志体验,从而引起或者加重郁病患者的病情。由此可见,痰邪停肺所导致的肺气不利、肺气受损与人体情志变化密切相关。
2.4 肾与寒痰及郁病的关系 肾阳为人体一身阳气之本,且肾主水,在水液的正常代谢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若肾阳虚衰,不能襄助脾阳,脾阳亦虚,脾肾阳虚,失于温煦,水津不化,内生痰饮,阻滞经络气机,气行不畅,从而诱发郁病发生或加重郁病患者的病情。《杂病源流犀烛·痰饮源流》曰:“在肾曰寒痰,其色有黑点,吐出多稀,多小便急痛,足寒逆,心恐怖,脉必沉。”以上论述表明在肾之痰名为寒痰,结合临床经验可知,寒痰证患者可出现畏寒、疲乏等阳虚表现,其色黑质稀,且寒痰证患者会出现心恐怖等症状。临床上老年抑郁患者多肾阳亏虚,其情感体验不以悲思为重、反以忧恐为主,多与寒痰证郁病患者的症状相合。
2.5 心与惊痰及郁病的关系 《证治汇补·痰症》言:“迷于心为心痛惊悸,怔忡恍惚,梦寐奇怪,妄言见祟,癫狂痫喑,名曰惊痰。”《杂病广要·痰涎》曰:“夫痰之源不一……有因惊而生者……其为病也,惊痰则成心包痛,颠疾……妇人于惊痰最多,盖因产后交接,月事方行,其惊因虚而入,结成块者,为惊痰,必有一块在腹,发则如身孕,转动跳跃,痛不可忍。”其阐明了痰迷于心者名为惊痰,惊痰证患者会出现惊悸恍惚、梦寐奇怪甚至癫狂等神志症状,这与临床上双心疾病患者的症状相似,这些古籍论述进一步佐证了痰饮内停可导致患者情志变化。明代医家王肯堂亦认为,心血亏虚、心神失养,则痰易客之,可发为惊悸,治宜豁痰定惊[20]。
3 从痰治郁病的分证论治
古语有云:“百病多由痰作祟。”痰是人体津液代谢障碍所导致的病理产物,与脾之运化、肝之疏泄、肺之通调、肾之气化等多个脏腑的功能均密切相关。对于痰致郁病的治疗,可根据所涉及脏腑的病机不同分证论治。如:若肝失疏泄,气郁痰停,则疏肝解郁,行气化痰;若脾失健运,痰湿内生,则健脾益气,化痰除湿;若痰停于肺,与气相搏,则补益肺气,化痰理气;等等。
3.1 从肝之风痰治郁 郁病初起多起于肝气郁结,现代医家治疗郁病时也多注重疏肝理气,常应用柴胡类方,但邢佳治以疏肝时不以柴胡类方为主,而习惯以升麻、茵陈蒿、川芎等药物升提中气,疏导气机。邢佳认为,郁病初起虽多起于肝气郁滞,然临床上所见的郁病患者多有迁延不愈、病程日久者,此时其病机或已发生变化,并非单纯的肝气郁结证,故单纯疏肝往往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疗效,此时对于使用柴胡类方疗效不佳者应注重转换思路,不可拘于常法,一味疏肝,反致肝气不足、肝血耗伤。
临床上郁病症状往往呈现出多样化、异质化的特点,而郁病症状表现的多样化恰与肝善行而数变的特点相合,肝风内动、与痰相合、结为风痰可令郁病患者的症状表现更加复杂多样,加重郁病患者的病情。肝为刚脏,体阴而用阳,主疏泄气机,故邢佳认为,从肝治郁应以柔肝养肝为主。一方面,应用酸敛之药以柔肝,如五味子、白芍、当归等;另一方面,滋水涵木以养肝,肾为肝之母,故应用生地黄、山萸肉等药滋肾阴以养肝阴。同时,脾为气血生化之源,健脾亦可达成养肝之效,故邢佳认为,亦应重视健脾,处方中往往兼顾治脾,具体用药可参见下文。
3.2 从脾之湿痰治郁 脾位于中焦而主运化,其生理功能对于水液疏布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金元大家朱丹溪重视从脾论治痰郁,《丹溪心法·痰》指出治痰当“实脾土,燥脾湿,是治其本”[21]。国医大师张学文认为,思虑不解,脾虚生痰,痰阻气滞,可导致郁证[22]。而对于因脾生痰进而致郁的相关病机,邢佳则认为:一方面,若脾失健运则运化无力、痰湿内生;另一方面,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弱则气血不充,而气血是人体情志活动的物质基础,气血弱则人体应对外界刺激的自我调节能力下降。故治宜健脾化痰,益气补血。
在健脾的遣方用药上,邢佳的经验为:一方面,重用黄芪以补脾气,黄芪用量根据患者情况逐渐加量,用量多在30~120 g,再辅以白术、党参、山药、茯苓等健脾益气,令脾气强健,运化恢复,气血生化有源,从而令人体情志活动的物质基础充足,面对外界刺激时情志调节能力增强;另一方面,重用半夏、藿香、石菖蒲等药物以化中焦湿浊,这对于痰湿困阻中焦而出现脘腹痞闷、少食作呕等消化道躯体症状的郁病患者往往有较好的疗效。另外,对于过食肥甘滋腻之味的患者,应嘱其注意清淡饮食,适量运动,例如配合八段锦、五禽戏等中医养生功法以助气机运行,进而帮助中焦湿浊得化。
3.3 从肺之气痰治郁 肺主通调水道,通调不利则水湿内停,久之炼液为痰,与七情郁滞之气相结而为气痰。对于此种肺气不利与痰相结之气痰,邢佳认为不可仅以祛痰药荡涤积痰,亦应兼以振奋肺气,助其恢复正常宣肃功能,肺宣肃有力,则水道得通,滞气得行,生痰之机自绝。对于肺中气痰的治疗,邢佳用药往往偏于轻扬。对于久郁咽中之痰,以紫苏子、紫苏梗合用以降气化痰;若痰郁膻中,痹阻胸膈,证见胸脘满闷者,以紫苏梗、荷梗、桔梗同用以理气宽中,宣肺利咽;若痰郁日久化热,可酌加竹茹、芦根等以清热化痰,养阴生津。若仍不奏效者,则常选用更加轻扬宣痹之品,如桑叶、枇杷叶、射干等,以轻宣肺中气痰,取“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之意。此外,虽主要目的为化肺中之伏痰,但同时需注意,痰留日久易化热伤阴,化痰则阴伤益甚,滋阴又易助生痰,故在化痰之初宜兼顾护阴液,在化肺中气痰之初即宜少佐甘寒之麦冬、玉竹护阴液以防痰热伤阴之变证,且兼能辅助化痰清心火,对郁证兼有心肺郁热者较为适宜。
3.4 从肾之寒痰治郁 肾蕴人体一身之元阳且主水,肾阳的温煦推动作用对于维持人体正常的水液代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景岳全书·杂证谟·痰饮》所言:“肾主水,水泛亦为痰。”刘乔[23]认识到,治痰不可拘于化痰一法,可温肾化气,则不消痰而痰自消。邢佳在临证过程中,对于存在肾阳虚病机的患者,注重温补肾阳,常用药物包括炮附子、肉桂等。附子归心肾脾经,可峻补元阳,引火归元;肉桂归肾脾心肝经,为辛甘大热之品,可补肾助阳。对于老年肾之阴阳均虚衰较甚的患者,则在温肾阳基础上伍滋肾阴之品,如在温补肾阳药基础上加上熟地黄、天冬、石斛等。熟地黄入肝肾经,可滋补肝肾之阴血,为滋养肾阴精之佳品;天冬、石斛亦入肾经,伍之可增强全方滋补肾阴之功。因阴阳互根,故阴阳兼顾,令阴阳互长,以寄疗效更著,如此肾阳得温,推动得力,水津得布,则寒痰不生,郁病患者因寒痰郁阻出现的畏寒、疲乏、忧恐等症状得以缓解。
3.5 从心之惊痰治郁 对于痰迷心窍而出现惊悸恍惚、梦寐奇怪,甚至癫狂等神志症状的郁病患者,邢佳常配伍天南星、半夏、橘红等药物。方中天南星燥湿化痰,橘红下气消痰、半夏亦可燥湿化痰,两者均可辅助天南星以增豁痰之力,寓合导痰汤以燥湿豁痰、开窍醒神之意。若水饮较重、惊痰结聚成块者,适量予京大戟以泻水逐饮,白芥子豁痰利气,寓“妙应丸”之意,正如《杂病源流犀烛·痰饮源流》所记载:“惊痰,因惊痰结成块在胸腹,发则跳动,痛不可忍,或成癫痫,在妇人多有此证,宜妙应丸。”如此心窍之痰得豁,心神不为痰扰,其正常神志机能得复,惊悸、怔忡、心神恍惚甚或癫狂之症自然不复为扰。
4 验案举隅
患者,女,55岁,2021年10月12日初诊。主诉:持续性情绪低落半年余。患者自诉半年前与配偶吵架后,渐渐出现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心情烦躁、夜寐欠佳,且伴有食欲减退、体重不减反增,以及胸闷气短、乏力懒言等表现。患者曾于肝胆脾胃科、亚健康科等多处就诊,服用中药治疗,自觉疗效不显。刻下症见:情绪低落,胸闷脘痞,乏力,健忘,纳差,失眠,二便调。舌质红,苔黄腻,脉弦滑数,右关滑甚。查看患者其他科室就诊经历,处方以疏肝理气之柴胡类方为主,患者服后虽自觉胁肋胀痛有所好转,然仍见心烦易怒、夜寐难安、头目昏沉、胸满痞闷等症。追问病史得知,患者于绝经前后出现不寐,伴有体质量增加较明显,至今已4年余,平素喜食甜腻之品。西医诊断:抑郁状态。中医诊断:郁病(痰热扰神证)。治法:清热化痰,解郁除烦。方用黄连温胆汤加减,处方:黄连10 g,竹茹15 g,枳实10 g,姜半夏15 g,炒陈皮10 g,炙甘草8 g,生姜10 g,茯苓10 g,石菖蒲15 g,郁金15 g,白术15 g,贯叶金丝桃15 g,黄芪6 g。14剂,1剂/d,水煎服,早晚两次温服。嘱患者清淡饮食,规律作息,适量户外运动。
2诊:2021年10月26日,患者诉情绪低落、睡眠不安等症状有所好转,但仍有胸膈闷堵、头目眩晕。舌淡红,苔薄黄腻,脉缓而滑。在初诊处方基础上加入厚朴12 g,紫苏子30 g,黄芪用量加至30 g。14剂,1剂/d,水煎服,早晚两次温服。余注意事项同前。
3诊:2021年11月9日,患者诉目前睡眠尚可,偶有气短乏力、口干口渴以及白日困倦,自觉胸膈闷堵、头目眩晕等症状改善不明显。舌红少苔,脉细而寸尺俱弱。在2诊处方基础上去厚朴、紫苏子,加升麻10 g,麦冬12 g,玉竹12 g,黄芪用量加至60 g。14剂,1剂/d,水煎服,早晚两次温服。余注意事项同前。
后患者每次复诊,根据其当时的病情状况酌情加减药味及调整药量,共门诊治疗半年余,治疗期间患者较为配合,按时服药,并及时复诊反馈。2022年6月末次就诊:患者自觉情绪状态及睡眠有明显改善,食欲及体质量逐渐恢复正常,气短乏力、胸膈满闷等较之前有较大缓解。嘱患者注意规律作息、坚持运动。6个月后电话随访,患者诉遇事偶有紧张失眠,平时情绪状态尚可,亦尚无其余不适。
按语:初诊时患者诉吵架动怒后逐渐出现情绪低落、头目眩晕、胸膈满闷等症状,四诊合参并结合病史,考虑患者素有痰湿内蕴,郁久化热,复因怒气伤肝,痰随气逆,痹阻胸膈,故见胸满痞闷;痰热上蒙清窍,故见头目昏沉。予黄连温胆汤加减以清化痰热,解郁除烦。2周后复诊,患者虽情绪低落、睡眠不安有所好转,但仍见胸膈满闷、头目眩晕等痰湿困阻之症。结合患者舌脉及症状,推断患者中焦郁堵之痰热已减轻,然痰湿之邪难以顿除,故仍见胸膈满闷、头目眩晕,予前方加厚朴、紫苏子以化痰湿、除痹阻,寓温胆汤合半夏厚朴汤之意。3诊时患者自觉胸膈闷堵、头目眩晕改善不明显。考虑患者因痰滞胸膈,故闷堵较重,而前方宣通上焦肺气之力不足,遂调整处方,以苏子化痰,并加入疏通宣透之豆豉、枇杷叶、射干以增加宣肺之力,同时加入苏梗、荷梗、桔梗等药味以疏通膻中气机。且患者偶见气短乏力、易于疲倦,加之舌红少苔、脉细,气阴两伤之症已现,故宜重用黄芪以补中焦之气,并加入升麻,配合黄芪升提脾气,以推动肺气升提,寓“培土生金”之意;兼加麦冬、玉竹等滋阴津以顾护阴液。宣通化痰与补气滋阴同用,标本兼顾,则郁痰得清,气阴得养,病情自然逐渐向愈。
5 结 语
现如今,郁病发病率较高,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心身健康。为了给郁病患者提供更为优质的医疗,更为合适的方药,深入挖掘郁病错综复杂的病机是必要的。邢佳总结自己治疗郁病的临床经验,并广泛查阅中医古籍中与郁病相关的论述后,认为虽然肝气郁滞可能是郁病病机的主要方面,但痰也是郁病的关键病机之一,应予以重视。当然,痰证临床表现较为多样,痰证未必皆致郁,但“怪病多由痰作祟”,郁病中涉及痰的病机者为数不少,故特将历代医籍中从痰论治郁病的相关内容加以总结,以期为郁病的临床治疗提供新思路。应指出的是,郁病中痰的相关病机亦有细微差别,不可一概而论,因此在面对不同病机时,应分别采取相应的治疗策略,如:肝风内动,风痰上扰者,宜息风化痰;湿痰困脾,中焦郁阻者,宜健脾除痰;气痰停肺,痰滞咽喉者,宜宣肺涤痰。四诊合参,辨明病机,辨证精准,方可选取最为合宜的治法,对症下药,以期契合病情,效如桴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