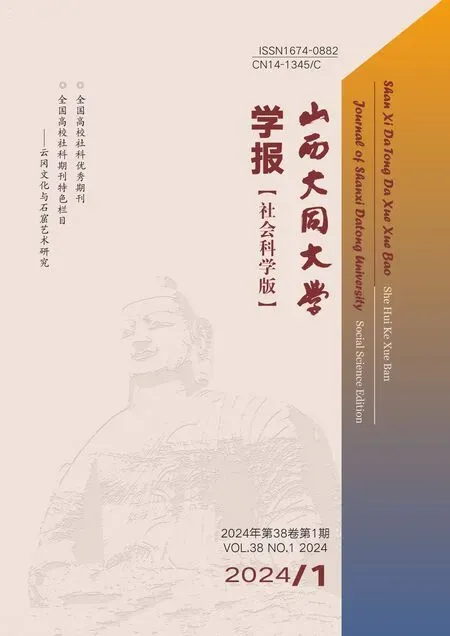西方现代人格理想的追寻与构建
——从哈姆雷特到浮士德
刘志强,鲍俊琴
(1.山西大同大学外国语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2.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西方文学和文化的历史,是人类不断认识自我,发展自我的历史。人作为主体是一个历史范畴,也是一个文化哲学范畴。在人类的蒙昧时代,原始人类对于自然(客体)和自身(主体)是缺乏区分的。随着认识水平的提高,到古希腊罗马时代,人类开始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区分,有了主体、客体的概念。俄狄浦斯的命运悲剧显示了人类认识自我的艰难以及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思想统治一切,人作为匍匐于上帝脚下的奴仆,迷途的羔羊,在教会的解释中并不具备认识自我的能力。随着文艺复兴时代的到来,这一时期西方的文学艺术极大繁荣,其文化硕果显示了尽管人类没有全知全能的天性,不过一旦从某种压抑状态中解放出来,便可以释放出超乎寻常的自信和创造力。文艺复兴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促进了人的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
作为时代的感知者和探索者,从莎士比亚笔下哈姆雷特的困惑迷惘到十八世纪歌德笔下走向社会人生的青年威廉·迈斯特对理想人性、自我价值的追寻,再到浮士德走出书斋,对走向广阔人生生命体验的拓展,这些人物形象标记了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西方人认识自我,发展自我的心灵的嬗变过程。当年轻的哈姆雷特尚处于古老的封建制度的阴影下并由此而感到窒息时,年轻的威廉·迈斯特则已迫不及待地去拥抱新的世界和新的自我了,浮士德则彻底地实现了现代人在个体价值意义上的积极自由。从哈姆雷特,威廉·迈斯特,浮士德的人生探索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到西方文学中人性发展和人格构建行进的基本轨迹。
一、精神的独舞者——哈姆雷特的迷惘
莎士比亚的笔下描绘了在文艺复兴时代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生动鲜明,组成了一条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引人注目的人物画廊。“人的发现”的时代在莎士比亚的戏剧舞台上被表现得淋漓尽致。第一次从中世纪基督教禁欲主义的束缚下解脱出来的西方人在神的面前重新获得了属于自身的价值和尊严,人性解放成为时代的呼声。这是人的主体性开始确立的时期,从神学的、上帝的权威那里,人重新以理性、智慧、情感确立了人的自身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确认了属于人自身的荣耀,就如哈姆雷特在剧中那段对于人的认知的著名论断,骄傲地宣称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1](P469)从基督教的原罪观念中认为人不过是“迷途的羔羊”,等待被拯救到公开赞美人自身所具有的一切优点,重新确立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价值,这种观念转变无疑意味着人的主体意识自我觉知的开始。
但就如所有的研究者认为的那样,文艺复兴作为一个灵肉解放的时代,在解放了人类丰富的情感、创造力与才华的同时,也释放了人的欲望与野心。莎士比亚悲剧所反映的即文艺复兴后期人文主义理想者的悲剧,所以哈姆雷特一走上舞台,他所面对的就是他所处时代的弊病与难题。哈姆雷特在威登堡大学接受的是先进的人文主义教育,当他回到丹麦,艾尔西诺王宫古老的风吹过,哈姆雷特就感到了不适应,宗法责任和社会责任加之自身的不幸,他成为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人。哈姆雷特是个性解放的时代发展至私欲泛滥的社会现实的见证者,剖析者与思考者。他的发问一开始,哲学的身份就一览无余,人物的标志性一览无余。在复仇的过程中,哈姆雷特对人、人性和人生意义重新进行了认知和思考,出于对人性的失望让他发出了“可是在我看来,这一个泥土塑成的生命算得了什么,人类不能使我发生兴趣。”[1](P469)“像我这样的家伙匍匐于天地之间,有什么用处呢?”[1](P481)的痛苦呼号,但直到戏剧结束,他的思考依然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在戏剧中哈姆雷特思考这一行为并没有彻底完成,他在剧中提出了问题本身,却缺乏在现实中行之有效地去验证的能力,他生活的领域囿于宫廷权谋争斗,这也让他无法在更广阔的社会领域中完成对更有意义和价值的人生的探索和实验,他的忧郁彷徨使他悬置于哲学时空,却难以在现实中解决问题。莎士比亚笔下哈姆雷特这一形象的存在,是一个时代的上帝之眼,在新旧时代价值转型时期,他洞察了时代的弊病,即人性的堕落与道德秩序的失范,对此有着超越同时代人的更为清醒敏锐的判断,并且有强烈责任意识和拯救意识,但作为一个没有更多实践经验和社会阅历的年轻王子,他总是在精神意识的层面进行哲学思辨,并且只是局限于与自我的对话,从而缺失了现实层面的实践意义,成为一个人的精神独舞。莎士比亚通过哈姆雷特的忧郁,困惑与复仇行动的延宕,描绘了一个主体意识刚刚觉醒但尚未得到发展的古代社会的传统人格形象。文艺复兴以来,人的主体意识已经觉醒,但古老的封建专制和宗教意识依然主导着人的精神,人对在实践中应用自己的理性力量依然心存疑虑,哈姆雷特无法克服时代和自身的局限性,这使他成为舞台上对人性发出永恒质疑的哲学身份象征。
二、审美主体的追寻者——威廉·迈斯特的人生舞台
歌德的长篇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后简称《学习时代》)和《漫游时代》被认为“在许多方面都近似于诗剧《浮士德》,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它们像是母体同时孕育生长的孪生姐妹。”[2](P1)不过《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创作要早于《浮士德》,但在创作时间跨度上,这部小说也长达五十多年。威廉·迈斯特是歌德教育小说《学习时代》和《漫游时代》主人公,他青年时代在人生经历和生活探索上很近似于后来的浮士德生活经历的展开,“但他活动的范围仅相当于浮士德的‘小世界’”。[2](P2)威廉出生于德国的商人家庭,他从小就表现出对戏剧艺术和表演的狂热兴趣,一次外出时遇到一个流浪剧团,就加入他们开始了漫游生活。威廉为人热情真诚,敏感聪慧,他从一开始就怀着提高自己和完善自己的美好欲望,希望能献身于戏剧事业并复兴德国的民族戏剧。在流浪的生活中他感受到了艺术给他带来的激情与愉悦,但同样也经历了天性与环境冲突之下内心的不幸与痛苦,他后来成为一家剧院的导演和演员。威廉在长期对戏剧艺术的追求中,在广阔的社会人生中经受了磨炼,完成了“学业”。
研究者认为,《学习时代》整个内容可归纳为“逃避庸俗”,体现了摆脱蒙昧状态的新人进一步完善自己的要求。学习实际上就是追求一种和谐完善的人格:追求理智与热情的调和,美和伦理的调和,爱和道德的调和,天性和修养的调和,内在冲动与外在法则的调和,最终达到一个“美的心灵”和一个“完整的人”相结合的境界。威廉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天性中的热情真诚使他具有一种审美的品格,并义无反顾地追求超越于平庸的艺术生活,但他并非没有缺陷,感情的冲动使他陷入了少年情事的纷争中,他的离家出走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责任的逃避。在加入流浪剧团后,威廉在戏剧艺术上显现的才华使他脱颖而出,他初次尝试到了成功和喜悦,但流浪剧团演员构成和表演的随意性与他追求完美的性格在不久之后就发生了矛盾,这让威廉陷入了痛苦。后来他成为另一家剧院的导演和演员之后,积累了经验,随着长期的舞台历练和社会阅历的增长,他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对艺术人生的追求。在情性方面,他的不告而别固然令家人不悦,但父亲在见到经历了社会教育脱胎换骨的威廉之后,对他的成长变化很是欣慰。他不仅与家人达成了和解,也真诚地认识到了年少的冲动与错误,并承担了责任,“彻底丢掉了身上的庸俗市民气,完全变成了一个新人”。[2](P8)
《学习时代》中威廉离开家庭,走向17 世纪末18世纪初德国的广大社会,但始终是在艺术团体中学习成长,接受教育,实现艺术梦想。也许是意识到戏剧艺术和审美教育的局限性,歌德在《漫游时代》中,让威廉接触到了有改良进步思想的社会团体,触碰到了相对严肃的社会问题,但小说却以威廉收获美好的爱情为结局,这显示歌德对改变当时德国落后社会现实方式的思考还没有完成,因而人物身上也带了某种开放性,预示着威廉的学习、漫游将永远在路上。在小说一开始,威廉的离家出走,可以说是威廉主动追求艺术理想的一种选择,但其后在漫游学习的剧团生活中,他的经历大多带有偶然性和随意性,并不显示出自我导向的行动意愿,在个体生命体验拓展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威廉·迈斯特通过游历也可以称得上是完成了对戏剧艺术和审美人生探索的扫罗。巧合的是,在《学习时代》的第四部第十二、十五章,第五部第四、五、九、十一章,歌德借排演莎剧的威廉之口对《哈姆雷特》发表了异乎寻常的独到、系统、详尽和深刻的见解,威廉有着和哈姆雷特同样敏感的心灵和诗性的品格,对人性的美和善同样有着超越性的审美追求,威廉走出了平庸的市民家庭,在艺术的实践中认识自己,认识与自己所生存的世界的关系,增长了聪明才智,丰富了阅历。或许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威廉代替哈姆雷特走出了宫廷,在行动和实践中实现了对审美的艺术人生的追求。
三、现代主体人格理想的实现者——浮士德的冒险
18 世纪的启蒙运动赋予民众以崭新的时代理念,强烈的个体意识空前强化,社会以理性的批判精神和理想追求精神动员民众,进而产生改造社会,推动历史前进的强大思想动力和精神能量。
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形象是当时启蒙运动的独特产物,是启蒙思想影响下的西方先进知识分子由传统走向现代,对理想王国的追求中自我实现的诗意性表达,是形象化的现代主体人格理想的实践者。在精神气质上,浮士德是个“现代进步的头号文化英雄”,[3](P106)“现代性意味着价值主体由神向人的转移。”[4](P163)在传统的信仰时代,上帝是一切造物存在的意义的源泉,也是个体生命意义的终极归宿,人在现世的生活毫无价值。在歌德的《浮士德》中,尽管在序曲中有上帝和魔鬼的打赌的情节,但上帝已经由传统经院神学中全知全能的上帝变为启蒙学者眼中创世第一因的存在,之后更是撒手不管,对梅菲斯特引导浮士德的要求,上帝只说:“只要他在世间活下去,我不阻止,听你安排。”[5](P38)这意味着浮士德从上帝手中获得了解放,个体行为的超验根基不再成为个体行动的束缚理由,拥有了自我实现的可能,个人生命体验和过程本身成为第一性。
作为现代主体的浮士德在情感结构和价值偏好具有鲜明的现代色彩。他有一个不安的灵魂,渴望有所作为,并放弃了对灵魂得救的渴望而重视追求此岸价值。在翻译《新约·约翰福音时》,因不满路德“太初有言”的译法,而将其译为“太初有为”。[5](P42)而后走出书斋开始探险生活的浮士德寻求对生命的每一种沉浸式体验,但他的追求不仅仅停留在感官享受的物质层面,而是在经验、强度、感受生活、行动、创造性等个体生命的深度、广度和可能性的体验层面,实现了以赛亚.伯林所说的“积极自由”。[6](P179)积极自由作为一个现代性概念,解释了现代主体的心理特征,强调个体的独立动能,即个体是自己的主人,是自主的和自我导向的行为主体,通过控制外在世界,使之符合自身的愿望,从而达到自我导向的目的。伯林认为积极自由既是对个人自由的扩展,也是个体价值的实现;但积极自由也会把个体的意志通过政治权力强行扩展到每一个个体,无视他人的权利,最终走向个体价值实现的反面。浮士德有着明确的自我意识和行动的愿望,他在知识、爱情、政治生活,艺术审美和社会理想五个阶段的极致行动体验中追求永恒。他的生命体验在每个层次都得以充分展开,尽管在每一个阶段他都会遭受挫折和失败,他也有过短暂的消沉与颓丧,但始终都表现出明确的自我意愿和导向,怀着雄心壮志不断自我更新,能够迅速恢复,并保持了对未竟之领域旺盛的探索热情。从诗剧年老绝望的学者开始到热恋的青年,从参政的政治家到古典美的追求者,最后成为雄心勃勃的封建领主,浮士德的身份不断变化,是其现世生命经验展开并一一体验的过程,也是其现代主体性得以充分展示的过程。浮士德身上的积极自由是18 世纪的西方时代精神影响的结果,歌德借浮士德充分肯定了启蒙时期个体现世体验的价值。启蒙时代以理性精神清算了封建制度遗留下来的各种痼疾,以更为符合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理想社会的蓝图和自由精神照亮了未来社会的路径,从而在理想人格的形塑方面也展示了人在精神发展上的开放性和潜能,而浮士德无疑就是这种人格理想的实现者。
不过,“浮士德悲剧”也带来现代性视野中发展的反思。浮士德并非纯洁的道德理想主义者,他追求行动和体验,却往往导致无度与失控。他追求爱情,最终却导致格雷琴一家和孩子的死亡,他在封建宫廷发行纸币,却引发了人们对金钱和享乐的疯狂追求,他填海造田却造成了奴役与死亡,浮士德的个人理想实践携带着的破坏性无疑又与启蒙时代个体价值的肯定精神相悖。诗剧接近尾声“事业悲剧”的阶段,浮士德作为一个永不满足的英雄却为魔鬼所欺骗,不禁心满意足发出“你真美啊,请停留一下”[5](P536)的感叹,立刻倒地死去。这一反讽性的结局体现了歌德对浮士德这一形象所代表的“发展神话”的一种思考。浮士德身上永不满足,奋发有为的精神气质代表了18世纪西方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的新兴资产阶级不断进取,求得自我发展的进步精神,歌德通过对浮士德这一现代冒险主体心理层面的展开,充分肯定了个体生命价值实现的意义。不过浮士德及其对立面魔鬼在每一阶段寻求积极自由拓展其生命经验的领域时,总会以毁灭旧的秩序或暴力的形式显现,其发展所带来的破坏力是提倡渐进改良思想的歌德不得不警惕的,浮士德的失败无疑是歌德对现代主体发展欲望的一种警觉与反思。
浮士德要求发展的主体性实践是在其愿望和意志的主导下开始的,与魔鬼梅菲斯特交换得来的黑暗力量使他在每一个领域的初始生命体验中充满了成就感,自由意志的充分实现令他充满了志得意满,这也进一步激发了他的征服欲,他甚至扬言要征服漫无目的的大海,他迷醉于应用自己统治劳动力的新权力,在普遍福利的名义下,在实现社会理想的同时以近乎疯狂和野蛮的方式组织强迫性劳动,而他身上以实现积极自由为开始的自我主导的主体性追求,最终不免演变成为梅菲斯特口中“自恋性的权力意志的古老故事”。[3](P88)
文学是人学,文学发展的过程也是人类逐渐发现自我、认识自我的过程。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通过哈姆雷特这一人物形象将西方文学对人性自我认识和人性复杂性的思考开掘到了新的高度。18 世纪启蒙时期的歌德作为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伟大思想家与文学家,他所关注的目标和中心点也始终是人,包括人的激情、本性,以及人与现实生活和人与世界的关系。歌德早期塑造的威廉·迈斯特形象代表了作者早年对和谐完善的理想人格的追求,与他早年尊重个性自由,崇尚激情的思想较为一致,而作为寄寓歌德自身生命活力的浮士德形象,在实现积极自由拓展个体生命领域的同时展示了强烈的自我导向和自我控制,使得“现代历险主体的心理层面得以细致展现”。[7](P178)浮士德的生命探险之旅就是歌德对理想人格实践历程的艺术化总结,同时也不乏对自己所处的风云变幻的时代思考,这种思考一方面超越了国家、民族和时代的局限性,既表达了启蒙时期主体性人格实现个体价值的积极精神,另一方面又以敏锐、前瞻性的视角察觉到浮士德所代表的那个现代的无限发展的自我,释放的是人性中不可控制的欲望,同时也可能是巨大的不受控制的和常常是有害的权力。诗剧结尾,歌德尽管意识到浮士德道德上的缺陷,但他还是坚持了让浮士德最终获得拯救的肯定性陈述,这说明他肯定了浮士德身上不断追求发展进步和自我完善的人性理想和精神能量,至于留下的疑问和道德考量则留给时间和未来来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