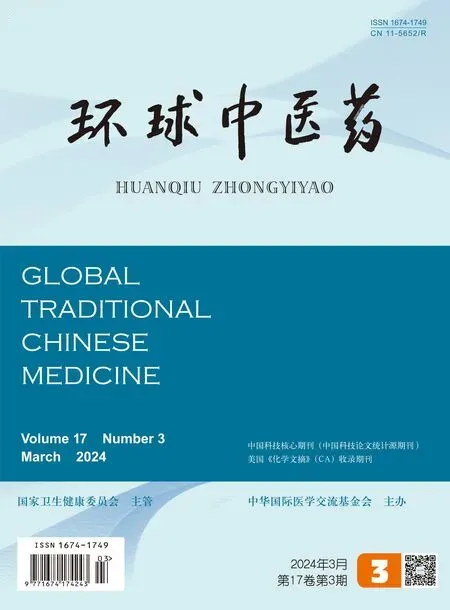《血证论》从脏腑辨治淋证探析
王萌萌 董艳丽 迟敬 孙雪英 王超众
淋证是以小便频数,淋沥刺痛,欲出未尽,小腹拘急,或痛引腰腹为主症的病证[1]。现代医学中的尿路感染、前列腺炎、尿路结石、尿道综合征等疾病具有上述表现者多从淋证进行中医辨治[2]。中医多认为淋证的病机为湿热蕴结下焦,肾与膀胱气化不利。根据淋证的不同特殊表现,将其分为热淋、石淋、气淋、血淋、膏淋、劳淋等进行辨证,按照淋证的类别、虚实、寒热遣方用药。
唐宗海是清代著名医家,代表医籍为《血证论》,书中“阴阳水火气血”理论[3]1,是其治疗血证的基本观点,同样运用该理论阐释了诸多内科疾病,其中对淋证辨证施治有其独特的方法。《血证论·淋浊》曰“淋者小便短数,淋沥不通之谓也”[3]124,并在医籍中提出了“分别脏腑施治”的淋证辨证角度[3]124,对不同脏腑的病理机制、治法方药进行了专门的论述。从脏腑辨治在指导现代中医治疗淋证上具有其特色,值得研究探讨。
1 淋证辨治溯源
先秦两汉时期,医家对淋证的认识主要体现在《黄帝内经》和《伤寒杂病论》为代表的医籍之中,《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中记载“小便黄赤,甚则淋”[4]70,指出淋证为小便淋沥不畅之病证。《素问·气厥论篇》认为淋证的病机为膀胱热[5]。《金匮要略·五脏风寒积聚病脉证并治》称淋证为“淋秘”,曰“热在下焦者,则尿血,亦令淋秘不通”[6],指出热在下焦为其病机,在《金匮要略·消渴小便不利淋病脉证并治》中对该病症状加以描述:“淋之为病,小便如粟状,小腹弦急,痛引脐中。”[6]
两晋南北朝时期,《中藏经》首次从淋证的临床表现不同分类辨证,将淋分为冷、热、气、劳、膏、砂、虚、实八种[7]。其辨证要点分别是,冷淋为“小便数而色白如泔也”,热淋为“小便涩而色赤如血也”,气淋为“脐腹满闷,小便不通利而痛也”,劳淋为“小便淋漓不绝,如水之滴漏而不断绝也”,砂淋为“小便中下如砂石之类,有大者如皂子,或赤或白,色泽不定”,虚淋为“谓肾与膀胱俱虚,而精滑梦泄,小便不禁者也”,实淋为“经络闭涩,水道不利,而茎痛腿酸者也”[8]。
隋唐时期,诸多医家延续了《中藏经》中按照淋证症状特点分类的方法,如《诸病源候论·淋病诸侯》中巢元方亦从淋证临床特点辨证,分别为石、劳、气、血、膏、寒、热七种,并统称为“诸淋”,将病机“诸淋者,由肾虚而膀胱湿热故也”归为肾虚为本,膀胱湿热为标。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和王焘的《外台秘要》均将淋证分为石、气、膏、劳、热五淋。
两宋时期,《济生方》中严用和大致继承《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的淋证分类,将淋证分为气、石、血、膏、劳五种。《济生方》中对淋证分类的不同在于血淋与热淋的有无,辨证的角度并无差异。
明代,《景岳全书·淋浊》中张介宾从寒热虚实辨治,并提出“凡热者宜清,湿者宜利,下陷者宜升提,虚者宜补,阳气不固者宜温补命门”淋证的治疗原则[9]。《医学入门·外感·火类》中李梴从湿热蕴结辨证为:“淋皆属热,间有冷者,外因当风取凉冒暑,湿热郁滞胞内,痿痹神不应用……湿热下流膀胱。”[10]《医宗必读·淋浊遗精门》中李中梓从脾肾亏虚辨证为:“劳淋,有脾劳肾劳之分,多思多虑,负重远行,应酬纷扰,劳于脾也。”[11]
清代,唐宗海《血证论》辨治淋证中,继承了《内经》和《伤寒论》中淋证多为湿热蕴结的病机,亦采纳张介宾淋证从寒热虚实辨证论治的方法。在此基础上,从肺、心与小肠、脾、肝、肾与膀胱分别辨别寒热虚实以施治,提出与前代医家治疗淋证的不同角度,丰富了古代淋证的辨治方法。
2 首辨脏腑定病位
脏腑具有其各自的生理功能与病理变化,淋证的病变脏腑不同,也会出现不同的证候表现。《血证论》认为淋证在于肺,心与小肠、脾、肝、肾与膀胱,这些脏腑发生病变,生理功能出现异常。
2.1 肺失制节
唐宗海提出“肺主制节,下调水道,肺痿则津液不流,气不得下,而制节不达于州都,是以小便不利”[3]124,这里指肺的生理功能异常,导致小便不利。在《中医基础理论》中“肺主治节”是指肺对气、血、津液具有治理与调节作用[12],其中的治节之意应与《素问·刺法论篇》记载的“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4]89中的治节语义相同。
笔者认为《血证论》中的“制节”是重点强调肺主通调水道的功能,“肺之气下输膀胱,转运大肠,通调津液,而主制节”[3]124是唐宗海进一步说明肺气的宣发和肃降对人体内水液的输布和排泄具有疏通和调节作用。通过肺气的肃降,水液下输于肾,再通过肾的气化作用,生成尿液,经膀胱排出体外。笔者考虑肺气失于宣发肃降,导致肺主行水功能失常,因此除小便不利外,还应有咳嗽、气喘的症状。
2.2 心火下移小肠
《血证论·淋浊》认为“心遗热于小肠,不能泌别清浊”,是指心火下移小肠,小肠失于泌别清浊导致淋证。关于小肠的生理功能记载于《类经·藏象类》中:“小肠居胃之下,受盛胃中水谷而分清浊,水液由此而渗入前,糟粕由此而归于后,脾气化而上升,小肠化而下降,故曰化物出焉。”[13]可以看出小肠清浊不分、水液吸收障碍、尿的来源减少则见小便短少等症。
笔者认为心与小肠的联系在于经脉络属,查阅《经络考》中心手少阴之脉的循行为“起于心中,出属心系,下膈络小肠”[14],心与小肠经脉相互络属,构成表里关系。再结合《苍生司命》中论述“如心有火,炎灼日久必遗热于小肠,则成小便淋秘”[15],心火亢盛,通过经脉下移于小肠,使小肠热盛,小肠泌别清浊功能失常,出现“小便赤短淋沥”尿少、尿赤涩刺痛、尿血等淋证表现[16],该理论与唐宗海从心与小肠辨淋证的观点一致。
2.3 脾土不化
《素问·至真要大论篇》曰“诸湿肿满,皆属于脾”[4]83,说明若脾失健运,则运化水液作用减退,水液的吸收、输布障碍,必然导致水液停滞,若留滞的水液弥漫体内则生水湿之邪,导致“小水不利”。这与唐宗海《血证论·淋浊》中记载“脾土不化,亦能壅湿,使小水不利”,脾失健运,水湿壅滞的观点相同。
笔者认为脾土不化应更多表现为腹满、便溏、厌食等症,而脾虚内伤又外感病邪,内外相引易为淋证,如《湿热论》记载:“太阴内伤,湿饮停聚,客邪再至,内外相引,故病湿热”[17],这里的“太阴内伤”与《血证论》中“脾土不化”的主要病变为脾的气机阻滞,从所用方剂五苓散可以看出唐宗海亦遵循“气化则湿亦化”的治疗原则[18]。该方剂具有利水渗湿,温阳化气之功效。以方测证,脾土不化导致的淋证病机为水湿内盛,膀胱气化不利。
2.4 肝失疏泄
唐宗海提出“前阴属肝,肝火怒动,茎中不利,甚则割痛,或兼血淋”[1]124,肝火旺盛,影响肝主疏泄功能,疏泄不及,肝气郁结,气滞血瘀,导致经络循行部位气滞血瘀,出现茎中不利、割痛,肝经火旺,灼伤脉络,迫血妄行,表现为血淋。这与《格致余论》中论述肝主疏泄功能密切相关,“司疏泄者,肝也”[19]。肝能够疏通调畅全身气机,促进精血津液的运行,肝主疏泄功能正常,则气机调畅,津血运行畅通无阻。
笔者考虑肝与前阴关系密切亦在于经脉络属,《灵枢·经脉》记载肝足厥阴之脉循行部位经过前阴“肝足厥阴之脉,起于大指丛毛之际,上循足跗上廉……循股阴,入毛中,环阴器,抵小腹”[20]91,肝经循行部位包括前阴和小腹,《灵枢·海论》亦云“夫十二经脉者,内属于脏腑,外络于肢节”[20]211,说明经络具有联络脏腑肢节、沟通表里上下的功能。《素问·大奇论篇》载:“肝壅,两胠满……不得小便。”[4]45因经脉络属,故肝与淋证的关系密切。
2.5 肾与膀胱气化不利
从肾与膀胱论治淋证多辨肾与膀胱气化不利,水液代谢障碍,如“肾为水脏,膀胱为水腑”[3]124。肾主水,膀胱贮藏、排泄尿液。《素问·逆调论篇》曰:“肾者水脏,主津液。”[4]34肾脏通过蒸腾气化作用,升清降浊,水液之清者上升,浊者为尿液下输膀胱。《素问·灵兰秘典论篇》谓“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4]13,膀胱的贮尿、排尿功能主要依赖肾的气化作用,肾气旺盛,固摄有权,气化正常,则膀胱开阖有度,若肾气不固,气化失司,则膀胱不利,出现“小便不化”的症状。
隋代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亦将淋证的病变部位归属于肾与膀胱,提出“诸淋者,由肾虚而膀胱热故也”,虽在脏腑功能异常导致淋证的核心论述相同,但将石淋、气淋、膏淋、劳淋、血淋、寒淋都归为一脏一腑,笔者认为相较之下《血证论》中从多脏腑辨淋证眼界更为开阔。
3 次以“阴阳水火气血”理论辨病性
中医基础理论认为,脏腑的病理变化可以由阴阳平衡失调来诠释。《血证论》中唐宗海以“阴阳水火气血”理论,在辨淋证所在脏腑后,进一步阐述其所在脏腑的病理机制。《血证论》中“阴阳水火气血”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人之一身,不外阴阳,而阴阳二字,即是水火,水火二字,即是气血,水即化气,火即化血”[3]1,是指人的生命活动在于阴阳消长、运动变化,水火是阴阳的具体表现,而水火气血相互资生。人的阴阳水火气血运行化生异常会导致疾病,若水与气化生失常,导致水气不行;火化太过,不能生血,或迫血妄行;血病可兼水病,水病亦可累血[21]。这些病理变化可以导致肺失制节,肾失蒸化,心肝火旺,脾土不化,膀胱气化不利,而出现小便淋沥不畅,形成淋证。唐宗海认为水火气血与五脏的关系密切,将两者概括为:“血生于心火而下藏于肝,气生于肾水而上主于肺,其间运上下者,脾也。”可见心、肝、肾、肺、脾在水火气血中的作用,在生理上互相协调,在病理上相互影响。
3.1 肺脾肾虚,气阴不足
从肺论治淋证多辨肺津亏虚,肺失制节,如“血家病淋,多是肺痿”[3]124。《血证论·咳血》中论述肺痿病机为“肺中阴液不足,被火克刑,则为肺痿”[3]124,认为水阴不足,津液枯竭不能濡养肺阴,出现津枯肺燥[23]。从脾论治淋证多辨脾气虚,脾失健运,水湿壅滞,如“脾土不化,亦能壅湿,使小水不利”[3]124。从肾论治淋证多辨肾阳不足,或肾阴亏虚。
《血证论》曰:“脐下者,肾与膀胱,水所归宿之地也。此水不自化为气,又赖鼻间吸入天阳,从肺管引心火,下入于脐之下,蒸其水使化为气。”[3]1说明膀胱中的水液需要肾气的蒸腾才能完成气化过程,气化水流于下,水道畅通而为溺。从原文可以看出,除肾的蒸腾作用,肺的肃降和心阳的温煦作用亦使水转化为气。津血同源,血病而水津虚损,肺无水以济,肺燥津亏而至痿,肺气不利,肺失宣肃;水津虚损亦损肾阴,水源枯竭,小便不化,阴损及阳,肾阳虚,肾失气化[22]。
3.2 心肝火旺,血虚失养
从肝论治淋证多辨肝经火旺,肝失疏泄,气血津液运行失常,如“前阴属肝,肝火怒动,茎中不利,甚则割痛,或兼血淋”[3]124。《血证论·阴阳水火气血》中论述心阴虚病机为:“如或血虚……心失所养,火旺而益伤血,是血病即火病矣”[1]1,认为阴血虚,血不养心,阴血不足,心阳偏亢,阴阳失调,出现心火亢盛。
唐宗海认为火为血制,血病可以导致火病,如血虚可以出现心肝阴虚火旺,“血虚,则肝失所藏,木旺而愈动火,心失所养,火旺而益伤血”[3]3。肝主藏血,肝血虚而致肝阴虚,肝体阴而用阳,肝失阴血濡养,故肝火上炎;“火为阳而生血之阴,即赖阴血以养火,故火不上炎而血液下注,内藏于肝,寄居血海,由冲、任、带三脉行达周身,以温养肢体”[3]2。心主血,心火在阴血的涵养下才能平而不亢,血虚心失所养,故心火旺盛[15]。心火下移小肠,肝火怒动,肝经湿热则小便短赤淋漓。
3.3 膀胱湿热,蕴结下焦
《血证论》提出:“汗出过多则伤血,下后亡津液则伤血,热结膀胱则下血,是水病而累血也。”[3]3津液虚损会导致血虚,湿热蕴结膀胱会出现尿血。血病亦可兼水病,“若病血而又累及于水,则上而喘咳,外而肿热,下而淋浊,均不能免”[3]124。由此笔者认为,虽唐宗海与历代医家均从膀胱湿热论淋证,而唐宗海所论深度不同。众医家从热结膀胱,邪热破血妄行,而出现血淋;唐宗海从血淋继续讨论,血淋可导致血病,即血虚,津血同源,阴血不足,不能濡养肺阴,肺燥津亏而喘咳,阴虚生内热,脾失濡养运化失常则肿胀,故外而热肿,阴虚内热又会导致气化不利,加重膀胱湿热,从而出现上中下三焦俱病。说明膀胱湿热会导致血家病淋不易治疗。水病累血,病机复杂,在治疗上宜治血理水,调和阴阳,左右逢源[24]。
4 补虚泄实分脏腑
依据《血证论》中辨淋证的不同病变脏腑,从津枯肺燥、心火热下移小肠、脾土不化、肝经湿热、肾阴亏虚、肾阳不足、膀胱气化不利辨证施治,根据不同脏腑的寒热虚实的病理性质,补虚泄实,平衡阴阳。从脏腑辨治不仅为中药性味功效的运用提供依据,更使中药的归经有的放矢。
4.1 甘寒润肺清火热
针对肺燥津枯出现的淋证,唐宗海治以滋阴润肺,利水通淋,具体用药“宜生地、百合、天花粉、知母、杏仁、桑白皮、滑石、桔梗、猪苓、阿胶、甘草梢治之”[3]124,生地、知母味甘性寒,清热泻火,滋阴润燥;百合、天花粉味甘性微寒,归肺经,养阴润肺;杏仁、桔梗味苦,归肺经,宣降肺气;阿胶味甘性平,归肺经,补血止血,滋阴润肺;桑白皮、滑石、猪苓、甘草梢性味甘寒,归肺经、膀胱经,利水渗湿、利尿通淋。用甘寒之品清肺热、养肺阴,味苦之品肃降肺气,甘淡之品利水渗湿,使肺热得清,津液得生,小便得通。
4.2 苦寒清心养阴津
心阳偏亢,心火下移小肠导致淋证,治以滋阴清心、通利小便,具体方药为“导赤饮加炒栀子、车前子、黄连、白芍、灯芯”[3]124。古籍中载有“导赤饮”的方书中组成略有差异,笔者认为《思济堂方书》所用方药更为贴切,书中该方剂应用范围、用法用量记录为:“导赤饮,治心经有热,小便短赤者;生地三钱,赤苓、木通、麦冬各二钱,去心;引灯心五分,用长流水煎服。”[25]导赤饮用于治疗心经有热,小便短赤者,有清心火、利小便之功。生地、麦冬味甘性寒,归心经,清心养阴生津;炒栀子、黄芩味苦性寒,归心经,清热泻火,增强清心泻火之功效;木通味苦性寒,灯芯草味甘淡性微寒,两药均归心与小肠经,既能清除心火又能利尿通淋;茯苓、车前子味甘,甘淡渗湿,利尿通淋;白芍味苦酸,属补血药之类,有养血之功,补益阴血,以制心阳偏亢。以甘寒之品养心阴,苦寒之品清心热,苦酸之品养阴血,使阴阳平衡,心火得清,小便通利。
4.3 甘淡健脾利水湿
在从脾治疗淋证方面,唐宗海认为在辨病位后应该辨湿邪病性,寒湿之邪“五苓散治之”;湿热之邪予五苓散去桂枝,加茵陈蒿、防己、黄柏、炒栀子。《血证论·阴阳水火气血》曰:“且水邪不去则水阴亦不能生,故五苓散去水邪。”[3]1五苓散药物组成猪苓、茯苓、泽泻、白术、桂枝。方中泽泻味甘淡,归肾、膀胱经,功能利水渗湿;猪苓、茯苓味甘淡性平,健脾利湿,增强泽泻利水渗湿之功;白术味甘、苦性温,益气健脾,运化水湿;依据《素问·灵兰秘典论篇》所载:“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4]13膀胱的气化依赖于阳气蒸腾,桂枝味辛性温,温阳化气利水。唐宗海治疗寒湿之邪运用甘温之品,通阳化气。唐宗海亦继承叶天士“通阳不在温,而在利小便”的学术思想,对于“湿中挟热者”清热燥湿利小便,其中五苓散去辛温助热之桂枝,加入味苦性寒之茵陈、栀子清热利湿;黄柏清热燥湿,防己利水祛湿。以苦寒之品清除湿热,甘淡之品通利小便。
4.4 甘温养肝辨虚实
在从肝治疗淋证方面,与从脾辨治相同,唐宗海在辨病位后应该辨淋证虚实病性,辨病机为实证者宜龙胆泻肝汤加肉苁蓉,辨病机为虚证者予地黄汤加肉苁蓉、黄柏、车前子治之,兼有血淋者加地榆、蒲黄。对于实证治以清利肝经实火,方中龙胆草大苦大寒,归肝经,泻肝经实火;黄芩、栀子苦寒泻火;泽泻、木通、车前子利水渗湿,导热下行;当归、生地滋养肝血;柴胡味苦微寒,归肝经,疏肝解郁,调畅肝气,引诸药归肝经;甘草调和诸药。以苦寒之品,清肝经实热。在治疗肝阴虚火旺的淋证虚证中,地黄汤出自《圣济总录》,具有养血止血之功效,方中方中当归味甘性温,归肝经,养血补血,为方中主药;生地、黄芩凉血止血;地榆、侧柏叶清热凉血、收涩止血;艾叶温经止血,伏龙肝温中收涩止血;蒲黄化瘀止血;生姜调和药性。以甘温之品补益肝血,平衡阴阳。唐宗海不论虚证实证,在治疗上都给予肉苁蓉,温补肾阳,重视肾阳的蒸腾气化作用;强调清除湿热,龙胆泻肝汤在泻肝胆实火的同时具有清利肝经湿热的作用,因地黄汤无清利湿热之功,故加黄柏、车前。
4.5 苦甘益肾化气津
唐宗海认为不论肾阴不足或是肾阳亏虚都可以导致肾的蒸腾气化失常,在辨淋证病位在肾与膀胱后再辨阴阳,在治疗上:“肾中阴虚,水源枯竭,则小便不化,知柏地黄汤少加肉桂以反佐之。若是阳虚不能化水者,金匮肾气丸治之。”[3]124知柏地黄汤的药物组成是六味地黄丸加知母、黄柏,金匮肾气丸是六味地黄丸加桂枝、附子。知柏地黄汤中知母、黄柏,味苦性寒,归肾经,清泻肾火,滋补肾阴;金匮肾气丸中肉桂、附子辛甘、大热,归肾经,温补肾阳。六味地黄丸中六味中药组成三补三泻,肝脾肾三阴并补,偏补肾阴。唐宗海在补肾阴时,以苦寒之品滋阴泻火,反佐少量肉桂阳中求阴;补肾阳时,用大辛大热之品补火助阳。
5 结语
从《黄帝内经》和《伤寒杂病论》对淋证病名和病机的初步认识,到《中藏经》中根据淋证特征表现进行分类,在之后的隋唐、两宋时期都在沿用《中藏经》中对淋证的分类方法,在具体分类数量和种类上略有区别外,辨证论治的角度并无太大差异。明代《景岳全书》《医宗必读》从寒热虚实辨治,提出热者宜清,虚者宜补的治疗原则。清代唐宗海继承张景岳淋证治则的基础上,在《血证论》中进一步提出“分别上中下,而又各区脏腑以施治,尤为精细”。根据不同脏腑的病理变化辨证施治,并且给予具体的方药。淋证在实际的临床过程中往往反复发作、病情迁延,所涉及的不仅仅为一脏一腑,病机亦多虚实错杂,在纷繁的病情中抽丝剥茧方能观其全貌。然而这并非首诊初治便能把握,就需要医者根据每一次的病证变换视角遣方用药,《血证论》从脏腑辨治淋证作为新的辨证思路为临床提供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