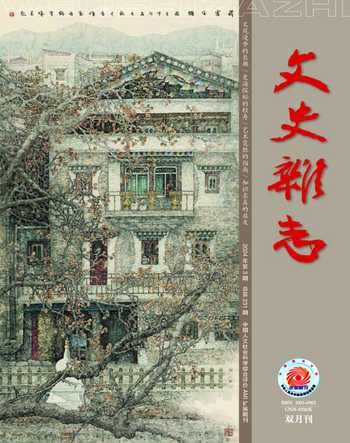三星堆出土的珍贵文物埋藏年代辨析
钱玉趾


摘 要:三星堆遗址珍贵文物的埋藏年代,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学者共同攻关,充分利用历史文献的记载、考古发现的成果、青铜冶炼与加工技术的特点、碳14测年数据与树轮校正的结果等综合研究确定。文物的埋藏年代应晚于商末。
关键词:三星堆;埋藏年代;碳14测年数据;春秋时期
學术界一般认为,新津宝墩文化是成都平原上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三星堆文化是由宝墩文化发展而来。本文主要讨论三星堆遗址埋藏坑的年代,那些珍贵文物是什么年代埋下的?
一、三星堆遗址1986年发掘的两个埋藏坑的年代
宋治民《蜀文化》依据《三星堆祭祀坑》介绍了1986年发掘的两个埋藏坑的年代以及不同学者的分析。[1]现列表介绍如下:
对于三星堆遗址两个埋藏坑年代的分析与认定,以上学者的差别就很大,现在倾向于商末的较多。
二、三星堆学术会对于年代的争论
赵殿增《三星堆考古发现与巴蜀文化史研究》说:三星堆遗址的文化遗存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西周初期,共分为四期:第一期约当中原龙山文化中晚期,属新石器时代遗存,测定年代在距今4740—4070年左右;第二期相当于夏代及商代前期,测定年代在距今4070—3600年左右;第三期相当于商代中晚期,测定年代大约在距今3600—3200年左右;第四期约在商末周初,测定年代距今3100—2875±80年。[2]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金沙:再现辉煌的古蜀王都》说:“三星堆文化约当夏商时期,绝对年代约公元前1700年—前1150年……金沙村遗址的文化堆积和年代约当商代时期至春秋,以商代晚期至西周的遗存最丰富。”[3](未见C14测年数据)
孙华、苏荣誉合著的《神秘的王国》一书说:“三星堆器物坑的碳十四测量标本目前经过测试的数据有两个,均出自三星堆1号器物坑。”送交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检测,“是在发掘后的十多年”,一个测年数据“为前3500+295”(树轮校正为前1520—前1470年),另一数据“为前3430+90”(树轮校正为前1880—前1430年)。孙华说:“可以肯定地说,三星堆器物坑的年代不会晚到商代末期,两个坑的器物都是在殷墟中期偏早阶段同时掩埋的。”[4]
江章华、李明斌说:“应当采取谨慎的态度,认真分析,而不能仅凭一两个数据就贸然对地层或墓葬的年代下断言……一两个孤零的数据,就其本身而论是没有多大意义的……碳14测年数据只能起提供参考的作用。”[5]关于成都十二桥遗址,学术界通常认为是三星堆遗址之后的重要遗址。江、李说:“关于十二桥文化的年代,仅有两个碳测数据……分别为距今3520年和3680年左右……明显偏早,因此只好排开不顾。”
1992年4月1—6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大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8单位联合主办“纪念三星堆考古发现六十周年暨巴蜀文化与历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说到对三星堆的碳14测年数值是距今3100年左右,也就是商末。但会下、会后有较多代表在议论,认为在测试过程中,取样品、送样品、测试数据的多少与准确性,都存在问题。孙华等《神秘的王国》一书曾建议:选用金杖包裹的碳标本等,多做一些“测定数据”。1994年,在德阳举办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术研讨会,国家历史博物馆的李先登研究员说:“我将三星堆青铜器与全国出土的青铜器按两个序列排队:一是按器物壁厚排队,越早器壁越厚,制作工艺越粗糙;越晚器壁越薄,制作工艺越精良。二是按器物的合金成分排队,越早合金成分的比例波动越大,越晚合金成分的比例波动越小(越稳定)。两个序列排队的结果是:三星堆两个坑出土的青铜器的年代为春秋时代。”笔者认为,李先登所说有道理。
三、关于碳14测年的发明、原理与测年数据的准确性
关于三星堆遗址埋藏坑埋藏器物的年代,从最初发掘到现在,主要依据碳14测年的方法确定。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威拉得·利比(Willard Frank Libby)于20世纪40年代发明了碳14测年技术(Carbon-14 dating),1950年开始应用于实际测年,1960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1955年,中国的仇士华与蔡莲珍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进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1959年调入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工作,负责建立中国最早的“碳14断代实验室”,并在此研究、工作一生。这两位是中国碳14测年研究的开创性人物,也是领军人物。仇、蔡合作撰成《14C测年及科技考古论文集》(以下简称《仇·蔡集》),应是这个领域的巅峰著作,也是本文的主要参考和引用的著作。[6]总体而言,与数千年人类文明史相比,碳14测年技术的发明与应用,应说很晚,是一项新兴的有待在应用中不断完善的技术。碳14,有多种写法,如,碳十四、Carbon-14、14C、C14、C-14等。(本文除直接引用外,为方便起见,一般写作C14或碳14。)
关于C14测年的原理是这样的:自然界存在3种碳(Carbon)的同位素,其中,C13占比很少,只占1.1%(其他更少),而且基本都是非放射性的;而C14则具有放射性,占比大至98.9%。宇宙射线同地球大气发生作用,产生中子,中子与大气中的氮核发生核反应的结果,主要生成了自然放射性C14,这种C14原子与氧(Oxygen)化合生成二氧化碳(CO2)。自然界的植物吸收二氧化碳进行光合作用,这些植物也就带有放射性C14。许多动物要吞食植物,因此,这些动物也带有放射性C14。放射性C14具有衰变性,例如,某种物体含有“放射性C14”,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如果这种物体具有生命,减少后又会从大气中不断吸收,使物体内的放射性C14含量保持相对平衡。但是,如果某种植物或动物死亡了,就不能再吸收,而只能衰减其放射性C14。物体内的放射性C14的衰变速度,是每隔5730年约减至原有数值的一半,即每年衰减56±14(Bq),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半衰期”。因此,所渭C14测年就是测量某种已死亡多年的植物或动物衰减后的放射性C14数值,利用其“半衰期”推算出死亡时间。这就是C14测年的原理。
放射性C14测年的应用领域有人类学、第四纪地质学、地球化学、海洋学和考古学;而测量对象则是有机物,如木炭、木头、动植物遗体、毛发、织物、泥炭、贝壳、骨头等,最佳的测量物是木质和木炭标本。无机物是不能测量的,如青铜器、玉器、陶器、石器等。对于这些无机物,只能找到与其埋在一起的有机物标本测量,间接地获取测年数据。
在《仇·蔡集》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撰写的《14C年代的误差问题》说:“应该承认过去由于测量精度的限制,在应用14C测定年代的基本假定和方法上比较粗糙或不够完善……”;又说:“14C年代与真实年代间的显著差别,使人们发生了怀疑,似乎应用14C测定年代的方法发生了危机……”[7]
《仇·蔡集》中的《14C测定年代与考古研究》一篇说:“14C测定的年代本身误差相当大……在西周共和元年以前……上推的夏商间的年代界限本身也就有问题。因此14C年代同历史年代的比较研究要从西周初开始逐渐向前推,这就使问题更复杂化了。”《仇·蔡集》中《夏商周断代工程与14C年代测定》说:14C年代测定“毕竟由于误差较大,难以解决历史时期的考古年代问题”;又说:“武王克殷的年代问题,是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最关键的问题,不同的说法有四十多种……14C测定并不能得出需要的年代……”[8]
三星堆遗址1号坑、2号坑是1986年发掘的,也应用了放射性C14测年,其测量误差偏大是可以想见的。《仇·蔡集》之《14C年代的误差问题》说:“有许多因素使14C年代与历史真实年代间出现差别。”在此文列举的7项误差因素中,非常重要的是第6项,即标本受到污染或特殊环境生长的标本引起的误差。[9]如何能采用到合格的检测标本?上文说;“标本长期埋在地下经历各种变化,可能受到不同时代碳的污染,如腐烂发霉,地下的碳酸盐,腐殖酸,新生植物的根、芽都可能使不同年代的碳混入标本中去……”为了尽可能减少误差,上文指出:首先要谨慎选对标本并予认真处理,其次要做到:“1.统一现代碳标准;2.作同位素分提效应校正;3.作树轮年代校正。”
动物的骨头可用于C14测年,但是骨头及贝壳样品含有的C14非常少,所以一般不用。《仇·蔡集》中《骨质标本的14C年代测定方法》说:“骨质标本的14C年代测定一直存在困难。首先,骨头中含碳量极少……可信度较差。”《仇·蔡集》中《关于考古系列样品14C测年方法的可靠性问题》说:“14C测定不能判断历组甲骨文是早是晚……我们只能遗憾地说,这是不可能。因为树轮校正曲线各段的特征情况不一样。在殷墟这一时期,峰谷密集,总体倾斜度很小,早晚各期样品的14C年代根本无法区别,而且往往出现颠倒的情况。”[10]
现在我们明白,殷墟甲骨文的载体、大量的兽骨与龟甲的年代,都不是用C14测年技术测出来的。那么对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象牙,则同样不能用C14测年确定其年代了。
对C14测年获得的数据,必须进行年代校正。《仇·蔡集》中《关于考古系列样品14C测年方法的可靠性问题》说:“14C年代不是日历年代……根据统一的现代碳标准和测出的考古样品的残留14C放射性水平计算出的样品的14C年代不是日历年代。要经过年代校正,才能转换到日历年代。”[11]校正的方法有多种,其中,树轮年代校正是较为重要的一种。蔡莲珍在《考古》上发表《14C年代的树轮年代校正》一文说:“原先假定几万年以来14C在大气中浓度基本稳定,但事实上大气14C浓度的变化最大可达10%,因此,14C年代需要用更为精确的计算方法进行校正……树木年轮每年生长一轮,可以通过清数年轮精确确定出每一轮的生长年代……两者结合即可将14C年代比较可靠地校正到真实年代。”[12]
《仇·蔡集》中《夏商周年表的制定与14C测定》一篇说:“木头树轮系列样品……证明测试的可靠性是好的……沣西两座西周中期墓葬M121和M4的棺木,按树轮系列测定,得出最外轮年龄分别为公元前940±10和919±14……河南郑州商城二里岗上层1期水井框圆木,测出最外轮年齡为公元前1400±8,应该相当于水井建造年龄。”[13]
问题是,在三星堆遗址已经发掘的8个埋藏坑里,有没有这样的“木头树轮系列”样品?有没有检测过这样的样品?实际情况是,能找到这样的木头样品很困难。何况,古代人不会为几千年后的树轮校正而专门埋下一段木头。
王仁湘等说:“树轮年代学有特别的分析方法……在中国还没有完成能延伸到史前时代的树轮年表,通过年轮对考古遗址进行定年,还有许多工作要做。”[14]这就是说,“许多工作”做完了,才能有真正的树轮年代校正定年。
《仇·蔡集》中《夏商周年表的制定与14C测定》说:“夏商周断代工程是由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专家联合实施的系统工程……主要有两条:1.对传世文献和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中有关天文历法记录进行整理、研究认定,应用天文计算推定其年代。2.对有典型意义的考古遗址和墓葬资料进行分析研究,采集遗址地层或文化分期的系列样品,以及分期明确的甲骨系列样品,进行常规和加速器质谱计(AMS)的14C年龄测定。”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才会得出尽可能合理的年代与年表。总之,考古年代学需要考古学家和测年工作者的共同研究,也就是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专家学者进行共同研究;这之中,人文社会科学应居主导地位。
河南殷墟发现的甲骨文载体的年代,也不是依据C14测量技术确定的,而是依据甲骨文刻写的人物、事件、天象等文献确定的。另外,陕西西安兵马俑发掘后,也不是用放射性C14测定其年代,而是采用了兵马俑坑出土文物上的文字。出土文物中,有一件青铜戈上刻有“寺工”二字,“寺工”是秦始皇执政时期的官名,职责是主管兵器制造等;戈上还刻有“五年相邦吕不韦造”,“吕不韦”是秦始皇执政时期的宰相。因此,这件铜戈上的刻画文字就成了确定兵马俑遗迹年代的依据。还有,司马迁《史记》也有关于秦始皇陵墓和兵马俑的记载(二者相距1公里)。上述文献记载与出土文物就成了兵马俑年代确定的可靠依据。这是运用了两重证据法。诚如地质学教授刘兴诗在其《三星堆的故事》一书说:“……中国历史悠久,每一层都埋藏有历史文物,比放射性(碳14)测年还准确。”[15]
四、三星堆遗址新发现6个坑的碳14测年简况
2021年,三星堆遗址新发现并发掘了6个埋藏坑,出土许多珍贵文物。北京大学的相关研究团队在这6个坑中选择足量的植物碳屑和骨渣(约200份测年样品),检测了38个放射性C14测量数据,分别测得了大致相当的年代和概率。其中4个坑测得的放射性C14数据分别是:
3号坑:8个;4号坑:11个;6号坑:10个;8号坑:9个。
测得的年代数据及概率为:
3号坑埋藏行为的时间落在公元前1117年至前1012年之间的概率是95.4%,落在公元前1109年至前1016年之间的概率是68.3%;
4号坑落在公元前1126年至前1016年之间的概率是94.1%,落在公元前1115年至前1054年之间的概率是68.3%;
6号坑落在公元前1201年至前1019年之间的概率是95.4%,落在公元前1125年至前1054年之间的概率是68.3%;
8号坑落在公元前1117年至前1015年之间的概率是95.41%,落在公元前1111年至前1020年之间的概率是68.3%。
此外,在5号坑与7号坑取得的样品,由于保存状况欠缺,测量结果不理想,没有公布数据。6个坑里有2个坑的测试样品不合格,不合格的比例占33%。
现在看来,这样的C14测年有待改进。北京大学相关研究团队公布上述6坑年代数值之前,使用了“初步可以判断”的谨慎用语,留下了允许继续探讨的宽容。
五、青铜器的铸造加工技术与年代的关系
在商代,中原地区与长江中游等地的青铜器的铸造主要使用块范法浑铸成形,其次配以分铸工艺。用分铸补充成形时,也是尽可能减少分铸的铸件数量与工作量。有一种观点认为,以上铸造都使用块范法,而不用失蜡法。
在孙华、苏荣誉合著的《神秘的王国》中,关于青铜铸造工艺一节,由铸造工艺技术的行家苏荣誉老师撰写。苏老师说:三星堆的青铜器,基本与商代中原地区的铸造工艺相同。巴纳(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对广汉埋葬坑青铜器及其他器物之意义的初步认识》(载《南方民族考古》第5辑)说:“巴蜀文化这常见的铜鍪和铜釜等器物上的索状耳是采用失蜡法铸成的。如广汉青铜器中实际已存在失蜡法或覆模铸造的情况确实的话,那么用这种方法铸造的器物的年代将是可以推定的,即大约在公元前400年左右或者更晚。”苏老师说:“巴纳的观察是正确的。”[16]
在先,屈小强说:“大型青铜立人像先采用分铸法,分铸头、躯干、四肢等部位,最后,再与方座及四花瓣状冠冕合铸而成……它既是古蜀文明的骄傲,更是中华文化的骄傲。”“在公元前1500年至前256年的商周青铜器中,发现有大量耳部或顶部开有孔洞的青铜面具”;“中国面具文化……个性鲜明,自成一统。”[17]
马承源主编的《中国青铜器》说:“目前中国最早用失蜡法的铸件是1978年5月河南省淅川楚王子午墓所出土的青铜禁……内部支条,尚可见蜡条支撑的铸态。王子午即楚王的令尹子庚,其活動时期在公元前六世纪中叶……所以在春秋中期和晚期之际,失蜡铸造的技术,已能成功地铸造最复杂的器件。”[18]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许多高大的青铜器的结构也比较复杂,这就要求青铜铸造与加工工艺当有相应的提高与发展,于是出现了切割孔洞技术和铸铆工艺等。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苏荣誉说:“中国自二里头文化迈入青铜时代后,迅即以泥范大量铸造青铜礼器为青铜工业转点。二里头时期的青铜器,基本上是浑铸成形的。发展到二里冈时期,随着青铜器的大型化、多样化和复杂化,分铸铸接技术被用于铸造大型和复杂青铜礼器……发展到殷墟前期,以妇好墓青铜器为代表,分铸法被广泛得到应用……一直到春秋晚期,分铸臻于兴盛……三星堆祭祀坑青铜器很多是分铸成形的”;“三星堆祭祀坑青铜器的制作,有两种工艺是其他地区所没有的,或者是最早的。一种是铸铆的方式连接部件,另一是切割孔技术。”[19]
苏先生还说:“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人面像中,有若干器物额和脸上的方形透空是切割出来的。”“切割成孔工艺是有悖于商周青铜工艺传统的。”[20]
由此是否可以推断:拥有青铜器铸铆工艺和切割成孔技术(商周时期中原大地尚未出现)的三星堆遗址的年代只能在商末之后,甚至晚到春秋时期?
六、鱼凫王朝存在于什么年代?
王仁湘《三星堆:青铜铸成的神话》一书提出,从开明王朝末年到蚕丛王朝初年,说有“四万八千年”不可信,说有1800年差不多。[21]这1800年应该是一种推测。据《华阳国志》载开明氏曾“王蜀十二世”,于公元前316年被秦灭亡。研究古蜀历史的多数学者采用1代执政30年计算,12代即为360年;开明王朝的初始(杜宇王朝末年)即为公元前676年;然后推定其他4个王朝都是12代,每代都是30年,即可推算到蚕丛王朝初年是公元前2116年(夏朝初年是前2070年),鱼凫王朝初年是公元前1396年,末年是公元前1036年(商末周初),也就是距今3420年至3060年。
周朝从周武王姬发定都镐京(前1046年)开始至东周周赧王死去(前256年)周灭为止,每一代君王平均执政约20年。再说从公元前905年,周孝王封嬴非子于秦邑(今甘肃清水县东北),建立秦国,到秦始皇再到秦二世胡亥、秦三世子婴,共有38代君王,每代君王平均执政的时间约为18.36年。而秦朝之后的朝代每代君王平均执政时间不到20年。我们放宽每代以20年计,从公元前316年开明王朝灭亡开始上推至蚕丛王朝,初年将是公元前1516年(商代早期);鱼凫王朝初年将是前1036年(周代初年是前1046年),末年是前796年(周代中期);杜宇王朝初年将是前796年,末年是前556年,相当于春秋(前770至前476年)后期。
对于三星堆1号坑与2号坑埋藏器物的年代,江玉祥认为是春秋时期;徐学书认为是春秋中叶。春秋的起讫是前770年至前476年,这基本上是杜宇王朝时期(前796年至前556年)。
敖天照、刘雨涛《广汉三星堆考古记略》说:“《华阳国志·蜀志》说:‘(杜宇)移治郫邑,或治瞿上。郫邑即今郫县,……三星堆至月亮湾一带,应是蜀王杜宇氏的都城‘瞿上。”[22]
笔者认为,三星堆埋藏坑应该是杜宇王朝与开明王朝夺权冲突引起的埋藏产物。此后开明五世或九世的开明尚,“因梦廓移”而迁都至成都。现在还没有鱼凫王朝建都于广汉的证据。如果将三星堆遗址的文明说成是鱼凫王朝的遗存,又把金沙遗址的文明说成是杜宇王朝的遗存,那么开明王朝就会变成既没有地方也没有年代可以存留了。
七、结语
三星堆遗址珍贵文物埋藏的年代,一直争论至今,但以商末为主流观点,其以放射性C14测年作主要依据。本文认为,这还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专家学者共同攻关。放射性C14测年只能作为参考。样品的保存不利等因素,影响到测年的准确性。再加上古蜀历史文献记载稀缺,考古发现的实物提供的年代证据不足,古蜀文字很少而且还不能解读等,都给三星堆遗址埋藏坑的年代确定造成了困难。
本文主要考虑,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6个坑,竟有2个坑无法获得C14测年数据;三星堆遗址的青铜器使用了铸铆与切割孔洞技术,这是春秋时期才出现的新技术;加上每代君王平均执政20年计算,三星堆遗址埋藏坑的年代,应晚于商末,或为春秋时期,较为合理(当然,有些埋藏物的制造时间会更早)。推断三星堆遗址埋藏坑的年代或为春秋时期,并不会影响古蜀文明的古老悠久与光辉灿烂。
注释:
[1]参见宋治民:《蜀文化》,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49-52页。
[2]参见赵殿增:《三星堆考古发现与巴蜀文化研究》,《四川文物》1992年专辑。
[3]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金沙:再现辉煌的古蜀王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8页。
[4][16][19][20]孙华、苏荣誉:《神秘的王国:对三星堆文明的初步理解和解释》,巴蜀书社2003年版,第338-339页,第429页,第438页、439页,第434页、436页。
[5]江章华、李明斌:《古国寻踪:三星堆文明的兴起与影响》,巴蜀书社2022年版,第203页。〔按:正规测试,由测试人亲自到测试场所(坑)选取样品,每个测试点最少取3个样品,每个样品最少测出3个数据。正规测得的数据,仍然只是“提供参考”。〕
[6][7][8][9][10][11][13]仇士华、蔡莲珍:《14C测年及科技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第22页,第115页、182页,第48页,第251页,第38页,第182页。
[12]蔡莲珍:《14C年代的树轮年代校正》,《考古》1985年第3期。
[14]王仁湘、张征雁:《金沙之谜:古蜀王国的文物传奇》,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0页。
[15]刘兴诗:《三星堆的故事:古蜀文明探秘之旅》,四川辞书出版社2021年版,第207页。
[17]屈小强:《巴蜀社会的文明轨迹、文化交汇与文化精神》,陈信远主編《巴蜀文化与西部四川开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20页。
[18]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517页。
[21]参见王仁湘:《三星堆:青铜铸成的神话》,巴蜀书社2022年版,第80页、84页。
[22]敖天照、刘雨涛:《广汉三星堆考古记略》,《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335页。
作者:四川省科协高级工程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