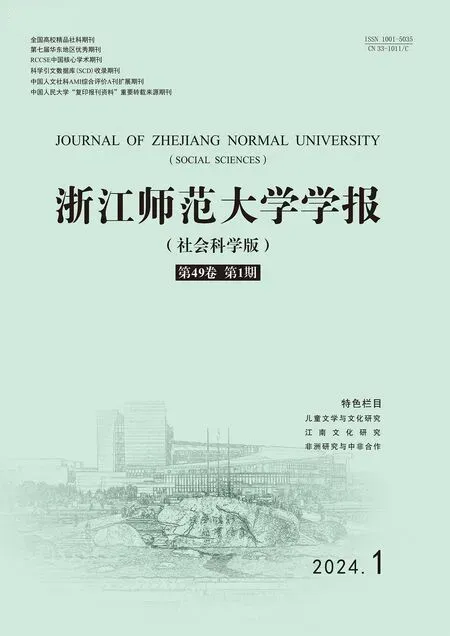欺骗、暴力与种族主义
——彼得·马修森《疯马精神》中的苏族印第安人声音
徐向英
(闽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引 言
彼得·马修森(Peter Matthiessen)在美国文坛上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他不仅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既以虚构类又以非虚构类作品赢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作家,同时也一直被公认为“为数不多的积极投身社会正义事业的美国作家之一”。[1]2他一生都在为弱势群体仗义执言,致力于“为不能为自己说话的人说话”,[2]尤其“关注美洲原住居民印第安人”。[1]2早在20世纪50年代,马修森就已经开始高度关注印第安人的命运,尤其是生活在北美中部大平原上北美最大的印第安民族苏族人(The Sioux)。非虚构作品《疯马精神》(TheSpiritofCrazyHorse,1991)是作家围绕20世纪70年代美国印第安运动苏族奥格拉拉(Oglala)部落领袖莱昂纳德·佩尔蒂埃(Leonard Peltier)事件而展开的书写。作品出版后,赢得《芝加哥论坛》《芝加哥太阳报》《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书评》《今日美国》等各大报刊的赞誉。有“西方作家院长”之称的华莱士·斯泰格纳(Wallace Stegner)称《疯马精神》堪与印第安土著文学经典《百年耻辱》(ACenturyofDishonor,1881)、《卡斯特因你之罪而死》(CusterDiedforYourSins,1969)和《魂归伤膝谷》(BurymyHeartatWoundedKnee,1970)相比肩,但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学者尚未对该作品展开相关的研究。
为维护印第安人的权益、促进传统印第安文化复兴,20世纪70年代在北美印第安保留地上爆发了美国印第安运动(American Indian Movement)。1975年6月26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印第安运动组织双方在南达科他州松岭印第安人保留地(The Pine Ridge Indian Reservation)的一个小村庄奥格拉拉发生了一场致命的枪战。印第安领袖苏族人莱昂纳德·佩尔蒂埃被指控在这场暴力冲突中杀害两名联邦调查局特工被美国政府审判,判处终身监禁。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莱昂纳德被定罪。此事在社会各界引发了巨大的反响和争议。马修森在大量走访和广泛调查的基础上,指出无论莱昂纳德在这场冲突中的性质和程度如何,对他的随意定罪和迫害“与其说与他自己的行为有关,不如说与历史、种族主义、经济有关,尤其是与印第安人的主权主张等潜在问题有关”。[3]XX为了呈现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客观地还原历史的真相,马修森在《疯马精神》中以莱昂纳德·佩尔蒂埃事件为切入点,回溯了19世纪中叶以来生活在大平原达科他州黑山地区的苏族人民为了土地与美国政府之间长达百年的斗争。本文旨在结合美国西进运动的历史,分析作家如何通过查阅资料及采访印第安人并适时阐述个人观点的方式,让历史中无法发声的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让读者从原住民的视角感受和体会长期以来他们“因祖先的土地被盗窃和破坏带来的悲伤”,[3]XXIII由此揭露美国政府在西进运动中为攫取土地,图谋利益,违背契约精神,并以“昭昭天命”为名对印第安人施加的欺骗、暴力和种族歧视,控诉了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民和印第安土地的侵犯行为,由此揭示了一个以全球人权、正义卫士自居者的真实面目,体现了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
一、违背契约:“他们用法律欺骗人”
众所周知,印第安人是美洲大陆的原住民,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欧洲殖民者开始踏上这片土地,自此之后印第安人与白人殖民者之间为争夺土地导致的冲突与矛盾就没有停止过。在白人主流文化关于这一冲突矛盾的传统叙事中,比如在北美本土流行的文学体裁囚掳叙事中,印第安人总是被建构成嗜血残暴的野蛮人的负面形象,而白人则是一副代表慈善正义的文明人的正面形象。这一建构的形象深入人心,业已成为美国历史遗产和边疆神话的重要组成部分。①马修森在《疯马精神》中一反主流文化叙事的传统,从印第安人的视角颠覆了两者固有的形象,呈现了历史的另一面。
契约精神在西方源远流长,是基督教文明的重要产物,基督教经典《圣经》几乎就是一部关于上帝与人订立契约的作品。占美国早期移民主要比例的英国清教移民在登陆美洲大陆之前为了相互约束而共同签署的《五月花号约》(TheMayflowerCompact,1620)也是基于契约精神而签订的,被视为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份契约。它不仅是美国作为法治国家存在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美国精神的先驱。契约精神是一种关乎自由、平等、守信的精神,遵守契约、讲求诚信是关乎信仰的极其重要的道德品质,正是这种精神和品质奠定了美国文明进步的基础。作为按照契约约定代表公民行使权力的美国政府本应遵守并维护契约的严肃性,但事实是,美国政府视与印第安人订立的契约为一纸空文,不但没有遵守契约、确保契约的有效执行,相反,用苏族酋长愚鸦(Frank Fools Crow)的话来说是:“白人政府总是不断地制定法律……然后打破每一条法律。他们用法律欺骗人。”[3]515对《拉勒米堡条约》(FortLaramieTreaty,1868)的违背就是美国政府制定条约又撕毁条约、肆意践踏契约精神的一个典型写照。
美国建国后,大批白人定居者开始跨过阿巴拉契亚山脉蜂拥而至大平原地区,印第安人也因此被一步步驱赶到贫瘠的荒原上。为了保证西部开发的顺利进行,减少与印第安人的敌对行为,美国政府和苏族的拉科塔人签署了《拉勒米堡条约》。条约界定了大苏族保留地(Great Sioux Reservation)的范围,规定他们对保留地“拥有绝对、不受干扰的使用权……没有印第安人的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穿越这片区域”。[3]7黑山地区正是位于条约规定的保留区的核心地带。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片曾经被白人认为没有价值的荒原却出乎意料地被发现蕴藏着北美最大的矿产资源。在该条约签订几年后,在这里发现的矿产引起了白人对这个地区的强烈兴趣。苏族人恪守承诺,忠实地遵守了条约,在条约规定的保留地里生活,但美国政府却无视条约中的承诺,举着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的幌子,强令苏族人出售黑山及其周边地区,“无论印第安人愿不愿意,都要购买黑山;如果他们选择拒绝500万美元,那是他们自己的事”。[3]11面对美国政府一副罔顾条约、背信弃义的霸权面目,苏族医生皮特·卡奇斯(Pete Catches)提出强烈的抗议:“他们欺骗、撒谎,破坏了每一项条约,甚至是保护黑山的神圣条约。”[3]XXXVIII
苏族人之所以强烈抗议是因为美国政府视《拉勒米堡条约》为废纸这一背信弃义的行为不仅违背了他们自己最基本的契约精神,同时也触犯了印第安人的宗教信仰。在印第安人眼中,这片埋葬着他们祖先的土地不仅是物质性的存在,也是精神性和宗教性的存在。在马修森对苏族人的采访中,他发现苏族人总是亲切地称呼地球为母亲。[3]18地球母亲上的每一寸土地在他们种族的记忆和经验中都是神圣的。在苏族人民的心目中,黑山是他们不可亵渎的圣山,“这些山丘形同一个身体倾斜着的女性,它的乳房上流淌着生命的力量……拉科塔人去这里就像一个孩子到了母亲的怀里”。[3]4跟其他部落的原住民一样,苏族人对地球母亲的信仰是一种超越了功利层面的、对万物存在本质的直觉的理解。苏族人不仅拥有自己的信仰,而且对待信仰十分虔诚。诚如美国作家和人类学家奥利弗·拉·法奇(Oliver La Farge)所做的调查,他们“对待宗教仪式一丝不苟,把宗教信仰融入生活的每时每刻”。[4]他们活在自己的信仰当中,自己的存在与自己的信仰是不可分离的一体。苏族人这种对待土地的信仰与对待信仰的执着绝不允许他们把土地当作商品进行肆意买卖。面对美国政府的言而无信,以奥格拉拉领袖疯马(Crazy Horse)为代表的苏族人发出自己的心声,表明了苏族人的坚决态度:“人们不出卖自己行走的土地。”[3]11面对白人强行购买黑山的强权行为,他们不为所惧,谴责白人政府的出尔反尔,坚决捍卫自己的土地和信仰。
然而,凭借着自己的军事力量和人口优势,美国政府无视《拉勒米堡条约》和苏族人民的强烈抗议,派军队强行进驻大苏保留地,追捕那些“最有可能抗拒理性声音的敌视白人的印第安人”。[3]11苏族的各个部落在疯马的领导下联合起来在黑山地区的小巨角河战役(Battle of Little Big Horn,1876)中打败了白人军队。但不幸的是,黑山的胜利加速了他们厄运的降临和最终的覆灭。用马修森的话说,这一次的胜利“为胜利者招来了冷酷的报复”。[3]12美国政府将黑山战争的失败归咎于苏族人的“好战野蛮行为”,[3]12单方面宣布《拉勒米堡条约》不再有效,赤裸裸地藐视了契约精神,奉行强权即是公理的霸权逻辑。被强行扣上“好战野蛮”的污名,疯马义正辞严地驳斥道:“我对白人没有任何敌意……我们有野牛肉为食物,有牛皮做衣服……但他们在大雪纷飞的寒冬中摧毁了我们的村庄……他们说我们屠杀了他们,但如果我们不自卫,战斗到死,他们就会屠杀我们。”[3]153一位参与这次战役的美军首领乔治·克鲁克(George Crook)在被问及向苏族人发动战争是不是很艰难时所作的回答佐证了疯马的驳斥,“是的,很难。但是,先生,最难的是去攻打那些你明明知道是正确的人民”。[3]11
无论是疯马的驳斥还是克鲁克的反思都在告知人们,苏族人绝非白人所污蔑的生性好战的野蛮人,相反,是白人违背契约和侵犯行为在先。对于苏族人来说,他们无法失去这块赖以生存的土地,失去它就意味着死亡。他们不得已的反抗是对白人掠夺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破坏他们家园的回敬,是公理对强权的反抗,更是对《拉勒米堡条约》的维护和对土地与信仰的捍卫。由此,马修森一改以白人为中心的传统叙事,给予印第安人发出声音的机会,从而揭露了白人政府对印第安人的欺骗,一反白人主流文化叙事中对印第安人的刻意丑化,揭示了白人的霸权逻辑。
二、暴力:“一个真正优越的政府怎能有如此的破坏性呢?”
伊利诺伊州大学历史学教授艾米·露易丝·伍德(Amy Lousie Wood)认为,在人类历史上暴力在大多数人类社会中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但对美国而言,暴力却是“这个国家形成的核心”。[5]纵观美国历史,从17世纪的殖民时期、18世纪的独立战争、19世纪的南北战争,一直到21世纪的今天,各种形式的暴力几乎贯穿美国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尤其是19世纪白人在大平原上对动物种群和印第安人族群同时进行大屠杀,更是史无前例的暴力行径。
黑山战争失败并没有阻止白人的扩张脚步,相反,美国政府陆续派出军队加大镇压的力度。虽然他们在军事和人数上占优势,但苏族人的英勇抵抗让他们一时难以迅速取胜。为了迫使苏族人放弃抵抗,他们改变战略,转而开始大批屠杀大草原上的野牛。长期以来,野牛是苏族人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基础,有人曾形象地把野牛比喻为苏族人“奔跑的百货商店”。[6]只要野牛还在草原上,就会有充足的物质和力量支持他们对抗白人。为了断绝他们主要的生活来源,美国政府将消灭野牛视为迫使苏族人放弃抵抗的有效手段,“消灭野牛是解决印第安问题的唯一途径”。[7]他们雇佣专业狩猎者对野牛发起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短短几年时间这些狩猎者就完成了对整个野牛群的毁灭,为白人政府扫除了障碍。美国西南地区的一位军事长官菲利·谢里登(Phil Sheridan)认为野牛猎手们在解决印第安人问题上所做的贡献“比整个军队在过去30年所做的都要大”。[8]128随着野牛越来越稀少,苏族人的生活一天比一天艰难,生存资源渐渐枯竭的他们在无奈之下被迫选择屈服、放弃抵抗。当年的一位铁路检查官在回答一名记者提问时说道,美国政府“从来都没有能够控制印第安人,直到他们的牛肉供应被切断”。[9]切断苏族人的主要生活来源后,美国政府强行与走投无路的苏族人签订《黑山法案》(BlackHillsAct,1877),把他们赶到更偏远的保留地上,霸占了黑山地区及其周围的大部分土地,向苏族人作出承诺“永久提供维持他们生计的口粮”。[3]13
奥格拉拉领袖坐牛(Sitting Bull)深谙美国政府一贯以来的言而无信,一针见血地道出了他们的真面目,“白人订立的条约,红人打破过吗?从来没有。白人和我们缔结过的条约,白人遵守过吗?没有”。[3]33《黑山法案》后不久,国会又通过了一系列法案,其中的《道斯土地分配法》(DawesGeneralAllotmentAct,1887)规定每个印第安成年男性可获得160英亩的土地。坐牛一眼看穿《道斯土地分配法》昭然若揭的企图,“他们想让我们放弃另一块部落土地。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他们企图攫取我们拥有的最后一块土地”。[3]19诚如马修森所指出的,《道斯土地分配法》表面上是为了印第安人的利益,解除部落体制实现印第安人的个体化,让印第安人接受白人的教育、讲白人的语言、皈依白人的宗教,美其名曰帮助印第安人进入美国主流社会,实则是垂涎这片土地。正如有些白人议员所坦言的,分配法“根本不符合印第安人的利益,只不过是他们觊觎土地的借口”。[3]17但遗憾的是,来自少数白人的正义之声被淹没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呼啸声中。马修森一语道破美国政府的真正目的,“通过摧毁对土地的共有监护权,分配法不仅破坏了印第安民族的团结,也破坏了他们为共同利益彼此慷慨解囊和完全分享共有的传统”。[3]18分配法让每个印第安男性获得160英亩的土地,剩余的土地由美国政府廉价购买后公开拍卖,最终全部落进了白人的手里,包括苏族人在内的所有印第安人的土地在这次分配中几乎流失殆尽。
《道斯土地分配法》出台三年后,像疯马一样,坐牛也被扣上“煽动麻烦拒绝被捕”[3]20的罪名而遭到杀害。坐牛被杀后不久,他所在的部落因为举行他们传统文化中寓意“和平和繁荣”[3]19的幽灵之舞(Ghost Dance)而遭到白人政府的阻止,上演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伤膝谷大屠杀(Wounded Knee Massacre,1890)。当地医生查尔斯·伊斯特曼(Dr.Charles Eastman)回忆当时自己的族人在逃命时遭到无情追捕和屠杀时尸横遍野的情景:“尸体散落一地……遍地哀嚎……已经冻僵了的尸体不是躺在一起就是堆在一起……其中大多数都是手无寸铁的老人、妇女与儿童。”[3]20查尔斯·伊斯特曼的回忆场面让人不寒而栗,却是不争的事实。伤膝谷大屠杀是数百年来北美印第安人悲惨命运的一个真实写照和缩影。当年率领美军参与该事件的纳尔逊·迈尔斯将军(Gen.Nelson A.Miles)晚年在反思这桩惨案时承认这是一场“最应该受谴责的、最不道德的、最应该被严厉定罪的大屠杀”。[3]21
伤膝谷大屠杀后,苏族人,用苏族酋长愚鸦(Frank Fools Crow)的话说,是陷入了“巨大的忧郁和匮乏之中”。[3]21被迫接受《道斯土地分配法》的包括苏族在内的一百多个印第安部落在试图适应白人的新制度时,一方面因为原先对土地的公共监护权被破坏了,另一方面又缺乏白人经营土地的经验,在无力偿还抵押贷款和税款以及饥饿的压力下渐渐解除了合约,失去了土地,沦落为依靠联邦政府提供食物救济的地步。奥格拉拉酋长红云(Red Cloud)悲伤地说道:“我们在痛苦中感到屈辱,没有人为我们说话,我们没有得到赔偿。我们的口粮又减少了。你们每天吃三顿饭,看着自己的孩子健康开心,你们无法理解忍饥挨饿的印第安人是什么感受。”[3]21在伤膝谷大屠杀后的半个世纪里,他们失去了三分之二的土地。土地是他们的命根,失去了土地、失去了野牛的苏族人生存处境每况愈下,他们被限制在白人划出的贫瘠的保留地里,依靠领点救济和补贴在白人带来的酒精中浑浑噩噩地活着。奥格拉拉酋长站熊(Luther Standing Bear)悲愤地控诉白人政府的罪行:“难道这就是所谓善良、睿智、乐于助人、仁慈的征服者带来的东西吗?一个真正优越的政府怎能有如此的破坏性呢?”[3]26
美国政府违背契约精神在先,随后对野牛群和包括手无寸铁的老人、妇女和儿童在内的苏族人不分青红皂白地进行大屠杀,这是美国白人在大平原上制造的对动物物种和人类种族双灭绝的罪行。北美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本可以为白人定居者提供与印第安人共享的生存空间和自然资源,但对土地的狂热让他们彻底迷失了方向,在这片土地上制造了一桩桩本不应该有的血腥暴力,不仅给印第安人带来了深重灾难,也摧毁了两个不同种族在这片土地上和平共处的可能性。
三、种族主义:“我的皮肤是红色的,所以我就是邪恶的吗?”
在19世纪美国西进扩张运动中,印第安人因为成为白人攫取土地的绊脚石而遭到无情的驱赶和屠杀。如果说土地是最直接的原因,那么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白人种族优越论作祟下的种族主义。1776年7月4日美国《独立宣言》(DeclarationofIndependence)开宗明义地指出人人生而平等,但在美国历史上种族偏见和种族歧视却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作为美国最贫穷和脆弱的一个群体,印第安人遭受的种族歧视尤为严重。美国白人举着“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的旗号不断地进行开疆拓土的西进扩张运动,在这个过程中,印第安人首当其冲成为受害者。白人坚信自己是优等民族,自诩是上帝的选民,得到上帝的眷顾来管理上帝恩赐的这片应允之地,完成上帝在地球上的未竟事业,而这些红色人种是“本性远比任何沙漠野兽都残忍和凶猛”[3]9的未开化的异教徒和野蛮人。所以,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和权利浪费土地,任其变成蛮荒之地,而理应为优等民族收回被他们所荒废的土地让路,这是上帝的旨意、是天命。“昭昭天命”所暗含的种族优越论巧妙地免除了基督教的仁爱精神对白人自我良心和道德的谴责,减轻了他们情感的重负,为他们开疆拓土过程中的各种掠夺与杀戮行径提供了名正言顺的理由。这些他们眼中的劣等民族如果阻碍了白人前进的步伐,他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以瘟疫、酒精和战争等任何手段驱逐、消灭他们,尽可能快地把他们从上帝指引的道路上清除掉。
带着上帝赋予的优越感和使命感,白人殖民者一步步自东向西来到了苏族人世代生活的大平原,以一副文明人的傲慢姿态鄙视红种印第安人,斥责他们的生活是“邪恶的生活”。[3]22但诚如酋长坐牛所反驳的:“白人看见我偷过他的土地吗?抢过他的一分钱吗?打破过一次条约吗?……他们说我是贼,说我是坏印第安人……我的皮肤是红色的,所以我就是邪恶的吗?”[3]33今天被白人称为苏族人的土著居民称自己为Ikce Wicasa,意为“自然人,自由的、野性的普通人”。[3]XXV人如其名,在白人到来之前,苏族人喝着小溪里的纯净水,吃着草原上的野牛肉,生活简单而自由、快乐,身体粗犷而健康,用酋长红云的话说是:“我们像风一样自由,像鹰一样不需要听任何人的命令……活得幸福,死得满足。”[3]22但是白人到来之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他们以自己的生活方式为文明进步的典范,视苏族人自由简单粗犷的生活方式为野蛮,把屠杀野牛的残暴行为解释成文明对野蛮的战胜,是帮助印第安人放弃“野蛮生活方式”,[8]145并以自己的宗教信仰为衡量标准,视苏族人地球母亲的信仰为邪恶。在小巨角河战败之后,深感奇耻大辱的联邦政府中开始出现灭绝印第安人的声音,因为在他们看来,“一个文明力量对待野蛮人不存在民族尊严的问题……红种人绝不配被当作人来对待”。[3]9在“昭昭天命”的旗帜下,白人为自己各种赤裸裸的屠杀行为开脱,终将西进之路彻底演变成了印第安人的血泪之径,酿成了一部种族大屠杀的血泪史。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上万名印第安人在战争中死亡,美国政府终于颁布《印第安人公民法案》(IndianCitizenshipAct,1924),在法律上宣布承认印第安人的美国公民权。然而拥有公民权的印第安人并没有结束被掠夺被歧视的命运,他们依旧苦苦挣扎于主流社会的边缘地带。酋长站熊痛心地道出了苏族人的困境:“今天印第安人的声音不仅无人聆听、无人理睬,而且他们仍然被掠夺、被抢劫。我的人民一直处于可怕的困境中,他们的健康因为饥饿渐渐恶化,而公众却还蒙在鼓里,以为政府正在照顾我们印第安人。”[3]26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白人在大苏保留地的蒙大拿州、怀俄明州和达科他州发现大量可供开采的铀矿和地表煤矿床,于是对这个地区的狂热兴趣再一次被点燃。为了将土地占为己有,“用土地做点事”,[3]28美国政府推出终止法案和重新安置计划,将包括苏族人在内的所有印第安人从保留地上分散到城市中,赋予这个“被迫依赖美国政府已经近百年的民族以独立”。[3]28作为独立的公民,大多数流落在城市里的印第安人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缺乏城市生活经验。马修森调查发现,无论他们被安置在哪个城市,几年之内他们都遭遇到普遍的疾病和彻底的贫困,尤其是那些拒绝接受白人文化、抵制同化的印第安人是“遭受绝望、冷漠、贫困、失业、酗酒和暴力最严重的群体……几乎在任何地方,这些人都遭受着这个国家任何其他少数族群都不能容忍的恶毒的种族主义”。[3]29-30即便是接受过职业培训的印第安人也发现自己面临着来自工会和雇主公开的种族歧视和偏见,“做的是最肮脏、最繁重的工作,领取的却是最低的工资,生活在城市的恶劣影响和被官方忽视的条件中”。[3]35-36
这些在城市中饱受种族歧视的印第安人在疾病、贫困、漠视中艰难生存,他们发现自己没有了根的归属,在自己的土地上变成实实在在的流亡者,挣扎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之间。印第安活动家苏族人站鹿(Standing Deer)告诉马修森:“在我说美国话之前,我讲的是土著语,我不知道妈妈什么时候开始教我讲美国话……我几次离家想去有印第安人居住的地方,但发现我从来都没有被印第安人所接受,因为……我不记得印第安人的语言、习俗。我变成了局外人。”[3]492站鹿的话道出了所有生活在城市里的印第安人的窘迫处境。一方面,在白人社会,他们因为不同于白人的红色肤色而遭受到严重的种族偏见和歧视,不被主流社会所接纳和尊重,成为劣等公民而屈辱地活着;另一方面,很多人跟站鹿一样在童年时代就从印第安保留地上被带走,在城市的贫民窟里接受同化教育,长大后的他们发现自己对印第安文化的记忆已经少之又少,再也回不到印第安人的传统生活中去。这些城市印第安人在自己祖祖辈辈曾经繁衍生息、自由生活的土地上变成了故乡的异邦人,徘徊在白人社会和传统印第安人社会之间,身体无处安放,情感无所依托,灵魂无所归依。
四、印第安运动:“绝望中最后的希望”
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谈到征服者与被征服民族之间的关系时曾说道:“除非被征服民族完全恢复了自由,自愿选择它的征服者作自己的首领,否则他们二者便永远处于战争状态。”[10]纳尔逊·迈尔斯将军晚年回忆伤膝谷大屠杀时曾做过深刻反思和警告:“被敌人征服的种族只会产生出最强烈的仇恨和敌意。”[3]607暴力只会制造暴力,暴力解决不了问题,相反暴力只会换来更大的暴力,美国白人对印第安人的暴力行径势必引起他们的强烈反抗,终止法案和重新安置计划点燃了20世纪70年代北美印第安运动大爆发的导火线。印第安运动的初衷是为了帮助那些被迫离开保留地生活在城市贫民区的印第安人,但随着运动的发展,其目标逐渐扩展到帮助所有印第安人恢复经济独立、振兴传统文化、保护合法权利、收回被非法夺取的土地等方方面面。印第安运动的成员们倒挂飘扬的美国国旗,携带枪支,设立街头巡逻队,参加各种示威游行、抗议活动,成为美国20世纪60—70年代为争取主权和平等权利而爆发的全美社会运动的一部分,赢得了全社会正义人士的支持和帮助,但同时也招来各种指责和谩骂的声音,认为该运动有激进暴力的倾向。然而,正如马修森所呈现的苏族人百年来的历史所示,我们不能孤立地评判印第安运动的行为。当我们从他们长期以来所遭受的苦难这一历史背景来看待这一问题时,他们的行为就显得情有可原。在印第安运动的背后,隐藏着印第安人长期以来饱受欺骗、大屠杀和种族主义的血泪历史。大平原上的苏族人百年来的血泪历史足以揭示这场运动的背后有着极其复杂和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马修森的立场很鲜明,他把自己放在他们的位置去理解并感受他们长期以来的不幸遭遇,为他们的行为辩护,揭露其背后真正的罪魁祸首。他认为恰恰是印第安运动的“斗士精神恢复了成千上万被打败的人的身份和骄傲,激发了复兴垂死语言和垂死文化的尝试”。[3]XXIV对生活在黑暗之中无助的印第安人民而言,这些年轻的斗士们让他们看到了黎明的曙光,是他们文化复兴最富有战斗性的倡导者,是他们“绝望中最后的希望”。[3]39
和许许多多的印第安斗士一样,印第安运动组织苏族领袖莱昂纳德从小就目睹族人遭遇的苦难,他继承了疯马和坐牛等先辈们的精神,为所有的印第安人寻求正义,带领印第安人走上了争取自由和平等的道路。在被关押迫害的漫长日子里,莱昂纳德仍然为所有印第安人民的生命、自由、平等、尊严、主权和未来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他著书为自己辩白,控诉美国政府的行径,呼吁所有人能够倾听他们全体族人发出的呼喊声:“我们的声音,我们集体发出的声音,我们如鹰般的哭喊声,才刚刚开始被听到。我们向全人类呼喊:听听我们吧!”[11]52他告诫他的族人不忘几个世纪以来印第安人民、文化和地球母亲所遭受的耻辱和不公正,“当压迫者成功地进行非法盗窃和掠夺时,这是所谓的殖民主义;当他们的殖民企图遭到抵抗时,就叫战争;当被殖民的人民站起来反抗和自卫时,我们却被叫作罪犯”。[11]52
马修森在调查中发现,在莱昂纳德被定罪后不久,连他的检察官都承认唯一声称目睹他参与杀戮的证人的证词毫无价值,证人本人后来也否认了这个证词,声称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签下了那份宣誓书。[3]XX但他依然被定罪,在没有任何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莱昂纳德被定罪关押的事件遭到纳尔逊·罗利赫拉赫拉·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等全球开明人士的强烈谴责和抗议,他们呼应着佩尔蒂埃的诉求,对审判的公正性进行质疑,要求重新审判、还他自由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但无一奏效。诚然,在今天的美国法庭上,印第安人拥有公民的法律地位,但事实上正如马修森所言,任何熟悉印第安人生活的人都可以证明,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保留地,对印第安人来说,“正义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随机的和任意的。尽管我们对其他国家的人权压制高谈阔论……但偏见和迫害仍在继续”。[3]XXII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莱昂纳德是否有罪对美国政府及其执法机构来讲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局都想让他消失”,[3]469因为他是印第安人“自由精神的象征……这是一种灵魂里的精神,是一种愿意放弃生命的精神”。[3]490美国女作家海伦·亨特·杰克逊(Helen Hunt Jackson)曾在《百年耻辱》中呼吁美国政府能够“从百年的污点中挽回美国的名誉”。[12]然而当年的美国政府并没有赎回美国的名誉,相反,马修森指出,这耻辱以“更阴险,更狡猾的”[3]XX方式又持续了一百年。时至21世纪20年代的今天,已是高龄的莱昂纳德仍然被关在监狱中。
莱昂纳德·佩尔蒂埃事件并非只是印第安人的事件,也不是已成往事的历史事件,而是当今美国社会更大故事的一个缩影。诚如莱昂纳德的顾问、美国前司法部长拉姆齐·克拉克(Ramsey Clark)所指出的,莱昂纳德·佩尔蒂埃事件是几百年来印第安人遭受美国政府“持续的不光彩的统治和压迫的象征”,只要莱昂纳德还在监狱一天,“我们这个伟大国家的每一个公民都有可能受到同样赤裸裸和傲慢的不公正”。[11]1
结 语
美国历史是一部不断向西开疆拓土的西进运动历史。在很多人心目中,西进运动就如同一部史诗,移民就是抒写史诗的英雄。这些英雄移民们在饥饿、寒冷、热浪、疾病、野兽等种种恶劣环境中征服荒野、战胜自然的精神成为开拓精神而被广为称颂。今天,坐落在黑山地区的拉什莫尔山国家纪念公园(Mount Rushmore National Memorial Park)正是美国西部扩张之丰碑和“昭昭天命”之见证,屹立在山上的四座美国总统(华盛顿、杰斐逊、林肯、西奥多·罗斯福)头像是美国建国、发展和强大的象征,代表了“美国的自由……是美国民主的神殿”。[13]然而,对苏族人民而言,“你的神殿是我的坟墓”。[3]XL美国这个国家的自由和民主是建立在违背契约、夺取印第安人土地、屠杀印第安人民、消灭动物种群、剥夺印第安人自由的基础之上的。这四座建立在他们圣山上的头像对他们而言是一种侮辱和亵渎,不仅侮辱了《拉勒米堡条约》的契约精神,也亵渎了苏族人民心目中最神圣的地方。巨大的雕塑高高地摆在那里,在苏族人看来就如同白人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时刻趾高气扬地提醒他们并向他们宣告:“因为我们的身体更强壮,我们的人口更多,我们的技术更进步……所以我们是征服者。”[3]XL
《疯马精神》是目前唯一一部全程关注并详细记录莱昂纳德·佩尔蒂埃事件的作品。马修森虽然出生在白人精英阶层,但他能以一个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从白人中心主义的藩篱中跳出,对印第安人的苦难遭遇深表同情。在经过大量走访调查后,他从印第安人的视角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带领读者走进苏族人民的生活,聆听他们百年来为保护土地与美国政府之间展开的长期斗争,肯定了他们为正义和自由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展现了百年来美国政府对他们的一系列政策造成他们一步步地走向边缘、走向没落、走向消亡的命运,揭示了一个以全球人权、正义卫士自居者的真实面目,以此唤醒美国人民的良心和正义。遗憾的是,直至2014年马修森去世时也没能看到莱昂纳德获得自由,但相信他的作品会让任何一个有良知有正义感的美国人在欣赏黑山上的那四座头像时能心怀愧疚,重新审视美国的进步神话,意识到这个国家是以牺牲印第安人和自然世界为代价换来的,直面并反思美国历史和社会黑暗的一面,帮助印第安人走出困境,还他们以自由和正义。《疯马精神》不仅对于人们了解和研究苏族人历史,纠正对苏族人的刻板、负面形象,还原苏族人的真实形象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在各种欺骗、暴力、种族歧视和种族偏见依然充斥着美国社会的今天,《疯马精神》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关于囚掳叙事具体参见金莉:《西方文论关键词:囚掳叙事》,《外国文学》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