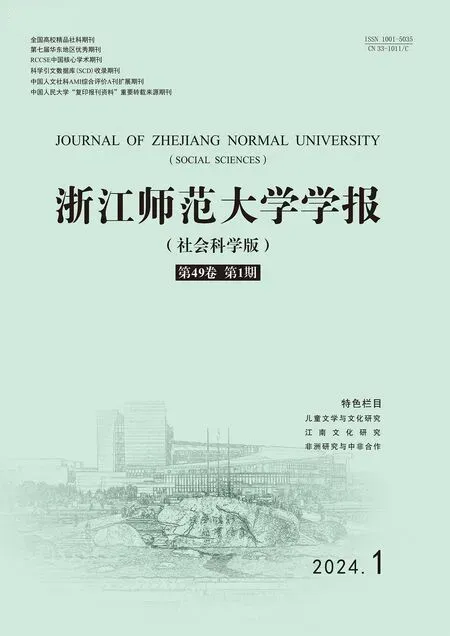自由主义文人对左翼作家的审视
——以徐志摩和邵洵美的《珰女士》为中心
余 凡, 卫俐米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1931年,徐志摩根据左联五烈士被捕事件,胡也频锒铛入狱后丁玲和沈从文四处奔波求助的真实经历以及自由主义文人仗义相助的相关文坛掌故等,构思创作了别具意味的现实主义题材小说《珰女士》,连载于《新月》月刊。不幸的是,徐志摩未及创作完成,就突然坠机而亡。1935年,邵洵美决定在承续徐志摩创作思路和理念的基础上对《珰女士》加以衍生和演绎。《人言周刊》1935年第2卷第11期发表邵洵美的《徐志摩的珰女士》一文,文中说明徐志摩的小说《珰女士》是因为他被朋友的故事感动而作。随后,《人言周刊》第2卷第11至14期重刊了徐志摩所作的《珰女士》的原文,第2卷第15至40期刊载了邵洵美的同名续作,题目旁小括号内注“徐志摩未完稿,邵洵美续”。[1]邵洵美续作基本延续了前作的基本主旨并有所发挥和拓展,突出对“营救胡也频”事件的演绎。徐志摩的前作,讲述蘩因从事革命活动而被捕入狱,蘩的妻子珰与好友黑四处奔走打探消息。其间,珰遇到了曾对她有好感,如今不择手段登上高位的崔,他口口声声说顾念旧情想要帮忙,实则趁机劝蘩自首并供出战友。故事最后以珰女士奔走无果、极度疲累之下陷入噩梦为止。邵洵美的续作,接续徐志摩未完稿的时间线和人物故事,讲述珰女士自噩梦中惊醒,强撑着再次出门打听消息的故事。珰女士先去找了诗人廉枫求助,热心的廉枫不仅曾借钱给黑用以营救并准备将蘩和珰女士的稿子出版,为其筹措经费。两人谈及她向当时的文坛领袖周老头求助的情景,周老头端着架子,尽说空话,不肯伸出援手。之后,珰女士与黑交流白天打探到的消息,两人在患难与共中暗生情愫。然而未及细谈就听说与蘩同行的三位同志已经受刑的消息,于是珰和黑顾不得私人情谊便再次外出求助。珰女士再次找到廉枫,求他帮忙打电话求证消息。最终,小说在珰女士和廉枫两人略带暧昧的交谈和联想中再次戛然而止。
《珰女士》是一部充满趣味的述录社会事件、笑谈文坛掌故、描写20世纪30年代初文坛作家的小说。“珰女士”暗指丁玲,“蘩”暗指胡也频,“黑”暗指沈从文,“云”暗指冯雪峰,“周老头”暗指鲁迅,“廉枫”暗指徐志摩,“辛雷”暗指邵洵美,“崔”暗指某国民党要员。可见小说涉及多位文坛著名作家,展现出自由派文人徐志摩和邵洵美的人道主义情怀,也从侧面反映出20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的复杂价值选择和审美趣味。《珰女士》这部小说的出现有着重要的时代背景。20世纪30年代初复杂而多变的时代政治和文化语境,赋予文学流派与文学社团以特殊的多元、歧义、暧昧的形态。《珰女士》这部作品的外在故事和内在影射所呈现出的暧昧态度,正是这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动荡的时局所迫,走出象牙塔后,在十字街头摇摆不定、左右为难的境况的真实写照。《珰女士》的发表有着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它是徐志摩作为小说家的重要代表作,代表着徐志摩创作上的重要转型,即一反过去被读者广为熟知的浪漫与唯美风格,转而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带有强烈的鞭挞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意味。
本文试图从《珰女士》的创作历程、现实影射和细部历史的考证出发,通过文史互证及对小说的纪实与虚构处的细致辨析,探究自由派文人与左翼作家之间的人道主义情谊、话语权争夺和爱国主义立场下的不同理解,考察包括徐志摩、邵洵美在内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左翼作家的态度及其思想根由。进而,为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思想史和自由派文人的复杂面相,增添史料案例上的脚注。
一、小说故事的原型印证与阐释
1931年1月17日,胡也频在参加会议时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逮捕,这是《珰女士》一书的写作背景。1月18日,胡也频从狱中给沈从文捎来一张字条,嘱托他向胡适和蔡元培求救。此时,胡也频已经与徐志摩有意疏离且久未联系,但沈从文还是“请徐志摩、胡适之先生代为介绍吴经熊,并去信南京中央研究院,请蔡先生同杨杏佛代为探听下落”。[2]157徐志摩交友广泛,他的交友圈虽以新月派作家为主,但与左翼作家也有些交情,1930年,他就曾介绍茅盾与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史沫特莱相识。由徐志摩主持的新月书店同时出版了部分左翼作家和文学研究会成员的作品,如胡也频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圣徒》(1927年9月版)便是由新月书店出版的。作为编辑的徐志摩遵循自由主义的原则,主张靠文艺说话,十分注重培养文学新人,徐志摩和胡也频及丁玲之间的交往便始于此。据梁锡华的《徐志摩新传》记载:“胡也频是沈从文的好朋友,最先向晨副投稿时还是个学生。徐志摩对他印象不深,对他也绝不如对沈从文之赏识。”[3]183可以说,徐志摩与胡也频之间的交往最初是借由沈从文这个中间人和《晨报副刊》这一桥梁,但从艺术的角度来说,徐志摩对胡也频的作品并非十分赏识,这与双方创作观念之间的差异不无干系。反倒是对于丁玲的作品,徐志摩和邵洵美都颇为赞许。邵洵美在续作《珰女士》的前言中更是坦言,徐志摩见到会写文章的人总爱。并进一步指出,平常人写小说,尤其是新文人,太讲意思忽略了故事,而珰女士却能够把事实展览出来,反而更精彩。[4]这就从艺术的角度肯定了丁玲早期作品的艺术价值。作为一个文坛上的新人,胡也频还是受到了徐志摩的提携,不时有作品出现在《新月》月刊。但是,如果就此认为徐志摩对胡也频施以援手是因为沈从文的关系或者徐胡之间的私交就太过表面了。因为胡也频在1929年前后加入了地下党,并自此和徐志摩断绝了来往。[3]183但徐志摩还是为了营救胡也频颇费周折,动用了不少人脉,远超两人的交情。
《珰女士》的创作与当时的时事密切相关,这一点在真实史实的发生时间和出版日期的对照中便可窥得端倪。有关《珰女士》的初版日期,论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①据笔者所搜集的资料,可知徐志摩的《珰女士》最初刊于1931年《新月》月刊第3卷第11期,第57-73页,文末注“未完”,但此后未再刊登,从创作和出版的时间来看,1931年1月17日胡也频被逮捕,2月7日被秘密杀害,但此时消息并未放出。2月7日至9日期间,沈从文和丁玲还在各处奔波,设法营救胡也频。2月9日沈从文在邵洵美处探得胡也频被枪决的消息,直至2月10日,丁玲和沈从文才得到胡也频已遇难的确切消息。同日,徐志摩的《珰女士》已在《新月》刊出。从时间线上便可以看出这部小说是徐志摩出于对胡也频一事的关心所作,以小说的方式对此事作出的一个及时的回应。
邵洵美作为徐志摩的好友不仅目睹徐志摩创作的始末,还是《珰女士》故事原型之一。谈及续写的缘由时,邵洵美称:“珰女士自身的故事比她写的文章更动人。”[4]足见其对丁玲为人为文的认可。因而,可以说这部小说正是两位作者从人道主义的层面,对作家丁玲的声援。1933年5月14日,丁玲被诱绑失踪,此后传出丁玲被枪杀的谣言。1934年10月,丁玲离开软禁处所,行动比以往自由,可以上街行走邮寄信件。据鲁迅致萧军、萧红的相关信件推断,学界大概是在同年11月传出丁玲还活着的消息。1936年3月,丁玲的小说《松子》初刊于《大公报·文艺》,这是她自被软禁后第一次发表创作。而邵洵美续作的《珰女士》(1935年6月22日起至同年12月14日止)正是在丁玲失踪期间刊发的。
如果说徐志摩与胡也频尚有些交往,邵洵美与胡也频则是互不相识,但他仍愿意搁置立场之间的成见和争议为营救胡也频付出心力。这体现出自由主义文人的人道主义立场和文人之间的惺惺相惜。沈从文曾为胡也频一事去找邵洵美帮忙,邵当即一口答应,并立即去寻国民党在上海市的党部负责人刘健群,要求他放人。[5]96然而,虽经多方斡旋,最终营救仍不幸失败。1931年2月7日深夜,上海南郊的龙华监狱接到南京政府的密令,突然提审23名“东方旅社事件”的“案犯”,并当即枪杀,其中就包括年仅28岁的胡也频。时为胡也频之妻的丁玲才生下孩子不久,她为胡也频痛心的同时又担心自己受牵连,一时间身心俱疲,生活难以为继。热心的徐志摩知道此事后,不顾危险相帮筹措救助经费。小说中说廉枫预备联系书店经理将珰女士夫妻的书稿高价卖出。事实正是如此,1931年5月,新月书店冒着风险出版了丁玲的小说集《一个人的诞生》,内收胡也频两篇,丁玲两篇。但因时局险恶,不便公开胡也频的名字,只署了丁玲的名字。此外,徐志摩又为她向邵洵美借了一千元。这与邵洵美在续作中所写的廉枫同情上门求助的珰女士,给好友辛雷打电话帮忙借钱的小说情节相吻合。沈从文《记丁玲续集》中的文字也与此相印证:“在那时她恰好得徐志摩先生帮忙,向中华书局卖了一本书,得了一点钱,又从邵洵美处借了一笔钱,我又从朋友王际真先生处收到了一笔钱。”[2]191而借钱给沈从文的这位朋友王际真也是经徐志摩介绍相识的。可以说,幸得徐志摩等人的帮助,沈从文和丁玲两人才得以离开上海,将丁玲的孩子即胡也频的遗孤平安送回丁玲的老家湖南常德。
在邵洵美的续作中,谈及以徐志摩为原型的人物廉枫的政治倾向时,他说:“诗人有的是同情,谈到政治也一样。”[6]现实中徐志摩的态度和故事里的廉枫相契合,“他的同情不分阶级,他时常会发出矛盾的理论,你不能向他要求判断,因为他总偏心于那求援的一方面:你要帮助,他会贡献他全部的身体和灵魂”。[6]这较为符合当时以徐志摩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文人对左翼作家的真实态度。左翼作家对于社会不公的愤慨和对弱者的同情与自由主义文人一直以来秉持的人道主义精神是相通的。可见,徐志摩的思想是复杂的,不只有诗歌中所呈现的“浪漫”,还有对底层人民群众的深切关怀。
二、徐志摩的人道主义与邵洵美笔下的“周老头”
《珰女士》是在真实事件的基础上加以演绎、以当时文坛几位著名文人为原型虚构而成的小说,在叙录真实事件的同时,还有虚构的成分,而虚构的文字,恰恰最能体现出作者对文坛事件和社会事件的态度和心境。
在徐志摩前作中,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和同理心,不惜笔墨对珰女士的心理活动进行了大量的描写。徐志摩运用传统的白描手法,对革命战士蘩和国民党要员崔进行了比较。小说中,珰女士眼中的崔身居高位,掌握着生杀大权,嘴上说着交情,当朋友求助时,却趁机落井下石,实施报复,不仅不肯相助,反而想诱导他们背叛革命。相对的,革命者蘩虽然一无所有,惨遭迫害,身体困极饿极,声若游丝,但心里仍想着斗争,“拏定了主意非得用血肉去拼出一条路来”。[7]本着知识分子的精神,徐志摩借珰女士之口指出舍己为人的革命者和卖身求荣的无耻之徒人格上的高下之分:“珰女士对蘩总存着一些敬意,觉得为这样的人受苦牺牲绝不是无意义的。所以当她看到崔通过无耻地卖身,卖灵魂,最后卖朋友,得来权财地位时,她只是格外夸奖自己当初准确的眼力,不曾被崔造作的热情所诱惑。”[7]在《珰女士》中,针对以胡也频为原型的革命者蘩被捕一事,徐志摩说:
这世界,这年头,谁有头脑谁遭殃,谁有心肠谁遭殃。就说蘩吧,他倒是犯了什么法,作了什么恶,就该叫人直拉横扯的只当猪羊看待……自从那年爱开张了他的生命的眼,他就开始发动了一种在别的地方或别的时间叫作救世的婆心。见到穷,见到苦,他就自己难受;见到不平,见到冤屈,他就愤恨。这不是最平常的一点人情吗?[7]
可以看出,徐志摩认为蘩,即现实中胡也频的所作所为是出于对苦难者的同情,肯定了他们革命活动的合理性。这无形中契合了作者在1925年发表的《列宁忌日——谈革命》一文中的观点:“实际有革命努力的,也不问他走的是正路是小路是邪路,也是值得赞赏的,总比在势利社会里装鬼脸的强得多。”[8]徐志摩认为,不问政党派别,思想来源,“只要它动活,精力开始往外用,自然会有走入正道的机会……它迟早有用对的一天”。[8]这说明徐志摩在看待知识分子时,是从知识分子的道义与堕落,即干预和关注现实的勇气以及责任担当的角度进行评判,而非按照党派区分文人。
徐志摩的前作对革命战士蘩所表现出的理解和尊敬正是现实生活中他对待左翼作家的真实态度的体现。但小说中也同时指出了蘩的固执、激烈和愚笨,并自称没有在任何一件事上和他完全一致过:“我不服他的理解,但我知道他的心是热的。我不信他的福音,但我确信他的动机是纯洁的。”[7]这段文字从侧面反映出他们彼此之间思想观念方面的差异仍是无法跨越的,徐志摩对革命者的献身和牺牲仍持有质疑,这与他在生活中对待革命者的态度相契合。
邵洵美的续作,在承继前作主旨的基础上,掺进了更多个人的情感和主观的想象,尤其体现在小说中对于以鲁迅为原型的周老头事件的增补、误读和演绎上。邵洵美在续作中认为,蘩为了革命赴死的举动,与其说是理智的支配,不如说是情感的冲动,并因此将革命者的矛盾和热烈,归结为气愤而起的反应。在邵洵美看来,胡也频他们的这种牺牲是因愤慨于社会的不公,同情于弱者的艰辛所引起的一种情感上的冲动。[1]沈从文在《记丁玲续集》中也认为促成胡也频转变的,只是一种南方人单纯勇往的热情,并非出于理智的抉择。然而,由丁玲《记一个真实人的一生》中提到胡也频从狱中托人递出的最后一封信中的内容来看,胡也频不仅声称自己不会投降,还嘱咐丁玲不要脱离左联,应该靠紧他们。因此,自由主义文人笔下所说的左翼作家的革命行为是出于非理智的冲动是有失偏颇的。
邵洵美的续作,最为重要且令人质疑的地方是塑造了“周老头”这一隐喻鲁迅的人物形象。续作中,珰女士在饥寒交迫之际,坐了一个钟头的电车去向周老头求助,周老头却只是不慌不忙地把她晾在楼下等着,好容易等到周老头下来,珰借机向他说了蘩的事情,他却在不急不缓间摆足了架子:“他在桌上的盒子里拿了支烟,塞在自己嘴里,划了五根火柴才点着,闭上眼抽了几口,就拔出来捏在手里……”[9]当珰女士向他求主意时,他只说:“这办法倒难想。”[9]周老头甚至还将革命者比作煤块,说要炼成金子,谁都免不了牺牲的这一天,言语间尽是推诿。文中通过对话描写对其只说不做的态度表示不满。邵洵美在表现珰女士面对周老头时心里的所思所想是用对话的方式直白地说出来的。如:“我心中顿时起了一种忿恨。谁愿意自己做了煤块,炼得金子让他享受?为什么他自己不做煤块?”[9]邵洵美在续作中用“文化同盟主席”“绍兴师爷”“身材小”“气量小”“好骂人”等字眼形容周老头,暗指鲁迅。这段借由珰女士之口说出来的对周老头的牢骚更多的是在表达作者邵洵美自己对鲁迅的不满,带有意气用事的成分。
邵洵美借《珰女士》对“鲁迅”的丑化,有着早期的积怨在其中。贾植芳曾在回忆录中提到,邵洵美在狱中极度困窘之际,恐时日无多,曾嘱托过两件事,其中一件便与鲁迅有关,邵洵美说他的文章均由自己亲自执笔,而非鲁迅所批评的请人捉刀代笔。[10]可见,邵洵美对于和鲁迅之间的论争始终耿耿于怀。邵洵美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认为文学是属于“有产的少数人”,对一些清贫文人表现出质疑和轻蔑的态度尤使鲁迅不满。在《拿来主义》中,鲁迅用“富家翁的女婿”暗讽邵洵美的钱是娶了盛宣怀的孙女不劳而获得来的,这场论争后来被文学界称为“盛家赘婿案”。由此就可以理解邵洵美为何在续写《珰女士》时,以鲁迅为原型,用尖酸刻薄的语言塑造了周老头这样一个人物形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珰女士》中,有关周老头的一段文字的最后说道:“我在想周老头儿这人也可怜。”[11]其中隐含着作者邵洵美对周老头的同情与理解。他看到周老头浑身是恨的背后反映的是对于社会的不满和难以改变的无奈。在民族危急存亡、当局昏庸残暴之际,每个人都自身难保,同为文人的邵洵美意识到个人在大时代下的无力,最终对周老头予以谅解。
三、爱国主义下不同立场的弥合
将《珰女士》置于整个20世纪30年代的场域中来看,表面上是时局将这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推向了同情左翼的立场,实际上是他们所共同拥有的改变时局的强烈渴望造成了这一切。换言之,不同文学观念和价值立场的作家,在面对爱国主义这一话题时,他们的言论方向和行为的取向是一致的。在民族危亡之际,共同的爱国情怀弥合了各派文人之间的观念差异。此外,1927年国共合作的失败使得阶级政治和斗争进一步激化和明朗化。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同情革命、理解革命的同时也意识到自己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所带来的身份认同的危机。正当这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彷徨于十字街头不知何去何从之时,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使得他们的幻想破灭,无形中将其推向了与左翼为友的立场。现实生活中的徐志摩和邵洵美同样心系家国,在国难当头愤慨激昂,不惜直斥当局,为祖国献心出力。
徐志摩曾于1918年8月31日在赴美留学的轮船上,写下慷慨激昂、豪情万丈的《民国七年八月十四启行赴美分致亲友文》:“诸先生于志摩之行也,岂不曰国难方兴,忧心如捣,室如县磬,野无青草,嗟尔青年,维国之宝,慎尔所习……诚哉,是志摩之所以引惕而自励也。”[12]徐志摩怀揣着“实业救国”的抱负留洋海外且自比为中国的汉密尔顿,在纽约期间还因书架上有介绍苏俄的书被叫作鲍尔雪微克(即布尔什维克)。[13]在日本人制造的“济南惨案”中,国民党军队的不抵抗,激起了徐志摩的不满,他在日记中不无愤慨地写道:“日本人当然是可恶,他们的动作,他们的态度,简直没有把我们当作‘人’看待……有血性的谁能忍耐?”日记中进一步将矛头指向当时的上层统治者:“但反过来说,上面的政府也真是糟,总司令不能发令的,外交部长是欺骗专家,中央政府是昏庸老朽的收容所,没有一件我们受人家污辱的事不可以追原到我们自己的昏庸。”[14]直指当权政府的昏庸无能。早在1925年,在《血——莫斯科游记之一》一文中,徐志摩就说过:“我不敢批评苏维埃的共产制,我不配,我配也不来,笔头上批评只是一半骗人一半自骗。”[15]对于当时的革命青年,他说:“我决不怪你们信服共产主义,我佩服只有骨里与髓管里有血的人才肯牺牲一切,为一主义做事;只要十个青年里七个或是六个都像你们,我们民族的前途不至这样的黑暗。”[15]可见,徐志摩虽然对苏俄的共产主义思想持质疑的态度,但对当时国内信仰共产主义的青年人肯做事、敢牺牲的精神却抱有极大的理解、支持和称赞。尤其是在民族危亡之际,他更是肯定了只有这样的青年人,才能使我们的民族走出黑暗。
这一点在小说中也有所体现。在徐志摩的《珰女士》中,蘩是一位以笔为戈、为消除世间不平而战斗的革命者形象:
他一个人伏处在没有光亮四壁发霉的小屋里不住笔的写,写他眼里见到的,心里感到的,写到更深,写到天光,眼泪和着墨,文字和着心肠一致的热跳。直写到身体成病,肺叶上长窟窿,口里吐血,他还不断的写——他为什么了?他见到种种的不平,他要追究出一些造成这不平世界的主因,追究着了又想尽他一个人的力量来设法消除,同时他对于他认为这些主因的造成者或助长者不能忍禁他的义愤,他白眼看着他们正如他们是他私己的仇敌——这也许是因为他的心太热血太旺了的缘故,但他确是一个年青人,而且心地是那样的不卑琐,动机又是那样的不夹杂,你能怪着他吗?[7]
这段描写使人不由得想起徐志摩在《猛虎集·序》中的一段文字:
我觉得我已是满头的血水,能不低头已算是好的。你们也不用提醒我这是什么日子;不用告诉我这遍地的灾荒,与现有的以及在隐伏中的更大的变乱,不用向我说正今天就有千万人在大水里和身子浸着,或是有千万人在极度的饥饿中叫救命;也不用劝告我说几行有韵或无韵的诗句是救不活半条人命的;更不用指点我说我的思想是落伍或是我的韵脚是根据不合时宜的意识形态的……这些,还有别的很多,我全知道;你们一说到只是叫我难受又难受。[16]
一个是积劳成疾、肺里长窟窿、口中吐血的蘩;一个是满头的血水却仍不肯低头的徐志摩,两者都在为世间的苦痛与不公而痛心,都在用笔做着无力又坚韧的抗争。小说与散文互文,两段文字的高度一致使人不得不怀疑,作者是在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文中的年轻人是故事中的蘩,也是故事外的胡也频和现实生活中的徐志摩,一个自由主义作家与一个左联作家在小说中重合,达到思想上的高度一致。换言之,徐志摩在小说《珰女士》和诗歌散文中共同建构起一个多元的、思想理念博杂的、文学性的“徐志摩”形象。
徐志摩在小说中写到珰女士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一个风雪中孤独又悲苦的妇人,她的孩子被饥寒折磨而死。这与他的诗歌《盖上几张油纸》中所描述的景况相一致。早在《先生!先生!》《叫化活该》和《谁知道》等诗中,徐志摩就曾描写过衣衫褴褛的乞讨者的惨状;在《拜献》中,诗人更是想进一步,“给宇宙间一切无名的不幸,拜献他胸肋间的热”。[17]在1929年3月5日致泰戈尔的秘书——英国人恩厚之的信中,徐志摩揭露和批判了国民党统治下民不聊生的惨状。同年在散文《秋》中,他认为正是统治者对百姓的残酷剥削,使得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乞讨者的惨状是徐志摩在硖石东山下独居时亲眼所见,它在诗人敏感细腻又富于同情的心中始终挥之不去,时隔几年又重新出现在他的小说作品中。徐志摩对处于贫困中的弱者所具有的同情可谓是贯穿了他创作的始终。
在邵洵美的续作中,当廉枫意识到蘩的政治倾向时,劝他拿定主意,走了就别停。虽然政见不同,但廉枫对蘩的这种选择整体上持一种理解和支持的态度。而对于蘩这个人物,邵洵美也是颇为赞赏的,文中说“你看他为了社会的不平,愿意牺牲”,因为“推动他的力量是爱,不是恨”,[1]因此“他也许愿意饿死不愿意让人当猪当狗”。[6]小说字里行间流露出的认可表明,邵洵美认为革命者蘩的所作所为是勇敢的、正义的行为,是在为他人可以吃饱饭而作出的牺牲。可见,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看来,但凡是对国家和社会有利的行为都是值得称赞的。
邵洵美也有着一腔爱国的热血,日军入侵之际,他一改此前反对艺术为政治服务的观念,主动用手中的笔和自己掌握的出版资源,不计成本、不顾危险地为宣传抗日做贡献。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时代画报》停刊,邵洵美随即投入抗日的行列,与好友创办宣传抗日的《时事日报》。1934年,邵洵美在《人言周刊》的创办缘起中自述道:“在这一个内忧外患频起的时代,情感丰富的人,都愿意停止一切个人的追求而把身体灵魂献给国家,平素曾说要把文学艺术作终身事业的,现在大半对政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18]分析这一转变背后的原因时,他说:“无非为了生活不得安定,精神不得聚会,要想牺牲一些工夫,俾合力来造成一个太平的环境。”[18]这一段吐露心声的自白无疑是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爱国情怀的缩影。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在孤岛这一特殊的环境中,邵洵美以宣传抗日为己任,于1938年9月1日创办刊物《自由谭》。该刊“具有强烈的控诉情绪和激昂的鼓动力,真实地录下了中国人民慷慨悲壮的抗日斗争”。[5]182-183除办报办刊外,他还曾与蔡元培、杨杏佛、邹韬奋等29位上海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联名致电国民党当局,强烈抗议其特务秘密绑架丁玲和潘梓年。不仅如此,邵洵美还曾在《自由谭》上发文盛赞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并帮助女地下党员将该文的英译本在海外传播。可见,在民族存亡之际,即便是与左翼作家针锋相对的自由主义文人也会放下党派之争和私人成见,在共通的爱国情怀之下,尽可能地予以理解和帮助。
结 语
探究徐志摩和邵洵美创作《珰女士》的根由,一个强烈而直接的原因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复杂而激烈的社会语境,其中隐含着他们对于改变当下时局的一种期待。尽管成长环境、教育背景、文学趣味和阶级地位的差异使得自由派作家和左翼作家在文艺创作方法和政治道路选择上存在分歧,但强烈的爱国情怀,对弱者的同情和悲悯以及对于当局造成的社会不公的愤慨又使得他们能够在民族危急存亡之际搁置成见,相互帮助,相互扶持。《珰女士》在邵洵美这里,亦是“未完成”的。邵洵美曾在《人言周刊》上刊登“为停刊《珰女士》启事”,启事中称《珰女士》原计划是分为三部长篇大作,但最终未能完成。结合20世纪30年代复杂的社会语境和文坛处境,邵洵美续作的“未完成”是一种必然。其一,《珰女士》原本就是干预社会、述录文坛事件的作品,当后续的社会事件、文坛事件并未出现新的、有讽喻意义的发展方向时,《珰女士》就没有了继续写下去的现实来源和素材支撑。其二,从邵洵美角度来说,他心思活络,除创作外,还同时进行着编辑出版等工作,由于时间精力的原因,他留下了许多残作,《珰女士》未写完也属正常。而续作写于丁玲失踪期间,当时社会上流传她已遇害的谣言,所以邵洵美才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在文中虚构珰女士向周老头求助一事,并大肆铺写珰女士和黑、云及廉枫之间的暧昧情愫。尽管邵洵美认为这是丁玲大爱的一种体现,但是根据丁玲此前并未准许邵洵美为她作传及否认徐志摩所写的《珰女士》以自己为原型一事可以推断,丁玲本人对此并不认可。因此,当丁玲摆脱软禁,再次公开露面后,《珰女士》作为影射小说与现实之间的裂缝无法弥合,创作也就难以为继。
注释:
①费冬梅的《“诗坛双璧”与一篇小说——从〈珰女士〉说起》中认为《珰女士》“刊于《新月》月刊第3卷第11期,1932年,具体出版时间不详”。黄红春的《新月派“自由主义”思想管窥——从〈世纪与义务〉和〈珰女士〉谈起》中认为《珰女士》“于1931年9月发表在《新月》第三卷第9号上”。此外,《珰女士》还收录于邵洵美的《贵族区:小说卷》,该书认为“1930年《新月》月刊第3卷第11期刊载徐志摩所作小说《珰女士》,未完”。中国文史出版社2022年版的《轮盘》文末注《珰女士》“原载:民国二十年一月十日《新月》第三卷第十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