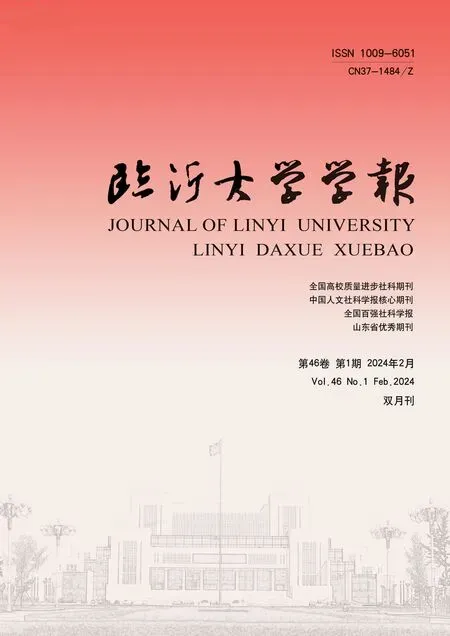荀子的“性恶”是“心恶”还是“欲恶”?
——从《正名》与《性恶》的张力说起
叶 晴
(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84)
主流观点认为,荀子的人性论是与孟子相对的“性恶论”,而善的来源是“化性起伪”。此外,对于荀子的人性论,也还有性朴论、性向善论、性恶心善论等不同的说法。①对于荀子人性论的不同界定,实则与“性”在此处的概念定义相关,因此不同的人性论实际上是“混淆荀子不同说法之间的理论分际所导致的结果”[1]。由于“性”的定义在荀子那里是变化的,说“性恶”其实过于宽泛,“恶”的具体来源有待进一步澄清。 因此,荀子学说中“恶”的来源究竟是什么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根据对“恶”之来源的不同认定,学者在“性恶”的基本结论下也发展出了不同的解释。
一般认为,就《性恶》篇看,荀子所说“恶”的来源是“情欲”,而“情欲”属“性”,所以是“性恶”。 但是从荀子的《正名》篇看,也有学者认为是“心恶”,“心”才是导致恶的根源。[2]61-62因此,对荀子的人性论形成了许多不同的看法,本文试图从《正名》和《性恶》的分析出发,去探究荀子“性恶论”的实质究竟是“心恶论”还是“欲恶论”,对“恶”之来源的澄清,亦有助于我们重新辨析当前对荀子人性论的各种界定。
一、《正名》与《性恶》的矛盾
在《正名》篇中,荀子对“欲”和“心”的作用做出了大量的论述。
有欲无欲,异类也,生死也,非治乱也。欲之多寡,异类也,情之数也,非治乱也。(《荀子·正名》)
在这里,荀子指出有欲无欲、欲的多寡,都不是治乱的原因。 在指出了“欲”与治乱无关后,荀子紧接着指出了“心”的作用:“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从所可,所受乎心也。所受乎天之一欲,制于所受乎心之多,固难类所受乎天也。 ”(《荀子·正名》)也就是说,“欲”是天生自然的存在,而人所追求的东西,是“心之所可”决定的。
故欲过之而动不及,心止之也。 心之所可中理,则欲虽多,奚伤于治? 欲不及而动过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则欲虽寡,奚止于乱?故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荀子·正名》)
荀子进一步指出,“心之所可”才是治乱的根源,如果“心之所可”中理,那么即使多欲,也可以达到治;如果“心之所可”失理,那么即使少欲,也会导向乱。 然后荀子得出结论说:“故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 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虽曰我得之,失之矣。”(《荀子·正名》)也就是说,治乱的关键是“心之所可”,而不是“欲”,所以人要从“心之所可”去追寻治乱的根源,而不是从“欲”去追寻。
从荀子在《正名》这一段的论述逻辑看,荀子的大致意思是说,“欲”之有,“欲”之多寡都是天生自然的,治乱与天生之“欲”没有关系;而“心之所可”决定了人的行动,“心之所可”是否合理,是治乱的关键,所以“心”才是治乱的根源和责任主体。 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去理解《正名》中该段的内容,则采取行动真正的动机力量在于“心”,是“心之所可”产生了行动,“欲”只是被“心之所可”选择的理由,“心之所可”既可以抑制“欲”,也可以产生不同于“欲”甚至超出“欲”的行动,则在人的行动中“欲”并不独自具有动机力量。 比如宋晓竹(Sung Winnie)就认为,在“欲不待可得,而求者从所可”中“求”的主语或者说发出者并不是“欲”,这里并不是说“欲”是自然的,而现实中“欲”去“求”什么要根据“心之所可”对“欲”进行选择后由“欲”作为行为理由去发动,这样就是把“心”作为一个关卡,决定“欲”是否被允许追求其对象,然后“欲”在通过这个关卡后去“求”。宋晓竹通过引入“欲虽不可去,所求不得,虑者欲节求也”和“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把“虑”“求”和“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这一句关联分析,她认为,“虑”是“心”选择“情”作为行动理由,那么“情”只是“心”所要考虑的一个要素,它自身不能激发行动,只有“心”才能直接激发行动。由此,“心”才是动机的真正来源,在这里“心”具有追求欲望对象的自然倾向,它本身是好利的,“心”才是造成“恶”的原因。“恶”不是因为“心”在行动中没有制衡“欲”,而是“心”对“欲”给予了不正确的权衡,并选择了错误的行动。也是“心”发动了行动,而“欲”自身不具有动机力量,它仅仅是为“心”提供了可供选择的欲望对象,那么“恶”的来源自然就是“心”而非不具有动机力量的“欲”。[3]
宋晓竹的看法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这一观点能够使得《正名》这一段的内容得到一个非常融洽的解释。 “欲”是“不待可得”“所受乎天”的存在,那么“欲”就是天生自然之人的一个结构要素,但是这个“欲”是静态的,而“心”才是动态的,“心之所可”在“欲”的基础上选择欲,或者不选择欲,“求”是由“心之所可”发出的,“心”成为行动真正的发动者。
许多注家对这一段的解释,也呈现出把“欲”作为静态的结构,而“心”作为一个动态的行动力量的倾向,并认为“心”才是“恶”的根源。比如冢田虎说:“所受乎天,谓生而具乎性之欲也;受乎心者,谓感物而动以求之也。言人未感物则其欲一而不分也。至于感物而动,则从耳目鼻口,而求者多也。从耳目鼻口,而所受乎心之求多,则所受乎天之一欲为之而制,而不能一焉。 故所受乎心与所受乎天,亦固难类也。 ”[4]921也就是“心”感物而动,所以才会产生了诸多的“求”,而“欲”即使是“一”,也不能够阻止“心”产生这么多的“求”。郭嵩焘也说:“生之有欲,一而已矣。 制于所受乎心之多者,以有欲之性听命于心,而欲遂多纷驰,而日失其故,漓其真,则与所受于天之一欲,又不可以类求也。 ”[4]921他虽然没有说“欲”是静态的,但是也承认“欲”是因为听命于“心”所以产生了过多的求,那么“心”就是使得欲望放纵的根源,而“欲”本身只是“一欲”。 如果“故欲过之而动不及,心止之也。 心之所可中理,则欲虽多,奚伤于治?”这句话中“心”是止“欲”还是“心”直接止“动”不明确,那么在“欲不及而动过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则欲虽寡,奚止于乱?”这一句中,“欲”既然不及,“动过之”和“乱”的责任主体似乎就只能是“心”。 总而言之,《正名》这一段中,“欲”似乎是一个无善无恶的存在,而善恶都是“心”的行为带来的后果,如果“心之所可中理”,“心”会导向治,也就是善;反之,就会导向乱,也就是恶。 从对《正名》的分析看,荀子的人性论就应该是“心恶论”。
但是,这显然与我们一般所认为的荀子性恶论中恶的来源是“欲”的理解不一样。 荀子在《性恶》篇中指出“乱”和“恶”的责任主体是“欲”:“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 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 ”(《荀子·性恶》)荀子在这里指出人生来有好利恶恶之性,有耳目之欲,顺着这样的“性”,则会导致乱,显然在这里荀子所论恶和乱的来源是好利恶恶的自然欲望、情感,在这里“性恶”其实是“情欲恶”。 那么“欲”才是导致恶的根源,而“心”反而是化性起伪、导向善的根据。
于是,根据上文的分析,在《正名》和《性恶》两篇中就对于“恶”和“乱”的来源是“心”还是“欲”就产生了矛盾。 那么,到底是“心”还是“欲”才是“恶”的原因呢?
二、“心”“欲”与“性”的关系
为了调和荀子《正名》和《性恶》中“恶”和“乱”的来源是“心”还是“欲”的矛盾,我们似乎需要重新解释“心”和“欲”及其与“性”的关系。首先,一个基本的共识是“欲”是属于“性”的:“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 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 ”(《荀子·正名》)“性”是生之所以然者,“情”是“性”的内容,而“欲者,情之应也”(《荀子·正名》)说明“欲”是“情”的表现,二者可视为一义,而情既是性,故欲也是性;同时“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 ”这说明“欲”也是天生自然的,则“欲”自然是“性”的内容。 如果按照《正名》中“心”的行动可以超出天生自然的“欲”而独立去行动,而把“性”理解为“情欲”,那么就是说“心”是独立于“性”的另一个结构要素,从行动的激发上,“心”大于“性”/“欲”的范围,既能够选择已有的情欲的活动,又能够单独产生超出天生自然的欲所追求的行动。但是荀子的“心”是一个独立于“性”的存在吗?荀子在《解蔽》篇指出:“凡以知,人之性也。 ”也就是说,能够知的“心”,也是“性”的一部分。 在《性恶》篇则有:“然而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 ”荀子把“知”和“能”作为质具,而“知”“能”的能力都属于“心”,则此处质具当属“心”;从此处荀子的表述看“涂之人……皆有”,也就是说,这是人人皆有的普遍内容,即质具蕴含了生而有、天之就的意味,那么此处质具又似乎属性。
总的来看,“心”本身也是“性”的一部分。[2]54-56从“性”作为“生之所以然者”看,“性”可以被作为一个包含“心”和“欲”的广义的范畴,而从《性恶》看,导向“恶”的“性”,应该是“性”作为“欲”的狭义的性,那么“性恶”说的实质就是“欲恶”说;但是从《正名》看,导向“恶”的“性”,就似乎是指涉“性”作为“心”的那部分内容,如此“性恶”说则成了“心恶”说。如果按照这种理解,心和欲都小于广义的“性”的范畴,心恶和欲恶确都可以说是性恶,进而“化性起伪”既可以说是“化心”,也可以说是“化欲”,但“恶”的根源仍然没有办法确定。
再回到《性恶》看荀子对乱的来源的论述:“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问题或许在于“顺是”指的是什么,如果为“顺是”添上一个主语“心”,那么就是说“心”顺“欲”,所以会导致混乱,那么是不是就可以和《正名》相容,把“心”作为责任主体呢? 但问题是,在这里即使说是“心”顺是,其顺是的内容仍然是“欲”,这无非是说,“心”没有作为,而放纵了欲望,导致了乱;则似乎“心”只是没有积极的作为,但是“欲”仍然是“乱”的主要原因。
考虑到“心”是否总是能够积极地发挥认知作用,我们可以参考荀子在其他地方论及“心”的内容:
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 (《荀子·王霸》)
故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声而声乐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妇女莫众焉,形体好佚而安重闲静莫愉焉,心好利而谷禄莫厚焉。 (《荀子·王霸》)
若夫目好色,耳好听,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 (《荀子·性恶》)
“心”自然有和“欲”追求一样对象的倾向,同样是“好利”的。而“心”本身是属“性”的一部分,既然“心”和“欲”都是“性”的内容,它们就其本来倾向而言具有一致性是完全可能的。 从“心”作为天生的官能,作为“性”的一部分而言,“心”的功能是知,但是知并不一定会导向理性、正确的认知,从而选择或抑制欲望。 也有在知没有合于理的前提下,“心”和“欲”保持一致,“心”放纵了欲望。 如果从这一点出发,“心恶”说应该是在指责“心”没有能够积极作为,从而正确地抑制和选择欲望,而不能说“心”错误地作为。如果承认这一点,对《正名》篇我们可能作出不一样的解读。
在《正名》中,荀子指出“心”的作用是征知:“心有征知。 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簿其类,然后可也。”也就是说,在耳、目、口、鼻、形等感性经验的基础上综合这些经验,心能够知。 可见“心”的认知能力是建立在对感官经验的主宰和统筹之上的裁决、判断,如果“心”没有在感性经验基础上进行统合、征知,那么后果就是耳、目、口、鼻等感性经验在行动中占据主宰力量,此时“心之征知”就失去效用。 而耳、目、口、鼻的感官经验,正是原始欲望放纵发展出具体欲望的渠道,所以天生之“欲”的变化和放纵就和耳、目、口、鼻等感官能力相关。 “欲”或许是天生自然的,多寡有定数,但是因为人同时有感觉经验的能力,这个本然的“欲”是动态变化的:“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 ”(《荀子·性恶》)“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荀子·王霸》)这都说明,本然的“欲”是可能经过耳、目、口、鼻之感觉作用而发展出复杂的具体欲望的;又比如,在“空石之中有人”的例子中,荀子说:“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觙。其为人也,善射以好思。耳目之欲接,则败其思;蚊虻之声闻,则挫其精。 ”(《荀子·解蔽》)当“耳目之欲”接,则会扰乱他原本的思绪,可见由于人的感官作用,“欲”是动态变化的结构,而非静态的结构。
荀子说:“故欲过之而动不及,心止之也。心之所可中理,则欲虽多,奚伤于治?欲不及而动过之,心使之也。 心之所可失理,则欲虽寡,奚止于乱? 故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 ”这里的“欲”指向的是天生自然的人的本然之欲,如果本然之欲过多,“心”这个关卡就能够制止过多的欲望,选择合理的欲望,产生合理的行动;而在“欲不及”的时候,“心之所可”由于失理,因此没有起到去抑制这种“欲”的作用,反而由于“心”在耳、目、口、鼻经验基础上没有“征知”做出理性判断和权衡,放纵了原始的欲望,发展出了不同的具体欲望而产生了过多的行动,那么“欲不及而动过之,心使之也”,就不是说“心”使“动过之”;“使”是表示心的消极不作为,使得原本“不及的欲”演变出了过度的行动。 在这里“心”的关卡作用没有做好限制本然欲望泛滥的拦截作用,本然欲望就可能在接触到经验世界之后导向泛滥的具体欲望,走向错误而混乱的行为。
按照这种解释,“心”只是一个关卡,但是导向乱的根源还是在于“欲”。“心”在这里不是恶的来源,它不具有独立的动机力量,行动仍然是由“欲”发出的,“心”至多是“欲”的“帮凶”,因为它没有发挥理性认识的功能,而使“欲”按照其本来的倾向发展甚至被放纵。 所以“心之所可失理”时“心”并非错误的作为而导致了“乱”——“心之所可失理”指向的是“心”的消极面,是“心”不作为,没有好好地发挥“征知”的作用,仅仅扮演着消极的角色,被感觉经验牵着走,其所知“失理”,它顺着本然好利之“欲”的方向,和“欲”同流,导致了现实中欲的泛滥和行动的过度。则“欲”始终是乱的根源,而荀子强调“治乱”之在“心”,是突出“心”对“欲”的监察、管制作用,如果“心之所可中理”,心能够有效地监察、抑制不当的欲望,从而导向治;如果“心之所可失理”,心没有发挥好作用,则“欲”顺着原本的倾向发展就会导向乱。
在这里,“心”具有主动的选择能力,那么如果“心”没有选择善而是放纵了欲望,则“心”确实对“恶”负有道德责任,正如东方朔所指出的:“荀子言性恶之目的原不在讨论‘自然之恶’,而在说明道德之恶,但道德之恶预设了责任概念,而责任概念又预设了选择自由。 ”[2]51所以,就道德责任而言,“欲”和“心”在导致“恶”上都具有道德责任,二者都应该视为道德失败的责任主体。但“心”的不作为并不代表“心”自身是“恶”的,“欲”是激发行动的动机力量,则“恶”的来源仍然是“欲”,直接说“心恶”,把“恶”的来源强加给“心”,让“心”成为“恶”的根源,反而把“欲”作为是天生自然,无善恶倾向的存在,这又有所不当,亦会使得对《正名》的理解和《性恶》难以相容。
综上所述,荀子所言的“欲”之多寡是天生自然的存在,但是“欲”在这里不是生而静态的不变的结构,而应该是在人的经验过程中可变的动态结构。“欲”可以产生“求”,表现为一种感物而动的动态心理结构:“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本然的“欲”都是有所求的,因此“欲”是动态的,会产生具体的欲求和相应的行动。②而本来多的欲可以减少“欲过之而动不及”,本来寡的欲也可以变多“欲不及而动过之”。 前者需要“心”的积极干涉,而后者是“心”不作为下“欲”的自然发展倾向。这里有受之于天的“本然欲望”和人活动过程中“具体欲望”的分殊[5],后者本于前者,既可能是被“心”选择的结果,也可能是“欲”不被干涉下在经验变化下发展的结果。③
从这个角度理解“所受乎天之一欲,制于所受乎心之多,固难类所受乎天也”,则“心之多”可能并不是指“心”发动了超过“欲”的过多的行动,而是说“心”的思虑之多,正如杨倞解释这句为:“一欲,大凡人之情欲也。 言所受乎天之大欲,皆制节于所受心之计度,度心之计亦受于天,故曰‘所受’。 ”[4]921李涤生也认为:“‘天之一欲’、言出于先天之性的欲,是盲目的自然反应,它不管可与不可。如‘饥而欲食,寒而欲煖’,人人皆然,故曰一。‘心之多’:言心之思虑是多方面的。‘欲’一而已,而所欲有可有不可,可之中又有轻重、缓急之分,这些都须要心的思虑、计度,故曰‘心之多’……‘难类所受乎天’者,言出于天性的欲既受制于心,故行为和欲望难以相类似。”[6]也就是说,“心”如果积极发挥思虑的功能,那么自然的“欲”就会被心所节制,按照“心之所可”发展为恰当欲望,而非按照本然的欲望去行为。 由此,“心”就应当被视为节制欲望的关卡,而不是把“心”理解为产生恶的根源。
在这里,基本上还是“性大于心”,也就是“心”是从属于广义的“性”的一部分,“心”如果不积极地作为,发挥其能够“征知”的积极作用,那么“心”的“知”就仅仅是根据耳、目、口、鼻之欲的方向去走,此时“心之所可失理”,“心”认可的就是“欲”本身的内容,“心”就没有起制约欲的作用。 其实“失理”下的“心”就是被“欲”牵着走,从而本然欲望在接触到经验世界后就表现出具体的欲望,表现出不当的行动,这是乱的根源。而这与《性恶》中的“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 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便可以对应,“顺是”也就是顺着本然欲望自由地发展,“心”的关卡失效了,所以就导致了乱;而如果“心”的关卡发挥着作用,“心”是通过“征知”的能力在感官经验的基础上去知理、知道的,此时“心”能对本然欲望进行抑制、选择,引导人去追求一些合于理、合于道的东西,比如“礼义”,这就是“伪”的产生。在这个意义上,心对治了顺是而为恶的欲,因此可说是“以心治性”;但若就“性”作为广义的“性”而言,此时是“以心全性”,“心”的积极作为和原本的“欲”形成了内部的张力,使得“性”按照心指引的积极方向发展。 而“化性起伪”中“性”就不可以等于“心”,这里不是说“心伪”是建立在自我转化的基础上,而是把“伪”归属于“心”,而“化”的对象则是“性”,但此处是广义的性还是狭义的性,则仍然不能确定。
三、“心”具有独立的动机效力吗?
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说,“乱”和“恶”的主要根源还是在于“欲”,心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没有积极作为,但是并不能说“恶”是心产生的。而反过来,“善”和“治”则是因为“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感官经验进行了主宰、统筹的“征知”,知理下的“心之所可”可以对欲进行抑制和选择,从而产生符合“理”的行动。还未解决的问题在于,当“心之所可”发挥积极作用时,“心之所可”是否独立于欲具有动机力量,因此可以攻克欲望,独自产生动机和行动;还是“心之所可”仍然是对欲进行选择,或者转化欲而产生了具体的欲望,从而产生了行动?
在“欲不待可得,求者从所可”中,如果“欲”和“可”的方向是一致的,那么心只是在原本欲的基础上进行选择,然后“求”来自那些合理的欲,此时“求”的产生者应该还是“欲”,这里的意思是说,欲是天生具有的,而欲能否追求其欲求的对象,则需要“心之所可”作为关卡进行判断。但是,如果“欲”和“可”的方向不一致,“心之所可”这道关卡可以变成发动行为的动机本身吗?“求”的主语是“欲”还是“心”呢?在荀子《正名》篇中所举的生死的例子里,可以看到“可”和“欲”之间的对立:“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恶死甚矣;然而人有从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此时“欲”作为本然之欲,是欲生恶死的,而“心之所可”则是“从生成死”,那么在人选择“死”的情况下,“心之所可”是否作为一个独立的动机存在,并且攻克了“欲生”的“欲”呢?仅从这一句看,“可”与“欲”似乎是处于一个对立的位置中,那么“可”与“欲”应该是独立具有动机力量,在一些时候“心之所可”攻克了欲,而使人的行为走向合乎道的方向。 所以,“心之所可”导向“治”和“伪”,是心攻克欲望作为行为的动机,还是欲望被心转化构成行为的动机,是另一个存疑的问题。在“化性起伪”的解释里,既可以说“性”是广义的性,包含着心,心伪对治了欲,所以能够化“性”,让“性”跟随心的方向而非欲的方向;也可以把“性”理解为作为欲的狭义的性,而说心转化了欲便是“伪”。
根据上文的分析,“欲”应该不是一个静态的存在,而是动态的存在,那么在“心之所可”产生的积极行动中,仍然可能有“欲”的参与。此时“欲”经过“心之所可”合于理的认知,从原本的欲转化为和“心之所可”方向一致的欲望,此时“欲”既是欲,也是“心之欲”。这更符合儒家“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道德理想,“欲”是“心之所欲”,二者方向便是一致的。正如荀子所指出的:“故浊明外景,清明内景,圣人纵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夫何强?何忍?何危?故仁者之行道也,无为也;圣人之行道也,无强也。 仁者之思也恭,圣者之思也乐。 此治心之道也。”(《荀子·解蔽》)圣人、仁者行道,不需要强迫,不需要作为,而就是“纵其欲”“兼其情”的结果,那么圣人的“欲”“情”和“心之所可”与“道”本身就是方向一致的,而非是以“道”为标准的“心之所可”去压倒情欲而勉强作为。
回到《正名》中讨论心与欲关系的第一句,即:“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无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凡语治而待寡欲者,无以节欲而困于多欲者也。”这句话的意思是,“治”的根源不在于“欲”的有和多,而“治”也不需要“去欲”和“寡欲”,因为欲的有无,欲的多寡都是先天的,无法改变的;“治”所需要的是“道欲”和“节欲”。 在这里,“心”去“治”的功能在于“道欲”和“节欲”,而非“去欲”“寡欲”,心的作用并不与欲形成对立,而是在于转化、引导原有的欲望,或者节制过度的欲望。这都意味着,“心”的作用是相对于“欲”而言,“心”不是要代替“欲”成为动机,而是对“欲”进行加工,使得“欲”成为合理的动机,产生合理的行为。 也就是说,“心之所可”是在原始欲望的基础上转出了新的欲望,这个欲望是合于理的欲望。转出的具体欲望可能是服务于原始欲望的“工具性”欲望,但随着实践的发展,其便能转化为“非工具性”的。[7]所以“化性起伪”应该是指“心伪”能够转化“欲”,而“化”不是指原来的“欲”消除了,“化”意味着在“伪”的基础上基于原来的“欲”转出具体的“欲”,后者是基于前者的“化”。
结语
本文的首要目的是证明“欲”自身是具有动机力量的,从《正名》和《性恶》的调和解释看,“欲”仍然是导致恶和乱的根源,此时“心”顺从了“欲”,没有发挥关卡的积极作用。但是,“心”仍然可以积极作为,因此它是治的根源也是伪的根源,是人能从“性恶”走向“善”的依据。 说“心恶”是不公允的,在“心”积极作为的情况下,“心”是善的;即使在“心”不作为的情况下,恶的来源仍然是“欲”。
“心”似乎总是对于“欲”发挥作用,而非独立具有动机力量,“心”虽然是治和伪的根源,是善的依据,但是“心”总是在对“欲”进行转化、选择和抑制的前提下发挥自身积极的作用。所以,“欲”仍然是唯一的动机力量,“心”只是理性认知对“欲”进行监察、选择的关卡,自身不具备独立的动机力量。
同时,本文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荀子人性论的各种不同观点。 “性恶论”的主张是由于把“性”作为狭义的“情性”“欲”去理解,而由于情欲之放纵是恶的根源,故可以说是“性恶”。 “性朴论”的主张,则可以从静态天生自然之性去理解,本然的“欲”和“心”作为静态的结构,是无善恶的,所以是“性朴”。 “性善论”则是把“性”理解为“心”,由于“心”的积极作为会导向善,所以“性”包含了善的倾向。各类对于荀子人性论观点的分歧,是由于荀子论“性”时候的模糊性,而使得对“性”的解释有不同的可能。但是总体而言,广义的“性”包含“心”和“欲”,所以问题的根源是寻找“恶”和“善”的根本来源和责任主体,以界定学者论“性”时的不同论域,辨析不同说法的合理性和局限性。
注释:
①戴震、陈兰甫、罗根泽、李经元、梁启雄、劳思光、傅佩荣、刘又铭、路德斌等,均在不同程度上认为荀子思想中包含有弱的性善说。 (廖晓炜:《性恶、性善抑或性朴:荀子人性论重探》,《中国哲学史》2020 年第6 期)儿玉六郎在《荀子性朴说的提出———从有关性伪之分的探讨开始》(《日本中国学会报》1974 年第26 辑)、周炽成在《荀子人性论:性恶论,还是性朴论》(《江淮论坛》2016 年第5 期)以及林桂榛在《关于荀子“性朴”论的再证明》(《临沂大学学报》2018 年第1 期)等文章中均指出荀子主张性朴论。人性论的不同观点根本在于对荀子所用“性”的界定不同。 对“性”的性质的不同看法本文不做详细分析,而把这些问题化约到寻找“恶”的主要来源和善的根据的问题上,解决了这一问题,某种程度上便能分别对应荀子人性论的不同观点。
②“欲”应该是“求”的发出者,“求”是本然欲望在经验世界中产生的倾向,是具体的欲望,因此“求”不应该和“欲”割裂来看。 “心”的功能是去对“求”进行约束,本质上其约束的对象是本然欲望发展的具体欲望。
③哈根指出,荀子讨论“欲”的时候,“欲”意味着我们基本的自然欲望,这是我们与生俱来不会改变的。 例如荀子写道:“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荀子·荣辱》)这和《正名》中荀子对“欲”是生而自然的描述一致。但哈根指出,对具体事物的欲望和人的基本自然欲望是紧密联系的,对某物的欲望有自然欲望的基础,具体欲望又是由经验和推理协调的。 尽管基本的自然欲望是不变的,但是一个人的具体欲望可以因为他有了新的经验或者更多的理性思考而发生变化。 荀子说的性恶,是因为自然欲望缺少理性的引导,会产生问题,但是荀子并不认为自然欲望可以改变,而是在此基础上用心的理智加以引导。 本文对本然欲望和具体欲望的区分,与哈根对“欲”的看法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