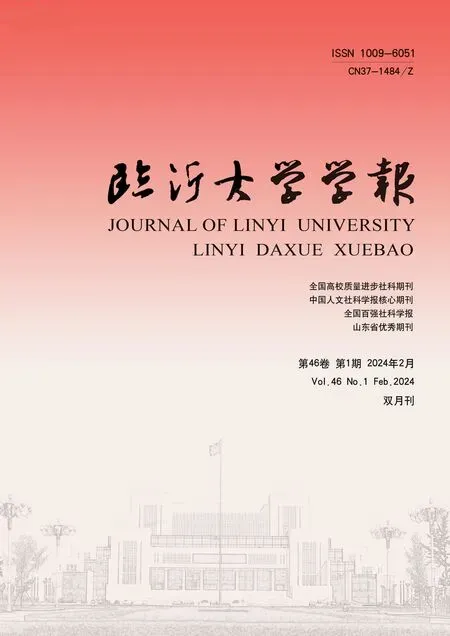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2023 年工作会议暨“天山廊道与中外交通”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马 悦
(上海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234)
2023 年11 月11 日,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2023 年工作会议暨“天山廊道与中外交通”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大学顺利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主办,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承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厦门大学、集美大学、兰州大学、暨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新疆大学、苏州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宁波工程学院、上海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30 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本次学术研讨会以“天山廊道”为主题,围绕中外关系与多语言文献、中外交通与文化交流、天山廊道与西域治理等学术议题展开讨论。天山廊道是指以天山山脉为主体,包括天山南北两麓绿洲、内部河流、草甸等所形成的沟通东西、贯穿南北的交通廊道。 这一地区是中国古代族群交流最活跃、贸易往来最繁荣、文化交流传播最频繁的地区之一,在中外交通和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次会议主要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重点探讨和论述。
一、中外关系与多语言文献
中外关系是本次会议的关键议题,学者们就中原经西域的对外交流、中原与北方草原的文明互动以及东西方的海外交流等进行了深入探讨。 其中,多语言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作为记载中外关系发展的重要资料,引起了与会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西域是中原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郑炳林在《敦煌:西汉与西域间交融的都会——基于敦煌出土文献的考察》一文中,以敦煌汉简为切入点,梳理总结了汉代以敦煌为中心的对外交流。文章论证了敦煌是汉朝与西域经济、物种交流交往之地,促进了华戎之间的商贸往来和物种引进;也是多种文化交融之地,儒家思想、佛教、三夷教等宗教思想及艺术风格都经此东西传播;更是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基地所在,保障了中原王朝在经营西域过程中获取主动权。
天山廊道是中原经西域开展对外交流的重要路径。 上海大学历史系张安福在《天山廊道视域下古代文明互鉴研究》一文中,以天山廊道为重点,介绍了天山廊道的地理环境和交通路线概况,指出天山廊道是中古时期欧亚大陆文明互鉴的桥梁,也是中华文明不断吸收融合外来文化和中华文化西传的重要路径。文章从长时段、多角度分析了天山廊道作为“民族走廊”“交通走廊”“文明走廊”,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形成,并在亚欧大陆物质文明、精神文化交流互鉴的过程中发挥着永动机的作用。直到现在,天山廊道仍是中国同中亚、西亚和欧洲等地加强交往的陆上枢纽。天山廊道族群流动的文明互鉴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机制,为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与提升中华文明的全球影响力提供了历史借鉴和路径选择。
关于中原与北方草原的文明互动。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白玉冬在《叶尼塞河畔的中华文明——以孔子为例》一文中,通过对镌刻于唐代三乐镜残片上的E77 叶尼塞碑铭进行释读与分析,认为铭文中记载的人名应为“孔子”,并对比古藏文史料中有关孔子形象的记载,推测镌刻孔子之名的物件被铭文作者视为“男儿的护佑物”。 该铭刻最有可能在黠戛斯与唐朝保持联系的840—866 年之间流入叶尼塞地区,侧面体现了华夏文化在当地的传播。文章对中华文明沿草原丝绸之路向北发展的足迹进行了追寻,弥补了这一领域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乌云高娃在《从〈华夷译语〉“来文”看明朝与四夷的贡赐品》一文中,梳理了从宋元到明清时期朝贡贸易的变化,指出朝贡贸易中贵金属币商品化和奢侈品化的倾向,并从洪武本12 篇鞑靼“来文”入手,分析了《华夷译语》中记载的四夷贡品及其地方特色,指出在与女真部的朝贡贸易中,明朝多以折物的方式给予回赐,少数情况下也会赏赐银两。 上海大学历史系舒健在《再论真金》中,对传统观点中真金是汉化蒙古人的看法提出了质疑。 他对真金的人际网络与来往事迹进行了梳理,认为真金的人际网络实则包括汉人、蒙古人及八思巴,真金与阿合马的斗争更多的是出于政治目的,而不是汉化与色目化的斗争。 舒健认为,真金不仅仅是汉文化的代表,更是多元族群文化交流的代表。
东西方的海外交流也是中外关系研究的重要议题。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宋燕鹏在《19世纪马六甲青云亭亭主再研究:以碑刻和祭祀簿为中心》一文中,以青云亭为具体案例探寻马来西亚华人历史,重新考证了青云亭的历任亭主及其任职时间,并且对亭主制度的组织架构进行了介绍。 宋燕鹏认为,马六甲甲必丹和青云亭亭主与明清时期知县一级的基层职官相似,其下里长负责维护地方统治秩序、处理乡党人纠纷等大小事务,总巡负责治安。 这种制度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明清时期地方政权组织的模式。暨南大学中外关系研究所刘永连在《海疆治理史——一个有待拓展的学术领域》一文中,则从边疆学、南海问题、海洋学和管理学层面梳理了海疆治理史研究现状,认为中国海疆史目前尚未形成一个专门的分支学科,海疆治理问题缺乏针对性和系统性研究。 他进一步指出了海疆治理史有待拓展的三个重要研究空间,即从地方管辖权看国家主权的落实;海疆日常经营、维护与国家主权捍卫;海疆治理体系与海疆的长治久安。海疆治理史有深厚的文献积累基础,为海疆史深入挖掘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海疆治理史在国家战略和海疆治理政策需求的背景下,有着广阔的研究前景。
二、中外交通与文化交流
关于中外交通与文化交流的文章,主要涉及了古代交通、宗教文化、中日文化交流及对外贸易中的茶叶等内容。
关于中外交通的议题,本次会议重点围绕着中国古代漕运发展、农牧交错带的商贸路线及丝绸之路上的地名研究等内容展开。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段伟在《中国古代的漕仓设置与河道治理演变》一文中,认为转运仓的设置中心从关中、洛阳逐渐向东、向京杭运河沿线转移、拓展,表明漕运的处境越发艰难,需要扩大转运仓的分布才能满足王朝政治中心的需求。随着成本上升,漕仓价值降低,漕运最终被海运、铁路所代替。明清两代不计成本发展漕运的措施,实际上滥用了民力,也破坏了沿河地区的生态环境,引发了更深层的社会问题。 苏州大学历史学系王晗在《“边疆内地化”视域下的清代蒙陕农牧交错带商贸路线研究》一文中,通过对蒙陕农牧交错带的毛乌素沙地进行长期调查和研究,从农牧业生产的选择、制度政策影响、蒙汉关系、商贸活动和沙化环境效应等方面入手,梳理出清代中国北方边疆地区内地化的整体发展历程。 这类聚焦于个案的研究,有助于学界更好地理解中央王朝对边疆地区的认知,并形成边疆和内地一体化的理念,从而可以更为准确地把握不同时期中原与边疆地区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上的不可分割性。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孙景超则关注到丝绸之路沿线地名的变化,在《汉唐间丝绸之路上的地名流动及其影响》一文中,他分析了丝绸之路沿线地名多民族、多语言的特点,认为受汉文化的影响,西域地名开始有了相对系统的汉语译音,形成了较为固定的对应汉字;部分地名具有了汉语语境下的审美和释义,或含有正向意义的译名;经典地理文献也吸收了西域新发现的山水地名。与此同时,西域地名随着族群的迁徙进入中原,具有“地随族迁”“地随人动”的特点。地名流动体现了各民族文化在特殊历史场景下的相互结合,反映了多民族文化的兼容和互补,证明了西域自古以来多民族杂居的历史事实。
宗教文化是中外文化交流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贤劫四佛信仰的兴起与发展》一文中,上海大学历史系陈菊霞认为,贤劫四佛信仰源于释迦信仰,其兴盛的原因一方面与贤劫诸佛的济世思想有关,信仰贤劫四佛可使人寿转增,脱离小三灾之苦;另一方面与“梵行久住”的崇高理想有关,贤劫四佛制戒、说戒使僧团健全,从而得以久住正法。 大乘佛教兴起后,贤劫四佛在从千佛拓展至三劫三千佛的过程中发挥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是千佛体系过渡阶段的特殊产物。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陈大为在《叶尔羌河流域的宗教遗址调查与研究》一文中,通过对叶尔羌河地区汉唐时期佛教遗存的实地走访,介绍了莫尔佛寺、塔什库尔干石头城、三仙洞、棋盘千佛洞、喀群彩棺墓葬、吉尔赞喀勒墓地等多处宗教遗址的保存现状,并分析了汉唐时期叶尔羌绿洲祆教、景教、摩尼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多元宗教汇聚的情况。
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陈广恩在《日用类书在日本的流传及其影响——以〈事林广记〉为考察个案》一文中,分析了《事林广记》在日本流传的情况,并总结了其流传方式主要有收藏、抄写、刊刻、引用等。他认为,《事林广记》能够在日本广泛流传,主要原因在于中日文化联系密切、内容贴近生活、主要刻地福建的地理位置优越以及学者研究的客观需求。《事林广记》等日用类书籍对日本社会的教化方面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为研究中日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媒介。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赵莹波在《日本唐房地区中的宋商文化》一文中,围绕宋代日本九州地区所形成的“唐房文化”,分析了这种文化形式在九州地区的三个发展阶段:唐朝萌芽期——修船补给阶段、宋朝发展期——留守妻子阶段、宋朝形成期——墨书瓷器阶段。唐房聚集了多重身份的宋商、日本入宋派遣僧、偷渡僧、宋商的日本留守妻子和混血宋商等,周边也因此形成了特殊的汉文化圈。
此外,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康健在《茶文献整理再出发——〈近代茶文献汇编〉序言》一文中,谈到茶叶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对世界历史产生的重大影响。尽管茶文献整理难度较大,但随着茶文化热度的增长,茶文献研究仍具有巨大的潜力。
三、天山廊道与西域治理
在本次会议中,天山廊道与西域治理的研究引起了与会学者们的热议。 他们从天山廊道的东西联防、天山廊道视域下的西域认知、中原王朝对天山廊道的经营以及天山廊道的交通与军防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关于天山廊道与河湟地区的东西联防问题。在《“勤王”与“拓边”:唐代河湟地区迅速失守的主观原因》一文中,宁波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张弘毅指出,唐军在河湟地区迅速失守的主观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首先,安史之乱后唐朝为了尽快平息叛乱,征调河陇一带半数以上的边关士卒入内平叛,导致边防空虚,为吐蕃进军提供了可乘之机。 其次,唐玄宗统治后期,唐军在河湟地区接连发动战争,兵员减损严重。 最后,唐朝在湟水谷地、黄河谷地,以及青海湖东、北两岸设置大批军镇、守捉,分散了原本集中于河湟州郡的兵力,削弱了唐军的战斗力,最终导致被吐蕃各个击破。
关于天山廊道视域下的西域认知问题,新疆大学历史学院侯晓晨在《再论隋代的西域范围》一文中,探讨了隋代的西域地理范围。他认为,根据《西域图记序》和《隋书·西域传》的记载,可以大致确定隋代的西域范围。通过分析《隋书》的成书过程、西域与西戎的统一性等方面可知,吐谷浑、党项、附国三国理应属于当时的西域范畴。此外,结合前人对《西域图记》中四十四国复原的商榷,罽宾、西突厥也应归入西域的范围。因此,通常意义上的狭义、广义的西域概念并不适用于概括隋代的西域,隋代官方对西域的认知也并不局限于“敦煌以西、葱岭以东、于阗以北”的地区。
屯垦戍边是中原经营天山廊道的重要方式。 上海大学历史系党琳在《屯戍路径下唐代天山北麓的民族交融研究》一文中,以屯垦戍边为研究视角,认为唐朝对天山北麓的屯田开发,将中原王朝治理西域的战略重心推向天山北麓传统草原游牧区域和中亚七河流域。 该举措为推动农耕与游牧经济的互动交流、多民族的交往交融提供了保障,并突破了汉晋以来中原治理西域的范围,奠定了后世治理西域的基础。至今,这一举措仍然是维护新疆社会稳定的长效机制。
学者们还从不同角度就天山廊道的交通与军防问题展开了讨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杜二雄在《杨和西域征伐史事钩沉——以〈杨公神道碑〉为线索》一文中,根据《四镇节度副使右金吾大将军杨公神道碑》的记载,考证了杨和在西域所参与的包括支援于阗、征伐突骑施和石国等多场重大战役,重点探讨了杨和第三次征伐石国的时间、行军路线以及在行军途中的军事物资补给情况。 文章最后还论及了碑文的书写情况,认为杨和之子杨预的政治地位是杨炎为杨和书写碑文的关键因素。 上海大学历史系马悦在《伊犁河流域军防和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作用研究》一文中,将研究视角放在伊犁河流域,梳理了汉、唐、清三朝在伊犁河流域所设军防机构的发展过程,认为伊犁河流域凭借其区位优势,在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过程中占据着突出地位。 上海大学历史系牛齐培在《唐代西域牢山地望新考》一文中,梳理了学界对于牢山所在地的不同观点,并从弓月道行军的作战地点、行军路线以及里程数据重新考证了“牢山”的具体位置,最后得出牢山位于今新疆也台达坂塔格的结论。
四、学科发展展望
本次学术会议聚焦“天山廊道与中外交通”,关注国家和社会发展需求,旨在认识并总结历史发展规律和经验。会议论文涵盖范围广泛,紧扣学术发展前沿问题,为各研究领域贡献了最新成果。与会专家学者们学术视野开阔,从新史料、多领域、多视角促进了“天山廊道与中外交通”及其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对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近年来,国内外西域史研究不断深入,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自2014 年“长安—天山廊道路网”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后,天山廊道又在族群流动和文明互鉴方面为学界提供了新的西域史研究思路。 天山廊道是中古时期欧亚大陆的“民族走廊”“交通走廊”“文明走廊”,也为中华文明不断吸收外来文化提供了动力源泉。研究天山廊道族群流动和文明互鉴,可以从长时段、多角度探讨中古时期的物质与精神文明互鉴的内在机理和深刻影响。Ѳ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 年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指出,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 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 探讨中古时期天山廊道族群往来互动可以认清欧亚大陆东西方文明互鉴的历史进程,有利于正本清源、正确阐明新疆历史、高度认识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与中古时期天山廊道文明互鉴的关系。 与会专家学者们对天山廊道研究发展也给予了更大的期待。 天山廊道作为多宗教汇集、多民族交流、多元文化交融的关键区域,在东西方交往中发挥了交通枢纽作用,该研究领域扩大了中外关系史的研究范围,从更为新颖的视角阐述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具有广阔的研究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