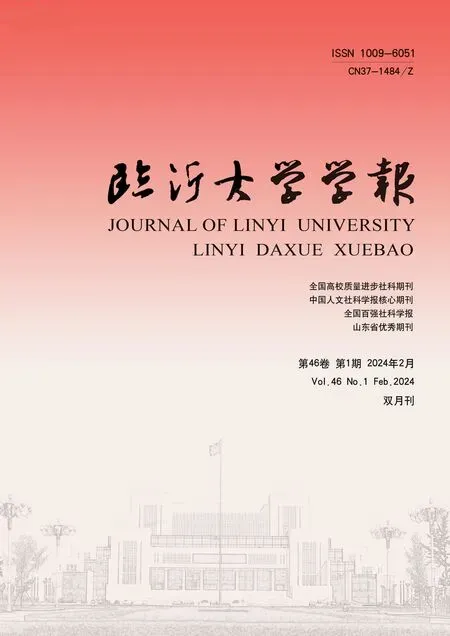中华文化多彩一体和兼收并蓄与中华民族的包容性
王震中
(1.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732;2.临沂大学,山东 临沂 276000)
2023 年6 月2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特别概括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其中,关于“包容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1]习近平总书记概括的中华民族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五个突出特性”,在中国历史上是联为一体的,笔者对此已从五个方面作了初步阐释[2],本文将从中华文化内部的多彩一体、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这两个视角对中华民族所具有的包容性作进一步的论述。
一、中华文化的多彩一体性
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是民族个性,亦是文化特征;既是历史,亦是现实。中华民族的包容性首先是与中华文化的多彩一体性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中华民族的包容性呈现在文化上就是中华文化的多彩一体性。 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中华文化之所以是“多彩”的,一方面是因为中华文化是由包括汉族在内的众多民族文化汇聚而成,它既包括汉文化向边远民族地区的辐射,也包括各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向中央王朝的汇聚;另一方面是因为汉文化本身也是丰富多彩的,而且汉文化的丰富多彩又与汉民族并非单纯的血缘意义上的民族有关,汉民族是以“滚雪球”的方式、经过各个历史时段融合了众多族群而发展壮大起来的民族共同体。 所以,中华文化的多彩一体既因56 种民族文化交融而成,亦有作为核心的汉文化的多彩多源的缘故。 中华文化“多彩一体”的“一体性”,既指它在主要载体上的一体性,又指它在国家文化层面上的一体性。
所谓载体的一体性, 是说中华文化是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汉语和汉字为其载体的,我们现在称之为“普通话”的汉语和规范汉字就是民国时期和新中国初年所说的“国语”“国文”。 当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在建立以郡县制为机制的“大一统”国家时,将小篆作为全国统一使用的文字,使得两千多年来汉字和汉文化既是中华民族的主干文化,亦是国家文化,成为维系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统一的纽带。
一般意义上而言,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幅员辽阔的中国由于各地方言的缘故,使得各地人们交流说话,有的能听懂,有的听不懂。例如,上海话、闽南话、湘西的一些方言,在外人听来简直就如听外语一般。但是,统一的文字——汉字却克服了各地方言的障碍,再加上浩如烟海的典籍图书,使得中国文化的统一性即一体性成为无可撼动的文明特征。 从秦汉到明清,即使在分裂割据时期,政治上是分裂的,而文化上却始终是统一的。 中华民族的包容性特性与中华文化的多彩一体性交互作用,使得中华文明始终丰富多彩地破浪前行。
中华文化的“多彩”与“一体”是辩证的:“多彩”使得中华文化的“一体”丰富且和而不同,和而不同是容许差异性存在的,它为中华文化的不断创新和创造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一体”使得中华文化的“多彩”更有序。 所以,多彩一体的中华文化是在一体性中有主体又多彩多样的文化形态。
中华文化的多彩一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民族融合是密不可分的。中华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表现在文化上则可称为“互化融合”。 历史上,对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而言,每每走上了“汉化”的道路;而对于汉文化乃至整个中华文化而言则应称为“互化”。“汉化”是沿用以往一般历史著述所使用的概念,但实际上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我更愿意使用“互化融合”这样的概念。[3]这里所说的文化的互化,指的是原有的汉文化因少数民族文化的汇入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吸收而发生的改变,与此同时少数民族也逐渐改变着原有的文化,所以是因对方而相互变化。 在中华文化里,既有少数民族汉化的一面,也有各民族文化互化的一面,汉文化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的不断丰富和壮大是互化的结晶。
无论是先秦多元一体的复合制王朝国家时期,还是秦汉、隋唐、元明清的“大统一”时期以及南北朝和五代十国的分裂时期,中国历史上灿烂的文化和文明都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走的是文化互化与文明共建的道路。 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向少数民族学习,通过“胡服骑射”而改变华夏服装和兵种——穿胡服、组建骑兵,就是民族间文化交融互化的结果。《史记·匈奴列传》说:“赵武灵王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4]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不但使赵国的军力和战力迅速提升,变得强大起来,而且还成为古代中国军事和兵种变革的契机。赵国的邻国中山国原本是北方少数民族鲜虞建立的小国,考古发现表明,中山国华夏化的程度很高。 从中山国两座王陵出土的包括青铜礼器、乐器、生活用器、雕塑、以及玉石器、漆器、陶器和青铜器铭文来看,这些物质文化与同时期的赵国、韩国和魏国墓葬出土的文物很相近,具有中原文化的特点,只是一些帐幕构建还反映出游牧生活的痕迹。[5]这说明战国时期北方民族鲜虞所建立的中山国,在与赵、韩、魏等华夏国家长时期的交往过程中,自己原来与中原华夏文化上的差异逐渐消失,走向华夏化道路。 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是华夏的胡化,而中山国则是胡文化的华夏化,二者的变化属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上的“互化融合”。
再以在音乐和文学艺术方面汉文化因吸收少数民族文化而获得发展为例,从南北朝到隋唐在北方流行的所谓“胡歌”“胡乐”“胡舞”“胡戏”最后都融进了汉文化,成为汉文化的组成部分。流传至今的《敕勒歌》,就是北朝敕勒人唱诵的一首民歌,它描绘了辽阔苍茫的草原景象,反映了北方民族的生活和精神风貌,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颗明亮的珍珠。脍炙人口的《木兰辞》创作于北魏孝文帝时期。 它以五言为主的杂诗形式,描写了一位巾帼英雄——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转战12 年,最后凯旋归来,不受封官赏赐,回到故乡的动人故事。它在艺术形象上反映了北方民族妇女的精神面貌和气质特点;在语言文字上,词兼胡汉,“天子”“可汗”并用,是在民族融合土壤上开放的一朵奇葩。[6]北朝的音乐直接影响了唐代的乐曲,唐十部乐有燕乐、清商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其中大多来自北朝的胡汉混合乐。 北方河朔文化和南方的六朝文化一起,构成了唐代高度发达的唐文化的两个来源,隋唐灿烂的文明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 元朝的散曲和杂剧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然而它却是各民族文学艺术交融的结果,是少数民族文化对汉文化影响和对中华文化贡献的又一显例。 不断吸收各民族文化、并通过互化而形成的汉文化和中华文化,其所具有的凝聚力,是因其许多思想内涵和艺术形式具备超越时空的价值而成为人类文明史上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中华民族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
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包容性还表现在外来文化传入中国后被中国化并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明在其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程度的与外来文化的交流和交往,它并不是封闭的,也就是说中华文明并不是关起门来传承发展的。
中华文明在起源和形成阶段,它既是本土的亦是多源的,五帝时代的“万邦”林立就形象地说明了其多源发展,多源经过合流,在夏商西周三代王朝形成了多元(源)一体;在之后漫长的发展中与外界的交往因时而异,但从来不拒绝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只是在吸收过程中很快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例如,关于中国铜器的起源和发展,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早期铜器是由西亚传入的。 其依据是西亚铜器起源的时间远早于中国,中国的早期铜器时代(五帝时代)甘肃青海等西部地区在器物的完整性和发现的数量上要优于中原。尽管这一观点有待于进一步确证,也还没有成为学术界的主流看法,但我们应看到一个事实,那就是从二里头文化时期到西周,即夏商西周三代,中国以礼器和武器为大宗的青铜文化是世界上同时代水平最高、最辉煌灿烂的,而且最独具特色的,中国灿烂的青铜文明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也就是说,即使中国铜器的起源受到西亚的影响,但它却在中国很快地获得创造性发展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进而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朝是中华文明发展到又一历史高度的朝代。我们从美国汉学家爱德华·谢弗的《唐代的外来文明》①一书中可以看到,唐朝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是多方面的,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家畜、野兽、飞禽、毛皮、羽毛、植物、木材、食物、香料、药物、纺织品、颜料、矿石、宝石、金属制品、世俗器物、宗教器物、书籍等170 余种;也有音乐、舞蹈和乐器等。 这些异域的物质文化、奇珍异宝、奇风异俗和异国情调等是由异域商队、使臣、僧侣、乐人、舞伎、胡姬等从海路和陆路带入唐朝境内的。 当时,“唐朝境内人文荟萃,奇货云集……所有的旅游者都将他们本地的各种货物带到了唐朝——或者作为国王的礼物,或者作为销售的商品,或者是仅仅作为他们自己随身携带的附属物品”[7]。大量的外国人,有的居住在长安、洛阳这样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也有的定居于象广州、扬州那样充满生机的南方商业城市。他们在带来物质文化的同时也带来了异样的精神文化,扩展了唐人的精神世界。 包括“遣唐使”在内的各种外国人也会把唐朝的书籍、典章、科技、丝绸、瓷器等带回本国。大唐盛世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辉煌时期,充分显示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
儒释道是中华传统文化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其中,儒和道是中国本土文化,自不待言。而佛教却是在西汉末年传入中国的,但很快就中国化了,成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在中国经历了由与中国本土思想竞争到中土僧人主动到天竺(印度)去学习和取经的演变过程。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原后,在魏晋时期乘儒学衰微的机会,借着玄学去推广佛法,而当时的玄学家也对佛教的“空”“无”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佛教关于“来世”的许诺,使在长期战乱中饱受苦难的人们有了精神上的寄托,从而在底层民众中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佛教在融入中国社会的过程中,中土僧人时有主动西行取经学习的壮举。魏晋南北朝时期,后秦的法显从长安出发,经敦煌一直向西,到达天竺,学习梵语梵文,抄写佛经经律,又到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求经。历时15 年,法显从海路回到祖国,翻译带回的佛经达百余万言,并把自己的见闻写成《佛国记》一书。 唐朝高僧玄奘去天竺游学取经19 年,期间在天竺(印度)讲经说法,获得很高荣誉。 贞观十九年(645 年),玄奘回到长安,带回梵文佛经657 部,他在长安慈恩寺专心译经20 年,对中国的佛教文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玄奘之后还有其他僧人前往天竺(印度)取经,为中印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到了明清时期,佛教寺庙中每每可以看到儒释道三教并存的现象,这都说明佛教文化已与中华传统文化融为一体了。
佛教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在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本身所具有的极大包容力。这种文化上的包容性促进了中华民族内各族的跨文化适应和文化融合。
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在历史上在凝聚人心、吸收外来文明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当代,它不但依旧是中华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的现实土壤,而且还使中华民族文化与时俱进,融入“新科技文明”的潮流中。
注释:
①爱德华·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版。 该著原名为《撒马尔罕的金桃——唐朝的舶来品研究》(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A study of Tang Exotics), 是西方汉学的一部名著,被视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古代文化的必读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