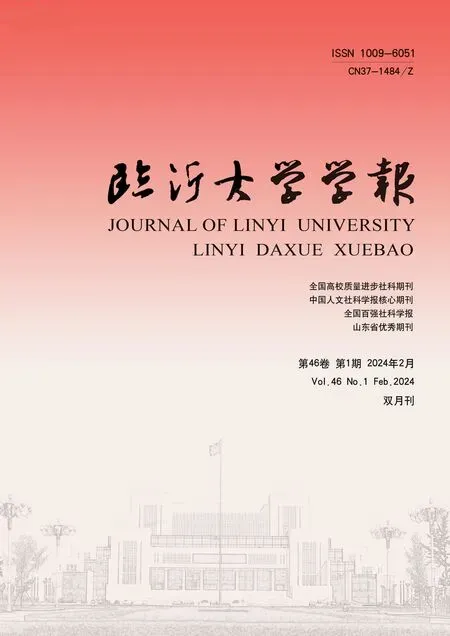共和国教育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现状与反思
李宗刚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共和国教育与中国当代文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随着学界对文学教育重视程度的增加,有关这一课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系列学术成果,相关学者已从多个侧面对共和国教育与中国当代文学间的关系进行了解读。 但是,系统全面地解读两者关系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因此,要深入拓展这一研究,就需要我们对既有研究现状进行必要的回顾,找出深化这一研究的路径。
一
在学界既有的研究中,关于“教育”与“文学”的命题已引起广泛关注。但是,由于二者关系过于密切,人们往往认为二者之间的关系不证自明,反而没有重视对这一关系的探讨。那么,“教育”与“文学”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何谓“文学教育”?对此,有学者作出过如下界定:“何为文学教育?它不是文学与教育的简单相加,它更强调的是由文学自身的特质所产生的育人作用和社会影响,是文学审美特性与教育功能的有机结合。事实上,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教育作用从来都是同时存在的,没有哪一部文学作品只是单纯的审美或单纯的教育。 ”[1]严格说来,在中国文学史“外部研究”的热潮中,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社会与文学的关系等都得到了人们的重视。但是,教育与文学的关系并没有像前两者那样得到应有的重视。结合研究现状可以发现,学界关注较多的是1949 年前的现代教育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并相继出现了一批论文、专著和科研课题,这固然与1949 年前的学校教育与中国现代作家关系密切有着直接的关系,历史的距离也为人们关注这一关系提供了需要的条件。 与现代教育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相对深入的研究现状相比,有关共和国教育与中国当代文学关系的研究便显得不够充分,也缺少具有代表性的成果。 基于此,我们发现,讨论共和国教育与中国当代文学关系的研究大都是在1949 年之前的现代教育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基点上拓展而来的,相关研究者也大都涉猎这两大领域。 胡适作为五四新文学的建构者,曾经留学美国,深受美国现代教育的熏陶,进而确立了现代科学观念,由此对中国文学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为五四新文学的发生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尽管胡适切身体会到了现代教育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 但并没有把这一问题当作自己研究的重要对象,也没有随之进行深入探究。不容否认的是,胡适审视问题的方法无疑为后人继续关注该问题提供了可借鉴的方法,也为后来者探讨这一关系奠定了基础。在胡适之后,陈子展从教育的维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进行过探讨。 但这一探讨并非全方位的,这既与这批先驱者的认知重点不在教育与文学的关系上有关,也与对文学教育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考察更多地侧重于实践层面有关。所以,现代教育与中国现代文学尽管有着直接的关系,但从根本上而言,这种关系与其说是体现在理论思辨层面,不如说是体现在实践层面。实际上,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固然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现代教育始终是最为核心的因素之一——毕竟,不断涌现出来的中国现代作家都是在现代教育的影响下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他们在学校深受现代教育,尤其是国文课程中的现代文以及学校业已开设的作文课程的影响。在现代教育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研究方面,代表性的学者很多,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学者自然非陈平原莫属,这一领域内取得有代表性研究成果的学者还有钱理群、桑兵、沈卫威、罗岗、方长安、张洁宇、姚丹、郑春、李宗刚、高恒文、黄延复、王培元、叶隽、季剑青、张伟忠、王东杰、李文华、杨蓉蓉、刘子凌等。 这些学者从1949 年之前的学校、教育、教师等维度,对现代教育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作了较为深入的解读,这标志着从教育视点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解读已为更多的学者所接受,这对推进该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此后,关于学校教育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不断得到学术界的关注,有关研究课题还得到过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 在现代教育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得到有效展开的同时,尽管共和国教育与中国当代文学关系的研究得到了人们的关注,但其取得的成果远没有前者那么丰厚。 笔者于2023 年12 月5 日以中国知网(CNKI)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为数据源,分别以“篇名”和“关键词”作为检索项,以“共和国教育与中国当代文学”作为检索词,匹配类型为“精确”,时间范围为“2021 年12 月31 日”前,检索结果显示为零;以“关键词”作为检索项,以“文学教育”作为检索词,匹配类型为“精确”,时间范围为“2021 年12 月31日”前,检索结果显示为(篇):2021 年50 篇,2020 年57 篇,2019 年74 篇,2018 年75 篇,2017 年68 篇,2016 年88 篇,2015 年79 篇,2014 年72 篇,2013 年88 篇,2012 年60 篇,2011 年60 篇,2010 年53 篇,2009 年54 篇,2008 年60 篇,2007 年47 篇,2006 年40 篇,2005 年37 篇,2004 年20 篇,2003 年17 篇,2002 年20 篇,2001 年13 篇,2000 年7 篇,1999 年4 篇,1998 年3 篇。 以“篇名”作为检索项,以“文学教育”作为检索词,匹配类型为“精确”,时间范围为“2021 年12 月31 日”前,检索结果显示为(篇):2021 年84 篇,2020 年115 篇,2019 年132 篇,2018 年141 篇,2017 年128 篇,2016 年140 篇,2015 年168 篇,2014 年131 篇,2013 年138 篇,2012 年111 篇,2011 年92 篇,2010 年92 篇,2009 年90篇,2008 年134 篇,2007 年99 篇,2006 年52 篇,2005 年57 篇,2004 年30 篇,2003 年30篇,2002 年23 篇,2001 年32 篇,2000 年21 篇,1999 年18 篇,1998 年15 篇,1997 年6 篇,1996 年10 篇,1995 年3 篇,1994 年1 篇,1992 年3 篇,1990 年2 篇。
在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中,以“文学教育”为关键词和篇名的文献,单就数量来说可谓较少。 其中,2015 年文献为247 篇,数量最高,其他大部分年份停留在100—200 篇;从作者构成的学术背景来看,博士生导师独立署名的文献也不多见。这种情形表明,文学教育作为一种跨学科研究,还没有得到较好的普及,也没有得到高校文科中从事科研的主力军——研究生导师的重视。
目前学界仍缺乏关于共和国教育与中国当代文学真正意义上的研究专著,有些专著仅仅涉及教育与中国当代文学之间的关系,但大都不是专题论述。 2011 年,陈平原出版的《现代中国的文学、教育与都市想像》一书,在“现代中国的大学教育”一编中对“中国大学百年”“当代中国人文学之‘内在兼修’”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但受制于论述需要,其分析阐释并没有突出共和国教育与中国当代文学这一话题;2016 年,陈平原又出版了《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增订本),其中第四章论述了“中文系的使命与情怀——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北大、台大、港中大的‘文学教育’”,但并未上升到共和国教育的层面进行分析;2016 年,陈平原又出版了《六说文学教育》一书,其关键词虽是“文学教育”,但其所论述多是大学文学教育、中学语文教育等问题。 赵焕亭在2012 年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学教育研究》一书,其论题尽管隐含了教育与中国当代文学间的关系,但就其论著本身来说,并不是从教育的维度来探讨其与中国当代文学之间的关系,而是从语文“教学法”的维度来探讨作品传播的微观问题;至于该书的主干部分则侧重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其焦点并不在教育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关系上。
在既有研究成果中,王先霈主编的《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一书梳理了21 世纪以来各种文学创作的产生和发展,文学创作、时代和外界影响的关系,其中,该书以附录的形式对1977—2003 年大学教育与作家创作关系做了较为充分的调查, 集中呈现了作家大学学历调查情况。此外,该书还对近年几个较为活跃的地域作家群进行了调查,如河南作家群、湖北作家群、广西作家群、湖南作家群、西部作家群、江苏作家群、北京作家群、上海作家群等作家群体。[2]该书没有涉及这些作家群的文学教育背景,可能缘于该书主旨并不在阐释文学教育与文学创作间的关系。
“共和国教育与中国当代文学关系”研究近年来受两种学术趋势的影响较大:一是文学研究的“跨学科”趋势,二是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 前者为文学与教育交叉研究带来新的学术生长点,后者则依托历史意识与客观史料阐释文学与教育的互动关系。 具体来看,共和国教育与中国当代文学关系研究有一条完整的学术研究脉络, 其发端于新式教育与现代文学的发生研究,成长于现代教育与现代文学关系研究。 它与同时期的现代大学文化与现代文学关系研究以及现代文学教育研究构成了1990 年代以来文学与教育关系研究的三大热点。从目前学界的研究情况来看,现代教育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研究已经较为充分[3],但对于共和国教育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关系这一问题,学界鲜有专门的关注。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对二者关系习焉不察;二是共和国教育自1949 年以来一直延续至今,对其作历史的观照并非易事,但共和国教育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关系研究已经具备条件。 其一,从时间上看,共和国教育已经走过了74 年的历史, 形成了1949—1976 年、1977—1999 年、2000 年至今三个较为明显的历史阶段;其二,从研究方法和理论上看,1949 年前的现代教育与中国新文学的关系研究所积累的研究方法与理论已初步成熟,其研究的经验与反思都有利于共和国教育与中国当代文学关系研究的开展;其三,从文献史料搜集的情况来看,共和国以来的文学教育史料与文学史料保存较为完善,史料搜集在数字化时代更为便捷,当事人口述史建设相对容易。
二
尽管文学与教育关系研究自1980 年代末提出,经过了1990 年代和新世纪以来“持续发酵”的趋势,但是历经70 多年的共和国教育与中国当代文学关系研究却相对薄弱,就其所依托的研究对象来看可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是机构研究,主要研究各类官方和非官方教育机构中的文学教育与当代文学之间的关系,典型的有关于中央文研所、鲁迅文学院以及各地大学的文学教育研究。 第二是制度研究,主要研究国家教育与文艺制度统摄下的文学教育与当代文学间的关系,典型的有教育制度、文艺制度以及学科设置与文学教育实践的关系研究。第三是理念研究,主要研究文学或教育理念与中国当代文学生产间的关系,典型的有中国当代文学教育理念发展与更新研究、 高校文学院或个人的文学教育理念研究、作家的文学教育理念研究。
(一)机构研究
机构是制度和理念实践的重要空间,文学机构亦如此,所以,文学机构或文学教育机构更能够反映一个时代文学生产的特点,这些机构又可具体分为国家官方文学机构和各地大学中的文学院或中文系。
国家官方文学机构研究主要以“中央文学研究所”(以下简称“中央文研所”)和“鲁迅文学院”(以下简称“鲁院”)研究为主。 中央文研所建立于1950 年,1954 年改名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1984 年正式定名为“鲁迅文学院”。 在1950—1980 年代,中央文研所研究并未得到重视,直到1994 年柴章骥、蔡学昌在《新文化史料》杂志发表《中央文学研究所创办录》一文,中央文研所才逐渐被学界重新认识。其后,在丁玲相关的回忆录中“中央文研所”成为高频词汇。 2000 年,徐刚的《文学研究所──文学讲习所》一文首次对中央文研所的历史变迁作了梳理。以丁玲为中心的中央文研所研究,在2003 年抵达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本年邢小群的专著《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详细梳理了中央文研所创办的过程,并辅之以大量的回忆录及口述史资料。自2003 年开始,中央文研所研究的中心逐渐从“人物”转向“机构”。 2008 年,郭艳首次将中央文研所的创办放置到1950 年代初的文学情境中考察,自此中央文研所研究开始逐渐“史学化”。[4]2015 年,中央文研所作为“机构”对当代文学生产的影响研究开始凸显。2015 年,毕红霞重点考察了中央文研所对作家的培养[5],2016 年又重点从文化社会学角度梳理了中央文研所的创办与发展史。同时期的叶炜也开始研究中央文研所, 从中央文研所的创办历史和丁玲的文学观念研究逐步拓展到1950 年的文学生态研究[6],接着又将考察视线向后延展到“文学讲习所”[7]、“鲁迅文学院”与新中国文学新人培养研究[8]、鲁迅文学院与中国当代文学生态研究[9]等。 在中央文研所创办历史细节史料发掘与细节深化方面,王秀涛和李蔚超作出了重要贡献。 2017 年王秀涛在《中央文学研究所的筹备与成立》一文中借助油印档案材料《讨论筹办文学研究所参考提纲》,详细考察了中央文学研究所创办的原因、目的、名称、领导关系、规模、研究人员的条件与待遇等。10]2019年,李蔚超在《社会主义文学教育的试验与试错——记草创阶段的中央文学研究所》一文中以“鲁迅文学院”的院史档案为依据,对中央文研所的创办过程进行了历史还原,突出了丁玲个人的教育实践对新中国文艺方向的认同与偏离,文章认为:“草创阶段的文学研究所既是社会主义文学教育的一次试验,也是一次试错。 ”[11]随着研究在史料和阐释方面的深化,文学机构对当代文学生产的影响开始明朗化,而中央文研所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第一个官方机构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也重新被学界认识。 2020 年,孙向阳在《中央文学研究所与作家培养》一文中考察了中央文研所和讲习所时期的作家培养和作品创作情况,他认为:“作为文学生产机制中的重要一环,文学机构对作家培养所做出的努力与探索是不能忽视的。 ”[12]
各地大学文学院或中文系的文学教育研究以作家和大学文学教育互动为切入点,反观大学文学教育对当代文学产生的影响,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的成就较为突出。
1.莫言与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文学教育研究。 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创建于1960 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唯一的一所多学科、综合性高等艺术院校。自创建初至今,解放军艺术学院人才辈出、硕果累累,不仅为文艺界输送了众多文艺人才,而且还创作演出了众多优秀的、脍炙人口的艺术作品,为中国当代文学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解放军艺术学院院系众多,如文学系、戏剧系、音乐系、舞蹈系、文化管理系、美术系等,这些院系在各自领域均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其中,成立于1978 年的文学系为中国当代文坛培养了一大批享誉世界的优秀作家,莫言、李存葆、朱向前、黄献国、阎连科、麦家都曾在文学系就读,由此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为中心形成了解放军艺术学院作家群。 因此,将解放军艺术学院作家群作为一个整体进行重点研究,透视作家所接受的大学教育背景与作家创作之间的关系,进而发现共和国教育体制与中国当代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具有独到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在对“共和国教育与中国当代文学关系”这一课题的研究中,我们应当注重历史的宏观描述与具体的个案解读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既要从整体上对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文学教育进行梳理,还要注重个别作家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接受的文学教育与文学创作的个案研究。 对作家的个案研究有利于帮助我们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现实,从小处入手,向大处着眼,更好地理清共和国教育与中国当代文学之间的关系。
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作家群中,莫言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作家,他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体制内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坛有极大的影响力。 虽然很多作家接受了大学中文系的文学教育,但在其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大学的文学教育并不是他们接受文学熏陶最主要的渠道,同样也没有为他们的文学创作提供最直接的文学资源,但是莫言却是典型的在接受大学文学教育的过程中逐渐确立了文学创作的目标并获得了丰富的文学资源和素养的作家,并最终成为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选择莫言作为个案,通过梳理莫言文学教育与创作的关系来研究解放军艺术学院作家群便具有了典型性。在有感于莫言研究不断取得可喜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对莫言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接受文学教育的研究却相对较少。 李宗刚的《莫言的文学教育与文学创作关系新探》(《新文学评论》2018 年第2 期)一文对莫言所接受的文学教育作了较为辩证的透视,认为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开设的文学课程摆脱了既有的文学教育窠臼,注重对文学创作内在规律的阐释,尤其注重作家的现身说法,其落足点在于启发学生文学创作的感悟能力和写作能力。 谢尚发的《莫言的“军艺时期”——从史料文献梳理作家的“大学生活”兼及一种文学史的观察》(《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 年第2 期)一文看到了大学教育对当代作家文学创作的重要影响,文章通过梳理相关史料,重现莫言大学期间学习和生活的历史场景,探究了莫言创作与大学教育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但是,关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教育与莫言创作关系的研究还比较少,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和价值。
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教育与莫言文学创作关系研究的可行性与创新之处在于:解放军艺术学院作为莫言接受文学教育的大学, 其诸多方面都对莫言从事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解放军艺术学院悠久的历史、优良的校风和文化传统所形成的文化氛围对莫言的熏陶以及学院师生对莫言的影响。 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师生中,对莫言帮助最大的当数徐怀中和朱向前。 莫言的成功离不开徐怀中的帮助:是徐怀中在莫言错过入学报名后将其破格录取;是徐怀中的推荐才使得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等作品得以顺利发表;也是因为恩师徐怀中,莫言才取消转业的念头,继续坚持文学创作。 至于莫言的同班同学朱向前,更是见证了莫言的一路成长,正是通过他的回忆,我们知道,当其他同学都在访亲探友、喝酒聊天的时候,莫言却躲在教室里写作到凌晨两三点。 这些都为我们研究莫言军艺时期的学习生活提供了佐证。朱向前还是莫言作品的最早评论者,正因为他的评论以及一系列研究文章,使莫言在文学创作上不断成熟,他成为莫言成名的助推器,帮助莫言回应了质疑。 综上,无论是军艺整体上的文化氛围还是师生,都对莫言的文学创作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正是在多方因素的作用下,莫言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成为一位优秀作家,并创作出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
对于莫言的个案研究,为我们研究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教育与作家创作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和方法,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结合解放军艺术学院不同时期的其他优秀作家,例如李存葆、朱向前、阎连科、麦家等人,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文学教育与军艺作家群文学创作的关系,从而理清共和国教育与中国当代文学之间的复杂辩证关系,总结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规律和教训,促进中国当代文学的健康发展。
2.河南大学作家群研究。 善于开掘校史和学科史的河南大学在2002 年出版了《河南大学作家群》一书,该书除了追怀河南大学文学教育的人文精神之外,首次弥补了现代以来学界对高校学科史研究“重学术而轻创作”的不足。 河南大学具有悠久的历史,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河南大学作家群就逐渐形成并绵延至今。按照时间维度,河南大学作家群在整体上可以分为三代:第一代是在1920—1940 年代,即新中国成立前在河南大学学习、工作和生活过的作家,例如王实味、范文澜、姚雪垠、郭绍虞、于赓虞、徐玉诺、蔡一木、任访秋、苏金伞、赵清阁、周启祥、万曼、樊粹庭、吴强、李蕤、邓拓、周而复、李白凤、马可、栾星、刘炳善等人;第二代是在1950—1970 年代,即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结束这一时期在河南大学生活过的作家,例如余非、刘增杰、夏影、刘思谦、苏文魁、周鸿俊、张永江、李洪程、余辰、屈春山、张俊山、张惠芳、王怀让、孙荪、鲁枢元、孔令更、王钢、李晓燕、彭燕彬、吴建勋等人;第三代是在1970 年代之后,即“文革”结束后由“老三届”与“文革”时期的青年学生组成的作家群体,例如刘学林、曲今敏、陈俊峰、宋立民、张清平、孟宪明、张国臣、王剑冰、程光炜、英子、阎连科、金惠敏、沈卫威、张鲜明、吴元成、焦国标、高有鹏、高金光等。这三代人一起组成了庞大的河南大学作家群,他们在小说、戏剧、诗歌、散文、文学理论与批评等不同领域均取得了突出成就,为中国文学理论及创作实践作出了重要贡献。[13]河南大学以其悠久的历史积淀和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和浸染了河南大学作家群体的行为模式和思维习惯,因此,以河南大学为切入点对中国当代作家的文学创作进行研究、阐释,对于揭示和把握大学文学教育与作家创作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和价值。 但令人稍感遗憾的是,在既有河南大学作家群研究成果中,还没有将其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学群体进行研究,研究河南大学作家群的文学教育与作家创作关系尚有极大的研究空间和价值。 因此,以河南大学作家群这个全新视角进行研究,对促进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3.华东师范大学作家群研究。 对于在华东师范大学文学教育影响下形成的极富规模的“华东师大作家群”,学界也同样给予了高度的关注。无论是钱谷融还是徐中玉,他们对于文学教育和写作实践的重视,使得一批新的作家登上了文学的历史舞台。周敏指出,在新文科教育背景和华东师范大学“学者群”文学教育的探索下,在“多元性”教学和大学“预留空间”的构建下,伴随着1980 年代的“文学热”,“华东师大作家群”得以产生。[14]刘莉娜指出,“华东师大作家群”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其耀眼之处在于其知名作家数量最多以及构成群体的作家在文学史上影响巨大。[15]
在以上这些高校之外,还有不少高校也在作家培养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限于案例的数量要求,我们就不再一一枚举了。
(二)制度研究
制度是一个时代文学生产的“文化框架”,它既规范着文学生产亦受文学反作用力的影响,因此,制度研究是共和国教育与中国当代文学关系研究的重要对象。制度研究又主要分为共和国教育制度研究、共和国文艺制度研究、当代高校文学教育制度研究等。共和国教育制度研究集中在1950 年代教育制度生成与共和国初期文学方面, 主要以当代高校文学类学科设置研究和文学教学研究为主。 如谢泳的《从“文学史”到“文艺学”——1949 年后文学教育重心的转移及影响》一文着重探讨了“五四”后确立的以“文学史”为重心的文学教育是如何在新中国建立初期被“文艺学”取代的。[16]在此过程中,1949 年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向华北各地高校下达的《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以及1952 年高校院系调整法令等文件对于共和国文学的“延安化”和“苏联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文艺学、中国现代文学等学科对当代文学教育的影响。 共和国文艺制度研究的重点是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历次文代会影响下的文学教育与中国当代文学关系进行研究。 当代高校文学教育制度研究主要涉及作家讲座制度和高校驻校作家制度。当代作家驻校制度是民国时期作家兼课制度的一个延伸,李宗刚认为,民国时期作家兼课制度一方面为作家创作提供了物质保障和精神空间,另一方面也为新文学在大学的传播提供了契机。[17]在共和国教育语境中,尤其是21 世纪以来的教育语境中,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山东大学等多所高等院校均建立了作家驻校制度。当前,国内高校作家驻校制度的实施方式大致有三种[18]:一是人事编制纳入高校,作家作为专职人员在大学开展写作与教研活动,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二是聘请专业作家作为兼职教师或客座教授, 作家作为编外人员在相对集中的时段内参与校园教研活动,比如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2013 年建立的作家驻校制度,包括专职和短期两种方式;三是以短期的“驻校写作计划”或“作家讲学计划”为载体,邀请作家进校园举办讲座、会谈与研讨活动,比如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先后邀请美国学者叶维廉、中国台湾诗人余光中驻校参与为期一个月的讲学、研讨活动。
(三)理念研究
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教育,教育理念对于文学的影响甚为关键。文学教育理念研究在共和国语文教育研究中也曾得到回应,在刘真福看来,文学教育包含四个版块:“1.知识教育:古今中外文学史知识,各类文学体裁知识,文学理论知识;2.以读文学作品为主的文学鉴赏训练;3.文学评论训练;4.创作训练(如大学里的作家班所做的培训工作)。 ”[19]时代的文学观念对于文学教育能够产生直接的影响,从1950 年代确立的“工具论”到1980 年代的“审美论”,再到1990 年代后的多元发展,时代观念影响了文学教育与文学创作风貌。 当代高校文学教育理念研究具体又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文学教育整体理念研究。谢泳在2003 年的《“文艺学”如何成为新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 》一文中着重探讨了山东大学文艺学教学批判事件,重构了1950 年代共和国文学教育的初始语境。 该文以1951 年山东大学中文系学生揭发文艺学教师吕荧讲课的政治问题事件为中心, 借助《文艺报》“关于高等学校文艺教学中的偏向问题”的讨论,揭示了新政治意识形态是如何作为一种规范化的“观念”植入到新中国初期文学教育场域中的,“文艺学”学科的确立及其由“欧美理论”向“苏联理论”的转向对大学文学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20]第二类是中国文学史课程、教材与教法研究,其中涉及现当代文学史教材与教学理念研究。 戴燕认为,中国文学史“始终是在按照自己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课堂教学形态,建构一套特有的经典系统和理论体系,养成一种特有的文学文本的阅读方式,并创造出当代对于过去历史的一种独特意识,从而融入到当代教育体制中去的”[21]94。洪亮对共和国教育中的现代文学史教材作了详尽梳理,并归纳了文学史教材的变革与政治话语变迁之间的关系。[22-23]李松通过对1950 年代四部现代文学史代表教材的分析,揭示了共和国初期教育中“历史元叙事”对文学史教育及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总体性历史元叙事作为一种本质主义的理论范式,将文学存在视作政治元叙事的表述工具,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推广到文学史的阐释之中。这种文学史观念对后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24]第三类是文学教育理念的传承与更新研究。 其一是文学史教学理念更新研究。 谢泳在《从“文学史”到“文艺学”——1949 年后文学教育重心的转移及影响》一文中将视线拉回当代文学教育,他认为,北京大学的“文学史”教育传统在1950—1970 年代曾接受文艺学“以论代史”的改造,但是在当下陈平原和洪子诚的文学史研究与教学中这一传统又重新复苏。当代文学教育理念更新研究涉及当下多个文学理念变革,比如旧体诗入文学史研究、港澳台文学如何入史研究、华文文学概念的提出与研究、抒情中国与革命中国不同之文学观念研究、少数民族文学入史研究等。 如纳张元认为,当下文学教育中应当重视“少数民族”,在互动与认同中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25]其二是文学创作教育理念更新研究,主要体现在21 世纪以来创意写作课程及二级学科建设实践等方面。其三是大学中文系名家文学教育理念研究。鲁定元在其博士论文中指出,“文学与教育有着天然的联系”,但显然,文学教育并非是在现代教育中一蹴而就的,正如周宪所言,“文学教育的传统在中国源远流长”[26],古已有之的“诗教”传统,便是将伦理目的与文学教育紧密结合的社会教化行为。按照韦伯之于现代性的相关论述,在不断分化的历史前进中,“祛魅”作为“分化”的重要步骤,使得世俗权力、宗教压力与文化分离,组成独立的场域,但此期间并未割断与教育的联系。进入现代社会,新式教育与文学联系愈发紧密,李宗刚在其博士论文中论证了五四文学的发生与新式教育的关联,而诸多现代著名作家,如鲁迅、胡适等均受益于此。 即便像沈从文这样的现代作家,“他一生中最自觉的努力和最重要的成就, 是根源于现代大学体制的”[27]。 由此可见,大学在当代社会仍然保持着文学教育的基本属性,正如利维斯对于大学和教育的看重,“在大学教育中他又认为文学教育居于核心地位”[28],其中,华东师范大学在文学教育中书写了极为璀璨的篇章。
学界对于华东师范大学文学教育的关注点首先集中于作为教育主体的教授即学人身上,钱谷融和徐中玉为其代表。钱谷融作为现代文学的研究大家,部分学者更多的是围绕其文学思想(多以“文学是人学”观点)进行探讨。刘为钦在《“文学是人学”命题之反思》一文中指出,钱谷融在1950 年代的政治与文学生态中提出“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并阐释文学的“人性”品格,具有非凡的意义。[29]季进、曾一果在《钱谷融先生的文学思想述论》一文中认为,《论“文学是人学”》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史上的重要文本,对于我们回顾中国当代文学史,乃至整个20 世纪中国文学史,都有着极大的理论价值和历史价值”[30],并对其理论的提出与构建以及理论实践与评价作出了详细梳理。 殷国明通过三论《论“文学是人学”》,以笔谈形式,置身于历史现场,还原思想理论生成过程,并对文学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他指出:“这篇文章所播下的‘人学’与美学相结合的种子,经过长时间的考验,终于还是成为我们建造现代文艺学的基石。 ”[31]许见军在其博士论文《钱谷融文学思想研究(1949—1966)》中从文学史进程入手,在钱谷融文学活动中阐发其“人道主义”美学思想生成的历程以及“文学是人学”理论的提出、深化与在新时期文学中的延伸与拓展。 显然,诸多对于钱谷融学术思想的探讨一方面是对钱谷融文学史位置的认可,对其思想的生成与影响也是在客观性与真实性基础上进行评判的,另一方面又在其原有理论基础上对其理论进行了开拓与创新,进一步完善了钱谷融的学术思想,延续了其学术生命力。 但是,由于研究方向的制约,这些学者并没有关注钱谷融“文学是人学”思想传播链条中被遮蔽的“文学教育”问题,正如钱理群在《读钱谷融先生》一文中所指出的:“谈钱先生,而不谈他对人才的培养,是绝对不行的。 ”[32]这也就是说,如果仅仅以文学理论家的身份定义钱谷融,是有失偏颇的,事实上,钱谷融极为重视学生的文学教育, 方仁念曾经回忆道:“研究生入学, 钱谷融先生给他们上的第一堂课,讲‘文学是人学’,他便强调文学是写人的,是写给人看的,是以影响人的思想感情为目的的,因此要真正懂得文学、研究文学,必须首先做一个心地坦荡、人品磊落的人,因为只有一个真诚的人,才能感受和欣赏真的美。谁要不是以‘赤子之心’来对待人,对待文学,他也就不可能读通文学。 ”[33]可见,“文学是人学”并非仅仅是严肃的文学理论符号,其中还包含着钱谷融饱含热情的文学教育理念。 对于钱谷融的文学教育实践,另有部分学者也给予了关注:陈平原提及钱谷融“在培养文学专业研究生方面,则另有高招……入学考试时不以知识而以作文为中心”[34];杨扬在谈到钱谷融对于“唯理论论”的排斥时指出,“借别人的思想以自重……未必是最理想的治学方式”[35]。钱谷融要求学生脱离死板的教科书,培养独属于文学的“才情秉赋”,他明确指出,仅仅依靠教科书上的固定知识考察学生是远远不够的,“要全面了解一个学生的思想、学识和才情,我认为最好的途径莫如通过他们所写的文章”[36]。 尽管有部分学者关注,但学界对于钱谷融的文学教育实践仍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与此相反的是,学界对于徐中玉的关注大多集中于文学教育领域。王同彤在《徐中玉先生“文化育人”的三重境界》一文中指出:“简要回顾徐先生在三个人生阶段中文学育人、学术育人、通识育人的历程,真可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7]孔冰欣基于徐中玉的文学教育实践与成就把他视为“一个正直的、‘中国的’知识分子”[38]。 汪寿明在与徐中玉对谈中指出,徐中玉“总是鼓励他们,讨论后各自再整理,扩展思路,写成文章”[39]。 此外,另有部分学者着重关注“大学语文”课程作为文学教育的重要途径与徐中玉密不可分的联系。陈丹叙述了徐中玉开创“大学语文”课程的艰辛历程,称其为“大学语文之父”[40];范耀华称徐中玉是“大学语文”教育事业的奠基者[41];陆晓光将“大学语文”与“人文精神”相联系,从徐中玉文论入手指出大学精神与“大学语文”的内在关联[42]。
总的说来, 关于共和国教育与中国当代文学关系研究已经呈现出大发展的基本态势,尤其是一些个案研究展开得较为充分,而宏观研究则显得不足。因此,对共和国教育与中国当代文学之关系展开研究便显得愈加必要。
三
系统地梳理和研究共和国教育与中国当代文学之间的关系,可以极大地拓展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既有版图,进而较好地把中国当代文学拓展到“跨学科”研究上来,这将使人们重新发现被遮蔽了的诸多问题——作家的文学创作与其接受的文学教育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共和国教育体制对文学创作到底产生了什么作用? 我们在未来的教育中如何进行教育体制改革,进而促进文学创作的发展和繁荣?
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我们能够在后续的研究中围绕“共和国教育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以及相关命题探索出新的学术路径。
第一,确认共和国教育与中国当代文学有无关系。实际上,人们对二者关系的理解要么习焉不察,要么模糊不清。 因此,确认二者有无关系便是我们展开研究的前提。 笔者拟通过对大量作家所接受教育的系统考察,明确二者之间存在着无法割裂的关系。
第二,将共和国教育与中国当代文学关系划分为不同的历史阶段。 历史发展从来都是在曲折中前进的,由此历史的发展便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 因此,把70 多年的历史划分成不同的历史阶段,便于我们对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关系进行具体分析。
第三,厘清共和国教育与中国当代文学之间的关系。二者之间有关系,仅仅是我们认识问题的起点,还需要进一步厘定二者之间的具体关系。二者是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的关系,还是相互掣肘的恶性循环的关系,抑或情形复杂、正反并存的关系,这样的辩证分析能够为我们的深入研究奠定逻辑上的坚实基点。
第四,回溯到1949 年前现代教育的历史河流中去探究共和国教育对现代教育,尤其是文学教育的扬弃、继承和发展。通过确认现代教育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找出共和国教育与中国当代文学之间发生联系的历史缘由。在此研究过程中,需要特别强调的是,1949年后的作家型的教师呈现出逐渐减少的态势,这与作家已经不需要依托学校便可以进入体制有关。许多作家因为文学创作离开了学校进入作家协会,并由此成为专业作家,这对中国当代文学既有积极的作用,也带来了文学教育与文学传承上的缺失。[43]
第五,探究共和国教育与中国当代文学之间为形成复杂关系的原因。严格说来,共和国教育在其70 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常受到来自政治运动的影响,在此情况下,共和国教育与中国当代文学之间复杂的关系也是可以理解的。
第六,以那些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作家为个案加以解读,从其接受的共和国教育背景对其文学创作进行深入阐释,发掘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
第七,总结共和国教育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经验教训。 分析共和国教育与中国当代文学之间的内在影响机制,总结共和国教育更好地促成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国当代文学更好地促成共和国教育发展的经验教训。
从共和国教育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中国当代文学,不仅仅是研究视角的转换,还是研究文学史方法的转换, 这将有助于我们发现中国当代文学被既有研究范式遮蔽了的内在规律。 共和国教育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也具有某些副作用;中国当代文学对共和国教育的发展,既有积极的正作用,也有某些副作用。尽管如此,共和国教育既对中国当代文学创建主体现代文化心理结构的建构起到了不可取代的作用,也对中国当代文学接受主体现代文化心理结构的建构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相互的作用促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呈现为螺旋式的发展态势。 实际上,新时期走上文坛的许多作家便是在文学教育的过程中逐渐确立从事文学创作的目标并最终走上文坛的。 当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文学教育并不局限于大学中文系,也不局限于中小学的语文课程,还包括民间多种形式的文学教育。实际上,一些作家并没有接受系统的大学中文系教育,有些即便接受了大学中文系教育, 但他们走上文学创作道路, 其精神资源也并非直接来自其学习的大学课程;当然,还有一些作家并没有进入大学,他们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较早地进入社会,但依然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接受文学的熏陶,最终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这些都表明,在对共和国教育与中国当代文学关系考察研究时,要对其复杂性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唯此,我们才会在从事研究的过程中,始终保持自我独立的学术立场和学术追求,而不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共和国教育仅仅是参与其发展的一个重要要素。但是,如果我们一味地受制于研究对象,未能较好地处理诸多参与要素间的关系,就有可能一味地扩大共和国教育的作用,而忽视了其他要素的作用。 实际上,我们在从事本领域研究之前,一定要克服思维上的形式逻辑,不能先验地认为教育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而看不到教育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的某些副作用;先验地把教育和作家的文学创作对接起来,而看不到教育之外的因素在促成作家文学成长中的作用。因此,我们更需要清醒地意识到,在此凸现共和国教育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作用,并不意味着遮蔽其他因素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作用;在此凸现被学界所忽视的共和国教育这一要素,只是表明我们对中国当代文学各种阐释中的教育维度解释,这并不是唯一的解释。事实上,我们并不认为共和国教育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是万能的,是凌驾于文学自身演变规律之上、超越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语境的规范制约的一种终极之因。因此,如何在凸显某一元素在历史中的作用的同时规避由此而带来的遮蔽,是研究者所必须警惕的;同时,如何进一步说明在共和国教育下的个人化文学书写,也是研究中的难点所在。毕竟,中国当代文学的创建主体无法摆脱他们所生活的时代而创造出新文学。
总的来看,系统梳理共和国教育与中国当代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可以深入地阐释共和国教育与中国当代文学之间复杂关系形成的内在机理,对中国当代文学以及共和国教育(尤其是文学教育)的健康发展提供有益的镜鉴。进而,在这块显得有些荒芜的园地里,播撒下学术研究的种子,努力促使其成长为参天大树,最终通过学术研究参与并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