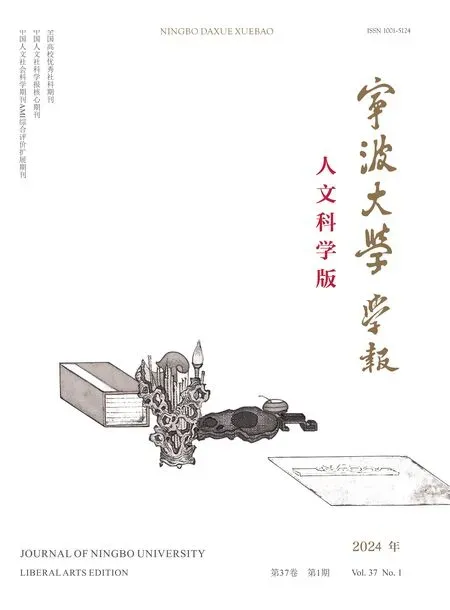话语、时空、限度:再论莫言《白狗秋千架》的电影改编
高 志
莫言的小说《白狗秋千架》发表于1985 年,2003 年被著名导演霍建起改编为电影《暖》。《暖》先后于2003 年荣获第23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和第16 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金麒麟奖),2004 年荣膺第11 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改编获得巨大成功。导演霍建起认为此影片最大的特点是“书写人性”。
我觉得人性这个东西比较不概念,人性最普遍。不像有些东西好像一定要这样或那样。比如我觉得文革前的中国,特干净,特别有秩序,虽然贫穷,但是简单,那时候有一种朴素的干净……所以我就特别喜欢表达人性的东西,不愿意表达那种特极端的内容,比较崇尚那种纯艺术呀,纯粹一点的东西。[1]43-44
小说《白狗秋千架》内涵丰富,具有超时空、超阶级和超政治的意义涵量。电影导演霍建起选取原作中具有丰富内涵的一部分,窄化了作品的意义空间,压制了意义生产的多种可能性。
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电影改编虽有其独到的一面,但也有其欠缺之处。本文梳理原作与影片的异同,勾勒电影改编的路径及其选择意图,发掘其意义内涵及其局限,旨在为影视改编祛魅。
一、语境效应:中心、边缘、启蒙
1985 年被称为“文化年”和“方法年”。新时期西方三大理论“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引进我国,文化、科学以及理性哲学成为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这些社会思潮与“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及启蒙精神不谋而合。莫言在这一年创作了《白狗秋千架》,旨在于红色经典小说影响的焦虑中寻找文学创作实践的突破口,因此五四主题“种的退化”成为莫言思考问题的焦点。莫言曾说:“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感到种的退化。”[2]4“种的退化”主题在他的小说序列中占据重要位置。莫言对该主题的书写接续鲁迅和沈从文,开拓出一套严谨的理论系统。在《白狗秋千架》中,人和动物形成互文和隐喻关系,凸显了“种”的退化的现状和救赎的路径。小说篇首点出山东地方杂毛狗繁衍盛行的态势,指出纯种白狗正在日渐减少,“高密东北乡原产白色温驯的大狗,绵延数代之后,很难再见一匹纯种”[3]199。杂毛狗成为贯穿全篇的线索,链接起女主人公“暖”与“我”的情感记忆。“暖”希望有健康的孩子,这是对健康生命体的认可和肯定;狗和人类似的生存危机和退化的态势,凸显了“种的退化”。莫言从“种”的血缘基因切入,强调以科学的基因遗传(科学的启蒙方式)去拯救生命力的衰落,并借用乡土民间故事的形式去演绎,同时将乡土伦理中血缘关系结构作为故事的主线。莫言以血统书写代替阶级划分,突破“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阶级划分的藩篱,个人化叙事替代一元化的阶级叙事。血缘、民间和爱情成为莫言创作的主元素,血缘为纽带的家庭伦理开始重新登上舞台,从文学边缘向中心移位。这一创作倾向成为20 世纪90 年代中期的“事件”级现象。经典的例子是家族系列小说的生产和传播,如张炜的《古船》《家族》《柏慧》,莫言的《丰乳肥臀》《食草家族》,陈忠实的《白鹿原》等小说。
在五四时期,“种的退化”叙事侧重社会问题维度。鲁迅批判封建吃人文化,沈从文倡导摒绝现代文明中的湘西人性和建构“希腊人性小庙”,周作人主张以希腊人性恢复近代中国人的生命力,废名崇敬的是世外桃源式的诗化人生。可见,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从多种角度探讨“立人”目标。鲁迅主张“破”的同时又突出“立”。他在《摩罗诗力说》《我们怎样做父亲》《狂人日记》等作品中,探索“立”的途径,提出“心声”“内曜”“朕归与我”等立人的具体路径,并指出这些路径是以个人健康发展为前提的[4]25-26。个人的发现和集体的警觉成为鲁迅“立人”的反正两面。周作人、沈从文和废名的主张和理论具有浪漫色彩,相较鲁迅的针对性和在地性,他们提供的是超越性的总纲,可行性不足。
新时期,在新的时代和国内外背景下,莫言从国族危亡的角度去反思传统文化,重新延续五四生命力衰弱的主题,并将“种的退化”问题剖析得更加深入。他从科学角度思考生命力衰退和基因变异问题,并极力从历史维度和民间维度去反思生命力强弱的内涵,思考现代社会对生命力戕害的多种因素,剖析了代孕事件、计划生育、父权制、阴性崇拜和婚姻状况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莫言《白狗秋千架》呈现了“种”的残疾和基因的缺陷等问题,从民间伦理和人性角度,思考解决女主人公的内在需求和纾解其社会压力的方法。“暖”希望营造有声世界,希望拥有健康的孩子,她的借种行为既是反叛儒家传统伦理,又是齐地(沿海区域)自由开放文化的表征。虽然借精求子违背了乡土伦理,但在儒家伦理的重压之下,双重悖论彰显了儒家伦理的自相矛盾,预示了其必将崩塌的社会命运。
作者通过对暖的不同场景的故事回忆和访问细节建构了暖的主人公身份。随着故事推进,暖的故事份量增加,凸显其主导地位。在爱情交往的多重回合中,暖成为叙事主角。暖的性格与《丰乳肥臀》中母亲的性格契合,她是作家赞扬崇拜的对象,如暖的善良、坚韧、泼辣和开朗的性格。“温柔、勤劳、善良、坚忍、宽容这样一些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在新时代的‘良家妇女’身上获得了新的十分活跃的生命力,从而在相当程度上以情感化而非理性的道德评判替代了更为深刻的历史评判和人性评判。”[5]小说中,暖在遇见返乡的“我”后,企图掌控自己的命运,并付诸实践,这推动了小说的行进,莫言将女性从被动提高到主动的位置。乡土女性地位的逆转反映了乡土社会父权制存在的危机。
电影《暖》抛弃了“种的退化”主题,主人公“暖”的生育需求被置换为爱情和知识,这与当时普遍兴起的情感叙事有关。20 世纪90年代,市场机制建立,电影的生产、传播和消费由计划调控走向市场调节,“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了直接的经济关系——这些背景的变化应该说都加速了电影的工业化进程”[6]。1993 年,“人文精神”大讨论,呼唤重建社会道德。《渴望》《新白娘子传奇》等温情片风靡一时,正是社会温情缺失的表征。在电影《暖》中,爱情成为电影叙事的主元素,电影以男主人公林井和的忏悔为线索,以回忆作为补充往事的媒介,将暖的三次爱情作为重点,去透视爱情观和其情感的变化历程。暖第一次恋爱是与剧团的演员小武,初恋朦胧而甜蜜。但电影叙事沿袭了传统小说始乱终弃的故事套路,改写了原著暖单恋的情节,借鉴古典爱情套式迎合受众口味,这也是电影的市场化价值目标使然。原著中的文艺兵改为剧团演员,暖的恋爱对象由政治身份转移到普通演员,这是对传统文学中优伶始乱终弃的形象母题的再演绎,电影将书写的古典风格作为魅惑市场的筹码。暖的第二次恋爱对象是知识分子林井和,两人虽青梅竹马,却是熟悉的陌生人。林井和最后违背了“大学毕业后返乡与暖结婚”的爱情承诺,留在城市,娶亲生子;林井和与暖之间的文化差异和身份悬殊阻隔了他们之间的爱情,暖的自卑或善良促使她毅然斩断情感的纠缠。她的态度由无能为力到主动抛弃爱情,由被动变为主动,反映了“暖”爱情观的转变和逐渐成熟的心理,同时体现了女性地位的提高,这也是电影艺术陌生化的内在需求。第三次恋爱,暖的对象是无私助人的哑巴。他们通过日常生活交往培养出爱情,水到渠成地组成坚固婚姻共同体。在故事结尾:“暖”拒绝离开哑巴,这与《白狗秋千架》中男主人公性幻想的达成大相径庭。电影中“暖”与哑巴的爱情故事,是对“互相扶持”的现实爱情的认同和肯定,也是中国普通人爱情生活的翻版和隐喻。
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精确描述了后革命时代意识形态中新的监控方式的实施。“革命传统依然存在,并且我们‘最终必须学会’与现存的和故去的革命传统一起‘生活’。”[7]226电影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表达的载体和建构文化霸权的新平台。电影《暖》是时代文化、政治、消费和市场合谋的经典。暖的三次恋爱涵盖新时期之前中国的几种婚姻类型:古典风格、浪漫风格和现实风格,它们丰富了电影的意义生产。
莫言的小说《白狗秋千架》带有拯救生命的启蒙使命,“暖”向“我”借精,“我”不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拯救者,“我”的知识分子身份还赋予拯救本身以启蒙意义。改编后的电影《暖》,意义也大大改变并减少,仅仅反思爱情的获得和失去的价值意义,对原著中隐含的五四知识分子“拯救者”启蒙身份没有显现。小说原著和电影中,中心和边缘的位置发生了翻转,这是时代、作者、导演、文化和消费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单个因素造成的结局。
二、意义生产:场域、意象、文化
意义是生产出来的,从工艺的角度讲,小说和电影的真实性也是被制作出来的,是某种理念的产品,“真实性不应被获得、被发现、被复制,而是应该被创造出来”[8]232。小说和改编的电影在场域、意象、文化和结局方面有较大的出入,换言之,改编的策略和方式直接影响了意义的生产。
场域是指艺术生产的时空体,它的配置、重组和选择会营造独特的氛围、风格和特色。小说《白狗秋千架》的背景是山东高密东北乡,天气、物候和动植物成为莫言故事独特的地理空间,凸显了原始生命的力量,透视出乡土社会对后代健康的重视和传宗接代的企盼。莫言借助北方的物象将此以直接或隐喻的方式加以表现。他细致描述农业活计,在《红高粱家族》《三匹马》《丰乳肥臀》等小说中,有收麦、割麦、耕地、运输等农活场景描写,表现了繁重的农活以及齐地风貌的特征。高粱叶、桥、河、白狗、大草驴、镰刀和秋千架是原著中出现的刻画地理空间特征的意象。高粱不仅是多子多福的象征,其耐寒耐涝的属性也具有繁衍生息的内在特性。莫言将“暖”的劳动与高粱融合和比衬,透视出乡村生活的繁重和艰难,也衬托了农民生存的不易与坚韧;高粱地是暖和“我”完成“种”的拯救任务的场所,也是民间藏污纳垢的空间。小说中设置的高粱地与革命时期建构起的正义意象——“青纱帐”形成鲜明的对照关系。莫言还原了高粱地及其高粱的隐喻。大草驴肩负生育使命,镰刀是劳作工具和力的映射,秋千架是庆祝丰收的器具,狗是人类忠实的伙伴。
劳作和生育是乡村生活的主要内容,“农活就是他们的职业,不是陪衬革命活动的副业,当现实生活中的农民能自主经营自己的生计时,银幕上的农民也就回到了祖家传给他们的农耕生活中”[9]。在长篇小说《生死疲劳》中,单干户“蓝脸”坚持以个人的劳作进行农业耕种,这是农民职责的表征,也是莫言对劳动的肯定,是对现代农民问题的回应和反拨。传统的乡村生育活动旨归在血缘绵延,重视宗族自治乡土社会的稳定,“血缘社会就是想用生物上的新陈代谢作用——生育,去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10]5。小说主人公暖试图以现代科学——基因遗传的原则去干扰血缘传承,她借种求子企求健康的孩子。从伦理层面上讲,这也为乡土社会安定植入了危机因子。秋千架是一种休闲生活,莫言将其设置为引起灾难的关键点,它导致暖的残疾,致使命运反转。总而言之,意象选择和对意象的认知是作者有意为之,这是莫言激活乡村生活经验和接受知识熏陶共同合力的结果。
小说《白狗秋千架》是一个复杂的文本,反映出时代、地方、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乡村伦理和文化是《白狗秋千架》书写的一个重要方面。健康后代的需求、乡村等级分层、知识的崇拜和认可、城乡差别域下乡村的自卑和无奈,以及女性男性化倾向等方面都传达出乡村伦理变迁和文化更易的信息。莫言以一个脱离乡村的农家知识分子身份去言说乡村衰败和拯救的故事,将衣锦还乡、知识分子的性幻想和心灵忏悔杂糅在一起,古典气质和现代风格混杂,且以卢梭的忏悔方式塑造拯救者身份,介入乡土社会,施害者变为拯救者,这一人物身份和职能的错位折射了城市与知识在现代社会分层化和制度化过程中的强势地位。
与小说相比,电影《暖》的故事场景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故事背景由北方的山东高密东北乡,挪至南方的江西古徽州。北方生硬的线条被南方雨水、池塘所代替,阴雨连绵和水泽遍布成为故事的背景,水的阴性品格赋予电影阴柔和舒缓的忧伤情调,感伤和温情是电影的主色调。在电影场景中的鸭子、蚕、池塘、发霉的墙、稻田、稻草垛和顺河而建的狭窄小巷等南方系列风物是爱情言说的景观。日常生活则成为暖爱情选择的理由和支撑整个小说框架的基础。电影没有褒贬哪一阶段或类型的爱情,而是以不同的色调表现不同类型的爱情,初恋采用暖色调和喜悦氛围呈现,第二次爱情采用清凉的灰调色,第三次爱情以雨雾的阴暗调为主,由浪漫气氛到现实情景,渗透了导演对爱情的认知和态度。电影贯穿着《诗经》哀而不伤的情调:篇末“暖”拒绝哑巴的建议仍然与他留在乡村生活,否定了《白狗秋千架》凸显知识分子文化拯救的价值,确凿证明了物质和知识并不是爱情的决定因素,“曲折的情节、充分的动作、鲜明的人物性格刻画和传统价值观念,这些小说特征更易于在影片中加以表现”[11]297。乡村在霍建起的电影叙事中获得了尊严和倔强的自救。
电影《暖》不再局限于具体的时空,而是拍摄出具有长时段历史文化的特征和风貌。21世纪初,市场经济建立,消费社会形成,文化染上消费的色彩。文学现代性的一个面向就是批判社会问题,对当下消费盛行、蔓延无序进行警示,并重申游移在边缘位置和被压抑忽视的情感元素。然而,电影发行需要符合“主旋律”的基本标准,“中国的电影在向市场经济迈进的过程中要面对进退两难的境遇和矛盾”[11]178。电影《暖》肯定乡土现实生活中的爱情,认同乡土社会的家庭伦理及其文化的连续性,这符合国家基层稳定的大政方针。乡村物质贫乏和城乡差别构成电影陌生化的基础,南方风景和爱情不同方式的展现迎合了电影市场的消费欲望。尼克·布朗尼认为:“最复杂、最有力的流行形式总包含传统伦理体系和新国族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妥协,这种形式能整合这两者之间情感冲突的范围和力量。”[12]117
三、填空装置:留白、多元、解构
吉尔·德勒兹和费利克斯·瓜塔里提出“根茎”概念,借助植物根茎的形象阐释非中心、无规则和多元化的思维方式。“所有根茎都包含着节段性的线,并沿着这些线而被层化、界域化、组织化、被赋意和被归属,等等;然而,它同样还包含着解域之线,并沿着这些线不断逃逸。”[13]10这种理论思想用于文学隐喻并跨界到数字媒介。小说《白狗秋千架》的语言精练,有“意在言外,韵外之致”效果,表意适可而止,为读者留下深刻回味、补充和联想的空间,如蔡队长与暖的关系,只用暖脸上的红晕去表现;蔡队长临别亲吻暖的额头,称之为“小妹”,文末省略号,这些都为读者留下想象填补的空间,需要读者借助知觉经验开拓审美视域,形成多种感觉融合,从接受美学的视角去促进文本的增殖和意义的生产。
电影和文学是不同的艺术媒介。文学表达具有暗示性和多义性的特点,电影则以画面语言和行动影像直接表情达意,它比文学表达更清晰。电影《暖》中,主人公和戏班演员小武的关系通过林井和与村民所见所闻揭示出来,并通过展示亲密场面和二人距离疏远以及镜头不断闪现去传达明确信息。而小说《白狗秋千架》通过肖像和语言表达,“他可没把我当小孩子。他决不能把我当小孩子”“他四肢修长,面部线条冷峭,胡楂子总刮得青白”[3]209。通过暖的语言和叙述者对蔡队长外表选择的描绘来暗示他们之间的关系。莫言将“暖”对蔡队长的一厢情愿叙述为幼稚的幻想,这不仅是作者对新时期之前社会建构的单一评价标准的反拨,还欲建构丰富的文学世界;莫言安排知识分子和文艺兵进入小说,并否定了他们的爱情观。知识分子和文艺兵的未来理想并不在乡土和农村基层,从概率上讲,不大可能留在乡村终老一生,也不太可能带农村姑娘到城里生活,可以看出作者是站在乡土位域上以大悲悯情怀审视乡土的衰败和未来前景的。莫言还对重实利的乡土婚恋观进行了否定:暖在现实的困境中嫁给哑巴,无声的婚后世界并不幸福,坚持求子则说明了暖的婚恋观的现实底色和婚姻的不幸。莫言的小说《白狗秋千架》探索乡村的未来,但没有给出具体的走向。
在电影《暖》中,对三种类型爱情予以同等地位的展现,作者肯定了不同类型爱情的价值。浪漫、回忆和现实温情填充了爱情的不同空间,导演并没有采取非此即彼的简单判断方式,每一种爱情都有快乐和悲伤,导演的辩证观点折射新世纪的理性特点。20 世纪80 年代,文学激进化、思想化和干预社会的能量已熵化,理性反思和回归“八十年代”成为研究热点。小说《白狗秋千架》多元化的意义反衬乡土思想的混杂:儒道文化、齐鲁文化及西方文化共同构成高密东北乡文化的“根茎”。新旧社会出现矛盾,思想杂糅体出现。在小说《白狗秋千架》开篇中,“暖”对知识分子“我”自诩的“高等人”有双重态度,既厌恶又羡慕。“厌恶”凸显乡人的自卑,“羡慕”反射乡村对城市及文明的向往,这在电影《暖》中也有类似场景。林井和赠与哑巴的名牌烟和承诺的二锅头,这使哑巴和林井和的关系由僵化到缓和,再到融洽。并且哑巴意欲让渡妻子,催促暖跟随林井和到城市生活,希望他们过上幸福的城市生活,城乡差别凸显出来。《白狗秋千架》的篇尾,暖说出了内在的原因:“怕你厌恶,我装上了假眼。我正在期上……我要个会说话的孩子……你答应了就是救了我了,你不答应就是害死我了。”[3]216小说开篇嘲讽的语气到篇末的羡慕态度的转变,折射了乡土社会在社会现代化中的尴尬处境。
电影《暖》肯定了乡村现实生活考验的爱情和婚姻的价值,肯定了对乡村及其文化的坚守态度,这是20 世纪90 年代城市扩张过程中对乡村的怀念和对当下社会的关注;而小说则探讨了乡村的未来发展问题,预设时间跨度相对较大,例如对狗的纯/杂的历史叙述。再比如秋千架娱乐设施的布置,文中“我”与秋千架共同绑架了暖的命运。秋千本来是对丰收年的庆祝设置,荡秋千仪式也是乡村美好希望的承载和缓解乡村劳动紧张和疲惫的形式。仪式是乡村文化的一部分,“仪式过程中最值得一提的普遍特征在于,它以高度特定的方式使持续期和延长期地方化”[14]240。然而在《白狗秋千架》和《暖》中却成为祸端的起因,秋千质量不过关和使用频率高成为祸端的根本原因,其中隐含着对乡村粗陋仪式的担忧。“我”的性补偿和帮助教育暖子女的补偿是否能够使纯种延续,是否能恢复生命力,还是未知数。在这一层面上讲,小说《白狗秋千架》对种的堕落、救赎与《红高粱家族》是有区别的,《红高粱家族》对“我奶奶”和“我爷爷”的赞颂,寄予了民族复兴的厚望,与沈从文创作理念有相似之处,但前者对此救赎方式存有一些疑惑。
小说《白狗秋千架》有“狗”的隐喻,电影《暖》中缺失狗的意象,增强了人的元素。戏班的武生与暖的交往,哑巴一直来对暖的倾慕、骚扰和帮助,“我”与暖的交往。电影中还掺入更多的现实元素:哑巴以实际行动感动了暖,暖也不离不弃;贯穿整个电影的是情,无声的爱情战胜了各种信誓诺诺的爱情,武生和林井和成为爱情的失败者,但他们却是社会的成功者,情和现实之间形成巨大的裂隙。电影末尾企图调和此矛盾:暖和哑巴让“我”把他们的女儿带走,意图使之拥有优渥的物质生活和优质的教育,究其原因,他们对社会等级的屈服出于对儿女命运的担忧。文中的“我”是否能够完成抚养暖和哑巴孩子的承诺,是否能够延续与暖的旧情,电影的末尾似乎给出了答案,林井和的承诺犹如飘蓬,没有根基。
鲁迅的返乡具有“恋乡”和“恨乡”的双重心理,儿时美好情景和当下乡村的衰败和沉闷鲜明对比,乡民和作者之间形成看与被看的关系,乡民封建传统伦理和启蒙个性形成对照关系,作者笔下流淌着悲悼、怜悯和救世情感。郁达夫的返乡反思旧式家庭婚姻的不自主性,家长意志与子女自主思想矛盾。周作人则以回忆家乡风物展现名士风度。传统文人品格和启蒙先锋思想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面对家乡的两种态度,有时两者也糅合在一起。小说《白狗秋千架》以第一人称回乡的视角铺展情节,互文“返乡文学”,这种思维模式凸显了“鲁迅式”的启蒙精神。莫言的《白狗秋千架》在忏悔的心情下叙述与女主人公的交往细节:巧遇开头,拜访探秘女主人公的生活现状,离乡返城。“我”在忏悔和希望艳遇的氛围下展开故事,这是《聊斋志异》式的思路和情节安排。尤其篇末设置的突兀的情欲满足,这种想象的艳遇完全依托乡土生育伦理,是靠不住的,且这种违反儒家道德的行为建基在乡土生育伦理之上,托词荒谬。“我”的知识分子身份获得乡土的崇敬和屈服,隐喻乡土文明以自身献祭于城市文明。莫言通过一个浪漫的男女故事反映社会现实,这也是第三世界的寓言式写作,“第三世界的文化和物质条件不具备西方文化中的心理主义和主观投射。正是这点能够说明第三世界文化中的寓言性质,讲述关于一个人和个人经验的故事时最终包含了对整个集体本身的经验的艰难叙述”[15]545。
电影《暖》以长镜头丰富了电影的内涵和意义。影片开头以景深长镜头和运动长镜头来展现林井和返乡,展现环山小路,上坡和下坡,为观众留白。风景被重新编码,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林井和在艰难和愉悦的基调下返乡,近景和远景交错,闪入和淡出,将回忆和现实有机穿插起来,凸显影片层次感。日常生活镜头不断闪现,延缓了小说中奇遇和“探险”的紧张感。永恒的自然和乡村融为一体,自在自为地反拨着城市文明的焦虑与峻急。电影运用了牧歌情调抒情,而小说则借助聊斋文化的古典风格和气氛去结构故事,它们共同的特点是以中国风格来解构现代文明的偏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