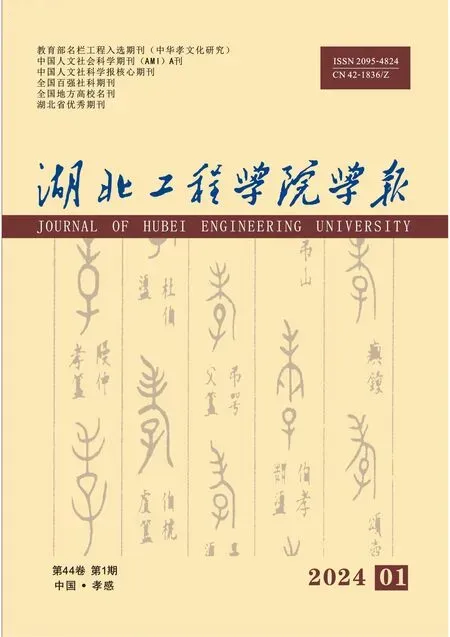黄道周《孝经集传》中的爱敬情感漫议
——兼及对阳明学爱敬关系的重订
陈萌萌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黄道周字幼玄、号石斋,是明代著名的经学家、理学家、书法家,其学统回归六经、重拾经世致用之风。《孝经集传》是黄氏孝经学集大成之作,民国经学家曹元弼曾盛赞该书:“自时厥后,注解多浅近,不足观,惟明黄氏道周孝经集传融贯礼经,根极理要。”[1]234《孝经集传》体现了黄道周对《孝经》乃至儒家孝观念的理解,其论孝多言及爱敬。作为两种不同的孝子之情,爱敬在互动与平衡中起到了不同的作用。
纵观《孝经集传》,言及行孝中的爱与敬之情,黄道周既有看似矛盾之语,亦有与阳明学迥异的观点:较之王阳明论孝多言爱而罕言敬的倾向,黄道周极为重视敬在孝中的位置,甚至有“性,知敬者也”[1]130之言;对于爱与敬的关系,黄道周一方面主张以敬为本,同时又认同爱在逻辑上先于敬而产生。黄道周“敬本”的特点已被当前学界注意到,如学者许卉便指出黄道周所论之敬“不仅是本体功夫,而且具有本体涵义”[2]。本文的问题意识在于:在黄道周的孝论中,爱与敬各自承担了怎样的功能?二者是怎样的关系?倘若黄道周认同孟子的“孩提知爱”“及长知敬”是儒家的不刊之论,那爱的发生必然在逻辑上先于敬,如此“敬本”又何以可能?本文拟对上述问题进行阐释,并在此基础上关注黄道周如何回应阳明学孝论“重爱轻敬”的特点,以期探讨传统儒家孝观念中,爱与敬两种情感是如何作为“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使行孝之际孝子情感发而皆中节。未得肯綮之处,恳请方家赐教。
一、二者立而天下化:黄道周论孝中的爱与敬
《孝经》言:“生事爱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尽矣,死生之义备矣,孝子之事亲终矣。”[3]145爱与敬是行孝中的重要情感,二者不可废偏。在论孝兼备爱敬的基础上,《孝经》历来注疏中多有论及爱与敬的关系,如董鼎便认为爱易而敬难[董鼎《孝经大义》记载:“上文兼言孝悌礼乐四者,至此又独归重于礼。至于言礼,则又以敬为主。盖父母于子,一体而分,爱易能而敬难尽,故经虽以爱敬兼备,而此独言敬。”(参见[元]董鼎:《孝经大义》,清通志堂经解本。],吴澄则认为爱与敬互文见义、不可偏废(1)吴澄《孝经定本》记载:“悦者,深爱和气愉色婉容之谓。上所教者言敬而不言爱,下所效者言爱而不言敬,互文以见也。”(参见吴澄:《孝经定本》,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由敬而生的悦乐同样也体现了爱。黄道周《孝经集传》一书多论及爱敬的作用与关系,诠释了孝子秉爱敬情感侍奉父母的意义所在。
(一)爱与敬的作用
《孝经》认为孝中所涵摄的爱与敬,在情感的倾注对象上有所不同:“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4]10孝子面对母亲,是亲爱之情更多一点;对于君主是敬多一点;面对父亲则往往爱敬和谐。黄道周认同孝涵摄爱敬两种情感,并认为对天下人的爱敬情感均源自事父之孝:“母亲而不尊,君尊而不亲。以父教爱,而亲母之爱及于天下;以父教敬,而尊君之敬及于天下。故父者,人之师也,教爱、教敬、教忠、教顺,皆于父焉取之。”[1]39上述观点认为爱与敬兼备于孝德孝行当中,且由于对象不同,爱与敬的比重往往有所差异,但根本上二者均是不可或缺的。爱与敬之所以如此重要,主要由于以下原因:
首先,敬主别异,爱主和同。儒家经典论及“和同”与“别异”,多以礼主异而乐主和同:“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好恶着,则贤不肖别矣。刑禁暴,爵举贤,则政均矣。仁以爱之,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矣。”[5]这即是说明,礼的功能在于保证上下之别与伦理秩序,乐的作用则体现在让人心生和同、使共同体内产生向内凝聚力。尊卑之分与伦理秩序的强化,使人自然对为尊上者产生敬意,而伦理关系中向心力的存在则使个体间能相亲相爱、融为一体。我们很容易感受到自己和父母因为爱而成为一个统一的共同体,这便容易理解缘何奉养父母须具爱的情感;但或有疑问,为什么侍奉父母一定需要庄严肃穆的敬意?传统等级伦理秩序的瓦解与现代对自由平等的推崇,更是让人提出诸如“儒家孝论所强调的敬是否会强化父子之间的尊卑等级”等批判性问题。对此黄道周认为,敬的意义不在于使子女成为父母的附庸,而在于让子女尊重父母的情志(过分尊重便导向“不敢谏”);且爱与敬应发而中节、相互协调,用爱的亲和来调适敬的疏离:“敬则不敢谏,爱则不敢不谏,爱敬相摩而忠言迸出矣”[1]189,“以不谏为正,则君无复正臣,父无复正子矣……则是君可以杀其臣,父可以杀其子矣也”[1]172。过分强调以敬事父,往往疏远父子关系甚至导致父有过而子不敢言;而不谏导致父母陷于不义则是更大的不孝。此时爱的意义在于使孝子感知到自己对父母的爱和关切,从而以委婉方式继续劝谏;敬的意义则在于劝谏之际不至于直言冒犯,甚至强迫父母改变行为,而是以合乎礼义的方式“义以正之”。可见在家庭伦理中,事亲以敬的目的不是疏远亲子,而是在于让子女明晰自己与亲长间的伦理秩序,使子女与父母均能依天理伦常而行合宜之道;事亲以爱的意义则在于调适“礼胜”而不可避免的亲情疏离,使得父子一伦中的双方能相互关怀亲睦,并能在有限的个体生命之上传承家庭的共同体命脉。
再者,敬能让人敬畏父母、不敢轻慢,爱能使人亲近关怀父母。《孝经》言圣人之政教能够“不严而治、不肃而成”,其根本在于父子伦理孕育了人能爱能敬的潜质:“圣人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圣人之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其所因者本也。”[3]86对此郑玄注为:“因人尊严其父,教之为敬,因亲近于其母,教之为爱,顺人情也。”[3]86郑注认为人能爱能敬,是基于圣王之教化顺应了孩童自然敬畏父亲、亲近母亲的天性。可见人性中本具爱敬之理,圣人顺人情而教化,因此爱敬情感得以从源初的家庭场域中推扩出去。郑注点出“为教本性”之义,黄道周进一步点出“为性本天”、从天的维度讲爱敬何以可能:“天严而人敬之,地顺而人亲之。敬之加严,亲之加忘。人托于地不知有地,覆于天惟知有天,其渐然也”[1]93,以及“敬不敢慢,爱不敢恶,得严于天者也”[1]94。据黄氏注,孝子能爱能敬,根本在于天的刚健自然让人敬畏,地的柔顺则让人亲近,圣人立道设教不仅本于孩提知爱敬父母的天性,更是本于人对化育之天和长养之地的敬与爱。而落到具体之个人,具备生养恩义的父母便是孝子之在世的天地。因此出于敬意,孝子则不会怠慢父母;出于爱意,孝子则不会恶对父母。正如子游问孝时孔子的回答:“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养护父母与养护犬马的区别正在于,敬意使得孝子尊重父母的地位与威仪,尊重父母作为独立个体所具有的意志与行为,不将自己的意志凌驾于父母。而爱则能使孝子侍奉父母不是出于身份义务的强制,而是出自真挚自愿的亲慕情感;因为爱的存在,孝子事父之际则不是屈意承欢,而能自然表现出和气愉色婉容。(2)《论语·为政篇》四条“问孝”体现了孔子对于孝中爱敬情感的理解,对这一问题的深入阐释,可参见蔡杰《孔子孝论的爱敬情感析论》,《伦理学研究》,2023年第3期,第59-66页。
最后,基于《孝经》学以“孝”为天地之经义的立场,爱与敬的意义体现在其让人不仅能不轻慢恶对自己的父母,更能尊重善待更广泛共同体中的他者:“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3]18出于对父母的亲爱与感恩,孝子自然能在事亲之际真正关切爱护、“不敢恶于亲”,出于对父母的敬重,孝子也自然能时时处处以礼节之,不至颠覆父子一伦的秩序;而将对父母的爱推移到更广泛的共同体中,便能关爱善待无甚关系的他者;将对父母的敬重之情推移出去,对待他人便不敢随意恶对怠慢。因此黄道周亦言:“夫父母所敬爱,敬爱之。其不可敬爱,如之何?曰:不敢恶慢焉已矣。”[1]22出于对父母的爱敬情感,孝子面对父母所爱敬的人事亦能抱以爱敬;即使不能爱敬,也不会恶对轻慢。因此孝子能将孝伦理中的爱敬情感推扩至更广泛共同体中,进而消除非血缘间的轻慢与恶对,底线式地止息了威胁社会共同体的人际危机,最终“暴乱既免而后礼乐可作”[1]67、实现“二者立而天下化”的政治理想。可见黄道周乃至《孝经》学重视爱与敬,不仅是基于这两种情感在儒家孝伦理中的作用,更是在《孝经》“孝本论”的立场上,希图通过从家庭伦理向政治伦理逐层推扩爱与敬,以期实现社会共同体的繁荣。
(二)敬者爱之实:爱与敬的关系
黄道周认同爱与敬应兼备于孝子之情中,且因对象不同,爱敬取舍的程度与先后顺序也应有所差异。可见爱与敬的情感并非完全等同,深究爱敬内部,二者同样存在着本末与先后关系。
对于爱与敬的关系,黄道周直言敬是爱之志:
爱者,敬之情也;敬者,爱之志也。非志无情,非敬无爱,故以一敬而教忠、教顺、教仁、教让,是文王之学之所从出也。[1]17
心之所之谓之志,“志”即意愿、心之所向之义,引申为指挥、导率。此言即是在爱敬关系上以敬为本,认为敬引领并导顺了爱,爱则是由敬之所发,是在敬的提撕引导下产生的情感。结合上文“爱敬相摩而忠言迸出”之例,可较好理解“敬者爱之志”:出于对父母的关爱,当父母有过时,孝子往往忧心焦虑以至急于劝谏。此时子女之行尽管出于爱,但仍往往因为“因爱生忧”而做出劝谏方式不当、霸凌父母意愿等伤害父母情志的行为。可见尽管子女行径是基于“过剩”的爱,但仍然造成了对父母的伤害,不可称之为孝。敬的意义正在于调适爱的程度、引导爱的方向,让孝子对父母的爱以合乎性理的方式呈现出来。
“爱者,敬之情也”一句则较难理解。黄道周此言是以敬为爱之本源,以爱为敬之所生,这或能推出敬在层级上是高于爱的,在产生逻辑上是先于爱的。而依孟子言,孩提知爱、稍长知敬是天赋之能,爱在发生逻辑上必然先于敬;且黄道周亦尝言:“爱至而敬亦至,敬至而色亦至矣。”[1]54这即是认为事父之敬是基于孝爱而产生,是先产生了对血亲的爱慕亲近,进而才生发出对尊长的敬重感。对此或有疑问,爱敬同属情感范畴,爱如何能从敬中产生呢?
黄道周本条注文是对《孝经》该句的发挥:“吾尽吾敬以事吾上,故见为忠焉;吾尽吾敬以接吾敌,故见为信焉;吾尽吾敬以使吾下,故见为爱焉。是以见爱亲于天下之民,而见贵信于天下之君,故吾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3]18经文基于“移孝作忠”等情感推移说,认为君子将事父之敬推移至君臣关系便呈现出忠、推扩至社会共同体中便呈现为对天下万民的仁爱。可见“爱者,敬之情也”一句,意为以敬的情感为根本,心怀敬意时面向不同的伦理关系均能产生合宜的情感,其中便包括对于非血缘的他者的关切与仁爱。此处爱与敬的关系在于,敬成为链接“爱亲之情”与“爱他之情”的枢纽:子女出生之时便自然具备对父母的依恋亲爱,这是天赋自然的孝爱情感;由于“爱至而敬亦至”,及其稍长便能对父母产生礼敬之情;由于事父之敬推扩到其他伦理关系中,均能使个体面向对象生出合宜情感,因此对于他者的爱也可以从“敬”中推出。由此可见,在黄道周乃至儒家父子伦理最为重视的爱与敬两种情感中,孝子之爱亲是泛爱、仁爱的情感源头,敬的情感则是使孝爱向仁爱的持续推扩的动力机制。
作为情感源头的爱与作为动力机制的敬,均是从源初的家庭场域中培养起来。曾振宇教授指出,《孝经》立足“孝本论”,使孝“跨越父子血缘亲情边界,向陌生人社会无限扩张与蔓延,衍变为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大经大法”[6]。基于《孝经》的立场,黄道周言“敬者,爱之实也”意在强调敬的“本体义”(3)对于敬的“本体义”,依黄道周“爱者,敬之情也”与《孝经》“吾尽吾敬以使吾下,故见为爱焉”等句,对他者具有亲爱情感,是因为“尽吾敬以使吾下”,对非血缘的他者的爱,是通过礼敬他人来实现的。因此“敬的本体义”以及下文“敬本”之语,意在指出敬的情感是泛爱他人的情感基础和推扩动力。对于黄道周“敬者,爱之实也”一句的“实”作何解,笔者认为该处或近似于朱熹对《孟子》“仁之实,事亲是也”的讲——“实”即为“华实之实”,即“基础、本源”之义。兹录朱熹原文如下:“‘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此数句,某煞曾入思虑来。尝与伯恭说‘实’字,有对名而言者,谓名实之实;有对理而言者,谓事实之实;有对华而言者,谓华实之实。今这‘实’字不是名实、事实之实,正是华实之实。仁之实,本只是事亲,推广之,爱人利物,无非是仁。义之实,本只是从兄,推广之,忠君弟长,无非是义。事亲从兄,便是仁义之实;推广出去者,乃是仁义底华采。”(参见《朱子全书》第15册,第1821页。)依朱子之言,行仁的基础与发端在于事亲,将孝爱推扩出去便是普遍性的爱他者,因此事亲是“实”(基础、端绪),泛爱万物则是由孝行推扩出的“华采”。同理类比黄道周“敬者,爱之实也”一句,人能超越家庭伦理而泛爱社会中的陌生人,正是在于以敬的情感为基础与端绪(“实”),心怀敬意时面向不同的伦理关系均能产生合宜的情感(“华采”)。:尽管逻辑上爱亲先于敬亲而产生,但从孝爱向普遍之仁爱推扩,需要敬作为动力机制推动爱跨越血缘亲情边界。这也不难理解,为何黄道周提出“语孝必本敬”[1]1,出于上述作用,虽然爱与敬同属情感范畴,但在《孝经集传》中敬的地位更被重视,甚至具有“敬本”之义。
二、爱敬与天通:黄道周的“敬本”何以可能
以上论述中有一个关键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敬凭什么能作为枢纽,推动爱的推扩与转化?这一问题的根本在于,敬相对于爱的“本体位置”何以可能?基于此,本章将探讨“敬”在爱敬关系中占重要地位的学理依据。
(一)从人道的维度言敬
爱与敬最先为人所感知和认识到,是发生在血缘家庭当中,孝子意识到父母的地位崇高,因此侍奉父母之时“敬”的情感得以显豁。可见敬是产生于具体生活之中、关切于现实存在的一种情感,探讨“敬”的尊崇地位何以可能,首先要从现实的维度(也即人道的维度)来切入。
黄道周十分重视德礼教化:“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是一片金声;礼者,敬而已矣,是一片玉振。”[1]970黄道周以孝为成德之本、以礼为成德之径,礼教在儒者人格培养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对此曹元弼评价为:“大本谓之孝,达道谓之礼……郑君而后见及此者,黄氏而已。”[1]235基于“孝本论”跨越血缘边界、将孝扩张至社会共同体的立场,人在血缘家庭中培养起来的爱敬情感是需要不断向外推扩的,而推扩与转化得以可能则在于礼教。而在黄道周看来礼教得以可能关键在于敬,敬是礼乐教化之实:“盖孝为教本,礼所由生,语孝必本敬,本敬则礼从此起。”[1]1礼教仪制真正行之有效,在于行为者意识到了礼敬对象美德与地位的崇高。可以试想,倘若我们并未意识到父母、先祖处于尊位,而是将其视为与自己平等,那我们便很难说服自己去礼敬父母,正如我们很少对同龄的朋友抱以敬意一般。黄道周进一步阐释了从“能敬”到“能行礼”的内在原因:“敬而后悦,悦而后和,和而后乐生焉。敬一人而千万人悦,礼乐之本也。”[1]141礼乐得以行之有效是基于“敬一人而千万人悦”:“敬一人”指孝子对于父母的敬意;“敬而后悦,悦而后和”则说明诚心礼敬父母能使家庭关系悦乐和谐(4)这里能体现敬之于爱的提撕意义:爱父母是孝子的自然情感,但要保证这种情感时时刻刻无间断地生发,则需要敬在其中提撕调适。;这种情感能从家庭推扩至其他共同体中,并面向不同伦理关系各自产生中正合宜的情感。可见“千万人悦”这一结果得以实现,实际上正是基于上文所阐释的“爱者,敬之情也”——敬的“本体性”意义,敬的情感确是礼乐之所从生。
总而言之,在黄道周看来,礼的产生与运作得以可能,如果要在人道维度或者人性内部寻一个根源,是基于敬的情感;而在具体生活中,敬的情感最早是在家庭场域中培养起来。基于《孝经集传》对礼教之于成德的重视,可以认为黄道周极为重视敬的效用。
(二)从天道的维度言敬
上文大多基于伦理学的视角,从人道的维度讨论敬之于家庭伦理乃至政治生活的意义;但倘若追问一句,为什么子女自然会对父母产生敬意,儒家又该如何解释自然情感的形上来源呢?值得注意的是,宋代以来“天”的维度逐渐确立起来,在理一分殊的架构中,孝子具体之敬源初产生于分殊之父子关系中,而这种油然而生的敬情实皆本于敬天。从天道的维度来看,因为人对于超越者(天)的情感是敬而非爱,所以落到具体的人伦当中就有了“语孝必本敬”之语。
唐文明教授指出,孝的终极依据在于天地之心:“孝并非一般人所认为的自然情感或仅仅基于血缘的情感,而是人直接‘对越天地’产生的一种超越的觉情。”[7]在面对“子女何以对父母产生爱敬情感”这一问题时,黄道周并未仅以孟子“良知良能”说来进行诠释,而是在将爱敬视为自然禀赋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爱敬父母是基于爱敬天地:
天地生人,无所毁伤。帝王圣贤,无以异人者,是天地之性也。人生而孝,知爱知敬,不敢毁伤,以报父母,是天地之教也。天地日生人而曰父母生之,天地日教人而曰父母教之,故父母天地日相配也。[1]91
黄道周认为天与地具备生生之德,这体现在天地孕育万物并使万物整全而无损伤。因此从现实层面来看,具体的每个人的生命是由其各自的父母赋予,是父母生养教育了子女;而从宇宙层面看,则是天地生生之仁心赋予普遍的“人”以生命。因此黄道周明言“人生而孝,知爱知敬,不敢毁伤,以报父母,是天地之教也”,人能切身感知天地生生之意,且由于“父母天地日相配也”,父母即是子女在世的天地,因此人面向生养己身的父母自然产生爱敬情感。
子女感念父母的生养恩义,其超越依据在于感念天地的生生之德;而感天地生生所应的孝情既包含爱也包含敬,对此又何以强调敬为爱之实呢?黄道周从天(父)与地(母)的性质角度,解释了为何多言“敬天”而非“爱天”:
天严而人敬之,地顺而人亲之。敬之加严,亲之加忘。人托于地不知有地,覆于天惟知有天,其渐然也。故严者始教者也,亲者终养者也。人养于膝下,鸟兽昆虫养于山泽,其养之皆地,其教之皆天也。[1]93
圣人之道,显天而藏地,尊父而亲母。父以严而治阳,母以顺而治阴,严者职教,顺者职治。教有象而治无为,故曰严父,不曰顺母,曰配天,不曰配地,是圣人之道也。知性者贵人,知道者贵天,知教者贵敬。敬者,孝之质也。[1]91
天的特性为刚健威严,对应父是肃穆严格的,因而人油然生敬;地的特性是厚朴顺承,对应母是温柔抚育的,因而人自然亲爱。而结合现实生活,人往往对于威严肃穆者能长期抱有敬意,而对于安养抚育者而往往忘却其功绩,因此敬的情感常常处于显见的位置,而爱的情感则多隐匿于润物无声当中。且地(母)主要是潜移默化地安养与治理,其作用在于保养万物并使其安乐幸福;乾健的天道则昭示着积极进取、自强不息,天(父)承担教化职能,能使人革除习染之弊、不断追求并践履理想人格,而后者恰恰是儒家更为重视的。
黄道周认为“君子敬天则敬亲,敬亲则敬身”,借助“严父配天”之说将父的职责与天的使命关联起来,并认为较之于无为的安养与治理,天与父所承担的教化职能更为重要,而人面向天与父的情感多为敬而非爱。这便不难理解,缘何在爱与敬之间,黄道周更为强调敬的意义,甚至直言“敬者,孝之质也”。
三、黄道周对阳明学爱敬关系的重订
黄道周少宗朱子,并盛赞晦翁之学“百世而无弊”;同时其又主张会通朱王,并作《阳明先生集要序》《重建王文成公祠碑记》等文,积极关切晚明的心学思潮。在孝论以及爱敬关系的话题上,王阳明与黄道周持不同立场,一言以蔽之,在于阳明多言爱而罕言敬,黄道周则重视敬的效验。现今已无史料佐证黄道周在这一问题上曾有意识针对阳明学派进行阐发和重订,但可以确认的是,黄道周之论确可在某些维度上纠偏阳明学的流弊。
(一)王阳明论爱敬关系
较之宋代《孝经》学以天地之心为孝的形上依据、因怀疑“私欲之爱”而强调敬的提撕调适义,《王阳明全集》除引《孟子》“爱亲敬长”之言外,几无面向孝中的爱敬关系进行阐释,更是鲜少论及敬在行孝中的意义。可以说,在面向孝的阐释中,王阳明体现出多言爱而罕言敬,重视爱的开启作用和忽略敬的提撕调适的倾向,这主要体现在王阳明是如何认识“孝子之行何以可能”这一问题:
《礼记》言:“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须是有个深爱做根,便自然如此。[8]3-4
将“和气”“愉色”“婉容”视为孝子侍奉父母时的具体情态与行为,上述孝行得以“自然如此”,则是基于以孝子对父母真挚的爱亲情感为根。在阳明看来,子女能够行孝,是因为人子生来便对父母具有诚挚的爱,出于爱意子女自然会关怀父母的生活、体贴父母的情志、做出诸多孝亲的行为。可见对于“孝何以可能”这一儒家关键问题,王阳明的立场是认为孝爱根植人性当中,是良知面向父子一伦的自然显现,行孝本于良知,而非对天地生生之意的感应。可见在阳明学的语境中,孝的根源在于吾心之良知而非天地之心,当良知面向父子一伦显豁,孝爱情感自然能产生。上述“重爱轻敬”的倾向甚至影响到泰州学派:“赤子出胎,最初啼叫一声,想其叫时,只是爱恋母亲怀抱,却指这个爱根而名为仁,推充这个爱根以来做人。”[9]836罗汝芳此论意即以爱亲之情为行仁的根本,爱父母的情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程朱对待已发之情的态度极为审慎,为防止自然生发的爱亲情感沦为私欲之爱,朱子重视克己复礼的调适功能;而在阳明学当中,礼敬之于爱的调适作用却鲜少被言及。对此或有疑问,倘若爱的自然发用导向过分与虚妄,这一问题该如何处理?传统的进路是:爱亲发用自然-有呈现为人欲之爱的倾向-礼敬提撕调适-爱合乎天理,这一进路中敬有着不可泯灭的作用。但阳明论及孝时多言爱而罕言敬,这是基于心学以良知取代了敬的作用:
澄在鸿胪寺仓居,忽家信至,言儿病危。澄心甚忧闷,不能堪。先生曰:“此时正宜用功。若此时放过,闲时讲学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时磨炼。父之爱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个中和处,过即是私意。人于此处多认做天理当忧,则一向忧苦,不知已是有所忧患,不得其正。大抵七情所感,多只是过,少不及者。才过便非心之本体,必须调停适中始得。就如父母之丧,人子岂不欲一哭便死,方快于心。然却曰‘毁不灭性’,非圣人强制之也,天理本体自有分限,不可过也。人但要识得心体,自然增减分毫不得。”[8]21-22
陆澄在其子病危之际的忧虑不已使阳明意识到,爱作为情感受制于个体形骸与私欲,其发用流行往往导向私欲遮蔽、过犹不及的状态。因此爱的发用离不开调停适中,调适的依据在于天理本然的分限,其路径则在于“戒慎恐惧”的诚意之功。在心学“心即理”的命题下,对情欲进行调停适中的依据则在于心体,作为心之昭明灵觉的良知承担了这一责任。可见在阳明看来,良知的觉察和判断能力,能在爱的情感发生偏离之际,对其进行调节;因此只要保证良知无蔽,爱之发用便能时时中和。
此外,在儒家论孝中,敬的情感多经由行礼来体现,《论语》“孟懿子问孝”一章便通过解释“事之以礼”来说明侍奉父母应包涵礼敬情感。然而在王阳明看来,后世的礼仪制度繁复支离,借助这种“孝礼”来事亲往往使子女流于形式化的恭谨与持敬,而非以诚挚的情感行孝:
后世大患,全是士夫以虚文相诳,略不知有诚心实意。流积成风,虽有忠信之质,亦且迷溺其间,不自知觉。是故以之为子,则非孝;以之为臣,则非忠……今欲救之,惟有返朴还淳是对症之剂。[8]248
阳明厌弃繁文缛节展现出的虚伪的敬意,在他看来虚礼不仅消弭了人之忠信,更通过伪饰的敬行阻碍了“真诚恻怛”的孝亲情感产生,影响了孝行的动力机制。按儒家讲法,敬是人天赋本有的自然之情,因此礼应是契合人情的导顺而非固定强制的准则。在讨论事亲之礼时,王阳明更强调情感的诚挚与自然,而非仪制的谨密与庄重。尽管在理论上,爱亲敬长的情感均是良知面向父子一伦的发用,但现实中由于孝礼的僵化,敬往往流于貌恭虚敬,难以发挥其应有效用。
王阳明孝论呈现为“良知发用-产生爱亲情感-良知察识调适”的架构,良知兼具情感源头和动力机制两种作用。不能否认,这一架构确实具备易简明白的优点,良知在其中也替代了敬的察识与提撕作用。但需要意识到,敬的意义不仅在于对自然情感提撕调适,同时体现在维持合宜的伦理秩序、使主体能因保有对外在超越者的敬意而自我省察克治等。上述意义的缺位一定程度促成了阳明后学中泰州诸儒“非名教之所能羁络”[9]767甚至“荡轶礼法,蔑视伦常”[10]25的思想风气。而晚明黄道周所关切的,正是通过在家庭场域中培养并推扩敬的情感,重建民众心中对天、父、礼的敬重感。
(二)黄道周的方案
据上可知,王阳明罕言敬的效用主要基于以下原因:从现实维度,敬作为情感往往流于形式化的恭谨与持敬,难以呈现为本源、诚挚的情感;从形上维度,人能行孝不再基于对天地生生之大德的感通,而是由于良知面向父子一伦的发用,天的维度被解构使得事天之敬意一并淡化,因此阳明学少有对外在超越者的敬。
首先我们来看黄道周对于王阳明所关切的“虚礼”、“虚敬”问题是如何处理。阳明学抨击虚礼、虚敬,乃是面对守旧僵化的传统礼制,主张尊重人情时代变化:“此虽先王未之有,亦可以义起,三王之所以不相袭礼也。若徒拘泥于古,不得于心,而冥行焉,是乃非礼之礼,行不著而习不察者矣。”[11]王阳明强调“心为礼本”与“缘心制礼”,突破了传统礼制的僵化桎梏,促进礼从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践履;同时也使得阳明后学流于士风蹈虚、招致“参之以情识”的批评。在此流弊下,晚明行礼之时多出现情欲恣肆而爱敬不存的情况:“凡来吊者,主人留以宴饮,甚至縗麻以侑酒,歌吹以燕宾,恬不知怪……使为人子者,辍哀痛之情,以周旋于宾友,薄送死之具,以尽力于豆觞,此尤风之最恶者也。”[12]可以说阳明学所带来的情欲恣肆,导致了现实中礼乐虚伪、爱敬不存。
黄道周所面临和关切的正是上述问题。阳明学的思路是:由于现实中的礼制典仪多为虚饰,这种仪式中的‘持敬’自然也是伪装的,既如此则不如抛却虚伪的持敬,直接发用本心的爱亲情感。对此黄道周的处理方式是,在孝本论的语境中爱与敬必然是真挚的情感,敬作为一种情感本身就不是虚伪的,礼文可能虚伪,但当礼本于人子之爱敬,礼就不是虚伪的:“故中和致则爱敬生,爱敬生则恶慢息,恶慢息则暴乱之祸庶乎免矣,暴乱既免而后礼乐可作也。”[1]67王阳明认为礼乐“得于心”,礼乐的创制和运作是需要基于人心人情,而不仅仅是孝与爱敬;而在黄道周乃至《孝经》学看来,孝是天地之经义,仁爱礼敬皆是从爱敬父母推扩而来,礼乐制度的情感本源在于家庭伦理中的爱敬情感。黄道周将爱敬情感视为圣人制礼作乐的本源情感,礼乐得以行之有效是基于敬的情感本身就是真挚的。可见较之阳明学,黄道周重新定义了“敬”与“礼”的逻辑序列:王阳明认为礼若虚则敬为虚,黄道周则认为敬为真则礼必真。因此对于阳明学所忧患的“礼虚因而敬虚”的问题,黄道周的方案是重拾敬作为本源情感的意义,当敬与爱一样成为根于心的本源情感,而非行礼时的外化显现,行礼之时外化的敬意自然不会流于虚假伪饰。正如学者蔡杰所指出,黄道周“立足并发掘父子一伦的天性情感,来救治身边的人伦关系,从而重新建立起社会秩序”[13]。黄道周从孝本论出发重拾敬作为本源情感,其意义在于扭转晚明情欲恣肆而仪制虚浮的弊病,重新让民众意识到行礼并非虚伪的仪典形式,而是怀着真切的对父母、先祖乃至天地的爱敬情感所自然产生的礼敬行为。
第二个需要处理的是,阳明后学缺乏对外在超越者(天)的敬重感,而黄道周则通过重建天的维度来使敬的情感有一个形而上的依归。结合上文晚明民众对待丧祭之礼的态度可知,此时外在客观的义理之天逐渐抽象并瓦解,人们难以感知到己身与天地的相通。因此问题的焦点便在于,通过打通天人关系来重新挺立天的维度。
如何实现形上之天与经验个体的相通?或者说现实世界中的我们如何去感知宇宙天地的生生之意并对其怀有敬意呢?据上文可知,在论述“爱敬父母的形上依据”这一问题时,黄道周以“严父配天”之说将父母与天地关联起来;因此在现实层面,倘若要使民众感知到对宇宙天地的敬意,那最直接的进路是从家庭场域中感知自己对父母的情感:
为天子者,以天下全归于天;为诸侯者,以社稷全归其祖;为卿士者,以禄位全归其君。一言一行,不忘其亲,久而后成亲,成亲而后成天,成天而后成道。[1]9
君子而思以淑人善俗,非礼何以乎?礼仪之在人身,所以动天地也。孝子仁人必谨于礼,谨礼而后可以敬身,敬身而后可以事天。[1]95
据黄道周所言,圣人以孝道治天下,出发点是父母子女之间的亲情天性,人能“成天成道”、参赞化育,工夫层面在于从现实生活的一言一行上培养并扩充爱敬父母的情感。而礼乐仪制是孝子一言一行的行为典范,现实生活中培养敬的情感,需要以具体的礼仪作示范。因此人子在行为上能诚敬行礼,便能培养爱敬父母之情进而爱敬己身(在儒家看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爱惜保养自己的身体便是孝的体现);在保身敬身之际人能感念到父母孕育己身之不易,进而感知到天地生生之仁心的创生恩德,最终参赞化育、“可以事天”。
对于敬天与敬父的关系这一问题,黄道周具有存在论与工夫论两套进路:从存在论的角度看,面向父母的敬意得以可能,其形上根基在于天地生生之大德,孝子之敬得以发用根本在于人与天地之心感通;而从工夫论的角度上,经验世界的具体个人并非先感知到己身对天的敬意后再去爱敬父母,反而是通过感知己身对父母的敬意并以合礼方式推扩开来,逐渐意识到对君、对天的敬意,感知到本然状态下的天地生生之仁心。综上可见,阳明学罕言敬是由于外在超越者的缺位,重视敬则需要挺立形上之天;而在具体世界中人能够感知形上之天,途径在于感知父母之于己身的生养恩义。所以按照黄道周以及《孝经》学的逻辑,人能敬天、实现天人相通,其方式在于对“在世的天地”——父母始终孝敬有加,行礼则是提撕升华敬意的有效手段。
四、结 语
在《孝经集传》中,敬作为一种情感,涵摄了父子一伦的事亲之敬和政治与社会生活中面向为尊上者的敬意:事亲之敬是在孩提稍长之时,在家庭场域中自然产生并加以培养的情感;这种面向父的敬意能够衍生出面向他者的敬意,而广义的“敬”则成为情感的推扩动力,实现从爱亲到仁爱的转化。在黄道周看来爱与敬的关系在于,敬能导顺爱的方向,使爱呈现为中正合宜的爱,且敬能推动爱的推扩发展,让爱不仅仅局限在家庭伦理内部,而是能从亲亲出发逐步推至仁民爱物。可见其爱敬关系,呈现出“爱亲情感发生-能敬父母-能礼敬他人-能仁爱”的进程。
黄道周极为重视“敬本”之意义,《孝经》五大义第二条即为“约教于礼,约礼于敬,令人知敬以致中,孝以导和,为帝王致治渊源”[1]255。“敬为爱之实”立足于《孝经》“孝本论”基础上:由于孝德不仅仅局限在家庭伦理内部,而是天下万世的大经大法,因此爱敬情感也不应滞于父子一伦当中,而应推扩成为社会共同体中的礼敬和乐情感。语孝必本敬,从人道维度是基于《孝经》学对礼教的重视,而礼的产生与运作得以可能,在黄道周看来是源自敬的情感;从天道维度是因为人能行孝根源于对天地生生之仁心的感通,而人对于超越者(天)的情感更侧重敬而非爱。“敬本”一说更是纠正了阳明后学罕言敬天而导致的晚明情欲流肆问题,黄道周挺立外在超越者——天的维度,敬从超验层面是出自人对化育万物之天的敬意,这就使得敬的情感有了形而上的依归。
黄道周《孝经集传》在重视敬本意义的基础上,对何以培养敬意提出了一套儒家方案:现实层面在源初的家庭场域中涵养自然的事父之敬,并以此为本逐渐推扩与转化;超越层面则去感悟宇宙天地间的生生之意,进而对天地之心有所感应而生爱敬父母之心。当前社会存在诸多问题其病灶皆在于“敬”的缺位:孝亲时忽略对父母情志的尊重、大肆破坏环境而缺乏对自然的谦逊与敬畏、“敬”成为趋炎媚上的手段而非对德尊者的诚挚敬服……实际上社会共同体中仅以爱来融合人际界限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亟需以真切的敬意来尊重万事万物各自的存在方式,防止爱的越位侵犯他者生存空间,使社会中的伦理关系有序和谐。
——从明代朱鸿《孝经》类编著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