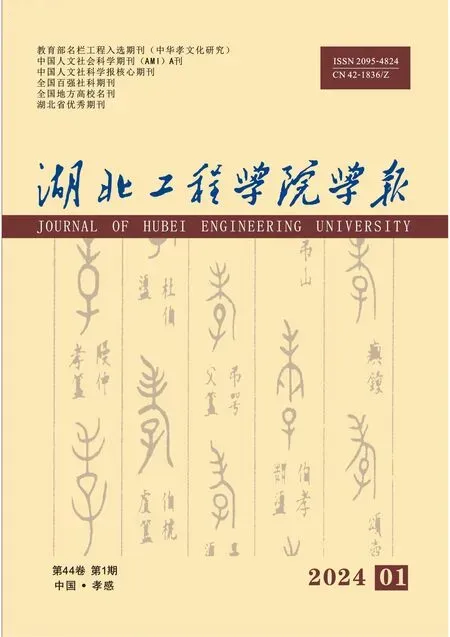为“颓废”正名:对中国自身现代性的探寻
——兼论《颓废审美风格与晚明现代性研究》
傅美蓉
(咸阳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播学院,陕西 咸阳 712000)
自17世纪以来,现代性(modernity)这一术语就开始流行于西欧。哈贝马斯认为“现代”(modernus)一词可追溯至公元5世纪,强调的是“古今之间的断裂”[1]122。相比之下,现代性更为复杂,不仅意味着理性对感性的压制,而且包孕着结构性矛盾和缺陷,呈现出反身性(reflexivity)特征。如果说西方的现代性理论只适用于解释西方的社会文化实践,那么,用它来解释中国社会文化现象,会不会落入“不是以西方的箭来寻找中国靶子,便是以西方的视角来有意无意地遮蔽中国问题”[2]29的僵局之中?在西方现代性理论的有效性饱受质疑的大背景下,国内学者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学与文化,以“晚明”为经,以“颓废”为纬,拨开了弥漫在“现代性”周围的丛丛迷雾,对中国自身的现代性做出了切实可信的图绘。有别于颓废观念接受史,妥建清的《颓废审美风格与晚明现代性研究》是第一本从晚明社会图景中发掘出“颓废”(decadence)现代性的专著,其将审美风格意义上的颓废视为晚明现代性的表征,指认晚明颓废审美风格为中国现代性的起源,超越了本世纪以来中国语境下的现代性话语批评路径。
一、“颓废”:中国现代性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
作为一个古老的概念,“颓废”与时间的破坏性以及没落的宿命相连,一方面蕴藏于所有古代民族精神的颓废神话里,一方面又在古典形而上学中有所表现。在柏拉图的理念论中,已经暗含了一种形而上学的颓废概念,并初步建立起本体论颓废观。自19世纪中期以来,颓废理论已然是一种意识形态批判,尼采对现代颓废深刻复杂的分析,构成了意识形态批判的最初尝试。作为一个现代性概念,“颓废”与现代性、进步的概念相互包含。美国比较文学教授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从美学角度分析了现代性,并明确把“颓废”作为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之一。他宣称:“进步即颓废,反之,颓废即进步”[3]170。其关于社会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的区分和思路为现代性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种理解现代性复杂性的路径。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对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探讨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现代性不是思辨的产物,正如尤西林曾指出的:“已成为全人类生产、交换与日常生活主流格局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及其现代性(modernity)同样是中国一百年来支配全部社会及其精神运动的中枢与基石”[4]。在李欧梵看来,现代性概念是西方学者和批评家“对于一些历史、文化现象在理论的层次上所做的一种概括性的描述”[5]2。中国的现代性观念是从晚清到五四时期逐渐酝酿出来的,对历史观、进化的观念和进步的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后,李欧梵转向现代文化研究,尝试把颓废的概念引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并把《红楼梦》视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颓废”小说[5]49。在此,“颓废”既是建构现代文学史叙事的一种策略,也表征着审美现代性对启蒙现代性的反叛与超越。稍后,王德威从晚清小说的蛛丝马迹中探寻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观点,把中国现代性的起源从“五四”推至“晚清”。为了论述“被压抑的现代性”,其引入了“启蒙与颓废、革命与‘回转’、理性与滥情以及模仿与谑仿”[6]12四个话语轴线,这就为“颓废”概念进入探讨中国现代性的话语场域提供了契机。在王德威看来,晚清小说的现代性是由严复与梁启超所贬抑的“颓废”气质迂回而生的,故明确把“颓废”定义为“一个过熟文明的腐败与解体,以及其腐败与解体之虚伪甚至病态的表现”[6]32。与此同时,其又根据颓废的“去其节奏(de-cadence)”之意,阐明了颓废与现代的对话关系,即:“颓废即是将正常异常化,并且暗暗地预设在所有有关现代性的论述中。”[6]32如此种种,其以“颓废”来评价晚清小说的做法为探寻中国现代性的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
近二十年来,妥建清以探寻中国文学自身的现代性为己任,与不少学者进行学术商榷。李欧梵、王德威两位学者均把晚清视为中国现代性的起源,妥建清认为中国现代性至少可以追溯至晚明,并为之展开了多方面的考据和论证。[7]8-11,[8]5-10其凭借着敏锐的学术嗅觉、超前的问题意识以及准确的学术判断,把“颓废”视为晚明文学现代性研究的新视点,力图从颓废面向来探寻中国文学自身的现代性。在《颓废审美风格与晚明现代性研究》一书中,妥建清借镜卡林内斯库关于现代性的区分,进一步把颓废审美风格区分为颓废社会审美风格与颓废文化审美风格,从社会实践与理论思辨两个层面揭示了颓废审美风格的“去道德化”(de-moralization),进而将此一风格标举为中国自身现代性的起源。至此,“颓废”成为研究中国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概念。作者在明知“从文学形式的角度探讨中国文学现代性上有一定的风险”[9]55-59的情况下,把“颓废”视为中国“现代”浮出地表的征兆,直接切入作为精神心态的现代性。
二、从“颓加荡”到“颓废”:一个现代性概念的“理论旅行”
在审美意识形态领域,颓废被视为一个负面的概念,往往被意味着腐败、衰退、没落。作为一种现代主义思潮,颓废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萌生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在不同民族、不同阶段均有不同的变体。法国是欧洲颓废主义文学的真正发源地与传播中心,颓废精神可以追溯至以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帕尔纳斯派(Le Parnasse)、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等人为代表的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批评中,“颓废”无论是作为概念还是作为术语都不占重要地位。一直以来,作为现代性表征的颓废背负着道德讥评,直到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FiveFacesofModernity,1977)一书为其提供了新的阐释和评价。
20世纪20年代,颓废作为一个美学范畴在世界范围内仍然是无足轻重的。五四时期,“颓废”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传入中国。到了二三十年代,被称为“十里洋场”的上海为西方颓废观提供了一个发轫的环境,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通俗与高雅等多元文化在此交融、混杂。作为来自西方的文艺概念,“decadence”以“颓加荡”之名登上中国现代舞台,推进了中国的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浪潮。20世纪20年代末,邵洵美首次把“decadence”译为汉语,并在诗歌《颓加荡的爱》中极力歌颂感官享乐主义”[10]14,以邵洵美为代表的“颓加荡”派对美与爱的颂扬一方面体现了积极的人文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又流于官能化和庸俗化。我国的颓废主义思潮是在欧洲唯美-颓废主义与日本唯美-颓废主义的共同影响下发生、发展的,在这一文学浪潮中,“颓加荡”被赋予了唯美情调以及享乐主义色彩,但因其对官能享乐与声色刺激的美化,也遭到了强烈批判。
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新文艺辞典》中,“decadence”也被译为“颓加荡”,该辞典明确了“颓加荡”即为颓废之意,并加以阐述:“十九世纪末的怀疑思想,反映到艺术上来的,便是一种病的偏颇的倾向,也就是强烈的传统破坏和病的感受性异常地受着刺激之一倾向”[11]377。显然,在这一时期,“颓加荡”普遍被认为是一种“病的偏颇”,由于其对传统的强烈破坏以及对“病的感受性”的表达而不被赋予正面价值。解志熙认为,“颓加荡”的汉译虽能恰如其分地反映这一时期“唯美-颓废主义文学的思想艺术品格”,但过于简单化、片面化和庸俗化[12]251。李欧梵则明确主张将“decadence”译为“颓加荡”,因为“它把颓和荡加在一起,颓废之外还加添了放荡、荡妇,甚至淫荡的言外之意,颇配合这个名词在西洋文艺中的涵义”[13]141。与此同时,他还指出,“荡”在现代语文的语境中贬多于褒。从直接意指层面来说,“颓加荡”的汉译已经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了“decadence”的意思,但从含蓄意指层面来说,这一汉译又被赋予了超出语义层面之外的道德涵义。尽管有不少学者主张为“decadence”正名,但均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其所蕴含的“激荡”之意,而选用了相对稳妥的汉译——“颓废”。当然,为“颓废”正名也非易事,郑克鲁曾直言道:在中国的文学研究领域内,“一提到颓废,往往就不分青红皂白地给予全盘否定,人们将颓废理解为对于生活的逃避,是一种堕落的不健康的思想情感”[14]1。尽管不少学者从词源考古学上为“颓加荡”这一译法正名,并通过援引有关魏晋、唐代的文献来对其内涵进行考释与深挖(如李白的“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限”等),但学界对“颓加荡”的态度却始终是暧昧的,甚至干脆避而不谈。在大多数学者看来,如若要为“decadence”正名,首先就要抖掉“颓加荡”这一历史包袱。“在中国思想文化场域中,颓废因陷溺于不道德的伦理困境,长期以来殊难获得诗学正义以及存在的合法性”[15]19。因此,妥建清虽然赞成“颓加荡”的汉译,认为这一汉译表征了颓废的“颓堕、放荡”之意,但又因其被冠之以“不道德”的恶谥,仍然采用了“颓废”这一保守的汉译。吊诡的是,在论及晚明文学的女性形象时,妥建清又将潘金莲作为典型的“颓加荡”的“尤物”形象加以细描,视其为放荡、堕落的化身。从理论层面来看,妥建清所探寻的颓废是“一种去道德化的审美精神”[15]364,具有现代性价值;但在其批评实践中,却又使颓废陷入道德化的泥潭之中,对“颓加荡”一词暧昧不明的态度恰恰凸显了其男性主体的论述立场。
从“颓废”在中国的旅行图谱来看,我国学界对颓废的误解与污名化由来已久。来自西方的“decadence”无论是译为“颓加荡”,还是译为“颓废”,其一旦与中国声色文学传统相结合,就注定了是“不道德的”。我国有学者指出:“无论是继续使用颓废一词,还是转向使用‘颓加荡’,都是中国传统的颓靡与颓放的合一,在颓废的理解中,将‘颓’视作衰落的开始,却又在衰落中荡起,在荡起中复有衰落,这样一种交织的状态,才是真正的审美层面上的颓废。”[14]233在《颓废审美风格与晚明现代性研究》一书中,妥建清所言的“颓废审美风格”即为一种“真正的审美层面上的颓废”。不过,作为一种文学价值观,颓废因偏离了传统文学所崇尚的中正平和之美,常常被正统文学排斥、贬抑。如在宗白华关于“世界未来文化的模范”的设想中,其所主张保存、发挥并重光的是一种“不可磨灭的伟大庄严的精神”[16]20。直到20世纪90年代,学界才开始以一种客观、理性的态度来评价和研究颓废现象。江弱水在以西方现代诗学的观点来烛照中国古典诗时,曾用“颓废”一词来概括南朝的历史特征,并认为这一时期的文学本身就是颓废的极致。自南朝起,中国古典诗已然形成一个有别于连贯叙述以及说教倾向的独特传统。在此,他强调的不是文学对于外在世界的功利,“而是文字的颜色和声音的组合游戏,及其摇荡人的性灵的力量”[17]26。此种以西方诗人为参照系,考察“颓废”现代性症候的研究路径,是对颓废理论中国化的尝试与探索。不过,在学界论及中国古典文学的“颓废”时,颓废已然不是西方古典意义上的颓废。
无论如何翻译“decadence”,颓废理论的发轫、穿行、接纳和改造均取决于作为旅行地的中国的思想传统与文学传统。如果说从中西语义流变以及实证性材料入手,有助于深入考掘颓废的内涵,那么梳理中国文化场域中的颓废思想谱系,从颓废社会审美风格与颓废文学审美风格的视角切入晚明思潮,则有助于深入发掘晚明文士文人与晚明文学所呈现的颓废审美风格及其现代性意义。
三、晚明颓废审美风格:中国现代性的逻辑起点及其文化表征
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性成为中国学术界的关键词,直接影响到我们观察社会和文化的视角和方法。无论是作为一种启蒙现代性,还是作为一种文化现代性,现代性都是一个极具张力的术语。妥建清认为,“现代性本是主体心性变化的正当性论述,有别于社会秩序变化的现代化、知识感受意义上的现代主义,现代性更是直指人心秩序的论域,其揭示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及其文化制度之质态和形态的变化,并且在人心秩序-社会秩序-人心秩序的框架中,赋予社会秩序变化以前提,表征着社会秩序变化的结果”[15]46。不过,现代性虽然有别于现代化,但其作为现代社会的特质,也是对现代化进程的反思。作为现代性的面孔之一,颓废归根结蒂也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正如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所言:“现代化免不了带来异化、沉沦颓废和无常等一类新旧价值观念冲突造成的消极面”[18]29。早在波德莱尔那里,就已经在颓废与现代性之间建立起了直接的关联。与现代性一样,颓废关注的也是主体心性以及人心秩序。
关于中国现代性的起点有多种说法,譬如“五四说”“鸦片战争说”“晚明说”“宋代近世说”等等。妥建清认为,晚明颓废审美风格标示着中国现代性的近代起源,并从社会审美风格、文学审美风格等方面逐一分析、整体审视晚明颓废审美风格之“美”。“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19]675。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颓废审美风格作为晚明文士颓废人格的表征,既表现为颓废社会审美风格,又表现为颓废文学审美风格。一方面,晚明社会的颓废审美风格孕育了晚明文学颓废审美风格,另一方面,晚明文学的颓废审美风格又是晚明社会颓废审美风格的表征。
从社会审美风格上来说,其所论述的颓废审美风格之“美”主要体现在晚明文士饮食生活的个性化、联觉化、本色化,服饰生活的艳丽化、复古化、新奇化,以及家居生活的意境与趣味时尚等方面。对晚明文士而言,无论是其放诞生活表现出来的“狂”“怪”,还是其任侈生活表现出来的“华”“奇”,抑或是其纵情生活表现出来的“痴”“俗”,都是晚明社会颓废审美风格的表征。在妥建清看来,晚明文士在饮食生活、服饰生活以及家居生活中对“美”的追求均为“当时文士被压抑的味觉、视觉等感性欲望的具象化表达”[15]23。从此种意义上来说,晚明文士的“狂者胸次”“品味奢华”“声色之娱”,既是对宰制儒家文化所要求的救世等崇高精神的一种逃避,也是从文化、审美的层面来寻求精神解放的一种尝试。正如其所断言:“晚明文士的颓废审美风格已经具有个性解放的价值,且表现出中国自身的现代性”[15]30。而在卡林内斯库看来,“当颓废把生活本身之外的意义归于生活时,当它引入一个救赎的‘彼岸’的观念时(无论这个‘彼岸’是根据基督教的‘死后生活’还是根据现代的世俗乌托邦构想出来的),它就是在反对生活。”[3]211简言之,当颓废引入“彼岸”观念时,就是在“反对生活”。在现代性语境下,“颓废者往往处在两个对立的、明显不融合的引力之间:一方面是世俗的生活,不可缺少的物质财富的荣耀;另一方面却又是他期盼已久的那种永恒的、理想的和精神上的东西。这两极之间的较量构成了典型的颓废主题。”[20]73-76尽管妥建清认为,颓废是以审美的方式回应“现代社会世俗化转向所导致的彼岸世界的失落,重建此岸感性生命的生存基础的问题”[15]29,但其立足点与落脚点均是实实在在的此岸世界,而不是虚无缥缈的彼岸世界,如在《颓废审美风格与晚明现代性研究》一书中,颓废即为一种指涉此岸世界的审美风格。
从文学审美风格上来说,妥建清所论述的颓废审美风格之“美”主要体现在文学的间性化、丑怪化和精致化等方面。在中国的文学-文化传统中,颓废审美风格至少可以追溯至南朝文学“不道德”的声色描写,但晚明社会赋予了晚明文学颓废审美风格以新质,表现出了间性之美、“丑怪”之美、绮丽之美等颓废审美风格。中国文化史上,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文化洋溢着阳刚之气,而晚明文化却是文人偏离此种阳刚文化的产物,故李欧梵认为“把中国文化的阴柔传统发挥得最光辉灿烂的是晚明”[21]99。其在思考晚明和现代文学的关系时表示,其心中的晚明文化就是“文人的文化”,如果说晚明文化表征为一种“过于成熟的颓废”,那么晚明文学也即“把一种颓废的心态用文学艺术的技巧表现出来”[21]93。不论是以诗歌等为代表的雅正文学的中心地位失落后,通俗文学对社会颓废世风的反映所表现出的具有间性之美的颓废审美风格,还是为中国文学传统中所压抑的谐谑风尚被重新发现后,晚明谐谑文学为躲避崇高主题而进行“加冕”/“脱冕”式戏仿时所表现出的肉身化、粗鄙化的戏仿审美风格,亦抑或是文学创作主体由传统士大夫逐渐变为中下层文化后,晚明小品告别宏大、追求阴柔之美所表现出的绮丽的唯美-颓废审美风格,均是晚明文学对颓废心态的艺术表现。就此,“颓废”可视为晚明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精神纽带。尤西林曾明确表示:“面对传统,颓废以其嬗变多元、偏执极端而成为中国‘现代’浮出地表的征兆”[15]封底。事实上,早已有学者从文学或史学的角度,把中国现代性的起点追溯至晚明,但极少有学者从学理上对这一说法进行分析。作为现代性的面孔之一,西方的颓废观涉及政治、历史、文化等诸多面向,表征着资产阶级腐朽没落思想,以及社会秩序变化的结果。在视西方美学为现代美学范本的今天,对西方颓废理论的改造是一项异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妥建清对晚明中国唯美文化的探寻,展示了晚明社会中“人”与“文”的觉醒历程,其以“中国眼光,为人类目的”回应生活审美化的世界潮流,意在以独特的中国审美文化引领全球现代性走出困境。在这项工程中,颓废理论的中国化既要符合历史规定性,又要符合逻辑规定性。因此,妥建清不得不在对颓废审美风格与魏晋个性解放、西方浪漫主义、西方个人主义的横向比较与纵向辨析中,揭示颓废所表现的个性解放的现代意义。其在接受西方颓废理论的基础上,又反观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对中国颓废现象进行历史寻踪,不惟看到了中西文化的相通之处,还探寻了中国自身现代性的独特之处。基于晚明现代性研究的理论困境,其以颓废话语来阐发晚明现代性,论证了以晚明为中国现代性逻辑起点的正当性,明确地回答了中国自身现代性的起源问题。
无论晚明文士的颓废社会审美风格,还是颓废文学审美风格,均可理解为晚明文士在寻求以一种审美解放的方式来消解社会压抑的可能性时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独创性。妥建清在《颓废审美风格与晚明现代性研究》一书中以审美眼光透视晚明文人的“颓废”生活,通过探赜颓废审美风格的现代性价值,把晚明现代性的逻辑起点移到了社会文本内部与文学文本内部,而其探寻中国自身现代性的过程,也是为长期被“误读”的泛道德意义上的颓废正名的过程。
四、由西徂东:颓废理论在中国的变异与回归
如前所述,现代美学意义上的颓废概念可以追溯至西方浪漫主义,几乎所有当代西方的文学理论问题都可以追溯至浪漫主义。西方浪漫主义是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主要思想资源,同时也是颓废理论的主要资源。在妥建清看来,要探寻中国自身的现代性,就必须建立有关颓废的知识话语体系。不过,中西方文论具有异质性,颓废理论经历了由西徂东的“旅行”,其在中国注定会发生一定的变异。
颓废理论在中国的“变异”首先表现在其与晚明社会的联结上,此种联结既“为中国审美文化史提供了新颖的个案与断代学术成果”[15]封底,又超克了对西方颓废理论的单向阐发以及中西二元模式的思维定式,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在此,“颓废”理论是对晚明浪漫精神的概括和总结,绝对不是简单的套用和比附,其理论内涵受到了中国特定语境的改造,并发生了新的意义。鉴于晚明现代性研究陷入理论困境,以资本主义萌芽、启蒙精神等惯性话语不能明确地阐发晚明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妥建清提出了将审美风格意义上的颓废视为晚明现代性的表征,并以此作为中国现代性起源的标示。在中国,无论是在文学领域,还是在生活领域,颓废与道德的关系都更紧密一些。晚明文士的颓废确实有此“去道德”的一面,但是如果不以道德主义为标准,而是以审美眼光透视此种文化现象,此种现象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妥建清在接受颓废在中国思想文化场域被赋予的“不道德”意义的同时,又对颓废审美风格进行了“去道德化”,并以“浪漫”来指称晚明颓废审美风格所表现的个性解放精神。尽管“浪漫”或“浪漫主义”是中西跨语际交流的实践成果,但浪漫主义的西方文化来源对于中国浪漫主义的发展并非具有决定性的力量。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没有陷入“以西释中”的单向阐发之中,而是回归到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反观以颓废审美风格为代表的晚明“浪漫主义”论,并结合晚明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黑暗的政治文化生态以及严酷的科举制度等因素来审视晚明文士颓废的精神追求。一方面,其话语范式和思维方式从西方理论那里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另一方面,其又保持敏锐的学术眼光和高度的文化自觉意识,反思宋代近世说,把晚明勘定为中国现代性的起点。中国与西方的相遇是一个相互发现的过程,在对晚明现代性与颓废审美风格的阐释中,作者不仅突破了中西二元模式的思维定式,而且有效避免了中西浪漫主义的同质化,凸显了东方的深层文化内涵。
颓废理论在中国的“变异”也表现为其向文学文本以及文学理论研究的“回归”,此种回归超越了对颓废的形而上的理论探寻,凸显了晚明文学所蕴涵的颓废审美意义,为重写文学史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学不断介入文学领域,加之文学理论边界的不断扩大,文学研究的本质也发生了变化。正如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所言:“文学研究的理论并不是对于文学本质的解释,也不是对于研究文学的方法的解释”[22]1。在文学理论研究的领域里,有关非文学的讨论太多,而关于文学本质方面的系统思考又太少,逐渐偏离了文学自身的轨道。尽管妥建清在《颓废审美风格与晚明现代性研究》一书中对晚明社会的颓废社会审美风格进行了详尽、细致的分析,但其出发点与最终目的均落在颓废文学审美风格上。对其而言,非文学的论述只不过是文学文本、颓废理论问题的“历史背景”,其对文学文本的细致分析使得“颓废”成为研究晚明文学的一个新维度。值得一提的是,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作者并没有把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当成“典范”,而是通过对《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儒林外史》等白话文长篇小说的文本细读发掘颓废审美风格。如果说李欧梵、王德威等人以知识考古学的方式发掘了晚清文学的颓废现代性,那么妥建清则在以知识考古学兼文本细读的方式发掘了晚明文士颓废审美风格和晚明文学颓废审美风格。此种回归文本、回归文学的“知识考古”,使得溢出文学之外的“理论”重新回到文学研究的轨道上来。
颓废理论在中国的“变异”还表现在其对晚明文化、晚明文学的“还原”以及对文学与文化关系的还原研究上,此种“还原”研究返回到现代性发生的原点,把颓废审美风格视之为晚明文士人格的精神外化,并把其归还到原本的历史现场与文化环境之中。“观念一旦因其显而易见的效用和力量流布开来之后,就完全可能在它的旅行过程当中被简化,被编码,被制度化”[23]138。多元文化景观的晚明促逼着学术界对现代性进行多维度的阐释,妥建清通过对晚明文化与晚明文学“还原”避免了颓废观念在中国被简化。“还原”是一个颇具复杂性和争议性的概念,但在一般情况下,主要指“回到原来真实的现状”[24]12。作者试图返回到文化原点,让静态的颓废观念复归于晚明文士的日常生活,以自己的生命体认晚明文士的生命,对中国的现代性问题进行一种还原研究。正如杨义所言:“还原的要义在于立足中国文化精华的根本,把握中国文化的总体精神,建立具有中国原创性的学理体系”[25]136。因此,“还原”不是简单挪用西方的外来观念来重写文学史,而是要从中国文化传统中抽绎现代思想,研究中国现代性的发生,重绘中国现代性地图。
总之,颓废理论在中国的“变异”既表现在其与晚明社会的联结上,也表现为其向文学文本以及文学理论研究的“回归”,还表现在其对中国文学史的“历史还原”上。从比较文学的意义上来说,《颓废审美风格与晚明现代性研究》一书重点在于研究“异”,即颓废理论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传播与接受,这就体现了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双重追求。作者试图通过一种“历史还原”来完成中国现代性的“思想建构”,以摆脱“西方文论在中国”的单向阐发模式,重建中国当代文论话语。
五、结 语
毋庸置疑,对中国现代性起源的探寻既需要根据中国传统美学的具体实际来借鉴西方的理论资源,又不能完全照搬西方颓废概念为普适性范式。从本土文学与文化来探寻中国自身的现代性,是妥建清一贯坚持的学术立场。在全球化语境下,“相似的人和批评流派、观念和理论从这个人向那个人、从一个情境向另一情境、从此时向彼时旅行”[23]138。晚明颓废审美风格不惟是“理论旅行”的结果,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衍生物。无疑,从西方现代性理论的流通中汲取养分,对西方颓废理论进行创造性的借鉴,以之观照中国的社会文化实践,探寻晚明现代性研究新的视角,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中国现代性研究走出困境。不过,从颓废面向来反思晚明现代性,又不可避免地遮蔽了现代性的其他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