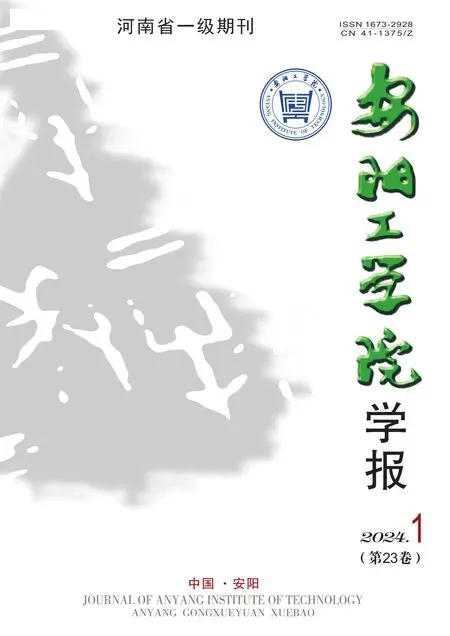如何面对和超越苦难
——析史铁生的创作基调
崔素敏
(安阳市高级技工学校,河南 安阳 455000)
史铁生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他在最青春的21岁时,却突然双腿瘫痪,一时之间,原本健康的身体、美好的生活戛然而止。命运的无常和残酷,曾经带给史铁生数年的折磨和痛苦,但是他并没有一蹶不振,而是不断地探寻自己内心最深处的真情实感,因残疾而历经生命无常带来的苦难和艰辛,反而使他在人性之海的深处不断升华自己,他用坚强的意志和乐观的心态将生、死、命运、爱情等一系列相关的人生体验和感悟灌注于作品中,用笔叙述和展示了残疾人对自身缺陷的静思(自身困境),对人本困境的探讨(人本困境)。
1 自身困境
史铁生1951年1月生在北京,196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1972年,正在延安插队的他因双腿突然瘫痪返回北京,从此没有恢复站立的能力。在经历痛苦、彷徨、绝望之后,史铁生重新“站”了起来——“路无法再用腿去趟,只能用笔去找”“把疾病交给医生,把命运交给上帝,把快乐和勇气留给自己”。自此,史铁生挣扎着勇敢向命运挑战。他的作品已与他的生命完全同构在一起,残缺的身体说出的是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体验了生命的苦难却表达出明朗与欢乐。史铁生的大多作品和个人的经历息息相关。对史铁生而言,是残疾将他推往写作的道路,开启了他的另一种人生。面对疾病困扰,“活与不活”“为什么活与如何活”是盘旋在他脑海中的艰难性抉择。写作对于一般人来说,可能仅仅是一份职业,对于史铁生而言,却是实现人生价值意义的方式,是他救赎自己,活下去的理由。《午餐半小时》是一部短篇小说,它以缝纫车间几个男女吃饭闲聊为背景,刻画了几个栩栩如生的小人物对发生车祸后的浮想联翩,其中一个沉默寡言的残疾小伙子是史铁生作品中首次出现的残疾人物形象。史铁生在这篇小说里,精准地掌握住写实笔法,针对特定的空间与时间,集中处理了外部环境和人物的内心活动,表达出自己对于“生命”的透彻感悟。一句看似轻飘飘的“唉,我可不想让汽车撞死”[1]话语背后是史铁生对人生的朴素理解——虽然生活艰辛,但也不至于拿命去换想要的东西。正如文中的残疾小伙子,虽然身有残疾但依然努力工作。
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史铁生从自身的经历和遭遇写起,创作了一系列的文学作品。在创作过程中,史铁生以自身残疾之后的遭遇与感受作为起点,以写实笔法呈现了残疾人形形色色的人生故事。
行动能力的缺失,无疑给史铁生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史铁生对生活的热爱,丝毫没有影响他对生命意义的探索,更没有让他陷入对生活的无尽的抱怨。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没有太阳的角落》中,史铁生描写了3个腿残的年轻人在生活、工作及爱情中的处境遭遇。小说首先描述了一个遭受“残疾眼光”看待的残疾青年,试图通过独立的工作能力挣得独立人格而不得的无奈。“内心深处的羞辱感、令人难堪的歧视、偏见像浓雾一样从四面八方压来,让人无处躲避,又像彻骨的寒风一般侵彻身心。”史铁生借“我”的口吻,突出残疾人求生存、期盼被公平看待的欲望。面对社会的种种质疑,强烈的自立意识让“我”不由自主发出内心的呼喊,最苦恼的不是解决物质生活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获得社会尊严的问题。此外,因残疾而受挫的心灵,史铁生寄托于“爱情”来拯救,这是从残疾所延伸出来的另一个议题,也是贯穿小说的轴线。通过对外在现实与内心欲望冲突的一系列场景和独白的描绘,生动表达了残疾人面对爱情既渴望又无奈的复杂心理。那些深刻而又沉重的文字,透露出作者的一丝感受,也深深刺痛了作为读者的我们。因为作品中的许多人,不仅仅是坏人,也包括好人,心灵深处都充满了对残疾人的一种固执而又坚定的偏见。正是此种偏见,粉碎了“我”渴望事业、渴望爱情的美好意愿。在对作品的主角的处理上,史铁生没有让他们停留在对自身遭遇的自怨自艾中,而是积极地生活着,积极地寻找在面对不幸遭遇时,如何使自己体面地保持有尊严的生存方式,这也象征着现实中的作者不向命运屈服的坚强意志,表达了史铁生对生活的热爱。
在史铁生早期的小说中,无论他采用了何种叙事角度,双腿残疾的人物形象总存在于其作品中[2]。在史铁生作品的残疾世界中,他赋予了“爱情”以拯救的内涵;在现实生活中,他也对自我进行了拯救,他选择了活着,因为他找到了活下去的理由。
即使身处生存的困境,他也不甘于沉沦,一直在发问,问生存的意义,这种对人生的终极思考构成了他与世界的根本关系,也构成了他写作的初衷和方向。史铁生用自己亲历的种种苦难、苦痛,不断地对人生进行思考和探索,形成了写作的蓝本,蕴含着思辨的哲学气息。
《山顶上的传说》是史铁生另一部具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充分展示了史铁生精神自救的历程。小说从第三人称叙事角度切入,陈述了一个残疾青年的心路历程。小说中一个以扫街维持生活的腿残青年,一心朝着写作方向发展,虽然受到其他作家与友人的肯定与鼓励,但因为创作理念不符合大众审美,作品一直无法顺利获得发表的机会;他原本与一位姑娘恋爱,却在相恋的过程中饱受外界的质疑,在女方家人的反对之下,姑娘最后只得远去南方,留下一只鸽子与他相伴,但鸽子却在姑娘离开后不久,无意间飞离他的身边,再也没有回来。从此,残疾青年开始了寻找的旅程。10天后,人们在山顶最后一次看见了残疾青年踌躇独行的背影,山顶上的传说因而流传下来。宏大的主题加上象征笔法的运用,使得《山顶上的传说》在形式结构上表现出叙事的完整性,内容上则展示了残疾人生命欲望的全面性,尤其是主人公在残疾的深渊中,领悟出精神自救的方法,可以说正是作者长期以来在写作和生命历程上的成长。此后,他早期文学创作中的那种压抑和困苦不复存在,这说明这个阶段的他已经克服了自己的困境[2]。《山顶上的传说》展示了史铁生的4种转变:第一是宿命观点的转变;第二是对自己文学创作的转变;第三是对爱情看法的转变;第四是对命运看法的转变。
2 人本困境
从广义上看,“残疾”不仅是指肉体的疾患,而是指人类先天的有限性,是永远无法完美的残缺,是每一个人都要面临的根本困境[3]。对于史铁生来说,长期的病榻生活给他带来了痛苦不便,也使他对生命有了独特的理解。在史铁生以残疾人物为主要写作对象的小说中,除了前述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之外,他还将目光放在了其他残疾人身上。他试图跳出自我残疾的身份的局限,在不同层面残疾人身上思考人生与社会的复杂关系。这类作品带有真挚的情感,抒发了作者的人道主义理念,也进一步唤起了人们对残疾人的关怀与思考[4]。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史铁生的写作风格发生了转变。随着其写作技巧的日趋娴熟,史铁生逐渐开始了人生意义上哲学层面的思考,作品中的写实成分慢慢减少。他不再仅着眼于残疾人物的生存境遇,作品的主题转向对人的内心探究。他所关注的不再是现实中个体残疾人的问题,而是从广义的角度对整个人类生存困境进行思考。史铁生想要表达的是在人类世界中,残疾的生命一旦开始,就不单是个人的事情,不是个人“背了运”,而是整个家庭甚至整个社会都必须去共同面对和承担的残酷事实;残疾人仍有梦想与追求,仍有权利与能力有尊严地活下去。
如何面对苦难,尤其是残疾,并以此为中心,或升华或扩大苦难是史铁生这一时期的创作基调。身体残疾的苦难迫使史铁生不再仅仅着眼于残疾人的物质生存困境,而是逐渐扩大他作品的主题意义,开始了对人的内部心理的探求,开始不断反思人类的精神困境和人本困境。他作品中的真实性与故事性成分开始减弱,弥漫出越来越深厚的哲学色彩。在《我之舞》中,作品通过谈话的形式,在反问、追问与沉默之中,探讨了对与错、有与无、生与死、虚无与存在、有限与无限等悖论在生命过程里的终极意义[4]。作品《毒药》则说明了人类生活在欲望横流的时代与环境之中,面对高涨的虚弱而不自知,偏离了人之为人的本质,忘却了正常的生活方式与基本的生存信念,不断求取的无止境的欲望,成了真正毁灭人的“毒药”。
史铁生于1987年出版的中篇小说《礼拜日》,是一篇描写人在孤独处境之中,寻求沟通的欲望与过程的展示。《礼拜日》代表史铁生在创作意识与写作形式上的创新与突破,作品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呈现出人类在当今世界的精神困境。小说借两对夫妻、恋人的相处情境与对话,展示了男女之间在互相寻找以及沟通上的隔阂;以母女之间的疏离关系,表现了两代人之间难以沟通的“代沟”现象;以老人对童年的追忆画面、他与女孩相伴的场景与对话,勾勒了人间正道是沧桑的感慨。隔阂成为人的根本困境。人与人之间有距离有隔阂就需要有理解,然而每个人的表达方式又不尽相同,经常又因语言的误解而造成更多的疏离,于是彻底的理解和沟通成了遥不可及的彼岸,唯有抱有永恒的沟通欲望,在不断的沟通之中贴近彼此,了解到理解的难以实现和不可圆满性,那么无论在理解或被理解的一方,都能突破心中的藩篱,宽容以待。
3 生存与欲望困境
史铁生由自身的残疾状态,看透了人生的死亡困境,他在作品中不断发问生命的目的和意义。史铁生认为,很多人缺少对人生的规划,因此他们的梦想多变,写作是史铁生探索人生困境产生原因的最佳途径。小说《毒药》描述了一个返乡归来的老人的人生顿悟的心路历程。老人手中的2粒药并非毒药,而并没有服药的那些岛民其实已被“养神鱼”这一念想荼毒,病入膏肓。这一对比设置颇为精妙,也彰显了题目“毒药”的含义——困境不一定是绝境,有时会成为通往希望的途径。《毒药》中,岛屿上的每个人都有一致的目标,但并非人人都能实现。当遇到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困境时,有人执迷不悟,有人毅然离去。有人在生死抉择之际,断然割舍欲望,生路得以豁然开朗。有人在求死的路上另谋出路,便又是生的可能。欲望造就了生死殊途的对比,坚定不移是一种态度,放下欲望又是另外一种态度。能适时抽离欲望执念去寻找更多可能的人,对生命有着坚定而强烈的向往,是更高层次的坚强。
腿残对于史铁生来说,一度是抑制生命的困境,但他在创作的欲望中反而领悟了舞动人生的欢乐所在。史铁生试图从对个人生命的追寻,扩展至对普遍人群内心的探问,这样的观念历经10年之久。也就是说,欲望是支撑人类活着的动力,人类生活戏剧的总导演是欲望。但人类的能力是有限度的,欲望达不到就会产生痛苦。史铁生由自身的残疾状态,看透众生的欲望困境,并反映在其文学作品之中,赋予了“残疾”与“欲望”别开生面的叙述。在史铁生看来,人类实现欲望的能力不及产生欲望的能力,所以人类在欲望方面存在永恒的缺陷——残疾。因此,人们需要不断超越自己的局限性,他认为作家应当追求精神的空间,相信文学能为欲望困境找到一条通往欢乐的坦途,这是史铁生对自我的期许,也是他对文学的期盼。
活,是漫长的过程。人的命运殊途同归,最后的终点都是一致的,差别只在过程。“人的命就像这根弦,拉紧了才能弹好,弹好了就够了。”[5]这是《命若琴弦》中老瞎子的师傅临终前留给老瞎子的话。弹断千根弦的老瞎子最后获得了他梦寐以求的药方,但是药方却只是一张白纸。痛苦之余,老瞎子豁然开朗了,最终明白了弹断一千根弦的意义。
史铁生认为,一个只想使过程精彩的人是无法被剥夺的,因为死神也无法将一个精彩的过程变为不精彩的过程,因为坏运也无法阻挡你去创造一个精彩的过程,相反坏运更有利于你去创造一个精彩的过程。于是绝境溃败了,而且必然溃败。你立于目的的绝境却实现着,欣赏着,饱尝着过程的精彩,你便把绝境送上了绝境。梦想使你迷醉,距离就成了欢乐,追求使你充实,失败和成功都是伴奏。当生命以美的形式证明其价值的时候,幸福是享受,痛苦也是享受。这是史铁生对“困境”的顿悟。他从个人精神自救的微观,升华至对人本困境的终极关怀:人与生俱来的局限就是能力和愿望之间的永恒距离,而生命的目的就是不断跨越困境的过程。
总之,史铁生从自身的残疾经历出发,在创作中不断思考,把人类所有的挣扎、努力、绝望、渴求,以其天才的笔触具体反映在其文学作品之中。他勘破生死的意义,乐观正视自身困境,勇敢与厄运抗争,向我们展示了人本困境给人类带来的一切,在困境中人们所寻找的爱不是为了占有,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与安慰彼此。时间终将慢慢地告诉人们,这个叫史铁生的人,这个在苦难面前镇定、乐观、坚强的人,怎样丰富了生命的内涵。他的作品将诗意和哲理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使读者体会到残缺者心灵救赎的心路历程和抗争奋斗的精神魅力,也将成为读者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他们获得勇气、对抗绝望的力量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