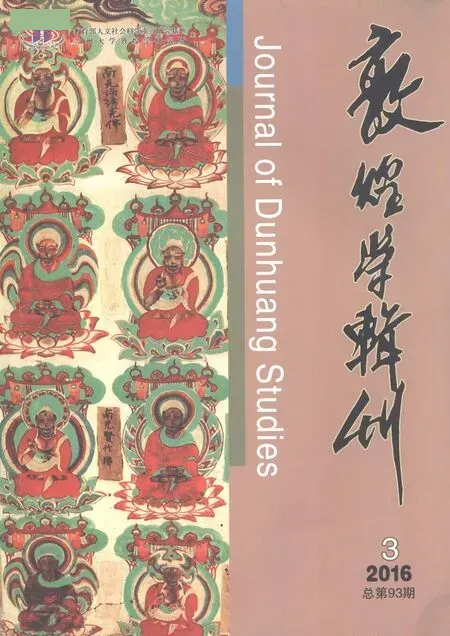俄罗斯汉学家孟列夫对国际敦煌学的贡献
柴剑虹
(中华书局,北京 100073)
今天,我们在涅瓦河畔举行敦煌学的国际研讨会,藉以纪念两位杰出的俄罗斯汉学家孟列夫和丘古耶夫斯基研究员的九十周岁华诞。他们两位,都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都对中俄文化交流与国际敦煌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值得我们永远尊敬和怀念。
我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与孟列夫研究员结识,交往近三十年,在学术上交流切磋较多,相互比较了解,故应孟列夫要求后以中国习惯称其“老孟”。2005年10月29日老孟逝世时,我也曾撰文悼念与追思,当时悲上心头,思绪万千,匆匆下笔,言未尽意*拙撰《悼念孟列夫先生》,柴剑虹《敦煌学与敦煌文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13-217页。。现谨以此文简述他对国际敦煌学的突出贡献。
1929年,奥登堡院士将所获敦煌文物交列宁格勒亚洲博物馆,第二年,博物馆改称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今圣彼得堡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前身),敦煌写本入藏该所“敦煌特藏库”。之后,该所的K.K.弗卢格研究员开始对这些写本进行初步的整理研究,到1934年,完成了其中307个“佛经写卷”的编目和2000余号写本的登记,并发表了相关文章。1942年,弗卢格研究员在德军围困列宁格勒时不幸去世,整理研究工作中断。当时,少年孟列夫在与极度的饥饿困苦抗争中幸免于难。50年代初,由于苏联国内政治原因,汉学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处于低谷。1957年2月,刚届而立之年的孟列夫不惧艰难,领头组织了三人专门小组,在对俄藏敦煌汉文写卷进行初步修复的基础上,开始了全面系统的整理编目工作。这个编目(以下简称《叙录》)体例,一开始就定为要编分类叙录的高标准。此时,英国人翟理斯(L.Giles,1875-1958)用了38年时间所编的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正待出版,该目依佛教、道教、摩尼教、世俗、印刷五大类粗分,每大类下分若干小类,存在问题不少[注]请参看白化文《敦煌文物目录导论》,林聪明主编“敦煌学导论丛刊③”,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第65-81页。;而中国北京图书馆所藏的《敦煌劫余录》等是按入藏流水号编写,王重民先生的《敦煌古籍叙录》尚未发表(该书1958年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鉴于敦煌写本抄写的特殊性与内容的复杂性(如佛教典籍及相关内容写卷占80%以上,同一纸张同时期或不同年代、不同内容的双面抄写等),俄藏写本残本碎片又占很大比例,因此,孟列夫小组面临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凭借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与比较扎实的汉文化基础,孟列夫和他的小组成员知难而进,用不到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近3000号写本的《叙录》,于1963年、1967年分两册先后出版。根据孟列夫所撰写的第一册序言,《叙录》由编号、定名(标题)、相关书目与参考书、写本外观描述、写本时间、写本内容的首行和尾行文字著录共六个部分组成,这已经是超越前人的规格了。而其中写本外观描述又包含了写卷尺寸、纸张、画栏行线、字体、卷背文字等9项内容,更令人惊叹他们工作的周全与细致。《叙录》第一册分为佛教经典、儒家与道家著作、历史与法律、文学、碑文、字典及参考资料、艺术·画图·印章及非汉文文本、医学·历法及天文学文本、占卜文、书法练习、文书共12类,第二册又精益求精,改进为10大类,增强了分类的科学性。尤其是对佛教经典部分,《叙录》进行了类目细分(按入藏的经、律、论,非入藏及汉文原著、诗体作品等分为十几个小类),体现了编目者经过研究对写本内容进一步把握的程度。可以认为,孟列夫、丘古耶夫斯基等人已经突破了之前其他国家专家按卷号编撰敦煌写卷目录或简单注记的局限,《叙录》堪称是第一部敦煌写本(以汉文为主)兼有较高资料与研究价值的分类叙录。这对于几位并未在中国受过系统传统文化修习的汉学家来说,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叙录》中文版,在孟列夫等俄罗斯专家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同道的共同努力下,于1999年正式印行。《叙录》俄文原著及中译本的具体内容及优缺点,敦煌学界已经有若干评介文章,我也曾写过简评[注]拙撰《〈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中译本简评》,柴剑虹《品书录(增订本)》,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35-141页。,兹不赘述。还必须提及的是,正是由于有《叙录》作为了解俄藏敦煌文献的导引与桥梁,也是在孟列夫、丘古耶夫斯基、克恰诺夫、鲁多娃等俄罗斯专家学者的倾情全力支持下,凝结着魏同贤、李伟国、府宪展等诸君的诸多心血与智慧,俄藏敦煌文献及艺术品,也得以陆续全面出版,成为世界敦煌学史上不可或缺的宏伟篇章。[注]参见李伟国《敦煌话语》中相关内容,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又参见府宪展《“探险”俄罗斯——〈俄藏敦煌文献〉出版记略》,刘进宝主编《百年敦煌学:历史·现状·趋势》,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6-216页。
经过中苏双方学术机构及孟列夫本人的努力,老孟终于获得了中国人民大学一个宝贵的进修名额,自1989年下半年起,来华进行为期半年的学术考察与交流。据我所知,他也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位来华进修的苏联敦煌学家。他在这期间的一个最重要的活动,就是要实现多年的梦想,实地参观、考察敦煌,成为继奥登堡考察队之后第一位亲临莫高窟的俄罗斯汉学家。他请求我帮助安排旅程,并陪他一路同行。为了节省当时外国进修生的有限经费,孟列夫坚持要和我买同样的硬卧火车票前往。当时从北京到敦煌,要乘乌鲁木齐的69次列车到柳园车站下来再换乘汽车。北京到柳园,火车要开行三天三夜,这对我来说已习以为常,而对老孟来说却是个考验。但是他却把这段时间当作是向我了解敦煌和练习汉语的好机会。当时绿皮硬卧车厢的条件较差,人多拥挤,交谈受影响,我还得常常从上铺下来挤坐在下铺和他聊,乃至到车厢连接处去聊;又因为餐车供应的饭品种单调数量少,有时连喝水都有困难,幸而我们从北京带了点吃的可以稍加补充。但老孟不以此为苦,抓紧时间向我了解中国敦煌学界的信息,包括相关的新出版物。在我向他了解1914—1915年间俄罗斯奥登堡考察队在敦煌的情况时,他认为该考察队当时并没有切割敦煌壁画。到敦煌的第二天,樊锦诗院长带他看的第一个洞窟里就有遭奥氏切割壁画的痕迹,老孟无语,但回到宿舍后他跟我讲,他还是不相信奥氏有这样的行为。这说明他既认定切割并劫掠壁画完全是非法、愚蠢之举,也是从心底里不希望自己的学术前辈有这样的举动。至于俄藏敦煌文献的来历及整理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我曾撰文论及,但不知道老孟是否读到[注]拙撰《关于俄藏敦煌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几个问题》,柴剑虹《敦煌学与敦煌文化》,第112-119页。。在敦煌,除了观看洞窟,他还同敦煌研究院的学者们进行了认真的座谈交流,后来又专程到兰州与那里的敦煌学研究人员进行交流。他在中国进修期间,还到银川、西安、扬州、上海、杭州等地参访。在敦煌学研究的新阶段,孟列夫是第一位亲临敦煌并和中国各地学者进行学术考察与交流的俄罗斯敦煌学家。因当时我需提前回北京工作,不清楚这些座谈、参访的详情,相信当时参加交流的同仁们会有清晰的记忆。而老孟则高兴地形容这些交流说明“中苏学术界的交流进一步密切起来了,坚冰已被打破了。”[注]见《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上册)孟列夫所撰《中文版序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页。
孟列夫也是最早从事敦煌变文研究的俄罗斯汉学家,他在1963年即出版了《维摩诘经变文与十吉祥变文研究》一书,并印行了《敦煌赞文(附宣讲)》的影印本,引起日本、法国等敦煌学家对俄藏俗文学写本的关注。上世纪70年代初,因孟列夫主编的《叙录》出版后一系列介绍敦煌学论文的刊登,尤其是他将所著《双恩记变文》寄赠先后寓居香港、台北的我国学术大师潘重规教授,促成了潘先生1973年8月首访列宁格勒,开启了中、俄两国学者在敦煌学研究中的实质性交流,意义非凡[注]拙撰《勇敢冲破樊篱的拓荒者——读潘重规先生〈列宁格勒十日记〉感言》,柴剑虹《敦煌学与敦煌文化》,第186-196页。。他对俄藏写卷中其他一些重要的变文、讲经文类作品(如弗卢格曾编目的Ф-223《十吉祥》、Ф-252《维摩诘所说经讲经文》、Ф-101《维摩碎金》、Дх.1225、1228、285a等)也做了前期的整理、介绍、研读工作。他所撰写的《敦煌文献所见变文与变相之关系》、《中国文学古文献〈莲花经变文〉》也先后被翻译成中文刊登[注]前文见《敦煌研究》1995年第2期,第114-117页,杨富学译;后文刊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编印《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88年第1期,第28-36页,徐东琴译。。1991年,孟列夫又到我国台湾地区参加了在台北举行的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他在会上提交的《关于俄国新疆考察队资料的研究情形》一文[注]见《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汉学研究中心,1991年,第23-28页。同年9月,他在《敦煌学》上正式发表《俄国新疆考察队(1914—1915)》的文章,见该刊第129-132页。,为学界提供了一些重要信息。可以说,在上世纪80—90年代,孟列夫是最热心将俄罗斯的敦煌学研究信息与心得向国际敦煌学界介绍,最积极地进行学术文化交流的敦煌学家。[注]这一时期,孟氏所撰写的《亚洲民族研究所敦煌禅宗中国手稿记述(前言)》、《论王梵志与惠能的共同点》、《被漠视的敦煌劫宝人——塞缪尔·马蒂洛维奇·杜丁》等文章的中文译文也先后在中国大陆、台湾的学术刊物上登载。
我1991年五六月间第一次在列宁格勒考察俄藏敦煌写本时得知,孟列夫是一位对中国古代文学情有独钟的汉学家,是著名汉学家、翻译家瓦·米·阿列克谢耶夫院士(1881—1951)的弟子。因此,孟列夫在他老师的影响下,不仅翻译了《西厢记》与《红楼梦》诗词,还花了不少精力研究、翻译唐代诗歌。记得当时我曾对看到的一些唐诗俄文译本(如李白的《静夜思》)发表过一些感想,认为过于直白的翻译往往减弱了唐诗的魅力。老孟说他也在尝试做这方面的工作。十年之后,2001年,他的《清流——唐诗选译》(Чистый поток——Поэзия эпохи Тан)由“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彼得堡东方学)”正式出版,他即赠我一册。翻阅之后,深感这个唐诗选译本不仅在选目上充分体现了他作为敦煌学家的喜好与眼光,在对诗歌的理解上也有自己独特的体会。是书选译50位唐人诗作144首,大致按创作时期编排。其中既有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李贺等一流诗人的作品[注]李白《静夜思》的译作即在其中,相较于其老师之译,给人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感。请参见本文下页注②。,也有陈子昂、岑参、高适、韦应物、孟郊、陆龟蒙、罗隐等有鲜明时代风貌与地域特色的诗篇。最让我感到惊讶和钦佩的是,他将在敦煌诗歌写本里最有特点的王梵志诗作为全书的开篇,而且一下子选译了16首,数量居于全书首位(其他被选诗较多的如韦应物13首,王维9首,李白、杜甫、王绩、岑参各7首)。
王梵志是中国隋唐之际民间诗体“梵志体”的代表性人物,其诗篇是佛教中国化背景下的通俗之作,既有直白说教,也有不少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带有明显的“反潮流”倾向,因此正式流传下来的不多,却被发现在莫高窟藏经洞写本里保存了相当数量。而且,中国学术界也正是因为依据孟列夫小组的编目整理,才得以知道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写卷即是《叙录》1456号(Ф-256+Дх.485+1349)著录的唐大历六年五月沙门法忍的“王梵志诗一百一十首”抄本,即其多数是保存在圣彼得堡所藏敦煌写本中,后来因台湾著名文史研究大家潘重规的热心绍介,由项楚教授对王梵志诗做了全面的整理、研究[注]见项楚《王梵志诗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孟列夫不仅在《叙录》中将其列为文学类诗歌的第一目,他又是第一位将16首王梵志诗翻译成俄文的汉学家。必须指出,对俄罗斯汉学家来说,翻译梵志体诗,较翻译其他唐人诗作难度更大。因为这不但要求准确把握它复杂内容上所体现的“神”(时代风貌、反潮流思想、宗教哲理、民俗特色等),又必须尽可能地表达它语言形式中的“韵”(节奏、声韵)。可以想见,老孟虽有翻译其他中国古代诗词的基础[注]请参见谷羽《阿翰林三译〈静夜思〉》一文中相关内容,见阎纯德主编《汉学研究》总第20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16年5月,第282-288页。关于孟氏翻译其他唐诗的成绩,容笔者另行撰文论述。,仍然会为梵志诗的翻译颇费斟酌。我曾经在悼念老孟逝世的文章的末尾引述了他所译王梵志《死竟土里眠》一诗(括号内为中文原句):
Кто уже умер(死竟土里眠,)
Тот под землею уснул;
Ну а живой (生时地上走。)
по земле куда надо идет.
Кто уже умер (死竟不出气,)
Тот бездыханен лежит;
Ну а живой (生时不住口。)
Открывает без устали рот.
Умерший рано (早死一生毕,)
Скоро окончил свой век;
Знать не дано, (谁论百年后。)
Что на сотый случилось бы год.
Ждет нас приказ: (招我还天公,)
Возвратиться к Владыке Небес,
Нам он себя (不须尽出手。)
Проявить до конца не дает.
按孟译俄文词意可转译为下列七言中文诗:
何人已死睡地下?活时地上到处走。
是谁躺下断声息?生时开口无止休。
早死一生结束快,无须评论百年后。
等候天公令我还,不必自己显尽头。
应该说,除了末句因对“尽”的理解有差而译文与原诗稍有出入外,其余各句的翻译均切合王梵志原诗旨意。俄文译文的前四句各用5个实词,后四句各6个实词,切近原中文五言;一、二、三、五句12音节,四、六、七、八句13音节;二、三、四、八句押т韵,第六句则押т的浊声韵д。总体来看,已经是相当规整了。再看他译的第16首梵志诗《我见那汉死》:
Увижу я:(我见那汉死,)
какой-то парень помер—
В утробе жар,(肚里热如火。)
Как будто от огня.
Не потому,(不是惜那汉,)
Что так уж парня жалко,—
Боюсь, черед (恐畏还到我。)
дойдет и до меня.
同样每句用了5个实词以切合中文五言,前三句各11音节,末句10音节,二、四句押я韵。也可转译成中文白话七言诗:
我见那汉已死亡,好似肚里火烧旺。
并非因为怜惜他,恐怕轮到我遭殃。
孟氏翻译时选用俄文词语是很到位的,如парень一词,俄语里常用作男子的俗称,正好对应中文的“汉子”,切合梵志诗的通俗性(王梵志诗里提及某某汉的有多处,至于其中蕴含的或褒或贬,可以见仁见智);又如中文里的“还”是有不同词性与多个义项的词汇,这里的“还到”,与前面一首“还天公”及其他各首里出现的“还你”“还我”“还他”中“还”的意思(回归、归还)不同,孟氏用表示“过程”的черед дойдет翻译,就区别了возвратиться或вернуться或ответить,词组后边又加上一个и,既增强了语气,又因增添了一个音节而起到整饬节奏的作用,也是颇见用心的。我不知道其他国家的敦煌学家是否也有将王梵志诗翻译成本国文字的,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孟列夫应该是第一位将王梵志诗翻译成俄文的汉学家。
当然,孟列夫研究员对国际敦煌学的杰出贡献当然还远不止于本文所述;而且,我相信,随着新阶段敦煌学研究的不断推进、发展,他在敦煌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也将进一步为学术界高度评价。
(2016年7月31日完稿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