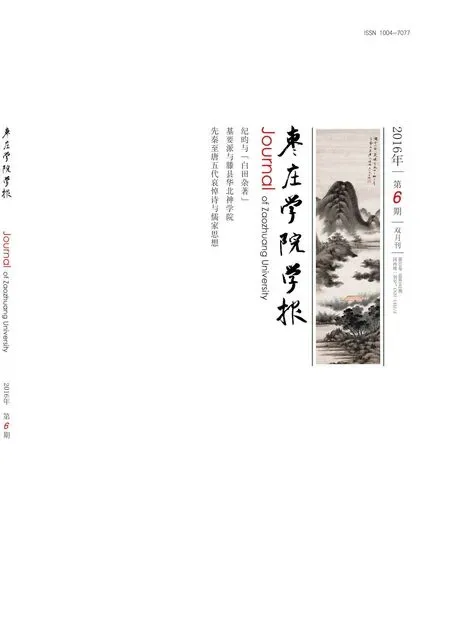《汉武故事》作者及史料价值探析
李峰
(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新乡 453007)
《汉武故事》作者及史料价值探析
李峰
(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新乡 453007)
《汉武故事》一书至迟在东汉中期就已经出现,后迭经学者续补,至南朝遂成定本。考虑到颇多西汉史著作曾在汉晋间流布,而张衡、潘岳又曾引据该书所载的史事,可以推断该书中的许多叙述定当渊源有自,故不可武断地斥其绝非信史,但是由于其中虚枉、错讹之事甚多,引据之时要加倍谨慎小心。
《汉武故事》;王俭;宋文帝;刘劭
《汉武故事》是一部出现于汉魏六朝间的文献典籍。由于诸家对《汉武故事》一书作者的著录颇相歧异,加之该书所载内容颇多怪诞,故自古以来对该书作者的考辨甚众。然而虽然学者们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问题不仅没能真正解决,而且又出现了种种新说,可谓聚讼纷纭。对该书的史料价值也是言人人殊,更有甚者有学者对该书的史料价值予以全盘否定,从而对学界研究汉代史事带来了相当大的困扰。因此笔者决定对该书的作者及史料价值展开进一步探析,以求正于方家。
一、《汉武故事》书成众手
关于《汉武故事》的作者,由于葛洪称其家有该书,《三辅黄图》称是班固撰,张柬之称是王俭造,刘弇称是班周撰,王应麟称是六朝人作。其中班固说、班周说已被证伪,并被学界普遍接受。然而20世纪以来,学者或持其他旧说,或另出新说,如鲁迅持文人所为说、李剑国持西汉成帝时文人作说和侯忠义持汉末建安时邺下亲曹文人所为说[1]。王守亮持汉未亲汉室文人所为说[2],师婧昭持成于成帝时人而为后世文人增删说等[3]。
因《汉武故事》有“长陵徐氏号仪君,善传朔术,至今上元延中已百三十七岁矣,视之如童女”[4](P5)。而元延为汉成帝年号,故李剑国等认为是成帝时人作。然而王守亮对此持异议:“从文献的角度看,检阅《史记》等唐前古籍,其行文述及古人,作者并不避以‘今王’等称谓称之。”[2]辛德勇认为这条史料可能是从托名成帝时人刘向所著的《列仙传》中摘出,因为东晋南朝道教中人引重该书中的记载,“故《汉武故事》中有关仪君的内容,更有可能是从《列仙传》中移录而来。惟《列仙传》传世之本已多有后人删削,迥非唐以前旧貌,今已难以比勘核实”[5]。而《汉武故事》又云“汉成帝为赵飞燕造服汤殿,绿琉璃为户”[6](卷七,P525)。“平帝时,哀帝衣自在柙外”[7](卷一《行次昭陵》)。汉成帝的“成”为谥号,故称“汉成帝”云云,当为成帝去世后所书。称“平帝”、“哀帝”者,显然也非成帝时人所书。故成帝时人诸说皆难以成立。
因《汉武故事》有武帝谶言:“汉有六七之厄,法应再受命。宗室子孙谁当应此者?六七四十二代汉者,当涂高也。”[6](卷一,P772)而“当涂高”之言出自东汉未年。《后汉书·袁术传》载,袁术少年时曾见谶书,其书言“代汉者当涂高”[8](P2439)。因此侯忠义认为是汉末建安时邺下亲曹文人所作,王守亮认为是汉献帝时亲汉室文人所为。然而东汉人张衡《思玄赋》述颜驷事、《西京赋》述长乐宫、明光宫与桂宫相通事、柏梁台灾事、卫后真发事,皆见于《汉武故事》[9]。可知此书至迟在东汉中期就已传布。故汉末文人说是难以成立的。
东晋葛洪在《西京杂记跋》中称其家藏有此书:“洪家复有《汉武帝禁中起居注》一卷,《汉武故事》二卷,世人希有之者。今并五卷为一帙,庶免沦没焉。”[10](P45)孙诒让、余嘉锡据此皆怀疑《汉武故事》为葛洪所作。然而不仅张衡曾引据《汉武故事》中的典故,晋惠帝元康二年,潘岳所作的《西征赋》也曾予以征引:“李善注《文选》,《西征赋》引《汉武故事》二条,其一为柏谷亭事……其一为卫子夫事。”[11](P1206)从张衡、潘岳皆引该书典故,且葛洪也并没有称该书为自己所作可以推定葛洪说也是难以成立的。
关于王俭说,始自初唐人张柬之。晁载之《洞冥记跋》引张柬之语云:“王俭造《汉武故事》。”[12](P16)晁公武称:“《汉武故事》一卷。右世言班固撰。唐张柬之《书洞冥记后》云:‘《汉武故事》,王俭造。’”[13](P362)辛德勇因持此王俭说,并以学者是否引述《汉武故事》为佐证:“今检刘宋裴骃《史记集解》与唐人颜师古《汉书注》,可见所引六朝以前古注都没有引述《汉武故事》,而南朝梁刘孝标《世说新语注》以及与之约略同时之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等始见征引此书,适与王俭的时代相接续。”[5]由于张衡、潘岳都曾引据《汉武故事》中的史事,故辛德勇的这一论述是不能成立的。
辛德勇又引余嘉锡的观点以为佐证:“余嘉锡以为张柬之所说‘自必别有据依,断非凭虚立说……至宋以后传本之题班固,则浅人所为,非其旧也’,即以王俭为本书作者。”[5]实则这是余嘉锡对《汉武故事》题名为班固的驳论,其对《汉武故事》作者推断是:“疑葛洪别有《汉武故事》,其后日久散佚,王俭更作此以补之。书名虽同,而撰者非一人,不必牵合为一。”[14](P1130)因《汉武故事》多言神仙怪异之事,盐谷温、周树人等认为《汉武故事》出自六朝词人之笔。辛德勇对此表示赞同,并认为王俭作为六朝时人,撰述这样的文字并不奇怪:“通览存世内容,知其所记无非道术信仰者以房中等法术修炼长生的行事,诚荒诞无稽之谈,而这正是东晋南朝时期以葛洪为代表的道家神仙学说盛行于世的产物,初不足怪。”[5]但是王俭并非道家中人,其自幼便宗奉儒学:“俭弱年便留意《三礼》,尤善《春秋》,发言吐论,造次必于儒教。”[15](P595)成年后“为时儒宗”[16](P663)。一生汲汲于俗世的功名利禄:“寡嗜欲,唯以经国为务,车服尘素,家无遗财。手笔典裁,为当时所重。少便有宰臣之志,赋诗云:‘稷契匡虞夏,伊吕翼商周。’及生子,字曰玄成,取仍世作相之义。”[15](P596)且仕途显达。因此对三十八岁即去世的王俭而言,其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去撰述、摘录这些神异荒诞之事。故胡应麟指出“诸家咸以王俭造”《汉武故事》,但他自己却不敢采信,仅是称“是六朝人作也”[17](P377)。姚振宗则疑非王俭所撰:“按此书为葛稚川家所传,而诸家著录皆不考其所始。六朝人每喜钞合古书,而王俭有《古今集记》。疑俭钞入《集记》中,故张柬之以为王俭造。殆亦不探其本意为之说欤!”[18](P265)
总之,综合诸家之说,结合张衡、潘岳曾引据《汉武故事》所载史事的事实,可以推断至迟在东汉中期《汉武故事》所叙述的史事就已经在社会流布,其书后迭经汉魏六朝学者续补而成。
二、《通鉴》所采录武帝与戾太子纷争史料非王俭所杜撰
辛德勇为证《汉武故事》为王俭所撰,对《通鉴》所叙述的关于巫蛊之乱的发生缘由以及对汉武帝与戾太子之间不同治国理念的描摹的文字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这段文字出自《汉武故事》,并且为王俭所杜撰[5]。其论旁征博引,言之凿凿,颇能眩惑视听。考虑到这些史料涉及对汉代重大历史事件巫蛊之祸的解读,笔者认为有必要予以深入辨析,以正视听。
考《通鉴》所采武帝与戾太子纷争史料,除“皇后亦善自防闲”、巫师方士变幻“无所不为”等文字与《汉武故事》颇相似外,其他如汉武帝让卫青向卫皇后母子传话之事、汉武帝让戾太子代理国事、苏文等谄害戾太子事,皆不见于《汉武故事》。故全祖望对其史料来源甚感困惑:“《通鉴》载戾园处疑畏之中,极其详悉,乃知戾园固无过,而武皇亦尚未失父道。天降厄运,生一江充以祸之。但《通鉴》此条,绝不知其何所出,《考异》中亦不及西京事。除《班书》外,唯褚先生补《史记》,偶有异同,而《荀纪》则本班氏。温公不知采之何书,大足改正班《史》,而惜胡梅磵亦未尝一考及也。”[19](P2028)吕祖谦《大事记》论及此事称:“《通鉴》引《汉武故事》诸书,戾太子及巫蛊事甚详。”[20](P518)王益之《西汉年纪》论《通鉴》中这段史料,引吕祖谦之语:“吕氏《解题》曰:《通鉴》引《汉武故事》诸书,载其始末甚详。”[21](P337)据此可知吕祖谦认为《通鉴》中的这段文字,所征引著作非止一种,因以“诸书”概括之。故《汉武故事》一书虽散佚颇甚,我们虽不能因为没有见到该书有相关史料,就否定该书没有记载这些史料,但也不能肯定上述史料一定出自《汉武故事》。辛文据吕祖谦、王益之语,认定《通鉴》关于这段史事的叙述,但凡不见于《史记》、《汉书》者,皆出自《汉武故事》,这种看法显然是不严谨的。并且姑且假定果如辛文所言,相关史料出自《汉武故事》,也不能肯定就是王俭所作。
辛文认为是王俭所作。理由有二:其一,“首先我们应当理解,这些内容,本来正符合神仙家的追求”。然后通过论述指出这些叙述属于虚妄无稽之谈。但问题是这些叙述并不涉及神异之事,辛文自己也说这些叙述“相对比较平实自然”[5],然其仍然与神仙家事相牵连,不免有穿凿附会之嫌。纵使其说言之成理,如前所言,王俭一生笃守儒家理念,他若要批评汉武帝穷兵黩武,也不会以神仙家思想立论。
其二,王俭出于个人原因,想“藉汉武帝与戾太子事来表现他对刘劭反对宋文帝之举的同情”[5]。关于这条理由,有数处值得辨析。
首先,辛文论王俭家事,称王僧绰、东阳公主亦即武康公主为王俭的“生身父母”。然史称东阳公主薨于刘劭发动宫廷政变之前,王俭“生而僧绰遇害”,成年后尚阳羡公主,宋明帝以王俭已故“嫡母”武康公主曾参与“太初巫蛊事”,不可以为阳羡公主的妇姑,欲开冢离葬,“俭因人自陈,密以死请,故事不行。”后超迁秘书丞,撰《七志》及《元徽四部书目》。“母忧,服阕为司徒右长史”[22](P433)。可见东阳公主并非王俭亲生母亲,且死于王俭出生之前。
其次,辛文认为王僧绰对待刘劭,至少是一个中立的态度。然而当刘劭发动宫廷政变时,史言:“会二凶巫蛊事泄,上独先召僧绰具言之。及将废立,使寻求前朝旧典。劭于东宫夜飨将士,僧绰密以启闻,上又令撰汉魏以来废诸王故事。撰毕,送与江湛、徐湛之。湛之欲立随王诞,江湛欲立南平王铄,太祖欲立建平王宏,议久不决。诞妃即湛之女,铄妃即湛妹。太祖谓僧绰曰:‘诸人各为身计,便无与国家同忧者。’僧绰曰:‘建立之事,仰由圣怀。臣谓唯宜速断,不可稽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愿以义割恩,略小不忍,不尔便应坦怀如初,无烦疑论。《淮南》云:‘以石投水,吴越之善没取之。’事机虽密,易致宣广,不可使难生虑表,取笑千载。’”观此可知王僧绰在此次宫廷政变中,态度鲜明、立场坚定地站在了宋文帝的一边。然而辛文对这段文字进行解读后,却得出了王僧绰对待刘劭,至少持中立态度看法,试问若王僧绰态度中立,为什么主动向宋文帝报告刘劭的动态?为什么要求宋文帝从速决断?所以议论史事,窃以为还是要以事实为依据。并且王僧绰遇害后,当时朝廷也认为王僧绰忠于文帝,“世祖即位,追赠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谥曰愍侯”[23](P1850~1851)。
其三,辛文因王俭坚决反对宋明帝改葬东阳公主事,认为“这说明王俭对其母附从刘劭反对宋文帝显然有所同情和理解”。然事实并非如此。王俭成年后尚阳羡公主,宋明帝以王俭已故“嫡母”而非生母武康公主曾参与巫蛊事,不可以为阳羡公主的妇姑,欲开冢离葬,为王俭阻止。其之所以如此,并非是因为对刘劭反对宋文帝有所同情和理解。因为王俭出生前,东阳公主已死,其出生时其父王僧绰遇害,王俭由其叔父王僧虔抚养成人,因此正如辛文所言,他对王僧绰、东阳公主在这场政治变故的认识,应主要得自他的叔父或其他王氏家族成员。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自王僧绰被害后,王僧虔就成了王氏一门的领军人物,王俭后身居高位,对于他仍甚尊重,因此王僧绰对此次政变的看法对王俭尤其重要。而王僧虔在其兄王僧绰被刘劭杀害后,“亲宾咸劝僧虔逃。僧虔涕泣曰:‘吾兄奉国以忠贞,抚我以慈爱,今日之事,苦不见及耳。若同归九泉,犹羽化也。’”[22](P591)观此可知王僧虔视刘劭为叛逆,认为王僧绰是忠于宋文帝而死得其所。自然他是不会认同东阳公主的行为的,所以王俭也不可能认同东阳公主的行为。
王俭之所以以死相争,反对将其嫡母离葬,应是出于为东阳公主尽孝之心,及维护家族声誉之意。王俭笃于儒学,少时便留意《三礼》,并撰有《古今丧服集记》,尤善《春秋》,极重《孝经》。元徽二年,王俭二十二岁时,编纂目录学著作《七志》,将《孝经》置于该书《经典志》所录群经之首:“王俭《七志》,《孝经》为初。”[24](P3)南齐时,国学设郑玄所注的《孝经》,领国子博士陆澄对时任尚书令的王俭说:“《孝经》,小学之类,不宜列在帝典。”并对国学所置《孝经》是否为郑玄所注提出质疑。王俭答称;“疑《孝经》非郑所注,仆以此书明百行之首,实人伦所先,《七略》、《艺文》并陈之六艺,不与《苍颉》、《凡将》之流也。郑注虚实,前代不嫌,意谓可安,仍旧立置。”[22](P683~685)他曾为齐高帝诵《孝经》之《君子之事上章》,齐高帝称“善”[15](P593)。王俭又曾与文惠太子论《孝经》,称该书“孝理弘深,大贤方尽其致”[22](P400)。王俭不仅精研孝道,而且还恭行之,其袭父爵时,虽数岁,然“流涕呜咽”,不失孝子之仪。宋顺帝“升明二年,迁长兼侍中,以父终此职,固让”[22](P433~434)。王俭“为朝宰,起长梁斋,制度小过,僧虔视之不悦,竟不入户,俭即毁之”[22](P596)。齐武帝永明三年,“叔父僧虔亡,俭表解职,不许”[22](P436)。对于父母之过错,儒家经典皆以为孝子不应当记藏在心,如《礼记·坊记》称:“子云:‘君子弛其亲之过,而敬其美。’”[25](P1620)并应该为其隐讳,如孔子云:“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26](P2507)《礼记·檀弓上》云:“事亲有隐而无犯”,郑玄注:“隐,谓不称扬其过失也。”[25](P1274)《公羊传》云:“《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27](P2244)《谷梁传》称:“孝子扬父之美,不扬父之恶。”[28](P2365)因此恭行孝道的王俭阻止宋明帝将东阳公主开冢离葬,应出于为嫡母尽孝之心,而非辛文的推理。因为东阳公主若被开冢离葬,其过失便会显扬天下,而遭世人诟詈,这不仅会让其先人蒙羞,并且也会影响到王氏高门士族的清誉,所以这对于笃守孝亲之义的王俭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因此以死抗争。
最后,辛文认为王俭可能从宋文帝与太子刘劭之事,联想到汉武帝与戾太子的纷争。然而,若说王俭由宋文帝兴兵北伐及刻薄寡恩而联想到汉武帝,当不无可能。但是认为王俭因刘劭为巫蛊并发动宫廷政变而联想到戾太子,则断无可能。理由有三:其一,双方父子关系不类。宋文帝对刘邵仁至义尽,虽知其使女巫严道育为巫蛊诅咒自己,仍然原谅了刘劭,后因担心京师出现非常之事,“辄加劭兵众,东宫实甲万人。车驾出行,劭入守,使将白直队自随”[23](P2426)。后得知刘劭仍在与女巫严道育往来,显见害己之心不死,方才打算废黜刘劭。而刘劭自有害父之心始,一直在处心积虑地算计其父。汉武帝则是晚年对戾太子刘据之宠衰减,后又精心布局,必欲除戾太子而后快,而史则不见载有戾太子有算计乃父之举。其二,巫蛊事不同。刘劭对宋文帝行巫蛊事,证据确凿;戾太子的巫蛊之事虽江充言之凿凿,但并没有证据显示实有其事,武帝自己后来也认为戾太子是无辜的。其三,攻守之势不同。宋文帝父子的宫廷政变,是刘劭主动进攻,宋文帝被动应对;汉武帝父子的宫廷政变,是汉武帝主动进攻,戾太子被逼抗争。
总此以上诸点原因,王俭不可能有通过虚构汉武帝父子纷争之事,来表达他对刘劭反对宋文帝之举的同情的动机。
三、《汉武故事》的史料传承
据刘知几幾称《史记》成书后,续补其书者有十五家:“《史记》所书年,止汉武太初,已后阙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29](P25)《后汉书班彪传》:“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李贤注:“好事者谓扬雄、刘歆、阳城卫、褚少孙、史孝山之徒也。”[8](P1324~1325)据杨树达考证,阳城卫与卫衡是同一人,史孝山即史岑。合此两说得续《史记》者十六人[30]。后班彪作《后传》六十五篇,班固因之而作《汉书》,班昭、马续等相继续成之。
汉史著作除《汉书》行世外,其他续《史记》之作亦颇有流传一时者,如《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31](P1714)。而葛洪称:“洪家世有刘子骏《汉书》一百卷”[10](P45)。班彪《后传》也曾流传,如王充称:“班叔皮续《太史公书》百篇以上,记事详悉,义浅理备,观读之者以为甲,而太史公乙。”[32](P615)且《汉书》为汉魏六朝之显学,为其作注解者甚多,研习者甚众:“始自汉末,迄乎陈世,为其注解者,凡二十五家,至于专门受业,遂与《五经》相亚。”[29](P25)此外《汉书·艺文志》还著录有陆贾所记的《楚汉春秋》九篇、《汉著记》百九十卷、《汉大年纪》五篇。其中关于《汉大年纪》,王应麟认为:“《高祖·文帝·武帝纪》臣瓒注引《汉帝年纪》,盖即此书。”[33](P17)考虑到臣瓒“生存年代,当在西晋”[34]。故王应麟之推断当可信。
因此必然会有为《汉书》所不载的汉代史事流传下来,故而对于汉魏六朝间流传下来的诸如《汉武故事》、《西京杂记》等书,学者虽知其中虚妄之事甚多,但一些叙述可补史传之阙也是不争的事实。故对其颇为珍视,著述之际,往往对其细加研析,谨慎征引,以增广异闻。
就《汉武故事》而言,因其中颇多神仙妖异之事,而其相对平实的叙述,辛德勇又认为是出自王俭的伪造,故断言该书“绝非信史”、“纯属虚构故事”,以此来论证《通鉴》采录《汉武故事》史事来重构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之误。李浩为驳辛德勇之非,则声称:“司马光《资治通鉴》全不取《汉武故事》之叙事”。论据是《通鉴考异》曾对《汉武故事》中的四件史事进行驳斥。《通鉴》在正面意义上使用《汉武故事》仅两处,且是以《汉武故事》证无关历史叙事之宏旨的名物,而“对它的叙事绝不采录”[35]。李浩的言论形同变相赞同辛德勇对《汉武故事》的断语。
实则如前所述,从《汉武故事》的叙事内容,以及张衡《思玄赋》、《西京赋》、潘岳《西征赋》引据《汉武故事》所载的史事,就可以看出该书至迟在东汉中期就已经出现。考虑到颇多记述西汉史的著作曾在汉晋间流布,可以推断该书中的许多叙述定当渊源有自,故不可武断地斥其绝非信史。
李浩为了申张自己的主张,却无力全面推翻辛德勇的观点,遂声称《通鉴》对《汉武故事》的叙事绝不采录,然其发语虽甚刚健,却没有说服力。因为事实并非如此。司马光确实说过《汉武故事》“语多诞妄”的话[36](P585),并对《汉武故事》中的史事屡有驳辩。但同时他并不排斥《汉武故事》中有价值的史料。即如汉武帝征和四年罪已事,就是采录自《汉武故事》。当然由于学者对于这条史料的认识不同,遂成聚讼。此外《通鉴》还对《汉武故事》一些史事如巫师方士变幻、武帝微行柏谷等史事予以征引,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虽没有讲明采录缘由,然细绎皆有采录之理,故为学者所认可。如吕祖谦论及《通鉴》采《汉武故事》诸书史实,以叙戾太子及巫蛊事称:“《通鉴》引《汉武故事》诸书,戾太子及巫蛊事甚详,如言是时方士及诸神巫多聚京师,率皆左道惑众,女巫往來宫中,教美人度厄,每屋下埋木人祭祀之,因妬忌恚詈,更相告讦,以为祝诅,上心既以为疑,因是体不平。此理之必然,盖可信也。”[20](P518)关于武帝微行柏谷事,据《汉武故事》载武帝微行柏谷“宿于逆旅”,向逆旅翁乞浆饮,翁答:“吾止有溺,无浆也。”并欲杀之,赖主人妪救护,武帝一行方得不死。还宫后,“乃召逆旅夫妻见之。赐姬千金,擢其夫为羽林郎”[6](P772)。其事颇与《汉书》所载武帝微行事相出入,据《东方朔传》载,建元三年,武帝开始微行民间,曾因损害禾稼而与当地百姓发生冲突,“时夜出夕还,后赍五日粮,会朝长信宫,上大欢乐之”云云[31](P2847)。《汉武故事》所载此事又被西晋潘岳《西征赋》所征引,显见此事至迟在魏晋时就已为人所熟知。《通鉴》因此采而入史。沈钦韩对此称:“按此事潘岳《西征赋》言之,定不妄也。”[37](P47)
辛德勇为全面否定《汉武故事》的史料价值,又以吕祖谦、王益之都觉得《汉武故事》的材料不可信据为证,实则吕祖谦、王益之对《汉武故事》都是既有批判又有肯定。既以吕祖谦论《通鉴》采《汉武故事》巫师方士变幻无所不为之事为例,如上所述,吕祖谦对此是认可的。王益之也予以采信。此外王益之采录的《汉武故事》史事尚有数条。
综上所述,《汉武故事》一书至迟在东汉中期就已经出现,后迭经学者续补,至南朝遂成定本。考虑到颇多西汉史著作曾在汉晋间流布,而张衡、潘岳又曾引据该书所载的史事,可以推断该书中的许多叙述定当渊源有自,故不可武断地斥其绝非信史,但是由于其中虚枉、错讹之事甚多,引据之时要加倍谨慎小心。
[1]刘化晶.《汉武故事》的作者与成书时代考[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6,(2).
[2]王守亮.《汉武故事》作者与成书时代辨析[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8,(5).
[3]师婧昭.《汉武故事》的作者及文本情况考辨[J].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13,(5).
[4]陆辑编.说纂甲集[Z].古今说海,上海:集成图书公司,1909.
[5]辛德勇.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J].清华大学学报,2014,(6).
[6]李昉编纂,夏剑钦,王巽斋校点.太平御览[Z].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7]高楚芳编,黄升校.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Z].明万历本.
[8]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9]李占锋,黄大宏.《汉武故事》的作者考述[J].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4).
[10]葛洪.西京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1]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2]晁载之.续谈助[M].丛书集成初编本.
[13]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4]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5]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6]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7]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丙部)[M].北京:中华书局,1958.
[18]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M].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Z].上海:开明书店,1937.
[19]全祖望撰,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0]吕祖谦.大事记解题[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1]王益之著,王根林整理.西汉年纪[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22]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23]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4]陆德明撰,黄焯断句.经典释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5]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M].十三经注疏本[Z].北京:中华书局,1980.
[26]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M].十三经注疏本[Z].北京:中华书局,1980.
[27]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M].十三经注疏本[Z].北京:中华书局,1980.
[28]范宁集解,杨士勋疏.春秋谷梁传注疏[M].十三经注疏本[Z].北京:中华书局,1980.
[29]浦起龙.史通通释[M].香港:太平书局,1964.
[30]杨树达.《汉书》所据史料考[A].大公报文学副刊,1932-05-23.
[3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2]黄晖.论衡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33]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M].二十五史补编(第2册)[Z].上海:开明书店,1937.
[34]刘宝和.《汉书音义》作者“臣瓒”姓氏考[J].文献,1989,(2).
[35]李浩.“司马光重构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说献疑——与辛德勇先生商榷[J].中南大学学报,2015,(6).
[36]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37]沈钦韩.汉书疏证(外二种)(2)[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王记录]
2016-10-20
李峰(1973-),男,河南社旗人,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政治史、史学史研究。
G256
A
1004-7077(2016)06-00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