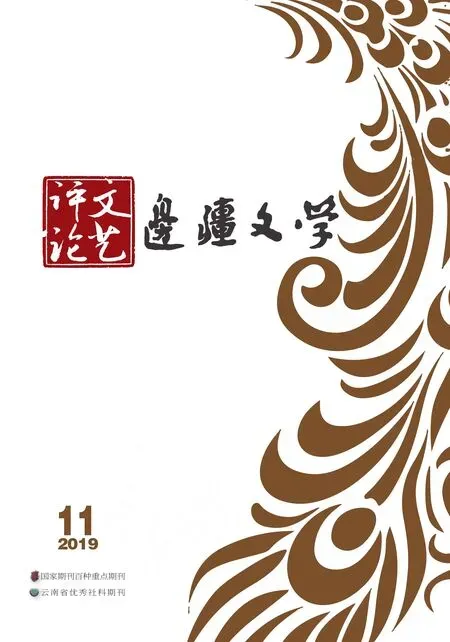从万物有灵看长篇小说《宾玛拉焚烧的心》
黄锦活
万物有灵的观念自古有之,是人类对世界的初步解读,是关于神灵物的一般信仰。英国人类学家泰勒认为:“万物有灵观的理论分解为两个主要的信条,它们构成一个完整学说的各部分。其中的第一条,包括着各个生物的灵魂,这灵魂在肉体死亡或消灭之后能够继续存在。另一条则包括着各个精灵本身,上升到威力强大的诸神行列。”在泰勒的文化观念里,万物有灵观是宗教的起点,它内涵丰富,概括起来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人有灵魂,人的灵魂可以离开肉体并且可以在肉体消亡后依然存在;二是除了人以外,一切的动物、植物、物品都拥有灵性或灵魂;三是神灵在万物有灵学说中占有重要地位,神的意识可以与人相通。人类社会从蒙昧步入文明,人们对科学文化的探究越来越深入,面对现代社会的冲击,万物有灵观退居幕后,其光芒也逐渐被各种现代思想遮蔽,幸运的是,一些作家,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作家笔耕不辍,在作品中重塑了许多已经慢慢远去的万物有灵的世界,在精神上重返原生态的民族生存图景,和晓梅就是其中的一员,她的小说具有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值得深入研究。
从历时态层面看,和晓梅的小说创作始于1998年,1999年发表处女作《深深古井巷》。自那以后,她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女人是蜜》《呼喊到达的距离》、长篇小说《宾玛拉焚烧的心》、儿童文学《东巴妹妹吉佩儿》等作品,揽下了“春天文学奖”“边疆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等奖项。从共时态层面看,作为纳西东巴文化的一员,和晓梅自身烙上了纳西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精神的印记,这种集体无意识精神影响着她的生活及写作,可以说,和晓梅在为本民族的过去和现在而写作,她的写作是一次漫长的重构东巴文化的文学之旅和精神之旅。和晓梅曾这样说:“我在现代社会里寄存着躯体,却在东巴文化的世界里寄存念想”,庞大、深厚的纳西族传统文化“一直停驻在我的心里,或者血液里,骨髓里,细胞里,或者任何一个地方。”作为东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万物有灵的观念不仅存在于和晓梅的血液里,还出现在她的文学世界里面。在一次访谈中,和晓梅谈及自己作品中复杂的时空设置时就认为,她的复式、立体的表达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关系甚少,而与个人所信奉的万物有灵观关系密切。她说:“像我们少数民族本身接触自然比较多,我们生活在自然、山水、田园之间,很多少数民族作家都信奉万物有灵观,在充满灵异的状态下,线性和单一的表达方式并没有办法让它构建他与自然的关系、跟社会的关系。”笔者认为,在《宾玛拉焚烧的心》这部长篇小说中,万物有灵观以各种方式散布其中,它不仅在形式方面表现为复杂神秘的时空设置,还在内容方面体现为灵性的自然万物以及神灵与亡灵的存在等,其主要特征由下可见。
一、灵性的自然万物
在万物有灵观的视觉下,和晓梅在《宾玛拉焚烧的心》里面常常赋予动植物以人的情感和思维,将动植物人格化叙述,一只狗、一头牛、一片叶子、甚至是一片苔藓,不管它们对人类友好抑或不友好,都有着自己的灵魂。
小说分为上下两部,主要围绕宾玛拉家族几代人的生活展开叙述,其中宾玛拉墨和宾玛拉金既分别是作品上、下部的主人公,同时也是作品上、下部的主要讲述者。在小说的上部,傈僳山寨的人们认为宾玛拉默过于野性自由,对主不够虔诚而将她驱逐到密林深处作为惩罚,几个傈僳族的女人帮助她在密林里修建了木楞房,这座木楞房是鲜活有生命的:“雨季过后,在我的家里,你会偶尔发现躲藏在墙壁缝里的黑木耳,或者一朵旁若无人,显得亭亭玉立的牛肝菌。至于苔藓,它们随处可见,而且长势喜人,有时候它们忘记了这个家到底谁是主人,会将它们的领地蔓延到任何一个可能的地方。”作为木楞房屋顶木料的一根映山红和其他木料一样也还活着,它长出了圆圆的小树叶,其中“有一片叶子特别喜欢聚集屋外的潮气,当水汽越聚越多的时候,就会形成一粒水珠,慢慢地在叶片上滚动,最后滴在我的额头上。”作者给予这些植物各异的脾气秉性,它们就像人类一样,有着自己性格和爱好,可爱又活泼,非常动人,与此同时,这样鲜亮的生命也给略显野蛮和血腥的文本世界增添了一抹温情。这样的将动植物人格化描写的语言文字在作品中是较为常见的,如“许多棵高大的野板栗树在乌卡刚才的凄厉长啸中瑟瑟发抖,现在终于抓稳了大地,停止了抖动,阳光的椭圆形影子,从一片树叶挪动到另一片树叶。有一只棕色的狐狸在远处静静地看着我,穿过树丛的它的目光,迷离而复杂”,以及“连一棵草都恨不得长出嘴巴参加到传言的队伍当中”等等,似乎万事万物都拥有自己的灵魂,它们是和人类处于平等地位的生命个体。
小说中,作者着墨最多的带有灵性的动物是一头黑牛和一条不停打嗝的狗。一天清晨,在宾玛拉墨的木楞房附近,一头黑色的健壮公牛死在了几个偷牛贼的手里,从小说后面的情节可以知道,这头牛的主人是宾玛拉墨的祖母——女祭司宾玛拉金,黑牛作为这位女祭司唯一的陪伴者,深受女祭司的喜爱和祝福。黑牛的肉体被偷牛贼分食和卖掉,遗留下来的一根腿骨嗡嗡作响,发出低沉而喑哑的嘶鸣,笔者认为,这代表着黑牛的灵魂在哭泣和哀怨。这根牛骨头持续的哀鸣使得宾玛拉墨饱受折磨,夜不能眠,想尽了办法都得不到摆脱,只有当牛骨头被她握住,才会停止发出只有她才能听到的声音。一个路过的普米族工匠用这根牛骨上的筋制作了一张弩弓,这张弩弓很少离开宾玛拉墨的背,因为一旦离开,它就嗡嗡作响,让宾玛拉墨片刻不得安宁。这张附着着黑牛灵魂的弓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宾玛拉墨成为一名出色的女猎人,还衍生了一系列的情节。当初的四个偷牛贼,一个因当时黑牛的反击流血过多而死,一个后来成了拉木非土司家的卫士,在和宾玛拉墨抢夺火铳时意外地死在了自己的火铳之下,一个成了非法的淘金者,在躲避官府的追捕时离奇地死于宾玛拉墨用来捕猎的兽夹陷阱之中。偷牛贼前赴后继的离奇死亡,让宾玛拉墨意识到这样的结局是偷牛贼们难以逃脱的劫数。此时只剩下一个不知身处何处的偷牛贼还活着,为了避开仅剩的这个偷牛贼依旧离奇死在自己面前的命运,宾玛拉墨做出了离开的决定,和乌卡长途跋涉,来到了热带雨林——乌卡的故乡。令宾玛拉墨战栗的是,仅剩的这个偷牛贼为了摆脱偷牛同伴们离奇的结局,无意中也来到了热带雨林,被乌卡的部落抓住并且即将用来祭祀树神,在脱逃时被乌卡用从宾玛拉墨背上拿走的弩弓击中了头部。当这个偷牛贼死去的那一刻,那张“性格怪异”“发疯作响”的弩弓也随之坏了,因为尽管出自无意,流淌着女祭司宾玛拉家族血液的宾玛拉墨最终还是促成了它的报仇任务,所以得到安息的黑牛的灵魂也就消散了。
因为怀念家乡以及乌卡移情别恋的缘故,宾玛拉墨孤身离开热带雨林,在路上遇到了一只患有严重打嗝症的瘸了一条前腿的狗,她将这只来路不明的默默地尾随着她的狗取名为乌卡,用来纪念已经不在身边的同名男人。乌卡是一只不同寻常的狗,它“早就活过了一只狗应该活的年纪”,拥有独立的思维和判断力,除了形态以外,其他的一切表现几乎和人没有差别。这只狗和宾玛拉墨形影不离,会做出摇头叹息、面露鄙夷或者面带犹豫等带有灵性的行为作为回应。比如,在儿子和“我”(宾玛拉墨)发生争执后而带着不满离去时,“乌卡习惯了我们的不欢而散,在不远的地方等着我,一面心安理得地打嗝,一面用它那双逆来顺受的眼睛,同情地注视着我”,在宾玛拉墨和它低声说起“我”(宾玛拉金)的反常时,“我看见乌卡目不转睛地看着我,若有所思。我还看见它悄悄地打了一个嗝,并且对这个不合时宜的嗝做了掩饰。”可见,在作者的观念里,动物是有灵性的,它们有思想,有感情,和人类相互映衬,是独立的个体存在。
和晓梅的这部作品中鲜活的、有灵性的动植物的出现满足了读者的阅读期待,它们比文本中许多冷漠、反常的人物更加真实可爱,在一定程度上柔和了作者建构的蒙昧和血腥的艺术世界,使作品展现出多面化的魅力。
二、神灵与亡灵的存在
在万物有灵观的学说里面,神灵和亡灵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神灵被认为影响或控制着物质世界的现象和人的今生和来世的生活,并且认为神灵和人是相通的,人的一举一动都可以引起神灵高兴或不悦。”在《宾玛拉焚烧的心》这部作品里面,作者就讲述了这样的事情:神灵和人是相通的,宾玛拉家族女祭司的能力之一就是通过占卦与神灵相通,寻找关于未知事物的答案。其中,最神秘的莫过于女祭司通灵时的情形,“她的目光停留在我们无法知晓的疆域……虚弱的嘴唇快速嚅动,吐露出一些无声无息的文字,似在同某位万能的神灵浅声交谈,获取指示,她那不归自己使唤的手颤抖着在沙盘上飞速移动,画出一个外人永远也无法看懂的奇异图形。”借助于这类神奇的描写,作者让读者更加深入地感受和理解潜藏在万物有灵观背后的那个意蕴丰富的东巴世界。
除了拥有独一无二的火塘神之外,宾玛拉家族还有着一些和自己家族关系要好的神灵,关于这些神灵的称呼和各自的能力具体如何,叙述者没有详细地告诉读者,但可以确信的是,尽管神灵们不止一次地捉弄女祭司,让女祭司的卦象啼笑皆非,但是在关键时刻神灵不会以虚假的答案欺骗女祭司。在作品下部当中,遥远的地方搬迁到落风村的宾玛拉家族遇上的第一个问卦者就是当地的拉木非土司,这是一次影响甚大、关乎整个宾玛拉家族安危的占卜。祖母宾玛拉赫作为一名虔诚的女祭司,她坚定地相信神灵传达的消息,把卦象显示的有损拉木非家族名誉的答案如实地告诉拉木非土司。从作品后面的内容可以知道,她得到的卦象和预言都是真实的,神灵没有在这种紧要关头欺骗她,但是拉木非土司和哲格汝总管精心设计了圈套,联手用阴谋名正言顺的处死了这个来处不明、不为权贵折腰的女祭司。后来,宾玛拉赫的外孙女——宾玛拉金也遇上了一次关乎自己性命的占卜,这位平常惯于在占卜中加入自己的思考,有时候甚至可能会根据问卦者的需要而歪曲卦象的聪明的女祭司,这一次却也像曾经的祖母一样,坚定地相信占卜得来的卦象,把卦象上面显示的极为不祥的内容如实地告诉问卦者卜撒南八世。这一次,神灵透露给她的答案也被证明了是真实的。除了这两次关系重大的占卜以外,作品中女祭司根据来者的需求为他们求神问卦,而神灵给女祭司透露答案的事情也时经常发生,除此之外,作品还经常出现叙述者和人物对神灵的指涉与议论,关于神灵的叙述构成了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神灵的理解不是单向的,缺乏辨析力的,作者在文本中侧面展示了神灵的在场,却不提倡盲目地、过分地依赖神灵的力量,对于热带雨林中格木人用成年男人祭祀树神、对树神的可堪狂热的敬仰行为,作者是持否定态度的。此外,信奉神灵并不意味着人类要把文明拒之门外,人类应该具有理性分析的能力,相信自身的力量,通过双手和大脑探索未知,发现未知,走向知识与文明的道路,就像宾玛拉墨所言:“除了从神那里获取力量以外,我们还应该向自己的身体要力量,毕竟这才是最行之有效的,神灵有时候无暇顾及我们。”
万物有灵观认为,人的肉体死去以后,灵魂可以依然存在,和晓梅的这部作品就描写了人死之后,以亡灵的身份留在人间的现象。宾玛拉金的两个舅舅因为拉木非土司的阴谋被名正言顺地卖到深山里的野蛮部落做奴隶,其中的一个舅舅忍受不了野蛮部落非人的折磨,逃跑未果被残忍地剥皮,成了一面鼓,舅舅的亡灵就附身在这面鼓上,一旦鼓被擂响,宾玛拉金就会听到舅舅凄惨的叫唤。海螺象征着平安和吉祥,却被用来吹响必定伴随着流血与死亡的战争的号角,尽管海螺的寓意再美好,卜撒南家族和拉木非土司家族发生激烈战争的地方还是出现了很多的亡灵。“那块坡地上成群的冤魂,因为得不到良好的超度,在风雨中喋喋不休地抱怨。”奇怪的是,普通人无法与神灵相通,却能感受到这些亡灵的存在,即便是天生的聋子和后天的傻子都能听到这些亡灵发出的声音。有意味的是,人们有时候也可以从这些亡灵的抱怨中获益。一个天生的聋子听到某个亡灵惊呼山洪冲走了他的鞋子,于是就到河流下游耐心地等待,果然捡到了鞋子。这些不同抱怨的亡灵停留在人间不肯离去,直到依牧喇嘛、傈僳族牧师、宾玛拉金这几位代表了各个地方的通灵者先后做了盛大的亡灵超度仪式以后,人们的耳根子才得以清净下来。
万物有灵观是历史上一些少数民族认识世界的原逻辑思维方式,在小说中,纳西族作家和晓梅也从这一角度表现了对纳西族民族习俗的关注和思考。笔者不能断言万物有灵观影响了作家和晓梅的全部创作,但在《宾玛拉焚烧的心》这部长篇小说中,关于万物有灵观的书写的确以各种方式渗透在作品中,展现出独特的魅力。笔者认为,这部小说是作家和晓梅深度描摹东巴世界的新高峰,和晓梅在作品中极力要展现的不只是一个万物有灵的世界,而是以万物有灵观为媒介,多角度地凸显由历史地理独特性孕育出来的传统纳西东巴文化。
现今,纳西东巴文化是一种失落的文化,人口的外迁和外来经济文化的冲击使得纳西人的民族自我意识淡化,许多纳西人贴着一个“纳西族”的标签,身上却几乎看不到东巴文化的影子,就像作品中的宾玛拉墨以及宾玛拉司令一样,有着“宾玛拉”家族的姓氏,却不明白“宾玛拉”究竟意味着什么,处于一种身份的迷失与寻找的状态之中。面对这样的现象,作家和晓梅开启了个人意义上的文化寻根,在作品中建构神奇的纳西世界,以此来保护自己所珍爱的民族文化。在书写民族文化的道路上,和晓梅做过艰难的跋涉,成就不俗,无论是在作品的思想深度上,还是艺术的表现上,都存在着令人惊喜的地方。期待和晓梅不断超越自我,创作出更加优秀的文学作品。
【注释】
[1][12] [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上[M].连树声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414、414
[2][3]和晓梅.呼喊到达的距离·后记[M].昆明:云南出版社,2012:326、327
[4]肖敬波. 和晓梅小说的女性书写·附录:当代纳西族女作家和晓梅访谈录音整理[D].云南师范大学,2017
[5][6][7][8][9][10][11][13][14][15]和晓梅.宾玛拉焚烧的心[M].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5:11、11、24、49、102、214、98、218、98、79、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