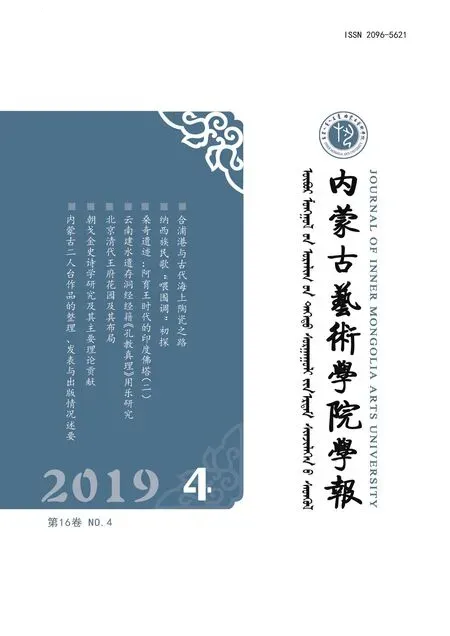历史情境下从女红看壮族女性意识的构建和表达
徐昕 张煜璇
(1.广西民族大学民族研究中心 广西 南宁 530006 2.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6)
女性意识是妇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它是历史的产物,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以女性的眼光洞悉自我,确定自身本质、生命意义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二是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审视外部世界,并对其加以富于女性生命特色的理解和把握。[1]“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性别不平等固然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但上述特征并不能代表中国文化性别的全部内涵。”[2]少数民族文化中性别文化的表述与渗透,与男性强势并存,是丰富而多元的。女红,指的是古代女性在家庭范围内主要以使用为目的的纺织、缝纫、刺绣等。女红不仅是壮族女子爱的艺术,同时它也是家庭经济来源,是女性意识的表达。女红对于女性意识的塑造主要表现在自立、自主和自由三个方面。本文把壮族女性置于历史的框架下,以女红为剖面,细致具体地考察女红对女性意识的塑造及展现,从而还原壮族女性丰满充盈的群像。
一、自立
经济活动中的女性分工及作用是其性别角色构建过程的一个重要途径和基础环节。壮风自古男逸女劳,[3](89)女子主导着生活、生产与贸易,“男子懒事耕商,妇女克勤”,[4](550)“男多逸,而女服劳春秋田作”。[4](551)《陆川县志》也载:“农家之妇女,当耕耘收获时,日则作田功,夜则纺绩……自老至少,绩纺不稍息。”[5](77)从而可见女性是家庭支柱和家庭经济的开源者。纺织,是传统女红中的首要项目,《汉书》中记载“农夫释耒,红女下机。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壮族女性通过女红对家庭和社会的贡献显而易见。
首先,女红满足了全家衣被等生活之需。虽然没有现金收入,但节省了不可避免的开支。
其次,还通过赋税的支付而转化为潜在的剩余价值。早在唐代,壮族先民即以将纺织品作为贡品。如唐《元和郡县图志》记载“贵州……贡苎布”、“宾州……贡筒布”,《新唐书·地理志》载“容州贡布”、“郁林州贡布”。在宋代,广南西路转运使陈尧叟鉴于实际情况,奏请广西户税以苎麻折算,宋真宗“准诏课植桑枣,岭外唯产苎麻,评折数”。[6](214)
第三,女性还大量参与圩市等进行女红贸易,“玉环穿耳谁家女,负贩归来坐小船”。[7](1020)圩市早在宋代,就已遍布壮族地区各地,承担起自产的手工业品和地方性农副产品交换的重任。雍正《太平府志》风俗中载:“墟场贸易,多妇女,货物惟布帛、菽粟、草缕、瓜瓠等物”。圩市因在“僚人”地区而称“獠墟”,如《岭表录异》载“夷人通商于邕州石溪口,至今谓之獠市”。[8](8)石溪口在当时声名远播,是方便左右江地区壮族人民互通有无的较大圩市。圩市三天一圩或五天一圩,如“容州夷多民少……呼市为圩(圩壮语叫肥)五日一集” 。[9](12)女性是圩市贸易的主要人群。永淳县“趁墟贸易,皆妇女为之”,[4](551)上思州“趁墟多系妇女,跣足蓬头担负业集”。[4](553)其中的纺织品,尤其是麻葛织品,如郁林细布、宾州蕉布、柳布、象布等,随“商人贸迁而闻名四方”。[10](233)
女红培养了女子的谋生技能,满足了基本生活需要,并是家庭经济的重要来源。经济上的重大贡献影响了女性政治、文化观念的发展,使其有能力去追求个性的独立、向往的生活和应得的权利,为其发扬自尊自强自信的女性意识提供了平台。
二、自主
壮族的婚恋较为自由开放,青年男女可以采用对歌择偶或绣球传情等多种方式寻找对象。《广西通志》嘉庆卷中载清广西思恩府,“春秋二社,士女毕集,男女未婚者以歌诗相应和,自择配偶”。民国《雷平县志》记载:“个侬尽可自由恋爱。”民国《三江县志》记载:“僮人在昔皆有歌坪,男女集于其间,而分界限,相距约半里,彼此唱山歌,互相应和……男女婚姻缔结之始于此场中者,虽尚有必经之过程,其最先媒介,则歌声也……男择女之相悦者相款曲,订会期。在进则可议婚云。”[11](154)壮族女性踊跃参加歌圩、赶集等社交活动,拓宽视野,把握增进男女双方了解的机会,以期对爱情及人生进行理性判断,“趁墟相约去歌坡,籴米归来女伴多”。[7](1014)
据《广西妇女社会地位调査》报告,广西妇女的婚姻自主率与广西男性相比仅低两个百分点,而与全国女性相比则高出26.2个百分点。[12](125)流传于红水河流域的壮族《传扬歌》,用喜闻乐见的山歌形式唱出人们对爱情的看法,女子认为“嫁得意中郎,持家喜洋洋。疼夫嫌不够,日子甜过糖”。[13](128)情感因素在婚姻选择中占据重要位置,因此壮族女性积极地通过女红来展现自我、表达情意,从而掌握婚姻幸福美满的自主权。
首先,女红展现了女性的美和勤劳。整个婚恋的过程中,男女双方在道德伦理和审美观念等方面和谐的要求是择偶的标准。这种标准构成于壮族社会的文化边界之内,受到社会的规训。壮族百姓勤劳淳朴,社会环境和谐友爱,反映在婚姻上的思想都与这些品德一脉相承。由于社会分工,女红一直由女性承担,是对女性完善自我的锤炼与塑造,同时也是社会群体及其文化体系对于女性形象的指认,是评价女性能力、品德的重要内容。
传扬歌宣扬的伦理道德中认为做人勤劳、心灵手巧是重要的美德,“说千言万语,勤劳是头条。苦命有尽时,瘦马能上膘”。[13](119)正如“娶妻貌美,不如娶妻手巧”,很多壮族山歌也作出这样的倡导,比如:“妺妹爱我爱她,妹妹爱我会种地,我爱妹妺会纺纱。”[14](242)云南壮族民间流传“买牛要买丫角牯,选媳要选老丈母;看妻先别看人才,进门先看绣花鞋”[14](98)的谚语。因此,就连女方婉拒男方的媒约,也以不善女红为由,如“女儿年纪轻,未曾懂什么,未曾学织布,未曾学绣花,……亲家定要娶,不知怎回答。”[15](60)
在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下,女红成为评判标准,因此女性对自己制作的女红产生价值观的自豪感。壮族女性通过女红大方地展现自己的德行、才貌,获得男性的认可,争取爱情的主动。女子在参加歌圩、赶街或走亲戚时,会打扮一新,如清朝诗人曾昌霆描述的“时颖新妆服色妍”。在云南文山壮族的“交友节”上,姑娘们会穿上自己亲手做的黑布衣服、绣花鞋,背上自己绣的花挎包。广西东兰县的壮族姑娘,也爱穿上自染自织的深黑色衣服,配上一双绣花鞋,故意露出染有蓝靛色的手,俗称“两黑一花”,以此吸引男青年。凤山县的民歌《彩云不敢飘》,赞美女方的勤劳能干:“妹在园中笑,鲜花红似火,妹在村中唱,百鸟都来和。妹呀妹,哪个比得你娇娥?丝线细又长,阿妹织布忙,白布铺成九里街,花布堆成万花筒,青布染蓝靛,黑里又透蓝,妹呀妹,千般手艺你高强。”[16](184)
其次女红是表达情意的方式。男女两情相悦,“歌毕辄携手就酒棚,并坐而饮,彼此各赠物以定情,订期相会”。[17](43)信物有绣球、布鞋、布料、衣物等。绣球源自“飞砣”,逐渐发展成为12瓣的绣花布囊。结构独特、选料考究,且全部以手工制作,早在宋代朱辅《溪蛮丛笑》就有记载:“俗节数日,野外男女分两双朋,各以五色彩囊豆粟,往来抛接。”
尽管是自由恋爱,但经历的环节都是慎重的。在男女婚事定局后,为答谢男方的礼物,女方父母送布匹给女婿,女儿送布鞋给好友歌伴,在接收这些礼物时,要唱《谢衣鞋歌》和《答谢衣鞋歌》;办嫁妆期间,同村姐妹来缝新被时还要唱《缝新被歌》。[16](123)
对于新娘来说,女红是嫁妆同时还是婚姻资产。女红是新娘必不可少的陪嫁。新娘的陪嫁看家境情况,过去通常为几床新被、蚊帐和几套到几十套衣服,有钱人家甚至送几十条壮锦新被。[18](49-50)清乾隆《归顺直隶州志》载壮人凡嫁女“嫁奁,土锦被面决不可少”。清人沈日霖《粤西琐记》“壮妇手艺颇工,染丝织锦,五彩斑然,与缂丝无异”。嫁妆由接亲队伍带回去,摆在厅堂上供客人观赏,向人们展示新娘的勤劳能干和娘家的大方富有。[19](162)陪嫁的女红不仅在婚礼上给新娘增加颜面光彩,而且日后可以经年使用,减少经济上的花费和婆家的掣制。
在民间文学中关涉女红的叙事,都包含着较为鲜明的女性自我解放意识。女性开始关心自己的身心感受,并以主动的方式选择婚恋,通过女红强调个人存在的价值以及温暖的情意。
三、自由
女红是载体,给女性以表达和选择的自由。女红的纹饰、配色,都是一种原生态的叙事意向,是壮族妇女关于生活愿景与社会观点主体性感受的表达。
“色彩是思想的结果,而不是观察的结果。”[20](25)壮族女性突破了自然界物象的固有色彩象征,跨越历史的阐释空间,构建了属于自已的视觉符号系统。壮锦设色明丽,对比强烈,如红绿相间,黄紫相配,但通过晕色过渡、补色协调配置和色彩间隔的运用,[21]使得壮锦既色彩斑斓又和谐统一。如图1(图1,壮锦。图片来源:余武章著《广西少数民族图案选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页)以真红色为底,凤纹、蝶纹和花纹用绿、黄、紫三色织成,形成明艳热烈的画面效果。同时在边缘又多用白灰色的线与面交错其间,起调合作用,突出主体图案。“深底人人爱,浅底也不坏”,暗底亮花也是壮锦中色彩运用较多的方式。深色底部可以中和花部的浓艳,增加稳重感,且颜色耐脏实用。如图2(图2,壮锦。拍摄时间:2019年7月31日,拍摄地点:广西龙州县金桂农贸市场李素英店铺;拍摄者:张煜璇),明蓝色图案在墨蓝色底纹的衬托下,越加清晰。并用对比强烈的粉红、杏黄作八角星花更显跳脱粗犷、生意盎然,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图1

图2
女红纹样的创作,将那些客观对象经由具象到抽象,进而固化为观念的替代物。首先现实生活和人间情味自由地进入女性创作领域。壮族人民生活在树林蓊郁、花草茂盛的岭南地区,人与自然相互契合,浑然一体。女性通过真实描摹,反映了一派生态和谐、生机蓬勃的美景。
其次壮族女性对人与自然进行意义上的联系,将外部的现实世界纳入个体的思维框架中。因此传统纹饰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除了具有美的形象外,还是壮族女性对生命、生活、历史及未来的思考。比如花的纹饰,已从对自然的摹画上升为对女性始祖“姆六甲”的膜拜。人们认为世间的男女都是姆六甲花园里的花,妇女怀孕在于始祖的赐予。花崇拜是“民知其母不知其父”的一种延续,是母权时代的遗韵和追忆。同样,青蛙纹饰也偏重于女性文化。壮族民间《蚂s歌》中“蚂s是天女,雷婆是她妈”,在正月蛙婆节“请蛙婆”“孝蛙婆”“游蛙婆”“葬蛙婆”等仪式过程中,也很容易找到彰显女性地位作用的主题。女性强大的创造力和崇高的地位通过纹样的形式在不断的承传讲述中得到延续和渲染。
此外,纹饰的选择也是自由的表达。当左右江地区掀起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战争时,女性挺起胸膛,响应号召,正如歌里唱到“裤子镶边衣绣花,又费银钱又麻烦。衣服绣了几道杠,就像犯人麻绳缠。年轻妇女不解放,还要等到哪一年?”[15](104)
总之,女红是个人通过符号的建构和选择,并完成自我呈现的实践活动。它不仅体现了壮族妇女的审美情趣,同时包含着对生命的体悟与智慧,对女性命运的探索和思考以及女子独立人格的高扬。
结论
壮族女红来自乡土中千百年的母系传承,地方色彩鲜明,在当地社会文化传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女红帮助女性对自身的价值进行认识,实现和评价,它是女性自身存在的自我呈现,将自我与社会结构相连,折射出历史的本质和时代的特征,形成民族性及整体文化的坚牢基础。在文化的进程中,女红由自我而来,同时又形塑自我。它积极塑造着壮族女性自立,自主和自由的文化意识,积极达观的人生态度和解放自我的天性。通过女红对壮族女性意识的构建和表达,反拨过往对传统性别文化认识的偏颇,从而更好地认识今日壮族女性的存在状态,为当代社会和谐的两性文化之构建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和借鉴。
——以传统文化与拼布艺术课程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