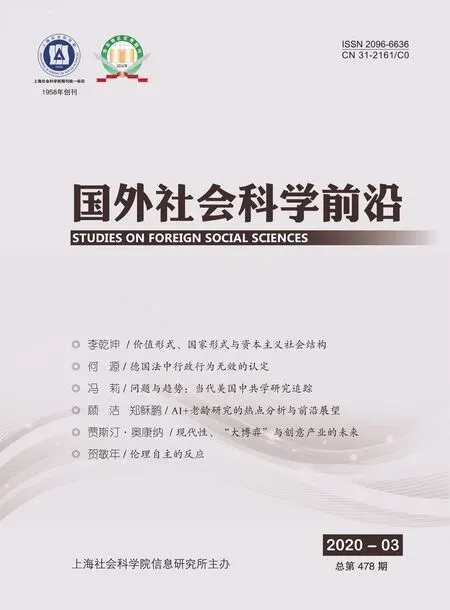现代性、“大博弈”与创意产业的未来 *
贾斯汀·奥康纳
内容提要 | 中国目前成功加入了全球创意产业的“增长”叙事,但在实力增强的同时,中国也与美国开展了竞争,尤其是在具有全球价值的技术设施领域。在被美国视为“超级对手”的同时,中国也面临着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之争。如何借“冠状病毒暴发”在全世界带来的喘息机会,认真思考何为“美好生活”,如何“共同建设美好生活”,是中国当下大有可为的命题。西方现代性强调“进步”与“增长”所制造的生态危机,需要中国以东方智慧,提供不同的道德理性来加以平衡。
现在看来,质疑中国的体制是否能打造一个“创意经济”,已经是过时的观点。当然我们可以说,一个拥有14 亿人口、收入在持续提高、服务业持续发展、国内消费持续增长的国家,总是会有一个庞大的文化产业在为其服务。中国的互联网防火墙并不像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所说的那样,是白费劲地把果冻钉在墙上,而是为自己堪称优秀的数字平台建设打下了基础。我们再也不能用“要么转型,要么出局”这样的两难困境来描述中国了——这个国家已经成功地与创意产业不断“增长再增长”的故事融为了一体。在有关“创意产业”的叙事中,唯一重要的政治议题是那些有可能阻碍这一“产业部门”发展,或是对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产生限制的议题。这对英国(尤其是脱欧后)、欧盟及其部分成员国(尤其是德国、法国和荷兰)等希望进入中国市场,也欢迎中国对其投资的国家来说,显得尤为重要。然而这对美国来说,没那么重要。美国仍然是全球文化产业中最重要的一支力量,目前仍处于由它的五大科技企业巨头脸谱网、亚马逊、苹果、奈飞、谷歌(FAANG)等在全球的成功所带来的亢奋状态之中。对美国来说,中国在内容上还谈不上“威胁”——事实上,所有人都认为中国的软实力,即便在东亚地区也是不温不火的。关键点在于,中国在数字平台构建了属于自己的庞大市场;此外,中国的数字通讯技术已经开始进入西方国家基础设施的核心。
虽然“软实力”这一概念将大家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内容上,但美国在全球文化产业中的主导地位依赖于它对一些基础领域的控制——商业、技术和法律等。美国通过打造蒂莫西·米切尔(Timothy Mitchell)在谈论石油产业时所提到的“技术层面”来控制文化产业,也就是“一套表面上看互不相关但实际上暗中协调的规定、一些精心计算过的安排、各种五花八门的基础设施以及为了控制对象和资源流动所设计的技术程序”。1Timothy Mitchell, Carbon Democracy: Political Power in the Age of Oil, London: Verso, 2011, p.40.被限制进入全球最大的市场是一回事,感觉你对某项具有全球价值的重大技术设施的控制权被某个国家削弱了,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因此,当创意产业那些过分乐观的经济师们正在欢迎一位新成员加入他们的“全球增长俱乐部”时,美国开始喊停了。2有关“全球增长俱乐部”,参见Stuart Cunningham and Terry Flew, A Research Agenda for the Creative Industries,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ers, 2019, pp.146-163.虽然有人会对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贸易战”中一些细节感到不安,但这些不安最终都会平息在美国两党已经达成的共识上:“中国一直在作弊,再也不能让它搭顺风车了。”中国开始同时扮演以下几个角色:一是“敌对帝国”的角色,该角色在20 世纪30 年代由德国和日本扮演过,后来又由苏联扮演过;二是需要被驯服的“经济对手”,就像《广场协议》签署前的日本和20世纪90 年代的欧盟;三是“敌对文明”的角色,譬如石油危机后的中东。作为一个信奉共产主义的地缘大国、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对手、一个截然不同的文明体,中国具有成为美国超级对手的所有条件。
1792 年,当随外交使团抵达中国之后,马戛尔尼伯爵(Earl Macartney)的副手乔治·斯汤顿爵士(Sir George Staunton)12 岁的儿子开始学习中文。勤奋的托马斯·斯汤顿(Thomas Staunton)作为非正式翻译人员,开始了他研究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漫长生涯,并于1823 年和他人一起创立了皇家亚洲学会(Royal Asiatic Society)。1840 年,在英国下议院那场关于是否要发动“鸦片战争”的著名论战中,托马斯·斯汤顿爵士强烈支持对中国开战,声称如果允许中国人焚烧广州仓库这样的侮辱行径存在,会对大英帝国的声誉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3Harry G.Gelber, Opium, Soldiers and Evangelicals:Britain’s 1840-42 War with China, and Its Aftermath,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95.他可以被看作有条件近距离了解中国的语言、文化和政治,但又对中国及其所代表的一切表达憎恨的西方学者或旅居者的第一人。中国具有的悠久文化,可能很少有外国人能够马上完全适应,但这并不会影响很多外国人对中国的好感与理解。然而,当他们的国家与中国的关系紧张之际,其中有些人会感到有必要站出来,说一些警告的话。目前西方国家反华言论的激烈程度——尤其在英语文化圈——达到了1989 年之后的最高水平,而那时中国的经济实力以及西方与中国的经济融合程度,远不及今天的水平。这些反华言论的主导修辞是“快醒来吧,中国的快速发展正在文化与意识形态上给全世界带来不可控制的影响”。在新自由主义的黄金时代,当“历史终结”以后,资本主义被认为是通往增长、进步和现代性的唯一道路,中国的快速发展只会让它在美国的“良性主导”下逐渐融入现代化的全球社会。现在,我们被催促着正视这一想法的天真,“我们被欺骗了,被搭了顺风车,现在我们必须超越对‘钱包’的关心,看到我们的基本价值观正在再次受到威胁这一事实。”这样做的目的和结果是,把大家紧紧封锁在“我们的”价值观之中,这些价值观与“他们的”有着根本的不同。
西方人早已学会了用满不在乎的口气谈论“政权更迭”。在代表着西方现代国家体系的威斯特伐利亚4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n System)是象征欧洲三十年战争(1618—1648)结束所签订的一系列和约,确立了“国家主权平等”等奠定现代欧洲国家体系的原则。——译者注核心地带以外,他们对类似事情一直是如此处理的。在“基本价值观”的范畴内,我们有一整套政治、经济、行政和技术安排,这些是不能被触及或是受质疑的,它们只能被出口,必要时可以动用武器。当下甚嚣尘上的所谓“认清中国”,就是要接受那些最愿意站出来坚决反对中国的政客,就是要把他们对西方价值观的传播当作不言而喻的真理。类似情况以前也发生过,而且发生过好几次了。
在这本书中,我们通过“创意产业”这一概念,勾勒出对“现代性”两种截然不同的叙事。这两种叙事,不断地互相交织和分离,有时和谐有时冲突,然而不知何故,如同复调音乐一般,它们最终抵达的是同一个“现代”目标:进步与增长。这两种与现代性有关的、至少从18 世纪中期以来就开始为人类带来生机与希望的叙事,今天正在走向终结。直到目前为止,西方和中国都还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一结局,也不知道这对他们各自来说,可能意味着什么。西方资本主义提供的是一个实践起来将产生最多问题的版本:它的帝国梦,现在集中于一种具有掠夺性质的全球化的新形式,其中没有任何有关多极化、多样性、多重性或互惠性的理想。正是对上述这些理想的追求,全世界开启了一个“后历史”的黄金时代。正如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所言,我们已经从全球化的“正向”发展阶段转向了“负向”发展阶段。1Bruno Latour, Down to Earth: Politics in the New Climatic Regim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8.眼下,仍然相信“进步与增长”的中国,正在猜想“现代性”能够以某种方式,克服它为自己制造的挑战。2019 年,根据刘慈欣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流浪地球》正式上映。在这部电影中,因太阳即将毁灭而对地球造成的生存威胁,被人类以推进引擎将地球移出运行轨道、驶向另一个星系而得以解决。停止地球自转所引发的海啸和地震,摧毁了地球上的一半人口,活下来的人也有很多无法被容纳进地下生存空间。电影中的中国工程师运用各种科技手段,拯救了地球和人类的未来。片中人物的态度是:为了保证人类物种的延续,拯救行动不受任何其他限制。目前,中国仍然将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城市化进程、大规模投资科技研发等,作为继续通往现代性的道路。这一“现代性”由中国共产党提供保障,也将进一步巩固它在这个国家的领导地位。
从全球来看,资本积累体系对文化领域展开毫无顾忌的吸纳,这一过程是从20 世纪90年代开始加速的。在世纪之交,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符号交换系统开始受到计算机“算法”的控制,导致一种“超加速”的积累过程,该过程只有通过对个人数据的大规模提取才能实现,而“监控”是这一过程的“暗物质”副产品。这样一个过程,对社会及其象征秩序、公共领域、言论的理想情境、理性对话的可能性等诸方面,都产生了负面影响,并且日益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上述这些领域,在西方和中国都处于一种重构的过程,但正如我们在本书中所指出的那样,这一过程是以不同的方式在进行的。在中国,代表着“象征秩序”的是“大他者”(The Big Other);2“大他者”(The Big Other)是拉康主义精神分析的核心概念。——译者注而西方则被各种不和谐的嘈杂声充斥,震耳欲聋。
数字平台及其所推动的“算法治理”存在着严重问题,即资本体系对个人价值的提取程度越来越高、侵入性越来越强。诚然,对那些关注“社会工厂”问题的人来说,他们所感到的是一种一直在进行的、不断从生活世界中提取价值以满足资本主义财富积累的不公。正如罗安卿(Anna Lowenhaupt Tsing)所指出的,资本主义总是能不断地从“前资本主义”、“非资本主义”以及“后资本主义”等各种社会形态中提取自己想要的价值。3Anna Lowenhaupt Tsing, The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On the Possibility of Life in Capitalist Ruin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然而,问题并不只在于不平等的“价值提取”,以及其中所可能存在的对生产者生活世界的扭曲与破坏。目前可以肯定的是,把文化系统逐步简化成“商品逻辑”,这一做法对“社会”自身具有极大的破坏性。这样的做法越来越阻碍了社会原本具有的、将“文化活动转变为知识”的能力。这就是伯纳德·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所说的“符号性贫困”(symbolic misery),1“符号性贫困”是法国哲学家伯纳德·斯蒂格勒在《论符号的贫困:超工业时代》中所提出的概念,指在超工业时代,大多数人的美学探索精神被市场营销学所营造的美学禁锢,失去了真实感知,以及与世界联接和表达自身的能力。——译者注他借此所要表达关注的是:我们人类作为有思想的存在,在表达自身对于意义的深层需求方面,正在表现出“集体无能”。在“商品化”和“算法”的控制下,逐步瓦解了的文化系统,导致他所说的“对知识本身的否定”。这是虚无主义的一种当代表现形式。
我们该如何克服这一困难,是一项紧迫的任务。我们不可能沿着陈独秀所说的“飞矢”2此处化用陈独秀语句:“人类文明之进化,新陈代谢,如水之逝,如矢之行。”出自1916 年1 月15 日《青年杂志》第1 卷第5 号《一九一六》。——译者注抵达未来——那是一条在想象中才有可能存在的、有关“进步”的“直线”。如果我们要避免在极端右翼学说影响下逐步蔓延开来的“黑暗启蒙”,及其所带来的倒退,那么我们对当下所谓“进步”的否定,就不能只是一次否定,还应该是对“启蒙”的一次彻底的重新评价。我们需要在“理性”被压缩为一个机械的、工具性的外壳以前,再一次向大家宣扬“理性”所具有的延展性与开放性。3关于“彻底启蒙主义”这一概念,参见Arran Gare,The Arts and the Radical Enlightenment: Gaining Liberty to Save the Planet, The Structurist, vol.47/48, 2007/8, pp.20-27.在18 世纪末的欧洲,艺术曾经有过一个特殊的“现代使命”,艺术具有表达和“消化”工业和民主现代性为人们所带来的深刻冲击的能力——这就是艺术的“世界相关性”。4也被翻译为“艺术与世界的恰当关系”。参见Sebastian Olma, Autonomy and Weltbezug: Towards an Aesthetic of Performative Defiance, Breda: Avans Hogeschool, 2016.对于艺术这一至今仍紧迫存在的历史任务,目前各国正在大力发展的以“消费”、“算法”与“产业数据”为核心的“创意产业”,不仅没有提出解决方案,而且日益成为人们在提出“艺术的历史使命”时所面临的重大阻碍。
一种经过重新思考的“现代性”,不会仅从欧洲和欧洲内部一个角度来进行论述。杜赞奇(Prasenjit Duara)认为,起源于公元前800 年—前200 年世界“轴心时代”的亚洲宗教与文化,为我们今天应对气候变化所需要的、具有全球视野的人道主义,提供了重要的道德理性。5Prasenjit Duara, The Crisis of Global Modernity: Asian Traditions and a Sustainable Fu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我们在本书中讨论了:中国的“儒家”传统以一种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的方式,构建了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其中有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加以利用的资源。我们对中国早期现代性中“非西方知识”的讨论,表明这些“非西方知识”曾试图为中国探索一条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后殖民主义、激进的女权主义和生态主义的思想与实践,都曾经对中国近代这些有关“现代性”的讨论进行了再审视,这些思想仍有可能为我们走出当前的困境提供有益的指导。也许更加具有争议性的是,我们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资源、它所经历的革命世纪,在中国社会发挥着重要的转化作用。无论中国未来发生什么样的改变,这一改变需要以中国自己的方式实现,而不必服从以美国意愿为中心的规则。
中国真正的变化不会发生在民众骚乱与地缘政治冲突相关联的地方。发生在大国边缘的这些冲突,很快就会被卷入互为对手的大国间的政治斗争之中。吉卜林在其小说《吉姆》(Kim)中详加阐释的“大博弈”理论6“大博弈”(The Great Game)特指19 世纪中叶—20 世纪初英俄帝国的中亚争霸战。这一说法因英国小说家吉卜林的作品《吉姆》而流传开来。——译者注自有其生命力,也许像“冠状病毒暴发”这样的挑战,正是对这一理论的最新回应。并不是像西方媒体所报道的那样,这次暴发“暴露”了中国政府缺乏透明度或者是它的“无能”,而是在突然安静下来的城市里,曾经由经济机器不停运转所造成的永不停歇的劳作,突然被按了“暂停键”,人们也许会因此而有时间来认真思考一下,究竟什么是“美好生活”?究竟什么是“美好生活”的真正基础?当然,人的生命与生存需要得到优先考虑,在这场疫情中,我们应当承认中国政府的能力——当它和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积极配合检疫隔离的普通群众一起行动起来之后。但在疫情中所暴露出来的社会问题,也值得中国政府和中国人省思:在向老百姓承诺了安全与繁荣之后,这个国家在政治、经济乃至社会生活领域,还有哪些需要加以改善的?
在艺术与文化的帮助下,通过特定形式实现的意义、知识与情感上的交流,必将是我们所需要的这种根本性变化的一部分。这也是“五四运动”在中国所开创的自由民主精神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所服务的中国人民的持续影响的一部分。在中国社会的日常空间,需要打开一个富有自我责任感的新空间,这或许是中国当下所需要的一种进步。这需要中国在追求“经济增长”之外,人们能以自己的方式、以文学与艺术的方式,提出和探索“何为美好生活”的问题。
像中共这样一个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过磨炼的共产党组织,没有理由做不到这一点。但它需要重新把自己正在推动的现实与作为行动依据的意识形态框架及根源联系起来。它所拥护的马克思主义在20 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遭受了重大挫折,中国此后试图在现代化的层面与西方加强沟通——“看看我们,我们也实现现代化了!”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是主政者与市场经济学家一起蹬“双人车”,他们共同探索能带来“进步与增长”的技术。在整个世界的发展前景越来越不确定的当下,中国可以敞开大门,积极探索并完善自身的发展道路,为全世界共同需要的巨大变革,带来更多可能性。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世界对这种变革的需求,正在变得日益紧迫起来。中国可以与东西方也在寻求这种变革可能性的人联合起来。如果它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它就真的可以宣称自己继承了“红色创意” 的衣钵。